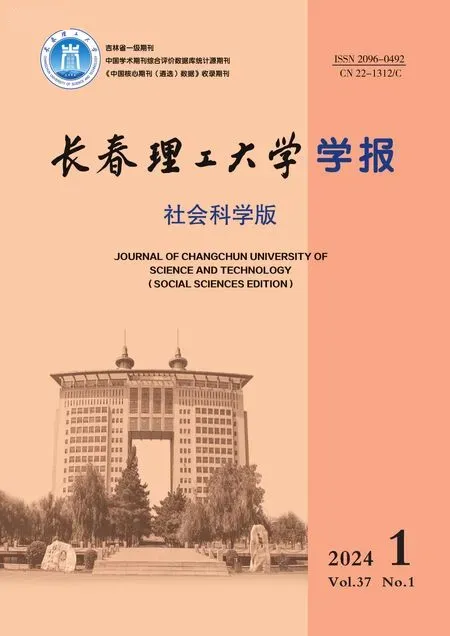文本视角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公正观研究
——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思考
2024-05-30徐梦琪汪盛玉
徐梦琪,汪盛玉
(1.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芜湖,241002;2.皖南医学院医学影像学院,安徽芜湖,241002)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地。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立足于理论和现实批判,充分考察“现实的个人”和“现实的运动”,详细描述了共产主义公正社会理想,较为系统地阐发了社会公正的基本思想内涵,为全面理解、概括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公正思想提供了基本向度和理论依据,也为当下中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理论指导。从文本视角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社会公正思想的研究路径,实现了理论与实践、批判与阐发、可能性与可行性相结合的完整架构,从而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公正观获得了由批判向重构的理论过渡、由理性思辨到历史实践的实践跨越、由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思维转变。
一、理论和现实双重批判的出场语境
实现社会公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理想追求。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公正问题的阐释路径是从充满批判性的现实场域入手的,其出场的理论语境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哲学家局限于“词句”的“运动”、脱离“现实的运动”的批判,现实语境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揭示与批判,这双重批判是马克思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公正观的重要语境,也成为理解其社会公正思想的逻辑起点。
(一)理论语境:“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
首先,揭示德国意识形态代表人物共同具有的意识形态的前提,是局限于黑格尔思想体系的一个方面加以反对,或者互相反对。体现在:一是将一切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结果只能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片面的说明;二是局限于用意识批判意识,“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非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既没有将问题指向德国哲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也没有指向批判本身与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因此,在他们“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的企图面前,这些哲学家的说明显得“微不足道”。
其次,揭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其一,费尔巴哈局限于“词句”的“运动”,把“解放”视为思想的活动,而不是历史活动,没有看到“解放”是由工业、商业、农业和交往状况促成的,“人”的“解放”只有在现实世界中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其二,费尔巴哈局限于用“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局限于仅凭单纯的直观和感觉去理解感性世界,并未看到其周围的感性世界是物质生产活动和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三,费尔巴哈在“人”的设定上局限于抽象的“人”,而非现实的历史的“人”,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局限于理想化的感情范围,因此,在应当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之处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
最后,揭示德国哲学在历史观上陷入的唯心主义。其一,批判德国哲学将历史超脱于现实生活和现实世界之上,因而基于历史的视角只能看到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以及“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把“想象”和“观念”变成决定实践的唯一性和决定性力量。其二,批判德国哲学在历史观上所具有的“纯粹民族的性质”,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用理论演绎代替现实生产,并指出这种“根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业绩是历史性的”观点带有民族偏见。其三,批判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费尔巴哈通过论证人与人的“互相需要”以期能够正确理解现存事实,然而,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在于推翻现存的事实;在人的本质问题上,费尔巴哈认为存在即本质,任何例外均属于偶然事件和反常现象,据此观点,无产者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当下的生活条件,这同圣麦克斯·施蒂纳对不满者的安抚之词和圣布鲁诺把恶劣关系归因于无产者自我意识的责难没有区别,而这与无产阶级的思想和革命实践是相悖的,对于共产主义者而言,“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二)现实语境: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的批判
首先,分工和私有制是产生社会不公现象的温床。其一,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阶段的差异,在前一阶段,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还完全没有分开,而在后一阶段,个人受劳动产品的支配,资本的统治使个人仅仅通过交换集合在一起,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催生出各种不平等现象。其二,分工和私有制导致城乡对立。城乡对立使得个人屈从于分工和生产活动,劳动成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致使人分化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和“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不断产生利益的对立。其三,分工和私有制促使阶级关系分化与对立,成为产生阶级剥削和压迫现象的温床,社会不公问题不断凸显和加剧。《形态》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导致社会普遍性不公正的经济制度根源,并对其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其次,工业化进程造成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占有和剥夺。其一,伴随工场手工业的出现,等级资本开始向商业资本过渡并积聚,为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提供了现实性和可能性,行会中的宗法关系被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而无论是这种关系还是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其二,作为思想的生产者,统治阶级同时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在精神上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控制与奴役。其三,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在消灭各国闭关自守的状态的同时,造成了生活境遇的空间差距,没有被卷入大工业的工人的生活境遇,比被卷入大工业中的工人更为糟糕,非工业性质的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的竞争中,资本和财富流向发达国家,加剧了对落后国家的剥削。
最后,利益的隔阂和对立产生支配个体的异己力量。其一,伴随分工的发展,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逐渐产生矛盾,共同利益以国家这种独立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凌驾于社会之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加强统治,往往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共同的利益,共同体对现实中的个人来说成为异己的强制力量。其二,个人被迫屈从于分工所限定的活动范围以获取生活资料,人自身的活动成为异己的强制性力量;在虚幻的共同体中,个人的自由仅局限于统治阶级范围内,而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则成为新的桎梏。其三,伴随个体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世界市场也逐渐成为支配个体的异己力量,“大量的劳力与资本隔绝或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被卷入竞争中的劳动者陷入绝境。
二、基于“现实的个人”和现实的物质生活的考察方法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公正的考察仍是在思辨哲学意义范围内进行,在研究方法上没有跳出黑格尔的框架,而在《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成为其社会公正观的新起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哲学的考察方法是“从天国降到人间”,即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这种意义上的“个人”是设想和想象出来的人,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方法则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其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有血有肉的个人本身,意识是个人现实生活过程的反射和升华。因此,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线索阐明了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将社会公正问题由抽象的思辨拉回到现实的物质生活。
(一)以“现实的个人”确立了社会公正的实现主体
首先,“现实的个人”是具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也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其一,个人是一种客观的肉体存在,具有普遍的生理特性,人所从事的任何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前提都由人的肉体组织的客观存在所决定的。其二,个人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个人身处的自然条件不仅决定着肉体组织的形成、造成种族差别,而且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体性发展态势。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研究和实现社会公正,首先要从生物学意义上对人的存在与发展给予肯定,肯定人是以自然存在为前提,而德国哲学把人的本质和形象抽象化,人的实践能动性既无从谈起,也无从发挥。
其次,“现实的个人”是具有物质生产实践能动性的个体。其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思想,而是在于生产自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其二,国家和社会结构是从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人以主体姿态出现在现实生活之中,并受到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制约。在个人的现实性上,虽然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感性的人”思想的影响,但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思想阶段,而是将“现实的个人”指向人的实践性、能动性,指向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这就赋予社会公正的实现主体鲜明的实践性和能动性。
最后,“现实的个人”是具体的、历史的个体。其一,“现实的个人”指向社会的具体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其二,“现实的个人”指向历史和实践相统一的人,人在物质生产中创造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消除社会不公,因此,历史是对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的描绘和记载,而非主体的想象活动,思辨哲学无法提供解决困难的前提,解决方案只能从对具体的历史的个人的现实活动过程的研究中产生。
(二)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确立了社会公正的实践方向
首先,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认为进行物质生产和交往的个人,在改变自身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所以“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在此前提下,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形式,这就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与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公正观划清了界限,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公正观的深化作出科学的铺垫。其二,德国哲学家们断言现实世界由观念世界支配,不同之处在于通过固定何种思想来统治和拯救“呻吟的人类”,而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真正的社会公正必须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没有物质生活的自由个体,更无法获得精神生活的自由。在此基础上,《形态》进一步揭示了经济领域的公正对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公正起决定作用,只有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实现个体在经济上的真正平等。
其次,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反作用。其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人所特有的生产方式,精神生产不仅涵盖了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还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这表明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重要内容,并且随着新需要的产生而发展,社会公正的内涵本身就是基于现存社会生活的一种学理性阐释,是“依社会条件不断改善而逐步实现的社会价值追求”[2]23。其二,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开始,产生了的真正分工,一方面精神生产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对物质生产发生作用。另一方面,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造成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发生矛盾,而实现社会公正的革命运动离不开共产主义实践和意识的共同作用。
最后,精神生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其一,精神生产具有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即便是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其思想也基本隶属于占据支配地位的阶级。此外,“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现代无产阶级无论从对社会不公的主观感受上,还是社会公正理念的培育与养成上,都为促进社会公正的真正实现提供了精神动力。其二,精神生产具有发展性,物质生产的发展推动着精神生产不断发展到新的阶段,使得精神产品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与此同时,世界历史性活动使得个体能够摆脱民族和地域的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精神生产发生联系,预示着人类文化整体时代的到来。在此背景下,人类对社会公正的认识正经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由此不断产生的精神食粮也为广大无产阶级提供了不竭的智力支持。
三、消灭社会不公和实现公正理想的叙事逻辑
尽管《形态》中并未就社会公正问题做出专门的阐述,但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唯物史观,通过各个向度的布展,形成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公正观的叙事逻辑,即阐述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不公的可能性,说明实现共产主义公正社会理想的可行性。
(一)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不公的可能性
首先,生产力的发展对消除社会不公具有决定意义。其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了基本前提,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私有制的消灭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没有发展和矛盾,便没有促使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没有消除社会不公的发展前景。其二,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超越地域性的普遍交往的建立为各民族无产者的联合建立了基础。“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其次,无产阶级的产生与壮大为消除社会不公准备阶级基础。其一,实行最广泛分工的大工业通过普遍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私有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无产阶级由此同整个旧世界相脱离,成为变革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力量。其二,因为无产阶级运动是“引导着所有的群众”消除不公生活境遇的革命力量,所以无论是同一个国家内大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还是因世界交往的普遍建立而被卷入普遍竞争中的非工业国家,都不能阻碍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与壮大。
(二)实现共产主义公正社会理想的可行性
首先,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主体力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公正观的价值旨归,在此意义上,《形态》对实现社会公正的主体力量进行了阐释。其一,《形态》中提出了“阶级的个人”“偶然的个人”和“有个性的个人”的概念,“阶级的个人”指向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屈从于物的力量的无产阶级,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身处其中,其个性和强加于他的生活条件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偶然的个人”指向资本主义社会中失去独立性和个性的无产者,而在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有个性的个人”是作为个人的联合而存在的,即个人能够把自身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置于控制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者要想成为“有个性的个人”,就应当消灭异化劳动,推翻国家。其二,在充分占有生产力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具有实现“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一致的必然性。这种占有一是受占有对象的制约,即“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二是受进行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能够实现充分的、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三是受实现方式的制约,这种占有唯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普遍联合和革命方能实现。
其次,阶级斗争是促进社会公正发展的基本动力。其一,《形态》中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使得人类社会按照五大社会形态依次更替,通过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不公现象进行批判,说明人类社会是由不公正向公正逐步发展的。其二,《形态》对阶级斗争的普遍性作出了阐释,将社会公正的实现路径指向现实的斗争实践。《形态》中指出,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统治阶级的,进行革命的阶级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统治阶级的,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建设新社会的斗争任务,“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无产阶级要实现联合,需要大工业城市和廉价便利的交通,然后通过带领广大群众进行长期的斗争,才能消灭旧的分工,使每个人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实现指向全体人民群众的社会公正。
从文本视角对《形态》进行解读可以看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公正观的形成是理论批判与实践总结相统一的过程,其社会公正思想在资本主义批判的出场语境中展开,通过实现主体和实践方向的考察维度,呈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公正观的内涵要义,从阐发消灭社会不公的可能性和实现社会公正理想的可行性,揭示出社会公正是共产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公正在共产主义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实现。《形态》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公正观思想形成中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折性作用,发掘其社会公正理论生成的文本根据,对于全面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