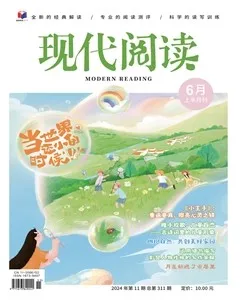巧妙的叙事时空,白描式人物刻画
2024-05-24冷江
特约名师:冷江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IMBA导师、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客座教授,曾获第29届“东丽杯”梁斌小说奖、第30届孙犁散文奖。作品散见于《小说月报》《北京文学》《安徽文学》《西部》等杂志。
导 语
鲁迅的小说和其杂文一样犀利,往往采用隐喻和暗讽的笔法以及对场景和人物精妙的白描技巧,赋予人物极其鲜明的形象。这些形象带着鲁迅式的印迹,往往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震撼。
孔乙己是鲁迅笔下仅次于阿Q、最成功的文学人物之一。虽然《孔乙己》这篇作品篇幅较短,仅2600多字,但其艺术魅力不亚于一部中短篇小说,甚至可以比肩长篇小说。
《孔乙己》之所以有长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场景和人物的时空穿插。
以场景穿插推进情节的写作技法,有人认为来源于马尔克斯等西方文学巨匠的著作,就像时下一些作家主张文学作品中的荒诞手法来源于卡夫卡的《变形记》。其实在中国文学经典著作中,比如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类似时空穿插的写作手法就已经非常熟练地得到运用。
对于时空贯穿的写作技法,鲁迅在《孔乙己》里运用得非常老到。全篇作品,从结构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写孔乙己断腿前,第二部分是写孔乙己断腿后。两相映照,对比强烈。作者先写场景,由景及人,层层推进。作品开篇将视角放在鲁镇酒店,而且一上来就点出这里与别处酒店的不同。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先声夺人,让读者急于了解这个不同点,从而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和阅读兴趣;二是为下文写主人公与别人的不同作铺垫。
作者“设计”了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注意,这个大柜台是作者特意为孔乙己量身定制的,以此突出孔乙己特殊的身份和特别的行为方式。在《孔乙己》里,作者从曲尺形大柜台写到“做工的人”“短衣帮”,再从“做工的人”和“短衣帮”写到孔乙己。这是先从个性化场景写到个性化群体,再由个性化群体写到个性化的核心人物。孔乙己穿长衫却只能站着喝酒,不能“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这体现了孔乙己的唯一性,也带给读者极大的冲突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孔乙己到底是属于站着喝酒的这拨短衣帮,还是应该属于那些坐着喝酒的长衫客?这是作品的“眼”,也是作者最想让读者思考的地方。反复阅读《孔乙己》会发现,这个“眼”是这篇小说最深刻的切口,远远比我们一味强调小说要追求起伏和转折来得高明。
小说中也体现了八面埋伏、逐步深入的螺旋式写作技巧。作品第一段描写了酒店场景,破开了一个作品的切口后,第二段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平铺直叙,而是转到“我”的主视角。“我”是鲁迅短篇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人物,在作品中承担着掩护、策应、串联以及冷静的观察者等多重角色。在《孔乙己》里,“我”还有着另一个任务,那就是对作品所在的时空背景和大环境进行烘托。写“我”的经历,并不会喧宾夺主,而是通过写“我”的感受来渲染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为核心人物的命运做情节上的铺垫。“我”的经历在场景和人物的时空穿插设置上,还是一条灵活的主线,为读者拉开距离感受人物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来看《孔乙己》的时空主线:首先介绍“我”在酒店的经历,这个交代是为了让“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孔乙己,进而感受特殊背景下核心人物的特殊行为,从而增强作品的真实性,也叫虚构的真实性,这是鲁迅短篇小说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接下来,通过时空穿插的方式,让孔乙己自己走出来。中秋在这里成了作者笔下一个有意的节点。曾经孔乙己还能穿长衫,“排出九文大钱”,可大约中秋前的两三天,孔乙己被打折了腿,中秋后只能盘着两腿,穿着破夹袄,“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自此,从年关到第二年端午,再到中秋、年关,“我”再也没有看见他。为什么要选中秋做时空节点?作者是有深意的。在中国人心中,中秋是全家团圆的时候,这样喜庆的节日氛围与孔乙己的悲惨遭遇形成鲜明对比,可以有效加深作品的悲剧性,增强艺术效果。结尾处,作者还特意加了一笔,“到现在”终于还是没有看见孔乙己,从而将孔乙己的命运凿实。
现实与过往穿插,配角与主角的命运穿插,特定意义的时间节点穿插,这几乎成了《孔乙己》中组合运用的场景型情节推进的基本方法。
其二,是对人物外在形象、内在心理,以及深度精神这三个层面的塑造。
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内外交融,层层叠进,这是《孔乙己》中塑造人物的另一个重要方法。
鲁迅在对人物外在形象进行描写时,往往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人物的特点。作者没有一上来就写人物的相貌,而是先写“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这种气氛的烘托,对人物出场起到了铺垫作用。
正式描写孔乙己的形貌时,作者这么写:“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一句话就让孔乙己的形象立住了。接着写人物的外在形象,“他身材很高大”,本应是魁梧的身材,最后却只能盘腿坐在地上,“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是在暗示孔乙己经常挨打且无钱医治,“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说明孔乙己虽然自认是读书人,却已沦落至无力顾及形象的窘境。对孔乙己样貌的描写,没有一句废话,每一句都有背后的意思,这是鲁迅写作的功力所在。
再看作者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为什么对短衣帮的穷苦人要这么说话?其实,行为背后是人物独特的心理活动,孔乙己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无意行为,而是人物内心刻意为之,目的就是要在短衣帮面前竭力维护自己的长衫身份。“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这两句经典的台词,则将孔乙己的悲剧特质无限放大,乃至深入到了精神层面。从外在形象到内在心理,再深入到精神思想层面,鲁迅用笔看似随性所致,实则精心谋划、步步为营。
在对看客的描写上,鲁迅也能通过三言两语直击人物的精神层面。我们看看诸多看客是如何戏耍孔乙己的:先是替他取了个很不友好的外号“孔乙己”,接着只要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这个“笑”带有嘲讽的意味,是拿别人的痛苦来取乐。鲁迅从不在作品里直接交代人物的精神和思想,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为,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这恰如国画淡墨山水中常有的意蕴技法和留白技法。
《孔乙己》里,作者对看客的刻画并非简单的罗列和堆砌,而是富有层次感,乃至一叠三叹,波澜起伏。孔乙己第一次出场,被取笑偷书吊着打,孔乙己“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孔乙己第二次出场,被旁人揶揄“当真认识字么”,否则何以半个秀才都没捞着,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于是“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孔乙己第三次出场,掌柜亲自挖苦,无情揭露他“又偷了东西了”,要么怎么会被打断腿,孔乙己最后一丝尊严丧失殆尽,用乞怜的眼神恳求掌柜不要再提,众人便都笑了,最后孔乙己只能在众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三次出场,孔乙己的遭遇一次比一次悲惨,众人的语言和行为虽然貌似都一样,但对读者来说,在精神思想层面的感受,却是一次比一次深刻,一次比一次震撼。最后,作者用“大约的确是死了”来结尾,让孔乙己无以复加的悲剧人生戛然而止,让封建制度和科举制度毒害下的落魄文人的悲哀上升到社会的悲哀。
可以说,场景的动态转换、人物形貌的白描与语言行为刻画,最终都是围绕着人物的命运来展开的。场景的背后是人物,人物形貌和语言行为的背后是人物的心理,人物心理的背后是精神与思想。
《孔乙己》的成功,不仅仅是写作技法的成功,更是技法背后人性刻画的成功、人性背后精神思想深化的成功。
(原文载于《现代中学生(初中版)》2022年第3期,作者有改动)
(同步链接:统编版语文九年级下册第二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