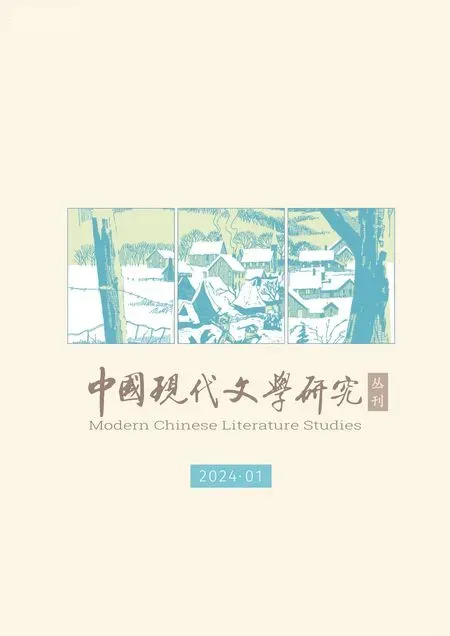“中国的病证”与“我活在人间”
——鲁迅1925年的“发热”与文学
2024-05-18李拉利
李拉利
内容提要:鲁迅文学在1925年通过由热而冷、从肉向灵这两个有关联的辩证法完成整体转向。一方面,近四个月的发热体验和医学知识背景催生了鲁迅式的冷热话语,使得1925年鲁迅的翻译和创作如同一剂凉药,针对的是个人与民族国家同构的热病。另一方面,鲁迅文学的主体从精神的虚空向下降落,成为“在人间”的精神界之战士。这样,鲁迅文学终于走出或“寂寞”或“无力”的困境,真正担负起撄心-立人-立国的文化使命。
1925年9月23日起,鲁迅经历了长达105天的头痛发热,由此带来的肉体病痛和生命危机感影响深远:其作品内外充满“热”“冷”表达,有热到发冷的杂文,有外冷而内热的散文诗,也有《走向十字街头》《艺术的表现》《从艺术到社会改造》等讨论天人苦乐、“灵与肉”交争的译文,透视“在人间”“两个世界”“象牙之塔”“文学与社会”等关系中的两极对峙。学界对鲁迅文学与疾病关系的研究不少,但大都瞩目于鲁迅小说中的疾病隐喻和身体叙事,对疾病体验与鲁迅文学的整体转向把握不够。1钱理群、程桂婷注意到鲁迅的发热与生命体验的问题,但前者所提的是鲁迅1923年、1936年两次大病;后者重点研究鲁迅1913年的发热数据及其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分别参看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程桂婷《疾病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研究——以鲁迅、孙犁、史铁生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还原鲁迅疾病体验和他的译作、创作的文本甚至是文字的关联,从“冷”“热”“补药”“泻药”视角来认识鲁迅生命体验和“精神界之战士”的人间具体性,可以更好地理解鲁迅文学在1925年“从肉向灵”的战略性调整,即“用唯物论尽向深奥处钻过去,则那地方一定有唯心论之光出现”1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从灵向肉与从肉向灵》,鲁迅译,《鲁迅译文全集》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5页。。
一 “中国的病证”
1925年9月23日,鲁迅日记“午后发热,至夜大盛”;此后一天,鲁迅在《〈望勿“纠正”〉附记》末尾落笔“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身热头痛之际,书”。身热头痛是症状,具体何病则未记,鲁迅按寒热失调或者消化不良导致的热毒病证处理,因为24日记“服规那丸”。规那丸即奎宁丸,鲁迅日记中也有记为鸡那丸的2鲁迅甲寅日记5月12日记“下午大发热,急归卧,并服鸡那丸两粒,夜半大汗,热稍解”。这里的鸡那丸即规那丸,有时也被记为金鸡那小丸。鲁迅乙卯、乙未日记有“八粒”“十粒”的记录,但只是“乞得”或“寄”而非服用。参见鲁迅1913年10月31日,1914年5月12日、9月30日,1915年1月26日,1919年8月7日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116、135、157~158、376页。,可解热,能“令泻”,与中医类凉药、泻药一类的专门治热病的药功能相类,是鲁迅家的常备药。鲁迅1913年10月、11月,1914年5月、10月,1918年10月中,都有服规那丸退热的记录。一次一两颗或三四颗不定,五颗是最大量的记录。周作人亦有服规那丸泻火的日记,如1917年5月8日记:“晴,上午往北大图书馆,下午二时返。自昨晚起稍觉不适,似发热,又为风吹少头疼,服规那丸四个。”同月11日:“阴,风。上午补服丸五个令泻,热仍未退。”3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669页。
“发热”在鲁迅日记中常见,9月23日这次发热持续时间很长,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影响很大,为方便言说,不妨称为“九二三热”。第二天24日,记服规那丸,未写量。29日鲁迅给许钦文写信,说“大约是疲劳与睡眠不足之故,现在吃药,大概就可以好罢”;30日又致许钦文,“病也好起来了”;实际上,“九二三热”不像往常,相当顽固,“好起来了”不过是鲁迅的乐观说法。10月的1、3、5、8、14、17、22、29日日记,都有“往山本医院诊”。11月8日致许钦文信:“我病已渐愈,或者可以说痊愈了罢,现已教书了。但仍吃药。医生禁喝酒,那倒没有什么;禁劳作,但还只得做一点;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11月“往山本医院诊”的日记有三次;12月“往山本医院诊”有四次。可以说,1925年9月23日到1926年初,鲁迅都是在大大小小反反复复的“热”的状态中写作的。巧合的是,这段时期的作品多和“热”、“病”、“夜”以及柔弱而顽强的“鲁迅”生命形象有关:11月3日的《弟兄》,有“猩红热”语;12月3日《〈出了象牙之塔〉后记》有“一帖凉药”语,落款是“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之夜,鲁迅”; 12月31日《〈华盖集〉题记》出现“沾水小蜂”“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等语。本年关于“九二三热”的最后一次的“往山本医院诊”是12月26日,鲁迅喟叹“病叶呵”的《腊叶》便是这日作的。到了1926年1月的3日、5日两次“往山本医院诊”后,“九二三热”才算是“好起来了”,持续了近四个月。在此期间,作于“夜”“深夜”中的文章是名副其实的“热风”。鲁迅在1925年最后一天夜里的《〈华盖集〉题记》中说,“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正如一个多月前《〈热风〉题记》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话,是如鱼饮水“冷”“热”自知。
热中鲁迅,深知“一帖凉药”的好处,对肉体,也对精神;对自己,也对中国。本年12月3日他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说:“著者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国。”12月18日写的《十四年的“读经”》中的“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和《〈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连用语措辞、标点符号、话语语气都一样。翻译和创作,外国与中国,因为热的“病证”一样,因此是可以服用他“移来”的这一帖凉药的。
“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倘不是洪福齐天,将来要得内务部的褒扬的,大抵总觉到一种肿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疮。未尝生过疮的,生而未尝割治的,大概都不会知道;否则,就明白一割的创痛,比未割的肿痛要快活得多。这就是所谓‘痛快’罢?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肿痛提醒,而后将这‘痛快’分给同病的人们。”1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270页。鲁迅早期的翻译是补药性质的,性“热”,如作为“文术新宗”的《域外小说集》,为补中国朝气不足之症,所谓“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说钼》《月界旅行》等也是,意在“拿来”“古源”所无、中国所需的新营养,作国民精神的补气养元之用。但是在1925年“九二三热”前后,鲁迅的翻译就成了类似规那丸一样的凉药、泻药,以泻火败热为主,有警示病证、分享治愈的痛快之效,如《出了象牙之塔》和《壁下译丛》中诸文。巧合的是,鲁迅此时所作杂文也多是凉性的清热药:11月18日《十四年的“读经”》,所清之热是:“读经”“尊孔,崇儒,专经,复古”“以孝治天下”“以忠诏天下”“以贞节励天下”;11月22日《并非闲话(三)》,所清之热是“纯洁的”“动机”;《坚壁清野主义》所清的热,是“几样主义”“正本清源”“澄清天下”“中国的妇女”的“解放的路”;11月23日《寡妇主义》的热,是“速成师范”“贤妻良母主义”“神道设教”“儒行”;12月8日《这个与那个(一)》的热,是“钦定四库全书”;12月18日《“公理”的把戏》的热,是“公理”“道义”“名流”“正人君子”;12月22日《碎话》的热,是“领袖”“正人君子”“思想”“公论”;12月28日《这回是“多数”的把戏》的热,是“多数”“通品”;12月29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热则是“费厄泼赖”。
鲁迅的翻译服务于他以文学改造社会的意图,从提供思想、文化、主义、理论等补品,变为先泻热毒后补营养,这是鲁迅的一个转变。热毒不去,补品反而有毒,“自问苟侥幸卒业,或不至为杀人之医”2鲁迅1904年10月8日致蒋抑卮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这一对意在救人反而成杀人医生的悲剧的自觉,导致鲁迅从留日时期的思想建设和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转向后五四时期的“杂文自觉”3张旭东:《希望与躁动:鲁迅杂文发生学小史(上)》,《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8期。。“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4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270页。立人立国,不破不立,在破旧中立新,此论由鲁迅1909年的《破恶声论》始,贯穿至1925年全面落实,尤其是“九二三热”后。以热文为凉药,先败火后滋补、凉热并用的意图,互文于鲁迅这个时候的著译文章。
热,不但是鲁迅的生命与魔障斗争的症状1“生命力旺盛的人,遇着或一‘问题’。问题者,就是横在生命的跃进的路上的魔障。生命力和这魔障相冲突,因而发生的热就是‘思想’。”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十三、思想生活》,鲁迅译,《鲁迅译文全集》第2卷,第325页。厨川白村氏的“魔障”,确切说是鲁迅用的“魔障”一词,和鲁迅用的“华盖运”一词,都源自佛教,表示磨炼生命的困厄,在鲁迅《生命的路》中又被称作“铁蒺藜”,而铁蒺藜也出自《地藏经》,是地狱中物。从这些名词可知,鲁迅对待生命的态度是积极的、勇猛的,颇有佛教中烦恼即菩提之智。这一点上,鲁迅和颇解佛教的尼采也有共鸣。在《快乐的知识》中,尼采说:“到自己的天堂之路,常是经过自己的地狱的欲界的。”尼采:《快乐的知识》,梵澄(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95页。,也是他的人生选择。在给许钦文的信里,鲁迅提到安特莱夫的四幕戏剧《往星中》的时候说:“我以为人们大抵住于这两个相反的世界(《往星中》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天文学家向往的广大神秘的、冷而平和的自然世界;一个是其子所关注的‘热,然而满有着苦痛和悲惨的人间世’)中,各以自己为是,但从我听来,觉得天文学家的声音虽然远大,却有些空虚的。”2鲁迅1925年9月30日致许钦文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517页。天文学家的冷或者是真的,合科学的,但鲁迅选择热而苦的人间世。鲁迅并非不求真,只不过求的是具体的以人为主体的真。对他来说,真理如果没有主体,即便完美无缺,那也是假而无趣的,正如天上大如车轮的花朵。3鲁迅:《厦门通信(二)》,《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2页。他宁愿在有瑕疵甚至大缺陷的主体中寻求真理,这样的真理不完美但真实、能“撄人心”。我们知道,早期鲁迅追求真理的态度是极端的“惟向所信是诣”(《破恶声论》)。这种不计后果的追求和鲁迅所谓“反抗绝望”的反抗,其实是一回事,共同统一于一个“诣”字。诣者,追求真理之行动、“指归在动作”之“动作”也。不同的是,《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时代的鲁迅,追求的是《往星中》的父亲式真理,以为真理存在于与人无关的冰冷的自然世界,行者鲁迅“指归在动作”,不在人——无论体格健全与否。此时期的鲁迅,冷静、冷漠,“并非迫切而不能已于言”。但“九二三热”前后,鲁迅的“动作”变成了不问成败的战斗4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页。,鲁迅作于此时期的《过客》,冷静但不冷漠,遵从自心的呼唤也感激小女孩的好意,因而具有冷热过渡的色彩,可看作对诣字的新解。鲁迅此时的求真,从《往星中》冷漠的父转为热烈的子,坚持真理的人间具体性,行者鲁迅转为反抗绝望者鲁迅,决绝的冷漠中,亦有对“国民”——无论精神愚弱与否——的同情。在6月18日的《忽然想到(十一)》中,鲁迅说,“我也另捐了极少的几个钱,可是本意并不在以此救国,倒是为了看见那些老实的学生们热心奔走得可感,不好意思给他们碰钉子”。这些人,这些事,在鲁迅笔下充满“人间至爱者”的温度:“几个小学生”“几张小纸片”“幼稚的宣传文”“弱小的腕”“带体温的银元”。这是他“人间世”立场的自然显现,此前“听将令”,作《呐喊》,译域外小说,此后扶持青年作文章,编刊物,出丛书,作《我要骗人》,参加政治社团,其“引以为荣”的“同志”,都是这样的弱者甚至愚者,是《往星中》“两个相反的世界”中的“热,然而满有着苦痛和悲惨的人间世”。
这个“人间世”首先是中国。1925年11月3日,在《〈热风〉题记》中,鲁迅提问“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中国的病证”在鲁迅文学中首次出现。弃医从文的鲁迅,惯于以病为对象,以文学为诊断、为药救:1902年和许寿裳讨论“理想人性”“病根何在”1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8页。,1919年《〈呐喊〉自序》提出救治精神疾病的“第一要著”,1925年4月8日致信许广平,要做“攻打病根的工作”2鲁迅:《两地书·十》,《鲁迅全集》第11卷,第41页。,12月3日《〈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说“同病的人们”。无论是病还是药,都是精神性质的,这都是我们已知的。但“中国的病证”,是他在“九二三热”的疾病体验中提出的,此前此后,他在译著和创作中大量书写“物质”“精神”“肉”“灵”“天国”“地狱”等“两个相反的世界”。从个人的病联想到“中国的病证”,对鲁迅来说不是新鲜事,但从冷色调的精神文本到冷热调和文本的转向,不仅是文学方法的变化,也是鲁迅整体文学观的战略调整,值得注意。
鲁迅的选择源于他的“生命之火”3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十二、生命力》,鲁迅译,《鲁迅译文全集》第2卷,第323页。,这导致他处处遇冷的华盖运。其实,并不是鲁迅的周围格外冷,以至于他非得“所遇常抗”不可,实在是作为热源“生命之火”的他,除非遇到同样是热源“生命之火”的一二“知己”,所遇常冷似乎是他这个心系家国兴衰的热心人的宿命。1比如同是百草园,鲁迅的“乐园”和周作人的“鸡零狗碎”园正好相反,见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7页。鲁迅文学源于鲁迅的“生命之火”,能点燃火种,却不能点燃“沙石”。鲁迅在《出了象牙之塔·艺术的表现》和《两地书原信·十五》中都说过类似的话。“因为施行刺激,总须有若干人有感动才有应验,就是所谓须是木材,始能以一颗小火燃烧,倘是沙石,就无法可想,投下火柴去,反而无聊。”2《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周围火种少而沙石多,导致鲁迅所遇常冷。和他热人冷命相契合的是,鲁迅的热在文字上往往出之以冷,冰冷。说冷热话,作冰火文,“于狂歌浩热之际中寒”,形成鲁迅特有的极热与极冷合为一体的奇诡文风。
1925年11月3日,在作《弟兄》的同一天,鲁迅作《〈热风〉题记》,说“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如前所述,鲁迅是冷空气中的热源,是灼人的“生命之火”。所以,站在鲁迅一方,无论他说的是冷嘲,是热讽,都是他“生命之火”的热的产物,名副其实的“热”之讽。何况从9月23日到写《〈热风〉题记》的时候,他已经“热”了整两个月了。他一再给朋友说热的原因是“睡觉少”,而他的“夜”并不属于“睡觉”,他一再在夜里写作。《〈热风〉题记》后依然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第二天日记,“晴。上午往中大讲。往山本医院诊”。
这种冷热体验,是鲁迅好用反语的一个内因。周作人在《鲁迅的杂文》中说,鲁迅长于以字句上的冷毒写其用心的火热,“发掘病源……掘到根柢里,所谓诛心之论,本心乃是为的要中国人好,这在一般的人是不大能够了解的,因为他的热忱与愤激,使得他的话不但显得尖锐,而且有时似乎刻毒”3岂明(周作人):《鲁迅的杂文》,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4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鲁迅文学,声每出以默,热每出以冷,意每出以反。正如鲁迅所谓“含笑的泪”。“大的笑的阴影里,有着大的悲。不是大哭的人,也不能大笑。”“笑里有泪”,“见了漫画风的作品,而仅以一笑了之者,是全不懂得真的艺术的人们罢”。1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艺术史上的漫画》,鲁迅译,《鲁迅译文全集》第2卷,第381页。
反语不仅是艺术,也是盔甲,以冷说热,如以冰包火,对旅行于无处不在、无所不染的沙石语境中的鲁迅文本形成一层话语保护。鲁迅在翻译《出了象牙之塔》时没有翻译其中的《文学者和政治家》,但鲁迅同意其中的观点,即文学者和为政者因为关注对象的相同,都是“民众的深邃严肃的内底生活的活动”,因此不可避免地有一种关联:“文学者总该踏在实生活的地盘上,为政者总该深解文艺,和文学者接近。”2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66、266页。鲁迅认可而不翻译的理由,明显是担心自己的文章被语境染指利用。他以为当时中国的政治与文学的接近“常有”,但却不是《文学者和政治家》所说的为了民众,而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双方的接触是在“黑暗的阴影中开演”,是鲁迅所提及的圣武与圣野猪3长谷川如是闲:《圣野猪》,鲁迅译,《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的合作,而不是为民众的。因此“因为自己的偏颇的憎恶之故,便不再来译添了”4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66、266页。。可见,1925年的鲁迅,不会超然地“为艺术而艺术”,也不会冷冷地“不顾利害的讲论是非”,而是要从“中国的病证”角度,看“疗效”。也就是说,他的翻译和他的创作一样,都是他的“一剂凉药”,而不是“纯”文学“纯”思想。他不会在政治与文学互相勾结的时候再“译添”一个文艺的论据给他们利用,尽管这个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两年后在他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得以呈现。值得一提的是,作于1927年底的这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没有被鲁迅收入《而已集》《三闲集》,而是在六年后被杨霁云收于《集外集》中,孤零零地列在“一九二七年”名下。这种说而不编的做法,再次证明鲁迅对这个正确但是无关当时“中国的病证”话题的消极态度。种种以序跋方式提一下而实际不翻译、不创作、不收编的话语方式,是对话语对象如“文学与政治”,如“自由”5鲁迅在1928年3月31日作《〈思想·山水·人物〉题记》中说:“那一篇《说自由主义》,也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对自由,自由主义,鲁迅不是不提倡,而是采取务实的态度,觉得这个和当时中国现实太远了。见鲁迅:《〈思想·山水·人物〉题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300页。的话语保护——不直说,不正面说,但是要话语留白。他爱而不说或者反着说,进而保护所说不被染指的话题,还有如费厄泼赖、宽恕等。
“九二三热”中的鲁迅,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意在做一帖凉药,泻掉诸如“民气”“五分热”“断指”“我们一向很好的”“中国书”“读经”“公理”“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等热毒,这些热毒之和即所谓“中国的病证”。热的病根不去,补药成毒,所谓“第一著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者,以此。
“大约是疲劳与睡眠不足之故,现在吃药,大概就可以好罢”的鲁迅,热中伏案,偏多冰语,“夜”“深夜”“深夜将尽”,这样不计后果的工作,颇有些“超越尘埃,解脱人事”“不和众嚣,独具我见”的“精神界之战士”风采。然而,精神战斗的同时,是种种身体/物质困境:“发热”“睡眠不足”“头昏眼花”“性命的斤两”“老态可掬”“口腹计”“衰老”“寿终”。在灵与肉的辩证关系上,重新思考我是谁,文学是什么的终极问题,在“九二三热”前后,成为鲁迅文学的一大特点。
1925年,日记中鲁迅的“生命之火”炽热燃烧着:作文、谈话、上课、写书帐、编辑、翻译、写信。他几乎一直在做那“攻打病根的工作”,因此一直处在“热”的状态。全年中只有一天例外——6月21日,鲁迅当日日记了七个字:晴。星期休息。无事。
二 “我活在人间”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鲁迅一生的思想和精神,那么我认为最恰当的或许是七个字:对人的终极关怀。”1严家炎:《史余漫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3页。
对终极究竟的问题,早在1919年,鲁迅就说过他的态度:“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2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1935年,他借木刻问题也说过“终极”之不可求、不必求的观点:“(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这问题之不能答复,和不能答复‘人的最后目的和价值’一样。”“但我想:人是进化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1鲁迅1935年6月29日致唐英伟信,《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页。作于1925年的《墓碣文》中,鲁迅追问“心之本味”,也在其终极究竟思考的延长线上,结果也是一个“不能答复”。
鲁迅“心之本味”和鲁迅“生命的泥”无法分开,或者说,是先有“生命的泥”才有“本味”而非相反。《墓碣文》与其说是鲁迅要寻求“本味”,不如说是要解构“本味”,是对凌空蹈虚,美妙而不真实的一切“好的故事”的告别:“漂渺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着,红颜的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这自然使人神往的罢,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我活在人间”,这是“九二三热”愈后三个月,鲁迅在1926年4月10日写的《一觉》中的话。这里的“人间”,和1925年1月1日“感得全人间”(《诗歌之敌》)、1925年4月22日“物质的头”(《春末闲谈》)、1925年9月30日“满有着苦痛和悲惨的人间世”(《致许钦文》)、1925年12月30日“不单是住在象牙之塔里”(《〈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一道,共同彰显着鲁迅文学“用唯物论尽向深奥处钻过去”的“人间”转向。这个时候,鲁迅几年前“第一要著”中的“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的冷酷已经被代之以“我活在人间”的热情,“并非迫切而不能已于言”而不被邀请即不做文章的“要我写”状态,逐渐变为“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么”2鲁迅1934年1月17日致萧三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11页。的“我要写”。只不过,经过“九二三热”的疾病体验后,鲁迅本人“精神的头”和“物质的头”合二为一,“我要写”的文学将大大异于“要我写”的文学。鲁迅文学从单向度的精神文本向“在人间”的文学转向之势,已经成为必然。
鲁迅作文的“第一要著”,出自他1922年的《〈呐喊〉自序》。鲁迅留日时期和五四时期的文学,作为“第一要著”的实践,具有很强的精神文本性质,这对具体的、“体格健全”而“精神愚弱”的“国民”来说,不啻为一种正确而冰冷的文学观。鲁迅对这种文学及其带来的“文学家”荣誉是不满足的,因为他不满意其“寂寞”和“无力”的命运,1李拉利:《“从文”还是“造文”——以鲁迅1920年代的“路”与“走”书写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这可证之以《〈呐喊〉自序》中大量的犹豫、转折词汇。五四以后,鲁迅文学逐渐进入“第二过渡期”2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第二过渡期”的说法、时限、意义有不同解释,参看汪卫东《杂文的自觉:自我与时代的双重发现》,《理论学刊》2011年第11期;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期;牟利锋《〈自由谈〉时期鲁迅杂文文体意识的自觉》,《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4期;钱理群《鲁迅杂文》,《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和之前的文学相比,鲁迅此时期文学的最大变化,是拒绝“一切都要从灵向肉,度着幽魂生活”3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70~271、267页。。鲁迅文学中个人生活史的内容越来越多,无论是虚构性的“五种创作”还是非虚构性的杂文,甚至是他的翻译和学术文,都成为“鲁迅”这个人的生命与生活的特殊话语。
鲁迅是谁,怎么写,对这种人与文的终极问题,鲁迅曾经热衷于思想和文学的方案,即所谓精神界之战士:“如果说早期提倡科学,还带有洋务派的烙印,参加革命活动是受了革命派影响,思考‘国民性’是受到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冲击,那么,当他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不和众嚣,独具我见’的精神界之战士身上时,他终于找到了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当时流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分道扬镳了。”4张全之:《从施蒂纳到阿尔志跋绥夫:论无政府主义对鲁迅思想与创作的影响》,《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1期。但是随着对“中国的病证”认识的深入,尤其是“九二三热”的体验,鲁迅从“精神界之战士”逐渐回归人间。因此,和思想家政治家分道扬镳不过是鲁迅的第一次转向,“九二三热”以后,鲁迅酝酿着和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家”分道扬镳的、可称为杂文自觉的第二次转向。
1925年底,在众多“人间”著译文字之后,鲁迅翻译厨川白村文艺论文集《〈走向十字街头〉序》,出现“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这样的话,可以说这是鲁迅思考“我是谁”的一个症候。此文中关于文学家兼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对应着鲁迅的相关思考:“在我所亲近的英文学中,无论是雪莱,裴伦……都是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评家;不单是住在象牙之塔里的。”5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70~271、267页。文学介入社会,文学家兼社会活动家,这是“热中”的鲁迅对1925年的总结,也是对以后道路和自我身份的新定位。无独有偶,鲁迅此时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第九篇,即研究英国作家兼社会活动家摩理思(W.Morris,1834-1896)的《从艺术到社会改造》,有对摩理思以文学家的身份进行社会活动的一段评论,几乎可以拿来作为鲁迅上述文字的论据:
他的前半生,摩理思是纯然的艺术至上主义的人,又是一种的梦想家,罗曼主义者。但在别一面,也是活动的人,努力的人,所以对于现实生活的执着,也很强烈。一面注全力于诗歌和装饰美术的制作,那眼睛却已经不离周围的社会了。1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从艺术到社会改造》,鲁迅译,《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文学与社会,文学家与社会活动家高度重合,正如译文开头的“引文”所说,“艺术家、诗人、工匠摩里思就是社会主义者摩理思;换言之,社会主义者摩理思就是艺术家、诗人和工匠摩理思”2文章开头的引文原文是英文,笔者翻译的是其中一部分:“Morris the artist, the poet, the craftsman, was Morris the Socialist, and that conversed, Morris the Socialist was Morris the artist, the poet, the craftsman.”转引自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从艺术到社会改造》,鲁迅译,《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495页。。
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摩罗诗力说》中呼吁“精神界之战士”,学界也一直将之视作“文学者”鲁迅的身份定位。但是,1925年“九二三热”后,鲁迅对“人间”“物质”的重视,对文学家兼社会活动家身份的一再提及,使精神界战士逐渐从天上降落,降落,直落到中国的土地上,成为“在人间”的“精神界之战士”。在此时,鲁迅翻译了六篇、创作了十五篇与“战士”相关的文章,这个降落过程,就反映在鲁迅这些文章里。3这些文章是《战士和苍蝇》《致许广平250323》《致许广平250331》《致许广平250408》《致赵其文250408》《灯下漫笔》《杂感》《导师》《杂忆》《新时代与文艺》《答KS君》《通信(复霉江)》《小说的浏览和选择》《孤独者》《伤逝》《思索的惰性》《从胡须说到牙齿》《自然主义的理论及技巧》《从艺术到社会改造(威廉摩理思的研究)》《从浅草来》《这样的战士》。这些文章,在用词、意见和态度上形成互文关系,是鲁迅对“我”——在人间的精神界之战士形象的辩证思考,之后的系列杂文集和《故事新编》也不断重复、丰满着这些形象。这些文章都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阐述战士和战斗的主题:一个是战士的物质性匮乏,另一个是战斗的精神性坚守,二者形成一种奇诡的反比例关系。细读这些文章可知,以“九二三热”为界,鲁迅对“战士”的精神属性有过一个追问、动摇和修改的过程,总体走向是从冷到热,从超然到介入。鲁迅“对人的终极关怀”,也以从肉向灵的方式实现。
首先,战士战斗的精神属性并没有改变——战士是什么,取决于对手,鲁迅依旧紧扣“中国的病证”的精神性,以对手的“无物”来定义自身的精神性。如1925年6月11日和13日,鲁迅三天内两次提到“巧人”:“白用了许多牺牲,而反为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巧人,鲁迅又称之为“阴柔人物”“聪明人”“伶俐人”,虽然有陈西滢、章士钊等具体人物作为“典型”,但鲁迅实际上指的是善于“舞文弄法”“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思想行为。以此为对象的战斗,只能是精神性的。为了保证战斗的精神属性,鲁迅不惜拒绝一切人间感情的牵挂,甚至冷酷地拒绝感激与好意。他1925年4月11日给赵其文的信中,对此有直白说明:
凡有富于感激的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
感激,那不待言,无论从那一方面说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譬如,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着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
又如,我们通了几回信,你就记得我了,但将来我们假如分属于相反的两个战团里开火接战的时候呢?你如果早已忘却,这战事就自由的多,倘你还记着,则当非开炮不可之际,也许因为我在火线里面,忽而有点踌躇,于是就会失败。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1鲁迅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477页。
这里,鲁迅顺带解释了一下《过客》中过客对小女孩的善意的拒绝,值得注意。这是因为,这种情感上的不近人情也出现在鲁迅此前此后创作的《故事新编》诸人物那里,如女娲之超然、后羿之沉着、黑色人之冷酷、大禹之沉默、墨子之坚毅独行。正如过客不能不在乎小女孩的“好意”,“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超然的同时具备了人间属性。女娲等人物也不再是超然的“精神界之战士”,而是全面继承发展了鲁迅此时所重视的人间具体性:从事精神界事业的同时,处处遭受人间世的“华盖运”,不是被谴责有伤风化,就是陷于“疲惫”“乌鸦炸酱面”“鼻塞”“起诉”等现实牵绊中,确实有“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的风险。
致赵其文信后,鲁迅仍持续思考这个问题,于5月5日的《杂感》中提出“无泪的人”的概念。无泪,源自鲁迅1903年在日本时期《浙江潮》上“无涕可挥,大风灭烛”的记忆。无泪的人,如《铸剑》中的黑色人,毫无父母、妻子等家人的牵绊1鲁迅说他本不要子嗣,“以绝后顾之忧”,一者烦累,一者株连危险。鲁迅1931年3月6日、4月15日致李秉中信,《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261页。,不会于决绝与眷恋中踌躇。
但也有因为情感羁绊而消解战斗意志的“反面教材”。1924年,王鲁彦创作小说《灯》,讲述的就是母子家人间眷恋与决绝的故事,和鲁迅作于此时期的《过客》《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这样的战士》有相似的情感主题,也和鲁迅《铸剑》的酝酿、写作和发表同步。鲁迅十年后将之收入自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灯》中的儿子以手剖心,还给母亲,自己的心和母亲的心合二为一,热血沸腾。儿子说:“母亲,我不再灰心了,我愿意做‘人’了。”2王鲁彦:《柚子》,北新书局1927年版, 第40~41页。这篇小说,形象地诠释了鲁迅所谓“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3又如1932年致台静农信:“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以致头白。”分别见《杂感》、鲁迅1932年6月5日致台静农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51页;第12卷,第308页。,也可以诠释他失去母亲的孩子做事“更勇猛”、更“无牵挂”的愤慨言说。其中的“我愿意做‘人’了”,模仿《狂人日记》“愈赴某地候补”,也类似鲁迅“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都可看作“战士”为“人间”所累、放弃“不问成败的战斗”行为。
其次,战士的精神属性一定呈现为“我活在人间”的形态。“精神界之战士”在此时不再“超越尘埃,解脱人事”(《文化偏至论》),而是要“民气”和“民力”兼顾,“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1鲁迅:《忽然想到(十)》,《鲁迅全集》第3卷,第94页。,这是“精神界之战士”的人间具体性。“九二三热”后,鲁迅生命和“魔障”搏斗的热,造成的痛苦与悲惨,是鲁迅的,也是有同样生存体验和抗争的中国人的。因此,鲁迅在热中体验的痛苦与悲惨,就不再因为它的少数个体性而“病死多少不必以为不幸”了。相反,从“中国的病证”中取材“热,然而满有着苦痛和悲惨的人间世”,反而可以辩证地生出“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2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54页。及其“唯心之光”来。从此以后,鲁迅在从留日时期的文言论文向着五四大众转向、获得“文学家”称号以后,再一次向着大众中的“个”转向:关注身边琐事,从肉向灵,以小见大,在最宽广的精神和物质细节层面上触及了“中国的病证”。从此,以鲁迅“生命之火”凝聚的鲁迅文学,真正成了疗救“中国的病证”的“一剂凉药”。
“鲁迅之为鲁迅的伟大处,只是在于他在历史与价值的心理冲突与煎熬中,终于没有落入乌托邦而最终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并且在对历史的执着中,同时没有舍弃对人的终极意义的关怀。所以他的文章既充满着历史感,又不乏人情味,他在二者中把握住了必要的张力。”3王乾坤:《由中间寻找无限——鲁迅的文化价值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这个张力的两端,一端“终极意义”,一端个人史,一冷一热,在1925年“九二三热”后逐渐汇合。从此,鲁迅的“精神界之战士”才得以“活在人间”,成为普罗大众中“无涕可挥,大风灭烛”式的豪杰;鲁迅文学不再是超然的“冷而平和”的精神文本,也不是热而琐碎的个人感觉,而是个人与群体、历史与当下、“心灵和上苍”4孙郁:《鲁迅的暗功夫》,《文艺争鸣》2015年第5期。相交流的中介,切实担负起其撄心-立人-立国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