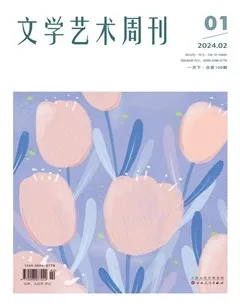马克斯·弗里施小说的自然书写研究
2024-05-17侯沛沛
文学作品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通 过分析文学作品不仅可以揭示其所反映出来的 生态思想的文化根源,也可以探索文学的生态 审美及其艺术表现。马克斯·弗里施是著名的 瑞士德语剧作家,他以独到、敏锐的目光,揭 示了工业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一系列严重 问题,体现出了强烈的生态意识。马克斯·弗 里施在小说《能干的法贝尔》中讲述了技术 员法贝尔笃信技术至上从而造成了人生剧变; 在《施蒂勒》中,马克斯·弗里施描写了雕刻 家施蒂勒不断地寻找自我的过程;在《人类出 现于全新世》中作者描写了年迈的盖泽尔对抗 一次突如其来的山洪的经历。这些作品无一例 外地反映了现代社会蕴含的自然危机及精神危 机。从法贝尔到施蒂勒再到盖泽尔,“自然” 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从被边缘化、沉默化发展 为生活化、可视化。本文将着眼于这三部作 品,分析主人公与自然对抗的反应及其共性, 阐述自然的功能,最终分析出作者的写作意图。
一、自然:远离理性的世界观
马克斯·弗里施小说中主人公的世界观和自我形象认知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主人公 从封闭的世界中观察到的自己来定义自我形象。 法贝尔不断压制他内在、无法控制的自然性, 通过拒绝和抵抗来表现自己,他用“我是技术 员”这句话定义了自己;施蒂勒则一直声称“我 不是施蒂勒”。两个主人公都从不同的角度声 明他们不能或不想做自己,两人都试图用一个 不代表自己的术语来概括他们的身份。个人身 份作为内在自然,如同外在自然,它们都是不 可计算的,而其不断地受到主人公的否认和抗 争,便构成了其身份危机的原因之一。然而, 法贝尔和施蒂勒都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身份不 仅仅是基于他们的决定和选择,也会受到自然 和社会的限制。完全脱离自然的生活是不可能 的,主人公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做出了相同的反 应,那就是都想逃到能够“计算”和“安全” 的世界中。法贝尔总是想刮胡子,而且每次出 汗时都想冲个澡,可以理解为这种反应的一种 表现。这一点在法贝尔在丛林中度过的那段时 间体现得尤为明显,他整天泡澡喝酒,谈到出 汗时说: “我从早到晚淋浴,我讨厌流汗,因 为这让人感到自己像是病人一样。”只要供电 他就刮胡子,因为他感到,如果不刮胡子,他 将变得有点像一株植物,这种行为显然是为了压制和“洗刷”其自然的特征。他的行程不间 断,科技的发展使得他今天在巴黎,明天位于 加拉加斯,实际上科技已经成功地“通过速度 稀释了世界,让我们不必去体验它”,他的这 种不休息可以说是一种拒绝在世界上“居住” 的直接表达。法贝尔的世界观中,空调设备可 以抵御高温,避雷针可以抵御雷暴,飞机甚至 可以在大雪中起飞,自然已在各个维度失去其 神秘性。自然现象具有的唯一合法功能是无处 不在的背景,有时候甚至退化成一种随时可用 的消费品、 一个漂亮的配饰。
而在《人类出现于全新世》中,盖泽尔更 是保持了与自然的距离,书名中“全新世”是 一种“气候”概念,作者将《人类出现于全新 世》这一错误概念作为书名,正是为了突出主 人公衰老和退化的状态。盖泽尔是一名空调专 家,可以说是一种与自然“对抗”的职业。他 爱看的书是罗伯特·容克的《比一千個太阳还 亮》,这部作品讲述的是科学家们如何完成原 子弹的制造,这与盖泽尔信奉的技术至上不谋 而合。盖泽尔和法贝尔都理性至上,这也体现 在他们的阅读文本选择上。法贝尔说, “我不 喜欢小说,有如不喜欢梦幻一样”;盖泽先生 也声称,“长篇小说在这些日子里根本不适合 阅读”。两人都坚持“现实”的文学,因为它 们代表了“新的实践精神”,而非虚构文本比 虚构的故事更适合这种精神。施蒂勒和法贝尔 一样,对他的出汗感到厌恶,并公开承认他不 喜欢自然。三位主人公都代表了开明、文明和 理性的人类:一方面,他们受到流行文化的影 响,被困在自己的时代;另一方面,他们又积 极回避任何对自然的真实体验,不断地去对抗 自然。
二、自然:死亡与性的对抗与压制
尽管主人公启动了所有防御机制,他们在自然中遇到的那些试图逃避理性的事物也是不 容忽视的。其中一个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 是施蒂勒对丛林生活的描述: “这地方好似天 堂,就在热带地区附近。那闷热的气候我真受 不了,还有那硕大的蝴蝶,黏糊糊的空气,潮 湿的太阳,连这里的气氛也是黏糊糊的,这一 切充满了杀气。”在施蒂勒的描述中,创造力 与消逝、生存与死亡都存在在自然中,通过自 然的不可预测性和随意性,向人们展示了掌控 自然、压制本能、逃避或否认死亡这些个人的 企图是徒劳的, 因为正如施蒂勒所承认的那样, 死亡是无法否认的。
人类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死亡,甚 至推迟死亡,在朱莉卡诊所停留期间,法贝尔 在他对人工流产主题的解释中证实了这一点, 但法贝尔最终却没有阻止伊丽莎白的死亡。因 为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无法逃脱死亡。认识 到这一事实,法贝尔提出了想被火化的愿望。 因为此时,法贝尔意识到他也终会死去,他的 身体也将会腐烂。尽管如此,他还是想至少避 免他的身体成为一种“灾祸”,因为土葬后“土 壤在一阵暴风雨后就是泥浆, 满是病菌的腐土, 真是可怕”。而被火化的愿望意味着法贝尔不 想成为自然新陈代谢的一部分,他寻求没有新 生的终极死亡。最终这种逃避也没有得到救赎, 正如法贝尔在丛林中修理发动机时被雨水所吞 噬一样,自然最终会占上风,他将无法逃脱死 亡的命运, 因此将必须成为自然循环的一部分。
盖泽尔墙上的笔记字条也出现了类似的情 况,这些字条在一股风穿堂之后,散落一地, 从而“毫无意义”。他从古籍词典中剪辑摘抄 文字及图表贴在墙壁上,通过这些分类和名称 来理解自然的恐怖,来对抗记忆的衰老。他想 以人类智慧作为对抗自然的工具的企图最终是 徒劳的。
因此,主人公用各自的方式极力对抗死 亡,他们想去逃避或者否认死亡是自然的归宿,是个体生命的必由之路。他们压制自己的本能 欲望, 自然成为他们身体和灵魂的威胁,可以 说,“自然”既压制他们的自然性,也阻断了 他们的社会性。
三、自然之功能:转折与“影射”
法贝尔要么相信技术,要么相信自己所 认为的,当他意识到没有人最终可以逃脱自然 的掌控时,他之前的世界观崩溃了,他不得不 承认“我不了解自己”。在与自然的斗争中, 那些以技术人员的身份去生活以及通过使用自 己的智慧来掌握世界的信念变得毫无用处,法 贝尔在转变后认识到这一点并承认: “我的 错误: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想方设法没有死亡地 活着。”他对技术的坚定信念动摇了,因为在 生活的引领下,他最终意识到,即使在技术时 代,个人的存在仍然是不可预测和不可计算 的。因此“自然”成为法贝尔的人生转折点。
盖泽尔对自然的处理纯粹是科学的,他有 时候问自己“我到底想了解哪类知识, 自己学 了知识又指望得到什么”。他对科学的态度也 只停留在表面。他试图逃离自然去巴塞尔也失 败了,这次失败的逃离也意味着他与自然之间 的联系是无法切断的。盖泽尔最后认识到,通 过分类和使用科学术语来消除对自然的恐惧是 无用的。他意识到, “自然不需要名字,巖石 并不需要他的记忆”。
而施蒂勒主要是逃离自己的内在本性。施 蒂勒虚构他在墨西哥时的生活时,描述的是一 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这种描述是一种 潜意识的社会批评,因为施蒂勒在墨西哥观察 到的生活在瑞士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他只能 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有留在那里呢”。施蒂勒 错过了接受自我的机会,尽管他觉得通过深入 接触自然会发生某些变化。施蒂勒在不断地否 定自己的身份,他沉迷自己的想象,以至于他
可以写下: “我坐在牢房里,目光向着墙壁, 望着墨西哥……”对他来说,想象力已经扮演 了“可见的现实”的角色,他也没有得到任何 真实的体验,他的生活仍然是与自己的斗争。
在主人公接受自然之前,他们都逃到理智 的客观世界中。法贝尔把自己塑造成一名技术 人员,他认为情绪是柔弱而神秘的。盖泽尔过 着完全孤僻的生活,并试图避免同其他人的接 触。施蒂勒以自我为中心,他试图去否认他的 内在本性,编造了假身份和一系列的故事来极 力否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主人公对自然的控制 建立在对自然的疏远之上,只有当他们能够承 认自己就像自然一样不可预测时,他们才能学 会接受自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自然打乱 了依赖科技的文明秩序体系,自然成为他们人 生的转折点。
四、结语
法贝尔、施蒂勒和盖泽尔都体验到他们生 活在一个与自然疏远的世界中,但都有过无法 完全逃避自然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 成为三位主人公之前人生观的试验台,也是他 们内心冲突的起点和试金石。虽然每个主人公 对待自然的方式有所不同,但自然在每个案例 中都通过相同的属性向主人公展示了自己的不 可抗拒、不可计算及不可掌控。
在当下,生态文学家开始关注文学中的自 然问题,马克斯·弗里施也不例外。他以“自 然”为书写工具,对人类纯功利性、纯工具化 对待自然的方式进行强烈谴责,号召人类去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对文 学与社会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 作者简介 ] 侯沛沛,女,汉族,陕西渭南人, 西安翻译学院亚欧语言文化学院讲师,硕士, 研究方向为德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