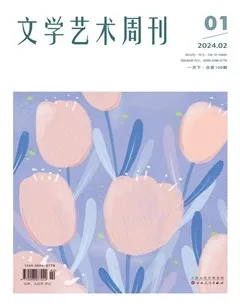徐霞客云南行的生态文学书写研究
2024-05-17李益
文学与生态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是亦有 联系。比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就是中 国先民们在长期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寻找的一 种平衡。在现代中国,生态文学经《寂静的春 天》《瓦尔登湖》等书的译介和出版,逐渐成 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关于“生态 文学”的定义,中国生态文学奠基者王诺先生 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 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 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 源的文学”。生态文学,亦是一种生态批评文 学,总体是文学的一部分,在今天也体现在感 悟自然、展现人与自然关系、探究生态危机等 多个方面。
生态文学虽是新兴的学科,但是它又贯 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在徐霞客游记中, 生态与自然随处可见。徐霞客笔下,云南确为 “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物种多样性凸 显。同时,和谐的多民族文化融为一体,自然 生态与人文交相辉映。徐霞客在云南的江源探 索和生动记录,既为后世考究明代云南多样的 地理风光及民族文化提供了依据,也对今天云 南的原生态旅游及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徐霞客与生态文学之渊源
徐霞客用游记来写生态,左手青山,右手
绿水,而在青山绿水之间展现出他对人生、社 会、生态的哲思,使得整部游记不失为一部生 态文学作品。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金银曾 说: “翻读《游记》,犹如参阅生态样本。一 部游记,遍地生花;满篇文字,到处生绿 …… 尊重天人关系, 追求文化意蕴, 崇尚自然法则, 遵从客观规律,成为徐霞客一生的遵循。”徐 霞客以游记的方式记录所见所闻,虽然无意书 写生态,却句句不离生态,甚至还从环境污染 角度指出山川皆是己之身体,爱护山川犹如爱 己之身。
关于选题的研究, 目前学者们集中在徐霞 客对喀斯特地貌、山水湖泊、滇中花木林草等 的记录, “溯江纪源”的重要发现及其生态思 想的研究上。胡晓文、陈海娴的《试析〈徐霞 客游记〉中的生态意识》,以徐霞客《滇游日 记》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 生态意识以及现实意义。张晋光的《徐霞客的 生态观考论》从理性的自然观、务实的地名观 以及伦理的山水观三个方面论述徐霞客的生态 哲学。张永双、曾爱民的《〈徐霞客游记·滇 游日记〉有关云南林木记载及其植物文化研究》 则从明代云南森林生态、《滇游日记》中云南 花草林木的记载和明代云南的植物文化三个方 面入手,探究徐霞客笔下的云南植物及其文化 意蕴。以上文献虽或宏观或微观地对徐霞客生 态思想、游记中的山水以及植物文化等进行探析,但是对其生态文学方面的研究较少。2021 年,野象迁徙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更为 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从江南水乡辗转来到云 南的旅人徐霞客,也成了云南学者们关注的焦 点之一。2021 年 6 月,陈庆江教授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指出徐霞客晚年所到的云南具有优越 的生态环境以及丰富的生物物种,“生物多样 性特征凸显”。另外,陈庆江教授也指出明嘉 靖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曾发生大规模极寒天气, 但是《徐霞客游记》中当时的云南动植物分布 却和今天基本一致,其中緣由和规律值得深入 研究。
总而言之, 《徐霞客游记》是展现明代 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重要载体,是一部优秀 的生态文学作品。徐霞客笔下的云南,堪称动 植物王国,其间山水林湖田交相辉映,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反观中原,连年战乱不断、盗匪 横行,人畜杂居,疫病此起彼伏,森林环境破 坏严重,不仅使得徐霞客寻求江源之路异常 艰辛,也让徐霞客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愈加强 烈,甚至直接在游记中指出并深切呼吁。
二、徐霞客云南行与生态文学书写
徐霞客怀着“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 的理想出发,终其一生都在为“江源”考究而 不懈努力。他人生的最后一站便是云南,为此 他开始了这一次艰险而又坚毅的“万里遐征”。 在他的笔下,云南自然生态美不胜收,人文生 态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静谧而又充满温情, 令他大为赞叹。
(一)云南多样的自然生态
徐霞客将云南自然生态、人文景观、民族 风情等各方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使得他的 游记成为云南历史上一笔珍贵的财富。在徐霞
客笔下,植物、动物、山水交相辉映,呈现出 生物多样性特征;云南各地整体上一片祥和, 依山傍水的民居、良田、美食、矿藏等,使得 人文与自然俨然一体。
1. 云南植物的多样性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海拔较高,气候总 体温和,只是“愈北而寒”。正是由于这种独 特的气候条件, 云南孕育出了丰富多样的植物, 是名副其实的“植物王国”。
初入云南,徐霞客便被云南独特的植物所 吸引, “觉树影溪声,俱有灵幻之气”,他一 边前行一边深情记录,偶或为采些植物样本铤 而走险。在他的笔下,云南植物种类繁多,有 名可知的植物多达七十余种,其中给予较多笔 墨的植物有山茶、山鹃、花红、黄菊、西番菊、 牡丹、兰花、梅花、桂花、攀枝花(木棉花) 稻、麦、黍、燕麦、蒿麦、柳、竹、桃、梨、 菩提树、优昙树、龙女树、仆树以及云南的古 茶树等。这些植物中,既有农作物,也有观赏 花卉以及经济林木,徐霞客对它们的描写较为 生动有趣。
茶花,是云南较为独特的花类,被徐霞客 誉为滇中奇花之一。《滇中花木记》中说:“山 茶花大逾碗,攒合成球,有分心、卷边、软枝 者为第一。”到了丽江,徐霞客受到土司木增 的礼遇,他曾在木氏别院观赏过被称为“南中 之冠”的茶花,言“其本径尺者三四株丛起, 四旁萎蕤下覆甚密”,以至于不能“中窥”, 而且此时茶花并未完全开放, “花少叶盛,未 见灿烂之妙”,他想着若是到了月终或许能成 “火树霞林”,但是又想着“此间地寒”,估 计花会迟一些盛放吧!
在云南,由于松柳繁多,这类植物不仅成 了云南人民的庭院装饰物,还被赋予了独特的 文化内涵。“柳”谐音“留”,因此被当作送 别礼物,中原就有“折柳送别”一说。徐霞客 曾记载,东坞五里之处, “有柳径抱,耸立田间,为土人折柳送别之所”;通安州治所东南 处“有柳两三株,在路右塍间,是为土人送行 之地”。可见,云南人民以柳送别与中原同 出一脉。松树四季常青,既是顽强生命力的象 征,还是云南人民的亲密伙伴。松毛可作引火 之物,也是农人借以改良土质的重要媒介,更 是云南地区“重礼”必不可少的物品。宏辩长 老曾为徐霞客“设盒果注茶为玩”,在他精心 布置的饮茶场所里,“楼下采青松毛铺藉为茵 席”,借以表示他对徐霞客的敬重。木增为招 待请来的客人徐霞客,不仅搭棚设宴,还“下 设松毛以示重礼”。在今天,纳西族依旧保留 这一传统,在重大庆典之时,人们都会用青松 毛来盛放果品或者以松枝作为祭祀物品。除此 之外,松子可食用,松明可作燃料等,也被徐 霞客一一展现出来,这些足可见云南人民对于 松的喜爱与利用。
关于云南的竹,徐霞客对其用途记录甚 详。“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在中原竹 文化的影响之下,云南亦是“丛竹娟娟”。庭 院植竹,自成“幽寂窈窕”之景,更有“竹林 清隐”之韵味。除了装点庭院,云南人民还利 用竹子建造房屋,制作竹床、竹户、竹笆,以 供日常家用,真正做到了与自然融为一体。在 吃的食物里面,竹笋也是云南美食中必不可少 的一类,可清炒,可煮汤,而“煨笋煮肉”是 较为美味的吃法。然而鲜笋的时节总是太短, 所以人们多采用“熏干瓶贮”的方法来保存, 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日常饮食。
在倾情描绘云南植物多样性的同时,徐 霞客还用科学的眼光对自我不甚理解的植物 进行考究。在大理蝴蝶泉,他描写了泉边大树 的奇景, “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须翅栩 然,与生蝶无异”,于是吸引千万真蝶“连须 钩足”“缤纷络绎”,形成“五色焕然”的盛 景。除了对植物外形特征详细记录外,徐霞客 还经常采用试吃的方法辨明其味,或者采摘植
物制作样本以便随时观察。在芭蕉洞,徐霞客 摘洞口的黑果来尝,尝过之后与之前在街子上 买来的黄果进行对比,他指出黑果是“真覆盆 子”,描述它的性状说“其色红,熟则黑而可 食”,又接着补充说: “黄者非覆盆。覆盆补 肾。变白为黑,则为此果无疑。”在登山时, 他见崖壁垂藤上长了一个如瓠匏一样的“瘿”, “心识其异,欲取之”,但是地势险峻很难取 得,后来还是在导僧的建议下回到住所,取了 斧头和梯子才得以“升木取瘿”。可见,徐霞 客对于植物的观察,是极为考究和深入的。
徐霞客笔下的云南,植物种类繁多,多样 性特征凸显。观赏花卉争奇斗艳,特色农作物 异彩纷呈, 经济林木瑰丽多彩, 以及众多的“古 木丛柯”汇聚一方,共同构成了云南多姿多彩 的“植物王国”景观。
2. 云南动物的多样性
在《滇游日记》中,徐霞客生动记录了云 南的动物种类, 有家养的猪、牛、羊、狗、鸡、 鹅、兔子、牦牛等,也有野生动物如鹦鹉、豺 狼、蛇、蜜蜂、鱼、蟾蜍、野鸽、老虎、螳螂、 猢狲、象、鹤、飞鸟(燕子)、蝴蝶、骆驼、 猿鼯、鹰、鹿、孔雀等,种类之丰,可见“动 物王国”所言非虚。
云南街子文化兴盛,徐霞客记载过兔街 子、羊街子、狗街子、牛街子、鼠街子以及马 街、猪矢河哨等地名,由此可推测这些地名多 与该地出产的动物有关。在描写云南动物多样 性之时,徐霞客大多是以美食观察者的角度来 叙述的。他指出,云南的鸡与中原不同, “生 鸡大如鹅”,而且“色黄而体圆,盖肥之极 也”。在洱源,他记载: “每年八月十五,有 小鱼出其中,大亦如指,而周身俱油,为此中 第一味。”在丽江, 木增以八十大肴来迎接他, 肴中“罗列甚遥,不能辨其孰为异味也”,据 学者推测,这八十大肴品类丰富,包括水产、 植物和动物, 总之是丽江物产丰富的生动体现。木氏土司日常所赠,有柔猪、牦牛舌等菜肴及 不同的果品,都让徐霞客大为赞叹。
除了种类之丰,徐霞客还指出云南特有 的动物(与中原不同)在南北两地存在差异。 “盖鹤庆以北多牦牛,顺宁以南多象,南北各 有一异兽”,明代的动物分界也和今天如出一 辙,牦牛耐寒,而象喜热,这一分布特点正好 验证了明代云南气候的多样性以及南热北寒的 特征。徐霞客還记载,云南当地的牦牛“多尾 大而有力”,可驮重物,因此不仅可作食物、 耕作伙伴,也可成为税赋的替代品,北地无田 耕种的人们便蓄养牦牛,“纳牦牛为税”,以 减轻经济负担。
3. 云南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徐霞客笔下的云南,山水林田湖草相得 益彰,共同构成了云南独特的生态景观。关于 云南的山水,徐霞客多次提及云南的高山及海 子, “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因此才 造就了云南多样的山水文化。西山、点苍(今 苍山)、鸡足山、高黎贡山、玉龙雪山、象鼻 山等 山名,盘江(今滇池)、抚仙湖、茈碧 湖、 明湖(今 阳宗海)、洱海等水、湖泊之 名,足见云南山水之复杂多样。同样是山, 徐霞客不遗余力地用“重崿绝巘”“群山丛 突”“巨石嶙峋”“石骨铮铮”“危峰”等修 饰语来描写,甚至将不同的山景作以区分,指 出云南石头之奇,有石萼、石乳、石梁、石 骨、石磴、石岫、石突、石濑等不同类型。同 样是水,徐霞客也以不同的心情观水, “自沙 涧至此,诸水俱清澈可爱”“滇中之瀑,当以 此为第一,惜悬之九天,蔽之九渊,千百年莫 之一睹”……在丽江,徐霞客看到古城中的民 居群落“依山就势,错落有致”,而依山的同 时,人们还选择了临水而居, “府治东向临溪 而峙,象鼻之水环其前”“中有水南下,万字 桥水西北来会之”“象鼻之水夹其东,中海之 流经其西”,东、中、西三条河流穿城而过,使得古城与自然相得益彰,融为一体。
此外,云南田畴遍野,“新谷、新花,一 时并出,而晚稻香风,盈川被隆”,虽部分地 区因盗匪、兵乱以及疾病等原因较为贫穷,但 云南总体上物产丰盈, “民安地静”,人民生 活相对安康。独特的林区如高黎贡山、苍山、 玉龙雪山等造就了云南独特的高原植物,适宜 的气候环境让云南古茶树生长良好。古茶树的 保护与开发,不仅为当地茶业发展提供了较好 的云茶品种,也推动了云南茶马古道的兴盛与 繁荣。
郑力乔教授说: “生态文学最大一个特点 是对自然景观的文学描摹再现, 并赋予它神性, 使它成为人类精神的象征和蕴藉。”徐霞客的 《滇游日记》,不仅展现了云南自然景观的多 样性,还将自然与人文紧密结合,正符合生态 文学展现自然与人之关系的特点。
(二)云南先进的自然生态观
云南是多民族聚居区,徐霞客也在《滇游 日记》中记载了这一文化现象。在云南, 彝族、 纳西族、汉族、回族等各民族聚居、交流,使 得当地在文化方面也呈现多样性特征。
自古以来,人们深知“人算不如天算”, 徐霞客也记载了自己行至云南时所遇到的豺 狼负羊、猛虎啮参戎马等事件。人虽能改造自 然、利用自然,但是宇宙之无穷也会使得人类 有很多难题不能解决, 如“旱灾”“出豆”等。 在《徐霞客游记》中就曾记载,当土地干旱之 时,人们便采用“移街”的习俗来解决;在 “出豆”疫病盛行之时, 当地人“极畏出豆”, 还在长期实践中慢慢掌握了“出豆”的规律: “每十一年逢寅,出豆一番,互相传染,死者 相继。”因为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人们只能采 取“避豆”隔离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明史· 云南土司传》载: “云南诸土 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
20 文学艺术周刊
在木氏土司的精心治理之下,当地“只分官民 二姓,官姓木,民姓和”,人民安定富足,纯 朴可亲。而在长期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木氏 土司逐渐探索出自己的生态发展理念,如土地 轮耕制。“其地田亩,三年种禾一番。本年种 禾,次年即种豆菜之类,第三年则停而不种。 又次年,乃复种禾”,这是徐霞客记载的丽江 地区种植方法,采用了典型的轮作之法,有利 于促进土壤的修复,体现了丽江人民固有的生 态理念。时至今日, “人与自然是兄弟”依旧 是纳西族人民心中坚守着的生态理念。
“土人浣于塘而汲于井”,这是徐霞客记 录的明代云南人民对生活功能分区的设计。井 水饮用,水塘洗衣,人们借助地下水和水塘的 自净特点,拥有了干净且稳定的用水来源。在 今天的云南,尤其是丽江地区,不仅户户门前 流活水,还有一种结合山水特点在城内建造的 “三眼井”——上塘饮用、中塘洗菜、下池漂 衣,以方便人们使用。这种循环利用的生态理 念,體现了古城建造者的别具匠心。
今天,人们的生态保护观念日益加强,但 是人与自然之间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人们还需 要不断探寻新路径,构建好“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而《徐霞客游记》便是一部较好地反 思生态危机与根源的作品。徐霞客曾描绘他所 看到的云南村庄: “良畴数千亩,村庐交错, 鸡犬桑麻,俱有灵气。”在他看来,明末云南 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人居环境优美,自然美 景让人流连忘返。当明末的兵乱、盗匪、人畜 杂居、猛兽伤人、滥砍滥伐、污染环境等现象 横生,且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之时, 云南却依旧保持着原生态的发展模式,依山建 屋,逐水而居, 以茅、树皮、瓦片等覆盖屋 顶,以竹、木等作屋梁、门窗。此外,人们充 分挖掘当地的特色产品,如牦牛肉、鸡葼、树 蛾、孩儿参、孩儿茶以及香草等以满足所需。 除了与中原相同的渔、樵、耕、读,人们还开发了畜牧业、采矿业及加工制造业等,在取之 自然的同时,他们崇尚“祭天”之礼,借助神 明、神物以约束民众,还以轮作、禁渔等方法 切实保护自然。
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在其《人类发 展生态学》中提出“人类发展生态理论”,指 出“个体的发展会受到其所联系的生态环境的 影响”。据此, 朱家雄教授进一步阐释说:“人 的发展是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不可分割的,特 别是与文化不可分割。”在徐霞客笔下,云南 土司将自我与云南的发展相结合,因地制宜, 无为而治,促使云南拥有了独特的文化底蕴。
三、徐霞客云南生态文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 义
徐霞客云南之行的记录,不仅丰富了云南 地区的文献史料,还推动了长江源起的进一步 探索,对今天云南生态保护以及旅游文学的发 展很有启示意义。
(一)生物多样性的珍贵记录
在徐霞客的笔下,云南的山水林湖田草相 得益彰, “湖多、樹多、花多、景多,生物多 样性特征凸显”(陈庆江教授语) ,犹如一个 生命共同体。徐霞客晚年从家乡出发,用脚步 丈量祖国山河, 最后来到动植物王国——云南, 他以妙笔写就的《滇游日记》,既展现了云南 不同于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更记录下了云南 地区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成为明末云南生物 多样性的珍贵记录,也为有着“动植物王国” 之称的七彩云南增添了历史依据,这些对今天 云南地区的生态保护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溯江纪源”的重要发现
徐霞客在云南遍览山河湖泊,欣赏滇中奇 花异木,更与很多云南土司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徐霞客在大理鸡足山逗留许久之后,便受邀前 往丽江,受到了土司木增的盛情款待。在木增 的帮助下,徐霞客得以接近长江正源——金沙 江。长久以来, “岷山导江”的说法无人质 疑,而徐霞客根据史料记载发现其中谬误“何 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岂河之大倍于江乎? ”在 丽江,徐霞客考察了大大小小的水系,甚至提 出过要去中甸考察,以求更近距离地探寻长江 之源,然而土司因考虑到徐霞客的安全,以 “中甸皆古宗,路多盗,不可行”为由拒绝。 徐霞客虽最终未能目睹金沙江的全貌,但在向 导的引领下登上玉龙雪山,大致窥见金沙江的 流向。通过长达三年的跋涉,徐霞客写下了 《溯江纪源》, 指出“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 为首”,而且究其根源,或许远在昆仑山脉, “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 南”。这使长江之源的发掘更进一步,也为其 后学者对“三江源”的探索提供了思路,为中 国地理、旅游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溯江纪源 虽止步于丽江,但是徐霞客与云南之间的渊源 远未停止, 《徐霞客游记》因此也成为今天窥 见明末云南发展的重要史料。
(三)云南生态文学的发展
在今天,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乎百姓生 活,也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 计”。“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2021 年 10 月在云南昆明召开的世界生物多样性大会, 是中国与东西方各国携起手来,“共同构建地 球生命共同体”的有力见证。
近些年来,自然环境的变化、生态超载的 出现制约着人类发展的步伐。在面临生态危机 和困境之时,生态文学应运而生。云南也积极 响应,该地的生态文学以独特的旅游文学作为 支撑,生动地展现了云南的多样性景观。如纪 录片《霞客滇游记》《徐霞客在丽江》, 影视 剧《木府风云》《去有风的地方》等,研究著作如洛克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小说如 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诗歌如 雷平阳的《两头大象从我身旁经过》《怒江》、 黎阳的《丽江千古情》,散文如汪曾祺的《昆 明的雨》、阿来的《一滴水经过丽江》等,分 别以不同的视角介绍了明代、民国以及现代云 南的别样风情。“生态兴则文明兴”,而云南 因旅游而发展,因文化而兴盛,也促使当代生 态文学不断发展。
四、结语
《徐霞客游记》是一部生动的生态文学作 品。一生志在山水的徐霞客,在云南观彩云、 赏名花、品名茶, 游走于山水之间, 适时惬意, 偶或艰险,但只觉“身与灏灵同游”,而自己 便以友人的身份与山水奇景对话,或借助山间 温泉缓解脚痛之疾,深情记录着所见所闻所感 的一切,因此为云南留下了较为珍贵的历史资 料。他的《滇游日记》展现了云南生物多样性 特征,也佐证了云南“山水林田湖草”的和谐 相映。此外,徐霞客还记录了明末云南的生态 实践——轮作、禁渔等,进而指出人在取之自 然的同时还要保护生态, 他认为自己的身体“乃 山川之身”,因此人能够“与山魈野魅夜话”, 故而应该像保护自身一样保护生态,禁止乱砍 滥伐。徐霞客将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既是对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生动诠释,也对 今天云南生态的保护和修复具有一定的影响。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 目“徐霞客云南行的生态文学书写研究”研究 成果,项目编号: 2022J1222。
[ 作者简介 ] 李益,女,汉族,陕西商洛人,丽 江文化旅游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元明 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