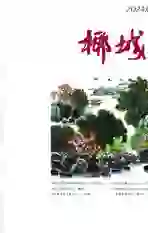失去的记忆与归来的遗忘(评论)
2024-05-09远人
作者简介:远人,197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诗歌、小说、评论、散文等千余件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化》《随笔》《天涯》《山花》《文艺报》《创世纪》等海内外百余家报刊。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评论集、诗集、近体词集、传记等个人著作30余部。曾获湖南省十大文艺图书奖、广东省第二届有为文学奖·金奖、深圳市十大佳著奖等数十种奖项,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日文、匈牙利文译介海外,在多家媒体开有专栏。现居深圳。
沈月沉这个短篇读来令人无端感慨。
就小说本身而言,它有一个开始,但似乎难说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这也是现代小说的显著特征。它不提供传统小说的模式。据说自后现代以来,人的生活就碎片化,小说也理所当然地碎片化。
沈月沉的小说就是一篇不折不扣的碎片化小说。
小说劈头一句“你认识虞诗诗吗?”这一奇峰突起的开头令人觉得,小说的女主角应该会是虞诗诗。但读到小说的最后一个句号,虞诗诗也没有出场。倒是“我”提出问题的对象冯月澄贯穿小说的五分之四,但冯月澄也难说是小说的女主角。简单来说,这是篇没有女主角的小说,那么男主角是“我”吗?同样难说。在“我”身上,并没有体现出小说该有的主角特性——即被所有的情节围绕。
如果“我”和冯月澄不是小说的男女主角,那么主角是谁?作者想塑造怎样的形象?
读完小说就能发现,小说的唯一主角是记忆,同时也是遗忘。
“我”的记忆是从与冯月澄的约会开始的。
就这篇小说谈不上情节的情节而言,“我”从欧洲回到阔别五年的家乡,父母希望年过而立的“我”能尽早成家立业,于是就有了“我”和冯月澄的约会。故事并没有从约会展开,但小说展开了。
五年没有回国,故乡自然会有变化,人也如此。在作者笔下,冯月澄是一个很喜欢看恐怖片的少女,两人也没有就电影展开共同的话题,在东一句西一句的闲扯中,“我”时而注意到冯月澄手中的团扇,时而听她谈起单位的领导对个人照片的选择。但不知不觉中,“我”总会问起关于虞诗诗的情况。其实“我”对虞诗诗并不了解,也几乎忘记了她的样子,但很奇怪的是,“我”总是记得少年时最后一次看见虞诗诗“站在白果树下,胸前抱着一本书”的样子。“我”承认,不记得虞诗诗当时抱的究竟是什么,但意外的是,“我”记得虞诗诗“一只眼的双眼皮还褶出了第三层”。这不是故事的伏笔,却是小说最内在的伏笔,它不需要解释,不需要后文有什么对应,“我”只是交代瞬间的记忆,也就是刻画小说最漫不经心而又最意味深长的瞬间。
这一瞬间和形象并不能推动小说,但它成为小说的一个凝固画面。这就是从“我”记忆中归来的遗忘。作者的高明之处,是没有将这一画面具有的抒情色彩来对应“我”的心理活动。作者一切都不交代,只告诉读者,他内心只不过复活了一个镜头,其中的隐喻就是,他的一段记忆在不知不觉地复活。但他还是不肯告诉读者,“我”是不是爱上了虞诗诗。伴随“我”的心理活动是,关于虞诗诗童年的一些碎片在脑海中前后不连贯地出现。它们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甚至就是一些童年的恶作剧,譬如虞诗诗站在电梯外面,当电梯门打开,就将灭火器喷向电梯里的人,作为报复,“我”也用灭火器喷过虞诗诗。
“我”的记忆碎片随着冯月澄一句“好想游泳啊!你会游泳吗?”的问题而无端展开。同样是童年记忆。“我”和虞诗诗在游泳池里。“我”在儿童池,虞诗诗却在成人池。作者想通过这些细节呈现什么呢?作者依然不做交代。或许,“我”仅仅是展开这些记忆,展开一些遗忘的事件。这些事件几乎没有意义。“我”不过在更衣室里发现游泳圈不见了,于是回转,在泳池中看见游泳圈,虞诗诗“站在出口处,隔着栏杆冲我叫喊”。生活的片段的确无意义,问题是小说一定要刻画意义吗?或许,最寻常的事件成为了记忆,就是事件存在的意义。
小说写到这里,作者笔锋一转,描写了故乡的南河。作为读者,同样看不出作者描写南河对整篇小说有什么推动,或许,作者也不过简单抒发了对物是人非的某种感叹。并在感叹中顺便交代“我”对新事物的拒绝。这大概就是小说始终在等待遗忘归来的唯一作用。“我”对冯月澄承认,哪怕占据生活的微信和网约车,“五年前我就不用,现在我还是不用”。
如果就此判断,“我”是一个纯粹的恋旧之人,一定有误判之嫌。“我”面对冯月澄,能记得自己“社交媒体常被冯月澄刷屏,不是天花乱坠的电影海报,就是惊心动魄的愤青文字”,但这并不表明“我”对冯月澄会真的抱上将其发展为女朋友的冲动。记忆在“我”那里,始终只是碎片。冯月澄的存在和行为,只是让“我”从很多细节中陡然想起虞诗诗,譬如冯月澄从手机照片里翻出一座塔,“我”会忽然想起,虞诗诗当年告诉过这座塔叫“冷却塔”。作者的运笔始终不推动故事,但从细节中推动了小说的内在发展,那就是“我”对虞诗诗的展开又一些记忆,譬如虞诗诗在看火车时因害怕而握住了“我”的手,而“我”随之闪现的记忆又转换成没有将从德国人那里得到的巧克力给虞诗诗吃。
所有这些记忆和遗忘,都在“我”的脑海里展开,“我”没有告诉冯月澄,哪怕对方告诉“我”足够惊心的事件——和他们一起长大的徐紫依奇怪地为父亲之死有着见死不救甚至推进死亡来临的举动,最后徐紫依也“最后驾着车从一号公路冲进了海里”自杀,也没有让“我”有什么震动。“我”只是觉得,“世上每一个人都有委屈,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哭的权利,是不是每一个人的眼泪都会被怜悯”。从这里来看,“我”其实已经对生活有了足够的冷漠,但冷漠的前因后果無须追索,如果生活没有答案,强行追索也难说就能真的找到答案。
在结束这场约会之后,“我”对父亲的询问只回答了一句“就是见见朋友。没朝那方面想,不太合适”的话,但“我”仍莫名其妙地在网上寻找虞诗诗,结果一无所获,小说以“我还是不知道,虞诗诗漂去了哪里。我的眼睛又湿了,真是没有出息啊”为结束。作者似乎在提醒读者,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同时在一个快速遗忘过去的时代,人的情感是不是有点多余?最起码在这篇小说里,虞诗诗究竟是怎样性格和为人,读者一无所知,也无从展开任何期待。
但作者的运笔会让读者想起许多自己也遗忘的记忆。这大概就是这篇小说看似不动声色,却产生震动人心的强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