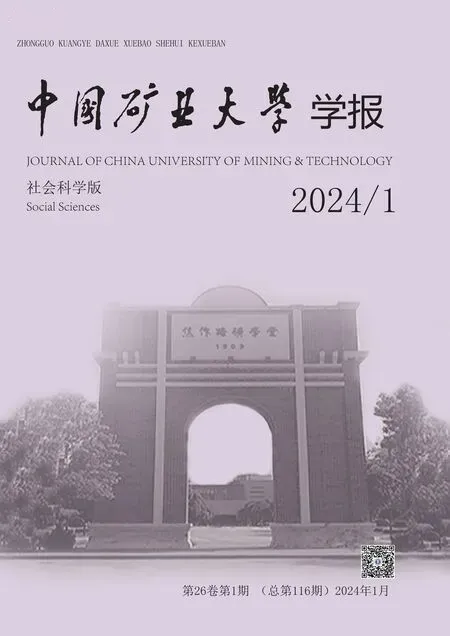德性如何“成于乐”
——基于先秦乐教演变史的考察
2024-05-07黄梦肖
黄梦肖
西周的礼乐之治是集国家体制、伦理规范、人文教育于一体的政治-文化模式,“礼”与“乐”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礼”是划分个体不同身份的行为规范,而“乐”是使不同身份的个体行为符合规范的教化方式。到了西周末期,制度层面的礼乐开始崩坏,而伦理道德层面的礼乐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就“乐”而言,西周乐教的精神要旨在儒家思想中得以赓续。孔子曾发出“成于乐”(《论语·泰伯》)的论断,如若将“成”视为德性实现的象征,那么孔子此言便喻示了“乐”于德性的重要性。与西方伦理学视野中德行与德性两分的观念相比①在西方伦理学的诸多相关议题中,可以看到德性与德行分野而治的研究路径,“德行”与“德性”两意并不同属一词。德行是指符合规范价值的个体行为,德性则对应个体的“品质”(traits)或者“品格”(characters)。,“德”字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既指外在德行,又指内在德性①杨国荣:《道德系统中的德性》,《中国社会科学》2000 第3 期,第85-86 页。,故而德性的实现包含了外在德行与内在德性的共同养成,两者最终统一并呈现于人格形态中。
以“乐”施教的教化形式,既需要用“乐”规范个体行为,使之符合外在规范的价值要求,亦需要“乐”作用于个体内心,使外在规范的价值内化为个体自身的德性品质。关于传统语境中“乐”的内容形式,近来学界普遍认为是由音乐、诗歌与舞蹈等结合而成的复合艺术形态②王顺然:《从“曲”到“戏”——先秦“乐教”考察路径的转换》,《哲学动态》2017 年第5 期,第45-46 页。,具有情感性、审美性与人文性等特质。经由西周礼乐之治的制度性建构及儒家思想的理论性建构,“乐”从一种复合艺术形态发展为一种教化体系,呈现出中华礼乐文明中独特的德性精神形态,这种德性精神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先秦乐教演变的经验事实,以这一时期“德”的内涵范畴变化为切入点,具体考察“乐”在个体德性方面的价值功能,还原其作为教化方式的德性精神样貌。
一、伦理规范:“礼、乐,德之则也”
西周礼乐之治中,“德”既是国家实体的共同价值追求——制度之德,又指实体中符合制度之德的个体行为——德行。而在西周“政治-伦理”型的国家实体结构中,个体德行与制度之德的实现方式具有形式上的统一性,皆实现于礼乐制度之中。其中,“礼”是划分个体不同身份的行为规范,“乐”则具有使不同身份的个体行为符合规范的教化功能,“乐”的教化功能依托于礼乐制度的规范功能,《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曰“礼、乐,德之则也”③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502 页。,正是此意。
“乐”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呈现共同体伦理精神的独特价值。伦理精神是伦理规范体系内蕴的价值指向与价值目标,是一种自觉的意义追求和精神指向④徐嘉:《礼乐的伦理精神》,《江苏社会科学》2023 年第2 期,第49 页。。梳理从上古时代到殷商时代,再到西周礼乐之治中与“乐”相关的伦理经验,不难发现,尽管“乐”在表现形式上呈现为一种复合型艺术形态,但其内容形式并不以审美性为第一价值追求,反而以凝聚群体、和谐秩序等伦理功能为首要目标,这正是先民以“乐”呈现共同体伦理精神的表现。氏族方国时期有记载的葛天氏之“乐”,黄帝时代的《云门》《咸池》等“乐”,颛顼时代的《承云》等等都带有浓烈的氏族风俗印记。可以说,“乐”自诞生就有群体性伦理特质,并具有记载共同体伦理习俗风俗的作用,伦理习俗风俗代表的正是朴素的规范体系。舞蹈、诗歌等艺术形式的加入都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共同体的伦理精神。此精神气质通过“乐”的内在感性方式传达给人们,使人们产生出集体情感与集体意识,从而达到凝聚群体、和谐秩序的作用。用“乐”来象征氏族伦理风俗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殷商时代,而西周伊始周公“制礼作乐”的行为背后,蕴含着化伦理习俗风俗为制度规范的政治倾向,“乐”被纳入西周伦理规范体系并不奇怪。
由分封制与宗法制构成的西周国家实体,个体处在一个庞大而缜密的伦理关系网中,人之所行处处皆是伦理规范。在这样一种结构的伦理实体中,个体德性只有通过伦理规范才可以实现,质言之,当个体处于西周“政治-伦理”制度中,德性实现于个体对相应伦理规范的遵守,最终表现为政治德行。考据殷商甲骨文中的“德”字,似并无今日所说伦理道德之义,而指人们通过巫术祭祀等方式向上天祈求降予的过程,如“王德正”“今春王德”等;《尚书·盘庚》中有关“德”的记载基本属“得”意,因此学者认为《礼记·乐记》所说“德者,得也”①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717 页。,较好地反映了上古时代关于“德”的通行看法②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5 第4 期,第194-195 页。,“德”指某种价值意义的获得。因为与上天有直接联系,可将这种“德”称作一种并无善恶性质的“天德”。与“天德”相对,发展到“人德”之德,当属西周开启的礼乐之治。西周将“天德”理性化为日常人伦的价值原则,即“人德”。上古氏族到殷商时期以巫术祭祀等神秘活动来凝聚集体,个体在恐惧敬畏的心理状态下遵循群体规范;西周时期转“天德”为“人德”的思想氛围中,个体的行为动机需由知、情、意共同决定。质言之,个体需要在这三方面对规范产生价值认同,才会作出相应行动。一旦个体认知到自身价值与外在规范的价值不一致,其行为动机就会与制度规范要求的遵守服从产生张力。显然,西周统治者尝试用“乐”影响个体的内在感性来缓和这种张力,认为“乐”可以将外在规范的价值化为个体内在价值,从而消弭这种可能的紧张性。“德”字在甲骨文中并无“心”旁,到金文中才屡见有“心”之“德”,侧面可以印证西周时期“德”能否实现,与个体的内心状态密切相关。那么西周统治者如何发挥“乐”的作用呢?
首先,西周时期依据国家实体的共同价值,对“乐”的形式内容有着明确规定,共同价值是追求“和而不同”及“等级秩序中的和谐”。这种价值追求由“礼”与“乐”共同完成,展现为“乐合同,礼别异”,其中:“礼”本意指人的行为模式,天然地蕴含着规范性价值,“礼”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伦理特质;而作为合同社会,个体的“乐”,其合同的前提是“礼”的外在规范带来的分异差别。“合”有聚集、使聚集之意,“合同”为会同、齐同、和睦之意。具体而言,西周宗法制与分封制是以亲亲尊尊的制度原则,将国家上下划分为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而礼乐制度规定等级秩序中不同的社会角色的责任义务,并且通过制度的规范性价值保障个体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以此实现国家实体的和谐稳定。周人日常生活充斥着“礼”,凡用“礼”处必有“乐”,正如《通志·乐略·乐府总序》记载:“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西周礼乐相伴相生的现实情况使得“乐”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礼”的规范性与等级性功能,所谓“乐以彰礼”;反之,“礼”亦对“乐”的形式内容有所规定,按照种类、内容,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两相结合,西周时期“乐”应被称作为“礼乐之乐”,“乐”从表达早期伦理实体的习俗风俗,到呈现出伦理规范体系的共同价值,其形式内容的价值依据已然发生改变。
其次,西周时期形成了以“乐”施教的教化体系。西方语境中,“教化”(Bildung)一词源自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的德国浪漫主义,“教化”比“教育”与“修养”有更深刻的意味,其指向“个人和民族的整体的精神品质从个别性的粗野状态向普遍性的文明状态的提升”①詹世友:《黑格尔论“教化”与政治文明发展》,《哲学分析》2023 年第2 期,第50 页。。《说文解字》有言:“教,上所施下所效也。”②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年,第226 页。“化,教行也。”段玉裁注:“教行于上,则化成天下。”上古时期就有以“乐”施教的经验,《尚书·尧典》中有一段关于舜命夔典乐以教胄子的描述:“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③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28 页。西周继承了这种乐教传统: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④杨天宇译注:《周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325-326 页。。
西周官方的乐教制度主要针对贵族子弟,即分封制下掌握实权的阶级,教学内容以歌颂古代贤王的政治德行为主。但以“乐”施教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贵族阶级,主要得益于以下三方面:第一,在由分封制与宗法制构成的西周国家实体中,每一个宗法团体的大宗都对小宗具有道德教化的责任。如何炳棣先生所说,“西周前半广义礼制之所以能充分发展是因为宗法制的推广及其无与伦比的‘社会教育’功能”,此社会教育功能依托于“万万千千根据宗法而形成的大小宗族”,最终达到“化民成俗”的效果⑤何炳棣:《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第165-166 页。。故而,西周教化体系不仅指针对贵族子弟的官学制度,更是一种包含各个阶级上下的治理方式。第二,西周时期存在着赐乐制度,为施行教化提供了具体形式内容。《礼记·王制》记载,“天子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鼗将之”⑥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252 页。,据有关学者考证,周天子赐乐不仅赐演奏乐器,还会赐乐官。诸侯以天子所赐乐官与乐器为荣宠⑦白川静:《西周史略》,袁林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 年,第99 页。,有时也会效仿天子,赐乐于封地内的士与大夫以表奖赏⑧王齐洲:《论中国“乐教”的发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1 期,第60 页。,士与大夫亦然。天子还会派人定期到各个诸侯国考察礼乐制度实行的效果。这样一来,代表最高技艺水平的宫廷雅乐有了流传民间的可能,使化民成俗得以实现。第三,“乐”内蕴感染人心与人情的独特价值,对社会生活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呈现出渗透性与弥散性的特点①王楷:《早期儒家乐教传统的演进及其当代价值》,《道德与文明》2018 年第2 期,第23 页。。荀子云“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②方勇、李波译注:《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327 页。,故而,圣王制“乐”来“善民心”与“移风易俗”。概而言之,基于西周宗法体系中教化理念的存在,及周天子将礼乐制度推行于各个诸侯国的相关政策,再加之“乐”易传播、易感化人心的特质,以“乐”施教的影响得以遍布于西周上下。
西周对“乐”的形式内容加以限定,并将乐教设置为国家制度的形式,这种制度化的建构过程对“乐”本身而言,首要意义在于为其纳入了伦理规范与伦理价值。如若不对概念演变史加以辨析,则很难厘清中国语境中“乐”的复杂含义。基于这些含义,“乐”才可以作为“德之则”,并行教化“德之行”的功能。因为西周礼乐制度的规范性特质,以及“礼主乐辅”的呈现形态,难免将“乐”之教化全然归纳为一种规范功能。然而,无论通过礼制对“乐”的形式内容加以何种规定,教化功能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乐”不同于“礼”的独特内在价值,因而以“乐”施教比纯粹礼制规范多了内在感化效果。西周早期统治者应当总结了夏商时期“乐”在凝聚群体、和谐秩序方面的独特价值,才会将其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正是西周礼乐制度的实行,使得“乐”的独特内在价值获得了普遍现实性,为后世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大量事实经验。
在这套“政治-伦理”规范体系中,西周统治者并不强调以刑罚等强制措施来约束民众,反而注重以礼乐教化民众。尽管这种教化形式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但在西周统治者“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③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462 页。的观念中,礼乐教化的客观效果亦使人民具有了“德”。所谓教化便是使人民在知、情、意方面具有稳定的精神定势,这基于外在规范的普遍价值,即伦理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教化便是使个体行为趋向于外在规范的重要方式。西周礼乐制度对中国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具有奠基性意义,生成了两种影响深远的观念:第一,个体德性自生长之初就由外在规范的共同价值而来;第二,统治目的在于通过教化使个体德性与外在规范达成价值一致性。这种政治模式被后世称为“德政”,西周礼乐之治作为德政的典范,经由儒家思想的不断建构,成为一个“政治上的永恒乡愁”④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19 页。。
二、内心的自觉:“人而不仁,如乐何?”
始于西周末年的“礼坏乐崩”现象,表现为周天子政治权力的削弱、各诸侯国权力地位的崛起,礼乐制度作为一套规范体系失去了普遍约束力,朝堂内外充斥着有悖礼乐精神的种种行径。由此可见,依托于国家政治结构的礼乐制度,其精神价值与规范功能受到了政治动乱的冲击。随着官方主导的乐教制度逐渐消亡,“乐”的教化功能也随之式微。直到春秋末年,“乐”在伦理道德层面的教化功能通过诸子百家的理论建构重新显现。
一方面,面对个体行为与外在规范之间的价值冲突,诸子试图提炼出一个超越于具体德行之上,具有普遍性原则的“德”。这一时期“德”的指向由个体行为转化为内在品格,关于以“乐”施教的讨论也更侧重于以“乐”实现内在品格的方法上①黄梦肖、徐嘉:《论“乐”的伦理精神》,《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4 期,第28-29 页。。另一方面,“礼坏乐崩”后的东周已不再是政治实权中心,亦不存在权威正统的官学中心,天子失官,私学兴起,庶人阶层的政治自觉与社会地位有所提高②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兴盛时期容纳了儒、法、名、兵、农等诸家,汇聚天下贤士多达千人。足以可见与西周时期的官办学制机构已大不相同,教化对象不再受限于贵族子弟是必然趋势。。故而,“乐”的教化对象不再受限于周人贵族子弟。两者结合,“乐教”逐渐从狭义的西周官学制度转变为一种广义的伦理教化形式。其中,孔子对“乐”的理论建构影响最为深远,孔子于外在规范失效的情况下挖掘了“乐”的内在自觉性价值,并以这种内心的自觉为道德动力,建立了一条凸显道德主体性的德性修养路径。所谓德性修养,其目的与西周以“乐”施教一致,都是为了赋“德”于人;差异性在于西周以“乐”施教是以制度规范的形式存在,“我”作为受教者是被动角色,而德性修养强调“我”作为道德主体的主动行为。以“乐”施教的官学制度体系中,判断“德”是否实现并不需要考证个体行为动机,只考察行为本身是否符合制度规范的要求。但在孔子所说的德性修养方法中,比起行为是否符合外在规范,更重要的是“我”通过这些行为成为一个道德主体,这就需要高度的自觉性作为行为动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③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76 页。,孔子这句话正是这条德性修养路径的“方法论提纲”,开启德性修养的动力源泉,正是通过注入“乐”的自觉性价值而完成的。
(一)“仁近于乐”的德性特质
普遍而言,“仁”与“礼”是孔子学说中两个核心概念,也是后世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仁”是兼具德行与德性的“德”,具有统摄其他德性条目的核心地位,朱熹称“仁是个全体”④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武汉:崇文书局,2018 年,第355 页。。“礼”指社会生活中的伦理规范,孔子之“礼”继承周礼精神而来,具有人文价值与规范价值。“仁”这一德性条目虽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但孔子赋予了它更为丰富的价值内蕴。
《论语》中孔子提到“仁”处众多,它既是一种价值原则,又是一种内在精神品格。杨国荣先生论证道:当“仁”作为一种价值原则时,首先涉及情感的凝聚与情感的沟通,情感的凝聚关乎内在的精神世界,情感的沟通则以人与人的交往为指向⑤杨国荣:《何为儒学?——儒学的内核及其多重向度》,《文史哲》2018 年第5 期,第6 页。。而当“仁”指内在精神品格时,是能使个体“爱人”的德性 ,并遵循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⑥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72 页、第188 页。的行为原则,这种行为原则强调人与人情感感受的互通性。基于孔子描写的“仁”之特性,以“乐”施教是培养有仁之人的极佳方式。因为“乐”作为一种复合艺术形态,能通过感性审美与情感体验两种方式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状态,感性审美可以引发正面的心理状态,如快乐与愉悦等,使个体在接受教化的过程中具有积极性与主动性。共同的情感体验可以使人与人通过“乐”达成某种共识性,譬如备受孔子推崇的《韶》《武》等“乐”,都以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尧、舜、周文王、周武王等为主题,通过“乐”至善至美的艺术形式来赞扬理想人格,以使民众心有所感。心有所感的前提便是情感共识性的存在。
以“人”为主体,“仁”指向个体的内在精神世界,而内在精神世界需要通过个体行为以及人格等现实形态呈现。孔子有言“人而不仁,如乐何”①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25 页。,意味着“乐”是“仁”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沟通桥梁。孔子作为周礼的忠实拥趸,其思想继承了西周以“乐”施教的传统精神。一方面,孔子将乐教传统中“乐”可感人心、化人心的特质,附加到“仁”作为一种内在德性的品质中;另一方面,通过强调人在获得“仁”时的情感共通状态,使具有情感特性的“乐”成为培养德性的极佳方式,确证其在教化个体方面的独特价值。
(二)作为道德动力的情感体验
孔子论及“乐”时,他要么批判与西周雅乐相对的新声——郑卫之音,如“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要么强调自身观“乐”的情感体验,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②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185 页、第211 页、第79 页。。前者是孔子传承西周乐教精神的体现,保留了对“乐”之形式内容加以规定限制的方式;后者则是孔子对传统乐教形式的创新,他将“乐”的情感体验视为个体内在的道德动力。
孔子尝试赋予此类情感体验以某种超越性特质,如“三月不知肉味”的描述,而这种略带神秘的体验并未纳入宗教情感,而归于道德情感(moral sentiment)。孔子通过道德情感将个体的行为动机与外在规范连接起来,这种表达方式可见于《论语·八佾》中一段孔子跟鲁国乐师的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孔子是这么描述“乐”的:“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③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35 页。张祥龙先生认为孔子将“乐”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解释为“让那摆脱拘束的始翕态(变而发动盛大貌)舒发开来,但又绝不让它散漫流行,而是保持其纯粹的生发和谐的势头,以至放射出明亮清白的(出自其本然素质)的光辉,反复再三,曲尽其意,一气呵成”,并认为《论语》中另一段孔子所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是对“始翕”“从纯”等状态的另一种述说④张祥龙:《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87 页。。
张祥龙先生关于“乐”的观点与西方学者将音乐的伦理性解释为一种“经验性形式意义”(experiential formal meaning)类似,他们认为音乐的演奏建立在时间的连续性上,以一个整体的形态向听众/观众展开,因此当人们沉浸在音乐表演时,需要通过认知和情感相互作用去经历音乐的连续性(sequences)①Koopman C, Davies S,"Musical Meaning in a Broader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esthetics & Art Criticism,2001,No.3,pp.261-273.。那么,当孔子观“乐”时体验到的这种连续而饱满且具有整体性美感的情感体验,对于当时不再认同伦理规范价值的人们而言,似乎是恢复伦理认同感的最好方式。
孔子把这种体验化入“仁”的伦理精神境界中。“仁”往往具有某种连接感,是由己以通达于人的道路,是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使人将孝悌之情逐步扩散到“泛爱众”①的能力。而“乐”为激发出个体的道德情感提供了一个客观载体。孔子认为,人一旦可以基于好恶之情来追求“德”,自觉作出符合“德”的行为,或避开有害于“德”的行为,往往这个人已可被称为有“仁”之人。可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②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106 页、第39 页。等句。
(三)理想人格的现实形态
通过孔子对“仁近于乐”的特质描述,以及将情感体验作为德性修养的动力,足见在孔子这里,有关“乐”的学习实践是一种凸显内心自觉的德性修养方式。具体说来,一方面个体通过“乐”引发道德情感,并将其作为行为动力;另一方面,一旦在“乐”中体验到道德情感,个体就会将自己视为道德主体,并对应当承担的责任义务产生价值认同,这样一来,“我”与外在规范的关系就会从“我不得不做”转为“我自觉这样做”。
然而,只是解决道德动力的问题并不能完全解决德性与规范之间的张力。因为,由“乐”引发的情感是个体特殊的感性直观体验,从特殊的情感体验上升为具有普遍理性的道德情感,还需要解决个体特殊价值与普遍伦理价值的张力,才能将“道德情感”变为一种解决规范与德性张力的道德动力。孔子通过设置理想人格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其思想中,君子、圣人等理想人格不仅指向内在德性,也指具体的外在德行。理想人格是内在德性与外在规范统一后的现实形态,既可在精神上激励个体修养德性,亦可为个体的日常行为提供一种规范性指导。西周官方乐教根据对象的社会等级“教而有类”,而孔子强调“有教无类”③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192 页。。孔子所定六艺虽继承自西周贵族的教育内容,但打破了只能贵族阶级享有的权利,成为民众人人可学习实践的修养方式。因此,理想人格的设置替代了不可变更的外在等级身份,成为激励个体进行德性修养的新内在秩序。
概而言之,孔子从德性特质的规定、道德动力的情感特质、理想人格的现实形态这三方面来建构德性修养论,而这三个方面中,都能找到与“乐”直接相关的价值逻辑。质言之,孔子从这三方面建构了“乐”在德性问题上的自觉性价值。他亲自删减编选“乐”,以宣扬理想人格与表现美好伦理生活为内容,来呈现内在德性与外在规范和谐一致的美好愿景,正是“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1733 页。之意。由此来看,“乐”既可激发个体进行德性修养的道德动力,又为德性修养的实践过程提供方法,其至善至美的精神特质象征着内在德性与外在规范的和谐一致,故而孔子将“乐”视为彰显德性的精神象征,并将西周以“乐”施教的制度形式转化为更具普遍意义的德性修养路径,所谓“成于乐”。
三、德性与规范的统一:“乐以养德”
随着诸侯割据之势,东周不再是天下文化中心,西周乐教在现实中的失落不可抵挡,所谓郑卫之音的新声层出不穷,受到民众与各诸侯国的推崇。孔子凸显内心自觉的德性修养论,并没有挽救西周乐教传统的颓势。这一时期,尽管“乐”的教化功能与德性修养功能都未实现,但其德性价值的理论体系反而得以建构。“乐”开始作为一种象征德性的精神符号,具有至善至美的精神气质特性,如“乐者所以象德也”“乐者,德之华也”②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730 页、736 页。等;而德性问题也开始变为以人性与人情为本体论基础的讨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③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136 页。“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④王文锦译注:《大学中庸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14 页、第31 页。等。由此,以“乐”为对象的伦理教化与德性修养逐渐被抽象为“养德”之含义。
根据学术界对于战国早期曾侯乙墓音乐的考据,这一时期乐律方面的知识已经相当完备,曾国乐学体系中已有关于绝对音高、相对音高的概念⑤薛永武:《〈乐记〉精神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 年,第8 页。。相比于西周乐教传统的失落,这段时间却是中国音乐体系走向成熟的阶段。彼时关于“乐”在如何实现德性问题上有更细致的讨论,具体到以乐律的特质来象征人的性情特质。“乐”在形式内容与社会功能上表现出来的特质被总结为一种普遍性原则——“和”,这种普遍原则既关涉人们对人之性情的规定,又是以“乐”来陶冶人之性情的价值追求。
受孔子崇“乐”思想较深的儒家七十子,通过对天命、人性与人情来讨论“乐”的教化功能。在《性自命出》一篇中,表述了人的情感根植于人的天性,而情感又是“乐”的本源,人通过“乐”抒发情感时,“乐”又反过来对人的情感产生影响。因此,形成以“乐”为中心的教化形式极为必要。后儒强调“乐”在实现德性方面的情感性价值,实质与孔子凸显道德主体性的方式相近。《性自命出》篇虽花了不少篇幅讨论“乐”与情感、教化、德性之间的关系,但主旨是儒家专门的心、性、情论作⑥李天虹:《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57 页。。侧面说明,关于德性的理论建构已逐渐完善,并不需要借由“乐”的特质及传统乐教来为德性作界定,反而愈发完善的德性理论体系来为“乐”的现实价值背书。对于儒家七十子而言,与情感紧密相关的“乐”具有比“礼”更重要的教化功能,如《尊德义》中说到“由礼知乐,由乐知哀。……有知礼而不知乐者,无知乐而不知礼者”①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182 页。。较孔子与七十子而言,孟子建立的思想体系并无重视“乐”的倾向。尽管孟子也说过“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但在孟子与齐宣王讨论“乐”时,他对今乐与古乐的态度是“今之乐由古之乐也”②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238 页、第19 页。,这与孔子对新声今乐的厌恶态度相反。可以说明,孔子强调“乐”之情感经验的伦理道德意义,在孟子时代已然不具备太多的现实价值了③杨传召:《论战国时代儒家乐教的失落》,《孔子研究》,2022 年第1 期,第101-102 页。。
这种思想模式一直延续到荀子,其“乐”论思想吸收继承了先儒音乐思想的精华,将“乐”的教化功能纳入其“隆礼重法”的思想体系中,从性恶论视角赋予了“乐”的教化功能以规范性价值,在规范节制人情的意义上建立了“乐”实现德性的方法论。处于战国末期的荀子十分重视“乐”,相关思想理论影响深远,基本上奠定了后世关于以“乐”实现德性的理论基础。无论是教化形式的“乐”,还是作为德性修养的“乐”,关键都在“乐”与人情的关系。后儒思想中关于“乐”在教化个体、移风易俗等功能上的理论逻辑基本不出其左右。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一是不同形式内容的乐律曲风对应人的不同情感;二是人情是一种欲望,可能导致个体作出不道德的行为,需以乐制情;三是以“知乐”作为君子与庶人的区别。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④方勇、李波译注:《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325-329 页。。
透过荀子论“乐”,可见其与孔子及七十子对情感的看法有所不同,这是荀子基于性恶论来讨论教化的缘由。荀子认为,人情不是确证道德主体性的道德情感,而是一种具有消积意义的情感,是先王作乐以教化民众的合法性来由。
荀子将人的欲望等同于情,认为人的欲望无休无止,必须通过外在规范加以遏制。其对“乐”的形式内容再次加以严厉限制,呼应了孔子对郑卫之音形式风格的批评。荀子引入性恶论,恢复了“乐”在德性方面的规范价值,强调了官方乐教制度存在的重要性。战国末年是“礼”与“法”的时代,在礼法两种具有强规范价值的理念中,“乐”基于内心自觉的德性修养功能逐渐边缘化,而荀子通过“乐”与人情、人情与欲望的关系讨论,强调了“乐”作为一种教化方式存在的必要性,使得“乐”在德性修养方面的独特价值得以留存。汉代《礼记》中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荀子以及先儒的乐教思想,并由此形成了以伦理规范与道德价值为依据的“声”“音”“乐”三种形式划定: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①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716-717 页。。
荀子关于“乐”具有规范功能的性情教化论,与孔子强调“乐”具有内在自觉价值的德性修养论互为补充,最终使得“乐”的德性精神留存于儒家教化思想中。“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②方勇、李波译注:《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329 页。
四、余论
从西周乐教的经验事实到先秦儒家的理论建构,“乐”的教化精神与德性精神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独特精神气质。“乐”既是古代德政典范的精神符号,也是君子、圣人等理想人格的精神符号。论及“乐”在个体德性与外在规范方面的价值,其独特性在于化外在规范价值于个体内在价值。个体的内在价值必须实现于外在伦理世界,才可称之为个体德性的实现。故而,一旦脱离现实环境,“乐”作为德性修养与教化形式,其功能并不如兼具实践性与规范性的“礼”,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德性理论,或者复归为只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形态。这或许正是秦汉以降,乐教可与礼教、诗教互相替代的原因,由此“乐”逐渐从凸显普遍伦理价值的“大乐事”转为辅助礼教的“小乐事”③王顺然:《“乐崩”现象的背后:“大乐教”到“小乐事”转向中的“学统”再造与礼乐关系重构》,《孔子研究》,2022 年第1 期,第106-114 页。。
在孔子所处的时代,西周礼乐之治的精神图景还未完全消散,其“洋洋乎盈耳哉”的情感体验是对这种美好景象的呼应。“乐”作为承载西周礼乐精神的艺术形态,具有独立于制度规范外的审美价值与情感价值,而能广泛流传于民间。礼乐之治的和谐稳定与诸侯割据政权的纷乱局势对比鲜明,作为曾经的鲁国贵族,孔子受浓厚的礼乐氛围熏陶,这使其尝试通过“至善至美”的“乐”来实现德性,从而恢复和谐稳定的伦理秩序。当以美好伦理生活与理想道德人格为内容的“乐”呈现眼前,个体通过“乐”产生向往“德”的道德情感,再自觉地进行德性修养。此外,国家也提供了以“乐”为实践内容的学校机构。这样一种以“乐”施教的德性修养路径,经由后世儒家的理论传承,终使至善至美的气质充盈于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