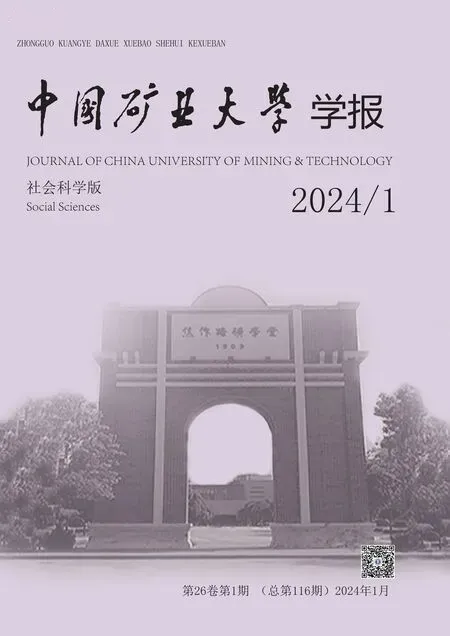《船长与仇敌》:格雷厄姆·格林历险小说中民族身份的反思与重构
2024-05-07周梅
周 梅
玛丽亚·库托认为对于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1904—1991)的创作起源,有几个影响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他童年时所读的历险故事、红衣主教纽曼、约瑟夫·康拉德和亨利·詹姆斯的宗教意识、道德伦理和审美情感,以及格林本人的旅行经历。”①Couto M, Graham Greene:on the Frontier: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Novel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8, p.10.在众多因素中,传统历险小说的影响贯穿格林成长和创作的始末。他自己曾说正是因为读了哈格德的小说《蒙特朱姆的女儿》,才产生了去墨西哥的冲动,而他最初对利比亚感兴趣,也与阅读《所罗门王的宝藏》有关。“尽管在格林创作时期维多利亚时代的历险英雄所依赖的或曾经支撑他们的价值体系已荡然无存,但格林作品的原型几乎都是源自维多利亚时代的历险故事。”②Diemert B, Graham Greene's thrillers and the 1930s, Canad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6.那时“具有历险精神是成为一名英国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而,“历险小说,作为传统意义上的通俗文学,对于民族特征和文化影响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为过”①Kestner J A, Masculinities in British Adventure Fiction, 1880-1915,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0, p.2, p.6.。
格林将历险、侦探、间谍和恐怖小说的元素融入自己的创作活动,实践“严肃性”与“流行性”书写的融合。因而,格林的“严肃小说”包含了“流行性”叙事元素,而其“通俗小说”则致力于发掘文化理想与责任,进行政治和文学拷问,并渴望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重建民族或社群身份。因而我们不应该把格林视为在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帝国历险小说传统中写作的作家,而应该把格林的历险小说视作对传统历险小说模式继承基础上的一种颠覆,或者可以说,他是在传统历险小说的废墟中写作,以反思和重构传统历险小说中叙述和呈现的英国民族特性。格林历险小说中的主人公或“反英雄”人物对家园和稳定身份的渴望与追寻却是以对传统历险英雄塑造模式的解构来实现的,同时解构的还有帝国历险小说中所描述的帝国及其历险者的活力、自立、权力与权威。
格林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船长与仇敌》(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1988)便是这样一部政治历险小说。这部作品在国内外研究者中所受的关注较少,部分原因在于小说内容和情节设计不属于格林研究中备受瞩目的宗教主题,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与格林其他国际政治背景的小说相比,这部小说深度稍显欠缺,如辛亚德认为其情节“顽皮而又曲折”②Sinyard N, Graham Greene: a literary lif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7.。伯贡齐则“希望他(格林)以一部更强(stronger)的作品收官”③Bergonzi B, A Study in Greene: Graham Greene and the Art of the Nov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p.182。伊格尔顿更是对格林在小说结尾处设计由“船长”这样一个“政治原则模糊的人来执行最果断的政治行动”提出质疑④Hoskins R, Graham Greene: an approach to the novel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28.。然而,纵观格林的小说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作者在《船长与仇敌》中以一种巧妙的自我参照的方式回顾了他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以主人公探寻自我身份为主题的小说《内心人》(The Man Within,1929)中的诸多要素,如最后一部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名字“丽莎”也延续了第一部中的“伊丽莎白”,而两人都是各自小说中男主人公建构自我的精神支柱或引路人。与第一部小说类似之处在于,格林在丰富的历险小说情节的基础上结合了间谍小说的元素,把自己本人的真实经历、人物类型和多种主题都再一次融入其中,为自己漫长的文学生涯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仿佛怀旧似地呼应了创作生涯的开始。六十年后,格林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身份建构之旅中再一次到达“危险边缘”(the dangerous edge)时,重新作出了自己的道德选择。在这部小说中,格林透过传统派历险人物的代表“船长”和质询派代表吉姆在历险中寻觅与建构主体身份的描述,反思并试图重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帝国的衰落与解体、经济大滑坡以及冷战后,在曾经的殖民地美国经济异军突起背景下的英国民族身份认同。
一、新老帝国的交替:对帝国历险本质的反思和解构
马丁·格林根据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和“传奇”的两分法,将历险小说定义为一种传奇(Romance),并将其与帝国联系在一起。因为传统英国历险小说与其海外帝国扩张的叙述是紧密相连的。文学作品中的历险故事与政治领域的帝国扩张相对应,激发了人们对英雄壮举、异域旅行和跨越危险边界的憧憬。而格林在《船长与仇敌》中对英国传统历险小说要素的颠覆首先体现在主人公吉姆想象中的“历险”与社会现实的巨大断裂,及其养父“船长”被格林塑造为“格林原”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从而呈现了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英国人的生存困境及身份和文化焦虑。
《船长与仇敌》的故事始于主人公吉姆在十二岁生日当天被自称为其父亲朋友的“船长”从学校“拐”走——“船长”的解释是吉姆父亲在一次西洋双陆棋中将他输给了自己。在家中,吉姆的父亲是母亲眼中的“恶魔”(the devil),母亲去世后将吉姆托付给了善良却无趣的姨母;在学校,吉姆是同学眼中的“亚玛力人”(the Amalekite),是他们的敌人①作为伯克姆斯特德学校校长儿子的格林曾因拒绝反抗父亲的“权威”而常被同学视为“敌人”,对他进行嘲讽与挑衅。。而吉姆和作者格林一样喜爱哈格德的历险小说。在“船长”出现之前,怀揣文学梦想的他已经读了四遍《所罗门王的宝藏》,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去往非洲书写自己的历险故事。因此,吉姆对“船长”的出现并未感到过多困惑,而是欣然愿意与他离开,去开启自己梦想中的历险旅程。
当“船长”带着他光顾“天鹅酒吧”时,吉姆幻想着自己憧憬的充满自由的历险生活似乎已经起航:“看着身边觥筹交错的人们笑着、聊着,我想到了木筏和我一直计划的长途航行。我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世界的另一端。在浪漫的瓦尔帕莱索,我正和在七大洋航行的外国水手们狂欢作乐。”②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15吉姆对历险生活的想象源于他所读过的传统历险故事,这些历险故事塑造了忠诚坚毅、自由洒脱、足智多谋、英勇无畏的白人男性历险者形象,他们在陌生或异域环境中仍能处变不惊、从容冷静应对并展示英国特有风度。他们是英帝国扩张时期所推崇的主流男性形象,并在英帝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随着二战后帝国的崩塌以及曾经的殖民地美国的异军突起,英国男性殖民者的权威也不断被瓦解。英帝国与其男性公民在诸多空间和领域日渐“去势”的现状使得他们遭遇了蒂姆·埃德华兹所定义的男子气概的外部和内部危机。外部危机主要指男性在家庭、教育、工作等领域优势地位的丧失。而内部危机主要指“男性对性别身份和男性气质的焦虑”,尤其是指男性的“无力感、无意义感和不确定感”③Edwards T, Cultures of Masculi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6.。格林小说中的“船长”就是这样一个深陷于男子气概危机之中的人物:一方面他仍坚守传统历险小说中白人男性在异域空间历经磨炼获得财富的成功路径;另一方面,阿诺德等维多利亚学者曾极力倡导的道德与文化已无法再为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英国男性在矛盾重重的内外帝国的生存提供引领力量。因而,“船长”注定是一个悲剧性的矛盾结合体。正如他爱用别人无法理解的复杂而又拗口的“难词”,如“generic”“Funambulist”等,更是凸显了其行为的“年代错误”。
因而,尽管“船长”极力美化自己的获利方式,吉姆从与其相识的第一天“船长”用装满石头的行李箱欺骗酒吧老板获取“免费”食宿,以及时不时上门询问其踪迹的警察口中基本能够断定“船长”和《内心人》中的“养父”卡莱恩一样,是靠盗窃和走私获利。而这种盗窃和走私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传统历险故事中主人公掠夺性财富积累和经济贸易活动的一种延伸。对于“船长”来说,这也是他“履行帝国责任与实现经济利益的两全其美的结合”①徐彬:《想象“他者”与“他者”想象——现当代英国流散文学与英国国家身份构建》,《外国文学研究》2021 年第2 期,第121 页。。“船长”不定期地“去往某地”,随着异域邮票而来的是信件中的大额支票。这里格林似乎在戏仿摄政时代奥斯汀笔下的达西等男主人公或维多利亚时代勃朗特姐妹作品中的罗切斯特和希斯克利夫去往殖民地,通过“海外殖民途径实现阶级跃迁”②于承琳:《〈呼啸山庄〉中的社会流动与帝国逻辑》,《外国文学研究动态研究》2023 年第4 期,第22 页。。“船长”曾表示自己非常欣赏吉卜林的历险小说③这可能也是他将养子的名字改为吉姆的原因。,认为吉卜林“真正懂得像他这样的人的感受”,吉卜林“似乎在与自己对话”。他告诉吉姆:“一般来说,我不是一个喜欢诗歌的人——但有一段诗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是一个叫吉卜林的人写的。”④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66.这里“船长”提到的“一段诗”来自于吉卜林1899 年写作的短诗《白人的责任》:“承担起白人的责任,将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传播开来,让你们的子孙离家远去,去满足你们的俘虏的需要……”吉卜林的这首短诗表达了白人天然的优越感,将帝国统治和殖民入侵的行径看作是对所谓落后的“蛮夷”“蒙昧”种族或民族的“教化”,继而传播有利于帝国主义扩张和繁衍的“先进的”西方文明。因而当吉姆质疑“船长”在巴拿马的身份时,他的回应是,“我正肩负着极其重要的责任。‘他们’急需我的帮助”⑤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129.。作为“天真派”历险者代表的“船长”尽管缺少传统历险者的“霸权性”或“支配性”男性气质,却仍然试图用传统帝国历险小说中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措辞来掩盖和净化自己不道德的财富获取行径,正如上文提到的达西和罗切斯特等小说人物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性财富积累“来解决故事中的现实难题”⑥于承琳:《〈呼啸山庄〉中的社会流动与帝国逻辑》,《外国文学研究动态研究》2023 年第4 期,第22 页。。
小说中,“船长”十分崇拜十六世纪英国著名的私掠船船长、航海家、伊丽莎白时代的政治家弗朗西斯·德雷克,并试图模仿其从巴拿马运出一袋袋黄金而发家致富的故事。然而,德雷克虽有多种头衔傍身,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海盗。他通过海上掠夺活动成为海军中将,在军旅中曾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攻击,还曾横渡了大西洋,更是被女王授予英格兰勋爵头衔,可谓是登上了海盗史的巅峰。德雷克的“成功”背后是英帝国的默许、鼓励、合法化甚至是通过国家权力干预和助推其掠夺行为。伯纳德·迪德里希指出,“英国的学校,甚至是殖民地的学校,都向学生们讲述这位伟大的英国船长和航海家的卓越业绩,以及他是如何为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公海控制权的”①Diederich B, Seeds of Fiction: Graham Greene's Adventures in Haiti and Central America 1954-1983, London: Peter Owen Publishers, 2012, electronic version.。直到一战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所默认的掠夺式财富积累,及其所推崇的爱国、忠诚、为国献身等价值观在英国公学中普遍受到重视。格林也曾亲历这样的影响。在格林进入父亲任校长的伯克汉姆斯特德的初中时,正值一战爆发。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军官训练团的阅兵式、高年级男生的战术和军备讲座、野外演习和唱爱国歌曲等活动成了校园内的主要活动。格林曾说在他很小的时候,在伦敦看过一场露天戏剧表演,表演中德雷克袭击了一辆满载金银的西班牙骡车,这辆骡车正穿越巴拿马地峡,驶向西班牙国王的加勒比藏宝地农布雷-德迪奥斯。在1976 年与迪德里希同游巴拿马的时候,格林因亨利·纽波特在其所写的关于德雷克的系列诗歌中提到德雷克被埋在农布雷-德迪奥斯湾的海域中而特意去探寻了这位“船长”的遗迹。其实格林在《内心人》中描述安德鲁父亲时就提到过德雷克:“当他的父亲想要一件渴望而不可得的东西时,他就会使用‘大棒与诱惑’相结合的方法:伊丽莎白老传统中海狗一样的形象。他是和海盗德雷克一‘国’的人,说着德雷克的语言。大海甚至赋予了他一点德雷克的脸型和举止、肤色、线条、咄咄逼人的胡须、大声说话、高声大笑。”②Greene G, The Man Within, Vintage, 2001, electronic version.
“船长”在小说中反复提及德雷克以及穿越巴拿马地峡的满载金银的西班牙骡车的情节,一方面体现了他对英国曾经作为海上霸主时光的追忆。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像罗利、约翰·霍金斯和弗朗西斯·德雷克这样的冒险者不断偷袭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宣称的商业垄断,使英国人逐渐意识到英国在利用海洋方面处于有利的位置。而英国之所以能长时间保持海域上的优势并不断获得辉煌的胜利,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并开始主宰世界贸易,很大程度上正是海上力量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海上历险成为英国民族性格的重要内容,而海上历险的精神也成为定义男性气概和民族理想的要素。海洋成了“英国特性的文本源泉”。由此可以看出,与历险和海洋相关的“男子汉景观”和帝国修辞都是充满意识形态的复杂产物。追溯性地回望维多利亚时代至一战前的“旧世界”,那个英国拥有海上霸权的世界、父权制的世界、让男孩们参加战争的世界,能够给予二战后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英国人一种情感的慰藉,因为“几乎所有关于既定民族特征的描述,要么源于对失去的恐惧,要么来自毫不掩饰的理想化和怀旧感”③Patrick P, Nation and Novel: The English Novel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另一方面,自二战后英美综合实力的对照以及冷战时期“冷”“热”战的持续威胁和谍报工作的无孔不入,彻底摧毁了英国传统历险小说中男性气质存在和展现的基础。
格林将《船长与仇敌》第三和第四部分的叙事背景设定为1977 年形势错乱复杂、谍影重重的巴拿马。当时吉米·卡特政府即将与巴拿马政府签订交还巴拿马运河的条约,同时交织在这一背景中的还有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与其反对者“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内战,以及萨尔瓦多亲美派执政党与反政府游击队之间的内战。小说中,吉姆到达巴拿马后才发现,英国在1900 年深陷第二次布尔战争时为了获得美国的外交支持,与美国签订的《海约翰-庞斯福特条约》放弃和丧失了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和分权——这里已经是美国人主宰的地盘。因而,“船长”在巴拿马所谓的“白人的责任”以及像德雷克一样掠获金银而发家致富的渴望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说自话。
格林在小说中描述了美国在巴拿马的经济殖民和文化殖民,以无情的准确性揭露了美帝国自诩的“特殊论”和利他主义话语的虚伪性、欺骗性和破坏性。小说中的巴拿马城因过度依赖以美国为首的外资借贷而迅速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20 多家国际银行的庞大金融中心。在《没有地图的旅行》中,格林提到美国在利比里亚的殖民行径时也指出,“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掠夺了他们的土地;美国更坏,给他们提供贷款。利比里亚自身没有任何资源……他们不得不一借再借。每次借来的贷款却几乎只够偿还之前的债务,剩下一小部分盈余,利息却不断飞涨”①格雷厄姆·格林:《没有地图的旅行》,邝国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第280 页。,导致的结果则是美国成为最大的商业赢家,而依赖外资借贷的利比里亚或巴拿马却越来越贫穷。小说中,美国在巴拿马城奢华的银行建筑、美国人居住区内整洁的草坪和豪华的别墅与巴拿马贫困家庭拥挤着居住的被格林戏谑性地命名为“好莱坞”的、“秃鹫栖身、摇摇欲坠的棚屋”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小说第一部分描述的战后伦敦衰败的景象与巴拿马“好莱坞”一样,既反衬了英国经济的衰退,也凸显了美国的自由主义带来的物质上的巨大成功。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所呈现的“炫耀性财富积累”,以及一种“无尽满足消费者品味”和“迎合人类占有欲的文明”②Baldridge C, Graham Greene’s Fictions : the Virtues of Extremity,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0, p.189.给以“船长”为代表的英国人展现了一个被敌对势力重新改造的世界,这里野蛮的力量和无情的效率取代了传统和人道美德。
英国人感受到的来自美国的威胁不仅仅在经济层面,“美国化”对第三世界国家或对英国的文化反向殖民更加剧了英国人的身份危机。在《船长与仇敌》中,尽管奎格利自称是一个“纯种”的英国人,虽然持有英国护照,但在被美国文化和教育“洗脑”后,忠诚地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效力,试图通过捏造和“挖掘”巴拿马政府的丑闻来破坏交还巴拿马运河的条约签署。他用精准的数字来表述一切。他打着金融记者的身份进行情报工作,并随时准备投入使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政治争端或战争中,即使要密谋杀害自己的母国同胞也在所不惜——他分别设计了“船长”和吉姆的死亡事故。奎格利是美国对英国文化反向殖民的一个典型例子。“英国曾经统治并塑造了美国,而现在‘形势实际上发生了逆转’,使得英国变成了美国新传媒帝国的殖民地。”①吉纳维芙·阿布拉瓦内尔:《被美国化的英国——娱乐帝国时代现代主义的兴起》,蓝胤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42 页。在冷战后期,处于美国核计划庇护之下的英国已然成了世界力量角逐中逐渐边缘化的一个美国小跟班,而英国的外交政策也正在把英国变成“美国的附庸”。以“美国化”形式对英国进行反向殖民成了英国人无法阻挡的一个必然趋势,更是加剧了英国人所遭遇的民族身份危机。
格林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在衰败的政治和文化世界中挣扎,不可避免地遭遇多重焦虑和存在主义困境,从而导致他们需要作出身份选择时陷入了种种困顿。吉姆发现“船长”在巴拿马拥有双重间谍身份,他分别服务于代表美方的奎格利和巴拿马社会主义领导人马丁内斯上校。在小说中,“船长”反复提醒吉姆要小心奎格利,一个“被美国化”的英国人。然而,无论是“船长”还是吉姆,尽管都不信任奎格利,却又都依赖他提供的物质“援助”。这映射了战后英国渴望借助二战后迅速扩张的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通过美国的帮助或新老霸主的联合,维护和重振英国的大国地位,使英国再次成为全球重要的核心国家。然而,美帝国主义的新霸权彻底打破了英国人希望“从美式创新中看到英国利益,同时又保留着英国处于发展先锋位置的理想图景”②吉纳维芙·阿布拉瓦内尔:《被美国化的英国——娱乐帝国时代现代主义的兴起》,蓝胤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40 页。。美帝国横加干预下的巴拿马复杂的政治冲突、信仰迷失、生存困境、种族歧视、革命暴动、资本当道、物欲横流等社会现象和问题,使得“船长”计划的在巴拿马寻找“那驮着一袋袋黄金的骡子”的梦想无果而终。
小说最后一章,“船长”在三百多年前被威尔士海盗亨利·摩根摧毁的旧城的海滨废墟中肃立了好长时间,“他似乎在寻求一个真正的答案”“废墟之美,在于它们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教训”③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134.。“船长”对摩根掠夺和屠城行径的不满反映了他对英帝国历史性错误的认知。而目睹美国在巴拿马的殖民行径更是唤起了“船长”对遗失的政治良知的感悟。面对以科技和资本为核心的美帝国主义所暴露的无知野蛮,“船长”深感无力招架,因而“弥漫着一种对于男性‘雄风不再’的焦虑感”④陈丽:《论格林〈问题的核心〉中的男性焦虑》,《外国文学》2021 年第5 期,第17 页。。这也造成了他在身份寻觅和建构的过程中陷入僵局。而在小说结尾,“船长”驾着他用来走私军火、被自己称为“骡车”的破旧飞机对尼加拉瓜独裁者所在的基地进行了自杀式袭击,这一行为成了他最终倔强的抗争。
而作为“质询派”历险者的吉姆生于英帝国日渐衰落的时代,在观察和审视了养父的“历险”经历后,他一方面能洞察传统帝国历险故事中的的意识形态性和“传教性”,另一方面也因对曾经的帝国经验和帝国经历的反思而能清晰辨别以美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行径的危险性。吉姆认识到,二战后的男子气概不再是通过以身体和力量为特征的传统英雄主义所推崇的外在品质表现出来,而是回归对人性的诠释、实践自我整合,并勇于承担责任。格林在其小说中阐述了“民族复兴的新使命不再依赖帝国权力和经济霸权,而是更多地关注个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①周梅、陈兵:《追忆·融合·回归——〈英格兰造就了我〉和〈名誉领事〉中“英国性”的发展探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1 期,第151 页。。小说中吉姆从一而终的选择便是远离传统家园,不断探寻和定义属于自我的新身份。
二、新旧家园的更迭:永久的自我流放
战后的英国人遭遇了强烈的存在焦虑、身份危机和一种空间迷失感,使得他们无法在外部大的地理空间(包括社会、文化、政治空间,如海外帝国)和内在小的居住地空间(如个人的家园)为自己作出存在意义上的定位,即“感到无法以有意义的方式图绘自己的位置和周围环境:一种表征的危机”②罗伯特·塔利:《文学绘图中的冒险:勘探,表征,投射》,方英译,《临沂大学学报》 2020 年第2 期第4 页。。而伴随着内外帝国不可弥合的矛盾和裂痕,曾经萦绕在英国人心头的以田园乡村风光和传统家园为特征的“小英格兰中心主义”也成了一种追忆,无法为处于身心“流放”状态的英国人提供精神上的慰藉。
“家”是英国人名副其实的城堡和美德的宝库。然而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格林一代作家扩展了“家”的意义。对被包围或入侵的恐惧以及对社会或政治上停滞静止状态的恐惧,导致作家们想要尽可能地在身体和精神上处于一种流动状态。格林作品中的许多人物都在不断的位移中,如《英格兰造就了我》中的安东尼、《喜剧演员》中的布朗和琼斯、《与姑母同游》中的普林等。格林自己的解释是,“如果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我会变得焦躁不安……这可能是战争的影响”③Donaghy H, (Ed.), Conversations with Graham Greene, Jackson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2, p.126.。“正是一种躁动不安让我不得不四处跑动,也许是为了让小说中的英国角色在一个不受特殊保护的背景中能够以不同以往和更加开放的方式表达和反观自己。”④Donaghy H, (Ed.), Conversations with Graham Greene, Jackson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2, p.54.雷德曼在《传奇的风景:景观与英国民族认同的形成》中指出,“任何情况下的‘家园’都离不开旅行,或者更抽象地说,离不开空间的移动。或隐性或显性,所有人都会用空间角度来定义他们与个人家园的关系:一个人在家、离开家、靠近家等等”⑤保罗·雷德曼:《传奇的风景:景观与英国民族认同的形成》,卢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21 页。。
寻觅和体验“在家”(“being at home”)状态的存在空间是二十世纪英国小说的主题之一。与格林《内心人》中的主人公安德鲁斯凝视着伊丽莎白的小屋那扇小小的窗户,渴望能够进入、受到欢迎和庇护相对的是,《船长与仇敌》中的吉姆对“家”的逃避和寻觅贯穿整个小说始末,却也指向他对自我和社群身份的持续性建构:母亲去世后,他投奔姨母,“住在里士满公园附近的一幢半独立式住宅里”,可是他“从来没把姨母的公寓当成家”①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12.。而当丽莎带着童年的吉姆参观自己居住和负责看管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时,他感觉像“探索非洲”一样激动②Greene Ge,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31.:“我觉得在这里比在‘那里’更快乐——比所有的‘那里’(theres)都要快乐,包括我姨母在里士满的‘那里’。”③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34.尽管“船长”和丽莎“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但我已经发现我喜欢他们胜过喜欢姨母,更不用说校长、我的舍监哈丁先生或我认识的任何一个男孩了”④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29.。吉姆对于“新家”的偏爱在于“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⑤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35.,而丽莎和“船长”与自己一样,也属于孤独的亚玛力人。
吉姆的“新家”成员因为各种奇怪的因素组合在一起:养母丽莎因与吉姆生父的情感纠葛而导致终生无法再孕;养父“船长”曾是吉姆生父的朋友,却因同情丽莎的遭遇而与其相爱,并将吉姆“拐”来以实现丽莎成为母亲的心愿。小说中的吉姆在“新家”成长的过程中承载了双重角色——“船长”和丽莎爱情的“旁观者”或“质疑者”,以及小说里“书中书”的作者。吉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格林在作品中的替身:他从小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并一直以文字的方式记录着养父母的故事。
随着了解的深入,吉姆发现养父是个多重矛盾结合体:尽管养父对他和养母尽到了一个父亲和丈夫应尽的责任,但他却是个“谎言家”(a liar)、一个“骗子”(a crook)。格林借吉姆之口曝光了“船长”通过“见不得光的勾当”积累财富的方式⑥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102.,实则也是对传统帝国历险小说中如海盗德雷克等人物殖民掠夺行径本质的揭露。养父每一次离开的“理由”都是为了积攒财富,从而能与丽莎一起过上富庶的日子。虽然他一次次离开,但“他始终会回来”⑦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78.。“船长”异域“历险”后的归来似乎是作者在戏仿《奥德赛》(Odyssey)中奥德修斯海上历险并回归家园的故事。或更像是参照笛福的《辛格顿船长》(The Life, Adventures and Piracies of the Famous Captain Singleton)中的船长最终通过组建家庭帮助其“洗刷海外掠夺的罪恶过往”,从而得以“回归国内正常生活”⑧郭然:《〈辛格顿船长〉中的金子与18 世纪英国国家身份的悖论》,《外国文学研究》2021 年第5 期,第172 页。。如果家园可以被视为一个“地方”,“它只可能是一个人的返回之地,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人总在返回的地方。这不仅是因为人类在地球上建立的家园并非仅为居住之地(栖居并非占据栖身之地)”,还因为“‘在此处’总是一种‘在别处’,它首先得通过出走才能成为可能”①转引自希利斯·米勒:《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陈旭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16 页。。这种“返回”或“回归”一方面展现了从一战“英雄的战争”到二战“人民的战争”中关于英国民族身份的一种转变——“摆脱了以往的英雄主义和官方男性化的国家命运公共辞令,摆脱了以往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大不列颠’中产阶级充满活力和传教使命的视角,淡化了帝国主义思想,从而更加的内省化、家庭化和私人化——或者用战前标准来衡量——更加的‘女性化’”②Webster W, Englishness and Empire 1939-196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9.;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主人公融入集体社群的渴求,及个人主体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因而,寻求和建构主体性及归属的经历是与重构民族意识和身份的进程紧密相连的。
“家”虽是私人空间的最小单位,“家庭空间的最深处却成为历史最错综复杂的入侵场所”③Bhabha H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13。二战的灾难性后果及冷战时期恐怖的社会政治氛围使得格林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意识到传统的家园模式已随着“闪电战”的硝烟而变得模糊,也造成了传统英国特性所无法填补的社会、文化和信仰的巨大虚空。此时,格林作品中主人公的“家园”也不再如往日那样是漂泊者历经现世的艰难之后能够让心灵眷恋和停靠的温馨闲适的港湾,因为“焦虑”和“恐惧”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关键词。情感的“疏离”成了“船长”所处时代的特征之一。
尽管思念充斥着“船长”和丽莎的人生,但“回家”似乎不仅“不能重拾想象中的美好,反而可能更加失落”④戚涛:《怀旧》,《外国文学》2020 年第2 期,第91 页。。这也是为何“船长”在敲响丽莎家门的时候甚至和初来乍到的吉姆一样都显得“有一丝害怕”⑤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26.。在吉姆记录的故事中,丽莎和“船长”的生活和爱情都是在回忆和思念中实现的。作为彼此“远方”的爱人,他们正是凭借时空上的距离感来对抗现实生活中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异化,即一种令人不安、不满、不适的“非家恐惧”,使得人们即使“在家”也感受体味到紧张的陌生感。这是一种笼罩在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之上的微妙却发自内心的骇然失其所在的空间焦虑。
新老家园的交替、“归家”和“离家”成为二战后英国人身心徘徊的一种持久状态。在《船长与仇敌》中,“船长”深受早期建立在男性气概和排除女性基础之上的英国公学制度的影响,呈现出一种“自我中心与利他主义的矛盾共存”⑥Ward P, Britishness since 187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29.。这也解释了为何“船长”始终认为自己有责任对女性负责或规范女性的行为准则,同时也为他们对意欲殖民的“落后文明”负责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因而,他对“家”有着极大的忠诚,体现在他始终承诺“归家”的叙事中。同时,“船长”又渴望“逃离令人窒息的文明以及女性家庭生活的地方”,“回归靠男性力量和劳动来获得荣誉、经受检验的真正充满男子气概的地方”,如小说中“船长”曾去往的德国、西班牙、巴拿马等地。然而,当英国人面对民族发展危机和新帝国的反向殖民时,帝国历险小说中传统“男子气概”的概念和定义遭遇冲击与瓦解,导致了个人主体内心的焦虑、矛盾、怀疑、恐惧与抵抗。
最终,在得知丽莎的死讯后,“船长”以自杀式袭击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船长”的行为使他成为双面间谍的双方力量,甚至使文学评论家伊格尔顿感到困惑,但他的选择似乎也是一种必然:作为传统美德和理想家园象征的丽莎的逝去,使得“船长”赖以生存的信仰基石分崩离析。而“船长”作为传统历险人物在当代的代表看似拥有宏大的理想抱负,但从根本上来说,他想实践的只不过是对于永恒“家园”的寻觅,只是这个“家园”因只存续于他的回忆和异域回望之中而显得虚无缥缈。
与“船长”相对的是成年后的吉姆始终将远离家园与自我放逐视为对抗“空间焦虑”和“非家恐惧”的一种表征欲望或重构自我的驱动力。从最初义无反顾地跟随“船长”离开学校和姨母的家,到成年后搬离将自己抚养长大的养母丽莎的家,再到飞往巴拿马与“船长”相聚,直至最终在其写作的小说结尾替自己,也是替格林的写作生涯画了一条终点线:“这条线意味着结束。我现在必须靠我自己了,我要跟着自己的骡子去寻找自己的未来。”①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180.吉姆的每一次成长都伴随着“离家”。与作家格林十岁时穿越那道隔开“家”与伯克姆斯特德学校的“绿色粗呢门”(the green baize door)隐喻着一场从“天真”走向“成人”的重要成长仪式相似的是,吉姆作为格林政治历险小说中的代表人物,面对内外帝国的衰亡和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经历了“从‘天真派’的传统历险转向一种新的以怀疑和质询为主旋律的历险小说模式”②Kestner J A, Masculinities in British Adventure Fiction, 1880-1915,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0, p.8.。这一成长仪式见证的不再是肯定或推崇某种男子气概的通过仪式,主角也不再是一个天真少年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符合帝国标准的绅士。纯真的逝去使得格林和吉姆发现外面的世界并非他们所想的那样,也并不像他们所读的书里描述的那样。他们目睹和见证了真实世界的样子——充斥着懦弱、耻辱、欺骗和失望。他们也逐渐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并不简单、并不勇敢,也并不总是讲真话,甚至常常被打败。在吉姆的梦中,他所追逐的骡子身上没有驮着如“船长”所描述的一袋袋金子。在他看来,“童话故事不可能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他也“从不相信灰姑娘会嫁给王子”③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68.。这种“成长仪式”使得格林历险小说中的主人公目睹了更多人性和政治的阴暗面及现代性带来的消极和负面影响,从而反思曾经的浪漫主义想象,解构了传统历险小说中帝国历险者的英雄形象,促使他们试图重构民族或文化身份与责任。
对于吉姆来说,他梦想和向往的瓦尔帕莱索的世界之所以吸引他,正是因为那里有“一种神秘感、一种不确定性以及对单调和无聊生活的远离和逃避,这一切都与普通的家庭生活恰恰相反”①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79.。吉姆的自我放逐一方面解构了以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家庭形态为典型的英国传统家园模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在后殖民主题中“永久的自我放逐成为了小说家所认为的典型的或本质上成为英国人的一种性格特征形式的最终手段”②Parrinder P, Nation and Novel: The English Novel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37.。精英阶层在心理和政治层面自信和权利感的丧失,曾经珍视的理想和信仰的逐渐幻灭,对与帝国思想密不可分的教育和道德体系的质疑,以及对失落纯真的追忆等都导致了英国人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和安全感的缺失。因而,小说中吉姆的自我身份建构并不依赖外部帝国的政治和权力之争,而是更多地关注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在历险或自我放逐中寻找和重构自我身份。格林在其小说中通过吉姆最终的选择,呼应了天主教中的堕落-救赎(the model of Falland-Redemption)思想——这里主人公通过“远离家园”或自我放逐实践一种“精神回归”的主题。
《船长与仇敌》中,吉姆一方面接受奎格利对自己的物质帮助,另一方面却十分欣赏马丁内斯上校难能可贵的纯真与和善。虽然冷战时期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被美国妖魔化而成为西方人恐惧和焦虑的来源之一,但英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格林,都试图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立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表示同情与理解,渴望英国在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时能够接受和包容两种或多种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和谐共存,呈现一种辩证、理性的态度和全面、开阔的视野。小说中,吉姆对人类美德的理想并不局限于人类的理性思维和行为能力,也不基于民族主义或种族优越感,而是带着对父辈所做选择的怀疑与质询、对既有身份和信仰的“疑惑”,以及对现实的厘清、接受或反抗,渴望通过历险的旅程探寻一种包容性的“英国特性”。
在面对奎格利和马丁内斯上校的双重谍报工作邀约时,吉姆最终选择了飞往自己梦想中的瓦尔帕莱索,正式回归和开启自己的历险旅程。而历险本身即暗示着一种反抗。克尔凯郭尔指出,“勇敢并不是没有恐惧和焦虑,而是即使害怕却依然前行的能力。冒险造成焦虑,不冒险却失去自己”③罗洛·梅:《焦虑的意义》,朱侃如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 年,第341 页。。正如使马丁内斯上校困惑不解的反复出现在吉姆写作的小说中的“金刚”(King Kong)一样,即使与全世界为敌,也仍不放弃自己追求的爱与理想。对吉姆而言,“在此处”与“在别处”、出走与返回家园、家园与世界彼此交融,成为新的共同体社群构建的基础。
小说的结尾,吉姆因奎格利对自己乘坐的飞机做了手脚而丧生,而他写作的小说却被马丁内斯上校缴获,并打算以西班牙语出版,甚至有可能获得“古巴文学奖”中的最佳外国间谍小说奖。格林曾说,“作家的作用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对其进行描述和表达”①Adamson J , Graham Greene, the dangerous edge: where art and politics mee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p.11.,以待后人评判。作家因其尤为敏感的心思和感知力对自身、周遭环境乃至大的时代背景产生强烈呼应,在对自我存在与外界的关联中上下求索,将内心的痛苦、矛盾、思考、怀疑与抵抗都倾注于作品之中,以文学叙事和文字言说的形式表征和对抗由内外因素导致的生存和空间焦虑。格林的历险小说是一种充满不安的艺术。小说主人公努力从现代性中逃离,追寻自由和理想的家园胜地。他们的生存和空间焦虑既是症候性的,也是指向抗争和疗愈的。因为,“文学文本世界不能仅仅看作是现实世界的翻版,而是要上升到一个更高层面,将文学世界看成对现实世界的质询,或是对一个更为理想的世界的构想”②金佳:《英国文学中的“花园”隐喻与共同体想象》,《国外文学》2022 年第1 期,第40 页。。
三、结语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重新洗牌,以及英国内外帝国的崩塌所带来的身份危机与空间焦虑,英国人在新老帝国交替之时审视过去的帝国统治,批判以美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殖民行径,以唤起人们的民族良知和民族历史意识。战后的英国人不仅遭遇了外部地理、社会、文化和政治空间焦虑,而且同时解构了以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家庭形态为典型的英国传统家园模式。他们自我放逐,试图从远离家园的孤立和丧失联系中体验一种充满活力的新知觉状态,以重构个体和民族尊严、重建精神家园和重塑身份认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船长与仇敌》是对英国历险小说传统的致敬,也是二十世纪后期已经式微的英国历险小说的一次回光返照。格林在小说中再现了二战后英帝国的衰落以及冷战期间世界各地的政治风云变幻和人情冷暖。格林通过以质询为主题的历险书写,致力于发掘政治、社会和文化理想与责任,因而是一种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文学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