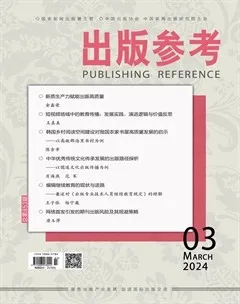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出版使命
2024-05-04王建辉
王建辉
柳诒徵曾言,“吾国史籍之富,亦为世所未有”。[1]刘洪权教授的这本《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研究》,就是研究我国史籍之富的。全书厚厚一大册,计14章,47万字,从做博士论文到申请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结项,用了十多年的功夫,厚积薄发,人过五十的第一本专著,最近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的博士生导师王余光教授,在序言中指出本书所具有的四个学术价值:一是对民国古籍出版做了系统的梳理,二是阐述了民国古籍出版的文化贡献,三是对新研究方法的吸收与运用,四是对民国古籍出版史料的发掘与利用。所论较为全面,笔者觉得除了这些学术价值之外,由于刘洪权教授曾在出版机构工作有年,对于出版的体验较为直接深入,使得这本书也极富出版专业眼光,对于当下出版也富有启迪价值,也足以弥补未从事过出版工作的研究者们亲历性缺失的某些不足。这里且与读者分享笔者看重这本著作的几个方面。
一、课题的开创性与重要性
其创新性自不待言,因为此前还不曾有这么专门而又综合的研究。课题的重要性,则来自于民国古籍出版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地位。民国古籍出版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具有续绝与新生的双重地位。作者在前面的几章指出,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以民营出版机构为主体、加上图书馆和私家共三大系统,这三大系统的古籍出版总数约27000种(含少数旧书业如扫叶山房等的古籍出版,本书有民国时期主要旧书业出版机构简况表,计含8家,第207页),其中不少是濒临死境的古稀之本,至少是珍贵之本。虽然这种统计不可能来得十分直接,主要依据各种书目,却也是一项浩繁的工作。在后面的篇幅里,作者还有专章(第十章)探讨民国古籍出版的数量与种类。民国古籍出版种数统计的意义在于,从总体上反映民国古籍出版的面目,给出一个总体的估值。依据这种统计,作者得出三个结论,一是民国古籍出版物与四部典籍总数相当,证明民国古籍出版的文化价值,历代经典在时局和社会动荡转型中得以流传,民国的古籍出版使传统文明没有断线,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厥功甚巨。二是民国古籍出版据此可分为五个阶段,1912-1919年为初始阶段;1920-1926为繁盛阶段;1927-1933年中衰阶段;1933-1937为鼎盛阶段;1937-1949为衰落阶段。三是在中西文化激荡的当口,中国的古籍文化何处去,当时的学界和出版界用自己的行动与实践做出了回答。新文化必须与古文化结合,才能在中国生根。而结合的重要着力点是古籍出版,为民众与社会提供古文化的养分,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宝贵资源。这也是古籍的新生。民国古籍的出版成为近代出版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并不是每一个时代都能做出这样的贡献。
二、古籍出版的时代机遇
作者重视这种时代的机遇性,其第二章基本上就论述民国古籍出版的时与势。尤其是本书的结语中引用了张元济的一段话:“影印之事,如果早十年,各种条件没有具备,不可以做;迟二十年,物力维艰,就不能够做。能于文化销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2]作者说,这是当事人的感受,读来令人为之叹息。张元济这句话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不能早十年,不能晚十年,指的就是时代的机遇。那一段时间,应该是1920年到1937年,前述作者的分期的鼎盛期便在这个时间段内。这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十年,也就是1927-1937年的十年。虽然作者有关民国古籍出版的阶段分期中,并未将这个十年作为民国古籍出版的一个完整阶段。为何这十年同时成为中国现代古籍出版的十年,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二层是说出版人的文化责任意识,只有善于抓住时代机遇才能实现文化使命与责任。民国出版人抓住了这个机遇。
三、方法与见解的结合
本书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延伸为国家社科课题,作为博士论文和课题研究,其第一章从出版史料、出版通史和区域史、出版机构、出版人物、出版物和印刷技术史等六个方面,对民国出版研究的状况做了梳理,既是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让自己的研究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并为学者尤其是并非学术专业的编辑人员和出版从业者提供了必要的参照。以这一部分内容和全书做对比,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在一些研究的薄弱方面拓展拓深研究的路子。
民国的古籍出版是前无古人的,因为机器文明为前人的古籍出版所不具备的条件,作者注意到了在中西文化激荡之下印刷技术的变革对传统古籍出版文化的影响,并正确地指出,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爆发式增长,重要原因在于中文印刷技术的进步,即雕版到石印、铅印的制版技术和手工到机械的印制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作者并有专章探讨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印刷技术(第九章)。技术的变革最终实现了“传统书业”到“现代出版”的转变,也让古籍出版实现了新生,总体上呈现机器印刷和商业出版结合的现代特性。此为很有见解之论,如果做一点发挥的话,新技术的采用还促成了民国古籍出版不同的整理路径,如张元济主要影印为主,以学术再现为主;王云五则主要以排印为主,以古籍通俗化为主(如《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基本丛书》等)。如图书馆等机构的古籍出版以学术为主,亚东图书馆与世界书局等则基本上走的是古籍出版的通俗化之路。
图书馆等机构是民国古籍出版的重要力量。作者鉴于民国时期图书馆古籍出版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特辟一章(第六章)作专题探讨。民国的图书馆是新型的文化机构,这些图书馆机构利用自身优势,另一方面为出版机构精选古籍版本和提供底本,一方面也刊行古籍,别树一帜卓有成效,如浙江省图书馆出版古籍,就數量和种类而言,并不逊于中华书局等商业机构。作者所统计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出版古籍丛书计43种之多,这样的古籍出版放大了图书馆的文化功能,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作者对民国出版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从章节设计就可看出作者的专业眼光与良苦用心,如对古籍出版流程与形制的探讨专设一章(第九章),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市场与读者(第十一章)、图书发行体系的现代转型(第十二章)、古籍出版的营销宣传与发行方式(第十三章)等章,更多地是从出版专业角度设计的,涵盖了民国出版领域许多重要方面和问题。在这些章节的论述中,作者时有创见,简单举其三端:其一,作者花气力论证全国性图书市场的初步形成需要政治、经济、教育、交通等各种现代要素的达成,出版机构各自的全国性发行网络作为主流模式和全国性图书市场形成有着相互关联。其二,作者对于古籍出版读者的分析也很充分,尤其是其通过有关数据分析,指出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两次预约,由士绅演化而来的传统知识精英个人订购达296户,接近保本的半数,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的订户中“官绅商学界个人”也超过了机构购书,从这些时人不够注意的简单史实出发肯定传统知识精英群体的消费能力对于民国古籍出版的市场贡献,这不失为一种独辟蹊径的研究。显然,如果没有这些订户,以销定产的大型古籍丛书是难以出版的。这一点对我正在构建的“以读者为中心的出版史”的命题也不无启发。其三,作者还通过报纸上图书广告的分析,认为出版商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是民国古籍出版者一种日常的经营行为,也是报纸广告的主要来源之一,重要的是在《申报》上的出版广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一部编年史。其同门师兄吴永贵教授的《民国出版编年史》,便主要是在充分利用《申报》等报刊广告资料上编纂成功的,是利用广告资源最充分的一项研究,可以作为这种观点的一个验证。
四、对当下出版工作的启示
行业从业者自然更会注意这方面的价值。作者在全书最末有一专节:民国时期古籍出版与当代出版业,主要意思是民国古籍出版为当代古籍出版业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作者更在绪论中做了比较明确的揭示,指出民国古籍出版对于当下出版者的现实意义和借鉴启迪,在于古籍出版的市场化机制和古籍出版的文化使命感(第36页)。这固然是到位的,不过或可做一点修正,一是这两条的先后可以颠倒一下,将文化使命作为第一条,其实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文化使命与责任,作者在绪论里非常恰当地引用了张元济相关的话,完全可以作为今日出版工作的座右铭:“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3]二是在這两条之外应加一条,就是民国高质量的古籍出版,最不可缺乏的是人的专业水平与技能。古籍整理刊印难度大,张元济晚年之所以要亲力亲为,就是“尚未得有相当之人可以托付”。就是作者也认为,中华书局在古籍出版方面较商务印书馆为后,原因之一也就是主持者陆费逵在专业素养及眼光上较张元济略显逊色。(第209页)所幸当时古籍出版三大系统从业者尤其是主要人员的深厚学养,不论是民营出版机构,还是图书馆机构,还是私家刻印,都是学有专长的人。前者如张元济、高梦旦、孙毓修等,商务《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百纳本二十四史》等古籍出版的工程巨大、精选版本、校雠精湛,书品美观,全赖张元济等的精审;中者图书馆主持者多学养深厚之人,如柳诒徵,是国学大学者,有名著《中国文化史》,在他主持下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总计刊印古籍65种之多;后者如刘承幹、罗振玉、叶德辉等,民国初年刘承幹的《嘉业堂丛书》为当时古籍出版的佳椠,为后来古籍出版效法欲与媲美,所依乃是作为藏书家的造诣。这些人或者就是民国时期的大学者,或者是大有造诣之人。而且他们之间还有深度的密切合作,力求精善,从张元济致刘承幹的信就可以看出:“敝处拟印《四部举要》(后改名《四部丛刊》——引者注),前承奖勉。草目业已拟就,谨呈上一册,伏祈鉴定。有未合处,千乞纠正。”[4]在《印行四部丛刊启》中具名的25人,堪称国内知名的藏书与大学者的大集结,他们共襄盛举更是一证。正是他们共推了民国古籍出版的高峰。在别一处,作者倒是指出了人、财、物是辑印古籍的一般条件,也是当代出版界筹印古籍的必要前提(第211页)。
还有一些是暗含的启示。作者善于发现问题。举例来说有一个《四部丛刊》续编和三编的责任问题。过去常认为无可争议的是张元济所主持,但作者找出了王云五的说法:“惟《四部丛刊》续编、三编等之继续刊行,则在余主持商务印书馆后十余年,除商承前辈张菊生、高梦旦两先生指导外,当然由余负其责任。”[5]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续编、三编到底是归功于张元济,还是王云五。作者依据《张元济年谱》的材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辨析,认为续编和三编应该是张元济主持的。这大体上站得住。不过本人倒想补充三点,一是王云五的这句话中“则在余主持商务印书馆后十余年”,不准确,续编、三编出版分别在1934年和1935-36年,王云五在30年代初期才担任总经理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哪来的十余年,如说主持商务编译所后十余年则无问题。二是王云五将张、高两先生的作用归于指导,而自己负其责任,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不对的地方是降低了他人的作用,突出了自己,对的地方是王云五不论是作为编译所所长还是后来任总经理,对续编、三编确实负有相当责任,至少规划决策与生产调度是少不了的,总不能完全抹杀。熟悉出版工作流程的人应该能体认这一点。三是这是一个好问题,对于出版界今日的操作来说,也不失有探讨的意义。
上述几个方面的把握,让作者的研究具有了一定的高度。作者又说:古籍出版,是为整理刊印古人著述的出版活动,最为依赖的是文化遗产和文献资源。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成就,赖以生长的土壤是丰厚成熟的中国古代图书文化。这样一句话讲清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古籍出版固然是为文化续绝,但必须本先有可续之命。笔者也在想,古籍的概念是在变化的,许多年后的人们会不会像民国的人们那样,来整理出版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著作,为这个时代续命。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时代能不能留下更多的优秀著作可供后人来整理出版,应该是留给学术界和出版界思考和实践的重大课题。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