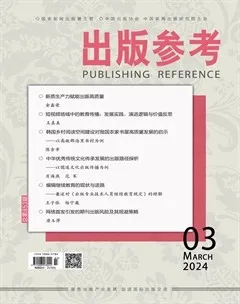出版人书信编辑实践浅析
2024-05-04崔萌
崔萌
摘 要:出版人书信,作为出版家思想与精神最集中的体现,是研究中国出版史与文化史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价值。戴文葆作为著名编辑家、出版家,曾荣获首届“韬奋出版奖”,获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戴文葆书信集》收录了戴文葆写给陈原、李中法、范用等出版界人士的书信,这些书信集中呈现了戴文葆作为出版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他的思想与编辑方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编辑工作者。本文从编辑实践出发,阐述了《戴文葆书信集》的编辑成书过程。
笔者最初见到戴文葆的名字,是在《平生六记》的书稿中,他是令曾彦修感佩的学者型编辑,更是曾彦修在特殊年代拼命为他证明清白,宁肯自己被打成“右派”也要保护的人;后来,编《范用存牍》,其中收录了两封戴文葆写给范用的信,所谈都是书、稿之事,写信时间大致为20世纪60年代。若说前两次与戴老的接触都是在书稿的一鳞半爪与只言片语间,那么这次笔者所“见”的戴文葆可谓其“自言”的一生了。
木心曾说,“信是写给别人的日记”。诚然,自传或许会因环境与心境的变化对当时的事件“虚美”或“隐恶”;回忆录或许会因为时光的流转而使记忆存在偏差,书信却不会,它是直录,是信史,是一个人一时一地的心灵镜像。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李频先生自2012年起,遍寻戴文葆书信,只为能更好地理解这位编辑家的经历、人格、职业以及他作为一代出版界知识分子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2022年5月,他将整理好的《戴文葆书信集》书稿交给笔者,这是327封戴文葆写给出版界友人的书信,从此也便开启了笔者从信札中走近戴公、理解戴公并最终将这位编辑家的书信编辑成书的过程。如何将对信札中的戴文葆的理解以及戴老的思想、精神通过书的形式传递给读者呢?笔者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一、利用注释构筑书信集丰富的意义空间
细读一封封书信,李频为每一位收信人都加了编者注,对于信中提及的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也做了注释、说明。在他看来,这是最为接近戴文葆编书路径的尝试,即“学习戴老的编辑方法编戴老的书信”。那么戴老是如何编书的呢?书信中透露着重要线索:编辑《鲁迅选集》,“正文三十万字左右,我又写了简单的题解和注释,结果发出去约八十万字”[1](致李中法信);编辑《宋庆龄书信集》,“我手上宋庆龄的八九百封信,虽经外文局等处同志译出,我还得再读一遍,人名、地名、团体名加写小注。”[2](致施梓云信)“得将全稿再从头看一遍,改正一些地方,补充某些注释。”[3](致李中法信)……《宋庆龄书信集》,共两卷,戴文葆为上卷做了361条注释,下卷做了225条注释。
编辑《胡愈之出版文集》与《胡愈之翻译文集》更是如此,在精细考查之余,戴文葆给每篇文章都加了题解和小注。做注或许就是戴文葆独特的编辑之道吧。在戴文葆看来,做注释是编辑主体性、创造力的体现,他通过注释提出新解,搭建文本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为读者打开新的阅读语境与历史情境,读者从注释中可以释疑解惑,亦可按图索骥获得更多信息,进而形成更有价值的新知识。
编者李频在《戴文葆书信集》中所做的也是如此。信件中提到的人物、事件、出版物往往只对通信双方开放,作为读者的第三人,会因脱离具体的语境觉得语焉不详,一头雾水,这就需要注释为读者打通阅读的关窍。例如,戴文葆在1991年4月14日致李中法的信中谈及:“那年写第一篇性学文章时”,李频做有一注,注释中写明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发表时的名字、发表刊物以及重要观点,同时关联到戴文葆责编的图书《性心理学》,如此,能够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信中所述事件的历史语境,以及一代编辑家在做书、评书方面敢于打破禁区,开风气之先的胆识。有时,一封短信,要三四条注释才能读懂。注释可谓这部书信集的一大特点,也是必须保留的一大亮点。
在编辑方面,面对众多注释,涉及人物的要核查其生卒年及主要经历,对于具体文章与书籍,要仔细核查文献出处,具体事件更需尽力向亲历者求证,以保证注释内容的可靠性。若遇到存疑之处,宁可与编者沟通不注,也不能抱侥幸心理错注。此外,为保证书信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除个别错字予以订正外,其余均保留原貌,一仍其旧,某些戴文葆在信件中简写或因记忆不确错写的书名与人名,亦在信件下方加编注进行说明。为区隔两种注释体例,编者做的注采用序号的形式标注,编辑做的注采用星号的形式标注。同时,在内文版式的排布方面尽量疏落有致,让读者沉浸在主文与辅文共同构筑的意义空间。
二、插图:有意味的形式
插图伴随着书籍的出现而诞生,在图书的构成元素中,图像与文字都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二者往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戴文葆书信集》的编辑过程中,插图的运用也是非常重要的编辑手段。《戴文葆书信集》中的插图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对文本内容辅以视觉上的解释、说明,以此提升读者对书籍的理解力以及图书的可读性;另外一类则是图片本身即“更有意味的图像”,能在图文互现之余开拓读者对文字以外内容的思考空间。
“编辑”无疑是戴文葆多重身份中最重要的一個。很多重要著作都是经他操刀责编的,像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以及信中多次和任桂淳教授往还探讨的书稿《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等。曾彦修说他曾看过戴文葆的审稿意见:“意见长长的,有学术根据,措辞谦逊,文辞简洁扼要,全部基本楷书,如有错字,不是划掉另写,而是另写一字或数字贴在上面,像考进士一样认真。”[4]若是能在信件之中穿插一些戴老编书过程中手书的发稿单以及他编辑图书的封面图片,相信读者对戴文葆的职业会有更直观的认识。编辑之外的戴文葆还是一位优秀的作家,1951年,巴金、潘际炯、黄裳为戴文葆出版了《中国,走在前面》《刽子手麦克阿瑟》两书,将其收入“新时代文丛”,这两部书都是其社论文章的结集;“文革”逆境之中,戴文葆更是“当束手时不甘负手”地完成了地方志作品《射水纪闻》;他增注的《板桥杂记》,虽被他自己视为“游戏之作”,却有“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托喻之感。在戴文葆赠给李频的《板桥杂记》扉页上,赫然写有:“秦淮佳丽比达观人品高百倍,往日整理扩编旧籍奉承。”这张图片穿插在信件中不禁让人抚今追昔,引发无限感慨。
对于戴文葆而言,职业角色之外还有一重身份尤为重要,那就是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老革命,著书立说,始终与社会思潮相激荡共鸣。1942年春起,戴文葆便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曾在重庆担任公开发行的《中国学生导报》主编;他还是党的秘密外围组织U.D.Y.的重要成员,晚年戴文葆依然致力于将U.D.Y.的历史整理成书出版。戴文葆赠给李频《号角与火种:〈中国学生导报〉回忆录》一书,扉页处除戴文葆的赠言外,右侧还有一行铅笔小字:“往事如梦,红岩泪下”。据李频先生讲,这铅笔小字也是戴文葆所写,想来这应是戴老对曾经历过的风云岁月的追忆吧。《板桥杂记》的扉页以及《号角与火种》的扉页插图,都属第二类,作为“伴随文本”携带着大量积极参与意义构成的因素,组合进信件文本中,共同丰富着《戴文葆书信集》的意蕴内涵。
三、装帧设计有巧思
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范用先生曾经说过,每本书有每本书的个性,装帧设计要把握书的性格,量体裁衣。如何在封面上表现《戴文葆书信集》的个性,是笔者与美术编辑着力解决的问题。首先,作为书信集,“信”的元素一定要有,而哪一封信才是打开这本书的钥匙呢?
这327封信起自1958年,直至2007年(戴文葆去世的前一年),若从时间起讫论,这本书信集应从戴文葆写给范用的信拉开序幕。1958年2月25日,戴文葆致范用一封短信:“今日下午一时许收到送下衣物,情意深重,至为感谢,衣物适度,可以自携,甚感设想周到。行期在即,到劳动现场后当即来信。今后一切均赖我自觉,望勿念念。家事均请照顾,特别是进进的教育。衣物中匆匆未见附信,想均安好。”[5]戴文葆行色匆匆,心思难定,他被划为“右派”分子,马上就要接受劳动改造了,想来,这是他临行前的一封信,是他人生面临巨变与至暗时刻对自我命运前途未卜的担忧,他对家中妻儿充满了惦念,却只怕忧虑太甚更令亲人难安,于是只能将这份焦灼的心情寄托给老友范用,请他代为照顾家中一切。信的抬头是:“鹤镛兄并请转诵娟”[6],“诵娟”为戴妻,从中更可见出这份托付的重量。这封信是整部书信集就时间序列而言的第一封信,而这也恰恰应该作为这部书信集开启阅读真正的起点。戴文葆的手书工整而清秀,以此为设计元素,为图书赋予了浓浓的书卷气。
戴文葆的人生因他的职业成就光芒四射,却因在特殊年代所经历的非人生活苦难丛生,然而他在信中并没有过多地讲述苦难,相反,他更愿意谈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读书生活、编的书稿、写的书评,以及特殊经历下思想的淬炼与蜕变,绝非自怨自艾的灰暗色调。故而,在封面颜色的选择上,笔者与美编一致选择了米白色。这样,封面与内文纸的米白形成了呼应。纸上印有斑驳的纹路,这纹路既像石纹又像水纹,纹路下方的书信手稿若隐若现,像大理石上的碑文,也像水纹冲刷过后依然磨灭不掉的印迹。摩挲着封面,在习惯了键盘敲击的今天,这些斑驳却充满深情的字迹,让我们恍若看到那个年代,一个老编辑家踽踽前行的身影,有关他与书的一切徐徐展开。
《戴文葆书信集》是以书信的形式,对编辑家及其从事的编辑活动进行梳理、研究的一次探索实践,同时从内容编排、编辑方法以及装帧形式上都尽可能地启发着编辑学界以编辑家为个案辐散整个编辑史及文化史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单位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