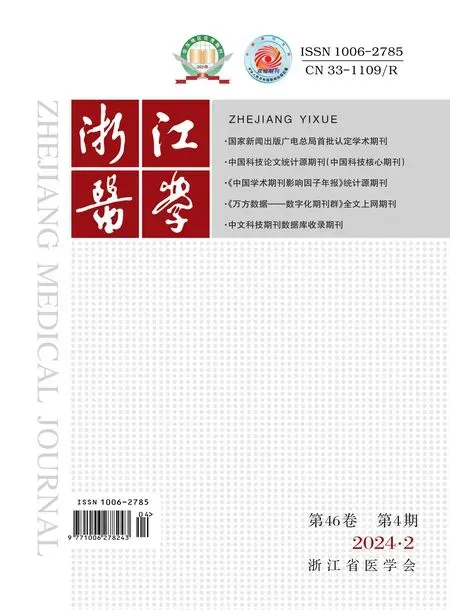肥胖影响乳腺癌发病的机制研究进展
2024-05-03阮慧邓显光范洪桥刘丽芳
阮慧 邓显光 范洪桥 刘丽芳
乳腺癌是目前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1],患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威胁女性身体健康。肥胖是指由遗传和环境等多种因素引起的体内脂肪堆积过多和(或)分布异常的慢性代谢性疾病。BMI 作为世界公认的肥胖程度判断依据,尽管无法准确反映体内脂肪含量,但由于计算简便,因此被广泛用于肥胖的相关研究[2]。世界卫生组织将BMI 25.0~29.9 kg/m2定义为超重,≥30.0 kg/m2定义为肥胖。近几十年来,全球肥胖率显著上升,有超过三成的人被定义为肥胖或超重[3],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数据显示,1992 年至2015 年,中国超重率从13%上升到30%,肥胖率从3%上升到12%[4]。对乳腺癌发病机制及流行病学特征的研究发现,肥胖是乳腺癌的重要危险因素。一项Meta 分析显示,与正常体重乳腺癌女性相比,肥胖乳腺癌女性的复发或死亡风险增加了约30%[5]。肥胖患者通过体内非正常水平的瘦素、脂联素、胰岛素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雌激素和肠道微生物群等多方面影响乳腺癌的发生及病情进展。本文就肥胖影响乳腺癌发病的机制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乳腺癌的防治提供参考。
肥胖患者体内的白色脂肪细胞经历肥大和增生,发生病理生理变化,包括游离脂肪酸(free fatty acid,FFA)和TG 水平升高、血糖升高和胰岛素抵抗等。肥胖状态下,脂肪组织会产生炎性细胞因子,如TNF-α、IL-6、IL-1β、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TGF-β)等。这些分子具有重要的局部和全身作用,可能通过对肿瘤上皮细胞的直接作用和对肿瘤微环境的间接影响从而影响乳腺癌的进展[6]。具体分述如下。
1 瘦素和脂联素
作为脂肪细胞的衍生因子之一,瘦素的循环水平与BMI、体内脂肪储存总量相关,被广泛认为是肥胖影响乳腺癌发生、发展和转移的关键驱动因素。研究表明,较高的血清瘦素水平与侵袭性恶性肿瘤存在关联[7],瘦素在癌导管附近正常乳腺组织中高表达,而在健康者乳腺组织中表达缺失,表明瘦素参与乳腺癌肿瘤发生的早期阶段。瘦素与瘦素受体结合可激活几种信号通路,包括Janus 激酶信号转导器(just-anotherkinase,Janus kinase,JAK)/转录激活剂(signal transduction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信号、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细胞外信号调节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ERK)、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PKB,又称Akt)信号和细胞因子信号通路的抑制因子,从而促进癌细胞存活、增殖和转移[5]。瘦素在乳腺肿瘤微环境中通过影响癌细胞以调节内皮细胞的迁移、血管生成、巨噬细胞表型和功能以及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聚集。同时,瘦素与细胞因子的相互作用也会影响乳腺癌的进展[8]:瘦素作用于肿瘤细胞和肿瘤基质,分泌炎性细胞因子,如IL-1、IL-6、TNF-α 和生长因子。虽然肥胖通过血清瘦素水平的变化来影响乳腺癌发病的潜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但目前可以确定瘦素可通过与多种因子和信号通路的相互作用并塑造利于肿瘤生长的微环境,以促进乳腺癌的发生和发展。
脂联素是一种由健康脂肪细胞产生的抗炎脂肪因子,循环脂联素水平与BMI 和体内脂肪总量呈负相关。脂联素可通过调节多种细胞分子机制来诱导乳腺癌细胞死亡和生长停滞,例如细胞自噬、炎性小体激活以及瘦素和雌激素驱动的致癌信号[9-11]。脂联素还通过激活单磷酸腺苷活化蛋白激酶(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MAPK 以及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的受体α 途径以此阻断瘦素信号传导[12]。此外,脂联素还可诱导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阳性和阴性乳腺癌细胞通过降低细胞内脂质含量来触发细胞中的脂筏破坏和凋亡。研究发现,脂联素还通过下调乳腺癌细胞中的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1(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binding protein,SREBP-1)抑制脂肪酸合成和激活乳腺癌细胞中的脂肪自噬来诱导脂肪分解[13]。与瘦素相比,脂联素具有抗炎作用,在乳腺癌的发生和病程进展中具有保护作用,但脂联素在炎症和免疫中的确切分子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2 胰岛素
胰岛素由胰岛β 细胞产生,主要负责葡萄糖摄取和储存,还参与其他细胞活动,如细胞生长、增殖和分化以及蛋白质和脂质合成等[14]。研究表明,脂肪分解抑制是胰岛素最敏感的代谢作用,高于正常水平的空腹胰岛素水平可显著抑制脂肪分解并促进脂肪细胞生成脂肪,从而导致肥胖[15]。胰岛素可以通过直接作用于上皮组织或通过影响其他调节剂的水平,如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s,IGF)受体、性激素和脂肪因子,间接促进肿瘤发生。正常人体内胰岛素与胰岛素受体结合并激活细胞信号通路,从而调节细胞稳态。而肥胖患者体内胰岛素释放增加,与胰岛素受体结合并激活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s-1,IGF-1)信号。胰岛素结合促进胰岛素受体和胰岛素受体底物(insulin receptor substrate,IRS)的酪氨酸磷酸化,IRS 使PI3K 依次磷酸化并激活下游Akt/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信号传导[16]。研究发现,乳腺癌女性患者血清中IGF-1 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受体(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s-1 receptor,IGF-1R)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女性[17],胰岛素和IGF-1 与其受体结合(胰岛素受体,insulin receptor,IR/IGF-1R),导致下游磷酸化级联反应,激活PI3K/Akt/mTOR 通路和MAPK,从而驱动癌细胞增殖、侵袭和转移[18]。胰岛素信号传导与乳腺癌发病存在一定联系,胰岛素可激活多种侵袭性乳腺癌的细胞信号传导通路。
胰岛素抵抗在临床上被定义为一定浓度的胰岛素发挥低于预期的生物效应的状态。肥胖患者的脂肪组织经历重塑,可分泌多种炎性细胞因子诱导胰岛素抵抗,在此过程中巨噬细胞浸润脂肪组织并分泌多种促炎因子引起胰岛素抵抗[19]。IGF 通过自分泌、旁分泌和内分泌等多种方式促进新生血管生成和加速细胞有丝分裂,从而为肿瘤细胞生长提供营养和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促进了乳腺癌的病程进展和转移,并增强了癌原发灶和转移灶之间的相互作用[20]。相关研究表明胰岛素抵抗通过多种分子机制和细胞通路间接影响乳腺癌发病与病情进展,但胰岛素抵抗与乳腺癌患病风险之间是否存在直接作用的潜在分子和细胞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3 胆固醇
胆固醇作为一种脂质分子,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类固醇激素、胆汁酸、维生素D 和氧甾醇等多种激素的前体,是细胞生长、繁殖的关键分子,在细胞信号转导中起关键作用。癌细胞等快速分裂增殖的细胞需要大量的胆固醇合成细胞膜,而高水平的循环胆固醇为细胞增殖提供了必要条件。有研究发现,肥胖患者体内血脂代谢异常,通常表现为HDL-C 水平降低和TC 水平增加[21-22]。尽管还未有直接证据证实胆固醇与乳腺癌发病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但实验结果发现LDL-C 是乳腺癌发病的危险因素,低水平HDL-C增加了乳腺癌发病风险[23]。另一相关研究显示,高TC水平(≥4.14 mmol/L)与女性乳腺癌发病呈正相关[24]。氧甾醇27-羟基胆固醇(27-hydroxycholesterol,27-HC)是胆固醇影响乳腺肿瘤生长和发展的关键调节因子,其机制可能是27-HC 可作为ER 调节剂促进ER-α 受体阳性肿瘤的生长,并作为骨髓免疫细胞中的肝脏X受体配体建立免疫抑制程序[25],因此靶向干预胆固醇摄取并转化为27-HC 可能成为未来治疗乳腺癌患者的良好策略,可待进一步研究。乳腺癌确诊前的高胆固醇水平可以有效预警以阻止肿瘤的发生、发展,因此临床提倡使用他汀类药物来抑制胆固醇活性代谢并降低乳腺癌发病的风险[26]。尽管目前TC 水平对于乳腺癌发病的影响仍有争议,但可以确定胆固醇与乳腺癌发病存在潜在联系,有待进一步研究并构思针对性的抗癌方案。
4 雌激素与ER
雌激素在人体许多生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包括调节能量代谢、应激反应、矿物质平衡以及性发育等。肥胖患者的脂肪组织代谢活跃,芳香化酶分泌增加,合成大量雌激素而导致体内雌激素水平上升。过多的脂肪组织产生过量雌激素被普遍认为是导致肥胖合并乳腺癌女性患者预后不良的可能原因。雌激素主要通过与ER-α 和ER-β 两种受体相互作用来发挥作用。ER 是乳腺成熟和女性生理活动(如青春期和怀孕)的基础。研究显示,雌激素增加乳腺癌发病风险可能与ER 介导的细胞生长和增殖有关,原因在于雌激素能够刺激编码不同生长因子的基因的表达,雌激素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活化代谢物形成的DNA 脱嘌呤化合物以及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可能在乳腺癌的发生中起到关键作用[27]。肥胖患者血清雌激素水平过高时,性腺类固醇激素的促增殖效应可能会导致细胞复制错误,从而导致细胞突变和乳腺癌的发生、发展[28]。乳腺正常发育过程中,雌激素起到刺激上皮细胞增殖和导管结构形成的作用,但当与受体ER-α 或ER-β 结合时可发生构象变化,产生受体二聚化并转移至细胞核中,与雌激素反应元件结合形成具有活性的ER 复合体,并因此促进乳腺癌细胞活化和增殖[29]。ER 与多种分子和细胞信号传导通路之间相互作用,如低氧诱导因子(hypoxia-inducible factor,HIF)、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 system,RAS)/Raf 蛋白激酶(Raf protein kinase)/MAPK 信号传导通路、PI3K/Akt/mTOR 信号传导通路和细胞瘤病毒癌基因(cellular-myelocytomatosis,c-MYC)转录调节因子等,进而影响乳腺癌的发病机制[30]。雌激素在诱导乳腺肿瘤发生、发展中有重要影响,肥胖患者脂肪组织产生的过量雌激素成为乳腺癌发病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雌激素及其受体通过多种作用机制影响乳腺癌进展,但雌激素与ER-α 和ER-β 是否各自独立作用仍有待研究。
5 肠道微生物群
人体内存活的多种菌落共同构成微生物群,通过和宿主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人体生理功能和健康状况。大部分微生物集中在胃肠道中,在肠内外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微生物群中不同菌落存在重要的个体差异而又相互关联,它们能够保护人体免受病原体的侵害,促进人体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以及免疫系统的生长发育,但同时也成为疾病发展的潜在决定因素[31]。研究发现肥胖患者肠道微生物群与健康人群存在差别,肥胖患者肠道生态失调与肠道内多种微生物菌群增加有关,肠道菌群失调可能改变胃肠道内肽的分泌,影响饱腹感而导致食物摄入量增加,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加剧肥胖[32]。肠道微生物群通过菌群产物调节肠道细胞产生的旁分泌信号分子来激活肠内分泌细胞。研究显示绝经后女性患者合并肠道菌群失调,其雌激素代谢水平发生变化并因此增加乳腺癌患病风险,而这一作用的机制可能是肠道微生物群诱导慢性炎症,干扰宿主细胞增殖和凋亡造成的[33]。此外,一项关于乳腺癌患者肠道微生物的研究表明,患有乳腺癌的女性表现出更多样化的肠道微生物,证实肠道微生物生态失调与乳腺癌之间存在密切联系[34]。
6 小结
肥胖与乳腺癌发病风险密切相关,是乳腺癌发生、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近年来关于肥胖和乳腺癌发病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肥胖可能通过瘦素、脂联素、胰岛素、雌激素、胆固醇和肠道微生物群等多种作用机制影响乳腺癌发病,各种分子机制和细胞通路相互串联、共同作用。现有多项研究已基本阐明肥胖影响乳腺癌发病的几种重要因子的潜在作用机制,但部分机制和结论仍存在争议。肥胖影响乳腺癌发病的作用机制研究日益深入,但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目前已知的肥胖对乳腺癌的作用机制是否能为不断增加的乳腺癌肥胖患者提供健康管理信息,是否可以根据已知的相关作用机制提出新的乳腺癌针对性治疗方案值得深入研究。因此,后续研究应就存在针对已知分子机制和细胞通路的药物或生活方式建立精准干预,从而来降低肥胖人群患乳腺癌和病情进展的风险,并提高乳腺癌患者生存率。此外,乳腺癌存在多种亚型,不同亚型乳腺癌形成的肿瘤微环境具有明显的差异,肥胖作用于不同亚型乳腺癌的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并寻找新的针对性治疗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