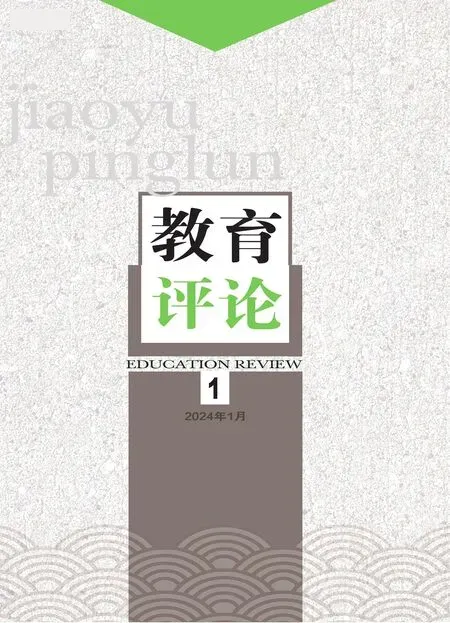王充以“实知”为中心的学习观述评
2024-05-02张惠娟
●张惠娟
一、问题的提出
西汉武帝时期(约公元前135年左右)确立了统一思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家经学教育成为此后两汉学校教育内容的主体,是学生从学校走向政治仕途必选之捷径。读经、考试、做官的教育模式自此基本确立。通晓儒家经典的数量、质量一度成为太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和人才选拔的衡量标准。在以竹简书写为主的时代,儒学经典的学习特别依靠教师逐字逐句的文字解读和释义引导,师说口传必有讹误,而考试的规范性进一步提出了经学从版本到释义内容的权威性、合法性要求。从汉武帝为太学设置五经博士至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官学的经学讲义逐渐有了国家认可的师法、家法之宗派源流。学生考选并通过五经中的一门即可为官入仕的方法,极易造成学习内容的窄化、碎片化,以至于破坏五经学习内容原有的丰富性、贯通性、完整性,导致学校教学日益唯书、唯师、唯考试,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成风而不自省,批判思维、实践能力的人才培养目标被日渐遮蔽和悬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针对西汉以来师法、家法众多引发章句之学(经学讲义)的繁杂歧义、浩繁支离之沉疴,以及朝野间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话语主导权之争,朝廷聚集学界经学大家召开白虎观会议,“议欲减省”,即精简学校经学学习内容。史臣班固根据会议观点和精神主旨编撰完成了10卷本《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主要选择与社会生活、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43个条目进行了释义简化,实际属于简明版的社会辞典、工具书类的性质。白虎观会议的核心成果是在东汉谶纬迷信之官方哲学的合理性问题上达成了学术界思想上的一致。因此,形而上学、教条机械的不良学风、教风无法在根源上得以矫正,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会议目的也无从真正实现。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朝野动荡、人口迁移南北各地,面临不确定的社会现实和生存困境,多元、求实、个性的教育需求和教育选择才逐渐打破狭隘、空泛、教条的儒学独尊的教育格局。
生活在奉行“以图谶为上”观念之东汉初年的王充,青年时期求学于乡野精舍大儒、亲炙于长安太学名士,读书过目不忘、学养丰富,能博通九流百家之学说。面对学校、社会流行的迷信守旧、谶纬狭隘的不良学风,少时有“以农桑为业”“以贾贩为事”生活经历的王充,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理论武器,以实事“疾虚妄”的批判精神撰写《论衡》(共30卷85篇)一书,以期社会在思想上认同“立真伪”、分真假,国家在教育上做到“辨伪以求实才、存真以利世用”,求实知、重实践的学习观成为纠偏教育时弊的关键议题。
二、以“实知”为中心的学习观
在学习观方面,王充秉持儒家“学而知之”、学以致用的学习传统和教育精神,否定“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主张“学之乃知”、不学不知,强调学、思、行三者连贯统一的学习过程,力主学校回归实学实才的育人本位、回归儒家济世治国的立学设教之初衷。其以“实知”“效验”为中心的学习观主要包括学习的作用、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方法等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变异故质”的学习作用
“学之乃知”“不学不成”。一个人的天赋、环境固然有先天性不足,但绝大部分是能够通过后天的环境创设、教育训练引导而获得积极改善。“其善者”,仍需“养育劝率,无令近恶”;“其恶者”,则需“辅保禁防”、渐积磨砺、骄节屈折,“令渐於善”。[1]人兽有别,人在根本意义上是社会性存在,必须通过社会化学习才能完成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换和生成;一个人贤愚与否的关键取决于后天的教育引导,“在化不在性”“彼蓬之性不直,纱之质不黑,麻扶缁染,使之直黒。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也”[2]。王充相信,纵然人性在源头上因禀“气有多少”而确有善恶聪愚之秉性差异,仍然可以依靠唤醒、修正、加速生长的外部教化力量的“渐渍之力”,潜移默化之间,“习善而为善”“简练其性”“雕琢其才”,并通过个体切己的践行、反思逐步实现“变异故质”“反情冶性”“尽材成德”。
成人和成才是教育的两大基本功能。在王充的时代,阻碍教育功能实现的两大流行病是虚饰教条的教风和空洞无用的学风。东汉前期,官学推行以固守师法、家法之权威文本的教学标准和考试答案,权威至上的教风终日里抱残守缺、纸上清谈,书本考试至上的学风倾向于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师生也习惯于“照着讲”、照着背,人云亦云,“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3]。其错误的根源是学人缺乏求真、较真、求实、务实的思考力、辨别力、批判力。学习发生有效作用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学习者能够独立思考,“精而思之”、辨善恶、分真假、有实知、“疾虚妄”。读书学习绝对不是浅表层次的“诵读”和复述,文字的记忆如果不能和分析、辨别、批判等思维能力结合、贯通,不能做到联系实际、追根究底、举一反三、闻一知十,那么抽离了主体能力真实生长价值的记忆资料不仅是空洞的、无效的,而且是无意义、无效能的学业负担。
学校教育里面,教师照着书本讲、学生照着书本观点复述的无效能学习现象,中外古今的教育史上,实则屡见不鲜,如欧洲中世纪盛行过的经院主义教育习气,陶行知批评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教育问题等。学而不知、学而不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虚掷了知识生成情境固有的特殊性、条件性、偶然性,尤其是抛弃了学习过程中具有能动意义、创造意义上的主体自我,掩盖了学习赋能与人真实的生长价值、智慧发展的教育本质,失真的学习效果就是学习者核心能力发展的表面化、虚假性,如死记硬背、食古不化、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当学习不能促成个体发生增值赋能的发展实效,成为学校教育一种集体性育人的弊病和痼疾,社会将因此失去发展必需的智力、创造力的动力支持。
(二)求“实知”的学习过程
“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4]依据学、思、行三结合的儒家学习过程论,王充认为学习开始于“学知”,中经“黜其伪”、辩真假的思辨活动,结果是在“实知”“效验”,这是一个从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三连贯通的发展过程,呈现出继承性、批判性、实践性为基本特征的学习品格和学习要求。
首先,“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5]“学知”的内容必须广泛,可以不限于五经典籍,兵家、法家、医家、农家等都可以也应该学习。若一个人知识面狭隘单一,则如死枯的动植物一样“气不通”,就会失去盎然生机和生长动力。博学能够滋养和唤醒个体的潜能,能够建立起个体与广袤世界的积极联系,博通连贯“天下之事,世间之物”,类似打通了个体社会化生命的任督二脉,触类旁通、合纵连横,广博而不孤陋、系统而不琐碎、实事而不虚浮。王充将汉代的知识分子分为儒生和文吏两种类型。“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学者,事也。”[6]道、事两个部分,既指具体做事的知识技能需要学习,也指儒家治国理政之道也需要学习,所谓道本事末、“道行事立”、事不如道。理论知识、实用知识的地位高下之别,在中国一般认为是源自先秦时期的孔子。在王充的时代,他对“道”的强调,不代表对“事”的轻视,而是主张“道”和“事”的结合,因为人能弘道、“道在事中”,“道”的彰显与否关键因素是行道之人的主体自觉和主体能力。“为道”的吏“事”在实践过程中,往往缺省了践行儒家治国之道的价值追求、道德品格。“夫德不优者,不能怀远。”“道”的遮蔽隐没且“无益”和“事”的急功近利而有效,不仅意味着推崇文化修养、人文关怀的儒家文化内涵的严重缺失,而且存在失去国家以儒治国、以儒化民的教育本位和立场之可能性。
其次,“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7]。所谓“虚妄之言胜真美”,学习者如果只凭耳目观察、道听途说、书本议论,极其容易惑于虚象假象、望文生义、遑论是非。因此,需要“观文之是非”“论文以察实”,其核心方法是要“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既要有心知的证实,也要有事效的证实。一方面,“不徒耳目,必开心意”[8]。闻见之知是重要的,但不能是没有结构、杂乱无章的“无所状”,而应该具有明确清晰的事实依据、因果关联和逻辑理路,即能够“据象兆,原物类,原理睹物”,在事实实物清楚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因果性、关联性的结构性逻辑分析,达到明确的知道而非知道的模糊不清。另一方面,有理有据的闻见也并非“实知”。“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文繁说,众(终)不见信。”[9]在如何“丧黜其伪”“存定其真”的认识问题上,先秦时期的韩非子提出“参验”类比的方法、荀子有实事“证验”的方法,王充认同并继承发展了墨子的“三表法”,提出了“类验”“效验”的方法,且注重历史经验借鉴,“放象事类以见祸,推原往验以处来事”。这种思维方式类似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即在相关资料、物证基础上,独立思考、逻辑分析和论证推理,别真伪、辨是非,发现合乎逻辑之真、实践之效的问题解释、解决的理论支持和方法依据。王充的“实知”不是要求孤立的事实证据证实即可,也不是停留在简单的知识复盘、还原,而是要做到“揆端推类,原始见终”,古今结合、慎思明辨、类比推理、辨证分析。“以心意议”“以心原物”的主旨,突出强调了比较、概括、推理等心智训练的学习价值和教学意义,以心知之、以心证之、以心信之、以心实之。王充有浅水见虾、深水见鱼、极深处见蛟龙的由浅入深的认知层次差别的比喻,隐含学习有必要从浅层认识走向深层觉悟的发展指向和积极要求。
最后,“人有知学,则有力矣”[10]。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人们必须通过后天的教育习得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生活能力、生产能力,学习不能是空说不练、知而不行。“学贵有其用”,既是对知识内容有用性的要求,也是对学习者实践能力的要求,评价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不能只看其纸上的笔墨功夫如何,还要“以事效考其言”,即要有实践能力的考核。如一个人入山见木、入野见草,其长短大小无所不识,却没有能力亲自动手“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即为博学无益。如学者的知识生产、著书立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11]。通览群书、集思广益的学习目的和价值,不是让人变成一个蚂蚁搬家似的“匿生书主人”、一个送书信的“邮人”或传令的“门者”模样,只会鹦鹉学舌之言语而没有了自我主张、创新和实践能力。会做事、做好事、做成事是读书学习的结果性要求,做成一件事“谓之巧”,做成百事“谓之良”,学习应如“良医服(用)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病;大才怀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乱”[12]。
(三)实学、专一、极问的学习方法
首先,学习者应该勤学、实学、积学。王充指出,每一个人在事实上确有天资和智力上的一些差别,但是不学不成、不为不能,大多数的人具有智慧潜能,有从无知到实知、且“知能十倍”的学习潜力。但凡一个人“好学勤力”,能够持之以恒、踏踏实实地勤学苦练,“日(目)见之,日为之,手狎之”[13],以铢积寸累之功而不是一暴十寒,反复练习、做中实学,如“干将之剑,久在炉炭,铦锋利刃,百熟炼厉”[14],自然就可能做到事“无不能”、技“无不巧”。王充曾以粟、臼粟筛糠、上锅蒸煮的饭食制作经历类比学习,指出学习也需要任务选择、去伪辨真以及足够时间的积累、思考、内化,不可能短期速成。他还以枫树生长快但木质不坚固、檀树生长慢但“其材强劲”为喻,论证了一个人在学习上更多的是要循序渐进、日积月累,而不能期望可以一时速成,因为拔苗助长、“轻躁早成”的教育结果,极可能是适得其反的虚假繁荣,如“肉暴长者曰腥”“酒暴熟者易酸”“其进锐者,退速”[15]。
其次,学习的专注力很重要。“学贵专一”,学习时的心态要一心不能二用。“干将之利,刺则不能击,击则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16]干将这种有名的宝剑虽然有很多功能,但不能同时用于刺杀和锤击。因此,即使学习者有很多的能力和兴趣爱好,在学习过程中,也要根据某项学习任务的特殊性、时效性,有针对性地选择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专心致志,集中注意力进行专门的问题研究和解决。
再者,学习活动要能够“极问”。两汉太学有考试选拔太学生直接入仕为官的权力,容易导致以仕进为求学、教学第一目的的教育短视,“怎么考就怎么学”,即使标准答案是“随旧述故”,也无暇去“考实根核”、质疑批判,盲从前师、无我之见的学术懒惰渐成大势所趋。“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17]面对机械教条的学习风气、随波逐流的学习者、教育者,王充明确反对无原则地“信师”,提倡“师弟子相诃难”,但凡圣贤之道里面有讲得不够清楚明白的地方就应“问以发之”,如有不能尽解其义的地方就应“难以极之”。“激而深切,触而著明。”师生间、学生间的问难质疑既是独立思考开启的关键环节,也是破除学习者的权威依赖心理、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思维、训练自主学习能力和习惯不可省略的阶段。
最后,学习者“欲极道之深,形是非之理”,须坚守学术求真之立场,从道而“距师”。“距师”的“距”有两层含义:一是距离。师生存在学术传承关系,但学习者不必一味模仿老师而丧失学术自我,姑且不论学生能否完全仿效教师,即便学生和教师在学术思想上完全一样,恐怕也算不上是成功的教育。二是抗拒。学生能够据理反驳学术权威,修正硕儒名师的学术错误和思想偏执。“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18]任何的学术观点都有问题场域、学术旨趣、知识局限等限制,不能简单地奉行拿来主义而不知所以然。“从道而距师”,根本上是要求学生不可拿经书讲义当作得官获利的敲门砖。精神上如果不被章句之学、宗师门派绑架,就不会失去抗拒世俗虚名的勇气,就能够以追求学术真谛的志向为内在指引,加之具有的抽丝剥茧、求真务实的研究方法和能力,以至“核道实义、证定是非”。
回顾历史,常能看到许多惊人的同声相和。譬如,春秋末年孔子倡导的以道择师、“当仁不让于师”的师生观,战国的荀子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习创新见解,唐朝的韩愈提倡“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师生关系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同样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无外乎在真理面前,力主学习者远离功利的学习目标、笃信“从道不从师”的学术精神。2000年前王充 “从道距师”的发声,既可以看作对先秦以来平等、尊重、质疑、求异为特征的儒家师道观、教学观的认同和继承,唯道是从而非唯师是从,也揭示和批判了东汉初年教育场域存在的浮躁、功利、教条等教育积弊的内生性原因在唯利是图。
“不当而是者,吾贼也。”王充在约2000年前还注意到世人存有的一种狭隘的社会心理,若唯利是图必投其所好。倘若学习者存在唯师是从、投师所好的自我缺省行为,教育者有时也会出现唯生是从、投生所好的学术自戕行为,如“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19]。教师为刻意迎合学习者的娱乐化学习心理,而制造夸张浮华失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实际上属于无意义、无价值的表演学派,表面“可爱”实际并“不可信”。
三、反思与讨论
王充的学习观包含博学、实知、实事等内容,批判章句之学的片面狭隘、强调知识学习的多联融通,批评功利性学习的浅表认知、强调思维力训练的深度学习,批评文字之教的空泛虚象、强调学以致用的社会实效,具有重申学习行为固有的生长、生效、增值、增质、利生、利世等发生学意义的内在意蕴和功能指向,既是对学理之实、逻辑之真、实践之能等学习本真价值的进一步的主张和表达,也是对东汉初年学校教育过程中失真、失实、失能状态的某种矫正和修复,倡导了由死守章句之教走向博学、“贵是”、实行的教育教学新方向。[20]
历史地看,尊重和遵循教学规律、学习规律的教育要求,在实践层面上常常表现为对于偏离规律、错位失真教育行为的不断纠正、对于教学生态系统不断重构的一个反复而漫长的过程。历史、逻辑、实践三者的多维碰撞、冲突、耦合,的确是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基本变奏和永恒图景。教育历史的持续性回顾和审视省思的目的,不是为了复旧守旧,而是履新创新。2000多年前的两汉,学校经学教育偏重学生的读书、背书、考书,而失于重视学生批判思维、实践能力的引领训练,在很大程度上与考试做官引发的泥古守书、偏重章句的教风、学风不无密切的关联。南北朝时期造纸术逐步广泛使用,纸质书逐渐取代了繁重的竹简书,学习者有机会对不同经学文本、释义著作展开比较、辨别和分析。社会动荡转折时期的清谈误国、实学有为的思想共识和教育选择,加速了两汉以来盛行的教条僵化、空疏无用之学风、教风的没落。[21]但是,后虽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以至现代,虚饰空泛的学习弊病、教育痼疾依旧间或更迭出现,固然因为历史绵延和赓续,该问题呈现出不同时代教育之不同的社会文化成因,以及不同的教育话语表达方式。不可否认的是,不断重申以智慧学习、实践学习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教学改革命题,仍是学校教育面对的基本主题和主要任务。学习质量问题不断被批评、被重申的原因之一,源自于传授书本知识是学校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就有别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主要任务。书本知识只是以文字符号的抽象性表意真实事物的间接经验,但不代表事物的真实性,耳目之见、文字符号的浅层了解不等于是深度认识,更不可能直接生成真实的做事能力、实践智慧。“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22]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有类似王充观点的另外一段解释:“总有一种危险,即我们所用的符号并不真正具有代表性,代表事物的语言媒介不能唤起不在目前的和遥远的事物,使之进入目前的经验、符号本身却变成目的。正规的教育尤其面临这种危险,其结果是,因为有了文字,通常称之为学术的咬文嚼字的风气常常应运而生。”[23]关于此学校教育痼疾的解决方案,杜威主张以“活动”对“书本”,王充则以“实事”对“虚妄”。无独有偶,古代的王充和现代的杜威都明确地回到个体学习的功能性价值深度而真实生成的根本方向上,回归社会生活的真实需要、回归学习的真实能力生成,这也是有史以来教育破解学习质量中功利、教条、空洞、虚饰之遮蔽的基本路径选择。
概言之,王充的以“实知”“效验”为特征的学习观呈现出的知识学习的广度、思维的深度、实践的社会适切性等功能性要求,对当下教学仍有启发意义。其一,有效拓宽学生知识学习的宽度和广度,重视学科融合贯通的教学价值。其二,提高教学过程中的思维训练品质的深度要求,重视学生怀疑、批判、分析、综合等思考力的培育。其三,加强学生学以致用的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注意引导学生经纬天下、济世利民的社会服务理念和学习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