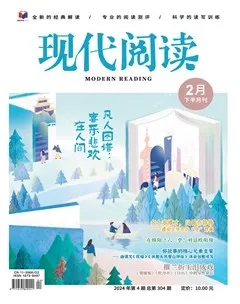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2024-04-29梁开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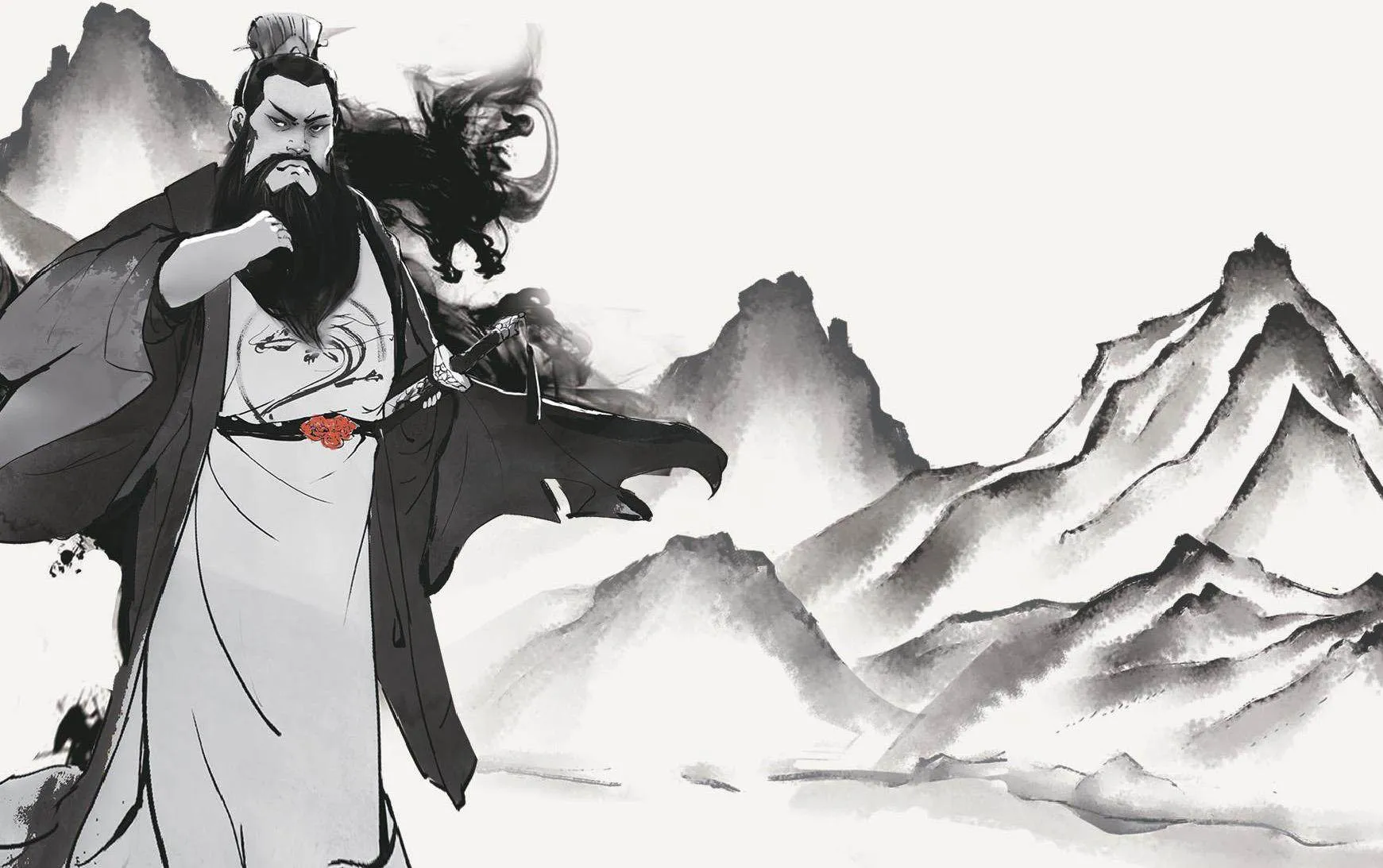
关于曹操《短歌行(其一)》的创作时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通常认为是在赤壁之战前后。此时的曹操已是半百之人,尽管“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人生易老,时不我待,其诗在慷慨之中自然添了几分悲凉之气。功业未成,只因人才难得,作为政治家和文学家的曹操便借这一首求贤歌,表达自己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宏愿。
感慨人生苦短
这种感慨寄于歌,寓于酒,一开篇便营造了浓郁而低沉的抒情氛围。清人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中对此作了精辟的评说:“截断已过、未来,只说现前,境界更逼,时光更迫,妙传‘短’字神髓。”不错,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看出“短”来,我们才能深入堂奥,与诗人的心志同频共振,这是诗人意绪的起点,也是整首诗的情感底色。
曹操《短歌行(其一)》属乐府旧题,继承了乐府诗的精神气质。“朝露”的比喻,在乐府诗中不止一次出现过。《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就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的诗句。而在《龟虽寿》中,曹操也有类似意思的表达:“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宗白华《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逝者如斯,人生无常,这样动荡不安的时局,最容易唤起人们对有限与无限的感喟,也最容易激发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追问。
岁月如朝露,人生是一场永不回头的旅程,“去日苦多”于是成了一种最普遍的感受和最无奈的情愫。这里的“苦”,不是“痛苦”,而是“苦于”,“去日苦多”的意思是已经过去的时光一天比一天多,未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少,“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曹操《精列》),怎不让人扼腕叹息?!在永无止息的时间长河里,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逢困厄和不幸,使命越大,责任越深,这或许是生命的本质。只有对酒当歌,走出时间,那种“不可断绝”的忧思才会结束。
抒发纳贤豪情
人之不幸在于我们控制不了生命的长度,人之有幸在于我们可以决定生命的厚度与力度。即或如露,我们也可以让生命绽放出耀眼的光华。对曹操而言,建功立业便是他生命的存在方式。而建功立业的前提条件是招贤纳士,让“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于是,他先后发布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而《短歌行(其一)》实际上就是一曲诗歌形式的《求贤令》,感怀之中,潜伏着诗人积极的政治目的,这也使得诗人之“忧”,不再只关乎个人,而是被赋予了更为深广和崇高的意义。
曹操为了巩固在庶族地主中的统治基础,积极打击地方世袭豪强势力,加强集权,大力提倡“唯才是举”。他在《求贤令》中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一千八百年前的曹操,在这里展现了一代枭雄的特立独行,他选贤拔能的标准是将“才”放在首位,“英雄各有见,何必问出处”。在求贤若渴的曹操眼里,凡真才实干者,都是需要去发掘的宝贵人才。所谓“明扬仄陋”,即打探和推举那些埋没在下层的贤能之士,其用人之道,关键是识人,而识人的关键,在扬其长而避其短。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中评:“像这样的政令文章,在战国以后,经过两汉几百年间,都不曾有过,两汉帝王也曾多次下过求贤的诏令,其中所说大都是先德而后才,没有讲‘唯才是举’的。”他认为曹操提出“唯才是举”,一方面是当时急需人才,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另一方面,东汉以来儒学式微,礼法失范,要用人才,必须打破传统,“不过曹操的‘唯才是举’主要是指那些为我所用之才;如果不为我所用,即使是人才也未必举的。”正如龚鹏程《改变中国历史的文献》有言:“曹操的《求贤令》代表了对东汉士风强烈的反动—道德无用,唯才是举。这种弃德唯才的政治风格,以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来,可谓其来有自……而曹操这种弃德唯才的用人导向,并不合理,不免被批评为奸雄作风……从政是造福百姓的事业,没有才能空谈道德是不行的;然而亦毕竟偏激,完全不要道德,造成魏晋南北朝长期的篡乱、烧杀。光凭才干,也不能解决时代大问题,故德才兼备才是合理导向。”
从某种意义上讲,《短歌行(其一)》可以看作曹操《求贤令》的文艺版。明乎此,我们才会对曹操求贤的殷切之意和昭昭雄心有更准确和更深刻的理解。
在《短歌行(其一)》中,作者的求贤之心是在反复咏叹中不断强化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直接引用《诗经》中的句子,比喻自己对贤才一往情深的思念。“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似乎是对一个人的当面倾诉,实则是对广大能人贤士的渴慕与召唤。“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为天下贤才描绘了一幅宾主欢宴、其乐融融的情景,表达了自己的真心诚意。不外如此,诗人还融情于景,热情而深婉地将自己的心愿寄之于明月,“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将贤士比喻为高悬的明月,光耀宇内,求而不得,不禁让人忧心如焚;“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则是劝告犹豫不决的贤士们早日来归,共谋大业。求而既得如何?求而不得又如何?诗人就这样用心周到地告知天下贤士,让他们放下所有的后顾之忧。诗歌最后一章“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激越昂扬,气势豪迈,广纳贤才的胸怀,建功立业的雄心,至此推向了顶点。
课堂指引
如若以天下为己任,在有限之中安放了使命和目标,生命便加注了非凡的意义。
春秋时期鲁国的叔孙豹与晋国的范宣子曾就何谓“死而不朽”展开讨论,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就是后代士人所信奉的“三不朽”。
曹操的雄心壮志,集中体现在“立功”上,所谓“立功”,即“拯厄除难,功济于时”,他希望能借千秋不朽之功业,来证明有限生命之价值,诉诸笔端,便成就了一曲《短歌行》,流传千古。从中,我们不难明白:诗人“忧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霸业未成。他求贤的最终目的何在?是治乱扶危,统一天下,实现河清海晏的政治理想。
叶嘉莹说:“曹操的《短歌行(其一)》在古今众多的诗歌中是很有特色的。因为,一般有诗人才情的人不一定有曹操这种雄图霸业的抱负;而有雄图霸业之抱负的人又不一定有诗人的才情。曹操具备了这双重的感情,所以他才能够写出这么好的一首诗来。”这样看来,读懂《短歌行(其一)》,体味其“志深笔长”,我们是有必要对曹操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完整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