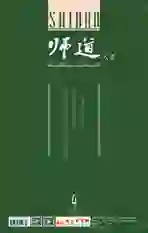在角落里微笑
2024-04-25贾未舟
贾未舟
作为一名教师,二十五年来,我一直有个哲学教育梦。
一
1995年,我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初识哲学,触动尤深。心智在启蒙阶段所遇见的东西,对人生有根本的影响。同年,我考上吉林大学西方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98年毕业,那一年,我27岁。偶然机缘,入职广东财经大学(前身为广东商学院),当时我主要承担公共课,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未有懈怠。不过,不能教专业课,总有不甘。逐渐地,我心里升腾起一个愿望,要在这所我栖身的大学进行哲学启蒙。
这是哲学品性的惯性使然,也是教师的职业责任使然。我觉得,一个财经类高校和它的大学生,一个人文精神相对匮乏的地方和群体,需要哲学。很多人会认为,一个财经类高校以实用性学科为主,培养技术性人材,要凌空蹈虚的哲学干什么?凌空蹈虚是哲学的表象,也是对哲学的误解。大学教育根本上是以能力和心性培养为中心的素质教育,而不仅仅是职业技能教育。实际上,哲学超越一切专业界限,也超越一切专业知识的局限,它的最大社会价值不在少数人的专业教育,而在大多数非专业的通识教育。哲学,是无用之大用,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的哲学家,一个人不一定要搞哲学研究,但是一定要有哲学思维。我觉得此“大用”,不是简单的成功学方法论汇集,也没有技术性的操作,而是一种贯穿生命整体的根本智慧。从通识教育角度看,大道化简,主要体现在三点:其一,认识自己,以立本体;其二,理性思考,富有思想,建构主体精神;其三,哲学所具有的深厚情怀、宽广格局与高远心态。以上三点,虽然不能说是哲学专属,但也是哲学专长,无可替代。哲学与教育在人类历史上也紧密关联、影响深远、源远流长:比如在最早期,孔子删定六经,设坛讲学,有教无类,而有孔门四科;柏拉图《理想国》中所谓的教育阶梯成为古典七艺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园千古流芳,其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谓道尽哲学教育真谛。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在本性上是求知的。哲学纯粹“爱智慧”,因此“无用而大用”,是自由的学问,进而,哲学教育,也因此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劳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虽不敏,愿学焉,终生明之,诵之,行之。
二
我任教的学校,建立时间不长,以经济、管理和法律学科为主干,或者说,这里的教育氛围很务“实”,人文精神弱淡。在这种环境下从事哲学教育,就不能以纯哲学专业的角度来开展,而要把哲学理论的纯粹性和人生哲学实用性结合起来,把哲学思维和学生具体专业特殊性结合起来,以期补益于大学生的智慧成长和整体发展,这是我的哲学教育指导思想。一所综合性重点大学,有广泛的人文学科的设置,人文资源丰富,人文精神彰显,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那么是不是一个务“实”的普通的财经类高校,就不需要人文精神?那些在这里读书的大学生就不需要人的全面发展,就不需要认识自己、富有思想因而具备做大事业的格局和视野?对于一个非哲学专业的大学生而言,哲学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部分,对专业教育有极大的助益,它的边际效应甚至大于哲学专业大学生。从另一个角度讲,从小就受“应试教育”模式熏蒸的大学生需要思想启蒙,需要转换思维方式,这是人生的“补课”,这是个现实问题,刻不容缓,时不我待!
我的哲学教育之路实现的途径,是从课堂开始的。我讲哲学课,总是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哲学是思想的魔力场,首先是无尽的“追问”,有了新问题,才能有不断的新思想所带来的创造。如爱因斯坦所言,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1998年,我来到广财的时候,这里还没有纯哲学课程,当时,我承担的课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一门政治理论课。我则力图把这门课的政治性和人文性相结合,因为我深深知道,思政课不能靠灌输而同样要靠理性地讲道理,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在我的课堂上,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个伟大革命家,还是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思想家。为此,我实操且据实感,写作了一篇论文《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本色》。从此,一边教学,一边写跟课程相关的文章,成为我的教学习惯,这些文章可以是教学论文,更多是随笔。我希望自己的课堂不是夸夸其谈,而是自己思考和实践的结果,学生看到思想化为文字,更有助于深入地理解,更容易相互产生共鸣。讲、思、写作相结合,遂成为我的讲课秘笈。
我开启了我的哲学教育之路,有计划开设或主讲系列哲学课程。1999年,我开设《当代西方哲学课程》,20世纪末的时候,商品经济在广东开始大行其道,如光速发展,经济导向似乎掩盖了一切。我为这个课程专门写作了《林中路——现代西方哲学》《哪怕做半学期的尼采》《祁克果的选择》《哲学修养与素质教育》等随笔。我告诉学生,哲学是一种逻辑分析讲道理的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价值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错之分,哲学不提供标准答案,却展示了诸多的可能性。2000年,我开设《西方文化简史》,全方位介绍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到当代的文化史。并专门写作了《什么是西方》《积极的虚无主义》等文章。2005年开始,我开设《西方哲学智慧》课程,讲授西方古代和近代哲学,正好和《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形成互补,在知识、思想、智慧三个层次谈论人生,为人与为文一致,学问与事功融通。为此课程,我也撰写了大量的哲学随笔。
2006年我舍西取中,考取中山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我的学术兴趣和精神旨归越来越回归中国思想和文化,同年,我开始主讲《中国哲学智慧》。我带领学生去剖析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发展背后的思维方式根源。
2012年,我开设了《中国管理哲学》课程,这门课契合财经类高校的专业特色,从国学与管理智慧相结合的角度梳理中国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传统思想派别的现代价值,无论对企业管理还是人生管理方面,都可以有效回击“中国文化落后”之谬论,一时应者云集,反响热烈。我为此写作了《文化中国与文化产业》《极简主义》《中道理性與中道社会》等随笔。2016年开始,我开始主讲《追寻幸福——西方伦理学视角》,这门课程梳理了西方思想史关于幸福观的论述,探讨了“什么是幸福”这一人生根本问题。我写作了《说幸福》《我是谁》等随笔。我告诉学生,如果生活的职业和生命的事业能够合一,不互相冲突,不必因毫无交集而分为两橛,这是人生的最大恩赐和福气。学生们拈花微笑,自性徜徉,或疑我所言,或信我所讲,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在他们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唤醒了他们的灵魂,激发了他们的思想,促使他们建构生命本体意识和主体精神,这是我——一个教师的最大的幸福。
在授课方式上,我习惯于干“笨活”作“苦力”,我建构的是纯粹的原始的“面对面”“心连心”的课堂。我始终觉得,课是讲出来的,我不太喜欢任何种类的电气化教学,我甚至觉得就连PPT都是累赘,都在分割连续性,都在阻隔灵感。哲学是生命教育,一堂哲学课就是一场生命之旅,只需要营造一个生命精、气、神共在的生命场景,让学生在其中徜徉,在其中融化。
若自诩大公无私,像《中庸》说得那样临深履薄、战战兢兢,这是虚伪的假话,但是,贻厥嘉猷,勉其祗植,我尽了绵薄之力了。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心灵的事业,不欺暗室,卑以自牧。我的哲学课堂,有苏格拉底的睿智,有斯宾诺莎的宁静,有叔本华的疯狂,有老子的大巧若拙,有庄子的凌霄俊逸,有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绝,也有王阳明“满大街都是圣人”的心胜,融知识、思想和智慧于一炉。若不能以思想统摄知识,知识永远只是外在的教条,若不能把知识和思想上升到智慧,生命何所依?思想是知识和智慧的津梁,以立本心,以迎朝阳。思想的创新性会带来理想主义的憧憬,思想的批判性会给人现实主义的清醒,同时,思想的超越性也会拒斥现世主义的酱缸与泥淖。但是,思想也会带来与众不同,这可能意味着来自周遭的隔膜,我告诉学生,要有批判精神:“一味肯定,最终必是怀疑,怀疑的结果是毁灭,学会怀疑,最终得到的是肯定,肯定的结果是升华。”《庄子·列御寇》中说“巧者劳,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要么庸俗,要么孤独。尼采也说:你今天是一个孤独的怪人,你离群索居,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民族。在哲学课堂上,认识自己,成为自己,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知识、思想并行,智慧、情怀共生,行有余力,关心人类,泛爱众而亲仁。
单纯的哲学课堂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不辅以阅读,尤其是哲学经典的细读,听课就只能是被动的,知识就不扎实,思想就不深入,在有限的时间里捕捉和深化思想灵感的能力就不足。于是乎,2014年6月21日,我和那些热爱思想的学生,共同创办了广东财经大学金兰细读会,把哲学教育延伸到课外,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当问题堆积而不得解的时候,我们不去做无谓的“口舌之争”,而是沉潜心志,去细读原著,厉兵秣马,待天时已到,传檄天下,号召各路诸侯,约定研讨会,华山论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们的口号是:宁少读,读经典,务细读。我们郑重其事,甚至为细读会共同创作了会歌——《金兰愿》:金萃兰芳,金萃兰芳,明日中华,薪传火飏。我们击节而歌,曲水流觞,声震屋宇,响遏行云,其情也真,其志也壮。
金兰细读会配合哲学课堂,专注于人文类的经典原著的细读,谦卑而虔诚地进入一个个思想的魔力场,让经典复活,打开思想之门,面向文本,培养扎实而深度的思考、研究、表達能力,做到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细读,因敬居静而品,是为书道,既是一种学习态度,学是学此学,乐是乐此乐,打通教育与生活的隔阂,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因而也是一种生活美学。我和金兰细读会的同学,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不断校正,不断补益,发展出了独特且富有成效的细读方法。在十年的金兰细读会发展历程中,迄今为止,一共组织了42次细读会,细读了42本中外原著,42个带读人和主讲人,每一次都那么欢欣、热烈和庄重。2022年,写作了六年也在实践中修改了六年的两万余字长文《细读的理念与方法》公开发表,成为金兰细读会哲学教育的见证,这是金兰细读会共同的精神创造。
哲学课程论文,我都要求手写,因为书写本身就倾注着情怀,而电子版不会有。金兰细读会上细读经典,我跟学生说,请读纸质版,而不是电子版,打开有墨香的书,生命遇见生命,还你一瓣心香。技术时代的发展趋势,无可改变,但是在这样一个网络虚拟电子化的时代,人要深根固柢,横而不流,不能被技术拖着走。在你年轻的时候,不妨用点儿笨功夫,不妨亲近自然,不妨大巧若拙,不妨更原始些,以触摸本真。就像我经常跟学生说,在你最好的年纪,不要急着去挣钱,不要急着见成绩,成长需要慢功夫,去阅读吧,思考吧,想象吧,创造吧,这是哲学的呼唤!教育是植根,而非插花。
哲学教育与经典细读,相得益彰;哲学课堂与金兰细读会,榫卯成善。
三
哲学课堂上的学生,他们那种寻根问底、艰深思考的表情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金兰细读会上的兰友,沉着雄辩的英姿,永远刻在我的心中。无论是哲学课堂还是金兰细读会,在方法论上,我始终认为“思想,是自己的事”,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天助自助者”,自教,是受教育的最高层次,自明,是受教育的最高境界。我有“五句教”:阅读是敲门砖,思考是点金石,切论是催化剂,游学是穿梭机,写作是收纳盒,在我二十五年的哲学教育实践中,未敢怠慢和苟且,这五者兼容并蓄,一以贯之。我尤其推崇“五句教”中的“写作是收纳盒”环节,我鼓励学生记录自己的生命和思想轨迹,不能“述而不作”,在个体的“小历史”里去“小写作”,在写作中整全生命,让万事万物各彰其能各得其所,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作家,从而获得明晰的生命经验、意义和价值。我们交流习作,奇文共赏,其乐融融。我们甚至约定,有一天财务自由了,办一份单单属于我们自己的《细读》杂志。这些哲学课程的考核方式,我要求根据自己的所喜所感所论,写一篇标准的课程论文,而从不用闭卷考试的形式。一则,哲学学习并不是死记硬背那些知识点,不上升到思想,只会给人带来更大的困惑,闭卷考试没有必要。二则可以在我的课上练习写作学术论文,论文写作既是大学生素质教育要求,也是自己生命的“小历史”里的“小写作”的一部分。因缘际会,那些哲学课堂和金兰细读会上的学生,在他们最好的年纪,遇见了思想,遇见了自己。每次上完课,每次细读会结束,一些学生仍意犹未尽,一边讨论问题一边送我到汽车站,依依惜别,师生互砺,学问相从。他们学会了阅读,长出了思想的翅膀,认识了自己,这些能够思想的芦苇的人生,将勇往直前、无所畏惧。
逐步地,我的哲学课堂从本科生延伸到研究生。研究生教育,我尤其推崇“经典细读型”授课方式,很多年后,研究生写信来,说求学期间印象最深刻的教育经历,就是跟我读了几本经典原著,尤其是《道德经》和《单向度的人》这两本,知道了如何细读,如何思考,如何写作。他们都走远了,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二十五年来,有数千学生进入我的哲学课堂,数百学生来到金兰细读会。他们各有不同的专业背景,他们在我的哲学课堂和细读会上,相聚了,以思想会友,以友辅仁。
他们毕业后,有的甚至走上哲学研究之路,洁净精微,疏通知远。广财第一个哲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都来自我的哲学课堂,算来已经有七个了。他们中有的放弃待遇优渥的单位,或自主创业,或自由撰稿,独辟蹊径,守心明性,或立志于基础教育事业,恭俭庄敬,作光作盐。他们凡人微光,隐于市,践履生活美学,即凡即圣,呈现本真、活泼、清凌的生命状态,他们说哲学使他们知道“认识自己成为自己”“人是目的”是人生最高价值,拼尽全力,去守护一个自由哪怕孤独的灵魂。“成为一个个体”,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这句箴言,是现代公民社会形成的精神前提。
更多的学生,广博易良,笃行致远,成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的思想者,成为哲学无用之大用的最好的践行者。成己成物,责斯尽焉。柏拉图说,真正的教育是灵魂的转向,诚如是。
通识教育视域下的哲学教育,就是人性教育,其唤醒良知,健全人格,点燃思想的火种,追求卓越。今天,学校里包括哲学教育在内的人文教育,已成共识,渐成气候,而我的哲学课堂和金兰细读会上的雏凤清声,愈发动听。
二十五年来的哲学教育之路,潜踪密行,吾道不孤。在路口守望,在角落里微笑。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 成 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