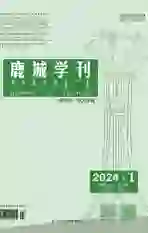楚辞之天象书写
2024-04-20梁利栋
梁利栋
摘 要:楚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天学传统,因而楚辞中有大量的天象书写。在巫文化和理性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屈原对天象的态度具有矛盾性,既在创作中大量运用神话化的天象,又在《天问》中质疑天文神话。楚辞之天象书写具有抒情性、象喻性,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上影响了汉赋之天象书写。
关键词:楚辞;汉赋;天象书写
The Celestial Writing of Chu Ci
Liang Lid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730070)
Abstract:Chu State has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 in the study of celestial phenomena,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abundant descriptions of heavenly phenomena in the Chu Ci.Under the dual influence of shamanistic culture and rational thinking,Qu Yuans attitude toward celestial phenomena is contradictory.He extensively employs mythologized celestial imagery in his compositions,yet he questions astronomical myths in “Tian Wen” (Inquiry of Heaven).The descriptions of celestial phenomena in the Chu Ci are characterized by lyricism and metaphorical language and have influenced the depictions of heavenly phenomena in Han Dynasty fu literature in terms of diction,sentence structure,and overall composition.
Key words:Chu Ci;Han fu;celestial phenomena depiction
江晓原认为,“‘天文与‘人文‘地理对举,其意皆指‘天象,即各种天体交错运行而在天空所呈现之景象”[1]“古代中国人未能清楚地认识到地球大气层的存在,以及由此造成的诸气象现象与天文现象的根本区别,遂习惯于将二者等量齐观。”[2]本文所用之“天象”主要指具体天象。具体天象,不仅包括日月星辰的状态与运行,还包括风雨雷电等气象。本文将从楚国之天学传统,楚辞天象书写的神化与质疑,楚辞天象书写的抒情性、象喻性,汉赋天象书写对楚辞的借鉴等五方面展开论述。
一、楚国之天学传统
“重黎”(单称“黎”)为楚先祖,职掌天文,传之后世,故楚国有源远流长的天学传统。《史记·楚世家》论楚之世系云: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3]
“重黎”为一人之名,当帝喾之时,任火正之官。“重黎”号祝融,亡故后其职与号为弟吴回承袭。然《索引》曰:“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为木正,黎为火正”[4],将“重黎”离析为“重氏、黎氏”,且二人各司其职。《索引》之说,显然受到《尚书》《国语》记载的影响,其文曰: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①[4](《尚书·吕刑》)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復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5](《国语·楚语下》)
《吕刑》未明言“君帝”为谁、“重黎”是合是分。孔安国《传》:“君帝,帝尧也”“重即羲,黎即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言天神无有降地,地民不至于天,明不相干”[4]。孔氏认为皇帝为尧,将“重黎”一分为二,且与“羲”“和”对应。此外,其对“绝地天通”的解释应借鉴了《国语》之说。《楚语下》中,“重黎”一分为二,“重”任南正以司天,“黎”任火正以司地,当颛顼之时。
《史记·楚世家》将“重黎”和“祝融”等同起来,应受《山海经》之影响。《山海经》卷十六《大荒西经》曰:“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卬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6]。《史记·楚世家》将“祝融”和“重及黎”相对应,合“重”“黎”为一。《史记·楚世家》将“祝融”和楚国相关联,应受《国语·郑语》之影响。《国语》卷十六《郑语》记史伯之语,提及楚为“祝融”之后:“且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5]。“芈姓”即楚之国姓。江林昌认为,“而据《国语·郑语》可知,祝融之后又发展出八个族姓。这八姓中,部分在中原,另部分则在淮河、长江流域。在长江流域者,以先楚芈姓族最为有名,即《郑语》所说‘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7]
关于“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之说影响甚大,《史记·历书》《汉书·律历志》《汉书·郊祀志上》《幽通赋》《应间》承之。兹胪列如下:
少暤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3](《史记》卷二十六《历书》)
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后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尧复育重、黎之后,使纂其业,故《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官,众功皆美。”[10](《汉书》卷二十一上《律历志上》)
及少昊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家为巫史,享祀无度,黩齐明而神弗蠲。嘉生不降,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亡相侵黩。[10](《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上》)
黎淳耀于高辛兮,芈强大于南汜。[11](班固《幽通赋》)
当少昊清阳之末,实或乱德,人神杂扰,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颛顼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则重、黎之为也。”[11](张衡《应间》)
《史记》对“重黎”史事的记载有异,原因在于《历书》采《国语》之说,《楚世家》另立新说。《汉书·律历志》将重、黎与后出之羲、和对应,与孔安国、扬雄之说同。《法言·重黎》曰:“或问:‘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羲,近和。‘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重黎。” ② [12]扬氏将重、黎分别对应羲、和。《郊祀志》基本上撮《国语》之要而写之。《幽通赋》在黎和楚的关系认定上与《史记·楚世家》相通。此外,《潜夫论·志氏姓》对“重”“黎”亦有记载。其文曰:
少曎氏之世衰,而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夫黎,颛顼氏裔子吴回也。为高辛氏火正,淳燿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继重、黎之后不忘旧者,羲伯复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别其分主,以历三代,而封于程。其在周世,为宣王大司马,《诗》美“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其后失守,适晋为司马,迁自谓其后。③[13]
《潜夫论》晚出,其说兼采《楚语》《楚世家》之说。“少曎氏之世衰……是谓绝地天通”与《楚语》记载基本相同。“曎”为“皞”之讹,因形致误。“夫黎……故名祝融”与《楚世家》记载有出入。《楚世家》认为吴回为重黎之弟,《志氏姓》认为黎即吴回。“后三苗复九黎之德……迁自谓其后”与《楚语》记载基本相同。《志氏姓》将“重、黎之后”与“羲伯”建立联系,增加了程伯林父受封、为官等细节。
从“重”“黎”的分合上看,《史记·楚世家》主合,其他文献主分。因此,《楚世家》之“重黎”应偏指“黎”,担任火正,号祝融。司马贞《索隐》引刘氏之说,其文曰:
少昊氏之后曰重,颛顼氏之后曰重黎,对彼重则单称黎,若自言当家则称重黎。故楚及司马氏皆重黎之后,非关少昊氏之重。[3]
少昊氏之“重”与颛顼氏之“重黎”相对而言时,“重黎”简称“黎”以示区分;仅称颛顼氏之“重黎”时,不须简称。高华平认为,“《史记·楚世家》本以‘重黎为一人,这里(笔者按:《太史公自序》)则始以之为二人,继则曰‘绍重黎后,似乎又以‘重黎为一人了。实则重、黎当为二人,《国语·楚语下》即以为二人。”[19]
关于“火正”之职掌,《左传·襄公九年》记士弱对晋悼公之语,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15]“火”本兼指“鹑火”“大火”,后专指“大火”。张正明认为,“传说时代的火正,降至商代称‘师火,乃至周代称‘火师,总之是司火之官。火正的职责主要有三项:一是观象授时,二是点火烧荒,三是守燎祭天”“祝融被称为火正,是因为他们能根据火星出现的时辰和方位来判定春分的日期。祝融观测的火星不是被称为‘荧惑的那颗行星,而是被称为‘大火的那颗恒星以及被称为‘鹑火的那个星座”[16]。张氏对“火正”的解释,充分体现了天文学意义。
从重黎所处的时代上看,《国语·楚语下》《史记·历书》《汉书·律历志》《应间》《潜夫论·志氏姓》认为当颛顼高阳之时,《史记·楚世家》《幽通赋》认为当帝喾高辛之时,《尚书》孔安国《传》认为当帝尧之时。之所以重黎被不同文献归属于不同时代,是因为五帝时代的历史具有不确定性。沈长云认为,“‘五帝并不是一个纵向的排列,它们之间应主要是一种并列的关系。即这些古帝(不止是“五帝”)大致都生活在同一個时代,相差的时间不会太久。他们之间的先后关系也不一定如过去人们理解的那种顺序。”[17]可备一说。不过,总的来说,“重黎”与司掌天地有关,与楚国有关。
楚国先祖重黎司掌天地,后代亦踵武前人,天学知识代代传承,形成楚国的天学传统。《楚语下》曰:“其(笔者按:即颛顼)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23]这段文字简要勾勒了重黎氏在三代的传承脉络。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为楚国贵族,与楚王同姓,必然受天学传统之影响。这一传统折射于文学作品,遂表现为楚辞之天象书写。
二、天象的神化与质疑
蔡觉敏认为,“相对庄子来说,屈原对神话的态度要复杂一些:一方面,他在《天问》里表现出对神话的疑惑,另一方面,《离骚》中,他自己又成为神性的人,《九歌》中,他塑造了众多可亲的神的形象。这种矛盾的态度缘于特定时代的影响,理性的发展使他认识到神话的荒谬,但是,作为在深厚巫文化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人,他又对神话和神还有着某种程度上的情感依恋,故此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对神的情感认同。”[18]屈原对神话的矛盾态度源于其所处时代、地域环境的复杂性。楚辞中部分天象被神话化,故屈原对天象、神话的态度有相通之处。
(一)天象的神化
楚辞中的天象及相关名物被神化,体现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日御“羲和”、月御“望舒”、风神“飞廉”、雷神“丰隆”、云神“屏翳”,不胜枚举。《离骚》曰:“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羲和,日御也。”[19]《山海经》卷十五《大荒南经》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6]羲和生日、浴日,更驾日而行,故称“日御”。《离骚》曰:“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王逸《注》:“望舒,月御也”“飞廉,风伯也”。洪兴祖《补注》:“一曰:雷师,丰隆也。”[19]屈原神游,以月御为前驱,让风神紧随其后,神鸟戒严,雷神报备,想象雄奇,语言瑰玮。
《九歌》的文本性质是屈原被疏之前为楚国祀典而作的祭歌。赵逵夫先生结合出土文献认为:
1978年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竹简,上载楚人所祭神灵多有与《九歌》所祭神灵相合者,看来《九歌》中主要部分是屈原根据楚国国家祭典的需要而创作的祭歌。其中只有《湘君》《湘夫人》二篇表现的是沅湘一带的民间传说,情节上具有明显的民间色彩。[20]
韩高年老师引述闻一多先生《什么是九歌》,总结道:
《九歌》祭礼是专为东皇太一而设的,其他众神都是配角,他们的任务是《汉书·郊祀志》所说的“合好效欢虞太一”。[21]
在《九歌》神灵体系中,“东皇太一”“大司命”“少司命”为星神,“东皇太一”尤尊,“东君”为日神,“云中君”为云神。
“东皇太一”为星神,亦是楚人心目中的最高神。五臣《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曰东皇。”[19]《韩非子集释》卷五《饰邪》曰:“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非(笔者按:此“非”字衍,从王先慎说)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非(笔者按:“非”字衍)数年在东也。”[22]与“太一”并列之物多为星象,故太一本为星名,后被神格化。关于上述记载,李炳海说:
韩非子的论述透露出了有关太一的信息:第一,太一是星名。韩非子为了证明星占的不足为据,连续列出了十四个星名,太一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见,先秦时期太一有时确实是星辰名称,这是它具体的天文学含义。第二,太一星位于东方。和太一并列的有摄提、岁星。[23]
李氏立足文本,言之有据。《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正义》引刘伯庄之语:“泰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3]《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记谬忌之语:“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3]泰一即太一,位在众神之上,故曰“皇”;楚人尚东,于东南郊祭太一,故以“东”饰“皇”。《新序》卷一《杂事·秦欲伐楚章》:“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东面。”[24]楚臣昭奚恤明言朝东之位为上位,足证楚人尚东。张正明结合楚墓情况说:“楚国公族的墓葬,头向从东。墓向与头向一致,也从东。其中可能有双重的意蕴:一则,作为日神的远裔,应朝向日出的东方;二则,作为火神的嫡嗣,同样应朝向最初的火神所居的东方。”[25]张氏将楚人尚东归结为日神、火神崇拜。“东皇太一”为楚国常祀之尊神,《文选》卷十九宋玉《高唐赋》亦云:“醮诸神,礼太一。”[26]诸神之外,特拈出太一,可见其尊。
“司命”为星神,五臣《注》:“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辅天行化,诛恶护善也。”[19]《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索引》引《春秋元命苞》曰:“司命主老幼”[3]。张衡《思玄赋》曰:“死生错而不齐兮,虽司命其不晰。”[11]主老幼即主死生。析言之,“大司命”“少司命”合称“司命”,同掌人之生死,但分工不同。大司命运筹帷幄,少司命身体力行。《大司命》曰:“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19]。“寿夭”“阴阳”即生死,大司命手握人之生死大权。《少司命》曰:“孔盖兮翠旌,登九天兮抚彗星”“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王逸《注》:“言司命乃升九天之上,抚持彗星,欲扫除邪恶,辅仁贤也”“言司命执持长剑,以诛绝凶恶,拥护万民长少,使各得其命也”“言司命执心公方,无所阿私,善者佑之,恶者诛之,故宜为万民之平正也”[19]。少司命登天抚彗,竦剑护民,惩恶扬善。闻一多于《司命考》中考证“司命”为“虚北二星”,其文曰:
《史记·天官书》曰:“北宫玄武:虚,危。”这是五行说应用到天文学上,将虚危二星派作北方帝的分星。虚既是北方帝的分星,而北方帝是颛顼,所以虚又名颛顼之虚。(《尔雅·释天》:“颛顼之虚,虚也。”)但我们猜想,在天上既有星代表着颛顼,可能也就有星代表着作为颛顼之佐的玄冥。经过研究,我们才知道,这星有是有的,不过它不是以玄冥的名字出现,而是以司命的名字出现的。[27]
“东君”为日神,王逸《注》:“东君,日也。”[19]《东君》为日神之祭歌,“日”意象是拟人化的全局书写,其他天象是客观的局部书写。“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二句[19],描写了日神以“雷”为车、以“云”为旗的出行场面,鲜活地表现出日神出行时的仪仗之美。“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四句[19],描写了日神以“青云”为上衣、以“白霓”为下裳的美丽外貌,弯“弧”搭“矢”射“天狼”的正义行为和以“北斗”为爵的浪漫之举。“天狼”“弧”“矢”(弧矢九星)连用的构思在汉赋中亦有体现。扬雄《河东赋》:“彏天狼之威弧。”杜笃《论都赋》:“亲发狼、弧。”崔骃《反都赋》:“握狼狐。”④黄香《九宫赋》:“狼弧彀张而外饗。”张衡《思玄赋》:“弯威弧之拨剌兮,射嶓冢之封狼。”[11]“援北斗兮酌桂浆”反《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之意而用之[28],气势豪迈。
“云中君”为云神,或简称“云君”,王逸《注》:“云神丰隆也。一曰屏翳。”[19]笔者认为,云神为“屏翳”,而非“丰隆”。“屏翳”状遮天蔽日之貌,故为云神之名;“丰隆”拟雷声轰鸣之声,故为雷神之名。《云中君》为云神之祭歌,由祭祀云神的巫觋和扮演云神的灵巫对唱,兼及云以外的天象。“与日月兮齐光”[19]以“日月”衬托云彩,反映了云借日月而生辉的事实;“猋远举兮云中”[19]以“猋”(笔者按:后写作“飙”,疾风)喻云,表现了云神离去之速。
(二)对天象成说之质疑
战国时期,理性思潮兴起,屈原在《天问》中对天发问,追问天文、地理、历史和现实。韩高年老师认为,“屈原的《天问》则针对天地宇宙、日月星辰,以及既往的历史兴亡、人生遭际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表现了诗人深刻的哲思与大胆的质疑精神。”[29]其中,对天文的追问体现了对天象成说的怀疑。
《天问》曰:“角宿未旦,曜灵安藏?”王逸《注》:“角亢,东方星。曜灵,日也。言东方未明旦之时,日安所藏其精光乎?”[19]《山海经》卷九《海外东经》曰:“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同书卷十四《大荒东经》曰:“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戴于乌。”[6]扶木即扶桑,为日居之处。屈原的言外之意是,太阳光芒万丈难以藏身,东方未明之时太阳居于何处不得而知,体现了对扶桑神话的怀疑和对太阳运行的思考。《天问》曰:“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19]《山海经》卷八《海外北经》曰:“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冥为夜;吹为冬,呼为夏。”同书卷十七《大荒北经》曰:“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是烛九阴,是谓烛龙。”[6]烛龙,烛照九阴,故又名烛阴。“视为昼”“其视乃明”表明烛龙睁眼形成白昼。太阳无所不至,烛龙视为白昼,二者为光明之源,难以并存,体现了对烛龙神话的怀疑。《山海经》卷十七《大荒北经》曰:“(若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6]若华,即若木之花,绽放时光照大地。羲和御日而行方可为世间带来光芒,那么,羲和未行之时,若华之光则无从解释,体现了对若木神话的怀疑。
神话是远古先民对世界的朴素认知,体现了以我观物、以我感物的原始思维,不应全用理性眼光审视它。因此,伟大的诗人屈原虽然对天文神话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但仍然在创作中大量使用,为作品增添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三、天象书写的抒情性
楚辞中的天象书写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天象是作者表情达意的重要载体。《离骚》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王逸《注》:“言天时易过,人年易老也。”[19]诗人借日月运行、四季輪转表达对时光易逝的感慨。《九章·涉江》曰:“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王逸《注》:“言己登鄂渚高岸,还望楚国,向秋冬北风,愁而长叹,心中忧思也。”[19]诗人登高而望,在秋冬之际的余风中叹息,表达了心中无限的哀愁。《九章·悲回风》曰:“悲霜雪之俱下兮,听潮水之相击。”王逸《注》:“言己上观炎阳烟液之气,下视霜雪江潮之流,忧思在心,而无所告也。”[19]诗句视听结合,诗人看霜雪惧下,听潮水相击,不禁“悲”从中来。
楚辞中的天象书写往往是景物描写,已达到融情入景、借景抒情的艺术水准。
四、天象书写的象喻性
楚辞中的天象常有象征隐喻性,进而为抒情、言志服务。《离骚》曰:“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王逸《注》:“飘风,无常之风,以兴邪恶之众”“云霓,恶气,以喻佞人”[19]。诗人以飘风、云霓喻奸佞小人,借风起云涌表明自己所处政治环境的险恶。《九章·涉江》曰:“山峻高?蔽日兮,下幽晦?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王逸《注》:“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霰雪以兴残贼,云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日者,谓臣蔽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群下专擅施恩惠也。霰雪纷其无垠者,残贼之政害仁贤也。云霏霏而承宇者,佞人并进满朝廷也。”[19]诗句的写景视野由高而低,复由低而高,具有回环往复之美;诗人借高山蔽日、阴暗多雨、霰雪纷飞、云海翻腾的景象,象征朝廷中君昏臣佞。《九辩》曰:“去白日之昭昭兮,袭长夜之悠悠。”五臣《注》:“白日喻君,言放逐去君。”[19]诗人以日喻君,借离开白日表明被放逐的事实。“日”“夜”前已有“白”“长”为饰,后又以“昭昭”“悠悠”形容之,不仅具有音韵美,还强化了失意落寞的情绪。
五、汉赋天象书写对楚辞的借鉴
楚辞是汉赋的重要源头之一,汉赋天象书写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两方面常取法于楚辞。
汉赋天象书写在词汇、句法上借鉴楚辞。《远游》曰:“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19]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咀噍芝英兮叽琼华。”[11]北大汉简《反淫》曰:“饮三危,□白露,欱沆瀣而充虚,精气洞于九野。”[30]《大人赋》《反淫》中保留了《远游》中“沆瀣”“朝霞”二语和“□沆瀣”“□朝霞”所使用的动宾结构。不同的是,司马氏改用“呼吸”“餐”等动词、动词性短语,《反淫》则改用“欱”;此外,司马氏将“沆瀣”“朝霞”并入一句,《反淫》则不用“朝霞”句。《远游》曰:“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19]司马相如《大人赋》曰:“贯列缺之倒景兮,涉丰隆之滂濞。”扬雄《羽猎赋》曰:“辟历列缺,吐火施鞭。”张衡《思玄赋》曰:“丰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晔其照夜。”[11]“列缺”意为闪电,首见于楚辞,汉赋中亦多见。《远游》和《大人赋》借列缺突出高,而《羽猎赋》借列缺突出快、《思玄赋》借列缺突出亮。
汉赋天象书写在构思上借鉴楚辞。《离骚》在局部、《远游》在全篇设置了游仙的情节,具有虚拟性,汉赋亦涉及此种写法,以《大人赋》《思玄赋》为代表。
楚辞之天象书写以楚国悠久的天学传统为背景,数量众多,内涵丰富。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其对天象矛盾的态度耐人寻味。楚辞是汉赋的源头之一,故在天象书写上楚辞与汉赋的会通之处理所应当。
注释:
①《尚书·吕刑》“皇帝”,孔安国《传》作“君帝”。“皇帝”一语晚出,故“皇”为“君”之讹,因形致误。
②“北正”之“北”为“火”之讹,因形致误。
③“羲伯”之“伯”为“和”之讹,因形、音相近致误。“伯”在上古为铎部字,“和”在上古为歌部字,二字阴入对转可通。
④《反都赋》中,“狐”为“弧”之讹。
参考文献:
[1]江晓原.天学真原[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1.
[2]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114.
[3](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1689,1689,1257-1258,1689,1289-1290,1293-1294.
[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36-539,536-539.
[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59-564,510-511,559-564.
[6]韩高年.《山海经》注译[M].北京:中华书局,2020:391,396,386,311,370,296,420,419.
[7]江林昌.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建构中国特色文史学科理论体系浅议之三[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37.
[8](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973,1190,1218.
[9]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518,772,1293-1294,248,387,437,562,595,119,120,256,595.
[10]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309.
[11](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5:411-412.
[12]高华平.墨家远源考论——先秦墨家与上古的氏族、部落及国家[J].文史哲.2022(3):118.
[13]《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66-869.
[14]张正明.楚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8.
[15]沈长云.五帝时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及人类学解读[J].中原文化研究.2020(5):24.
[16]蔡觉敏.庄、骚比较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176.
[17](宋)洪兴祖撰,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方进点校.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7,28-29,57,71,69-70,73-74,76,74,75-76,59,58,58,89,93,6,129,160-161,29,130-131,185,166,174.
[18]赵逵夫解读.楚辞[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39.
[19]韩高年.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M].北京:中华书局,2006:325.
[20](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122.
[21]李炳海.东皇太一为大火星考[J].辽宁大学学报.1993(4):32.
[22](汉)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1:99.
[23]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06.
[2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81.
[25]闻一多.闻一多全集·楚辞编 乐府诗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6-7.
[26]《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89.
[27]韩高年.论“诗骚传统”[J].文学评论.2017(5):116.
[28]北京大學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31.
(责任编辑 陈润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