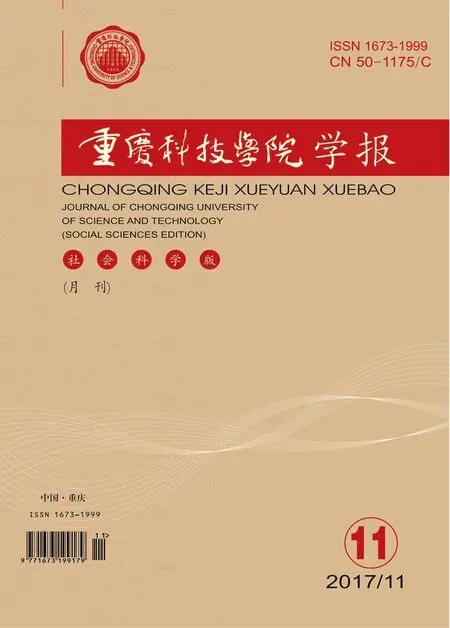20世纪汉赋研究中的道德批评综述
2017-03-22杨海霞
杨海霞
20世纪汉赋研究中的道德批评综述
杨海霞
汉赋自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异常严厉的批评,宋代文人对汉赋的道德批评是在理学思想背景下进行的,20世纪的道德批评则是在疑古思想下展开的。综述了20世纪汉赋研究的全盘否定论者和部分否定论者的道德批评观,并以两本文学史教材对汉赋的批评为例,认为20世纪汉赋研究的道德批评依然存在偏激倾向,但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汉赋研究;道德批评;全盘否定论;部分否定论
自汉代以来,就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辞赋观:一种以杨雄和王逸为代表;一种以司马迁和司马相如为代表。司马迁主张赋必须言志,必须讽谏,即赋要承担起文学的社会功能。这种主张直到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前都颇为兴盛。宋代文人对汉赋进行的批评属于道德批评,他们从汉赋是否具有讽谏价值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文学形式。这种批评存在的前提是“文学必须具有道德功能”,但是,关于文学是否必须具备道德功能,目前并没有一致的观点。康德认为文学作品不应以道德的实用为创作目的。在康德的思想体系中,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是截然不同的[1]。
20世纪以来,汉赋研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对汉赋的思想价值、艺术成就、源流演变、作家作品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汉赋的道德批评也呈现出了明显的倾向性。例如,龚克昌认为:“大赋作家的作品中多有微讽帝王的旨意在。”[2]针对汉赋是否有讽谏作用、批判价值,徐宗文认为汉赋的讽谏纯属表面文章[3]。王缵叔则认为,汉赋根本不管人民的生活疾苦,缺乏现实批判意义,因此认为汉赋是一味地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宫廷文学,其对汉赋持否定态度[4]。何新文认为,汉赋对大一统皇朝的赞美和歌颂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具有现实意义[5]。章沧授从《诗经》中的颂德传统来肯定汉赋为帝王歌功颂德,认为这是继承了历代文学的传统,是进步的文学[6]。
一、否定汉赋思想价值的道德批评
(一)全盘否定者的道德批评
王国维把“汉之赋”和“楚之骚”“六朝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相提并论。王缵叔对此持不同观点,他认为汉赋早就泯灭了,不仅没有继承者,就连有幸保留下来的几篇汉赋也只是供专业工作者研究使用罢了,并无欣赏者。他指出汉赋远离人们的生活,一味地取悦帝王,这是汉赋与生俱来的不足。汉帝国政治稳固、经济繁荣,再加上帝王的提倡,汉赋便兴盛起来,影响汉文坛数百年之久。可见,汉赋从诞生起就是受命于君王、供统治者享乐的御用文学。所谓的“一代之文学”应将反映人民的生活疾苦作为自己的责任,但汉赋中并未有这样的内容。另外,一切文艺作品都应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产物,然而汉赋则是“奉诏而作”,并不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也不是作者情思的描绘,而只是追求形式之美。汉赋大肆铺陈、因物造端,大量堆砌奇文怪字,违背了在简洁的篇幅中蕴含丰富内容的文学创作原则。此外,汉赋还因袭模仿,缺乏创造性。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或新的写作方法的出现,接踵而来的便是竞相效仿的模拟者。汉赋作品只能流为雷同,不能给读者带来新意,更不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由于汉赋缺乏独立的生命,所以无法经受时间的考验[4]。
王缵叔对汉赋的艺术和价值都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所以,他将汉赋称作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认为它无视人民的疾苦,一味地粉饰太平,是一种专供帝王消遣的宫廷文学。王缵叔对汉赋的批判沿袭了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否定汉赋论者的观点,都将汉赋归为“宫廷文学”“消遣文学”等非现实主义文学一类。但是,对汉赋作品进行全盘否定也太过偏激了,缺失了评论的客观性。
郑在瀛对汉赋的价值也持完全否定态度,他给“赋”下的定义是:像诗般押韵,像骚般体制宏大,句式像散文般长短不齐、富于变化。郑在瀛并不认为汉赋是独立的文学形式,只是其他文学形式的拼凑,将其视作一套死板的公式:开头是序,中间是赋,最后是发点议论。中间赋的部分往往主客问答,颇似纵横家之辞令;最后的议论部分也起不到任何的讽喻作用。所以,他认为汉赋之创作形式僵硬呆板,毫无价值。在论及汉赋的语言时,他说:“更可恶的是赋中大量出现冷僻的字、词,成群结队的连绵字,几乎把一篇辞赋变成了一部连绵字典和难字表。”[7]“可恶”二字表达了他对汉赋的厌恶之深!他对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赋作品斥之为挖空心思地铺采摛文、玩弄文字游戏,是“为文而造情”,是追求形式美的文学。
(二)部分否定论者的道德批评
与王缵叔全盘否定汉赋的观点不同,姜书阁虽然对汉赋的价值持否定态度,但却主张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深入的研讨和适当的批判。姜书阁的汉赋观集中体现在《汉赋通义》一书中。《汉赋通义》是20世纪80年代非常重要的一本考辨类汉赋专著,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释义、溯源、考史、综论,下卷论汉赋在思想内容、结构形式、句法句式和音节声韵方面的特色。姜书阁对汉赋价值的评价虽然持否定态度,斥之为粉饰太平、仅供消遣的宫廷文学,他是一个汉赋否定论者,但与汉赋全盘否定论者不同的是他将汉赋作为一种客观的文学现象,并主张对汉赋在音节、声韵方面的特色进行深入的探讨[8]。
马积高肯定汉赋在开拓文学体裁、表现主题和丰富文学词汇、提高艺术水平等方面的贡献。在论述汉赋作品存在的缺陷时,马极高分析了导致这种缺陷产生的历史原因是:汉赋作品的歌颂是由赋家的身份和地位所决定的,赋家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只能在作品中谨慎地表达对帝王的规劝之意;汉赋作品以大为美,将各类题材融为一体,大量铺陈,还要满足语言的华美与对称。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汉赋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难免削足就履,进入一种文学创作的僵局,缺少创新之意。马积高的汉赋观较之以往的汉赋否定观显得更加客观与公正,他既指出了汉赋存在的缺陷,又分析了导致这种缺陷的原因[9]。
马积高认为,汉赋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肯定汉赋在赋的发展史上也占据着同样重要的位置。相反,他认为汉赋不仅不能代表赋的最高成就,而且还是赋的发展史上一个较低级的阶段。马积高将汉赋作为一种客观的文学现象,肯定了它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也肯定了它的历史贡献。但是,就汉赋的价值而言,马积高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也将汉赋斥之为粉饰太平的宫廷文学。他将唐赋称为是赋发展史上的最高峰,对其中的讽刺小赋更是赞之为“一丛鲜艳的玫瑰,与唐代那些优美的讽刺诗和精悍的杂文一道,在遍体芒刺的尖端上放出夺目的光芒”[10]。讽刺小赋反映世态人情、剖析社会弊端,笔风犀利,一针见血。马积高对这样的赋作大加赞扬,可见他沿袭了长期以来的讽或颂、现实主义或非现实主义的汉赋评价标准。
如果说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还属于学术争鸣,那么,作为高等学校的文学史教材则应该相对客观地介绍和评价汉赋的价值。然而,20世纪出版的多套《中国文学史》教材对汉赋持否定态度的居多,并对其进行了道德批评。
二、《中国文学史》教材对汉赋的道德批评
(一)中科院文学所编辑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简称“中科院文学所”)编辑的《中国文学史》于1962年出版,全书分为封建社会以前的文学、封建社会的文学两个部分。封建社会以前的文学主要是古代神话传说与 《诗经》,封建社会的文学则按朝代逐一论述。此书在论及汉赋时主要分析了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蔡邕、赵壹的作品,并给予了不同的评价。对于贾谊的代表作《吊屈原赋》,此书认为基本上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批判性。而对其另一代表作《鹏鸟赋》,此书则认为除一些句子“用形象的语言来说明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11]111比较深刻外,其余皆意思枯燥、语言乏味。此书认为汉初最重要的赋家是枚乘,因为他的代表作《七发》继承了《楚辞》的传统,具有讽谏的意义,而且其中的描写有中心、有层次、有变化,不像一般汉赋完全依靠所谓“奇字”的堆叠,而是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11]113。尽管如此,枚乘的赋作也因对事物铺写过多,因而减弱了说服力。该书还认为封建文人把司马相如和屈原、司马迁并列是一种偏见,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被夸大了。他的代表作《子虚》《上林》表现方式呆板,《大人赋》用字多生僻,艺术价值不高。王褒的赋作文笔虽生动简洁,但在描写劳动人民时却明显带有嘲弄的口吻,所以思想内容的价值也不高。张衡的《两都赋》在体制上可堪称鸿篇巨著,但其文学价值也不高。而对扬雄、班固等人的赋作,只是略加提及,一带而过[11]122。
该书论述汉赋所用的章节极少,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也只是进行了概述,从总体上评价了优劣。书中沿用了两汉以来的汉赋评价观,仍以现实功利性为准绳来衡量汉赋的价值。此书被许多高等院校作为教科书,所以书中的汉赋观对其后的汉赋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于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另一本为高等院校中文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教科书。此书涉及汉赋的篇幅也很少,主要论述了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和张衡等人及其作品。该书指出贾谊是汉初唯一一位优秀的骚体赋作家,其作品兼有屈原、荀卿二家体制,在当时独树一帜。关于枚乘的代表作《七发》,此书指出他标志着汉代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它在艺术上的成就却很低,它的铺写过繁,刻画有余,生动不足。对于司马相如的赋作,此书则持否定态度。认为《子虚》《上林》歌颂了汉帝国无可比拟的气魄和声威,这在政治经济空前繁荣的局面下确实具有现实意义,但司马相如作品的主要部分在于夸张帝王的物质享受,渲染贵族宫廷生活骄奢淫逸的风气,迎合了武帝的好大喜功[12]121,即使是赋末的委婉致讽,也只是扬雄所谓的“曲终奏雅”,实际上起不了多少讽谏作用。此外,书中还指出司马相如的赋作在大势铺张,使用大量的连词、对偶,层层渲染,增加了作品富丽文采的同时,但也往往夸张失实,“虚而无征”,铺张过分,转成累赘。而且由于层层排比,呆板少变,堆砌词藻,好用奇词僻字,读之令人生厌[12]122。而且,两赋中所表现的时代风貌并没有真正反映出时代的特色,只是一种非常畸形和表面的描绘,所以,此书认为司马相如的赋作并没有多少价值可言。但书中却指出司马相如的赋作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原因在于它确立了一个“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
汉赋以歌颂王朝声威和气魄为其主要内容,后世赋家相沿不改,遂形成了一个赋颂传统。如果说这种传统在司马相如时代还不是全无意义的话,那么,随着时代的变化,它往往流为粉饰太平,对封建帝王歌功颂德而全然失去了意义。尤其是他们所形成的大赋体制,被后世赋家所效仿,愈来愈失去了创造性。
教材中的汉赋观对其后的汉赋研究影响深远,被大多数汉赋否定论者所沿用。“赋颂传统”“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不仅成为了20世纪全盘否定汉赋价值者的统一论调,而且也成为了汉赋研究争论的焦点。
三、结语
古人对汉赋的评价不一。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王国维则赞之为“一代之文学”。在汉赋研究繁荣的20世纪,这样的争论依然存在,尤其是作为高校教材的《中国文学史》,继承了儒家的文艺观,对汉赋提出了严厉的道德批评,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和过激的倾向。但较之以往的汉赋研究,20世纪对汉赋的研究除了道德批评以外,也有了新的变化:部分学者肯定了汉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汉赋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为后代文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有学者也肯定了汉赋在丰富文学体裁、丰富文学词汇方面做出的贡献;还有学者从音节、声韵角度研究汉赋,拓展了汉赋的研究领域。这样的发展变化体现了20世纪的汉赋研究者逐渐将汉赋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这是汉赋研究的一种进步。
[1]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24.
[2]龚克昌.论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J].文史哲,1987(2).
[3]徐宗文.“辞”“赋”“颂”辨异[J].江海学刊,1984(6).
[4]王缵叔.略论汉大赋的泯灭[J].文艺研究,1981(2).
[5]何新文.关于汉赋的“歌颂”[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5).
[6]章沧授.论汉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2).
[7]郑在瀛.“赋自诗出”浅证[J].北方论丛,1980(6).
[8]姜书阁.汉赋通义[M].济南:齐鲁书社,1989:58.
[9]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5-37.
[10]马积高.论赋的源流及其影响[J].中国韵文学刊,1987(1).
[1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2]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编辑:文汝)
G122
A
1673-1999(2017)11-0085-03
杨海霞(1984—),女,硕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文论。
2017-07-1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世纪汉赋研究史论”(15XJC75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