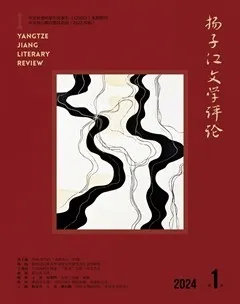《登春台》与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创作特征
2024-04-14颜水生
自从进入新时代以来,“讲好中国故事”就成为中国小说家的共同追求,长篇小说创作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长篇网络小说和长篇科幻小说愈发繁荣,传统型的长篇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艺术质量有了很大提升,如梁晓声的《人世间》、陈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徐则臣的《北上》、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王跃文的《家山》、葛亮的《燕食记》、艾伟的《镜中》等长篇小说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时代中国小说家一方面努力汲取中国文学的艺术传统养料,另一方面积极借鉴域外文学的创作资源,使传统型長篇小说在文体形式、叙事技巧、思想内涵等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特征,比如杂糅式的文体形式、现代主义的叙述技巧、辩证性的哲学意蕴,格非的长篇小说可谓是典型代表。格非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后,又陆续创作了《望春风》 《月落荒寺》等长篇小说,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最近出版的长篇新作《登春台》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了新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创作特征和发展趋势。
一、小说传统与文体形式
2012年,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强调了中国传统的“说书”艺术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说书”也就是“讲故事”,“说书”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小说,也对中国当代小说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赵树理到莫言的当代小说创作都有着鲜明的“说书”痕迹,比如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梁晓声的《人世间》和徐则臣的《北上》,都有“说书”的烙印。在20世纪80年代,格非以独特的叙事技巧和小说风格被誉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但在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格非有意识地、积极地借鉴中国小说传统。他不仅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说书”传统,而且在新时代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大量运用了“说书”艺术。“江南三部曲”中大量镶嵌的中国古典诗词曲赋,可以说是格非由“先锋”转向“传统”的重要标志,格非在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望春风》中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说书”艺术,最近出版的《登春台》又对“说书”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登春台》是一部典型的“说书”体裁的长篇小说。从叙述形式方面来看,《登春台》使用了传统“说书”艺术中常见的“讲故事的人”来叙事。虽然格非曾经质疑“将小说定义为‘讲故事的艺术”a,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早期小说通常是故事的记录形式”b。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于陆秀米、张季元、谭功达、姚佩佩等人的故事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传奇色彩,“江南三部曲”都可以看成是故事的记录形式,只不过“江南三部曲”没有明确出现“讲故事的人”。从《望春风》到《登春台》,“讲故事的人”登堂入室并在小说中发挥了多种作用。格非在《望春风》中把赵伯渝设置为“讲故事的人”,《登春台》则设置了多个“讲故事的人”,如沈辛夷、陈克明、罗记者、窦宝庆等,轮替讲述故事。他们既是小说人物,又是小说中的“讲故事的人”。赵伯渝向小说读者讲述儒里赵村的故事,《登春台》第一章由沈辛夷向姚芩讲述沈辛夷自己和母亲的故事,第二章则由陈克明向沈辛夷讲述陈克明自己的故事,第三章是陈克明阅读由罗记者采编的窦宝庆的故事,第四章是窦宝庆拼凑的关于周振遐的见闻、谣传和故事。从小说结构方面来看,从“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风》,格非喜欢运用“四章”的定型结构并且拟定了每个章节的标题。《登春台》在主体四个章节的前后分别增加了“序章”和“附记”,其中的“序章”相当于中国古典说唱文艺作品中常见的“楔子”。格非在“序章”中交代了周振遐的生病经过以及姚芩、陈克明、沈辛夷等人物身份,也说明了第一章的故事来源和讲述方式,“附记”则告知了周振遐出院后姚芩、陈克明、窦宝庆等人物的近况,最后又回到沈辛夷向姚芩讲故事的场景,从“序章”到主体四个章节再到“后记”,《登春台》形成了一种圆形结构,使人物在小说中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从叙事技巧方面来看,格非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大量使用了“说书”套语,比如“你容我慢慢道来”“好吧,我们长话短说”等。格非在《登春台》中还大量使用了“说书”艺术作品中常见的“扣子”,比如小说第一章结尾设置了悬念,格非以沈辛夷的口吻提出窦宝庆的去向问题,并且强调每当提起窦宝庆这个人,同事们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这是典型的卖关子写法,使读者对窦宝庆的故事产生好奇和阅读兴趣。又如小说第二章结尾提到窦宝庆与一桩残忍的凶杀案联系在一起,不仅交代了第三章的写作方式和叙述人称,也为第三章讲述窦宝庆的故事埋下伏笔。
格非在《登春台》中不仅借鉴了传统“说书”艺术,而且对“说书”传统进行了转化和创新。首先,格非在《登春台》中创造性地设计了众多“听故事的人”,使其与“讲故事的人”形成了多重复杂的对话交流情境。众所周知,“说书”体小说大都设计了隐含的听众,正如本雅明所说“听故事的人总是和讲故事者相约为伴”c,从赵树理到莫言的小说都是如此,《望春风》中的“亲爱的读者朋友”也是虚拟的“听故事的人”。《登春台》第一章的姚芩、第二章的沈辛夷都可以看作是“听故事的人”,他们分别聆听了沈辛夷和陈克明讲述的故事,从而形成了“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的交流情境。《登春台》第三章由罗记者编写/讲述“你”(窦宝庆)的故事,“你”(窦宝庆)既是第三章的主人公,同时又是第三章中的“听故事的人”,因此,第三章隐含了“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的转化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你”(窦宝庆)还是第三章中的“讲故事的人”,窦宝庆给郑元春讲了多个故事,使窦宝庆与郑元春之间形成了“讲-听”故事的关系。第三章不仅形成了多重复杂的“讲-听”故事的人物关系,而且形成了明显的对话交流情境,如小说写道:
当你的讲述陷入停顿的时候,郑元春将削好的苹果递给你,冲你笑了一下:
“我听着呢,你接着说!”
——《登春台》d
这里不仅阐明了人物之间“讲-听”关系,也推动“讲故事的人”继续讲下去,从而成为小说的叙事动力。《登春台》不仅虚拟了“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的对话交流情境,而且描绘了“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在“讲-听”故事时的心理状态,如小说写道:
本来,你以为,故事讲到这一段,郑元春一定会被吓得六神无主,小脸儿发绿。可是,她比你想象的要镇定得多。她慢悠悠地泡茶,不时瞄一眼叮当作响的手机。
这里区分了“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对故事的不同态度,“讲故事的人”以为故事惊心动魄,而“听故事的人”则漠不关心,从而表现了“讲故事的人”的孤独处境。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叙述人称随着故事主人公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格非分别使用了“她”“我”“你”“他”四种不同的人称。《登春台》第三章中的叙述人称显得尤为独特,使用了小说作品中非常罕见的第二人称“你”的叙述方式,第三章在总体上是以记者写/讲故事的方式讲述窦宝庆的人生经历,第二人称叙述方式不仅使小说隐含了虚拟交流情境,还让罗记者与“你”形成了“讲-听”故事的人物关系。由此看来,《登春台》中的“听故事的人”和叙述人称比以往的“说书体”小说都更为丰富复杂,这样使小说形成了多重复杂的故事线索和对话情境。正是从这个方面来说,《登春台》仿佛一部云集了芸芸众生喜怒哀乐的大型交响曲。
格非在《登春台》中灵活设计“故事”,实现了对传统“说书”体小说的转化与创新。故事在古典小说中不可或缺,尤其是传统“说书”体小说大都追求故事的独特性和传奇色彩,当代“说书”体小说也大都具有传奇性,《红高粱家族》 《活着》 《生死疲劳》 《额尔古纳河右岸》都是如此,《望春风》中的赵孟舒和王曼卿的人生经历也具有传奇色彩。格非曾经认为现代小说的繁荣意味着“‘故事的减损或取消”e,这在《登春台》中有着明显表现,格非以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的故事结构小说,然而他们的故事都是世俗人生的平凡经历,几乎没有独特性和传奇性,也没有传统故事中的转折、发展、突变和高潮,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的故事性。更为重要的是,格非在《登春台》中借小说人物的话明确指出,小說人物的一些故事是拼凑、瞎编、虚构的,完全不同于“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f;尤其是小说中多次指出故事有着无数个分叉,每个分叉都会自动生长出新故事,并且故事本身有一种执拗神秘的力量,能够自动讲下去,也能够阻止“讲故事的人”讲下去,这在一定程度上了消减了“讲故事的人”在小说中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方面来说,《登春台》充分暴露了现代小说中的“讲故事”艺术与“故事”本身之间的悖论,因为传统“说书”体小说遵循的是“故事”的逻辑,而现代小说虚构“故事”遵循的是“感觉”的逻辑。此外,《登春台》四个章节分别讲述了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四人的人生经历,仿佛四篇人物传记,因此又可以说《登春台》是一部典型的纪传体长篇小说。纪传体是司马迁创立的文体,它通过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事件,纪传体小说形式也是格非的一贯写法,从《人面桃花》 《山河入梦》到《望春风》都是如此。如果说《望春风》以“‘史传笔法”g反映了中国乡村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那么《登春台》则以“‘纪传笔法”反映了中国城市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由此看来,《登春台》通过多种艺术形式丰富了“说书”体小说的创作方法,形成了文体杂糅的小说体式。
二、域外镜鉴与小说技法
新时代长篇小说文体形式极为丰富,除了说书体和纪传体,方志体长篇小说也逐渐“潮流化”h,如贾平凹的《秦岭记》、王跃文的《家山》、林白的《北流》、乔叶的《宝水》、付秀莹的《陌上》、刘汀的《老家》等都可以说采用了方志体,此外李洱的《应物兄》和吴亮的《朝霞》可以看作记言体,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余华的《文城》和阿莹的《长安》可以看作传奇体。新时代长篇小说的说书体、纪传体、方志体、记言体、传奇体等文体形式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然而,东西的《回响》和房伟的《血色莫扎特》的侦探体以及格非的《月落荒寺》的音乐体更多地受到域外小说文体的影响。实际上,新时代长篇小说文体极为复杂,有些作品不仅众体兼备,而且同时汲取了中外文学作品的创作方法与写作技巧,格非在域外镜鉴方面也可以说是典型代表。
格非具有渊博的知识,他不仅创作了一些体大思精的小说作品,而且出版了众多见解深刻的理论著作,如《小说叙事研究》 《塞壬的歌声》 《卡夫卡的钟摆》 《文学的邀约》等。从这些理论著作可以看出,格非不仅非常熟悉域外小说作品,对托尔斯泰、福楼拜、乔伊斯、卡夫卡等作家作品几乎信手拈来;对域外小说理论也深有研究,诸如本雅明、昆德拉、纳博科夫的理论观点经常出现在他的著作中。格非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大多借鉴了域外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方法,诸如意识流、“冰山”理论、叙事空缺,回忆叙事,他的《褐色鸟群》被誉为中国当代最玄奥的小说。2012年,格非在自己的作品系列集的序言中讨论了作家的“变与不变”,这说明格非“有强烈的革新小说技法的主观动机”i,从《褐色鸟群》到《登春台》,可以看出格非的小说风格一直在不断变化。《登春台》不仅汲取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而且融合了域外小说的创作方法,集中表现了格非努力攀登世界文学高峰的探索精神。
《登春台》借鉴了域外小说理论中常见的“元小说”的创作方法。域外学者对“元小说”现象进行了深入讨论,比如威廉·加斯、戴维·洛奇、帕特里夏·沃等,他们大都把“元小说”定义为“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j,“以强调小说关于自身叙述形式的‘反身指涉和‘自我意识”k。实际上,“元小说”并非域外小说的发明,在传统“说书”体小说中,虽然“作者在‘讲述,读者处于‘聆听者的位置,他既不质询,亦不追问,更谈不上积极的合作、介入、创造”l,但是仍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评书、说书人传统中,就有诸如‘话说曹操这种强调叙述者叙述的自我意识”m。从这个方面来说,格非大量运用“元小说”创作方法是中外文学互鉴的产物,这在《望春风》 《登春台》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望春风》多次表现了小说叙述者的“反身指涉”和“自我意识”,如小说第一章“妈妈”小节中,叙述者不仅交代了避免谈论妈妈的理由,而且强调作家“应该尽量忠实地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记录下来”n。又如在第四章中,叙述者多次提到春琴要求删改故事,还指出“我在写作时已尽可能地使用了烟云模糊之法,写得极其隐晦”o。这些都是在小说中讨论该小说的写作方法和叙述行为,从而“强调故事真实性引导读者认同叙述的可靠性和权威性”p。《登春台》也有许多讨论写作行为和故事本身的语句,如: “其中也有一点虚构的成分,您不妨把它当作小说来读。”这种讨论是在强调叙述行为和故事的虚构性,明显不同于《望春风》强调叙述行为和故事的真实性。
又如:
这个故事将出现无数个分叉,而每一个分叉上,都会生长出一个新故事来。你发现,根本用不着怎么编,故事本身就能自动讲下去,你跟着它往前走就行。
这里是在讨论故事本身,强调故事本身具有生长能力,认为故事可以脱离叙述者,甚至可以阻止叙述者的讲述。由此看来,《登春台》在整体结构上构建了一种“反身叙述”系统,不仅强调了叙述行为和故事本身的虚构性,而且通过模糊小说人物、叙述者、故事、读者之间的界限,最终“使读者拒绝认同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性和权威性”q。
《登春台》通过“元小说”这一创作方法,不仅实现了与后现代主义小说理论的对话,而且实现了与域外经典小说作品的对话。格非经常在小说中讨论写作过程和写作方法,并且引用域外经典小说作品进行比较,比如:
你不能向我抗议说,故事讲到一半,怎么又弄出个全新的人物来。正如你不能向夏绿蒂·勃朗特抱怨说,为什么在简·爱和罗切斯特的关系渐入佳境时,阁楼上硬生生地又冒出一个伯莎来。你无权提出这样的质疑,原因在于,阁楼上的那个疯女人,只是你看不见她而已,在桑菲尔德的庄园里,人家其实一直都是在的。蒋承泽也是这样。在大部分场合,他并不掺和到我的故事中来,但这不等于说,此人的存在,和我们的故事完全没有关联。
这里是把陈克明讲述的故事与《简·爱》进行比较,强调在故事讲述过程中插入全新人物是世界名著的惯用写法。这个观点可谓是对域外现代主义小说的经典概括,比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等小说的故事走向大都是通过人物的感觉来安排,甚至故事自己会往前走。格非认为这些小说家“在讲述故事时,不再依赖时间上的延续和因果承接关系,它所依据的完全是一种心理逻辑”r。福克纳、乔伊斯、普鲁斯特可以随时介入故事或者抛开它而进入另一个故事。这里既讨论了小说的写法,又把《登春台》中的蒋承泽与《简·爱》中的伯莎联系起来,两者都是高深莫测、云遮雾罩的人物形象。在《望春风》中,格非也试图将赵伯渝讲述的故事与《一千零一夜》进行比较,并说可以模仿《一千零一夜》的结尾来结束整部小说。这种在小说中讨论作品的写作过程和写作方法的现象,不仅表现了格非具有强烈的革新小说创作方法的意识,而且为“故事的叙述结构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为故事的走向提供了一系列新的美学原则”。s
格非不仅借鉴域外经典小说作品的创作方法,也努力与域外名人进行思想对话。《登春台》中提到了许多域外作家,比如沈辛夷长期像法国作家普鲁斯特一样终生都为“声音”而苦恼,桑钦身上有一种梭罗式的“寂静的绝望”;又如小说中提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提婆达多,这些对沈辛夷和桑钦的形象塑造具有重要作用。格非不仅喜欢通过域外作家的特征来描绘小说人物的生活和性格,而且列举了许多域外名人名言,比如莎士比亚的“时光催人急如星火,原来世上未曾有我”、卢克莱修的“死亡所至,我不在彼;我之所在,死亡不至”,以此来揭示小说人物的思想状况和精神状态。《登春台》还把黑格尔、尼采、谢林等哲学家的深奥晦涩的哲学观点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笑谑事件,以此表现了陈克明的浅薄和可笑,也表现了格非的幽默感和丰富的知识。《登春台》叙述方式的不断变化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方式,也使小说获得与哲学同样的思考深度。由此看来,《登春台》中出现的名人名言大都与小说人物融为一体,不是可有可无的知识堆砌,而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辩证思维与哲学意蕴
格非是小说形式的探索者和创造者,几乎所有的小说形式都被他运用得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小说在格非笔下俨然成了一种游戏。在“说书”体的文体形式和“元小说”的叙述框架中,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的角色不断发生变化,这些人物“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进行互动交流、解决问题和推动故事情节”t,使《登春台》与当下流行的以角色扮演为核心的“剧本杀”游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转化传统和域外镜鉴主要表现出格非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那么格非通过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的人生经历透视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从而使《登春台》延续了《月落荒寺》的思路,则表现了鲜明的辩证思维和深厚的哲学意蕴。《月落荒寺》通过对众多哲学家、哲学观点的描绘与阐释,则表现了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月落荒寺》中的哲学教授林宜生的名字在《登春台》中再次出现,或许暗示了两部小说在主题思想或哲学意蕴方面存在联系;黑格尔、谢林、海德格尔、卢克莱修等域外哲学家的名字及观点在《登春台》中的大量出现,也表现了《登春台》与格非以往小说的区别。《登春台》开篇第一句话就包含哲理意蕴,正所谓每个人降生的瞬间极其相似,离场的方式又各有不同,由此揭开了小说人物不同的人生命运。周振遐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人物形象,他经常在大街上观察陌生行人,以揣测、臆想尘世人生的命运。小说通过周振遐揭示了人终将永远消失或寂灭,人的生命只不过是两个虚空之间短暂的火花闪动,人在生前暗昧、死后则沉寂,从而体现了格非对人类命运的悲悯意识。声音景观一直是格非透视社会状况和人类命运的重要途径,如果说《月落荒寺》通过众多的音乐曲名及音乐演奏场景再现了多种多样的声音景观,那么《登春台》则通过一些深奥的声音话语和精细的声音描摹,再现了格非对声音的心灵感受和哲学思考。
格非对声音有一种深刻而又独特的认识,他经常赋予声音以深厚的哲学意蕴。在20世纪90年代,格非曾经把自己的一部小说命名为《寂静的声音》,起因是他与一位菜农谛听了乡村树林中的寂静之声。在《望春风》中,拆迁后的儒里赵村远离市声,惟有死一般的寂静。无论是记忆中的乡村,还是现实中的乡村,格非似乎对静寂的声音带有深刻的懷念和向往。如果说《春尽江南》和《月落荒寺》中的音乐之声大都体现的是审美意蕴,那么《登春台》中的声音话语大都具有哲学意味。在《登春台》中,周振遐在昏迷时听到的庄重而又遥远的声音其实就是对人生价值的哲学思考,小说引用牛顿的名言“上帝是关联的声音”,认为声音暗示了文明发展的既定轨迹,隐含着一种将世间万物联系在一起的绝对性逻辑。这正如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所揭示的,“声音是在普遍形式下靠近自我的作为意识的存在”u,不仅个体意识的在场是通过声音建立起来的,人类历史的在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通过声音建立起来。德里达认为“声音之谜似乎对于声音在此要回答的一切都那样纷繁深邃”v,《登春台》中的声音也具有丰富复杂的形而上学意义。周振遐人生最后的愿望是去海上的荒僻渔港听听风声,或许他只有在风声中才能够靠近自我,才能够寻觅到人生的意义,他已经把声音看作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这也就是德里达强调的“现象学的声音就是在世界的不在场中的这种继续说话并继续面对自我在场——被听见——的精神肉体”w。
格非不仅揭示了现象学的声音,也精细描绘了众多声音的现象。《登春台》十分重视声音的意义,小说通过声音景观描绘了喧嚣的社会景观。格非在《登春台》序章第一节通过周振遐的视野描绘了尘世繁忙的都市景观和意蕴深厚的声音景观,道路上人流穿梭,但所有人都心事重重、神情肅穆,彼此之间从不交谈,除了汽车的鸣笛声,甚至听不见杂沓的脚步声,四周弥漫着诡异的寂静。格非描绘的“诡异的寂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消极寂静”,是为了突出城市的噪音和喧嚣。众所周知,“现代城市是一个‘声效战场(sonic battleground)”x,尤其是公路上充斥着汽车的轰鸣声、汽笛声、车轮声、刹车声、撞击声等各种噪音,行人饱受这些噪声的侵扰却又无可奈何,他们被汽车噪音所压制,以至于“听不见杂沓的脚步声”,他们不得不以一种否定性反应来抗拒噪音和喧嚣,因此,这种“诡异的寂静”“更多时候表现为一种‘听而不闻(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的孤独、空洞与麻木”y。《登春台》不仅描绘充满噪音和喧嚣的城市景观,还塑造了一些饱受噪音和喧嚣折磨的人物形象,比如沈辛夷因长期深陷噪音而苦恼、焦虑甚至崩溃,那些纷纷攘攘、无止无息、无孔不入的声音成为她每天必须面对的炼狱。沈辛夷甚至认为自己“被抛到了一个无形的、陌生的、由各种声音组织成的嘈杂空间里”,世界上已不存在“寂静”,各种各样的声音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又如周振遐自工作以后就住在阴暗、嘈杂、脏乱的筒子楼,后来又长期遭受邻居们的“声音入侵”,这几乎让他感到生无可恋。《登春台》精细描绘生活中的噪音和喧嚣,不仅表现了沈辛夷和周振遐的听觉感受和生存状态,而且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在小说中是“妨害”的意思,这样看来,小说主题俨然有些接近“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哲学。
格非通过声音景观表达了对宁静和谐生活的追求。正如喧嚣与寂静是相对立的词语,无论是对喧嚣的积极抵抗还是消极抵抗,实际上都是在追求寂静或宁静的和谐生活。在《望春风》中,叙述者赵伯渝牢记了堂哥杜撰的一则格言:“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z在《登春台》中,沈辛夷为数不多的快乐记忆就是童年时期与父亲一起在乡村生活,父女俩到访过的寂照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寂静的地方。沈辛夷小时候通常在各种声音中安然入睡,小说描写了一处声音景观:
风声。雨声。雷声。大雪压断松枝的声音。竹鹧鸪在山林深处的鸣叫声。竹笋在春雨中从土里冒出时发出的拔节声。院子里的知了以及不知名小虫的低声吟唱。溪水在初夏暴涨时的泄水声。那里,恰恰是这些声音所织成的厚茧,保护并滋润着她黑甜的睡眠。
这里表面上是在描摹声音,实际上是在恭听大自然的和谐乐章。周振遐多年来对安宁和自在也有着苛刻追求,他觉得降生在喧腾纷攘的人世间的目的就是为了寻觅不被打扰的宁静独处,他喜欢一个人独坐窗前饮茶静坐,他把在万籁俱寂中看风景当作人生难得的乐趣。周振遐就像瓦尔登湖畔的梭罗以及那些有出尘之想的隐逸人士。这正如从《老子》中的“鸡犬之声相闻”到《桃花源记》中的“鸡犬相闻”,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是通过声响来表达对宁静和谐生活的追求。
喧嚣与寂静作为一种对立的声音现象,在小说中的同时出现也就成为一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格非对人物关系的思考也是辩证性的,他不仅揭示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提婆达多”,也表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贵人”,比如周振遐就是陈克明的贵人,让他在跌倒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如此看来,《登春台》中的辩证性哲学意蕴无疑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超越。辩证性的哲学意蕴在李洱的《应物兄》、艾伟的《镜中》等小说中都有着鲜明表现。比如《应物兄》中出现了众多哲学家或哲学观点,无论是从柏拉图到霍克海默,还是从孔子到王阳明,李洱不仅重视哲学的现实性,还更重视哲学的辩证性,为此李洱在《应物兄》中安排文德斯出版了一本名为《辩证》的哲学著作。又如《镜中》的对称美其实也就是对中国传统的阴阳哲学的追求,小说通过庄润生的人生遭遇表达了对人生苍茫和生命无常的悲悯。《镜中》引用的《金刚经》 《法华经玄赞》以及《老子》中的名言,不仅使小说作品与中国古代哲学形成了对话,也使小说作品表现了辩证性的哲学意蕴。
结 语
格非认为:“写作应是一种发现,一种勘探,更应是一种谛听。” @7所谓“谛听”,也就是谛听声音,《登春台》通过传统讲故事的方式,不仅使小说在整体上构造了一种声音话语,而且使读者在形式上构成了一种谛听。格非通过发现和谛听,不仅感悟到人生真谛,也感悟到文学创作的精髓,他一方面对中国小说传统进行转化和创新,另一方面又积极从域外小说借鉴经验,把传统“说书体”小说与域外“元小说”融合起来,以坚持不懈的勘探创造了当代小说的新形式,表现了强烈的文体创新和文学探索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格非在小说中大量运用“元小说”叙述和名人名言,有可能使小说作品陷入热奈特所说的“议论对故事,随笔对小说,叙事话语对叙事的‘入侵”@8,因而可能影响小说的阅读效果。由此看来,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发展不仅要积极汲取古今中外的文学资源,更要“超越欧美现代性资源的理论阈限”@9,才能创作出符合中国老百姓审美需求和阅读习惯的优秀作品。
【注释】
abe格非:《故事的消亡》,《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53页、52页。
cf[德]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 论尼古拉·列斯克夫》,[美]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10页、99页。
d参见: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版,以下引文皆出自此版,不再一一作注。
g孟繁华:《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长篇小说的基本样貌》,《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
h晏杰雄:《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3期。
i格非:《变与不变(代序言)》,《欲望的旗帜》,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j[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 页。
kpq王丽亚:《“元小说”与“元叙述”之差异及其对阐释的影响》,《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lrs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48页、48页。
m高孙仁:《元小说:自我意识的嬗变》,《国外文学》2010年第2期。
noz格非:《望春风》,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74页、385页、313页。
t罗长青:《现场社交:戈夫曼拟剧视域下的剧本杀现象考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uvw[法]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1页、17-18页、18页。
xy张聪:《从“神圣噪音”到“世俗寂静”——嗓音政治及其反叛》,《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3期。
@7格非:《小说的十字路口》,《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8[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9颜水生:《跨学科融合:风景研究的历史逻辑与当代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0期。
作者简介※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