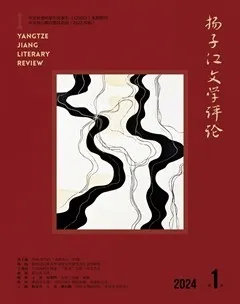史诗气度与“三部曲”新模式
2024-04-14徐勇
徐勇
被誉为宁夏文坛“新三棵树”之一的作家张学东,其最新作品《西北往事三部曲》 (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让人瞩目。这是三部长篇小说的合称,凝聚了作者近20年的持续思考和探索。三部作品,表面看来风格各异,人物不同,彼此之间总体风貌的差别之大,让人有硬塞强加的感觉:“三部曲”之“三”字似乎只是数字的简单叠加。但若细细思之,便会发现三部小说之间,其实有着内在的关联和生气灌注的东西。三部小说,表现在整体上,彼此之间构成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和浓重的重复意味。这种关联,不能简单理解为三部之间表现出时间上和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上的切近——都是以1958年后的西北作为故事发生的时空坐标;这种关联,最主要的表征就是,三部小说都是在写成长,而且是父辈的具有创伤记忆的成长。因此,这里的问题就变成,成长的个人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成长中的个体,面对时代的错动与狂热,是被动地做出反应,还是主动适应迎合。而事实上,不论是主动迎合还是被动反应,个人的选择空间总是极其有限的,我们既深陷在自己所属时代的主导精神的束缚之下,也无力挣脱作为“人”的构成部分的欲望的控制,因而某种程度上,成长过程中的时间的流转所带来的,就常常可能是永劫轮回的沮丧和疲劳。张学东的小说显示出来的正是这种永劫轮回的沮丧和突围的艰辛的辩证关系——我们虽无法挣脱施加于我们身上的种种限制,但我们可以做到对自己的放逐或者表现出自我救赎的努力,虽然这其中的自由总是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但也足够让人唏嘘感叹,感动不已。
一
第一部(卷一)讲述的是关于狗的故事。故事主要围绕着两条狗和两个人之间展开,这里既有狗与狗之间的同气相求,也有狗与人之间可能产生的深厚友谊:它(他或她)们(狗与狗,狗与人)之间可能存在误解、敌意,甚至伤害,也有彼此间的同情和心心相印;小说所着力聚焦的就是这样的过程。而这些,又都与特定的历史年代,比如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密切关联。这就使得狗与狗或狗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沉重的社会历史内涵,即是说,这看似是在写狗与狗或狗与人之间的关系,着力点却在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着特定语境的刺激而变得紧张、畸形而不可信时,反而不若狗与狗或狗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得纯粹和自然。某种程度上,这是借狗与狗或狗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小说中其他关于社会历史的表现,都是建基于此一关涉点上,我们不能脱离这一关键,而过度强调作者重写历史的野心,当然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作者献给女儿的礼物(见张学东《写给女儿的一本书》)那么简单。
这也意味着,小说其实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表面上,狗与狗或狗与人的关系,是这部小说的主题,两条狗“大黄蜂”和“坦克”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内在结构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真正决定着小说中狗与狗或狗与人的关系的设置。即是说,我们应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去理解狗与狗的关系和狗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相反。这是我们进入这部小说的抓手。我们不应跟从或被作者的叙述节奏所左右。
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论,这部小说采取的是儿童的陌生化的视角。小说主人公刘火所在的镇上和镇中心学校,开始是一个祥和与秩序井然的世界。外地女孩谢亚军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宁静。她的名字的男性化和她的穿着的洋气,凸显出她的新奇异样,立刻引来了同学们的“多少有些粗鲁和怪诞”的“嬉笑”。刘火和谢亚军的关系由此生发,刘火、谢亚军和同学们的关系也从此刻埋下伏笔。这种关系里面,有着外来者和本地人的陌生化关系,也有着男性同学对女性同学的欲望化的窥视成分,同时也有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种种关系之下,围绕刘火和谢亚军之间,形成了镇上青少年之间的错综关系。
就该小说而言,儿童化视角的好处是,能撇开所有无关的枝蔓,而只需关注儿童的所见、所闻和他们所感兴趣的事情。这是介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视角,儿童的理解能力的限制,决定了他们眼中的事情,多少有着主观视角和限制叙事的倾向。这就需要读者自己的判断。小说其实是以狗与狗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所构成的鲜明反差来表现主题的。表面看来,狗与狗(“大黄蜂”和“坦克”)之间,从一认识似乎就显得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但这种表面的紧张关系背后却是狗与狗的关系的纯粹:它们之间一旦熟识起来,彼此气息相通,就变得亲密无间。这正好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反。人与人之间看似彼此客气、友好和秩序井然,但其实横亘着秘不可宣的利益考量和权力竞逐。人与人之间文明关系的外表之下,是彼此间的赤裸裸的欲望,陷阱丛生。
另一重对照还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都由狗与狗之间的关系所引起。小说情节的推动力,总在狗身上。狗充当了小说情节联结的纽带。“大黄蜂”与“坦克”的撕咬,带出了刘火与谢亚军姐弟的关系;“大黄蜂”咬伤了工作队,招致了刘火和谢亚军弟弟谢亚洲的被羁押;“坦克”的缺席导致谢亚军被骡子强奸,又是“坦克”最后报复了骡子,如此等等。这使得另一重对立,即偶然与必然的对立凸显。表面看来,小说的情节之间,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这一方面是因为狗的行为总具有情境的随意性,以狗的行为所推动的情节之间因而不免缺乏必然的逻辑关联。比如说谢亚洲被刘火误伤就是一例。这里面有太多的偶然,如果不是偶然遇到“坦克”,就不會出现“大黄蜂”和“坦克”的第二次撕咬;如果不是“大黄蜂”在首战中失利,落得伤痕累累,刘火不会架起弹弓助阵;如果谢亚洲不做出奔跑的动作,弹弓就不会打到谢亚洲的眼睛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由偶然性引发,却具有极大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彼此间的不理解和信任感的缺失,钩心斗角和相互算计,以及人性中的恶的面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程度,当然与特定年代有关。特定年代的社会关系,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畸形关系的推动器,但却不是根源。比如说花嫂,她的丈夫在矿难中牺牲,她也是“被损害的”,但她同样也是一个施害者,她间接导致了自己唯一的女儿绝食而死。这里面,是人性的阴暗面在起作用,而与时代社会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其关乎更多的是人的自私自利以及与私有财产观念息息相关的冷漠。对此,我们能予以道义的批判,却很难苛责。这可能就是现实的残酷吧。小说通过狗与狗之间的纯粹,写出的就是这种现实的残酷性。
这种现实的残酷,是被包裹在青少年主人公的成长主题中展开的。这一成长主题,涉及友谊、背叛和伤害,同时也指涉忠诚和心灵相通。换言之,成长是在伤害和理解中逐渐完成的。这可以说是第一部的主题。残酷,但也让人感动,这是在互相伤害的前提下的成长。但作者又让人看到,互相伤害之下,仍旧有着深深的心心相印和彼此的互信互助。这一互信超越了算计,超越了权力。这毋宁说是世界上最为美好的感情。而且,这一感情,作者是以狗与狗之间和狗对人的感情表现出来。因此,某种程度上,作者在这里提出来的其实是“感觉的逻辑”命题:这是感觉对理性的克服,是感觉的胜利。因为,在狗与狗之间,在狗与人之间(这里的主体是狗),狗评判人和同类的标准是感觉或感官:它们靠嗅觉,或者说直觉行事,而且它们始终以这种直觉作为自己行事的依据,一刻没有改变。那么人类呢?他们评判对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由此不难看出,张学东其实是借狗的“感觉逻辑”展开对人类理性智识的批判。
当然,作者采取的是欲擒故纵的手法。小说伊始,先从镇上的本地狗“大黄蜂”写起,才写到“大黄蜂”的主人刘火。小镇上出现一条陌生的绰号“坦克”的大狼狗,狼狗构成了本地狗们的挑战,于是乎就有了“大黄蜂”同狼狗之间的殊死较量。第一个回合以“大黄蜂”的失败告终。这是狗與狗之间的关系,纯粹而自然,它们的关系,是从剑拔弩张开始的。但随着彼此的接近和熟识,它们的关系开始变得亲密起来。“大黄蜂”和“坦克”之间的友谊,在它们同野狼之间的战斗中发展起来。通读小说不难发现,狗与狗之间的关系中,起着维系作用的是那种脾性的适合与否,而不是利害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算计。它们通过全部的感觉,而得出朴素的真理:值得交往,生死相托。
二
三部曲中,第二部(卷二)最是奇特。小说以一种充满诡异的隐喻和寓言(或预言)的形式开篇,颇有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流风余韵:
秀明老师怎么也忘不掉,那年冬天的早晨,有个男社员怒气冲冲地闯进她的课堂,硬把一个学生从她的眼皮底下提溜走了。
那是我们羊角村有史以来,腊月里最寒冷的一天。那天的空气里仿佛暗藏着无数看不见影儿的针尖和麦芒,冰冷坚硬地戳刺人脸……
无须继续援引大段的描述,便可明白一点:小说其实是告诉我们,羊角村此后发生的所有一切,都可以从这一刻中找到蛛丝马迹,羊角村的历史将从这一天起发生逆转。而这也意味着,这一刻的主人公——秀明的学生——将作为整部小说的主人公出现。红亮就是这样一个学生,有趣的是,他甫一出场就在随后小说叙述中消失了。小说讲述的羊角村的大部分故事,其实都与红亮无关。
但实实在在,羊角村此后发生的一切又都有着红亮的影子。他是以“缺席的在场”的方式影响着羊角村,他就是羊角村的每一个人,当然他又与羊角村的每一个人都不同。而说他是羊角村的每一个人是因为,红亮身上背负着宗教意义的原罪,他之所以被父亲“提溜”出教室,是因为他小小年纪就用刀捅伤了屠夫三炮。他的消失,因而也就具有了逃避和自我救赎的双重意味。与他相反,羊角村的每一个人则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以他们的行动演绎着欲望、罪恶、暴力倾向和杀戮的人性之恶的本相。他们是自己的奴隶,他们得不到解脱。从这个意义上讲,红亮的消失,则显示出逃避自我和解脱自我的可能,而事实上,小说就是这样刻画红亮的:他的出生就具有这样的意味,母亲生下他难产而死掉,他的出生就是原罪的表现;同时,他的出生又被小说叙述者做了神秘的解释——“据说正是这一天,我们羊角村的所有屋顶、树杈、草垛、墙头,乃至整个村子的上空,到处都是鸟雀成群地飞来飞去”“这叫百鸟朝贺,羊角村该有贵人降生了!”祥瑞与灾难共存,这就是红亮出生这一刻的情况。理解不了这点,便可能失去对小说的有效把握。
祥瑞与灾难共存的隐喻,其实是给小说设置了一个总的基调:这是即将毁灭的村庄,也是一个即将浴火重生的所在。红亮作为小说主人公,正是这种毁灭和重生之间转化的可能性的显现。这样来看,小说中的人与事就处于一系列二元对立之间:恶/善、原欲/禁欲、狂热/冷静、感性/理性、毁坏/建设、黑夜/白天、无眠/睡眠、暴力/温顺、血腥/洁白、阴/阳、失序/秩序,等等。如果说红亮是构成这一小说的主题和核心主人公的话,那么身处这一系列二元对立中的芸芸众生们,他们中的大多数,则很难说属于上面的二元性中的明确的哪一极。他们属于浑浑噩噩的一群,没有自己的意识,一方面被意向性和欲望所推动,一方面又具有从众性,他们大都属于被动型的人物,有着二元对立之间相互转化着的可能。某些时候,他们会变得极其暴力和血腥,但另一些时候则会变得很温顺,甚至很纯良;他们中的某些人,比如寡妇牛香,即使看似荒淫无度,但其实仍具有不被泯灭的人性之美,比如说广种,看似残暴,但其实是色厉内荏。只有那些有清醒意识的人,他们才会显得具有二元性的鲜明对立性,比如说秀明、三炮、虎大,只不过,前者(秀明)是小说中善的代表,而后面那些(三炮、虎大等人)则是恶的代表。他们之间泾渭分明,是不能互相转化的。
二元对立性,也正表明了循环的存在。这里的循环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芸芸众生的左右摇摆,忽恶忽善,亦恶亦善;一种是三炮与虎大之间构成的重复关系——三炮是对虎大的重复,朱队长是对三炮的重复,他们之间关系的设置,颇类似于新历史小说中所惯用的历史翻烙饼的写法:后一种循环关系,决定着前一种循环关系,以至于羊角村始终处于一种永劫轮回的循环往复的重复之中,其最为显明的表征就是黑夜和白天彼此颠倒,羊角村人突然就颠倒过来了——白天睡觉,晚上干活。走不出这种循环,就无法把颠倒的重新倒转过来。但显然,张学东无意遵循新历史的惯例,他并没有让历史深陷循环往复的永劫轮回之中。同样,张学东也没有重复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的做法,即在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之时,让羊角村所有发生的颠倒重现倒转:倒转的秩序得到恢复,昼与夜的颠倒又被颠倒过来。
张学东的思考显然有了进一步的表现。秀明是绝对的善,但这样的善只是凤毛麟角。绝对的恶,虽也有自我的意识,但却难有自我反思:小说中,虎大是不会反思的,三炮也不可能,他们的结局只能是历史的审判。张学东所聚焦的是作为芸芸众生的民众的救赎与自我救赎的可能性。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人们深陷在这种浑浑噩噩的对立中,很少能有自我的意识,而实际上,对于大多数芸芸众生而言,他们是不可能做到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的。在如此认识下,他转而求助于具有神秘气息的宗教。宗教具有救赎普通芸芸众生的可能性,其神秘的力量,能促使人们幡然醒悟并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深自忏悔。
这样来看,红亮当初用刀捅伤屠夫三炮就具有某种深意在。三炮是绝对的恶的象征(他为了权力,献上了自己的妻子,甚至谋害了自己的父亲),红亮伸向绝对恶的屠刀,让他感到并充满了忏悔之意。这是一种典型的佛教/佛家的普度众生的思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事实上,绝对恶之人是不可能做得到放下屠刀的,所以红亮就只能代替恶人去自我忏悔:他的自我忏悔里面,有代替他人忏悔和赎罪的意思。在小说中,与红亮构成对应关系的是寡妇牛香,她也是一个误入歧途的人,早年为拉扯子女,有口饭吃,她把自己的身体作为礼物献祭给羊角村的头面人物虎大,甚至是三炮。但当她的儿子强奸了虎大的女儿后,她幡然醒悟:原来,她所造下的孽,在子女们身上以另一种形式重复,寡妇和虎大的畸形关系,在他(她)们的子女身上延续。正是在这一重复所昭示的循环关系中,寡妇牛香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深深的罪孽,她于是开始了自我忏悔的漫长之路。她把自己“锁在院子里”,通过每天结绳的方式用无止境的重复劳动惩罚自己;显然,这种惩罚方式有其鲜明的象征意义:这是在用绳子捆缚住自己的原始欲望。不难看出,这样一种惩罚显示出如下的逻辑关系,即“重复”和“循环”只有在自己身上显示出来的时候,它们才能发生伟力。“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这是她从太爷爺讲过的民间故事里听到的,历史就在这一次次的重复中延续下去,历史在在给人以无限的疲劳感,牛香很早就洞悉民间的故事中隐藏的智慧。因而在她那里,通过每天结绳的方式惩罚自己,就是认识到这种重复并试图以一种永恒的方式挽救自己于重复之外,绳子捆缚自己的欲望,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以永恒性抵抗和归顺重复的象征。
三
三部曲中,写得最为感人的应属第三部(卷三)。这部小说最为朴实,最具有主观性色彩,也最为动人。其所表现出来的反讽的力量、对叙述距离的把握,和对人性复杂内涵的揭示,都在在表明小说的浑厚圆融。这部小说显示出作者写实风格的成熟,它无意隐喻和象征(像第一部),也不是侧面映衬的刻画(像第二部),它采取的是正面强攻,用第一人称儿童主观视角讲述。限制叙事而又是正面强攻,这使得小说具有浓郁的“不可靠”叙事性,极具反讽意味。“我”的观察视角呈现出来的世界,是异己的、陌生的和不能理解的,但同样也是充满主观色彩和有着偏见的。一开始,“我”对家庭成员——哥哥、姐姐、弟弟、父母——之间的奇怪关系十分费解。这是一个奇怪的家庭,家庭成员性格怪异,哥哥像狐狸冷酷狡猾,姐姐蓝丫莫名其妙,父亲暴躁,母亲刻薄,彼此之间关系紧张,相互猜疑且充满着刻毒的仇恨。这是作为小环境的家庭的构成。作为大环境的时代社会,则是轰轰烈烈的运动接连不断,此起彼伏。“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在这里,大环境与小环境既构成对应关系,也彼此生发相互促动。大环境的变动频仍,使得本就紧张的家庭结构加速解体,先是父亲被批判收监,而后年仅一岁的哑巴弟弟离奇失踪,中年男人刘庆福的出现,姐姐离家出走,父母长时间的闹离婚等等。“我”游走于家庭和社会之间,既成为家庭中被忽视的存在,也不能真正融入外在世界之中。在这里,家庭关系对“我”理解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小说中关键的一个“事件”是哑巴弟弟的离奇失踪。弟弟失踪前,“我”与世界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对立关系,弟弟的失踪,使“我”对外在世界心生怀疑和陌生感。此前,虽然父亲的被羁押也使“我”费解,但并不构成“我”与世界之间紧张关系的始源。因为显然,家庭成员中,只有“我”和弟弟之间关系纯粹。哥哥、姐姐和母亲,都视哑巴弟弟为累赘,“我”却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兄弟情。显然,这是“我”与世界和他人之间的异己关系转向内在的表现。外面世界的可疑,让“我”在同弟弟的关系中感觉到可靠和信任。可见,“我”同弟弟的信任关系,反衬着“我”和外界(包括家庭)之间的对立和紧张。虽然并不很明显,但小说若隐若现地是把这种异己关系或者说“异化现象”作为小说主人公“我”的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主题来表现的。“我”处于与世界的陌生的、异己的关系中,“我”也在那些疏离异己于世界的人和物身上,感觉到奇怪的亲和性,比如说哑巴弟弟、二流子四孬、厂长的女儿罗杨、傻子大头等。“我”在这种夹缝中“野蛮成长”。异己关系构成“我”的成长背景,因而创伤就成为成长需要克服和面对的状态。从这个角度看,小说临近结尾,“我”的一家中母女、父女和兄妹之间的和解,构成了“我”的成长的隐喻。小说第三部,其实写的是精神创伤产生和治愈的过程。
精神创伤,源自家庭的奇怪关系,这种精神创伤,使得“我”始终与社会、他人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中,既不过分投入,但又难以挣脱。因为,处身其中的,与“我”有着种种关系的人,都是“我”所深爱着的、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的亲友:父亲、母亲、姐姐、哥哥、初恋罗杨。“我”深爱着他们,但他们既彼此伤害,也伤及着“我”。这里面有一种深深的无奈。这种无奈里,毫无疑问有着时代的因素:特定的不正常的时代,当然会放大“人”身上所固有的劣根性和人性的弱点,但根子里,还是彼此的性格因素在影响和左右着他们间的关系。小说作者并没有放大时代的决定因素,而是相反,他聚焦于人物间彼此的性格因素和“人”身上所潜在与暗含的自私自利。父亲、母亲、哥哥和姐姐,他们彼此间互相伤害,大都源自他(她)们的性格缺陷和自私自利的本性。
主观视角有其限制叙事的局限,但也能带来阅读上的陌生化效果,它给读者提出的要求是:需要我们同主人公一起感同身受,一起逐渐认识这个多少显得陌生的世界,最后是一起成长。因此,小说中看似矛盾的地方,其实是内在的统一的,小说具有反讽的表象,其实是内在张力的显现。比如说叙述上的节制和夸张,整体风格上的真实和主观印象上的虚假,观察上的限制视角与整体上的洞悉一切,如此种种张力关系,都在小说的结尾得到妥善解决。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可靠的不可靠叙述”。小说并不隐藏叙述者“我”的局限,但对这种局限有一个整体的和全局的把握,它并没有提前告诉我们,而是让我们同叙述者“我”一起经历挫折,感到沮丧,让我们同叙述者一样,深陷困惑之中并充满期待;这一切,都体现在叙述的进程之中,并在小说结尾处有集中的交代。小说阅读的快乐正体现在这种感同身受,及其发现和探索之中,原来,父母兄姊之间,并不像表面显现得那样冷漠无情,他们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爱和对彼此的关心。小说越到后面,越构成对前面的叙述的内在的颠覆和重写。小说的阅读,正是在这种不断地“重写”中完成。第三部小说的阅读,因此也是最为复杂的——并非从一开头就预示着的,它注定了是一次正向推进和逆向回溯相交织的阅读体验。
四
通过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三部小说的成长主题,彼此之间构成着某种重复关系,彼此构成对方的重复。这种重复关系表现为,都是在表现1950-1970年代的西北历史,都是在时代的失序下表现主人公的成长,都写到狗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一、二部)。但在这种重复里,有着希利斯·米勒所说的重复的两种形式之间的区别。米勒告诉我们,看似彼此差别很大的事物之间,其实有着内在的相似之处;同样,他也告诉我们,看似彼此相似的事物之间,其实在本源上彼此不同、甚至南辕北辙(见《小说与重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同狗与狗之间的关系,有着相似之处,但却有本质的不同。狗与狗的关系里,没有政治经济学内涵,人与人的关系中,却因理性的思考和利益的考量而变得不纯。这种不纯,或者可以理解为浪漫主义所理解的堕落——人性的发展是一种向下的堕落过程。所谓失序和成长,某种程度上就成为这种堕落的两面:我们在失序的状态下成长,成长构成了对人性的堕落的反抗和对“始源”的复归的隐喻。
这样来看,就会发现,三部小说的成长主题,彼此不同,又内在统一。张学东虽充分感受到成长随时间的流转所具有的永劫轮回的沮丧和疲劳感,但也深刻地体会到成长主题所永远具有的积极意义。如果说狗与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关系的话,人的成长过程则体现为一种人为的主动性。他并不是要我们回到狗与狗之间的关系所呈现出来的自然状态中去,他所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种主动性:人类可以通过对善和纯粹的识别而完成自我的救赎(第一部),通过忏悔而完成自渡渡人(第二部),通过自我疏离的冷静观察而达到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和解(第三部)。三部小说在成长的“人学”命题的思考表现上有着内在的一贯性。这是一种新的成长主题的表现,与一般意义上的成长写作并不完全相同。
当然,成长的主题之外,《西北往事三部曲》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对照结构。这种对照结构,其实可以看成是两种重复形式的复杂关系的呈现。在第一部中是谢亚军同白小兰的对照关系,第二部中是红亮同他自己的对照关系,第三部中是“我”同二流子四孬的对照关系。对照结构,表现出来的是对世界的朦胧看法。谢亚军外向、白小兰内向,她们彼此构成对方的“他者”和镜像关系:他们是对方的真理,同时也是内在的缺陷。但他们总能最后走向自我的复归。白小兰最后绝食而死表明的正是对自己的忏悔和复归,每个人都可能犯错,但只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总能改正。
对照结构也是一种重复形式的表现,这种重复关系,既相似又具有内在的差异性。张学东想表明的是重复的第一种形式,即差异由相似产生,最后又能回归相似。白小兰的绝食而死,表明的就是这种复归。因此,不难看出,张学东仍旧是一个有着古典情怀的古典主义者。他想建立的正是这种传统的复归。比如说第三部中“我”和傻子大头的关系,“我们”之所以成为彼此不能分离的朋友,正因为这种彼此之间的相似,虽然“我们”之间有着不可否认的差异关系。小说通过傻子大头的意外死亡这一细节,竭力维护的正是这种同一性,同一性在傻子大头的意外死亡中被夯实。小说的第二部中,对红亮虽然着墨不多,但他仍旧可以看成是小说的主人公,小说中构成对照结构的是前后两个时期的红亮。这是两个人生阶段的红亮的对照,其中有过一段时间的偏离,但最终还是走向了自我的复归与合一。因而,世界也复归了秩序。成长就是回归。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三部小说的成长主题,虽涉及不同情节、不同情境,但其实指向的都是回归。成长是更高意义的回歸。这种回归,通过几个层面完成;第一是通过秩序的回归,而实现的自我回归。第二是通过对自我的批判而实现的自我回归,白小兰的绝食表明了这点。第三是通过对亲情的回归,而实现自我的回归,小说第三部是典型。
就文学史的角度看,《西北往事三部曲》的意义还在于“三部曲”模式的创新和尝试上。文学史上的三部曲,比如说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 《春》 《秋》)、梁斌的“红旗谱三部曲”(《红旗谱》 《播火记》 《烽烟图》)、笛安的“龙城三部曲”(《西决》 《东霓》 《南音》)等等,大都是主题、人物、情节和风格,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还有一种,以茅盾的“蚀三部曲”(《幻灭》 《动摇》 《追求》)为代表,三部曲之间人物、情节上彼此不同,但在主题和风格上却是首尾贯通的。这类三部曲虽不构成三部曲现象的主体,但也不绝如缕。人物、风格和主题的统一,当然有利于情节的设置,但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出现用力不均和难以为继的现象。文学史上的三部曲,多有这种情况出现,比如说《创业史》 (柳青)第二部不如第一部成功;而至于续书,比如《红楼梦》的各种续书,更常常只能是狗尾续貂,一部不如一部。从这个角度看,张学东的《西北往事三部曲》则可以说创造了“三部曲”的新范式。三部曲之间,主题、人物、情节和风格,彼此分殊,甚至可以说大相径庭,但在总体上却具有内在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正体现为空间背景的地域一致性、时间线索的连贯性和风格间的彼此映衬性。可以说,正是时空关系的一致性,保证了各部作品间的风格的分殊具有了内在的统一效果。这里的三部曲,也可以称之为“蒜瓣式结构”。
三部曲中,多属于“珠串式结构”,其中时间既是彼此连贯和递进,人物、主题和情节也彼此关联和具有推进关系,而事实上,这种推进往往是很难实现的——现实当中,时间的先后关系并不总能做到层层推进的。而至于“扇形结构”的三部曲,比如说“龙城三部曲”,其中的时间空间彼此交错,彼此之间情节也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互文性”的三部曲,虽然单独阅读其中一部,并不影响其他两部的阅读,但就总体上看,却是彼此不能分开,分开就不完整了。“蒜瓣式结构”则又有不同,三部曲分开来,是一部部独立的作品,具有其各自独立的主题和风格,合起来又有统一的构思。有彼此间的主轴(即蒜骨),又时断时连和似连实断。“蒜瓣”间的关系是各自独立又内在连贯的。
题旨相似,风格各异,彼此交相辉映,构成了这部作品的整体特色。《西北往事三部曲》的出现,表明了张学东创作的成熟。他一直以来在两种风格之间举棋不定,是实写还是致幻,是复制世界的影像,还是制造幻象?这三部小说,以整体上的互相辉映的方式回答了这点。从这点看,这三部小说整体上兼具史诗气度和魔幻风格。
作者简介※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