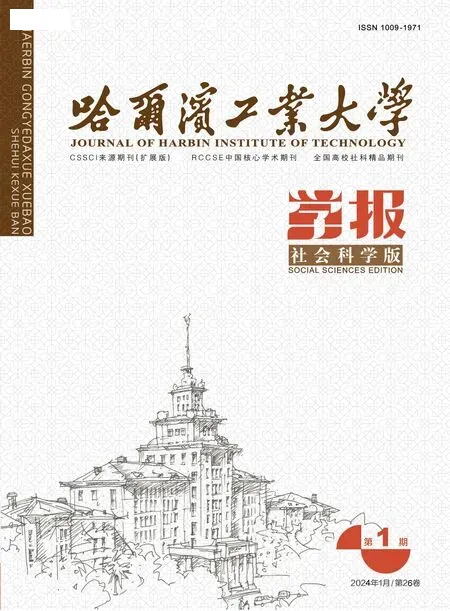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2024-04-07王洪军
王洪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25)
汉王朝以前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两次大的历史变局。 一是商周之变,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论之甚详。 周人封邦建国,周王为共主,行政主导权在诸侯国,周王以礼乐文化制度为统摄。 其利在于以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基础,其弊则是以周王为共主的诸侯国逐渐强大而走向了形式上的分裂。 二是周秦汉之变,对此当代学人阐述尤繁。 秦人以强势的军事手段统一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帝制国家并且惠及两汉。 “大一统”帝治国家政权的建立是一种全新的政治模式的不断尝试与完善。 在这一动态的变化过程中,汉代国家的文学也随着思想政治体制的调整而发生变化,形成了统一国家独有的文学镜像。 而我们的研究正是将汉代文学置于四百年统一国家体制的建设进程中,考察统一国家士人精神的变化、国家文学形成的内在机制,以此探索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学气象。
一、 两汉士人的入士精神与国家情怀建构及其消解
汉高祖刘邦厥受天命,“改正朔,易服色”[1]1256,成就了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汉代的“大一统”,不仅是政治、地理上的“大一统”,更是文化思想上的“大一统”。 汉代儒家士人在对“天地常经”“古今通谊”的追求中,形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国家认同感,并深入血脉内化为整个时代的人文精神。 “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2]671,与这种“大一统”人文精神相匹配的,是汉代盛大宏丽的文学气象。
(一)儒家“美政”理想的制度设计与理论建构
《荀子·儒效》云:“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3]120与屈原以具体君臣关系为目标的“美政”理想不同,荀子所说的美政是儒家士人对国家政治的全面介入,包含了“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3]117等方面。 汉代儒家士人对荀子这种美政理想的实践,在历史文献中以“大汉继周”说为中心,贯穿了儒学作为汉代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确立的全过程,反映了两汉士人积极的入世心态,也奠定了汉代文学发展的精神底色。
高祖刘邦不喜儒生,《史记》《汉书》有诸多记载,那么,儒家经学是如何介入汉代政治生活的呢?《汉书·礼乐志》以“犹命”言之:“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 高祖说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4]1030而实际上,“正君臣之位”,甚至是高祖之“说”,才是儒学与汉代政治生活契合的起点。 《汉书·叔孙通传》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制礼仪”的来龙去脉。刘邦鼎定天下被尊为皇帝之后,仍出现群臣饮酒争功、醉而妄呼、拔剑击柱等混乱的局面,这引发了刘邦的忧虑。 叔孙通敏锐地捕捉到了皇帝的担忧,提出“共起朝仪”的建议,并以“长乐宫成”为契机,让刘邦在“朝仪”中找到了“天子之贵”的感受。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4]2126,汉代儒家士人的美政行为在大汉王朝的起点处,适应了“大一统”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
汉初儒家士人的美政实践,是对“郁郁乎文哉”社会制度设计的回归。 史家向有汉承秦制之说。 朱永康曾就文献中的“汉承秦制”原义所指等作详细辨析[5]。 “汉承秦制”是否成立,关键在于对“制”的解释,而有关于此启示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汉初至武帝时会“独尊儒术”,儒家士人自身又为此做了怎样的努力? 求诸史实会发现,从汉代建立之初,儒家士人一直在为“郁郁乎文哉”社会制度设计的实施进行不懈努力。 前有叔孙通“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的理论铺垫,随后陆贾“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的现实诤问,其次是贾谊直言:“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4]1030儒家士人对礼乐文明的实践或呼吁,以“大汉继周”说为中心,走出了儒学昌阜于汉代的坚实脚步,本身亦是汉代儒家士人美政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儒家士人的美政历程,集中体现为围绕礼、刑之争的理论争辩。 “大汉继周”面临的现实情况是“汉承秦制”,为使“大汉继周”成立,西汉时期的儒家士人不断将两者进行对比,《汉书·礼乐志》勾勒了这种对比的大体情况。 文帝时,贾谊言“兴礼乐”的目标为“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4]1030;武帝时,董仲舒有论:“刑罚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 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 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如以汤止沸,沸俞甚而无益”[4]1031-1032;宣帝时,琅邪王吉上疏进谏:“务在于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4]3063;成帝时,刘向上疏:“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 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4]1034在汉儒那里,礼、刑之争从对立关系走向补充关系,其中又引入治世与乱世等必要参照元素,凸显了预防犯罪与惩治犯罪不同功用的儒、法差异。
汉代儒家士人的“美政”理想及其理论建构,在现实层面达成了儒学的思想体系核心地位。 文学创作,或者作为这种理论构建的一部分,或者作为这种理论构建的产物,或者接近于这种理论构建而被选择性保存下来,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文学。
(二)文章焕然的文人气象及其盛世人文精神的萃集
汉初之文章,受屈原影响最大,多有贤者失志、离谗忧国之作,“贤人大儒逸在布衣,以不用而多暇,失志赋诗,本其天以鸣不平”[6]191,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但显然,汉代文章并没有在“贤者失志”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经历了汉初短暂的家国动荡阵痛之后,迅速凝聚起只属于“大汉”的盛世人文精神。
王利器注贾谊《过秦论》“以成大汉之资”说:“自秦、汉之际以还,国号加大,已约定俗成矣。”并列举《诗·大明》及《国语·吴语》中“大商”“大虞”等文字,上溯其渊源[7]57。 实际上,就“大汉”而言,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和盛世人文精神的体现,不宜简单用“约定俗成”概括,其有特定的形成过程。 至少,除司马相如《封禅书》外,“大汉”的提法在《史记》中极少出现,而多见于《汉书》之中,《后汉书》中则更为常见。
以“大汉”认知为核心的盛世人文精神,建立在地域之大和国力之强的基础之上。 汉哀帝初年,贾让奏言“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的治水之“上策”,其背后是“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4]1694的强者思维。 汉和帝永元元年,窦宪等“勒石燕然”,班固以“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8]815言之,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铿锵掷地之声。 班固以“大汉初定”领起《匈奴传》的写作源起,因其本身的追溯与总揽性质,则展示了历史记述中“大汉”作为一种文化概念的形成。
文学创作中反复出现的“大汉”,是基于汉代盛世人文精神的自觉书写。 在贾谊《过秦论》及司马相如《封禅书》外,“大汉”作为自称或表述对象,多次出现在汉赋等文学作品之中。 如扬雄《河东赋》言:“遵逝乎归来,以函夏之大汉兮,彼曾何足与比功?”[4]3539《解嘲》有:“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4]3568班固《答宾戏》言:“方今大汉洒扫群秽,夷险芟荒。 廓帝纮,恢皇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4]4228《西都赋》有:“佐命则垂统,辅翼则成化,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螫。”[8]1314杜笃《论都赋》中,“大汉”凡四见。 至蔡邕《释诲》仍言:“今大汉绍陶唐之洪烈,荡四海之残灾,隆隐天之高,拆絙地之基”[8]1984,则可视为“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4]212的具体体现。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较之有针对性的历史叙述,文学作品中使用的“大汉”语言环境更为复杂,因此也更具普遍意义,体现了“大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深刻性和广泛性,进而影响后世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历程。
作为盛世人文精神的显性符号,“大汉”不只代表了光荣与梦想,同时也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内省与反思。 与“大汉”相近的一个概念是“强汉”,王子今曾就“大汉”“强汉”等概念分析汉代的国家意识等问题[9]。 那么,为什么成为汉代文化精神代表的语言符号是“大汉”而非“强汉”? 回答这一问题,从表象上看取决于历史文献自身的选择即概念出现频率,更深层次上则是因为“大汉”一词浸润了儒家文化的深厚基因。 汉武帝建元六年,淮南王刘安谏征讨闽越之事曰:“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言莫敢校也。 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4]2784-2785可能使“大汉”蒙羞的是“不备而归者”,更是“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诗教之不行。 大汉,以地域广大和国力强盛为基础,但其内涵远不止于此,否则,其无法蕴养文章焕然的文人气象,也无法成为盛世人文精神的闪亮标识。
(三)国家道德秩序的重建与个体道德的自我融通
儒家经学是汉代儒家士人的德业所在,在五经博士制度建立之后的长期实践中,尤其是宣、元、成帝时期儒家经学全面振兴,儒家士人形成了以刘姓君主政权为依托的家国情怀以及集体政治道德。 董仲舒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天谴说发明之后,成为衡量汉代政治得失的尺度,汉嗣三绝之后,西汉士人的集体道德开始随着再受命的革命学说而转向,这是王莽能够禅汉的最基本的原因。王莽建立大新政权、光武帝刘秀中兴大汉,都与“符命”之事相关,也就是理论先行。 河图、符命之说虽古已有之,但真正走入历史舞台乃至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导,也正是始于这一时期。 而且,以河图、符命等为内容的图谶之使命,并没有因王朝的建立而终结,《春秋元命苞》言:“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实。 质文再而改,穷则相承,周则复始。”[10]393从受命到改制,图谶深刻影响了东汉时期的政治生活。 此外,图谶与纬书结合形成的谶纬理论,通过介入经学体系等方式,重建了社会文化及道德秩序,士人精神于此不得已重新凝聚与提炼,体现出一种个体道德的自我融通,深刻影响了此一时期的文学发展。
东汉时期的社会文化与道德秩序重建,是通过谶、纬结合并介入经解系统完成的。 王莽、刘秀先后通过“顺符命”走上权力巅峰,这本身即包含着这样一个命题:“符命”是一柄双刃剑,不只一个人可以利用,想要开太平之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对其做出规范。 同时,对于“符命”之说,当时的社会上鲜有不同的声音。 “丹书著石”“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后,《汉书》言:“符命之起,自此始矣。”[4]4078-4079稍后又以简洁的文字描述了王莽自立“符命”的文人群像:“是时,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4]4122以至于王莽不得不使出“非五威将率所班,皆下狱”的雷霆手段。 对自光武帝刘秀始的东汉时期的“符命”之事,《文心雕龙》说“桓谭疾其虚伪,尹敏戏其浮假,张衡发其僻谬,荀悦明其诡诞”[2]31等反对图谶之“精论”,不同的声音更为显著。“符命”自身的“双刃剑”属性和这些事关政权根底的声音,要求统治者尽快为“符命”找到合适的位置介入主流文化体系,实现这种介入的,就是白虎观会议。
白虎观会议从官方将谶纬纳入解经系统,从思想层面规范了社会文化与道德秩序,同时,又通过封建纲常伦理系统的建立,将封建政权神圣化,将男女之间的社会地位等绝对化,此与通过为谶纬“正名”而维护统治的思想一脉相承,但对社会道德秩序的影响更为直接。 对此,解读者较多,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探讨这一问题。 在白虎观会议之后,班昭“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而作《女戒》,以“卑弱”起,以“曲从”等终[8]2786-2790,此与刘向“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4]1957时对待女性的态度有极大的变化。 同时,《后汉书·列女传》前、后汉女性形象之间的差异,也是对东汉时期国家道德秩序重建的反馈。
如前所言,在东汉重塑国家文化与道德体系的过程中,有些人挺身而出发表了不同的见解,而有的士人在新秩序中选择了自我融通,这使东汉呈现出异于西汉时期士人精神风貌的同时,也展示了在核心文化圈政治动荡时多元文化并存的可能。 《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之“论”言:“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洁放言为高。 士有不谈此者, 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8]2069为何会有此种“遁身矫洁放言”,现实层面如吕思勉所言:“汉世进趋,多由乡曲之誉,故士多好为矫激之行以立名。”[11]473而《后汉书·儒林列传》中体现的无官职即不仕而可留名的情况,《后汉书·独行列传》中记述的丰富多彩的人生片段,都显示了士人在新的道德秩序面前进行的自我调适。
(四)汉末士人澄清天下的责任与家国情怀的凝聚与消解
白虎观会议形成了汉代国家政治与文化相结合的高峰,这种来自顶层设计的主观规轨,其实质亦展示了一种文化禁锢,在文化发展内驱力层面孕育了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并最终以士人群体与外戚、宦官之间的矛盾为突破点爆发出来。 党锢之祸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拐点,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士大夫阶层的家国情怀由理论上升为实践,部分士人表现出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而魏晋时期“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2]675的文化、文学取向,亦由此奠定与萌生。
以儒家士人为主体的士大夫群体在汉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影响了汉代社会的走向,禅汉之王莽即是由今、古文士人共同推举的皇帝。 也正因如此,虽然推举王莽的士人大部分又投入到光武帝的麾下,但光武帝对这些士人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 章培恒、骆玉明言:“东汉初期起中央统治集团就对一些被认为有害于自己的士大夫实行‘禁锢’,并连及其‘党’。”[12]212光武帝时期的欧阳歙案件等表明了这种“禁锢”的存在。 然而,“禁锢”,终究只涉及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到东汉末年成为党锢之祸,显然局势已经失控。 更为重要的是,党锢之祸的受害者与光武帝时期的士人不同,“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8]2191,其自毁的,是“大一统”社会形态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其打碎的是胸怀澄清天下之志的士人的光荣与梦想。 范晔论曰:“向使庙堂纳其高谋,疆场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辞,举厝禀其成式,则武、宣之轨,岂其远而?”[8]2042此论虽指向“东京之士”,而以是观党锢之祸的受害者,实亦宜哉!
我们可以从李固和范滂的行事中感受汉末士人的家国情怀与澄清天下之志。 李固是汉末名臣,《后汉书》中至少七次提及其被“枉杀”的最终结局,原因均归结为外戚梁冀的诬奏,《天文志》更 言: “懿 献 后 以 忧 死, 梁 氏 被 诛, 是 其 应也。”[8]3246其以星象之因果应验将此事神秘化。阳嘉二年,出现了地动、山崩等异象,李固对策于汉顺帝且言“当世之敝”:“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譬犹一门之内,一家之事,安则共其福庆,危则通其祸败。”[8]2076直言不讳刺讥时弊,忠臣赤子拳拳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李固的家国情怀,体现在贤者时人的口碑之中,黄琼有“疾笃”之言:“故太尉李固、杜乔,忠以直言,德以辅政,念国妄身,陨殁为报,而坐陈国议,遂见残灭。 贤愚切痛,海内伤惧。”[8]2038范晔于其本传论曰:“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 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 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 至矣哉,社稷之心乎!”[8]2094-2095较之李固,范滂亦为汉末名士,“案察”冀州之饥荒时, “滂 登 车 揽 辔, 慨 然 有 澄 清 天 下 之志”[8]2203。 其后历事黄琼、宗资等人,均于“澄清天下”有所建树。 范滂与李固的不同之处,是其得不到礼遇或“知意不行”时,会主动选择全身而退,颇有蘧伯玉之遗风。
范滂对介入国家政治有所选择,以申屠蟠等人则选择了远离政治。 《后汉书》所见申屠蟠之行事,可以用不行、不就和不答约略总结:“郡召为主簿,不行”“太尉黄琼辟,不就”,同乡以“孔氏可师,何必首阳”相劝时,“蟠不答”。 此与其逢父忌日“辄三日不食”,以及“因树为屋,自同佣人”等行为结合起来,已见魏晋之名士风流[8]1750-1754。申屠蟠为代表的《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传主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东汉末年士人家国情怀的消解。以“大一统”及家国情怀为代表的汉代文学的底色,在此刻悄然退去。
二、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汉代大赋的“风雅正变”
在汉代只有汉大赋才能与“大一统”的王朝气质相匹配。 换而言之,也只有大汉王朝氤氲的气象精神,才能孕育出汉大赋这样的千古绝唱。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汉大赋创作主体适应了“言语侍从”的角色定位,从诗学的“风雅正变”理论中,我们或可窥见汉大赋于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特质与地位。
(一)藩国文学对养士之风的文化赓续
养士之风盛于战国,各诸侯国之间频繁的战争和诸侯国内部的权力倾轧,造成社会阶层基本定位的松动,能力尤其是实用能力在人才的判定标准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各诸侯国的君主及权贵招揽社会上的流动人员,使文士群体的力量在此一时代得以集中展现;与私人养士呈现出不同的风貌,齐之稷下、楚之兰台活跃着另一批士人群体,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并以“文学”名世,成为秦汉社会的文脉源流;战国末期吕不韦的养士,则有着更为精准的政治目标,为后世留下了《吕氏春秋》这部总揽诸子的旷世奇书。 汉初各藩国之主养士,在主体上对上列三种情况都有所继承与体现,吴王刘濞在出发点上主要类于前者即培植自己的势力;梁王刘武所集中的士人,在文学创作上最为后世所称道;淮南王刘安在最终“成果”上与吕不韦不遑多让。
汉兴十二年,高祖刘邦衣锦还乡,留下了一个政治副产品是封刘濞为吴王。 记录汉初七国之乱时,《史记》云:“吴王濞弃其军,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1]2076这里所说的“壮士”与军队有别,应为刘濞所养之士,由此可判断出其麾下士人的规模。 “壮士”之外,刘濞还招揽了包括邹阳、枚乘等一班文士,这些文士有的成为汉初藩国文学的创作主体,其作品亦成为汉代早期藩国文学的代表。 刘濞因叛乱被杀,其所属之士在叛乱前后亦各自散去,同因叛乱而死的淮南王刘安手下的士人群体,则由于刘安酝酿实施叛乱的时间过长,得以为后世留下兼具文学与史料价值的《淮南子》。 《汉书·艺文志》更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之记载[4]1747。汉初的藩国文学,最著名的是隶属于梁孝王的“梁园文学群体”,曾从属于吴王刘濞的文士,部分投奔到梁孝王刘武的门下,刘武自身亦“招延四方豪杰”,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等“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1]2083。 其后又有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的加盟,梁园文学之盛况,使后世文人墨客为之仰望与倾倒。
以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等为中心形成的汉初藩国文学,文学创作主体的凝聚均与政治目的相关,这决定了其文学创作的政治属性。 跟随吴王期间,枚乘、邹阳等的作品如此,我们能看到的署以“淮南小山”之名的《招隐士》,也被认定是为淮南王招揽贤才所作。 所以,早期藩国文学的作品,或者在语言及审美等方面有所突破,但在本质上与战国时期的纵横之学更为接近。 完成由纵横之风向骋辞之美转变的,是以梁孝王刘武为中心的“梁园文学群体”。 对邹阳等文士由属刘濞到从刘武,《汉书》记载:“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 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4]2338-2343这段文字表面上反映了文士群体所跟随之人从叛乱者到觊觎皇位者的变化,而由“说吴”到“从游”,实际体现的是文士群体行为方式的根本转变。 这样的转变,必然最终影响文学创作,如孙少华总结“梁园文学”的成立时所说,“梁园文学”群体“有其写作共性,即写神仙不死题材”[13],文学在政治之外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题材,这是文学的概念由广义向狭义发展道路上的一大步。 同时,微观上,“兴从剡溪起,思绕梁园发”,《西京杂记》等所描述的梁园主客盛状,《雪赋》所描述的“置酒命宾”等,都展示了以梁孝王刘武为核心的藩国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而梁园文学的应酬唱和,也打开了文学发展的另一条路径:“言语侍从”。
有关汉初文学,必须应强调儒家思想在其中的位置。 汉初盛行黄老之学,但儒学在汉武帝时期得到朝廷的重视,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其积累过程,此在文学创作中亦有呈现。 枚乘是汉初藩国文学有始有终的代表作家,其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七发》以劝谏“楚太子”为指向,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外物与人的和谐有度,而这样的人与外物的关系,一直是儒家思考的主题,且只有儒家,将其具体化并理论化。 《七发》文末对于孔、孟的态度,也是枚乘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明证。 汉初的藩国文学,其最终走向明确,但其自身存在状态显然是复杂的。
(二)“言语侍从”:宫廷文学创作主体的身份标志
藩国文学兴起的前提在于藩国的强盛。 随着汉代中央集权的加强,藩国鼎立的局面逐渐消失,国家走向真正的“大一统”,与这种“大一统”精神互为表里的文学也应运而生。 汉代文学的代表是汉大赋,只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汉大赋才能匹配大汉天朝的精神与气质,对此人们少有异议,但对于汉大赋的存在状态,人们在言说时往往瞻前顾后。 班固于《两都赋序》总结汉赋的作者群体时说:“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14]235汉赋的创作主体,实为“言语侍从之臣”,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似乎文学创作主体的地位并未发生变化。
“言语侍从”彰显的是内外之别。 《汉书·严助传》云:“严助,会稽吴人……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 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 相如常称疾避事。 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颜师古注“中外”曰:“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也。 外谓公卿大夫也。”[4]2775显然,班固所列举的“言语侍从之臣”,指向皇帝近臣,亦被视为天子宾客,此与藩国之养士有异曲同工之处。 而所谓的“言语侍从之臣”之内部,亦有更细致的分划。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赞曰:“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4]2634“言语侍从”之臣中或者有因“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而被列入“滑稽”者,但其终究仍为“兴造功业”之臣,司马迁所说的“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4]2732,大抵只是带有个人情绪的一时气愤之语。 “言语侍从”文学之传统一直持续到西汉结束,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班固《两都赋序》论及武帝、宣帝之世的创作时具体举例说:“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於郊庙。”李善注:“《汉书·武帝纪》曰:‘行幸雍,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又曰:‘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又曰:‘甘泉宫内产芝,九茎连叶,作芝房歌。’ 又 曰: ‘得 宝 鼎 后 土 祠 傍, 作 宝 鼎 之歌。’”[4]21其揭示了汉武帝时期作“歌”的一个侧面。 《汉书·武帝纪》间或记述了其他作“歌”的情况,对这些“歌”的内容,部分在《礼乐志》中有所呈现,如元狩元年冬十月,作《白麟之歌》;元鼎五年六月,作《宝鼎之歌》;元鼎五年秋,作《天马之歌》;元封二年四月、六月,分别作《瓠子之歌》《芝房之歌》;元封五年冬,作《盛唐枞阳之歌》;太初四年春,作《西极天马之歌》;太始三年二月,作《朱雁之歌》;太始四年夏四月,作《交门之歌》。《汉书·武帝纪》中记载了九次作“歌”的情况,这九首“歌”中只有五首在《礼乐志》中保存有内容,而《礼乐志》共录有郊祀歌十九首,且言:“其余巡狩福应之事,不序郊庙,故弗论。”[4]1070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汉武帝时期作“歌”的盛况,并由此窥视汉代宫廷文学之一斑,体会藩国文学与宫廷文学之间的巨大政治差异。
(三)汉大赋的“风雅正变”
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带来的不只是汉赋的繁荣,更有“大一统”精神对文学的融入,此于司马相如之处体现得最为明显。 《汉书·艺文志》批评司马相如等“没其风谕之义”,扬雄更确言相如之赋“劝百而讽一”。 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大赋与讽谏之间的关系,自汉代即成为认知汉大赋的关注点。 理解对汉大赋“没其风谕之义”的批评,其核心应在比照《诗》之讽谏的情况,所以,可以借助诗学中的“风雅正变”理论进行观察。
“风雅正变”之说倡于《毛诗序》,其言:“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 情, 民 之 性 也; 止 乎 礼 义, 先 王 之 泽也。”[15]271-272这段文字在郑玄和孔颖达处凝结为“风雅正变”理论,后说甚繁,成为诗学的重要理论范畴。 《毛诗序》及相关“风雅正变”理论,对认识汉大赋与讽谏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以下三点提示。
第一,如何进行讽谏。 对此,《毛诗序》的答案非常明确,即“主文而谲谏”。 朱自清解释说:“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16]75《诗》之讽谏,不管是以上对下的教化还是以下对上的谏刺,都不是简单的直陈其事,而是通过譬喻等委婉的方式达成的,这样才能使言者无罪、听者足戒,达到“温柔敦厚”之诗教的效果。 那么,《诗》之风、雅的讽谏方式是“主文而谲谏”,以“曲终而奏雅”为汉大赋之讽谏的方式,亦实无不可。 况且《上林赋》言:“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 曰:‘嗟乎,此泰奢侈! 朕以览听馀间,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於此,恐後世靡丽,遂往而不反,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4]2572能够使“闻者”自我反省,或者通过自我反省的表现形式引发“闻者”的同感,汉大赋的讽谏较之《诗》,可能更具感染力。
第二,如何把握讽谏的尺度。 “主文而谲谏”只是一种指导思想或者至多只是一种方法,《诗》之讽谏,是有边界的,《毛诗序》于此的答案是“止乎礼义”。 讽谏是《诗》的功能之一,且相对而言,“变风变雅”中的讽喻更为突出,但“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即使是“变风”的讽谏,也有自己的上限。 对此,我们可以思考另一个诗学命题即“诗亡春秋作”,《诗》为何会“亡”,《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汉书·礼乐志》亦言“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4]1042。 代表“先王之泽”的“礼义”消失了,《诗》之讽谏失去了边界,也就失去了产生的空间,至少,此时的诗不会被孔子纳入选《诗》的视野,是为“《诗》亡”。 而汉大赋所在的大汉天朝,儒家学者正在打造“大汉继周”的伟业,“礼义”的重建,使汉大赋继承《诗》之讽谏精神成为可能。 所不同的是,董仲舒等所重建的“礼义”对讽谏双方即君臣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更为苛刻的规范,讽谏的空间被无限压缩。 所以,汉大赋的“风谕之义”有所弱化,实为情理中之事。 同时,“劝百而讽一”注重的是量,“止乎礼义”强调的是度,考察汉大赋的讽谏,后者作为标准的意义更大。
第三,要不要讽谏。 《毛诗序》评《诗》有美有刺,孔颖达在具有明确“风雅正变”意识的《毛诗正义序》云,“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郑玄《诗谱序》言:“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 教 尤 衰, 周 室 大 坏, 众 国 纷 然, 怨 刺 相寻。”[17]3-8一方面,《诗》本身并非都具有讽谏之义,另一方面,讽谏主要出现在政教衰败之时期。对产生于“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之汉武帝时期的汉大赋,是否应该以讽谏作为臧否之首要标准,这本身即是一个问题。 同时,要不要之外仍有能不能的问题。 《汉书·礼乐志》载平当论重整雅乐:“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鎗,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 是以行之百有余年,德化至今未成。”[4]1072大汉的公卿大夫,对雅乐已经不能知晓其意了,《诗》之讽谏想要在汉代重现,已经没有存在的土壤。
如上,以《诗》之讽谏衡量汉大赋的优劣,实在是一种强求。 如果一定要将其比之于《诗》,我们大可将其视为“论功颂德之歌”,视“润色鸿业”为其社会功能。 当然,也可以换一个视角观察:在美刺之间,可能还有一条不美不刺、自美其美的中间道路,而这条道路,或者就是纳入儒家教化系统之前的《诗》的样子,抑或其属于我们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文学的道路。 扬雄《法言·吾子》载:“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 如其不用何?’”[18]51《汉书·艺文志》亦有类似记载。 对此,论者多将其看作是对汉大赋的批评或扬雄对自身赋作的反思,实则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扬雄对赋的区分。 扬雄所谓“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汪荣宝解释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者,谓古诗之作,以发情止义为美。 即《自序》所谓:‘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故其丽也以则。 《艺文志》颜注云:‘辞人,谓后代之为文辞。’‘辞人之赋丽以淫’者,谓今赋之作,以形容过度为美。 即《自序》云:‘必推类而言,闳侈巨衍,使人不能加也。’故其丽也以淫。”[18]51依汪氏之注,则扬雄做出的是“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 汪氏进一步引挚虞《文章流别集》之言:“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 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 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 常 矣。 文 之 烦 省, 辞 之 险 易, 盖 由 于此。”[18]51区分汉大赋与《诗》的意图更为明显。同时,汉代对于官员的职能区分已经非常明确,《汉书·百官公卿表》言:“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 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4]727《汉书》更是多次记载了自汉武帝起征召“极谏之士”的诏书。 则讽谏之功能,不应独为“文学”所承担的职责。 所以,汉大赋的创作,应被视为儒家士人的独立行为,而由此形成的与汉代“大一统”国家精神相匹配的文学奇观,不必一定要纳入“美刺”之《诗》学体系,进而以《诗》学理论批评汉大赋。
三、两汉史学创作范式的形成及其文章学意义
王充《论衡·须颂篇》云:“高祖以来,著书非不讲论汉。 司马长卿为《封禅书》,文约不具。 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 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 陈平仲纪光武。 班孟坚颂孝明。”[19]854两汉时期之史学在政治地位上虽不如经学,但在创作上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更产生了《史记》《汉书》两座史学高峰之作。 章学诚说:“自获麟以 来, 著 作 之 业, 得 如 马 迁、 班 固, 斯 为 盛矣。”[20]368以《史记》《汉书》为代表形成由事而人、由时而类的两汉史学创作范式,是中国文章学的重要奠基。
(一)由事而人:汉代的史学书写转型
历史学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学科,其可以追溯的时间也最为久远。 较之前代的历史记录与书写,汉代史学所作的最大改变是对人的关注,《史记》《汉书》等都将人作为历史书写的中心。 而此前,《诗》中的“史诗”记录事件、《春秋》《左传》书写事件、《国语》等记言成分较多但仍然围绕事件展开。 所以梁启超说:“自从太史公作《史记》,以本纪、列传为主要部分,差不多占全书十分之七,而本纪、列传又以人为主。 以后二千余年,历代所谓正史,皆踵其例。 老实讲起来,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21]168历史书写的对象由事而人,同个体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作用的大小相关。 直接决定因素,来自“大一统”社会之文化精神所影响下的书写者的观察视角。 书写对象由事而人,不只关系历史书写自身,其对包括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形成等整个中华文化体系延承都有重大意义。
人是事件的执行者,《史记》之前的历史书写不可能不涉及人,甚至也存在为某位人物单独立传的倾向,如《左传》《国语》中对晋文公的集中书写,《左传》不惜出现文字重复、在叔孙豹去世前对其主要行事进行的专题回顾。 但是,一则,这样的书写在整部著作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再则,这些著作中事件的发展鲜由某位人物的言行所决定,事件更极少是由某位人物所运筹或规划的。也就是说,从《左传》等著作中,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事件或事理的中心地位,即人物从属于事件或事理、事件先行存在,是叙述者选择了出场的人物,而非主观的人物形象塑造。 《战国策》一书对人物的高度重视,则为论者所共识,其对张仪、苏秦等的描写记述,向《史记》等纪传体史书又迈进了一步。 《战国策》突出人物,是对贵族社会解体后,在权利与财富的重新分配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力量被凸显出来的真实反馈。 而这样的书写意识,并没有因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而稍有缓解或终结,其因为西汉初期的官吏选拔政策被内化为历史书写者即文士的血脉,又在儒家文化的规范下,披上“立名”之外衣。 对《史记》的创作动因,《太史公自序》记述了司马谈的话。 为了督促司马迁继续自己的写史事业,司马谈从远祖“尝显功名”说起,又给出了两个与“立名”相关的原因:“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不“废天下之史文”。 如果前者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内在动力,那么后者则可能涉及司马谈遗留下的文本的内容,至少是其希望的“史文”的内容,即关于“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件。 对此,司马迁自己在回答壶遂之问时,也有类似表述:“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 堕先人所言, 罪莫大焉。”[1]3299从中,我们可以思考《史记》以人物为中心之纪传体形成的原因。
历史书写由书事到写人,是汉代史著的内在根本转变,《史记》如此,《汉书》亦然,且《汉书》书写历史人物有家族化的趋势。 《史记》中有类似于家族的记述,但主要限于诸侯王及大贤大儒,《汉书》将“传主”家族化的范围进一步向下延展,对“普通”入传者的先人后嗣亦多有提及。 如《于定国传》,向前追述其父于公“祭孝妇冢”而为郡中百姓所敬重之事,向后叙及其子于永“浪子回头” 的 情 况, 直 记 至 其 孙 于 恬“不 肖, 薄 于行”[4]3046。 这样的历史书写方式,与“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的《左传》不同,是对由事而人的历史书写对象的进一步发展。
(二)由时而类:《史记》《汉书》的史学创作范式
就内容而言,《史记》为通史,《汉书》为断代史,而在体例上则同属于纪传体史书。 二者鼎定了中国古代正史的写作范式,包括开创于《史记》而在《汉书》中有所修订的“五体”之史书结构,包括本传加序或赞的具体文章形式,也包括实录无隐之修史主旨、儒雅彬彬的文章修辞,甚至包括《史记》“成一家之言”的个人情感融入。
“五体”,即《史记》所开创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书写体例,《史记》开其例,《汉书》定其体。 论者对《史记》之“五体”是开创还是有所因袭或有争论,但对其于正史写作之影响,都是认同的。 而以此共识为基础观察两汉史学创作范式的形成,应考虑两个问题是:《史记》以“五体”为例,具体对历史书写方式做出了什么样的调整?后世写史多本于《汉书》,从《史记》到《汉书》,体例上发生的变化背后隐含了怎样的文化符号? 这涉及后世史书对两汉所创史学范式继承内容之实质的问题。
《史记》“五体”是开创还是有所因袭,如前所言之“《史记》开其例”,本文认可其开创性质。“五体”中最有可能于其前存在相近形式的是“表”,对此胡家骥以出土文献有证说。 但一方面正如其本人所言,两者只是形式上的相似;另一方面其衡定出现先后之时间,没有将司马谈的问题考虑进去[22]。 其他“四体”,以因袭论之实无确证,而在文献资料层面上,张大可、赵生群诸位先生已立高论。 相对于《史记》“五体”是开创还是有所因袭,仍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史记》对已有历史书写做出了怎样的调整。 对此,论者多以由编年体而纪传体概言之,而由编年体到纪传体,在由事而人的同时,另有由时而类的问题,即由依时记事到依类记事。 如果说“五体”是《史记》的框架,那么这个框架的确定需要准则,而这个准则就是类。 《史记》依类构建了“五体”的整体框架,在“书”类下又具体划分了礼、乐等类别,在“列传”中有因标准明确而将一群人编入一传的情况如《循吏传》,也有由不同关系维系而并入或附入一传的合传,如《孟子荀卿列传》。 《史记》这样做,有因为编撰通史而不得不考虑容量的客观因素,其具体划分,则与区分传主社会地位、明确君臣及层属关系之“大一统”思想密切相关。
《汉书》对《史记》书写体例的调整,同样与“大一统”思想密切相关,是皇权强化甚至绝对化的产物。 《汉书》对《史记》书写体例的调整主要有四,其中至少在两个方面与皇权集中相关。 其一是变“本纪”为“纪”。 司马迁的“本纪”并不是天子帝王之纪,本纪记录的是国之所本,“大一统”之前为五帝、夏、商、周、秦,“大一统”之后为秦始皇、项羽、汉高祖等,所以,其才会作《秦本纪》《项羽本纪》,才会将汉惠帝之事附于《吕太后本纪》之中。 也就是说,《史记》将几千年的历史不间断的在本纪中展现,并以“国之所本”维系,具有国家观念,也体现出“大一统”思想,但皇权在此时还没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而《汉书》变“本纪”为“纪”,体现了皇权的独一无二。 其二是删去“世家”。 此维护皇权的意图最为昭著。刘知几言:“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23]574《史记》只是“抑彼诸侯”,对董仲舒等拱卫下而膨胀的皇权显然不够,历史上从来不允许出现“第二名”。 或者以为,《汉书》为断代史,诸侯或藩王逐渐消亡,所以《汉书》无法保留世家,但显然,《史记》世家中记载的不都是诸侯。 此外,《汉书》改“书”为“志”:总名为“书”,其下又称“书”,此事在《太史公书》处就颇为可疑,自当改之;至于删减《史记》“列传”为“传”:《史记》以一人之名为众人之传,言“列”名副其实,《汉书》置所有传主之姓于传之前,本身就是“列”,无所谓改动。
由编年体而纪传体,体现在体例上是由依时记事到归类记事。 《史记》贯通几千年的中华史,体现了“大一统”的思想也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基;较之《史记》,在体例上《汉书》与“大一统”社会的政治要求更为契合,所以成为后世正史书写的典范。
(三)两汉史学创作范式的文章学意义
《史记》《汉书》所形成的史学范式,成为后世正史书写的典范,部分文学性较强的“世家”“列传”等,成为史传文学研究讨论的对象。 《史记》的发愤为文,继“诗可以怨”之后,成为观察中国文学的另一面镜子。 而《史记》《汉书》的序传或传赞结构,在文体中自成一系。 这些都成为两汉史学创作范式之文章学意义的支撑与代表。
两汉史学范式的文章学意义,首先体现为对后世史书创制的垂范。 如前所述,基于同为断代史等原因,两汉之后的史书在写作体例上与《汉书》更为接近,然正如《补史记序》所谓:“夫以首创者难为功,因循者易为力,自《左氏》之后,未有体制,而司马公补立纪、传规模,别为书、表题目。”[24]4109《史记》所使用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之“五体”,对正史书写体例的规范之功是不容磨灭的。 是以郑樵曰:“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 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25]1赵翼也深有感触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26]3后世之正史在体例上对《史记》开创的“五体”或者有所损益,但结构不出此框架;在具体人物的归属或褒贬上或者各有其标准,但以类划分的总体原则并没有改变。《史记》《汉书》是古代文献的翘楚,且诸多治史者亦作文,其之史学范式的文章学意义可见一斑。
《史记》“五体”中的本纪、世家和列传,是其开创纪传体史书的依据,而其中的列传因为较强的文学属性,又被视为史传文学的代表,由此开始形成了由列传、墓志、年谱、行状等组成的史传文学研究传统。 史传文学究竟应该以何为起点,这是另一个问题,《史记》中诸多文质兼美且成规模的人物传记,则是一种不争的存在。 李少雍指出:“纪传体的精髓就是把‘人’摆在 第一位,肯定了‘人’的历史作用。 它的记人之传,一般都写得很具体,很生动,个性鲜明,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这样,纪传体便同按年月记事的‘纯’历史有了距离,而与以‘人’为对象的文学靠近了。 从‘编年’到‘纪传’,从记‘事’到写‘人’,从历史到文学,这条线索是颇有启发性的,是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思考的。”[27]文与史都以文字为表现形式,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其间界限的模糊。 李少雍的意见对观察文史分野问题是极好的提示。 至于《史记》中的传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28]84,所以其被作为史传文学讨论,则是大文学观下之文章学的应有之义,客观上也可以带动文学研究对铭诔等所谓的应用文体的关注。
《史记》《汉书》所奠定之史学范式的文章学意义,还体现在其“序传”或“传赞”结构对后世文章创作的影响。 “序+正文”是汉代作文的经典模式,实际上这种模式在《诗》等早期文献中已经存在,而汉代尤盛。 《史记》中的“序”,包括《太史公自序》中介绍各个部分写作缘由的集中的“序”,此在《汉书》中单独成为《叙传》,且每个“序”的文字体量有所增加;也包括出现在“表”前同本部分内容关联更直接的文字,这些文字在申明写作背景的同时提供了更多理解本部分内容的线索。很多汉赋都有“序”,论者一般将其区分为“自序”和“他序”,并认为“他序”不应作为赋的组成部分。 汉代的赋序所起到的作用与《史记》“序传”结构中的序类似,或说明写作源起,或介绍写作背景。 “序传”结构在后世发展为“序+诗”或“序+文”等结构,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文章形式。 以“太史公曰”为标志形成的“传赞”结构,成为“史论”的重要讨论范畴,其对于后世文章创作亦影响深远,如我们熟悉的《文心雕龙》中的“赞”。
此外,两汉史学范式的文章学意义仍应包括《汉书》典雅的文字形式对文章创作的影响。 《汉书》的主要作者班固亦是作赋之大家,这使《汉书》在文字风格上与《史记》有较大的差异,刘知己认为:“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 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29]124《汉书》雅正的文字,影响了包括文学理论著作等后世文章的语言风格,其“赞”之文字,甚至有骈体的倾向。
四、东汉的盛世文学观念及“大一统”文学精神的变迁
西汉儒学的繁荣主要以内容上“斟酌经辞”的形式反映在东汉的文学创作中,这与扬雄的“通经”反思相关,其实质更是文化发展内驱力作用的结果。 儒学在东汉初期达到发展顶点并随之固化,与之对应的是班固、王充盛世文学观念的鼓吹,其为时势使然,但可以引发在文学与经学及“言语侍从”等复杂关系中文学如何突围的思考。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大一统”文学精神失去存在的土壤,而在建安文学中略有流风余韵。
(一)东汉中前期“斟酌经辞”的文章意旨
刘勰以“献帝迁播”为分界,将东汉时期的文学发展区分为两种形态:“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2]673虽然经历新莽政权后东汉儒家士人的思想倾向有复杂化的趋势,名节与入仕之间的矛盾已经突显,但就创作而言,对经典的重视甚至是进一步向儒学的靠拢,着实为主体潮流。 而这种“渐靡儒风”的原因,除刘勰所说的“历政讲聚”外,文学发展自身的内驱力也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文学与经学的差别是显著的,其后的文出五经之说,只是汉代学术构建的一种余音。
汉代的儒学与文学,大体经历了从合到分再到“合之努力”的发展历程。 儒学与文学最初的结合,是广义的文章学与儒学的结合,儒士往往集此两者于一身。 而“文学”,是儒家士人最初的进身之道,即汉初的“以文章进”。 西汉初期的选人制度,为文学创作主体的涌现和积聚提供了机会,造就了其后文学创作的繁荣,而此时,当初的儒士亦分化为两个阶层:言语侍从之臣和公卿大夫,儒学与文学亦开始分化。 应该注意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此时的“言语侍从之臣”的创作,更接近于今天所说的狭义的文学,论者谈汉代文学的自觉,大体以此为主要依据。 儒学与文学分化后,各自有不同的走向,儒学因为与政治的契合,成为汉代文化的主导,发展为经学;文学虽然也在汉代政治体系框架内,如西汉有“文学掌故”“文学卒史”之类的职官,但大体是不入流的,而一度繁荣的“宫廷文学”创作,有的成为“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1]3318的“滑稽”,甚至滑向俳优的边缘。 此时,以扬雄等对文学创作的反思为表现,儒学与文学得以重新靠近。 东汉中前期“斟酌经辞”的文学创作意旨,以此为形成背景。
汉代儒学与文学所作“合之努力”中,扬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言》中包含了对其时代之文学的认识,亦体现了较早的宗经、征圣文学观念。扬雄的这种文学观念,可以从其对前人的批评中观察。 其一,由推崇模拟司马相如到反对批判。《法言》记:“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状夫不为也,悔作之也。’”[18]49此视经学与文学为“大道”与“小辨”之关系,论者所言繁多。 其二,对东方朔的批评。《汉书·东方朔传》之赞记:“扬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4]2873与对司马相如的批评比较,文字中出现了正面的对象即“师”和“德”。 其以“言不纯师,行不纯德”批评东方朔,那么“纯师”和“纯德”应是其所坚持的对象,而结合扬雄作品中的思想,这里所说的“师”应为儒家先贤,“德”应为符合儒学思想的品行。 其三,对屈原的评价。 《汉书·扬雄传》记:“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 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4]3515“天命”观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孔子对“遇不遇”各自如何对待亦有明确态度,扬雄此言表达了儒家入世观,其所作《反离骚》等,则体现了对“贤者失志”之文学的摒弃。 司马相如等的“言语侍从”之作之前,被认可具有较强文学属性的是屈原等的“贤者失志”之作,此两类作品不但是汉代文学的主体,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较大的比重。 扬雄希望这两类作品,回到“纯师”“纯德”的轨道上来,也即以儒学为经纬。
文学与儒学结合,本质上是以文学传递或解读经义,这也是扬雄所希望的“通经”,但无论从扬雄自己的创作实践,还是东汉文章的“斟酌经辞”上看,这一点很难做到。 刘勰所以在征圣和宗经之前加上“原道”,也是对征圣、宗经只能作为方法而无法成为文学主题的一种妥协。 也就是说,征圣或宗经,可以“《诗》曰”等形式直接出现在说理性文字中,对有自己独特形式的汉赋而言,则难以直接介入。 所以我们看到,东汉文章的“斟酌经辞”,主要表现形式为用典。 许结、王思豪认为:“汉代赋家引述经典之方法,最明显表现于‘取辞’与‘取义’两端。”进而说明:“赋家用经取义,本质也是取辞,只是所谓‘取义’,更多的价值是赋家引述时重在发掘经文之内涵与历史意义,并融之于作品之现实情感。”[30]“斟酌经辞”的主体,是将经文的历史本义与作者所要表达之义融合,与传递或解读经义,实不可同日而语。 如张衡《思玄赋》中涉及的《易》之《遁》卦,对《诗》之《关雎》的举例,涉及《尚书》《左传》等中的具体事件,其实质只是一种用典。 儒学与文学之合,最终只能是一种存在于理论上的努力。 东汉中前期文学创作的“斟酌经辞”,让我们看到的是文学与经学之间的距离,体现的是文章对经典从征引到化用的变化,带动的是中国文学的用典传统。
(二)王充、班固盛世文学观的阐发与弘扬
汉代对盛世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理论总结,武帝时期即有之。 元狩元年获白麟、得奇木,武帝以之为异,终军上疏言:“臣闻《诗》颂君德,《乐》舞后功,异经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又曰:“夫天命初定,万事草创,及臻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必待明圣润色,祖业传于无穷。”[4]2814-2816其指出了文学的功能和歌唱盛世的必要。 东汉前期的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进一步激发了文士儒生的盛世意识,其与当时的选人、用人制度一起,推动了盛世文学观的形成。 东汉时期的盛世文学观,以盛世认知为基础,以大规模颂扬盛世作品的涌现为土壤,以成体系的理论构建为标志。
东汉时期的盛世文学观之理论主要是由王充、班固建立的。 班固在弱冠之年因一篇奏记步入仕途,在奏记中其盛赞东平王苍:“将军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灵之号,昔在周公,今也将军,《诗》、《书》所载,未有三此者也。”[8]1330以之比于周公,且言“未有三”,颂赞贵胄的起点极高。 班固对盛世文学观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对“贬损”文章的批判。 《典引》序言所谓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31]682,明确与班固的“具对素闻知状”相关,实为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这体现了班固的作文立场。 其二为“因时而建德”观念的提出。 班固认为:“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其解释说:“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4]22此与其“盛哉乎斯世”的“时”之认识一起,构成了盛世之歌的出现条件。 其三是对文章之职责问题的提出。 《典引》言:“至令迁正黜色宾监之事,焕扬宇内,而礼官儒林屯朋笃论之士而不传祖宗之仿佛,虽云优慎,无乃葸欤!”李贤注曰:“不传谓不制作篇藉,以纪其功德。”[8]1381-1382“焕扬宇内”而“不传”,是作文之人的缺憾,也是文章职能的缺失。
对盛世文学观做出明确而系统阐述的是王充,其《论衡》以《须颂篇》为中心为我们具体描绘了文学与盛世的关系。 我们可以视这种行为为颂扬盛世的理论化与合法化,也可以将其视为在文学与经学、文学与言语侍从等复杂关系中,对文学如何发展的突围。 王充的盛世文学观主要从鸿德须颂、臣子当颂、颂方知德、汉德可颂、或有增益等五个方面立论,由鸿德须颂到臣子当颂再到颂方知德,汉德可颂且应颂结论水到渠成,《论衡》中甚至明确了如何颂的具体方式。 王充之盛世文学理论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至少从三点观察:其一,确定文学与盛世的关系。 王充从《诗》之成立即孔子与《诗》的关联,以及制礼作乐的释义开始确认“鸿德须颂”的前提,进而列举“夔歌舜德”“周歌棠树”等实例为证,在儒家的话语体系内讨论文学与盛世关系,使其更具说服力。 其二,为作颂者正名。 《后汉书·马融列传》云:“初,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8]1972人们对于颂赞之辞的态度是不一致的,为作颂赞者正名是颂赞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其三,提示了“称古”还是“称今”的问题。 王充认为“汉德不及六代”,是因为“论者不德”“成汤遭旱,周宣亦然”“无妄之灾,不能亏政”“论好称古而毁今,恐汉将在百代之下,岂徒同哉!”[19]852汉代之兴盛比及三皇五帝,舆论上之所以不如三皇五帝,是“论者”的责任,而这些,在根本上取决于“好称古而毁今”的观念。 此是王充的盛世文学理论留给我们的哲学命题。
《须颂篇》多处强调《论衡》一书对彰显大汉盛世的作用,结尾处更以“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为由争取与皇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这对其盛世文学观的构建有所冲淡,甚至令人对这种盛世文学观的构建初衷有所疑虑。 但回到现实层面,我们需要思考文学的出路这一根本问题。“常称疾避事”的司马相如,扬雄以为“壮夫不为”;“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的东方朔,有“客难”之忧;阳球“罢鸿都文学”之奏议言:“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8]2499文学不只是作颂一途,但文学的主体即作者需要生存,甚至他们还希望有尊严地生存,甚至是列备高位。 王充的盛世文学观,或者只是其在文学与经学、文学与言语侍从、文学与时代等复杂关系中,对文学如何发展的一种思考。 这种思考,并无理论远离实践之荒谬。
(三)儒学的式微与“大一统”文人精神的消解
白虎观会议压缩了儒家经学的发展空间,章帝之后东汉恶劣的政治环境挤压了儒家士人的生存空间,对经典进行章句训诂及典章制度等研究的繁荣背后,是儒学在汉代的式微。 起于新莽时期的士人思想取向多元化,与经学衰落一起见证了“大一统”文学精神在汉代的变迁。 由关注国家转而关注内心世界,成为东汉后期儒家士人精神追求的走向。
汉代的儒学应该从治世之儒学与治学之儒学两个方面观察。 汉章帝建初四年的一份诏书择要回顾了治学即作为学术之儒学的发展历程:“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 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 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 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8]137-138正是在这份诏书的动议下,白虎观会议召开。 白虎观会议的主旨为“论定《五经》同异”,是儒学之盛事,在一定时间内也促进了儒学的繁荣。 但与汉宣帝时期召开的石渠阁会议鼎定儒学地位相比,此次会议是对儒学具体内容的“论定”,在客观上压缩了经典的解释空间,从而造成儒学的固化。 这种固化带来的后果是,“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到汉安帝时期,则出现“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 颓 敝, 鞠 为 园 蔬, 牧 儿 荛 竖, 至 于 薪 刈 其下”[8]2547的“薄于艺文”之局面。 此后虽有偶尔的复兴,“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8]2546-2547。
对应学术层面的儒风衰落,治世层面的儒学同样受到冷落甚至打击,包括儒家士人的进身之路被压缩,更体现在来自宦官及外戚集团的直接迫害。 西汉早期的“以文学进”及其后形成的察举等选人用人制度,在东汉中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儒家士人极少有直接进入政权核心的机会,热心于仕宦者且只能依附于个人,“独行”或“逸民”阶层出现并不断扩大。 对汉代儒学打击最为直接的自然是禁锢党人。 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其一,汉代政权对儒家士人的打击一直存在。《史记·平准书》记:“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1]1424像枚乘等那样,能够在吴王谋反前另投他主甚至其后又得到皇帝垂青的,不知几许。其二,汉代儒家士人的力量不容小觑。 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欧阳歙因罪下狱,不但出现“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的震撼场面,更有礼震“驰之京师”“上书求代歙死”。 徐复观论之曰:“东汉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历史中能占一很重要的地位,乃是另有一部分置生死贵贱贫富安危于不顾,绳绳相继,在政治的极端黑暗中,作出各种不屈抗争的节义、名节之士。 一直到党锢祸起,这些抗争不屈的节义、名节之士,才与东汉同归于尽。”[32]172-173这些“抗争不屈的节义、名节之士”的出现,本身就是儒学衰落之映像的组成部分。
国家统一、政治安定下的文化繁荣,是“大一统”文人精神赖以存在的土壤,伴随着东汉中后期儒学式微的是“大一统”文人精神在汉代的黯然离场。 《后汉书·皇后纪》言:“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汉仍其谬,知患莫改。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8]401此“主幼时艰”虽为言古,而实为东汉中后期政治的真实写照。 关于主幼,汉章帝以后东汉又历十帝,即位时的年龄都很小,有三人在位时间不超过一年,而且如上所引,“外立者四帝”,这决定了东汉中后期动荡的政治局面。 关于时艰,自然灾害之外,更多的是对外战争,“汉氏征伐戎狄,有事边远,盖亦与王业而终始矣”[8]2860,但“中兴以后,边难渐大”,建立燕然勒石功绩的同时,仍有很多“得不酬失,功不半劳。 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8]2900的情况,这显示了东汉中后期局促的外部存在环境。 东汉中后期的内忧外患,侵蚀了“大一统”人文精神赖以生存的土壤,取而代之的,是儒家士人价值追求与思想意识的多元取向。《后汉书》之《独行列传》《逸民列传》等的记述,反映了这种思想的根本转变。 治世当振羽,乱世可偷安,由治而乱的文火慢煮,导致思想精神的耗散,这是东汉后期儒家士人的群体宿命。
(四)建安文学对“大一统”文人精神的出离与眷顾
建安文学是东汉末期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公元196 年,汉献帝改元建安,也是在这一年,朝廷迁都许昌,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同时,网罗文士且亲身参与文学创作,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内容上多为对个人情感的抒发与关注,形式上极少有汉大赋的形制,赋作一般比较短小,精神气质已无“大一统”的人文底色。 但同时,建安文学创作中体现的慷慨之气,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与别样的家国情怀,与哀婉低回的《古诗十九首》等在风格上差别明显,仍体现着“大一统”文人精神之余韵。
“大一统”文人精神的分野,在于事物观照格局的大与小、事理所持观点的公理与权变、个人情感融入的平和或哀怨。 建安文学以三曹、七子为创作主体,《三国志》云“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33]602,但由于曹丕等的推崇与甄选,“七子”声名更显。 曹丕在《论文》中提出“七子”之说并分别评论,在《与吴质书》又言:“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 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 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 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 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 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 仲宣独自善於辞赋,惜其体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34]591后人论建安七子,多以王粲为先,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曹丕对徐幹的推崇。 徐幹的文学作品今多不存,但从其《中论·治学》 所说的“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35]9“大义为先,物名为后”等观点来看,其对文章创作的家国情怀是有要求的,文章的视野格局应该是开阔的。
同样在作品中展示出开阔视野与格局的还有曹植。 建安文学关注个人,但对个人的关注,不只是在内容或情感上以个人为中心,还包括以个人的视角去思考问题、去观察世界,后者决定了作品的视野与格局。 曹植在《白马篇》中塑造了一位“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的游侠形象,叙写铺陈之后,在结尾处以“名编壮士藉,不得中顾私”明确了游侠所作所为的原因在于责任与担当,“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更体现了乱世的人生理想与家国情怀。 在相同的外在环境中看到不同,在同样的建功立业追求中强调责任,身处乱世时清晰区分“小家”与“大家”,曹植文学创作背后的人文精神是需要认真考量的。
事有大小,理亦有公私,言公理者其气自正,其慷慨之音自高。 顾炎武云:“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36]469顾炎武将汉末的风俗流变归因于曹操的用人标准。 实际上,人的品性是不容易改变的,如孔融的刚直;追逐功名与寻求正义之间亦有契合点,如陈琳的创作。 在建安文学里,陈琳以“章表殊健”著称,能为“章表”决定了其与同时期其他文士的不同。 在东汉末年影响较大的何进借助外力“清君侧”事件中,陈琳谏曰:“《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 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 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8]2249此与王粲劝刘琮归顺曹操之言相较,公与私、凛然正气与苟且权变之差别高下立见。 王粲的话是:“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在仓卒之际,强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 当此之时,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 观古今之成败,能先见事机者,则恆受其福。 今将军自度,何如曹公邪?”[33]598对陈琳文学创作中展现的凛然之气,更可以从其作品如《神武赋》《武军赋》等中感受。
迁都许昌时东汉政权面临的状况是:“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 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8]379皇室以及权臣尚且如此,一般士人和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就更加艰难。 所以建安文学作品中多有对这种时代境遇的描述,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追问,此类作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最为论者所重视。 但同样是感时伤情,在不同作者那里有不同的呈现。 如曹操的《短歌行》,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起,在“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短暂感伤之后,主体内容包括间或的愁绪皆为哀而不伤之词,慷慨激昂中蕴含的是平和之气,这是建安文学最大的亮色,也是汉代“大一统”文学精神的袅袅之余音。
结 语
汉代“大一统”帝治时代的国家建立是一种全新的政治模式的尝试,儒家士人在这种政治模式完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即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学术体系的重构,成为汉代政治思想体制建设的重要部分,儒家士人的政治理想、知识结构、文化精神又成就了“大一统”国家文学建构的使命。 汉代文学也就成为国家政治与经学思想双重影响下的文学,这样的政治人文环境决定了汉代文学的底色:以儒家士人的入仕精神为发展动力,以“大一统”的国家情怀为外在呈现。 虽然我们不能否定从战国纵横风气走来的汉初士人的文化乃至文学的贡献,但是,有汉一代,儒家士人精神的凝聚在西汉的武帝、宣帝时期,东汉的明、章帝时期达到了高峰,恰恰又是汉代政治的鼎盛期,更是两汉文学创作繁荣与文学理论蜕变时期,可见,贯穿于两汉的儒家士人内蕴的人文精神对于汉代文学影响是巨大的。 两汉国家政治的沉浮、儒学体系的变换,则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具体发展脉络,并随着大汉政权的瓦解和经学的停滞最终走向对个人的关注,迎来魏晋时代的文学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