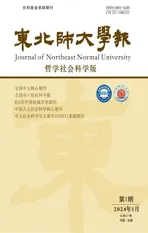数字农业中农民保障的制度创新
2024-04-07于霄
于 霄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的数字化发展,数字社会也越来越完整地反映真实的社会关系。消费关系数字化是最为人熟知的领域,而生产领域的数字化却可能给社会带来更深刻的改变。从200多年前的钢犁和收割机的大规模使用,到现代的大规模种植机械和转基因种子等的进步,人类不断寻找新的方法来养活世界上不断增长的人口。每当农作物生产与人口的增长面临失衡的时候,各种技术的融合总能推动农业生产的新发展,化解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挑战。而数字农业也试图通过高性能计算、自动化、智能化和大数据的力量来实现农业的新转型。
数字农业在我国正在快速发展。比如湖南、江西、重庆等地依托北斗卫星、物联网、5G等数字技术,启用智能化育秧工厂、自动插秧机等,大大提升了春播效率(1)参见刘洁:《各地抢抓有利农时 做好春耕春管生产工作》,载央视网,2022年04月07日,https://news.cctv.com/2022/04/07/ARTIVEVhhEj7hL3T5BvgsVpa220407.shtml。;内蒙古将信息化引入农业生产全过程,打造智慧农场和智能温室大棚,实时采集监控土壤温度、水分、pH值等参数,普及智能化温度控制、湿度控制、灌溉等系统(2)参见富丽娟:《数字赋能 内蒙古农牧业尽显“科技”范儿》,载人民网,2021年12月14日,http://nm.people.com.cn/n2/2021/1214/c196689-35050245.html。;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数字农业示范区”依据销售终端的大数据形成的采购订单确定采摘数量,根据销售终端提供的数据分析,提前给种植大户编制下一阶段的种植规划(3)参见陈平丽:《浙江衢州推行数字农业 大数据指导农民种地 助农增收》,载央视网,2021年03月26日,https://news.cctv.com/2021/03/26/ARTIJ6INA2unAU2rT0H4J8Hw210326.shtml。。
数字农业的发展将会深刻改变我国农民保障的制度逻辑。随着农业数字化,数据成为与土地同等重要的基本生产要素,数字知识替代经验知识成为主要决策依据,农业公司成为中心化的农业组织。这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会损害农民的权益。损害的可能是农民的既有权益,也可能是农民的发展权益,而发展权益是主要方面。比如我国现在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收益大都以传统粮食生产收益为基础(即粮食生产收益转换成租金),农民很难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收益。另一方面,可能使原有制度结构无法运行。比如农业自动化使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进一步被边缘化,使土地承包保障体系发生根本性改变。
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农业的发展。数字农业是较“精准农业”更为系统化的概念,不但涵盖生产,也包括销售、服务等上下游产业。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要求“把信息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制高点,推动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应用”(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6-07/27/content_5095336.htm。。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将“大力发展数字农业”作为构建现代农业体系的一部分(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www.moa.gov.cn/ztzl/xczx/zgzygwygyssxczxzldyj/201811/t20181129_6163945.htm。。2019年至今,《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一批支持数字农业的文件公布。各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相关实施政策,比如《上海市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5年)》计划打造10万亩粮食生产无人农场和一批智能化菜(果)园,建立涉农数据标注和整合利用机制(6)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的《上海市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5年)》,沪府〔2020〕84号。。
目前国内外关于数字农业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数字技术给农业带来的效率提升,而忽略了其对农民的负面影响(7)See M.Kansanga,et al.,“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transition:Examining the impact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n smallholder farming in Ghana under the new Green Revolution”,26 Int.J.Sustain.Dev.World Ecol.11,11 (2019),https://doi.org/10.1080/13504509.2018.1491429.。从过去技术驱动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看,比如:绿色革命和生物技术,这些技术带来经济效益,也会产生社会和制度风险(8)See Kelly Bronson,“Responsible to whom? Seed innovations and the corporatization of agriculture”,Journa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Vol.62,No.2,2015,pp.62-77.;转基因生物种子专利,保护了种子研发公司,提高了作物产量,也损害了传统农民的种植收益,加深了农民对种子公司的依赖(9)See Maurice E.Stucke &Allen P.Grunes,“An updated antitrust review of the bayermonsanto merger”,The Konkurrenz Group (Mar.6,2018),https://www.farmaid.org/wp-content/uploads/2018/03/An_Updated_Antitrust_Review_of_the_Bayer-Monsanto_Merger-03.06.2018.pdf.。现在大型农业公司通过兼并公司、垄断种子和化肥专利以及数字平台的专有数据等方式来垄断数字农业,将农民从独立的经营户转变为从属性极强的数字平台用户(10)See Kelly Bronson,“Looking through a responsible innovation lens at uneven engagements with digital farming”,90-91 NJAS-Wageningen J.Life Sci.100294 (2019),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573521418302173.。
我国数字农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所以数字农业对现有制度的冲击尚未完全展现出来,但数字农业必将迎来高速发展。为了更好地在数字农业中保护农民权益,在制度层面对农业数字化做出应对,应当对数字农业对制度的冲击进行深入研究,并对现有的农民保障制度进行创新。
二、数字农业社会转型的特殊性
(一)从数据控制到知识替代
数字农业在很多国家已经有深入实践,这从一些侧面揭示了数字农业的技术路径。20世纪60年代,精准农业出现。“精准农业是将有关生长条件的信息与复杂的、由计算机控制的农业设备连接起来,以便农民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耕作单一区域内的不同土地。”(11)J.Kim Kaplan,et al.,“High-tech fattens the bottom line”,AGRIC.RES.,Apr.1996,pp.4,http://www.ars.usda.gov/is/AR/archive/apr96/tech0496.pdf.比如通过产量测绘系统,农民可以获得更充分的信息来决定下一季的农业生产安排。精准农业本质上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数据分析、智能算法、网络传输等技术,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准确、更精细和更经常的决策辅助生态。
农业公司正在通过控制数据的方式控制农业生产。其一,农业公司通过投资获取主要数据搜集渠道。数字技术的使用需要大量初始投资,并且数字农业投资一般回收期较长。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更倾向于更直观见效的投资,比如修建更多大棚。其二,农业公司通过垄断技术获取主要数据搜集渠道。数字农业具有一定的技术依赖性(12)参见钟文晶等:《数字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改革》2021年第5期。。数字农业的运营包含数据的采集、传输与分析,农业决策的形成,农业机械的数字化操作与控制,等等。但即使是数据采集所用传感设备的安装这种相对比较简单的操作,也并非普通农民可以完成。加之,我国农民基本条件差异性极大,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也会影响数字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对于认识与行动能力较弱的农民来说,数字农业可能是一种复杂、昂贵和难以预期的生产手段。
农业公司与一般平台的数据控制有相似之处,但在程度上具有很大差异。在投资上,一般平台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甚至大众平台的用户也同时是投资人。而农业公司的投资大都来源于非农民群体,投资人与用户具有明显的利益区隔。在数据的采集上,一般平台搜集的是用户相关数据,而农业公司采集的则是农业生产相关数据。这一点对后续的知识垄断和身份从属有决定性的影响。
数字农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以经验为主体的农业知识系统,这相较于以工商业为代表的其他行业更具颠覆性。数字农业的知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数字农业知识载体数据具有数据量大、形式复杂、难以读取(加密技术)的特点,超出农民的认知能力。二是数字农业系统的决策更值得信任。在输入端,传感器比人更不容易出错;在知识端,数据量大,可以更精细地认知环境与条件;在决策端,算法可以纳入决策考量的变量更多,权重更科学;在验证端,决策更具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数字决策几乎可以保留完整记录。三是数字知识传输效率高,决策更便捷。相较工商业知识体系,农业知识体系更为传统与分散。农民一旦产生关于生产的疑问,主要靠“打听”获取知识。而相较于口耳相传的知识,数字农业系统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由其提供算法决策建议更加便捷,成本更低。数字农业知识系统取代传统知识系统更为容易。
数字农业导致的知识替代与一般意义上的数据控制具有本质不同。首先,知识不仅包含信息,更是被证明为真的信息;而数据是客观信息的数字形式,其范围非常广泛,真实性能为人接受的数据仅占很少比例。其次,尽管一般平台通过数据控制也可以获得信息优势,但信息不对称所形成的行为影响远弱于知识替代的效果。信息不对称是平台控制数据的后果,但知识替代描述的是在获取信息、分辨信息和评价信息上的地位差异。
(二)从知识替代到身份固化
知识系统的替代会引发农民身份的改变,农民逐步成为数字农业系统的从属主体(13)即数字农业系统的主体。参见胡耀辉:《安全配置:福柯治理术的运转机制》,《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1期。。购买和使用产量监测系统通常是使用数字农业技术的第一步。产量监测系统是由大量传感器、网络传输设备、中央服务器和软件技术支持(包括算法与技术人员等)组成,用于在收获期间实时收集、计算、显示和记录农作物产量的系统。当农民完成以上系统建设后,传统知识就失效了。传统知识与数字农业知识只能选择其一,两者并不相容。农民也会对数据的使用有所担心,但只能依赖专业机构进行指导与维护(14)See Thomas Dietz,et al.,“Support for climate change policy: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structural influences”,Rural Sociol,Vol.72,No.2,2007,pp.185-214.。已采用数字农业技术的农民很难回归传统农业生产。同时,很多传感器不能收集的地方性信息也随之失效,传统农业知识中的一些重要经验也将遗失。这一过程可以被看作福柯所说的治理术,即通过制造用户身份来管理行为和影响社会身份的权利行使技术。通过身份在新环境下进行治理,有很长的历史。比如美国在印第安人居住区以森林管理为借口为土著印第安人创建了行政身份,而印第安人在这一身份引导下为保护森林权益将身份内部化(15)See Purabi Bose,et al.,“‘Forest governmentality’:A genealogy of subject-making of forest-dependent ‘scheduled tribes’ in India”,Land Use Pol,Vol.29,No.3,2012,pp.664-673.,政府正是通过新身份维持了对森林和印第安人的治理。
农业公司正在成为数字农业的组织中心。在知识替代过程中,农业生产越来越远离小农式的分散经营,走向“信息数字化、传输网络化和决策中心化”的新模式。在数字农业技术的持续运用中,农民开始“像算法一样行动”(16)See M.Carolan,“Acting like an algorithm:Digital farming platforms and the trajectories they (need not) lock-in”,Agric Hum Val,Vol.37,No.4,2020,pp.1041-1053.。比如,John Deere拖拉机不允许用户自行维修,拖拉机一旦故障,用户只能到公司授权维修处进行维修,因为拖拉机上安装了大量传感器,为平台服务系统提供数据,而公司并不希望用户访问、控制或拥有这些信息(17)See Michael Carolan,“Automated agrifood futures:Robotics,labor and the distributive politics of digital agriculture”,Peasant Stud,Vol.41,No.1,2020,pp.184,201.。农业公司利用技术手段(比如安装电子锁)、合同与知识产权来保证自身对数据的控制权。高效技术的使用,使农民产生了依赖性,更多的设备、更大的投入、更日常的数据上传建构与固化了新的生产秩序,形成“结构性锁定”(18)参见张欣:《从算法危机到算法信任:算法治理的多元方案和本土化路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在这一秩序中,农民更依赖农业公司提供的种子、化肥、新设备、农业生产决策等。
数字农业在我国具有一些特殊性,使农民形成身份从属更为可能。其一,政府将其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途径加以支持。近年我国技术条件取得很大进步,数字农业发展具有很好基础,特别是在人造卫星、无人机、无人驾驶、遥感、云计算等方面已经跨入世界先进行列(19)参见王士英等:《关于加快中国精准农业发展的思考》,《世界农业》2021年第4期。。在这种背景下,农民通过数字技术改进农业生产以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愿望,变成了其应当接受的一种行政推广命令(20)See Declan Kuch,et al.,“The promise of precision:Datafication in medicine,agriculture and education”,Pol.Stud,Vol.41,2020,pp.527-546.。其二,农业公司利用资本推动农民接受技术改造。数字农业使技术密集型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较其他农业生产方式更具优势(21)See StartupAUS,Powering growth:Realising the potential of AgTech for Australia,2016,https://www.commbank.com.au/content/dam/commbank/assets/business/can/agri/ag-tech.pdf.。而数字农业的资本密集性对农业公司具有重要意义。相较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农业公司更重视资本在农业技术转型中的参与度与预期红利。其三,社会价值观推动数字技术应用。因为数字农业技术更具效率,支持者将“农业创新”“公共利益”“绿色环保”等这些具有社会价值指向的表述与之联系,这使对接受新技术的农民的鼓励成为对不接受的农民的谴责(22)See H.Godfray,et al.,“Food security:The challenge of feeding 9 billion people”,Science,Vol.327,2010,pp.812-818.。接受新技术的农民没有成为被赞扬的先进者,而未接受新技术的农民却成为对粮食增产的威胁、环境污染的原因和公共利益的破坏者(23)See Michael Carolan,“Automated agrifood futures:Robotics,labor and the distributive politics of digital agriculture”,Peasant Stud,Vol.47,No.1,2020,pp.184-207.。所以,我国也正在或正要面临以上这些技术转型中的问题,甚至面临更多挑战。
三、数字农业对既有制度解构的三个维度
从理论上分析,农业的数字技术转型将会对我国农村制度总体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其一,生产资料结构的转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我国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从几乎完全的人民公社公有转变成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个人所有。而数字农业在发展初期需要大量基础性投入,但其收入却是远期的(24)参见李淑芳:《中国精准农业推广对策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19年第4期。,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个人都难以完成(25)参见倪浩、刘志民:《家庭农场互联网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9市270户家庭农场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需要农业公司的参与。所以,农业的投入结构改变可能导致农业生产资料的资本化。其二,农业生产劳动结构的转变。在农业生产决策的过程中,数字知识逐步替代传统农业经验知识,而物理劳作也逐步由自动化机械替代,这使大量传统农业生产者脱离农业生产,而由于大量技术工人加入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更加社会化。其三,社会关系结构的转变。生产结构转变意味着我国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当资本、机械、技术工人大量进入农村社会,农村原本的治理模式、熟人社会、地域依赖、文化认同等也将转变。
具体到对农民保障制度的冲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土地保障能力受到数据生产地位提升的削弱
传统上,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所谓基本生产要素是指缺少这一要素生产无法进行,并且这一要素对生产效果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掌握这一要素就可以从要素控制的生产中稳定获取收益。对于土地,清朝张英认为,其“不忧水火,不忧盗贼,虽有强暴之人,不能竞夺尺寸;虽有万钧之力,亦不能负之而趋”(26)张英:《笃素堂文集》卷十四,康熙刊本,第392页。,是稳定的财富形式。囤积土地在保守的农耕社会成为最好的财富积累手段。清朝庞尚鹏在家训中强调,“如商贾无厚利,而妄意强为,必至尽亏资本;不如力田,犹为上策”(27)庞尚鹏:《庞氏家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正因为土地传统上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我国才将土地作为农民保障的基础。
我国现行的农民保障机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生活保障、劳动机会保障和其他保障。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三重保障由生产队负责。经过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逐步普及,农民保障制度发生了质的改变,形成了以宅基地为中心的生活保障、以农耕为主的劳动机会保障和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依托的其他保障的基本形态,其中前两者为土地保障,后者为组织保障。集体组织的保障以集体财产为依托,而集体财产很大部分来源于土地。所以,我国农民保障可以说是以土地为基础的保障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化的推进,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给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带来了重大改变,我国农民的保障体系也受到极大影响。2014年,三权分置改革试图将农村土地从农民保障功能中解放出来。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民保障的制度体系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相比没有本质变化。
以数据为依托的数字农业具有以土地为依托的传统农业所不具备的优势。其一,数据使农业生产创造更大效益。随着数字农业各项技术手段的运用,农村土地地理数据、农作物产量数据、农业机械运作数据、农作物销量数据等各种数据,逐年积累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巨量的数据辅之以相适的算法,农民、农业公司、农产品销售平台等可以在农业的生产、经营、销售和投资等方面做出更科学合理的决策,并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其二,数据使农业生产更加精细(28)参见姜靖、刘永功:《美国精准农业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科学管理研究》2018年第5期。。数字农业系统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科学算法的设计所得出的农业运作模式是传统农民基于一般经验与猜测无法比拟的,甚至数字农业的模型也远远优于一般农业科学家的知识经验。数字农业系统可以随时提供农民所需要的决策建议,更为便捷,成本更低。其三,数据使农业生产更具市场性。市场数据在生产中的参与使农业生产可以更适应市场需要,客观上提高了农产品的价值。更先进的智能数据分析甚至可以发现潜在的市场需求,从而引导农业生产更有效进行。此外,数据可以优化农产品流通,使农产品分配更迅速与合理。
在数字农业中,数据成为与土地同等的基本生产要素,甚至比土地更具基本性。“水资源、土地资源等传统要素对于农业的制约逐渐下降。”(29)赵敏娟:《智慧农业的经济学解释与突破路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4期。因为数字农业的优势,传统农业无法与之竞争。没有土地无法进行农业生产,而没有数据将会使农业生产价值受到根本性的损害。随着农产品的市场化越来越深入,缺乏竞争力可能使部分农产品无法商品化。农业生产中,土地可以提供实物保障,而数据才能保障经济收益(30)参见聂召英、王伊欢:《链接与断裂:小农户与互联网市场衔接机制研究——以农村电商的生产经营实践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21年第1期。。于是,数据在农业生产中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与具有决定性的要素(31)参见阮俊虎等:《数字农业运营管理:关键问题、理论方法与示范工程》,《管理世界》2020年第8期。。
农业公司通过控制数据控制农业生产会损害农民的既有利益。农业公司意识到农业数据的商业价值之后,会更积极地攫取这些数据,但我国农民大多还没有数据保护意识。数据控制权的丧失就意味着竞争力下降和收益减损,甚至意味着受到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的损害。农业公司利用数据既可以与农民实现双赢,也可以损害农民利益(32)参见胡键:《算法治理及其伦理》,《行政论坛》2021年第4期。。比如种业公司可以根据数据更精准地提供产品,减少物流费用和错配,帮助农民优化农业运营;但同时,农产品销售平台也可以利用数据预测产量,从而压低收购价格。但如果没有对损害的正确应对,那么这种损害则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农业公司控制农业生产会剥夺农民的发展利益。我国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利用土地要素的基础性来为农民提供保障。在数字农业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保障表面上可能并不会减弱。比如农业公司通过长期租赁的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然而,农业公司通过数据取得了相对于拥有土地权利的农民或集体的谈判优势地位,农民在三权分置中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就退化成一种极低价的固定收益。
所以,随着数字农业的发展,农业公司通过对数据的控制可以逐步控制农业生产,进一步通过支付极低价的固定收益,获取土地使用权。而以土地为中心的保障体系由此丧失了发展性,甚至农民原有利益也会在此过程中受到损害。
(二)知识替代使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被边缘化
随着上传的数据越来越多,新旧设备不断更替,决策习惯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农民逐步将数字农业系统辅助内化为自身的行为模式。农民开始接受并依赖数字系统的决策,这包括农业生产本身,也包括对数字农业的新增投入建议。农民在与数字农业系统的互动中,依赖性逐步增强,最终形成一种农民单方面接受数字农业系统指令的新行为结构。在数字农业的指令中,既有为农民服务的、基于技术分析的农业生产建议,也有从农业公司利益出发的、被伪装成有利信息的建议。这种依赖性成为农业公司新控制权的基础(33)See Deborah Lupton,“Digital sociology”,London:Routledge,2015,pp.24-26.。
农民的社会身份最终也会随之改变。虽然农民在数字农业中的用户身份主要通过自身的使用行为创建与强化,但数字治理权力主要控制在农业公司手中。数字用户身份在人与算法的互动中被不断加强,并最终反过来影响农民的社会身份。农民数字身份的基础是农民对数字农业系统的信任,而在这种身份稳定之后,农民便以一种道德视角来观察数字农业。农民在向现代农民、数字化农民、创新型农民转变的过程中,越来越将数字农业视为一个道德社区(34)See Dario Castiglione,ed.,“The handbook of social capital”,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01-121.,他们认为收集数据、接受算法和运用自动化机械是一种道德实践。所以,对数字农业的接受逐步转变为一种理想化的价值观,而非量化精确的风险与利益评估。由此,农民的用户身份在社会上得以固化。
知识系统的替代与农民身份的转变意味着农民退出农业决策机制而成为农业工人。在数字农业生产中,农民只是算法辅助的主体(35)See Declan Kuch,et al.,“The promise of precision:Datafication in medicine,agriculture and education”,Pol.Stud,Vol.41,2020,pp.527-546.。智能化机械会进一步替代农业劳动,农业劳动将会被重新分配,农民与生产之间逐步被数字鸿沟分割(36)这包括信息、设备与投资差距。参见陈潭、王鹏:《信息鸿沟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症候》,《电子政务》2020年第12期。,农民越来越不能理解农业生产的过程。人工智能和非标自动化的普及还可能导致农业工人失业的高风险(37)See Martin Ford,“Rise of the robots: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 future”,New York:Basic Books,2016,pp.83-86.。然而,集体经济组织原本提供的保障具有实物性、地理限制和管理能力限制。在新的条件下,单一地理条件的保障限制了边缘化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权。
知识替代改变了以传统农耕为主的保障逻辑。农民的劳动机会保障这里主要指提供经常性的劳动机会。在人民公社时期,我国农民的劳动机会由生产队提供。1961年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规定,“生产队应该组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劳动”(第30条);生产队负责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分配制(第20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人民公社的劳动机会保障体系。1982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发〔1982〕1号)要求实行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联产就需要承包。承包形式多样,主要是包干,即“包交提留”,取消工分分配。所以,从历史上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时是建立在人民公社公有制经营基础上的一种计酬制,但随着土地承包制的发展,其优越性得到了体现,承包的农民越来越多,希望承包的面积也越来越大,就出现了土地需过于供的情况。于是,生产队平均的劳动机会保障就逐步转变为承包机会保障,即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了一种具有保障性的权利。数字农业时代,知识替代一方面替代了一部分的人工劳动,更重要的是使农民从农业劳动主体转变成了从属主体。农民不再可以凭借集体成员身份获得平等的劳动机会。
(三)集体经济组织的保障能力受到农业公司的减弱
集体经济组织是我国传统的农业基本生产组织,也是我国农民保障的经济依托。“六十条”规定,“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社员的生产和生活的单位”,也是“人民公社这个联合经济组织当中的独立经营单位”(第2条第2款)。基于生产的收益,集体经济组织也是我国农民保障的经济依托。首先,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医疗保障的经济依托。2003年,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03〕3号)建立了现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的基本框架,规定新农合由县政府统筹,而筹资实行的是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机制。虽然该意见规定农民个人和地方财政每年的筹资标准不低于10元,但农民数量多、地方财政压力大,而个人缴费过高会影响参保率,所以集体经济组织的筹资至关重要。并且,新农合只能解决农村医疗保障的部分问题,并非所有农民都参加了新农合,新农合报销比例有限。现在,新农合报销比例根据就诊级别不同分为20%—60%不等,并且设有限额。所以,一旦农民因病致困,集体组织仍然是救助纾困的重要主体。其次,集体经济组织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养老保障的经济和组织依托。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制度。与新农合相同,新农保也面临缴费与参保率冲突的问题,这需要集体经济组织补助和协调。并且,新农保远不能满足农民养老保障的需求,比如每年缴费500元,缴费15年,实际领取每月只有117元。更为重要的是,养老保障是人财物一体的保障体系,仅有养老保险很难达到农民养老保障的目的。所以,只有集体经济组织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积极采取建设养老设施、组织养老服务人员、提供五保老人救助等措施,才有可能实现农村养老保障。
农业公司一般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公司,在数字农业中指农业数字服务平台,但因为农业数字服务很多都与机械和设备紧密相关,所以在此简称为“农业公司”。农业公司是与数字农业相关的数据搜集和处理、算法应用和信号传输等软硬件基础设施的运营主体。数字农业技术的最初工具是地理信息系统,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智能化应用的发展,数字农业技术已经远远超出农业生产的范围,扩大到农业运营的整个链条。我国数字农业的发展模式是数字生产与网络销售、全国物联并行发展,所以在数字农业的语境下,农业公司包含的范围更大,包括所有与农业有关的公司,比如农业生产公司、农业上游产业公司、农业技术服务公司、农业物流公司、农业销售公司等。
农业公司通过弱化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组织地位,弱化了其保障组织能力。农业公司在数字农业全流程中居于核心地位,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地位受到弱化(38)参见韩庆龄:《从“脱嵌”到“嵌入”:农村电商产业与土地秩序的关系博弈》,《现代经济探讨》2019年第2期。。一是农业公司运营数字化。农业公司掌握数据、算法和端口准入。数字农业系统需要搜集数据的传感器、网络的基础设施、算法的开发、与现有或新进农业生产设备的连接等,必须由专业技术团队来运营。前期的投入与技术的控制给予农业公司获得农业数据的机会,也为它们为其他目的使用这些数据提供可能(39)Se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Precision agriculture in the 21 century:Geospati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crop management”,Washington DC: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1997,pp.108-109.。端口是数字系统的接入权,是农业公司身份控制的手段(40)控制主体性的方法,参见彭树涛、李建强:《从福柯的“治理术”到阿甘本的“原始结构”——生命政治现代性构序的暴力双曲线》,《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二是农业公司通过算法进行决策更具效率和规模性(41)孟山都、嘉吉、先正达和杜邦4家公司在世界农资领域的行业集中度已超过 50%。参见刘丽伟、高中理:《美国发展“智慧农业”促进农业产业链变革的做法及启示》,《经济纵横》2016年第12期。。因为数字农业成本更低、收益更高,农业公司可以通过扩大使用规模来搜集更多数据。在深度学习技术的帮助下,更多数据意味着更科学的算法和更有效率的决策。在这一技术促进效率的循环中,数字农业可以吸收更多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参与,并实现所需的规模性。
农业公司的规模性决定了其具有中心化的特征,受影响的农民范围广泛。虽然农业公司并非一个主体,但在细分领域数字服务平台的中心化是技术趋势。随着农业公司规模的扩大,在一个或多个领域中,中心服务提供者将会越来越集中,正如在移动互联时代商业领域发生的一样。此外,数字农业的效率与垄断使被排除在数字农业之外的农民易受负面影响。数字农业新的投入和协作会更倾向于受信任的农民(用户),使这部分农民更深度地参与并结合在数字农业系统之中。而农业公司通过对用户与非用户的区分,精细地控制接入权,可以进一步稳定其中心化地位。
四、数字转型中农民保障的制度创新
人民公社对农村进行公有化改造,是我国集体经济的基础,而农民保障是公有化改造的制度承诺。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但城乡二元社会尚未取得实质改变,维护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更需要坚持和完善农民保障制度。数字农业有利于提高农业的总体效率,有利于改善供求关系,但因为在技术转型中土地在农业生产中的基础性发生了改变,经验知识为数字知识所替代,农业公司也成为中心化的基本生产组织,传统农民保障制度逻辑被打破。所以,应适应新的技术条件,创新数字农业条件下的农民保障制度。
(一)在数据形成过程中为农民设定保障
数据为农民提供保障具有可能性。生活保障是最基本的保障,主要包含居住权、获得食物和其他最基本生活物资的权利。为农民提供保障的物质基础应当具有人身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三个特点。我国城市社会保障通过国家信用提供稳定性与持续性,而传统农村社会保障是通过土地实现这一目的。数据与土地一并成为数字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意味着数据如同土地一样可以提供保障,其收益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也可以人身化。
法律上确认农民对数据的所有权无法解决农民保护的问题(42)See James R.Walter,“A brand new harvest:Issues regarding precision agriculture data ownership and control”,Drake J.Agric.L.,Vol.2,1977,pp.431,440.。一是农业数据不一定受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条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但是,农业数据很多是生产数据、地理信息,这些数据不属于“与自然人有关”的信息。二是农业数据保护的现有方案可追责性差。世界上现有农业数据保护方案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保证获得数据的企业或个人不会不适当地使用或披露数据;必须合理地、最低限度地使用和披露数据;必须制定和执行数据访问程序;必须为保证被披露的其他人也制定保障措施(43)See Jacob Strobel,“Agriculture precision farming:Who owns the property of information:Is it the farmer,the company who helps consults the farmer on how to use the information best,of the mechanical company who built the technology itself”,Drakej.Agric.L.,Vol.19,2014,pp.239,252-253.。而现有农业数据的保护方案缺乏责任与监督机制。三是在某种程度上以传统形式保护农业数据事实上不可能。数据与有形财产存在重大差异,甚至与知识产权也存在很大不同,数据的复制、传输与使用都可以以隐匿的方式进行。数据通过算法做出决策,回溯与追查都极为困难。
综上,只有在数据形成的过程中为农民设定保障,才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即农民应当在农业数据采集(包括传感器的安装和持续使用、带有传感器的机械的使用等)的过程中获得收益。这种方式更为直观,农民和农民集体更容易掌握,并且难以受到信息差的影响。农业数据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可以作为保障的数据主要有农业土地数据(不管由国家、农业公司或农民个人提供)、农业生产数据(不管是由农业机械自动上传还是由农民上传)、农产品数据。农业土地在制度上具有对农民保障的功能,土地数据在新技术条件下也应当承担这部分功能。而生产数据在传统上本由农民掌握,由于传感器的普及,使生产数据由农业公司掌握成为可能,但为了保护农民传统上的知识地位,生产数据也应当成为农民保障的基础数据。农产品数据是农业生产的衍生数据,很多属于农业公司的商业数据,但因为其与前两项数据存在密切联系,也可以成为农民保障的部分基础。
农业数据的提供者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农业公司、农民个人。比如地理信息主要由地理信息系统提供,而可以为农民提供保障的数据则主要是农民提供的数据和农业公司通过在农民土地上安装和使用传感器或通过农民安装的传感器等收集的数据。
经验上,对数据保护通常是通过保密协议实现的。保密协议是一种信息被披露方向披露方承诺不向第三方泄露信息的协议,它广泛地应用在各种重要市场交易之中,特别是技术类交易和股份类交易。农业数据保护也可以通过保密协议实现。比如美国农业机械数据采集协议由 John Deere和HarvestMax等公司提供,协议内容主要包括保密信息的内容、保密手段、保密期限、保密人员等。但是,在我国仅以保密协议难以实现对数据的有效保护。一是,违反保密协议的证明非常困难,特别是在智能技术应用的时代。借助算法,公司可能没必要为了利用保密数据而披露保密数据(44)See David V.Radack,“Understanding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s”,J.Of Minerals,Vol.46,No.5,1994,p.68.,只需要向第三方开放数据库。受害方有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受到的损害是由数据泄露导致的。二是,保密信息的除外条款有时会成为数据泄露的漏洞,比如平行开发或获取条款。三是,农民或其他披露方法律经验不足。农民没有经验也没有经济实力去获取专业的法律服务。在受到侵害时,农民也没有意识和能力采取有效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动。所以,在我国可以在保密协议之外签订数据采集协议,约定农业公司一次性或周期性地向农民支付数据搜集费用,以平衡农民可能受到的损害。
为实现数据保障的功能,还应当采取一定行政措施。比如制定农业公司相关协议的指导版本,明确农业公司在进行数据采集行为中的告知义务和说明义务,将部分重要农业数据(比如粮食生产细节数据)纳入监管范围等。
(二)特定农业公司股权中应设农民集体特留份
农业数据形成过程中的收益多数不具有持续性。它只能部分解决农民保障的问题,并不能解决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被边缘化的问题,农民很难享受既有土地权益的发展权益。将数据视为财产,使农业公司一次性买断数据采集权的保护结构不能完全实现农民保障的目标。因为借此提供的权益不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并且在授权过程中,农业公司很容易凭借谈判优势地位侵害农民权益。
负责任创新要求农业公司不但要承担一定的创新风险,还要在创新过程中考虑技术的社会道德因素(45)See Richard Owen,et al.,“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From science in society to science for society,with society”,Sci.Publ.Pol.,Vol.39,No.6,2012,pp.751-760.。因为在创新中,大量投资人与管理人并不参与创新与运营的整个过程,非追溯式的责任方式远远不能控制其追求短期利益的冲动。互联网公司通过扩张、融资、上市的方式为管理人和前期投资人创造大量财富,而短期利益使管理人容易忽视创新的社会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数字社会创新很多处于传统法治难以规范的领域,更容易滋生对社会产生负面效果的行为。农业公司创新与发展要避免互联网公司的不良发展模式。
为农业公司设置保障责任存在合理基础。一是农业公司是保护、使用和收益数据的最优主体。农民向数字农业系统提供的数据,对数字农业发展起到基础性作用。本质上说,农民与农业公司在共同生产知识。然而,在此过程中,农民普遍缺乏保护意识,国家保障机制不完善、执行成本高导致农业公司与其他主体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46)参见王海燕等:《农村电商平台交易信息不对称困境及规避对策研究》,《情报科学》2020年第11期。,只有让农业公司承担责任才能实现数据的有效保护、使用和收益。二是农业公司享受了垄断利益。农业公司从农民提供的数据中提炼出来的知识不可逆地替代了经验知识。因为数据化的知识更精确、可复制、中心化、资本化,用农业数据替代农民的知识,部分实现了“知识锁定”(knowledge lock-in),本质是一种资本积累策略,即用资本换取不可替代的资源以实现垄断。这种垄断对数字农业技术的发展是有利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数字农业要求数据标准化、规模化,只有这样算法才能够通过数据训练提高科学性,从而增进整体效率。三是农业公司享受了道德补贴(47)学术研究的道德倾向性,参见汪旭晖等:《数字农业模式创新研究——基于网易味央猪的案例》,《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8期。。农业公司通过知识治理实现农民社会身份转变,从而固化技术治理。经过宣传、信任、知识生产、知识锁定、知识治理、身份化、治理固化的过程,农业公司通过话语转换将农民变为数字农业的道德主体,即不参与数字农业就是阻碍农业现代化。这有效降低了证成数字农业优越性的成本,也使大量数字农业得到了政府的政策支持(48)参见龙江、靳永辉:《我国智慧农业发展态势、问题与战略对策》,《经济体制改革》2018年第3期。。
农业公司承担农民保障责任的方式有多种,但不能影响其市场主体地位。农业公司向农民承担保障责任应主要以股权的形式实现,以保证其持续性和发展性,这包括发行股权特留份、与合作社合股等。将特定股权保留给农民或为农民成立的基金等有成熟的参考模式,世界大多数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日本、印度、新加坡等都对外商投资在电信、资源、金融和农业等领域设有一定限制,其理论基础有一部分就是对本土主体的保护。农业公司股权中设定一定比例用于保障农民利益与外商投资限制在机制上存在相似性,只不过前者是通过提供可持续收益的方式实现这种保护。合股的形式也比较成熟,比如政府主导、商农合办、工农联办等(49)参见蒋璐闻、梅燕:《典型发达国家智慧农业发展模式对我国的启示》,《经济体制改革》2018年第5期。,只是要将农民保障特留份明确在土地、资金和劳动力投资股权之外。股权特留份可以由农民个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基金会持有,为不影响农业公司创新发展,一般不享有投票权,不参与公司的运营与管理。
农业公司承担农民保障责任的主客体选定应当制定一定规则。农业公司承担农民保障责任的基础是垄断地位,即农业公司通过排除农民选择的方法弱化了土地保障作用,所以只有达到一定标准的农业公司才应当承担为农民提供保障的法律义务。这一标准的设定可以参考数字平台依据用户数量、资本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等分类。接受保障的农民应当是作为保障基础的农业数据的利益享有者,包括农业土地数据基础土地的承包权人、农业生产数据的传感器所有人、管理人、数据上传人、基础农产品数据的生产者等。
(三)农业公司应承担本地用工义务
进城务工已经部分实现了农民劳动机会保障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已经深刻冲击了改革开放初期构建的农民保障制度。一是宅基地的生活保障功能越来越趋近居住保障,而农民生活的其他方面越来越多地由进城务工的收入承担,为新农村建设、农业建设用地开发、城镇化提供了可能性。二是农业经营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例减少,给农业生产规模化提供了机会。更多农民可以脱离农业土地,获得更大地理发展空间,从而获得更高收入成为可能。三是农民收入的提高和自我保障能力的增强,为我国建立更完善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可贵的窗口期。
但是,目前农民的劳动机会还是受到一些限制。城乡二元机制中,农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还不能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保障,所以一些育儿、患病、年长、抚养老人的农民需要留乡返乡就业。虽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为留乡返乡农民提供承包土地,但由于有些农民已经将承包土地流转,劳动机会事实上还是难以实现。
数字农业中,农民会进一步丧失保障性劳动机会。农业数字化使农民逐步退出农业决策过程,而自动化和智能化使大量原本复杂的非标准化农业劳动变得可以替代(50)日本智慧农业相关技术发展情况,参见马红坤等:《小农生产条件下智慧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基于中日两国的比较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12期。。农业劳动需要参与的人力更少。美国农场工人的比例已经从1950年占劳动力总量的9.93%下降到2000年的3.19%,减少近三分之二(51)Se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https://www.ers.usda.gov/topics/farm-economy/farm-labor/.。此外,数字农业使农业劳动更需要技术工人而非农民(52)参见方向明、李姣媛:《精准农业:发展效益、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11期。。在这种条件下,更多的农民会由于身体健康、缺少技术等原因而无法获得劳动机会。
数字农业将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劳动机会分配。农业生产和销售链的中心化使农业整体协作中心化,所以农业劳动机会将在全社会按市场分配,这与小农经济按土地分配劳动力的模式存在很大不同。数字农业有时在物流、销售、二次加工等环节的劳动力分配与生产环节劳动力分配同等重要,并且前者的劳动与土地的关联性远不如农业生产本身强。所以,本地用工是在数字农业转型中极为重要的举措。本地用工是指农业公司在数据来源集体所在地开放一定数量以上的劳动岗位,承担按一定比例在集体成员中用工的义务。岗位数额可以设定在10人或以上,比例以20%—40%为宜。本地用工义务应当是法定义务,用工主体是农业公司。
保护本土劳动者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比如新西兰用人单位“必须在合适的新西兰人可能会申请的全国性招聘网站或频道上刊登至少两周的招聘信息,并满足其他广告要求。广告宣传必须在您提交申请前的90天内进行。如果工作符合以下条件,则无须提供广告宣传证据:工资至少是新西兰工资中位数的两倍,或属于绿名单上的职业”(53)Apply for employer accreditation,New Zealand Immigration (Oct.12,2023),https://www.immigration.govt.nz/employ-migrants/new-employer-accreditation-and-work-visa/steps-to-hiring-migrants-on-the-aewv.。很多国家并没有明确的本土用工优先或按比例用工的规范要求,因为这可能引发对劳动权不平等的质疑,但多数国家都会通过工作签证的限制来保护本土劳动者,比如美国2023年H-2B非移民工作签证有64 716份(54)Temporary Increase in H-2B Nonimmigrant Visas for FY 2023,U.S.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Oct.12,2023),https://www.uscis.gov/working-in-the-united-states/temporary-workers/h-2b-non-agricultural-workers/temporary-increase-in-h-2b-nonimmigrant-visas-for-fy-2023#:~:text=On%20Dec.%2015%2C%202022%2C%20the%20Department%20of%20Homeland,64%2C716%20additional%20visas%20for%20all%20of%20%28FY%29%202023.。少数国家会直接通过限制外国劳动者的比例来保障本土劳动者,比如泰国规定用人单位每使用1名外国劳动者就必须雇佣至少4名本土劳动者(55)Several incentives approved to attract long-staying foreign investors,wealthy foreigners,Thai PBS (Sep.14,2021),https://www.thaipbsworld.com/several-incentives-approved-to-attract-long-staying-foreign-investors-wealthy-foreigners/.。
保护本土劳动者与本地用工有相似之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有助于社会发展,但同时也会形成劳动市场的弱势区域。弱势区域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地区。比如对于移民目标国来说,大部分的低端工作需要保护,否则移民将会挤压弱势群体的工作机会。在一国境内,特定条件下劳动力流动也会引发这种问题。比如农民原本可以依靠土地承包经营来获得劳动机会,而农业数字化后,保障性的劳动机会则转变为固定收益(租金),而固定收益随着通货膨胀越来越难以维持其保障功能,并且本地农民在竞争中又不一定可以获得市场化的劳动机会。
本地用工义务的设定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一,作为原有保障基础的土地资源具有本地性。由于技术条件的发展,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型资源替代了土地,土地的保障性受到削弱。在数字农业推广普及中,农业公司很容易完成从数据控制到知识替代再到身份固化的过程,但是直接通过新型资源进行保障会遇到很大困难。所以,在制度上规定劳动机会的本地属性具有现实必要性。其二,农业公司在取得知识优势和身份优势后,本地用工是其应承担的替代性保障义务。农业公司利用技术优势消解了我国原本为农民设定的保障性利益,虽然技术优势本身并不具有负面性,但它使农业公司与农民之间形成了主体上的不平衡,制度应当对此做出回应。这种回应在劳动法、反垄断法等的形成中已经获得了正当性的证成。其三,农业公司不会面临股权特留份面临的制度干预风险。事实上,股权保留会使农业公司面临一些管理和财务上的困难和成本,所以只有部分农业公司需要承担这种责任。而本地用工在多数情况下不会增加农业公司的用工成本。农业公司本地用工本身就有利于降低成本,新增的义务并不违背市场规律。并且,本地用工是按比例用工,并没有剥夺农业公司的用工自主性。其四,本地用工有利于维护我国集体经济制度。集体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农业的产业中心化、运营市场化对原有的集体经济制度造成了冲击。本地用工对于稳定农业保障、重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