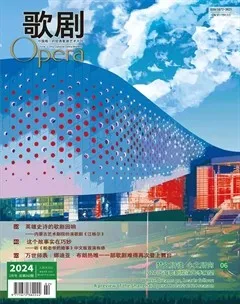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2024-04-06陈姝婧张建国
陈姝婧 张建国

《幸福的煙火》是由中共三明市委宣传部、三明市文化与旅游局、中共沙县区委共同打造,由三明市歌舞剧院和上海歌剧院联袂推出的原创音乐剧舞台作品。这是一部视听效果和时代鲜度兼顾得不错的新作,既有艺术性也不乏思想性。故事围绕沙县小吃跨时空产业发展中人们生存、生计、生活的现实经历,通过聚焦沙县小吃从业者群体的小人物之常情、常理、常态的命运际遇,引发人们省思人生命题。我们在面对永远存在变量的生活方式、生存境况、社会现实的时候,究竟要如何妥善、及时地安放好我们内心深处那份玉壶冰心的生命情感?显然,本剧主创团队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虽距演出观摩已有颇多时日,杂感良多,然略一回味,难抑笔者对此剧的溢美之冲动。
(一)
沈亮导演对全剧的把握,显得轻松有余。这一点不在于如何体现出她对文本基础上的开拓性和创造性,而是在条件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几乎并不影响她对这个剧目体裁在舞台整体艺术呈现上格调水准的发挥与拿捏,这便是实力。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这一点已经是真心难得。沈亮执导的这部剧目有一种令人不可名状的感染力。她的艺术创构和别具匠心,在条件极为欠缺的情况下,丝毫不减地惊艳到了大家。从客观上说,出品方三明歌舞剧院是个地市级的艺术生产单位,无论是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还是综合实力都难以和一线城市同日而语,还存在演出场所的局限、舞台软硬件的缺乏、台前幕后行动力的短板等现实问题,会直接对演出质量造成不可避免的影响。然而,《幸福的烟火》在沈亮主导的主创团队的精诚协作下,献给观众的是一席视听艺术盛宴,故事跌宕起伏,演出精彩不断。临场之下,谁也不会觉得这是在“将就”环境中进行的“攻坚克难”。比如,剧中男主林茂生与妻子吴慧珍的几次对话,需要妥善处理空间上的转换和交代场景上的阴阳相隔关系。没有旋转舞台,沈亮就充分加强演员和灯光的舞台调度,呈现出的效果令人看得明白,故事理得清楚,一点不影响观众从视觉逻辑上的理解。可以说,沈导在全剧的二度创作上,故事展开的主辅线与人物关系条理性分明,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至于还需不需要进行提升修改的问题,正如沈亮导演自己所说的那句话,“主要在于对标”。“对标”?说实话,乍听起来略有“不接受反驳”的味道。但是也说明了,沈亮对剧目打造是面对市场还是面对评委,是面对领导还是面对百姓,她心中有——且实实在在地有那杆秤。笔者窃以为有这杆秤的导演一定会是个好导演。

一部戏给人以极尽奢华的视听感受,往往是容易的。相比之,艺术品相留给人以极尽匠心的冲击力,则显得尤为难得。要特别指出的是,《幸福的烟火》不仅体现出艺术家团队的敬业品质,同时也体现了出品方以及当地主管部门的精明能干。远离“人傻钱多”“盲目高大上”,耻于“假大空”“面子工程”,鄙视“乱作为”“瞎作为”,旗帜鲜明标榜“真善美”——让纳税人的每一分钱花得其所啊!此处,理应获得掌声。
(二)
《幸福的烟火》编剧杨硕有着很好的题材敏锐性,直面现实的时空事物,对城镇化、现代化、城市化等带来的新旧分歧与老少隔阂等乡村振兴战略上难以避免的社情民意,能较好地以诗性的笔触书写人们对守护精神家园的本真愿望,既有同情又存有光明。
首先剧目名称是笔者很是喜欢的。“烟火”一词在中国人心中有种特别的共情基础、价值认同、亲切感、厚重感。烟火,它是关乎宗亲的、族类的、文化的,甚至是关乎灵魂的。它是传统的也是经久弥新的。农耕时代“烟火”是必需的,工业时代它也是不可少的;数字时代它需要被重新重视,智能时代它仍然为时不过,而且更需要激活它的温度。正如该剧作者想表达的那样,无论智能时代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节奏,我们始终是以家为单元的人——对于中国人而言,家园就是情感安放的栖所。
大方向大气磅礴,有现实性又不乏思想性。这是笔者对杨硕的故事创构最为欣赏的地方。当然,也不是说除此之外就是完美的。比如对于如何表述城乡之间条件悬殊的心理认知问题,至少在价值立场和措辞上应谨慎视之,应体现出知识分子、艺术家们以化解社会矛盾倡导优秀价值观为己任的神圣使命。举个例子,剧中人物香奈儿的登场,笔者个人认为过于概念化,多少有些生硬。笔者能理解作者意愿是好的,是对现实反映的深刻性体现。但作为文艺的塑造对象,好的切入点便能带来好的共鸣和良性反思。歌剧《茶花女》《波希米亚人》等核心人物从社会价值观上看都挺“负面”的,但戏剧效果上却并不会令人“不适”,便是这个道理。

杨硕的台本文辞才情有余,唱段的文字结构很具备音乐的曲式结构性,显见作者在这方面的得心应手。杨硕对韵脚的使用较为严谨,长短句的穿插安排平衡感不错,音律感把握也很稳,“这个剧本很音乐剧”这是笔者在观摩中特别强烈的印象。一个剧目一个团队,成员之间相向而行彼此多走近一点就有不一样的艺术成色产生。目前唱段的抒情性做得都很足,笔者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在于抒情性之外,对叙事性、谐谑性、悲情性以及哲理性等方面的音乐形象对比空间幅度较小较平,略有单一之嫌,特别是唱段之间在全剧的整体规划上偏“单曲”并联,缺戏剧表现一体性,有点像“话剧式对白”加“歌曲连唱”而使得音乐戏剧性动力性不足。由于现场观摩来不及推敲,不确定是音乐还是本子上的问题。音乐剧除了剧本故事本身的巧思妙构外,一个重点是要在音乐本体唱段、乐段艺术形象的精心设计上,另一个就是舞段的重点打磨上。一旦可看性、记忆点得以落实,这个剧目的市场价值就有了质量保证,剧目就能够走得更远。
本剧的角色安排和舞台表演方面游刃有余,轴心性的人物关系预设建议进一步推演确定。沙县小吃是一个企业脉系极其发达的商业现象,也是一种中国大地上事业发展较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讲好这个故事很不容易,但是有着很可观的现实意义。剧作家愿意倾力在这个着眼点上下功夫,其用意是难能可贵的。其难在于,要把某种程度上已然与现代城市节奏存在一定违和感的“烟火”阐释到“幸福”层面的人生哲学高度,并能充分博得在场观众的认同和共鸣,这是本剧最难为且又最必须倾注的无形笔墨,很考验剧作家的情理架构智慧和情节安排匠心。

吴慧珍作为林茂生的妻子,勤劳贤惠,最后积劳成疾,是舞台上虚化空间的登场人物,也是目前故事中父子冲突关系的节点性人物。儿子不能够原谅父亲的偏执心理和父亲对儿子的爱不得偿,都是源于母亲的阴阳相隔。女一号演员扮相好,造型上可以不那么唯美、阳光,或可以增强一些稍显孱弱又不缺其精明干练的气质。在故事演绎的调度处理上,夫妻之间阴阳虚实的对话形式以及舞台情境呈现重复得可能多了些。但所有这些都调节到理想状态的话,笔者还是认为,吴慧珍作为一号人物感觉欠缺了分量和必要性。一个不成熟的建议是能否将儿子林夏至作为一号,会不会更契合“烟火”的主题性。林夏至有留守家乡孤独艰辛的童年,有青春期缺乏陪伴落寞危险的少年,有对母亲阴阳相隔而在灵魂深处埋藏的锥痛点,更有对父亲及其生活变故导致的新动向的抵触与排斥。更重要的是作为新时代年轻人对家为轴心的“烟火”情怀的觉醒,对“烟火”对家庭回归的认同等等,倘若将林夏至作为核心性人物,这些着眼点都有助于盘活整个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互动。
陈秀珠形神内外都较为准确,适当地在故事中安排她在林家店铺的生活存在,既有助于林茂生情感正面性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有助于增强父子矛盾与和解的真实性、复杂性以及深刻性的具体推动落实。目前的呈现,她和父子间必要的关系没形成充分的或者说较为令人感动且信服的作用力。林夏至是个富有时代气息的小伙子。他对父亲、父亲与陈秀珠乃至对烟火气的沙县小吃等问题,有一个误解到和解的过程,本质上是受教育而后逐渐成熟起来的过程,韩笑笑只是给林夏至的转变提供个契机而已。核心五个人物的合理归位,是直接决定本剧目戏剧表现高度的内在因素,值得好好审视。音乐剧亦俗亦雅,打磨得好,前路无限,戏会也就会走得远。
(三)
卢荣昱的唱段设计,让我们看到中国演员以母语歌唱的优势。本剧中,几乎所有的唱段、旋律和台词的交融度处理都相当好,凸显了通俗音乐语感的共性特征,充分体现了作曲家对语言音乐性的优秀驾驭能力。笔者一直呼吁中国作曲家对汉语音乐性的重视,甚至倡导“语言大于音乐”的作曲理念,这也是笔者深耕于传统唱腔“依字行腔”谚诀深度教学实践中略有所得的。中西语言差异的本质,是语调语义性和音节语义性的不同,这是东西方文化基因中的差异,一定不可漠然视之。
还有,本剧在配器方面的基础性呈现都较为均衡协和。基于“沙县小吃”这一故事题材,笔者有一个较为不成熟的建议:是否能让音乐在个性值上做加法?比如,以锅碗瓢盆碰撞声的原声提取、顾客用餐声响的艺术形象加工,以及城市喧嚣的建筑工地声、乡村乡野的自然环境声等的音乐化处理贯穿铺垫,并在整体的布局和着色上有意识、有目的性地融合到剧情的展开之中。

舞蹈对于音乐剧本体而言,分量不可小觑。目前舞段的进出、虚实、渲染等,从呈现来说,就像一幅刚处于打底色阶段的大开面画作,虽面面俱到,但深入的艺术表达尚有些欠火候。笔者期待,其中的有些舞段更具备可看性、观赏性、艺术性,不要都是那么克制、点缀。因为本剧的人物个性都是可以被放大渲染,无论主要人物还是有不同身份的类型化人物。比如,和面、包饺子、舀汤等职业动作,也可以抽象加工为舞蹈动律的素材点,这些舞蹈都可以撑起舞台场面,甚至可以作为肢体技艺的表现,渲染舞台表演热度。这种个性化的舞蹈处理,做好的话可以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为剧目品相大大加分。
《幸福的烟火》全剧在嗓音艺术形象塑造方面,总体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上海歌剧院、三明歌舞剧院的独唱演员都有扎实而科学的发声技巧,而且看得出都有一定的舞台经验,演绎“轻量级”的音乐剧可谓驾轻就熟。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洋”唱法在身的演员们,并未陷入“声音规模”“声音规格”的窠臼之中。当然,从音乐剧的角度来看,特别是中国音乐剧的角度,笔者认为语气的变化和强调,在人物声音和形体造型等方面,还有磨合空间;声音造型中的情感渲染有待进一步加强,声线收放的铺排也值得进一步平衡。目前的舞台呈现,在人物的自我定位上还缺乏一些小细节。人物会因为交流產生身份的自我确认,随物赋形地形成自我塑造。比如交流对象的不同,语气、语调一定是不一样的。现在人物在舞台上,某种程度上来说缺乏更深层面的塑造和升华。

“烟火气”是一种幸福。它关乎中国社会特色的生命情感、人生哲理和文化传统的接续,指向以家为枢纽的中国社会特性。唤醒烟火气的价值认同,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种失而复得的共情点。烟火,在笔者看来,或许是本剧最为核心的艺术书写对象,是普适的,是新时代下值得打造的一个很有内涵的文化热点。音乐剧《幸福的烟火》,一方面是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增强文化自信的作用。这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