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亮人生的常识,向何处寻
2024-04-02王梓霖
王梓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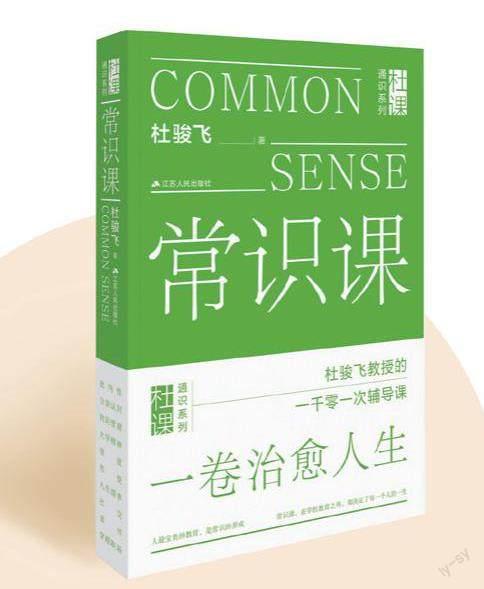
杜骏飞
南京大学二级教授,传播学者,社会教育工作者。“杜课”“杜课堂”创办人。长期致力于面向社会的人文教育,已通过个人公众号“杜课”、抖音号“杜骏飞”与视频号“杜课书院”等推出一千多期在线公益教育课程。著有《常识课》《数字交往论》《弥漫的传播》《花山集》等。
2016年的冬天,南京大学教授杜骏飞决定在网上开办一个特别的公益课程,几天后,微信公众号“杜课”由此诞生。从教以来,在专业课教学之外,他还会给自己加点码,或是下课后留在教室里答疑解惑,或是和学生一同用餐接受他们的访谈。那些时常出现的迷茫与困惑使他意识到,学校教育中忽略的某些议题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时至今日,杜骏飞已经实现了在“杜课”上更新“一千零一次人文课”的目标。在新著《常识课》中,他选择了其中最接近“基本常识”的90篇文章,通过较为感性的事例、多变的文体,呈现出那些锱铢积累的对话,那些文字“确曾在夜雾中點亮过微茫的灯,也曾指点过遥远的行路人”。
教人成己者,善之善者也
《教育家》:当前整个社会中存在激烈的“教育内卷”,而您在书中多次提到学业对于人生的影响并没有那么重要。您认为我国的教育面临哪些困境?
杜骏飞:任何一种教育体系都有其优缺点,我们采用某种体系主要考虑的是其合理性。中国是一个地域宽广、历史悠久的大国,基础教育的任务繁重、管理压力大,必然需要通过实施某种大一统的、规范化的、强调均值的教育模式,促成更多个体共同提升。而这几乎必然带来重规范、重知识的义务教育,如今的教育困境也由此而来。
比如过于强调规范,导致个体的齐一化,出现均值高、方差低的问题。我们对孩子学科知识的培养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对特殊人才的培育,以及对天性发展的重视、意志品质的培养远远不够。从零到一的创新长期稀缺,大量青少年陷入抑郁,这些与他们早年接受刻板化的教育、个性受到遮蔽有关。又如在标准化的衡量尺度之下,只能看到个体的“切片”。我们一直习惯采用单一的教育评价来培养人、评判人,这看上去很公允,实则很偷懒、很将就,甚至可以说很不负责。从小到大,很多孩子无论是接受外部考评还是进行自我考评,都习惯了将分数作为唯一准绳,升入大学后还延续着中学的习惯,仍一味地追求分数和成绩。而一旦脱离了考试环境、走入社会,突然感到自己不会生活,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人生该走向何处,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性危机。精致利己主义或优绩主义这类社会病症的出现也与他们此前接受的教育有着一定关联。
学业对于人生的影响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在未来的人生中,大部分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非知识的底层能力,拥有相应能力的个体在人生的所有年龄段、所有事情上都能焕发活力。而一个高分低能、只会背书不会思考、只听从指令缺少自由思想的人,则有可能陷入抑郁情绪,甚至出现反社会人格,这不是很糟糕吗?我曾写过一句话:“教人成人者,固教之善者;教人成己者,善之善者也。”将个体培养成才固然不错,但使其成为他自己更了不起。对教育个性化的重视应不亚于规范性。
《教育家》:基于您从教37年的接触与观察,陷入类似困境的学生多吗?经过四年的大学教育,他们产生了什么转变?是否找到了自我、明确了主我?
杜骏飞:大部分学生有过类似的困境。经过大学的缓冲和沉淀后,不少人确实有所恢复,而有的则始终处于半抑郁、封闭且紧张的状态。中小学教育的确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成长症候群,影响了他们的性格、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和社会的认识。进入高等教育阶段,仍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延续常见的满堂灌式教学,给学生们评优评奖时也一律采取“学术路线”,不太关心他们的心理成长,更不去治愈他们的内心。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曾发表两位青年人的信件《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信件讲述了80年代中国青年人的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共鸣与广泛讨论,被称为“潘晓之问”。前段时间有两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找到我,告诉我他们和潘晓一样迷茫,交流中他们一度情之所至,湿了眼眶。我不知道以他们为代表的那些学生以后成长得怎么样,当他们走向社会、走进人海,很多人被时代的浪潮所吞没,我再也没能看见他们的踪影。只是在我能看到的人中,我发现他们有过症候、内心备受煎熬,带着许多疑问走向新的世界、新的社会。我当然相信我们的教育曾给他们带来许多成长,但这些成长或许主要集中在知识层面,而他们的挣扎则体现在心灵层面。考虑到这个因素,我觉得教育的另一重要困境就在于此。
《教育家》:与过去相比,现在青年人的某些问题是否更为突出?这种心灵上的困境相较以往是否有所加深?
杜骏飞:每一代青年都是不同的,但令我惊讶的是某些问题始终存在,特别是一如既往地欠缺自我认知、自我发展的能力。当年的“潘晓之问”主要讨论个人与集体、自我与社会的问题,今天很多青年问题依然类似。并且,很多问题似乎愈演愈烈了——青年人的抑郁40年前有之,今天亦有之,只是40年前那些已经使人产生眩晕感和抑郁感的问题在今天看起来更明显。原生家庭对子女的伤害似乎比以前更大,简单粗暴的审视和考评给孩子造成的压迫似乎更强,全社会对知识有用性的讨论好像又出现了一次新的反复。20世纪90年代盛行过一句话“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今天这个历史的故事似乎又“押韵”了。很多正在求职或刚走上岗位的青年突然发现,过去20年左右的学习原来是一场空。他们的那种痛苦和困惑是真实的、深刻的,所以他们愁云满面甚至泣不成声。他们想去问些什么:为什么满腹“知识”,迈向社会后却觉得一无所用?我想,那代表着一种时代的追问。
人最宝贵的教育,是常识的养成
《教育家》:在现今高度专业化的教育体系中,您如何定义“常识教育”?其价值与意义何在?
杜骏飞:社会需要形形色色的人才,但理想的人才有大致相似的轮廓:知识丰富、身心健康、思维活跃、拥有个性,有着正确而坚定的政治立场。我曾在书中写道:“人最宝贵的教育,是常识的养成。常识课,在学校教育之外,却决定了每一个人的一生。”
根据一些教育史学的研究,我们主要学习的是苏联以及普鲁士的教育体制,强调规范度、整一度、纪律性,因此也遮蔽了一些比较普适的教育精神,比如自由开放的教育、强调个性的教育、心灵成长的有教无类。学校教育即便不能完全做到这些,至少也该提供一种可能,不以单一的标准去要求学生们。记得我的儿子在小学时写过一篇“我的同桌”主题作文,他写的是“我的同桌有两个缺点……”语文老师打了个不及格。孩子向老师问起原因得到的回答是:“大家都在表扬同桌,你怎么能批评呢?”孩子回来问我能不能那样写。我的回答是:“如果老师是在做思想工作,那他说得对,他希望你能与人为善。如果站在写作者的角度,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真诚地表达内心的想法。”作为家长,我时常要保持这样的对抗,使他能够养成一个相对理性的视角、健康的心灵,实现个性化的成长,否则长此以往,一提到“爱”他可能写的就是感恩父母、热爱祖国,一写“同桌”就是思想好、身体好,一写“未来”就是社论中的口号。且不谈真诚与否,至少这样的孩子缺少了些创造性。这类现象并非个例,经过不适宜的培养,很多学生最终失去了才华,他们的思维曾被伤害,个性曾被湮没,渴求曾被忽略,甚至无从幻想自己的人生。
在反思教育文化的基础上,我想还是要力所能及地做些改变,尽可能对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文化做些调整。如果不从观念上加以调整,机制上大概也没办法更开放。如果说中国有十件大事要谈,教育文化的改良一定是其中之一。我的建议是,不妨寻求那些能够驾驭、审视和改善知识的能力,如感知、想象、统合、批判、辨识、抽象、同理心等,我将这些统称为常识教育。在课上,我的常识教育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价值观,比如爱国爱民、关心他人、追求真理等;二是元能力,比如创造力、沟通力、协作力、批判性思维等;三是类似于大学里的通识教育, 包括专业适应能力、人文与科学的学习能力。这些需要从小建构的常识积累是他们人生中最可倚仗的基础。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教育家》:高等教育属于学校教育的末端,您一直在高校从教,在教学中看到了很多因常识教育缺失而造成的心灵的苦闷、人生的迷茫,这应该引起基础教育阶段教师什么样的警觉?
杜骏飞:我只能站在人才流水线的末端,以及此前对基础教育的观察,去推测我的学生们在中小学里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整体而言,教师们认真严谨、不遗余力,孩子们知识丰沛、善于考试。另一方面,很多孩子呈现出群体性的痛苦和困惑,以及元能力、通识能力、核心素养部分的缺失。
与中小学教师面谈时,我最想说的大概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我非常能理解你们的不容易,如果是我,可能不会比你们中的一些人做得更好。”中小学教师可能是这个社会中最累的一群人,除了教书育人还要承担各类其他事务,有些教师自己活得就很煎熬,整天疲于奔命、忍辱负重,甚至夜不能寐、心力交瘁。在标准化的、高升学率的要求下,他们不得不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學科教学中,难免忽视常识教育。当然,再往上追问,校长可能也很无奈,据我所知,一些教育局长其实有苦难言,在大胆推行教育改革时遭遇过不少家长的质疑。
教育工作中确实存在无奈的现实,但一个知道何为“对错”而做错的人,和一个不知何为“对错”而做错的人有着重大差别。所以我想和教师们说的第二句话是:“我们得清楚正确的航向,思考教育的真正使命。”作为教育者,一旦我们认同某些道理,就有做些什么的可能。所谓的谆谆教诲、以人为本、和蔼可亲都是修辞,真正重要的是具备教育家的灵魂,关心孩子的灵魂,减少模板化的要求,尽力促成他们的生长,哪怕只有一点点。就像孟子所言“尽心焉耳矣”,尽力了就好。可以时常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为孩子的问题思考过,是否与之共情,说了该说的话、做了该做的事。
《教育家》:您认为学校教育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应塑造什么样的人?
杜骏飞:我尊重学校的所有工作,这些年来的教育成就大家有目共睹,教育者的辛勤付出也可见一斑。校长们希望有点成绩无可非议,只是即便从功利性的角度来看,全世界在评判一所学校时普遍认同的标准是看50年内培养了多少杰出校友、多少拔尖人才。校长应该思考“拔尖人才有什么特征”,一定不只是单一的知识能力。校长应该秉承的理念是既培养均值,更培养方差。我们期望学校能够发扬孩子们的天性和天赋,让那些偏才怪才也有成长的机会,促使他们涌现出对良知良能的自主追求。因为这是真正有价值的部分。
从非功利的角度来说,校长要意识到教育不是为了业绩,是为了无数人的人生,而人生是一个丰富的概念。校长就像一艘船的“船长”,全校教师、孩子言行的方向是由你去把握。校长至少要践行两方面使命,一是有政治觉悟,忠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二是有教育觉悟,一切为了培养鲜活的人。若能意识到自己挑着这两副担子,校长就更应该体悟自己工作的神圣性,为了多元、多维的培养责任,必须对学校教师、学校环境、考评体系、课程设置提出以人为本的要求,决不能敷衍了事、缺少关怀。
对于教育者而言,最不幸的事或许是教了一辈子书,取得了一堆荣誉,结果发现自己教出来的学生只会答题考高分,而无法实现自我发展。你会怀疑自己的职业人生,我做得对吗?难道要看着孩子们带着高分和心灵伤害离开学校?会反思什么样的教育会抹杀学生的活力,让他们失去人生的色彩?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以我的理解,古代读书人的读书、教书,都是在建设自己,如今许多教师只希望被考评所承认。我想教育者应该通过关怀社会来建设自己的人生,又通过教育孩子关心未来的社会人。唯有如此,我们才会觉得自己的职业是圆满的,才能拥有自豪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