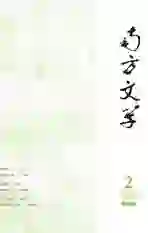沿河街(二题)
2024-03-29陶永喜
陶永喜
男,苗族。湖南省绥宁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民族文学》《芙蓉》《湘江文艺》《湖南文学》《芒种》《黄河》《文学港》《百花园》《当代小说》《儿童小说》《少年文艺》《小溪流》等。有小说入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国际性主题作品选》等多种选本。著有小说集《不知名的鸟》《草把龙》等。
遗 物
清早,沿河街枫树脚的胖嫂突然觉得鼻子痒,打了一个喷嚏。
哈啾——哈啾!接连又打了两个喷嚏后,胖嫂已经坐在床上了。胖嫂的喷嚏把男人臭皮惊醒了,男人臭皮从被窝里翻起身来,忙问:“怎么啦,受凉了?”
胖嫂用右手掌护住眼睛,说:“眼睛疼,火辣辣的。”
窗外晨光熹微。隐约传来公鸡的鸣叫声。臭皮下了床,摁亮电灯,然后给胖嫂披上衣服,他着急地掰开胖嫂的右手:“让我看看——”果然,胖嫂的眼睛红红的。
哈啾!胖嫂又打了一个干喷嚏。臭皮已经找来感冒药,倒上温水,让胖嫂吃药。“我脚冰凉——”胖嫂吃过药,又这样说。臭皮把手伸进被窝一摸,胖嫂的一双脚,果真像冰棍一样冰凉。
“你是受凉了。”臭皮赶紧去烧水给胖嫂烫脚。水还没烧开,胖嫂“哇——”地叫了一声,她想呕吐。她挣扎着要从床上爬起来,却没站稳,重重地摔在地板上。臭皮闻声跑过去扶,无奈身子骨太瘦弱,无法搀扶起厚重的胖嫂。
“你走来晃去,我脑壳晕——”胖嫂死死抓住臭皮不让他动。臭皮只得焦急地紧紧抱住胖嫂。胖嫂开始接二连三打喷嚏。打着喷嚏的胖嫂猛然又叫喊起来:“地震了,房子塌啦,砖头从我身上滚过去了啦,钢筋扎进我的心尖尖啦——”她说她听到了轰隆轰隆的房子倒塌的响声。臭皮说:“房子好好的,也没有地震。”被男人臭皮抱在怀里的胖嫂破口大骂:“你就是个聋子傻子!”
又哭又闹的胖嫂觉得胃在翻腾,吐出了刚刚吃下的药,吐出了昨晚没完全消化的饭菜,开始呕清水,呕完了清水,呕黄黄的苦胆水,呕完了苦胆水,没有什么呕了,又大声干咳,咳得眼泪水直流。男人搂着胖嫂,手脚无措干着急,像个做错事的孩子陪着胖嫂流泪。
胖嫂咬牙踉跄着站起来。臭皮使尽力气将胖嫂搀上了床。胖嫂脸色寡白,开始无法控制地在床上滚来滚去。臭皮伸手过来想替她揉揉身上。胖嫂口里尖叫着大喊:“不要碰我啊!我要死啦,我痛啊……”后来,胖嫂嗓子叫哑了喊不动了,开始咬枕头,咬床单,汗水湿透了全身。
“去医院看看……”折腾了一阵后,见胖嫂慢慢安静下来,男人臭皮仿佛才突然想起来,人命关天,该送老婆胖嫂去医院让医生检查检查。
胖嫂去医院看了急诊。看病的医生挺热心,细致地询问了病情,把了脉搏,听了心脏,看了看舌头……然后开出检查项目:抽血,头部颈部胸部CT,心脏肝脏脾脏肾脏B超,胃镜肠镜,脑电图心电图……胖嫂把检查做完,又等了两个小时,结果全出来了,所有检查过的部位和指标一切正常!
胖嫂病情的状况好像也是极其配合检查结果,早上发生在她身上的癥状都消失了。胖嫂脸色恢复了红润,耳朵不响了,眼睛不痛了,胃也不抽搐了,就是有点疲倦。胖嫂好过来了。
臭皮怀疑地问医生:“医生,真的是没什么问题?”医生说:“是没什么病呢!”“这就怪了!早上她又喊又叫,上吐下泻,寻死觅活的,怎么就没病呢?”臭皮有点茫然地望着医生。医生说:“她很好,看不出也检查不出有什么不对。”
若真的没病,那早上发生在胖嫂身上的事情怎么解释?回到家里,臭皮左思右想越想越坐立不安,便带着疑问去请教隔壁的王老先生。
臭皮家以前是个河滩,小地名叫枫树脚。当年,臭皮爷爷逃荒逃到巫镇的时候,没地方落脚,便在巫水河边捡了些别人做柴火的废木,在枫树脚搭了个茅棚子,住了下来。臭皮爷爷靠帮人扎排、打下手、挑水卖过日子。臭皮的奶奶是涨大水时,臭皮爷爷从河里捞上来的。臭皮爷爷捞上臭皮奶奶时(当时还不是臭皮奶奶),臭皮奶奶一条腿断了,仅剩一丝气息,戾气满面,身上只缠了几根破布条。死人一个!众人劝臭皮爷爷不要枉费心了。臭皮爷爷二话没说,把她背到巫镇唯一的草药郎中那里,守了三天三夜,硬是给救活了。臭皮奶奶虽然瘸了一条腿,却是眉目如画,秀外慧中。“老谢捡的大水财!”好多年过去,沿河街的街坊邻居还这样取笑臭皮爷爷两口子。
臭皮奶奶的身世是个谜。枫树脚也没有枫树。枫树脚以前是有大枫树的。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后来,枫树脚的臭皮爷爷奶奶把茅棚子改建成了吊脚楼。
胖嫂嫁到枫树脚臭皮家不到三年,胖嫂和臭皮商量要把吊脚楼改造一下,建成小洋楼。臭皮说:“只有地基是现成的,买砖水泥钢筋要钱,还要开匠人工钱。我们手里没那么多钱啊!”胖嫂说:“现在手里没钱,不能说一辈子没钱!我们有手啊,有手就可以挣得钱来!”
择了个良辰吉日,把吊脚楼拆了。臭皮又去请了隔壁地理先生王先生端罗盘定好向,开始动工修建小洋楼。
泥水匠请的高沙肖师傅,肖师傅带了个徒弟,徒弟是肖师傅的儿子叫做蒙宝。肖师傅五十来岁的样子,身材高大,力气也大,一百斤一包的纤维袋装水泥,左右手各提一包,走四五十米也不吃力。
肖师傅做点工,儿子蒙宝刚学手,收半价。肖师傅墙砌得好,手脚又快,做事利索,一天比别人要多砌两百个砖。众人都说,肖师傅做一天工当得人家两天的工。
肖师傅性格开朗,黝黑的脸上总挂着笑,胸脯上的肌肉一股股。肖师傅爱唱山歌。“四月插田咙来个咙,五月薅哟依哟。六月车水喃呵嗨,救禾苗情哥哥咚咚。十八满姑咙来个咙,来车水哟依哟。天不下雨喃呵嗨,何开交情哥哥咚咚……”肖师傅边砌砖边哼歌,有点嘶哑的嗓音,把每一句的尾音拖得抑扬顿挫。
见胖嫂在听自己唱歌,肖师傅伸了伸腰,不好意思地笑笑:“瞎唱——”
胖嫂也笑:“肖师傅肚才真好!”
肖师傅两手不停歇,摆砖,擦浆,刮缝,手里的活一丝不苟,嘴里说:“瞎唱瞎唱!”
胖嫂说:“唱得真好听。”
肖师傅说:“嘿嘿,日晒雨淋的泥水匠,一身臭汗臊气,靠唱山歌调味……”说完,肖师傅自己也笑了。
胖嫂和臭皮做副工。先是胖嫂和浆,臭皮挑浆。做了两天,臭皮挑浆挑得肩膀肿了,吃不消,把红肿的肩膀露给胖嫂看。只好换工,臭皮和浆,胖嫂挑浆。
肖师傅笑臭皮:“真像个读书先生。”
“一个咯子铜钱滚过界,山上咯子妹子哟穿草鞋。山上咯子妹子爱唱歌哟,情歌咯子越唱越拢来……”肖师傅继续哼山歌。
胖嫂姓肖,肖师傅姓肖,胖嫂就认了肖师傅为娘家大舅哥。胖嫂喊肖师傅哥,肖师傅喊胖嫂妹。肖师傅让儿子蒙宝喊胖嫂姑姑,喊臭皮姑爷。
肖师傅在臭皮家也就不把自己当外人。肖师傅父子俩做起工来格外使劲上心。
肖师傅不喝酒不抽烟,喜欢吃胖嫂做的油糍粑,胖嫂隔三岔五做油糍粑吃。胖嫂喜欢吃河鱼。肖师傅晚上赤了膀子去巫水河里摸鱼。肖师傅水性好,有时摸到鲤鱼,有时摸到黄鸭叫,有天晚上摸到一条三斤多的鳜鱼。
臭皮说:“想不到大舅哥有这么多本事!”
肖师傅谦虚地说:“哪里比得上做老板的妹夫子。”在外做手艺讨吃的匠人常常把主人称为老板。
胖嫂对臭皮哈哈一笑,说:“哪个像你,好吃懒做,酒囊饭袋……”
臭皮人简单,不精明,没什么花花肠子,但心肠不赖,就是酒瘾大,一个人也喝醉,喝醉了发酒疯,动不动就打人。
那天,臭皮喝酒喝得上劲,胖嫂劝他少喝点,还要帮忙做事。臭皮眼睛一横,揪住胖嫂的头发,抡起拳头就朝胖嫂劈过去。一旁的肖师傅像老虎钳一样的大手稳稳抓住了臭皮的胳膊,臭皮挣扎了几下,肖师傅的手越扣越紧,疼得臭皮嗷嗷直叫,却是动弹不得。
肖师傅说:“妹夫啊,我给你说句话,人都是父母养的,老婆是拿来疼的,不是拿来打的。”
肖师傅的话音量不大,却落地有声。听到肖师傅的话,臭皮酒劲醒了一大半。
肖师傅的话如醍醐灌顶。从此,臭皮戒了酒,也不打胖嫂了。
小洋楼封顶了。肖师傅父子俩明天就要回老家高沙了。晚饭后,胖嫂在灶上煮茶发油糍粑,给肖师傅父子俩路上消暑充饥。肖师傅说是觉得闷热,去河边歇凉。到下弦月挂在天边,肖师傅也没回,他一直在那里哼山歌:
在生和妹讲得来吔,
死了和妹同棺材呢。
阎王面前双双跪哟,
二世投胎又再来呀……
静静流淌的水面洒落着半边月亮的银辉,隐隐约约泛着粼粼波光。肖师傅的歌声让胖嫂心里一阵阵发紧。灶台上的茶壶咕噜咕噜响了一个通宵。
臭皮找到王先生。臭皮把早上胖嫂发病的情况,胖嫂到医院检查的情况说给王先生听。王先生虽然已是鲐背之年,但童颜鹤发,思维清晰。王先生通地理,精卦象。王先生慢条斯理地说:“神明庇佑,谢门家宅素来清泰,无人犯煞。女主失常,莫不是……”王先生附在臭皮耳边小声如此这般道出问题所在。
臭皮回到家里,二话没说,翻箱倒柜地寻找起来。胖嫂问他找什么,他也没说。
“你在找什么?”胖嫂问臭皮。
“没找什么。”臭皮翻了衣柜,又拿了根竹篙掏床下,只差没有挖地三尺了,还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胖嫂说:“你是怀疑我私藏了金银财宝吧?”
“没有没有。”臭皮双手一摊,摇摇头不找了。见胖嫂神色正常,太阳开始西落,臭皮找出了渔具,对胖嫂说:“我钓鱼去!”说完,往河边走去。
傍晚时分,一辆小车停在沿河街枫树脚胖嫂家的小洋楼前。车上走下一个中年男人。中年男人径直进了胖嫂家。他见了胖嫂,跪下去施礼。胖嫂心里惊了一跳,慌乱中忙把男人扶起来。这时,她才发现来人腰上合了根麻绳。
“姑姑,我爸走了,今早卯时落的气……”来人是肖师傅的儿子蒙宝。他哽咽地向胖嫂说。
“噢……”胖嫂正犹豫着,觉得眼前一黑,心口被什么重重地捶打了一下。
“姑姑……”蒙宝轻轻地叫了一声。
胖嫂回过神来。她忙去给蒙宝倒茶。
“你爸得的什么病?身体那么强壮的……”胖嫂问。
“冠心病,发现十几年了……”蒙宝说。
“心病……瞒得这么紧……”胖嫂叹气道,低下头,眼睛红了。
“姑姑,我爸说,让我来取一件遗物……”蒙宝说。
胖嫂木木地站在那里,心里翻江倒海,六神无主——整整二十五年啦。沉默了一会,表情木然的胖嫂跌跌撞撞去了房里。过了一会,胖嫂出来,缓缓地伸出双手,将一个布包递给蒙宝。
蒙宝接过包,谢过胖嫂,正要动身走,胖嫂叫住他,把一个红包塞在他衣袋里。“蒙宝,替姑姑给你爸烧炷香,愿他一路走好……”
“好的。谢谢姑姑,姑姑多保重!”蒙宝上车,发动车,轻轻地鸣声喇叭,慢慢远去了。
“这开车的是谁呀?真像给我们修房子的肖师傅。”不知什么时候,臭皮钓鱼回来了,他问胖嫂。
胖嫂没有回答臭皮,呆呆地坐在那里。
臭皮说:“今晚上吃鱼啰。”他把桶子里的河鱼亮给胖嫂看。
胖嫂瞄了瞄桶子里的魚,她突然感觉到有一股强烈的腥臭味钻进鼻孔。“哇——”胖嫂张开嘴猛吐起来。
偏 方
辛家住沿河街街尾,背靠一座小山包。房子是木房,有点陈旧,是四排三间两层的吊脚楼。吊脚楼柱头板壁清一色的杉木料,小青瓦盖顶,夯土铺地,干净整洁,夏天很凉快。
辛家平时只有辛三爷两口子在。女儿嫁了,一年到头难得回来那么一两次。儿子儿媳在外打工。还有孙子孙女,孙崽成成读完大学,在省城谋了份差事,孙女方方三十岁了,在上海读博士。辛三爷常笑孙女方方,人都读老了,还没读出身。方方说,我读我的书,反正我这辈子又不嫁人。辛三娘听了,有点不高兴地骂方方,读书读得人都哈了。辛三爷两口子在家很安静,弄不出什么动静来。
这天,歇在门口的黄狗汪汪地叫过两声。一个男人从炙热的太阳下走进了吊脚楼。
辛三娘在摊筛里晾晒刚切碎的紫苏、藠头、韭菜,摊筛放在一个木架子上,切碎的紫苏、藠头、韭菜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混合香味。旁边还摊晒了很多新鲜的嫩辣椒(是开水焯过的),辣椒被太阳一晒,有的表皮已经开始发白。辛三娘在准备做灌辣椒的原材料,灌辣椒是巫镇的一种地方传统美食。每年暑假回来,孙女方方都要吃奶奶做的灌辣椒。辛三娘做的灌辣椒是巫镇最讲究的。
“三娘好。在忙啊——”来人和辛三娘打招呼。
“哦——莫怪三娘眼花,拢了才看清是德伢子,快进屋快进屋。”辛三娘放下手里的活路,赶紧地招呼客人。“来就来,还讲什么礼性。”接过客人手里的东西,辛三娘去倒茶。
“瞎忙,好久没来看你们二老啦。”来客德伢子说。德伢子圆乎乎的脸,眼睛笑起来一道缝。德伢子早先也是沿河街的住户,辛三娘他们看着长大的。德伢子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打拼二十多年,混得不错,开了几家公司,有一家是上市公司。
“你几时回来的?你娘身体好吧?还住得惯?”辛三娘问。德伢子爹去世后,德伢子把百岁老娘带去深圳住在一起,专门请了一个保姆服侍。德伢子娘天天闹着要回沿河街,嫌城里的自来水臭腥。
“昨天回来的。我娘好呢,托你们的福。三爷是我娘的救命恩人……”德伢子说着,声音有些哽咽。
“那就好那就好。”辛三娘又告诉德伢子说,“你三爷在里屋……”
辛三爷正在里屋石槽里倒捶一块乌黑的东西。满屋子药香。德伢子端了茶进来,毕恭毕敬地叫了声“三爷”。辛三爷应了一声,起身让座。
外面骄阳似火,屋内却是清凉扑面。德伢子称赞道:“真是别有洞天。”
辛三爷笑着微微颔首,说:“自得其乐。”
里屋靠山坎那面有眼井水,暴雨不溢,天旱不干,一年四季清水常流,冬暖夏凉,甘洌可口。里屋没装门,外人可以自由出入。沿河街的人常到这里打水。
“好久没喝这里的井水了。”德伢子说着去咕噜咕噜捧井水喝。
辛三爷和德伢子说话的当儿,辛三娘切了西瓜、洗了李子,端进去摆在桌案上。然后,辛三娘继续忙自己的事。一只母鸡带一群小鸡崽唧唧咯咯围着幸三娘的腿转。
德伢子和辛三爷说了阵子话,准备辞行,辛三爷辛三娘留德伢子吃饭,他说另外有事,留着下次来吃。临走,德伢子向辛三爷说:“三爷您老好好考虑我的想法。”辛三爷点头应了。
沿河街只一户姓辛的,全巫镇也仅此一家辛姓。辛家祖上是从北方来的。辛三爷听老辈子口传,他们本来也不姓辛,是姓辜。辜家祖上是宫里的御医,很得皇上恩宠。因遭人陷害,株连九族。太祖婆抱着辜家十个月大的男婴,乔装打扮,一路逃奔,昼伏夜出,餐风露宿。三年后,逃到了山高皇帝远的偏僻之地巫镇。为掩人耳目,把辜字去了头,改为辛字,隐姓埋名。从此,刀耕火种,筚路蓝缕,饱尝人间苦难。
到了巫镇,太祖婆带来的男婴已经四岁,太祖婆叫他老鼻儿。老鼻儿是个哑巴。太祖婆逃出辜府时,怕老鼻儿的哭声,引来官兵的追杀,给老鼻儿下了哑药。老鼻儿十八岁那年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得梦,梦中遇见一青衣老人,如此这般教他采药用药。第二天早上,老鼻儿直奔后山,采撷数种药材,回家如老人所教如法炮制,得黑药。其时正好一乞儿拄杖路过,腿患毒疾,肿大如桶,痛苦不已。老鼻儿给他敷上黑药。两个时辰过后,乞儿腿肿处恶露流得一地,红肿消退,乞儿已能行动自如。祖宗显灵了。太祖婆问清老鼻儿做药的根由,心里这样想。太祖婆继而又和老鼻儿说,这事可不得声张。来年夏,倾盆大雨三天三夜,巫水河暴涨,巫镇街道积水及膝。暴雨后,毒日炎炎。巫镇出现一种怪病,患者全身长红疮,奇痒无比,毒性强,易传染。不到七天,死人上百。医家术穷,无药可治。县衙贴出告示,称谁能治得此病,赏白银千两。年轻气盛的老鼻儿瞒着母亲(太祖婆)去揭了榜。老鼻儿到山里采来药草,在县衙门口架上大铁锅,熬制药汤。凡身上长红疮者喝药汤一碗,另拿荷叶包盛的黑药回去搽涂患处。不到三天,果然见了奇效。巫镇的怪病被老鼻儿制服了。老鼻儿声名大振。老鼻儿回到家里,高兴地比画着和母亲说,镇里的老百姓都在夸赞他,县老爷要兑现承诺奖赏他。太祖婆被老鼻儿吓得不轻,她告诫老鼻儿,儿啊,药是拿来治病的,不是用来赚钱的。老鼻儿听了母亲的话,没有去领县衙那千两赏银。县衙后来给老鼻儿家送来楠木匾——扁鹊再世。太祖婆给老鼻儿立下家规,药方只能救急行方便,无论贵贱。
说来也怪,辛家到巫镇三百年,到辛三爷这辈是十六代,人丁单薄,几乎代代单传。老辈子又有话,太祖婆带着十个月的孩子逃出生天,已是老天对辜家的格外开恩,像岩壁上的草,不求人丁旺盛,只求辜家血脉得以延续。
辛三爷曾爷爷那辈有两兄弟,大哥叫猛子,小弟叫求狗。求狗广结富家子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成天穿梭歌楼酒榭,寻花问柳。求狗在一场酒局上结交了摩天岭土匪头头青面猴。青面猴行事暴戾,民怨极大,但迫于他的淫威,谁都不敢招惹他,官府拿他也没辙。青面猴腰患毒疮多年,大如铜钱,疼痛不已,四处求治不愈。求狗说他有祖传秘方,包治。青面猴说,只要治好,金鱼三条。求狗心里欢喜那三根金条,乐癫癫回家拿药给青面猴敷上。第二天,青面猴倍感劇痛。撩衣查看,疮大如碗口,脓水如注。青面猴二话没说,让手下剁了求狗的脑袋,把求狗血淋淋的脑壳挂在河边的一棵麻叶柳上。三天过后,青面猴腰上的毒疮好了。青面猴这才知道求狗被他错杀了。他口里却骂,狗日的,说一天包好的,害得老子多痛了两天。
辛三爷读完高中那年,巫镇医院把他招进去做集体工,医院聘用医院发工资,没豆腐票,不吃国家粮。辛三爷说,我不会看病,来医院碍手脚。院长告诉他,现在国家号召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医院偏僻缺人才、缺药品,加上我们这里山高林密,瘴气重,你家的祖传秘方啊土方子啊偏方啊正好派上用场。这话还真让院长说准了,辛三爷在巫镇医院被人称为辛医生的那两年,的确解除了好多人的病痛之苦。赢得了十里八乡乡亲的交口称赞。
那年秋天的一个早上,云雾寨用竹架子抬来一个十五六岁的病人。病人面黄肌瘦,脖子上长个拳头大的瘤子,摸起来硬邦邦的,瘤子严重影响到呼气。因家里没钱看病医治,拖了半年之久。眼看瘤子越长越大,父母亲看到实在痛得挨不过了,才送到医院来。辛三爷接的诊。他看了病人的情况,说,你们大意了,人命关天的事,耽误久了要误事的。病人父亲说,知道,可看病要钱的……辛三爷说,没钱可以想办法,命去了就没有了。辛三爷安排病人住下,给他熬药汤喝。病人姓蓝名大和。住了七天院,吃了七天药,蓝大和脖子上的瘤子消肿了,面色也红润起来。蓝大和命保住了。蓝大和高中毕业后入伍参军,在部队提了干。每次回家探亲,蓝大和都要提了礼性来看望辛三爷(那时辛三爷已经从医院辞职),感谢辛三爷的救命之恩。后来,蓝大和转业到地方,做了副县长。做了副县长的蓝大和还来看过辛三爷好几次。但想不到的是,就是前年,快退休的蓝大和却出了事,因犯贪污受贿罪,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判刑五年。听到这个消息,辛三爷惊了一跳,感慨道:“那么老實的一个人变坏了。药,救得了人命,治不了贪心!”
辛三爷在医院工作时,偶尔也工作之余出外诊,主要是帮那些行动不便或者熟人看病送药。药是自己炮制的,又是工作之余,辛三爷出诊不收费。有时收点烧纸、线香。因为治好病人要给先祖老鼻儿烧纸烧香还愿。那年头正值破四旧。烧纸烧香敬神属封建迷信,医院的医生烧纸敬神肯定不允许。辛三爷被拉去办学习班。辛三爷家珍藏的楠木匾“扁鹊再世”也被搜去,一把火给烧了。学习班一结束,辛三爷就到医院办了辞呈。院长好言挽留他,辛三爷说:“古语云,人参害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
辛三爷房子后面围了个园子,园子里种了藤藤草草的药材——七叶一枝花、乌头、天南星、金银花……七叶一枝花、天南星花事正旺。修长的乌头苗郁郁葱葱。金银花花期已过,盘虬卧龙的藤蔓攀爬成一个荫凉的棚架。两只绿色的树蛙依附在藤蔓上歇凉。那棵高大的杜仲树上鸟飞蝉鸣。
辛三爷喝茶。他喝的茶是巫镇特有的一种茶——棠鹅梨茶。棠鹅梨是俗名,书名三叶海棠,一种四季常青的灌木。辛三爷每年去海拔两千米的宝鼎山上采一次。叶子和树干都可做茶。叶子用来泡茶,树干劈成小块用来熬茶。茶呈金黄色,只是叶子泡出的颜色淡,树干熬出的颜色深。辛三爷偏爱熬茶,用生铁壶子,放温火上慢慢熬。这种茶有独特的味道,入口有点涩,但特别润喉,咽下去后回味甘甜,放十天半个月不馊、不变味,有生津止渴健脾胃的功效。
辛三爷多次跟儿子说,祖上传下的偏方他应该接下来。儿子说,还是在外面挣钱自在,不肯回来。
辛三爷不是在里屋捣药喝茶,就是在后园子里侍弄药草。德伢子来拜访辛三爷,是德伢子正在筹划成立一家中药研发公司,邀请辛三爷出任顾问,还说如果愿意,辛三爷可用他家的祖传秘方入股分红利。经历过非典、新冠疫情的惨痛教训,人们认识到了中医中药的重要性。德伢子说,中医中药是古老的骄阳产业。
“老朽老朽,入黄土的人,不中用啦。”听了德伢子的话,辛三爷摇摇头,笑着说。
“您老莫谦虚。中医就像老酒,越陈越香。”德伢子说着,陪辛三爷笑。
“我就懂几个土偏方,应急的,登不了大堂。你是见过大世界的。”辛三爷低头喝茶。
“您这偏方千金难求。您老小天地有大世界。”德伢子也低头喝口茶,然后抬头望着辛三爷。
“哈哈……”辛三爷朗朗地笑了。
“嘿嘿……”德伢子也笑了。
就在当天太阳落岭时,黄狗又叫了。在上海读博士的孙女方方,拖个拉杆箱稀里呼噜回来了。
方方叫了辛三爷,然后抱着辛三娘叽里呱啦亲热个够。
“爷爷奶奶,这回我不走了。”方方突然说。
“你毕业了?”辛三爷问。
“是的。毕——业——啦,不——走——啦!”方方加大语气回答爷爷。“我要回来继承祖传秘方,向你学习炮制中药的方法!”
辛三爷一口茶没咽下,被呛了喉,瞪着眼睛望着方方:“你博士不是学的这科啊……”
“跨界!跨界!”方方哈哈一笑,“我觉得我有这方面的天赋。我回来了,天天可陪伴你们,天天吃得到奶奶做的饭菜,好开心呀,哈哈……”
“这疯女子。”辛三娘轻轻地骂一句。
方方放落行李,跑进后园子,张开双臂,对着那些药草哇哇大声叫喊:“亲们,我来咯……”
辛三爷怔怔地站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来。
(编辑 黄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