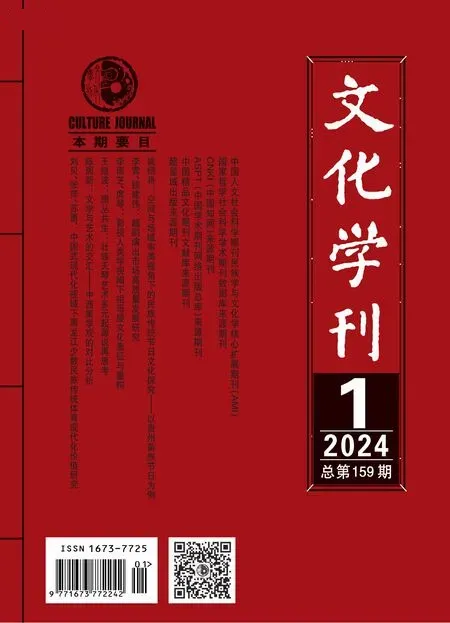空间视域下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成因初探
2024-03-22王倩倩
王倩倩
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在安娜这条线索中讲述了一个因爱情出轨的贵族妇女在同命运斗争无望后卧轨自杀的故事。小说于1956年出版后便成为各类文学家研究的重点对象,很多学者从文本出发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宗教、悲剧成因、女性意识进行了分析。在对安娜悲剧成因的分析中,韩家胜、康佳琼分别从社会和个人因素出发将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归咎于制度的禁锢,张璐从“自由的悖论”角度指出安娜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她的死亡悲剧,等等。这些研究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安娜死亡悲剧的成因,但却没有从空间理论视角对造成安娜死亡的原因进行分析,忽略了在上流社会权力规训下形成的狭窄女性空间对安娜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剥夺。“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1]小说揭示了空间生产其实是一种空间规训,安娜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是对自身生存空间及精神空间的扩张奢望。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为出发点,从空间侵占和权力规训方面论述造成安娜死亡悲剧的原因。
一、空间的辖制
(一)社会空间规范下的社交宠儿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空间三元辩证法,即构建了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征性空间的三位一体,将空间划分为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强调了统治、服从和反抗的关系,它具有潜意识的神秘性和有限的可知性,作为一种开放性的亲历性空间,它是一种实际的空间。”[2]空间表象“与生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强加的‘秩序’捆绑在一起,从而也与知识,与符号、代码,以及种种‘台前的’关系捆绑在一起”[3]。由此可见,《安娜·卡列尼娜》中上流社会等级森严、阶层明显的社交界体现和承接的正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统治阶级对空间秩序设定的具象化呈现。
上流社会从贵族个体到社交界都是权力规训下的产物,安娜的社交活动主要由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组成,这是封建贵族地主中女性成员的生活常态。家庭生活中,安娜最初安分地扮演着贤妻良母角色。比安娜大20岁的卡列宁是由安娜姑妈介绍而来,虽然他冷漠呆板,但安娜仍然对其及家庭充满热情。此阶段的安娜正是被沙俄上流社会驯化出的一个美丽贵妇人,她发不出“从来如此,便对么?”[4]的质问,因为她的家庭生活正是上流社会推崇的“家庭范本”。在社交生活中,安娜经常涉及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三个小圈子,一个是她丈夫政府官员的圈子,关系错综复杂;一个是卡列宁借之发迹的圈子,以李雅迪伯爵夫人为中心;后一个则是十分轻视半上流社会的社交界,奢侈华丽。在上流社会空间辖制下长大的安娜显然对各类社交得心应手,安娜在社交场的八面玲珑正体现出了社会空间对个体的规训,她无意识地服从着空间规训,扮演着饱受赞誉的女性角色。
社会空间中等级森严的各类社交场所其实正是阶级、权力、社会意识形态的表征,无形中影响着个体的身份认同。此时的安娜连自己都尚未意识到自身生存空间是怎样瑟缩于社会空间的紧紧辖制下。
(二)安娜自我空间意识的萌发
“我们所关切的社会阶层和各种群体界限,以及渗透其中的社会权力关系,均镶嵌在一定的空间里。”[5]女性作为社会空间网罗下的个体,经营自我空间的同时也经受着权力规训。克瑞西达·海斯(Cressida J.Heyes)对空间规训颇有想法,她认为规训塑造出了服从的个体,“个体是一个循规蹈矩、温顺、自我监督的人,他被期望以特定的方式发展,并受制于更严密但看似更良性的管理形式”[6]。彼时俄国古老的封建地主受到西欧资本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新思想一定程度上对上流社会空间有所渗透,安娜的女性意识因爱情得以滋生,其自身的空间意识也因此萌发。与伏伦斯基的偶遇扭转了她的人生走向,“她故意收起眼睛里的光辉,但它违反她的意志,又在她那隐隐约约的笑意中闪烁着”[7]55。两个富有生气的人开始互相吸引,但已有家室的她本能地隐藏着这份欣赏。回家的列车上,安娜因沉浸式读书神往和男主人公同至新封领地,此时的她感到害臊,于是反问自己“但他究竟有什么害臊的?我又有什么可害臊的?”这个质问影射了安娜对自身与伏伦斯基关系的看法,是安娜对自我生存空间的第一次质问与反思。舞会之后,伏伦斯基设法与安娜在列车厢偶遇,安娜深受触动,在与丈夫碰头后,安娜萌生“他的耳朵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7]91的想法,“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熟悉的感觉,也就是在对待丈夫关系上的虚情假意。她以前没有注意到这种感情,现在却十分明白而痛苦地意识到了”[7]91。伴随着爱情滋长,安娜的女性意识由此觉醒,同时意识到自身精神空间在社会空间规训下的狭隘。安娜自我空间的意识萌发得益于列车媒介,在鱼龙混杂的车厢或车站,安娜仿佛暂时脱离了等级森严的上流社会空间的规约,抓住了审视自己心意的瞬间。
二、试图冲破空间束缚的女“斗士”
(一)安娜对生存空间遭受挤压的反抗
权力无处不在,“但列斐伏尔并没有像福柯那样,面对无孔不入的权力控制而悲观地认定现代人已经‘无可反抗’ 或 ‘无家可依’,而是认为,空间既是压迫的重灾区也是反抗的间隙处”[8]。
安娜因为伏伦斯基体会到了爱情在生命中的重要分量,深觉自身生存空间正遭受着社会空间的无情倾轧。于是她开始追随自身心意行事,一系列行为正是其对生存空间遭受挤压的本能反抗。夜谈失败后,安娜和卡列宁之间生出隔膜,其实这种隔膜一直存在,只是伴随安娜女性意识的觉醒得以显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安娜表面上热衷社交,实际上到处都同伏伦斯基见面,安娜最终怀孕了,这是她无意识中扩张自我生存空间的第一步。
女婴顺利降生,安娜与伏伦斯基双双度过生命危机且更加确信双方的重要性。安娜未与卡列宁离婚且选择和伏伦斯基一起出国,此时场所发生转移,与情人出国是安娜自我生存空间扩张的第二步表现。
旅行结束后回国,即使社交界大门已对安娜关闭,可她还是不顾伏伦斯基的劝阻去观看了众多名流在场的歌剧,这种在外人看来是公开挑衅的做法,是安娜为拓展自身空间树立起的一面旗帜,是安娜为扩张自我生存空间所迈出的第三步。
这一系列行为实际上正是安娜为扩展自身生存空间所进行的反空间实践,是一场抓住一切间隙扩展自身生存空间的权力博弈。
(二)安娜对自身精神空间的扩张欲求
精神空间是“人物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人物意识在空间实践中的表现”[9]。安娜多年来深受上流社会的空间辖制,谨守自己的一隅空间。可当爱意汹涌而来,安娜的自我空间意识迅速生长,精神空间的扩张欲求愈发强烈。
与伏伦斯基的热恋是引发安娜扩张自身精神空间的第一个动力来源。在上流社会,人们普遍对有妇之夫或有夫之妇与情人、情妇的暧昧持容忍态度,但绝不允许私情公开。安娜接受不了如同做贼般把爱情的火焰压在暗处,于是便仇恨上这虚伪的社会空间,拼命想实现自身精神空间的扩张,在与伏伦斯基痛快的热恋中践行自我爱的权利。
卡列宁在发觉妻子出轨后几次发出谈话邀约,可安娜屡次婉拒,因为那些话无非是对妻子因“堕落”而溅到丈夫身上污泥的批判。对卡列宁而言,在妻子出轨所带来的冲击里,使自己名誉受损和上升通道受阻占了绝大部分,由此也可看出安娜确实在这无爱的家庭中饱受压抑。爱情滋长使安娜深刻认识到自身生存空间的逼仄,进一步激起其扩张自身精神空间的欲望。
事态愈演愈烈,安娜终于在赛马事件后向卡列宁坦白,这种行为表现出安娜在饱受心理折磨后对爱情的坦荡追求,对自身精神空间独立性急需确立的渴望,对脱离上流社会空间规训和男权空间束缚的精神追求。面对安娜的坦白,卡列宁书信一封要求安娜留在家中以保持体面,安娜发出“我要冲破他这张想束缚我手脚的谎言的罗网”[7]251的呐喊。扩展自身精神空间的欲望和深陷泥潭难以抽身的现实共同威逼着安娜,她因深感无力冲破任何罗网而处于无尽痛苦之中。
三、挣扎不出的空间围困
(一)社会空间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挤占
如福柯所说,空间中的群体必然会受到“空间规训”。“所谓‘空间规训’,意指通过对空间的刻意为之的筹划、设置与构造,对个体的心理状态和人格结构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心悦诚服地屈从于既有的社会——文化秩序,并逐渐蜕变为驯顺而高效的‘被规训的物种’。”[10]
两人的桃色新闻流传时,伏伦斯基在生活表面上还可以继续按照旧有生活轨道进行,安娜却遭受着社会舆论的重压。可见社会空间对女性进行着更为严苛的束缚,这是社会空间规训女性的印证,更是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空间摇摇欲坠的表现。安娜同卡列宁彻底摊牌,继而又在诞下女婴后同伏伦斯基出国旅行,此时俄国上流社会对安娜的排斥表现出社会空间对女性生存空间的严格束缚,如果女性想要逃离空间规约,就会受到社会空间的进一步施压。而后,安娜与卡列宁共赴乡下庄园,希望从上流社会空间的约束中挣扎出来,此时安娜已把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于伏伦斯基。寄居庄园的安娜几乎没有了社交活动,表面上看似脱离了上流社会的空间束缚,实际上其生存空间已被挤压到极点。上流社会通过对安娜的排斥实践着权力规训,同时也以安娜的“悲哀”下场对上流社会其他成员进行警示,借此维持城市空间的话语权,保持社会空间的稳定性。
生存在社会空间中的安娜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身在其中却不被接受的境遇展现出安娜自我生存空间屡遭挤占的现实,空间施压是导致安娜死亡的重要推手。
(二)安娜自身精神空间的数遭围堵
作为被上流社会权力空间网罗下的女性,安娜无法斩钉截铁地做出离婚决定,只能在慌乱中说出“‘一切都完了,’她说,‘我除了你,什么也没有了。你要记住!’”[7]132安娜也清楚,一旦对上流社会发起挑战,被排斥是必然结局。但上流社会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挤压让安娜无法自处,她只好在迷茫中将未来寄托于伏伦斯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安娜精神空间的自为性扩张。在彼时俄国上流社会的空间规训下,依附男性生活也是女性生存空间逼仄的原因之一。可安娜别无他法,因为社会没有为她提供独立机会。因此出国旅行时,只要伏伦斯基回家稍晚,安娜便疑窦丛生,这样的生活状态已显病态,也为安娜的死亡埋下隐患。回到彼得堡后,安娜深觉社交界对她的排斥,因此情绪起伏极大,这说明安娜在拓展精神空间的过程中屡遭轻蔑,精神世界非常脆弱。安娜不仅失去了整个社交界,还失去了看望儿子的机会,在参加巴蒂歌剧时更是受到名流们明里暗里的轻蔑,安娜在精神空间扩张的路上再遭围堵。
在乡下庄园,安娜的精神空间已因社会空间排斥而萎靡,在她看来伏伦斯基是唯一的希望。可伏伦斯基只把爱情看作人生中求索的一部分。“总之,我什么都可以为她牺牲,就是不能牺牲我男子汉的独立性。”[7]543伏伦斯基的想法是压倒安娜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与外界的交往是如此让安娜恐惧。归根结底,安娜因生存空间逼仄而对伏伦斯基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因此,当安娜误解伏伦斯基对她的忠诚和深爱时,她的精神空间几近消亡,生活对她来说毫无可留恋之处,于是安娜选择了自杀。
安娜最终选择了在火车站赴死,火车站其实正是社会空间相互渗透的一个交界点,是空间划分不明晰的一个交界处。安娜的自我空间意识由火车站始,由火车站终,在空间的缝隙里觉醒,又在空间的缝隙里湮灭,她的精神因为没有挣扎出权力空间的围困而漂泊无依。
四、结语
从空间视域下对安娜的死亡悲剧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内化在空间中的权力意志对安娜的全方位束缚。安娜因为女性意识觉醒而本能地探求着自身生存空间与精神空间的扩张,却因空间的裹挟只能苦苦挣扎。这场必然会输的空间博弈实际是女性群体为突破自身生存空间与精神空间饱受压榨所做的努力,展现了陷于空间囹圄的女性的本能性抗争。安娜自身空间的扩张行动虽最终以死亡告终,但却发人深省,“血和泪往往能给我们比欢笑更甜美的滋味”[11]。托尔斯泰在书写安娜命运时持有同情之心,隐晦地批判了当时俄国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盘剥,其对受压迫女性的人文关怀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