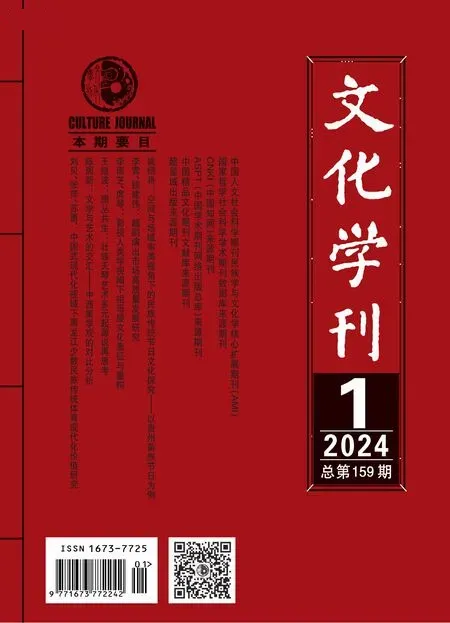圈丛共生:壮族天琴艺术多元起源说再思考
2024-03-22王继波
王继波
在中越边境地区普遍存在“天”信仰观念,祭祀天的仪式称为“做天”。仪式中,壮族天琴艺术以“天”之乐、“天”之歌、“天”之舞的形态外显于仪式信仰,成为“嵌入”仪式制度的固定元素。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去语境化”“再语境化”,壮族天琴艺术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文化变迁,例如:从民间法器上升为民族乐器;突破性别禁忌,建构起新的展演空间;结构功能不断延伸,成为族群、地方和国家文化认同的象征性手段。
由于缺乏对壮族天琴艺术完整而系统的文献记载,加之壮族天琴文化变迁不断,以致学界对其起源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形成“本土起源说”“外来传播说”和“百越民族共有说”不同观点。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重新思考壮族天琴艺术的文化身份,对增强跨境文化交流互鉴,提升边民文化认同具有理论实践双重意义。
一、本土起源说
关于壮族天琴艺术的起源,“本土起源说”影响最为广泛,其主要依据有三:民间传说、骆越巫术信仰以及族源—地缘关系。
其一,在壮族民间,有多则关于天琴起源的民间传说,其中尤以龙州县《妈勒访太阳》[1]和防城区《端亚造琴说》[2]较为典型。
《妈勒访太阳》传说中的“妈勒”系壮语“母子”之意,与广泛流传在桂西南、桂西北一带的民间传说“妈勒访天边”系同源变体的关系。相传古时候的人望见天就像一个锅头一样,圆圆地笼罩着整个大地,出于对宇宙探索求知的渴望,以“妈勒”为代表的传说人物形象开启了对自然现象探索的旅程。“妈勒访天边”是一则象征意蕴明显的壮族传说,寓意着古代壮族先民为追求光明,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通过对比不难发现,上述关于壮族天琴艺术的《妈勒访太阳》传说与《壮族神话集成》[3]中所收录的四则传说的版本异中有同,可以说前者是后者原型改编后的一种文化再造行为。借助“母体”传说的传播影响,有关壮族天琴艺术的本土起源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
《端亚造琴说》是流传在防城港地区壮族布偏族群的民间传说,其中的农端、农亚被当地民间天琴师“仙婆”奉为他们的行业神进行崇拜。关于“农端”“农亚”的传说,《壮族百科辞典》有载:“古时,有对青年男女,男的叫侬端,女的叫侬亚,能歌善舞,精通琴艺。他们的歌唱能唱走偏人的苦难,弹的琴声能解除壮家的闷愁,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和称赞。后来侬端化成金龙,侬亚化成金凤,一齐升天为仙。从此,偏人尊奉他们为歌、舞、乐的‘先师’,把他们所唱的歌称为‘天歌’,所跳的舞为‘天舞’,所弹的琴称为‘天琴’。”[4]上述有关天琴艺人的称谓、“农端”“农亚”为民解难的传说与壮族古老的巫觋信仰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作为骆越人的后裔,巫文化信仰在壮族地区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列子·说符》有言:“楚人鬼而越人禨”。禨,祥也,信鬼神与禨祥。在壮族巫觋信仰发展过程中,受汉传道教的影响,巫觋经过分化出现了性别制度上的不同安排,即男性执仪者演变为“麽公”或“布麽”,而女性执仪者仍称之为“巫婆”或“仙婆”。两性在仪式分工上既有区别又有关联:二者之间的区别体现为“仙婆”主事通神问卜,“麽公”则除了卜卦以外,还可以驱邪赶鬼、禳灾解厄;二者的关联表现为本质上都是为人们排忧解难,禳灾祈福。
其二,壮族天琴艺术“本土起源说”的第二重证据与骆越巫术信仰相联系。有学者指出:“天琴是壮族祖先古骆越人流传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来源于古骆越人对超自然力量存在和万物有灵的信仰。”[5]作为沟通人神的法器,天琴的产生与当地的巫术信仰观念紧密关联,可以看作是古骆越巫文化的历史积淀。亦因此,壮族民间社会习惯于将壮族天琴艺术看作是壮族祖先古骆越人对超自然力量存在和万物有灵信仰的结果。众所周知,龙州地处祖国南疆,自古属于骆越之地,并且民间广泛流传“鬼出龙州”“龙州鸡鬼”一说,因此,以驱鬼逐疫、祈福平安为目的的壮族天琴艺术仪式行为就成了壮族巫文化信仰的外显性行为。
其三,持壮族天琴艺术“本土起源说”观点的另一个依据与族源、地缘有关。一方面,此说认为壮族天琴艺术源于壮族布傣族群支系的乐器。另一方面与壮族仪式经书《塘佛》历史有关。有学者推测:“天琴的早期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汉代。此外,根据凭祥认为天琴产生于九百多年前、宁明认为产生于三百多年前、防城区认为产生于两百多年前的说法,可以大致推测,天琴从宋代至19世纪初相继流传至凭祥、宁明、防城等地。”[6]
二、外来传播说
关于壮族天琴艺术起源的“外来传播说”当以潘林紫、曹军二者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据清朝黄誉于1803年纂修的《龙州纪略》中所载:
龙州遇有疾病者,即延鬼婆之家永夜弹唱,亲族妇女以饮啖为散福,鬼婆大约年轻者多,手弹二弦脚抖铁链、银铛之声以锁鬼,其宣扬诅祝哪哪之音,非但内地人不能聆会,即龙之土民亦毫不解识,猥云传自交趾,其信然耶抑盘瓠之流传耶。[7]
文中所言“二弦”即当下流传的天琴;“鬼婆”则是以驱鬼祈福为目的的仙婆;“交趾”即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一带;至于“盘瓠”一说,徐松石认为“盘瓠”之事应在汉初。由此,潘、曹二人认为,天琴在汉代已经出现,但考虑明清以前记载广西风土人情的相关文献并未有任何关于“叮”或“鼎”的记载,同时结合金龙峒天琴仪式专家板烟屯“农”“马”及板池“李”姓族谱推算,天琴最早“流传范围应是在现今的越南境内,至明代,传入桂域。……‘叮’传入龙州应从1803年上溯至1387年(明洪武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另外,潘、曹二人认为,“天琴”这一名称称谓并不是起源于龙州县,而是由防城区传播而来,“因来源于‘天’这个民间艺术总称及相关的民俗活动,龙州地区把‘叮’称为‘天琴’应是借用防城对该琴的称谓”[8]。
三、百越民族共有说
有学者认为应将壮族天琴艺术的起源归于百越民族所共有,其主要依据有二:其一,南宁地区文联于1991年出版的《壮族风情录》中对天琴的起源做了三种推测,分别为:作为壮族本土创造的古老乐器;作为西南地区古代各族原有的乐器;作为我国古老弦乐器秦琵琶的变种乐器[9]。其二,结合“西南地区古代各族原有的乐器”这一推测,研究人员进一步梳理了流传在于国内云南傣族、布朗族、景颇族,及国外越南、泰国流传的自称中含有“Ding”(1)如:云南傣族拉弦乐器“玎俄”、布朗族弹拨乐器“赛玎”、景颇族弹拨乐器“玎”、壮族天琴“鼎”或“叮”,因称谓之间存在差别,故使用汉语拼音“Ding”指称。的乐器,通过比较联系,从形制结构、弹奏手法、族群渊源的角度提出了天琴“最早为百越民族所共有”[10]的观点。
四、对于不同起源说的再思考
艺术起源是古往今来学术研究过程中的重要话题,但若想就某一文化事项的起源达成共识亦非轻易之事。正如有学者所言,或许“对于音乐发生学来说,这种‘无解之解’方为音乐在文化哲学上的最初之‘解’”[11]。不论是“本土起源说”“外来传播说”,抑或是“百越民族共有说”,都是哲学意义上有关壮族天琴艺术“最初之解”的一家之言。
其一,就“本土起源说”来看,民间传说、巫术信仰、族群关系、地缘结构乃至师承体系等一系列证据链夯实了壮族天琴艺术本土起源这一观点。但据“凭祥天琴产生九百多年,宁明天琴产生三百多年,防城天琴产生两百多年”的民间口头记忆就断定天琴源于金龙峒,并先后传播至凭祥、宁明、防城地区的说法似乎又不能够合理解释各地天琴的差异性。从仪式执仪者性别的角度看,目前龙州天琴师以男性“魓公”为主,女性天琴师是随着舞台表演的需要而逐渐增加的,而防城、宁明、凭祥三地的天琴师则以女性“仙婆”为主,男性天琴师较为罕见。以民间口头记忆材料进行历时性勾勒是不可或缺的维度,但巫信仰这一民间传统的历史存在也不容忽视。“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巫信仰的观念体系特征来推断,人类社会出现的最早巫师是女性。”[12]这一说法或许为理解天琴师“男魓女仙”现象提供了新的启示,面对壮族天琴艺术不同流传区域的“男魓女仙”现象,显然光靠单线传播一说未免过于牵强。
其二,持“外来传播说”观点的学者以史料记载中的“交趾”以及“鄙俚之词”“安南之音”“喃喃啾啁不可辨”等现象判断壮族天琴艺术来源于越南。对于这一点,有学者就“龙州及宁明、凭祥等地的仪式活动,村民基本可以理解执仪人的唱词内容,……在防城地区的天婆所唱之词,确实如文献所记录的即便为当地村民也不能听解其中之一二”[10]提出了质疑。同样,仙婆在执仪过程中通常会被通灵附体,此时执仪者的身体成为“祖先”“神灵”的依附载体,导致个体进入一种“以己之身,代神之言”的迷幻状态,遂现场给人一种“喃喃啾啁不可辨”的话语形态。此外,“天”信仰是中越边境地区龙州、防城、宁明、凭祥普遍存在的一种共同现象,而天琴的挖掘及命名与壮族音乐家范西姆的努力亦是分不开的[13]。
其三,在“百越民族共有说”方面,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确有一些自称“Ding”的乐器,但对比研究可发现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首先,像壮、傣、布朗、景颇的语言系属不同,它们之间本身语言方面存在着差异。不同语系之间虽然具有发音相同的“Ding”,但其所指未必属同一物象。其次,壮、傣、布朗及景颇的“Ding”类乐器形制结构不同。例如,傣族“玎俄”为拉奏类弦鸣乐器,傣语“玎”为琴,“俄”为黄牛角,“玎俄”意为用黄牛角制成的琴。布朗族“赛玎”是通过不同途径从傣族和境外布朗族传入的弹拨乐器,上设三五个音品,张四条钢丝弦。景颇族的“玎”据说从傈僳族地区传入,是一种三弦弹拨乐器,琴杆表面不设品位,共鸣箱上蒙以牛皮或羊皮[14]。它们虽与壮族天琴同属弦鸣乐器,但彼此形制结构存在较大差异。比较而言,天琴形制因其信仰化属性而表现出其独特性,如:琴筒以葫芦壳蒙以桐木板制作而成,因禁忌要求而不选择表面蒙以动物毛皮;琴杆为具有辟邪象征意义的桑木;琴头刻有龙、凤、鸟、太阳等不同壮族自然崇拜物象。因而从天琴制作形制来说,本身就蕴含丰富的壮族文化意蕴。就此,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以“Ding”自称的弦鸣乐器是百越民族后裔中较为广泛流传的一类乐器,但是具体到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件乐器,显然其文化属性各具特色。
五、结语
综上所述,正如人类学早期对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与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阶段一样,学界对壮族天琴艺术的溯源也经历了从起源到传播的路径探析。梳理上述不同学者有关壮族天琴艺术起源的观点可以发现,当下壮族天琴艺术是通过不断演变“建构”而来的文化事项。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既来自历时性的文化积淀,又离不开共时性层面异文化接触及文化位移的相互作用。“正如‘发生认识论’这个名词本身所表明的那样,我们认为有必要研究认识的起源;……相反,从研究起源引出来的重要教训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15]壮族天琴艺术的起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非某一瞬间的“突现”,本身具有“多重文化时空叠合”[16]的复合文化特征,因此,与其机械静止地从历时性考察入手,罗列一些非连贯的历史记载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不如正视历史传承过程中的多元文化互动过程,将壮族天琴艺术的起源置于发展的社会过程中进行理论观照。
作为中越边境地区的天琴文化现象,其文化“原发因子”显然是根植于壮族传统历史文化而生发出来的,并且在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糅合了汉传道教、佛教文化的元素,形成了壮族地区特有的“男魓女仙”式文化现象。针对现存民间不同区域的不同使用情况,或许可以将其看作壮族天琴艺术文化圈丛共生的特有现象:即以龙州壮族天琴艺术为主文化丛,以凭祥、宁明、防城壮族天琴艺术乃至越南天琴文化为辅文化丛的圈丛文化结构。这种圈丛共生的壮族天琴艺术文化现象既源于受本土传统文化影响形成的原生层结构的存在,亦有传统文化变迁适应过程中文化嵌入再整合形成的次生层乃至再生层的涵化、濡化以及交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