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的“不响”
2024-03-13柳嘟嘟
柳嘟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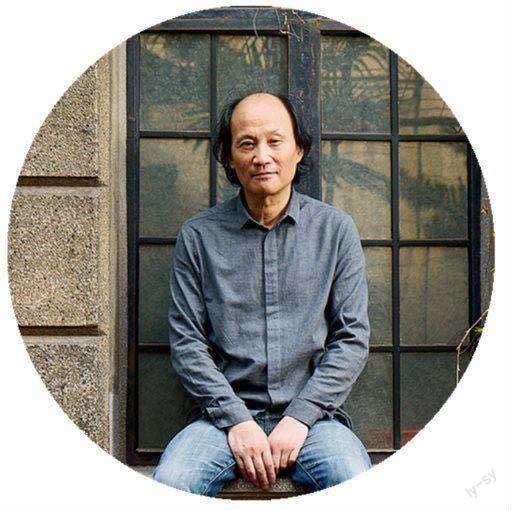
电影《阿飞正传》的最后:梁朝伟在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接下来,他全身笔挺,对着镜子梳头,三七分,讲究……最后,关灯。
在作家金宇澄的眼里,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电影在这里结束,《繁花》从这里开始——阿宝出场了。
当他走进剧集,他便走进了宝总的传奇人生;当他走进书本,他便走进了上海的烟火人生。前者是王家卫,后者是金宇澄。2012年,《繁花》出版,不久之后,王家卫就问他买下了影视改编权。王家卫说:“侬写的,就是我哥姐的生活。”金宇澄被打动。10年之后,王家卫拍的电视剧终于跟观众见面,故事跟原著没几毛钱关系,金宇澄说“没法看”。尽管书粉对王家卫骂骂咧咧,但我依旧想说,这未必不是一件幸事。
走进真实的上海,还得翻开《繁花》,而走进《繁花》,先要走进金宇澄。
1
《繁花》的故事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是金宇澄的少年时代。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因为生产时非常顺利,父母便为他起名为“金舒舒”,可惜生逢乱世,他自打出生就很不舒坦。
金父是落魄家庭出身的少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弃笔从戎,投身抗战,加入了中共秘密情报系统。母亲姚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家里经营着银楼,打小衣食无忧。她与金父一样,是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热血奋进,渴望救国。
1942年7月29日深夜,金父在寓所中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刑讯多日,下肢几乎瘫痪。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远东第一大狱”——上海提篮桥监狱。
金父被捕后,一家人零落了,父母只能通过写信来分享舒舒的成长。到了上学的年纪,报纸上号召全社会支持“民办小学”,父母便为他报了名。哪知这种非正式的小学,条件一塌糊涂,老师都是粗通文墨的弄堂妇女,教室也都是在居民的家里,地点换了又换,实在难有学习的氛围。民办小学教育粗糙,根本不关心小孩的心理健康,“金舒舒”这个名字,也让大男孩屡遭嘲笑,渐渐地,他就开始逃学了。
他的兴趣都在学堂之外,收集植物标本、去小书摊看书、画画、攒邮票、看电影……兴趣多种多样,但人总是独来独往。
直到“文革”初期的某天,他終于提出来要改名,金父一想,“舒舒”的确“过于资产阶级化”,于是才引用了毛主席“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里的一词,为他更名“宇澄”。
1969年,金宇澄16岁,初中毕业,恰逢“上山下乡”开始。在云南和黑龙江之间,金宇澄果断选择了后者,因为“云南一年四季种地,东北冬天不用干活”。而实际上,东北的生活也异常“惨烈”,他在这里种地、盖房、装窑、伐木、养马、做棺材……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
难得吃上一顿肉,他也顾不上文青的体面,一顿哄抢,狼吞虎咽。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涯,给金宇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全是灰色影像。
大时代下的人,命运如同蒲公英,吹到哪儿就落在哪儿,一切都由不得自己做主。
该如何形容那些岁月呢?金宇澄说:“好多年的恩怨情仇,罄竹难书。”
2
东北的蛮荒之地,精神资源也一样贫瘠。知青们彼此交换仅有的几本小说,反反复复地阅读,一册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几乎被盘出包浆。
实在没书可读,金宇澄就开始给上海的朋友写信,聊的尽是东北的生活。为了更加生动,他还在信中配上了大量的插图。朋友读着很欢喜,有一次他在回信中说:“你写得太好了,以后应该可以写小说。”这句话在金宇澄心里,埋下了小小的种子。政策宽松之后,越来越多的知青开始返乡,为了尽快回上海,知青们想尽各种办法。
那时候只要生病,便可以办病退回上海。于是金宇澄在患胃溃疡的一个月中,冒名帮六个上海青年进行胃部钡餐检查,医生说这简直是搏命般的疯狂。1976年,金宇澄终于回城。
此时的他,既是本地人,又是外乡人,难寻自己的位置,兜兜转转,他进入了一家小的钟表企业,整日与滴滴答答的时间作伴。工作之余,金宇澄开始了写作。
早年间他书写的都是东北记忆,看那些作品,你大概会以为他是个东北作家。
1987年,他的小说《风中鸟》获得了《上海文学》短篇奖,第二年,他便被调入《上海文学》编辑部,从此与文字为伴。那是个文学蓬勃发展的年代,金宇澄也想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于是边当编辑边写作。
但同时干这两个活儿非常拧巴,晚上好不容易琢磨出来的东西,第二天一早坐到编辑的位置上一看,怎么都不顺眼,索性,一门心思当个编辑。
30多年过去,小金变成了老金,一晃大半辈子。这期间,时代变了又变,改革开放了,人们有钱了,文学的光也逐渐暗淡了。
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什么东西都在变。
2011年,某个平凡的日子,金宇澄路过上海延安路高架和陕西南路交叉口的人行天桥,无意中看到一个在那里摆地摊的女人。她的岁数很大了,正在卖小孩的鞋袜一类的东西。
“就像文字里说的惊鸿一瞥”,金宇澄认出这个女人是“我青少年时代静安寺地区最有名的一个美女”。这个年少时的模糊印象,被他类比为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那种少年人对年长的美丽女性的迷恋。
“我看到她,并不是想说她怎么潦倒如此,在这个地方摆地摊,而是想表达时间的残酷性。时间能够把你印象中已经记不起容貌的美女,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场景,最终成了金宇澄动笔写《繁花》的重要原因。在此之前,他已经封笔近20年了。有些东西再不记录,就真的消逝了。
2011年5月10日,金宇澄以“独上阁楼”为笔名在“弄堂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写一些杂乱零碎的故事。读者都是上海人,所以他也一直使用着沪语写作。原本只是消遣,但金宇澄越写越上头,有时候会凌晨跑进网吧猛敲键盘。
那些琐碎的、荒诞的,甚至是三观不正的故事,多是他从饭局上听来的,故事中那些被世界忽略的人和事,都真实地流淌在上海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里。
每个故事,都得到了热烈回应,网友每天催着他更新。5个多月的连载,竟积累下一本长篇小说,暂名为《上海阿宝》。2012年,这部作品正式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起名为《繁花》。《繁花》一出,惊艳世人。
3
一朵花开时,大家都觉得美,但没有人去仔细记录她慢慢枯萎的过程。金宇澄说“静安寺美女”并没有成为小说中某个具体形象,而是幻化为一种“好花不常开”的情绪。虽如是,但书中的每一位女性,几乎都有“静安寺美女”的影子。金宇澄笔下,《繁花》中的女性各有各的美,但无论是谁,好像都逃脱不了“好花不常开”的命运。譬如淑华远嫁东北后发疯,李李看破红尘剃度出家;譬如阿宝的初恋雪芝中年“丰腴发福”,弄堂“花蝴蝶”大妹妹被发配到安徽山区;譬如梅瑞沦为“上海滩最吓人的女瘪三”,汪小姐产下不知生父为谁的“双头怪胎”……
用书中的话形容,“讲得有荤有素,其实是悲的”。《繁花》一招一式里的有荤有素,都是上海腔调。
从时间上,以阿宝、沪生、小毛三兄弟为线索,串联起全部故事,奇数章节讲60至70年代的上海,偶数章节讲8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的上海,双线叙事穿插进行,几乎将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囊括。
在区域上,不同于很多写上海的作品逃不出“十里洋场”,《繁花》涵盖了从法租界到“下只角”棚户区的广大地区,不同区域中不同阶层的一百多号人物,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眼花缭乱,繁花似锦。
在语言上,小说罕见地用沪语写作。在国民通晓普通话的今天,很少人会再去用方言写作。而金宇澄说,文学最要紧的就是语言,“读者打开一本书,第一个接触到的不是故事,是语言”。在大家都说普通话、思维也趋同的当下,“用上海话写作,它的语感、它的句式、它的形式上立刻就不一样”。
金宇澄不担心北方观众看不懂。原因很简单,“我觉得最近十多年来,观众最习惯的就是字幕”,既然现在人们看英剧、美剧、韩剧,有字幕就能看懂,那么上海话更不成问题。
作家李敬泽评价《繁花》:“《繁花》延续了《红楼梦》《金瓶梅》的情感调子,它无限地实,又无限地虚,把人生比附于自然,万物荣枯,盛极必衰;现代以后的中国小说中,得到《红楼梦》真正精髓的不是很多,应该说金宇澄做到了。”
2015年,《繁花》成功拿下了茅盾文学奖。
某天,单位门房交给金宇澄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是一份祝福:“你当充分享受你的快乐”。这封信没有署名,但金宇澄猜想,他或许就是当年鼓励自己写小说的那个朋友。人生的际遇有时就在一瞬间。
朋友的一句话触发了他的作家梦,一个无意中的帖子成就了一本著作,再往前看,七年的东北经历也是源于下意识的抉择。
命运是看不清的,难分对错的,金宇澄把这个态度也带到了《繁花》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故事,他只做陈述,不做评判。
所以,《繁花》是亲民的,从人群中来,到人群中去。写就《繁花》之时,金宇澄60岁了,他形容自己是“老妪怀孕”。一时间,鲜花来了,掌声也来了,金宇澄难以招架。他坦言,成就感所带来的幸福只有几秒钟。
剧版《繁花》正在热播,宣传铺天盖地,热搜上个没完,金宇澄却是沉默的,他拒絕了所有采访。无论是舞台剧、电影,还是漫画、评弹,《繁花》的各类改编,金宇澄并不过多介入。“我这个人特别遵守业内和业外的规矩,我不可能去导一个剧或者去做一个电影,因为我不懂这一块,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是完全听导演的……这个剧也是,我不会主动去说哪里不合适,因为这个事我是外行。”
乐观其成。他多次用这个词来表明自己的不介入。这四个字像极了《繁花》小说的主旨:不响。舞台剧导演马俊丰说,“不响”深刻体现了上海人的市民精神——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上海人就不说。金宇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年轻时,金宇澄对作家有着谜之崇拜,以为作家是个全知全能的神。到这个年纪他才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莫说世界之大,能把自己立足的几平方米写明白,就已经十分了不起。《繁花》之后还有繁花吗?
金宇澄不响,他只说,自己的笔不会停下……
改编自《最华人》《十点人物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