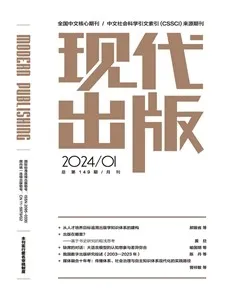再思“出版”:一个传播学的视角
2024-03-09秦艺丹韦嘉
秦艺丹 韦嘉
内容摘要:中国出版研究长期以来在建制与知识的双重层面上面临困境。通过对中国出版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与分析,发现中国出版学界形成了三种有关出版的话语,这些话语根植于出版的历史实践,与国家和业界需求结合较为紧密,从实践层面很好地回应了中国出版业发展面臨的热点与难题,但在理论层面则略显薄弱。从其他临近学科中汲取资源,或有助于拓展出版研究的想象力。从传播研究的视角来看,中国出版研究对传播研究的接受存在一定的偏向与盲点,总体而言更青睐美国大众传播研究范式,对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理论等传播研究的另类范式重视不足,但这些研究范式都曾对出版问题有过关注,有助于出版话语与研究边界的拓展。
关键词:出版;出版研究;学科边界;知识生产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4.01.007
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出版研究不论是在学科建制上还是在知识积累上都逐渐完善,取得不少成绩。但同时,领域内部有关知识问题的讨论也逐渐升温,“出版无学”“出版学是行业之学还是学科之学”等相关讨论长期弥漫于学界。这些讨论的存在,预示着出版研究正面临着知识正当性的焦虑。从这些知识焦虑的表层话语中抽离出来,值得一问的是:这些焦虑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知识焦虑?从何处入手可能克服这一焦虑?
本研究尝试借助作者自身的传播学背景,从传播研究的视角去思考出版研究的知识生产问题。中外出版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比起一个有着固定边界的学科,它更像是一个聚集地,研究者们带着特定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介入对出版问题的研究。由于出版研究的历史并不算长,其他那些更为成熟的临近学科也常被称作“宿主学科”(host disciplines)、“学科之伞”,而充分汲取这些学科的思想资源——或用澳大利亚学者西蒙·穆雷(SimoneMurray)的话来说就是“异花传粉”(crosspollination)——也被认为是拓展出版研究知识边界的方法之一。传播研究可以被视为中国出版研究的宿主学科之一,双方在建制与知识的双重层面上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前者指的是,编辑出版学在中国被置于新闻传播学的一级学科之下;后者则指的是传播理论构成了出版研究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
具体来说,本研究所谓传播学的视角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以出版研究与传播研究的学科交叉作为观察对象,思考出版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与边界移动;其二,以传播研究知识反思史作为参照对象,推进出版研究的知识反思。出版研究今天面临的知识合法性危机及自我挣扎也贯穿于传播学的学科史中。自20世纪50年代末领域早期的参与者发出“传播研究已经枯萎”的讣告后,这种自我挣扎就从未停止。从传播研究的经验来看,即便不能对“向何处去”“学科未来”
这样的问题给出周全的解决方案,但对学科本身的建制史、学术史、知识史的不断反思与总结,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廓清问题,拓展知识边界与学术想象力。具体来说,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1)中国出版研究目前处于何种知识状态之中?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进入出版领域,围绕着“出版”产生了哪些话语与知识范式?(2)出版研究近些年来在与传播研究的“异花传粉”过程中,传播研究中的哪些思想资源被凸显了?哪些被遮蔽了?是否以及为何会形成某种特定的偏向?(3)传播研究思想资源的进入,将如何推进我们对出版的理解?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如此表述存在一定的风险,就好像传播研究是一个具有固定边界的领域。本研究并不具备界定什么是传播研究或什么不是传播研究的能力,也无意做这样的界定——传播研究本身的边界是开放的、松动的,而发展至今,传播研究本身也引介了许多其他学科的思想资源。因此,本研究在讨论传播研究时,指涉的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大致涉及美国实证主义范式的传播研究、批判学派,以及媒介理论,也会将一些在传播学领域已经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纳入讨论范畴。
一、出版研究在中国:建制与知识焦虑
外国学者一般用publishing studies来指称出版领域的学术生产。在中国学界,“出版学”与“出版研究”均有使用。一般来说,讨论作为建制意义上的学科时,多使用“出版学”或“出版学科专业”;讨论知识生产层面的出版学术研究时,则多使用“出版研究”。本研究绝大多数时候倾向于使用“出版研究”的概念,并认为其包含建制与知识两个层面的内涵,这一方面是因为本研究核心关切的问题是出版研究的知识生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相较于出版学,出版研究的说法所指涉的对象更为松散,是一种开放性的描述方式。不过,就实际情况而言,建制与知识层面常常相伴相生,互为关联,因此,本研究也会涉及对出版研究建制层面,即出版学科专业的讨论,尤其是在本部分。
从建制层面上来看,中国出版学作为一门学科专业的历史却并不久远。据考证,汉语体系中的“出版学”一词大概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5年,“出版学”出现在陈伯逵在《南洋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中;1931年,杨家骆在其编的《图书年鉴》中也提出“出版学”。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的出版教育逐渐起步。“文化大革命”后,对于建设出版学的呼吁声日益高涨。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充实印刷技术研究所,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这是出版研究第一次被写入中共中央文件。在这些呼声中,出版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提上新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日程。1983年,武汉大学开办“图书发行学”本科专业(后更名为出版发行学专业),招收本科生,正式开启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篇章。1985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率先响应试办编辑学专业。同年,我国第一个从事出版发行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建立,部分省市还成立了出版发行研究所或研究室。从1986年起,上海、河南、陕西、四川等地的高校开始借新闻、法学、文学的名义招收出版学研究生。与此同时,出版学的教材与学术期刊的建设也在同步进行,为出版教育与学术交流搭建平台。
1993年,编辑学入选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教育部对目录进行了调整,编辑学与出版学自此合并为“编辑出版学”,归属于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之下,列为二级学科。2002年,教育部特批武汉大学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一级学科目录下自主备案设立“出版发行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此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也开始招收出版学博士,逐步推动出版学最高层次学位教育。到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增设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这标志着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正式列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到2019年,全国共有71所高校开设编辑出版专业,19所高校开设数字出版专业。开设出版专硕的高校有28所,另有17所高校依托一级学科博士点招收出版博士。近两年来,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与学界同仁的努力下,出版学科建设工作进一步展开。自2022年7月首次全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会召开以来,截至2023年年底,中宣部、教育部共推动了8所高校与相关单位部门开展学科专业共建工作;2023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又印发了《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自主知识体系。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已然结出累累硕果。不过,整体而言,出版学的学科地位还是颇有些边缘化,比如出版学到现在还未能成为一级学科。其直接后果是,学科的发展速度也受到影响。到2020年,我国开设出版学本科专业的高校从原来的213家锐减至55家,而主要的原因是2011年国家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没有出版学。囿于这一现状,诸多学者提出只有将出版专业独立为一级学科,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该学科发展的桎梏,并身体力行推动出版学的学科建设。
在知识生产的层面上,出版研究也长期经受着“出版无学”的知识合法性危机。整体而言,作为知识领域的出版研究,尽管取得了不少知识成果,但不论是在核心概念、理论范式还是在方法论上都还处于争议之中,算不上成熟完善,“尚未产出令学界与业界信服的重大理论”“未形成多元、独特、成熟的研究方法论”“不重视实证方法,大多数研究停留在传统思辨和经验总结的层面”等知识生产层面的现象和问题依然存在。
出版领域在建制与知识层面上的困境,并非中国独有。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丹尼尔·博斯韦尔(Daniel Boswell)曾讲述了自己的尴尬经历——每每与朋友聚餐,遇到几个新认识的人,被问及职业及专业时,当回答“出版”之后,总是会迎来一阵疑问:“我不知道这还能成为一件事”“你在教课的时候都教些什么”“这就是那些新的学科领域之一吗——而这里所谓‘新指的是不必要的、非法的”。不到十年前,法国学者索菲·诺尔(Sophie No?l)也在一篇文章中坦承自己直到2014年参加某次会议之前都不知道有“出版研究”(publishingstudies)的说法,但他本人已经在书籍出版这个事上做了好几年了,“这意味着我一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事出版研究”,而对法国出版研究进行检索的结果更是令诺尔失望:相关研究成果极少,甚至“出版”与“研究”都没能连在一起形成“出版研究”的固定说法,而谷歌上的检索则更多地将“出版研究”指向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职业课程,而非一个连贯的研究领域。
这些学者的个人化叙事尽管未必能反映出全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出版研究在其所在国家学术系统中的边缘地位。穆雷也曾更为直接地说,建制层面的不稳定,伴随着出版研究职业取向以及由此带来的继发性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严谨性的缺乏,加之弥漫于学界与业界的“书籍之死”的讨论,都使得再去讨论作为研究学科的出版研究是脆弱的。
从一方面来看,建制与知识层面互为关联。建制层面的不稳定与边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出版研究的知识生产。尤其是,尽管编辑出版学被置于新闻传播学科之下,但现实情况是各个高校编辑出版专业设置归属要更为复杂,除少数高校已经建立专门的出版学院,大部分出版学学科专业广泛地栖居于新闻传播学院、文学院、信息管理学院之中,如此分散的分布在给出版研究带来丰富滋养的同时,也往往会带来核心概念界定不清、领域边界不明、研究范式混乱等诸多问题。而作为知识生产的出版研究,若未能生产出具有原创性的知识,也会使得出版学的知识根基不稳,缺乏知识正当性,这也不利于出版学科的发展。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建制与知识却并不始终呈正相关。传播思想史学者约翰·彼得斯(JohnPeters)就曾提示我们区分建制与知识的区别。在对传播研究的知识史进行反思时,他曾雄辩地指责了传播学知识贫瘠的建制性因素,即在传播学的建制过程中大大窄化了传播研究的知识地图与可能性,也就是说“知识”在“建制”的焦虑下丢失了。比如,彼得斯就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众多传播理论并未被用在“传播”建制性领域的“国家建设”上,因为这些理论在地理上分布于其他系部。
而且,建制意义的出版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不仅有赖于学者个体的努力,也非常依赖外部条件,很多时候非个体研究者力所能及。因此,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思考知识生产可能是一项更为基础的命题。基于此,本研究在后面的部分将侧重从知识生产的层面展开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对出版研究的知识生产有所贡献。具体来说,将基于对既有出版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分析,尝试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各种不同知识背景的研究者,进入出版研究領域之后,是如何言说出版的?聚焦什么问题,产生了何种有关出版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在什么社会与知识语境中产生的?
二、有关“出版”的三种学术话语及其盲点
“话语研究不是研究一个事物是什么,而是研究为什么人们用某种方式对该事物进行表述,是什么社会条件导致了这种话语,这种表述是否能够自我证明,它导致了什么后果。”对“出版”学术话语的分析,是理解出版领域知识生产的重要切入口。通过对中国出版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大致区分出目前学术界比较常见的三种有关“出版”的话语,这些话语体现于研究者对“出版”的概念定义中,同时也隐匿于对出版的研究实践中。
(一)作为信息/知识活动的出版
在出版相关的学术研究或词条中,早期对“出版”的界定大都是对出版工作流程、出版业务的描摹。比如,1914年,北洋政府制定了《出版法》,其中对出版的定义是:“用机械或印版及其他化学材料印刷之文书图画出售或散布者,均为出版。”1980年出版的《辞海》对出版的定义是:“把著作物编印成为图书报刊的工作。”再比如,1988年出版的《汉语大字典》对出版的定义则是:“把书刊、图画等编印出来。”罗紫初将类似的界定总结为,将出版活动视为印刷工作,并认为这种界定是长期在计划分工模式运作条件下形成的,缺乏对出版内涵的关键部分也即出版目的的描述。
此后的界定则更加突出对出版目的的描述,即进一步将出版明确为一种信息活动,目的则是信息/知识的传播与传承,从而形成了“出版实践描摹+出版目的”的表述方式。这种表述方式相较于上述界定更完整,并在一定程度上抽离了具体的出版实践,整体上强调出版的信息活动属性。张志强曾梳理了20年来的11本出版学概论中关于“出版”的定义,指出关于“出版”概念的论述出现了逐步强调出版的信息传播功能的趋势,认为这是对出版实践新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反映。从“出版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到“出版是将文字、图像或其他内容进行加工整理,通过印刷等方式复制后向社会广泛传播的一种社会活动”,再到“数字出版是以数字技术对传统文本内容进行转化和呈现,将数字技术与内容融合,以内容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文本传播活动”。可以看到的是,尽管二十余年来出版的形式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革新,但其作为信息/知识活动的话语线索始终绵延。
将出版视为信息活动的话语紧紧围绕着出版实践展开,出版实践的历时变迁也会带来这一话语中具体概念的变化。比如,所谓信息活动指的是编辑,还是同时也包括印刷、发行等其他环节?1950年,我国公布的《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提出将国营出版印刷发行企业进行分工与专业化,划分为三类独立的企业单位,即出版企业、印刷企业和发行企业。如此分工的结果是,编辑工作成为出版企业的核心,印刷与发行活动则不再属于企业的职责,因此也逐渐衍生出狭义的出版概念。将编辑视为出版核心的看法,就体现于叶再生的观点中。在1988年出版的《编辑出版学概论》一书中,叶再生就强调之所以使用“编辑出版学”而不是“出版学”,是因为“出版学的重点是图书编辑学”。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体制改革后,在市场化浪潮下,编辑、制作、发行等环节渐渐开始被整合,出版的概念也逐渐开始发生改变,销售、创作、评论、阅读等环节都开始被整合进出版的概念。
而新媒介技术的出现,也催生了对有关出版具体概念与研究对象的再调试。比如,早期出版依赖的技术手段是印刷术,对于出版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研究也都凸显印刷的面向。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随着出版物质载体变得多样化,对“印刷”这一环节的表述,也出现了“印刷或非印刷”的转变。又如,在新媒介技术之前,出版对应的出版物主要是书籍、期刊等,不需要进行专门的区分。
而新媒介技术使得信息、知识的传播与流通更为便捷,为了将出版与其他文化实践区分开来,学者们逐渐开始强调出版的知识属性,“作为知识生产的出版”这一表述也就开始增多,从而出现了作为信息活动到作为知识活动的出版这一细微的转变。
将出版视为一种信息/知识活动,一方面是对出版实践客观描述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言说者的知识、学科背景有关。许多将出版视为信息/知识活动的学者,都在一起程度上受到传播研究的影响。比如,师曾志就认为出版的本质属性是传播性,而出版行为、出版过程以及出版系统可以说是传播行为、传播过程和传播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一视角也见于李新祥的著作《出版学核心:基于学科范式的范畴、方法与体系研究》和《出版传播学》。
以传播之眼来看出版,出版就成为信息/知识活动,而对出版的研究自然而然就成为对这一信息/知识活动过程及其要素的研究,传播研究中的诸多理论,如传播的“5W模式”“使用与满足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等,也就成为这一面向的出版研究的理论资源。比如,李新祥将出版学划分为宏观出版学和微观出版学,在其构想的微观出版学中,就基本以5W模式统摄起对出版的理解,出版由此被视为出版者、作品、出版物、发行渠道、接收者这五个要素的组合。而在新媒介技术与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播的5W模式在出版领域的应用也不断被重新阐释。除5W模式以外,许多其他的大众传播理论亦被引入出版领域,比如夏德元曾详细分析了“拟态环境”“议程设置” “ 意见领袖” 如何可以嵌入出版的“告之”“造势”“促销”及“鉴赏”等环节之中。
作为信息/知识活动的出版,首先体现的是中国出版研究降生于出版业之中的历史渊源,早期的出版话语也多是对出版实践的描摹。此后,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加之传播学的影响,出版被进一步抽象地描述为信息/知识活动。作为信息/知识活动的出版,基本上也涵盖了对出版实践的描摹,最终形成“出版实践描摹+出版目的”的表述方式。在出版研究领域,作为信息/知识活动的话语最为基础,因为不论出版被视为其他的什么,它都首先必须是对出版实践及其基本属性的总结与描述。
(二)作为事业/产业活动的出版
如果说围绕具体的、微观的出版实践,形成了作为信息/知识活动的出版这一话语,那么,围绕更为宏观的出版业,则形成了作为事业/产业活动的出版的话语。这一出版话语将出版视为一个事业或产业,突出其意识形态与经济属性,并引入经济学、管理學等学科的理论资源对其进行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版业亦是如此。到1956年,所有私营出版业、印刷业和发行业都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新中国出版体制全面建立。改革开放之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从1980年开始,国家出版局开始着手推动发行体制改革;1984年,全国地方出版工作会议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讨论出版社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相关改革进一步提速。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出版业改革在这一大背景下继续展开,开始推动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组建出版集团。
作为产业活动的出版,也是在这一社会语境中出现的。在这一视角下,出现了包括出版体制改革、出版产业经济、版权等诸多面向的学术研究,这些研究大都以经济学理论、信息学理论、管理学理论和市场营销学理论作为资源,凸显出版的经济属性,为出版产业的发展与管理提供政策建议。比如,周蔚华较早地开始从事出版产业研究。他在《出版产业研究》中,就运用产业经济理论、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管理理论等资源对我国彼时的图书出版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集团化、产业管理等问题展开了详尽的分析;近些年来,数字技术的出现给出版产业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研究者开始关注数字出版的未来,或是从数字营销的视角,探索出版社的数字营销策略;或是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提出产业融合的发展思路与具体路径;或是从产业管理视角,回应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出现的法律法规不完善、行政管理色彩过浓等问题。
在市场化的浪潮中,出版的经济属性相较于以往更为凸显,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则相较以往有所弱化,但也并未离场。2015年,《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就明确了以社会效益为先的“双效统一”原则,进一步深化出版企业生产经营制度改革。尤其是,当作为产业的出版在经济利益的驱逐下,生产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出版物时,对于出版意识形态属性的强调又会重新被提到重要位置,以社会效益为先的“双效统一”原则也成为出版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正是在这一语境下,方卿等学者从出版价值、功能和构成等理论问题切入,从经济、文化等视角分析了对出版价值进行引導、干预的必要性以及方法。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出版也始终与“意识形态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中国式现代化”等话语与实践相联系,以讨论出版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意识形态功能。
作为事业/产业活动的出版,突出出版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属性,与国家需要与业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很好地回应了中国出版业体制与技术转型中遇到的问题与困境,在出版话语中占据着主流的位置。
(三)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物的出版
作为信息/知识活动的出版与作为事业/产业活动的出版,相对都比较侧重就出版谈出版,在将出版与更大的社会语境进行关联的问题上着力较少。将出版视为社会文化建构物这一话语的出现,是对前述两种话语的补充。事实上,从出版的历史实践来说,自古以来,出版在中国就被视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文化活动,如“盛世修大典”在中国就有悠久的传统。但真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将出版作为社会文化过程进行的研究,则出现得相对较晚。
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物的出版,往往将出版视为一种社会文化过程,一方面,它被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形塑;另一方面,它也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力量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形塑作用。这一话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书籍史、传播学等学科的影响。比如,彭建炎早在《出版学概论》中就曾专辟一个章节“出版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功能”讨论社会因素对出版的影响以及出版的社会与文化功能,而且在其规划的出版学学科地图中也专门为“出版社会学”留下了位置。后文将详细论述,早在这一时期,彭建炎就已经注意到了多本文化社会学的著作。
再比如,师曾志在《现代出版学》中也强调借鉴传播学理论去研究出版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的地位、作用,了解出版系统与其他系统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各方面因素对出版的影响。张志强在《现代出版学》中也专辟一个章节“出版与社会”,讨论出版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从自然条件、国家政权、技术条件、文化环境、宗教五个方面探讨了社会对出版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从“推动人的社会化”“延续社会文化”“推动人类实现思想解放”“国民经济重要的产业”四个方面总结了出版之于社会的影响。近些年来,中国亦有不少学者受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等学者的影响,提出不能仅仅将出版物视为信息产品、文化商品,还要“从人类意义交流整体网络之高度,将出版物视为一种由出版者和作者、读者共同构造的意义交流空间”。出版史研究特别是书籍史研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在年鉴学派、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下,逐渐从过往相对较窄地考察书籍的版本目录和生产流通,转向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去考察围绕着书籍的活动,社会文化的视角开始凸显。但如有学者已经指出,在整个出版研究领域,出版的社会文化视角在出版史中最为凸显,“社会文化”的转向未能惠及整个出版学。不过,值得期待的是,在这些学者的努力下,中国现代出版研究、数字出版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或呼之欲出。
(四)“出版”学术话语的偏向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有关“出版”的话语虽然各有侧重,但互有交叉,并不彼此割裂。但在整个出版研究的学术史中,三种话语不平衡。其一,作为信息/知识活动的出版这一话语最为基础。其二,受彼时社会语境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事业活动的出版占据主导位置。21世纪初,当周蔚华开始关注出版产业时,相关研究还非常少,作为产业活动的出版这一话语非常边缘。但在国家整体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背景下,近十多年来的情况已然发生变化,出版研究领域在这一期间逐渐壮大,“出版产业”“版权”等问题则逐渐成为出版研究的热点之一,作为产业活动的出版这一话语从边缘位置向中心移动。但与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作为事业活动的出版这一话语始终在场。其三,将出版看作社会文化建构物的观念基本处于隐而不显的萌芽状态,如上文所言,尽管早在21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出版社会学”,但在整个出版研究中并未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而且相关论述更多停留于观念性的层面,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也并不多见,出版研究的整体学科范式偏向产业范式,社会文化视角在出版研究中的基础较为薄弱。
就此而言,出版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诚然,回应国家社会需求是学术研究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但如果在研究思维上与业界捆绑过紧,又缺乏其他视角的平衡,则有可能缩小学术研究的空间。显然,这并非中国出版研究独有的特征。诸多国外的出版研究者亦观察到,“出版研究深深地适应于主宰着产业参与的经济与实用主义考虑”,许多产业研究与出版职业信息指南的目标“不是对出版业的做法提出批评,也不是提出行业规范——除了对利益最大化的普遍追求以外”,“鉴于图书出版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文学毕业生可能去干的闲职,这类职业指南通过突出该行业的商业而非美学优先事项来进行过度补偿”,“它与媒体经济学中最具经验主义色彩的一极异花传粉,产生了社会科学风格的图书行业定量调查”。
法国学者索菲·诺尔(Sophie Noel)也颇为担忧出版研究的知识生产,即它与商业组织捆绑过紧,缺乏科学研究的传统——一套研究技术、方法与理论。诺尔当然不是鼓吹学术研究要脱离外部世界,但他坚持认为,“知情的分析、带理论武装的批判性观点使学术研究和教学变得宝贵”。在诺尔看来,出版研究的未来就应该像达恩顿对书籍史研究的畅想一样:在规模上具有跨国性、在研究方法上具有跨学科性,但同时不能失去概念的一致性。这与穆雷强调的“异花传粉”不谋而合。
传播学长达数年的自我反思运动也提示我们保持领域边界的开放性对于知识生产具有重要意义。1959年,美国传播学的早期参与者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在一篇文章中宣告了传播领域知识生产力的枯竭,彼时致力于传播学建制的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随即反击了贝雷尔森的这一论调。但贝雷尔森的断言却犹如“鬼魂”般引发了传播领域持久的反思:1983年,《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出版了专刊“领域的躁动”(Ferment in the Field),邀请10个国家的41位作者撰写了35篇文章,就传播研究的方法论、知识角色、知识特性展开讨论;1993年、2018年,该期刊再次推出反思性专刊,不断探索着传播研究的知识边界,吸引着更多研究者参与讨论,施拉姆当年对传播学设置的边界不断遭受挑战,更多理论资源进入传播研究领域。那么,对于出版研究来说,一个有趣的问题就出现了:它能与什么知识传统进行穆雷所说的富有成效的(fruitful)“异花传粉”呢?为从知识的维度确认出版研究的学科位置,尤其是探究出版研究如何可以从其现有的宿主学科汇聚起来,穆雷曾专门对出版研究的学术地图进行了考察。他将当代图书出版研究最为集中的五个节点总结为:产业研究和职业信息;个性化叙述,如回忆录、自传、传记和出版社历史;书籍史;传播、媒介、文化研究和社会学;民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研究,并详细分析了每一个节点出版研究的知识生产问题与可能。穆雷的分析显示,由于方法、学科与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些研究节点之间的关联尚未被完全打通,这就阻碍了出版研究的知识生产。
穆雷的梳理并不包括中国出版研究,但中国出版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中国出版研究的 “学科之伞”多元而丰富,如新闻传播学、编辑学、文学、信息科学、管理学等。从上述梳理出版研究的三种话语来看,这些学科及其相关理论资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出版研究者关注和吸收,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盲点。下一部分,作者将主要从传播学的视角,详细分析这一盲点的形成以及可能的接合——媒介、文化研究与出版研究之间有很大的“异花传粉”潜力。
三、以“学科之伞”拓展出版的话语与研究边界
总的来说,中国出版研究对传播学的挪用大致呈现出三个特征。其一,在研究理论资源上,较多受到二战以来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影响,尤其是颇为青睐拉斯韦尔的传播5W模式、使用与满足等理论。但这并非传播学的全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众传播学逐渐受到其他研究范式的挑战,传播研究也进入了相对多元的发展阶段。发展至今,传播研究大致可以被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的路径:美国大众传播研究;批判研究,包括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理论。相较其他几种研究路径,出版研究更多受到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影响。
其二,对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挪用,亦存在着一定的盲点。以对出版功能的研究为例。“传播的功能”是传播研究主流范式的一项经典议题, 已经有诸多学者就这一问题提出过理论假设。其中,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Lazarsfeld)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的功能说颇具批判色彩,包括“社会地位赋予”“社会规范强制”“麻醉的负功能”,这代表着社会学大师默顿早期为美國传播研究贡献的另类视角。但这些功能说几乎未能进入出版功能研究的视野。出版研究领域对于出版功能的讨论,目前还大都是经验总结,未能激发出对这一问题的经验研究与批判性反思。而且,尽管在研究范式上多受传播学主导范式的影响,但出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又相对不太重视实证方法和中层理论的问题,仍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停留于现象归纳、经验总结的层面。
其三,对传播研究的其他研究范式重视不足。有趣的是,传播研究的其他范式都曾触及出版研究的核心问题。比如,已在传播学中产生较大影响的著名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对于文化生产场的研究《艺术的法则》也涉及出版问题。具体来说,布尔迪厄是在讨论有关“作品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时提到出版问题的。布尔迪厄强调有关“作品的科学”不仅要考察那些直接生产者,还要考察全体行动者和制度,其中就包括所有与出版相关的行动者与机构,出版由此作为重要力量参与作品的生产。
又如,美国学者珍妮斯·A.拉德威(JaniceA. Radway)在其研究现代通俗浪漫小说阅读的作品《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中,也特别从书籍的出版而非小说文本或是阅读活动说起,因为在拉德威看来,书籍的购买与阅读并非仅仅关涉文本与读者的活动,而是根本地受到出版的物质性影响,由此,出版作为拉德威所说的“一个具有社会组织性的生产与分销技术”,便参与了意义的生产。再如,也有学者注意到,法国学者雷吉斯 · 德布雷(RégisDebrey)就是在研究印刷文化与宗教传承关系中提出媒介学的概念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出版学与媒介学的关系更近。
事实上,这些思想资源在早期曾不同程度地进入中国出版研究者的视野。比如,林佩就观察到,罗紫初就曾进行过与德布雷相似的表述,即将出版作为一种中介,并将其视为一种传承,“人类积累的精神财富,只有通过一定的中介,被编辑、印刷、制作成了物质载体形态的产品——图书、期刊、报纸以及电子音像出版物,才能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个中介,便是出版。它把人类文化物化在一定载体上,使成果跨越时空界限,一代代传播下去”。而如前文所言,文化社会学的著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进入了彭建炎的视野。在其1992年出版的《出版学概论》中,他就已经注意到《传播媒介的垄断》(本·巴格迪坎,1986)、《媒介社会学》(戴维·巴特勒,1989)、《文化社会学》(罗贝尓·埃斯卡皮,1987)、《文化社会学》(司马云杰,1987)等文化社会学与媒介社会学的相关著作。
由此,林佩曾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既然早期出版研究者已经采用媒介学范式思考出版学问题,为何在近十年的研究中却鲜有相关的代表成果?这一提问也适用于其他研究流派在出版研究中长期的缺席。
林佩本人并未对这一问题给出解答。本研究尝试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一方面,从出版研究的角度来说,与业界的紧密关联,加之早期出版研究者学科背景较为单一,或使出版研究对媒介理论、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学派并不敏感。另一方面,尽管对出版问题有所关注,但客观而言,许多研究领域的核心知识兴趣有时候又将出版的诸多重要对象或问题排斥到边缘。比如,传播与媒介研究对于新媒介技术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就与作为旧媒介的书籍有所冲突;又如,许多书籍史研究都将出版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列表,但其特定的时间意识又往往与现代出版有所冲突;再如,文化研究也对书籍出版有所关注,但整体而言更关注其他诸多形式的流行文化,尤其是强调从受众与文化消费的角度进行研究。
结果是,这些领域对于出版问题的关注如果要被移入现代出版研究中,往往存在着较高的学科与知识门槛。而且,这些研究领域之间本身也都存在一定壁垒。穆雷对此的观察比较敏锐,也适用于中国的情况。比如,书籍史与媒介、文化研究在意识形态与哲学层面存在一定的契合性,但双方长期处于互不关心的状态,当书籍史研究要讨论现代出版的问题时,往往就没有吸收媒介、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而现代出版研究也常常被割裂开来,一边是书籍史研究,一边是媒介、文化研究,未能实现思想与方法资源的融会贯通。
这些壁垒都给出版研究与临近学科领域的接合造成困难。出版研究要想获得富有成效的接合,显然就需要去打破这些领域之间的学科壁垒,从而为我所用。可以观察到的是,这种接合正在发生。近年来,许多新闻传播学背景的研究者开始从自己的研究视角涉足出版研究。其一,批判研究。比如,曹晋、张志安等就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切入对出版的关注。如果说以前的出版研究更多是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出版产业的转型与效益问题的话,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则更多从批判的视角切入出版产业的版权与出版从业人员的劳动问题。由此,中国出版产业改革发展过程中更为复杂的面向被呈现出来。
其二,媒介理论。媒介理论主要聚集媒介本身,对长期关注媒介内容的传播研究有所修正,在传播学内部持续掀起层出不穷的讨论,重构了传播学既往对“媒介”“传播”等核心概念的认识。近些年,这些讨论也开始在出版研究领域发生,比如,有学者呼吁以媒介作为入射角拓展出版研究的知识边界。在新的视角下,“出版技术”“阅读”等出版研究的基础问题也以新的方式被探索。比如,在出版研究中,印刷术等出版技术一直是重要的研究面向,但此前的研究大都较为传统,多从史学的视角展开,注重史料的整理与发掘,媒介理论的进入则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视野,吴璟薇等以“文化技艺”为切口对中文打字机的研究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再比如,媒介理论的进入也给阅读研究带来了新取向。以往对阅读的研究多使用问卷调查、实验法、深度访谈法等对(数字)阅读主体、(数字)阅读动机、(数字)阅读素养、(数字)阅读效果等问题进行研究,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引入媒介哲学的视角,重新思考阅读与数字阅读的问题。比如,张文彦从柏拉图、卢梭、阿伦特、德里达、斯蒂格勒、弗卢塞尔等学者入手,梳理出了一条从线性文本时代到技术图像时代的理论脉络,对当下数字技术带来的阅读问题进行了回应。传播学边界的拓展,相应地带来了传播话语的拓展,不论是罗伯特·T.克雷格(Robert T.Craig)总结的“作为话语实践艺术的传播”(修辞学传统)、“作为通过符号的交互主体调节的传播”(符号学传统)、“作为他者经验或是对话的传播”(现象学传统)、“作为信息处理的传播”(控制论传统)、“作为表达、互动与影响的传播”(社会心理学传统)、“作为社会秩序(再)生产的传播”(社会文化传统)、“作为话语反思的傳播”(批判传统),还是刘海龙总结的“传播是传递”“传播是控制”“传播是游戏”“传播是权力”“传播是撒播”“传播是共享和互动”,都反映出传播研究在多元路径滋养下的丰富话语与研究实践。
同样,一旦出版研究引入这些更为多元的思想资源,也会获得对于“出版”的新理解,并开启许多新的研究面向。粗略地说,其一,在文化社会学、文化研究的视角下,“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物的出版”这一话语或许会更加凸显。其二,援用刘海龙对传播话语的分类,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派都对传播中的权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些思想资源之下,则产生了“作为权力的传播”这一话语。同样,以这些思想资源观照出版研究,或许也会产生“作为权力的出版”这一话语,并开启丰富的研究面向。比如,利用相关的分析框架与工具去研究书籍的生产层面(通过政治经济批判)、文本分析层面(通过符号学、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范式)以及消费层面(通过受众民族志以及粉丝行为)。作为诸多身份政治研究的“学科之家”,文化研究亦能够提供丰富的工具去关注印刷文化中印刻的性别、种族、民族、性等维度的差异秩序。此外,更加关注政府文化政策的文化政策研究亦可以提供不同的视角去分析重要的书籍产业政策,如政府发起的文学奖、书籍津贴、作家节、图书馆政策、版权政策等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与文化研究的接合,将有助于促进出版研究的人文转向。穆雷在对出版研究的知识地图进行梳理后,最为强调的一点是“出版研究必须通过与当代文化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对话来参与主流的人文辩论”。在穆雷看来,这一点对于当代出版研究来说,是非常缺乏的。这与中国出版研究的情况一致,即中国的出版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并未参与穆雷所谓批判性的“文化政治”的讨论。而一旦我们纳入文化研究、民族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视角,出版就不再是被动的渠道,它本身就变成维护或挑战意识形态结构的东西。
其三,在媒介理论的视角下,或许也会促成出版话语的媒介转向。与传播研究相似的是,出版研究也长期存在着重内容、信息、文本而轻媒介、物质的特征。如果引入媒介理论,我们或许可以不再仅仅将出版描述为“通过可大量复制的媒介实现信息传播的社会活动”,因而也就不再仅仅去讨论这种信息传播的效率、社会功能;也不再仅仅将出版描述为由社会文化建构又反过来建构社会文化的过程,因而也就不再仅仅去讨论其社会文化意义或进行政治经济学的与意识形态的批判;除此之外,我们或许还可以将出版视为一种技术过程,去考察人类主体性与技术自主性互动博弈中组织起来的知识生产、传播与阅读实践。
总的来说, 出版研究领域已经处于知识性的躁动之中。在这种躁动中,“出版”与出版研究的边界不断被拓展。不过, 从传播学知识反思史的后来之见来看, 我们或许还可以将思考继续向前推进一步。尽管上文提及的1 9 8 3 年“ 躁动” 专刊及此后的持续反思拓展了传播研究的知识边界,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个直接的知识后果,即“传播”这一核心发生动摇,尤其是不同研究路径的学者倾向于在自己的话语体系内捍卫某种知识正统性, 领域逐渐处于一种“创造性的混乱”状态之中。这种混乱也使得一些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创造共识和对话,以使传播理论成为一个连贯的研究领域(coherent field of study)。
且不论这种一致性建构的努力是否真的能够实现,这至少提示我们在从事出版研究领域的知识反思性活动时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不同的研究路径、不同研究方法并非完全互斥,而是可以积极寻找可通约性。比如,尽管作为产业活动的出版与作为权力的出版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于出版的理解,但出版产业研究所擅长的对于出版与图书市场的调查与分析也许能够为批判研究提供扎实的经验材料。其二,如前文已经提及的,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理论等研究路径都有其特定偏向的研究对象与问题兴趣,出版研究领域与这些研究路径的知识兴趣客观上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吸收这些理论与研究资源的时候,应注意区分出版与其他文化实践的差異,警惕对理论的照搬或是无限泛化出版的边界。
结 语
本研究通过锚定当前学界较为常见的三种有关“出版”的话语,大致回溯了出版领域的知识生产状况,并从传播学视角对传播研究资源在出版领域的接受偏向以及未来可能的接合展开了讨论。需要说明的是,使用“宿主学科”“学科之伞”的说法,并不是暗示传播研究比出版研究更具有知识正当性,而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出版领域的知识生产,因此自然而然有了从其他学科看待出版研究的优先视角;其二,客观而言,出版研究的确以传播理论作为其学科的重要理论脉络之一。
这也意味着,将传播研究视为出版研究可以借助的“宿主学科”也并不是固化“从传播学到出版研究”的单向知识流通,恰恰相反,这种知识流通完全可以是双向的。事实上,出版研究完全不必被其他研究传统所束缚,而是可以主动地在一些中间地带有所作为。如穆雷提示我们的,媒介、文化研究对精英文化/流行文化秩序的挑战使其更偏好浪漫、犯罪、科幻等类型的小说题材,而文学题材小说经常就被遗漏下来成为学科真空,出版研究则可以对此有所作为。就出版研究而言,学科与领域的交叉地带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进而贡献原创性知识,与其他领域的既有理论形成对话,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缓解知识焦虑的问题。
最后,囿于作者的视野与学识限制,本文所谓传播学的视角是个体性的,或许也不够完整,而列举式的论述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讨论的深度。就出版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流与对话而言,未来还需要更多细致的理论讨论与经验研究,唯有这样才有可能产生真正富有成效的“异花传粉”。
[作者秦艺丹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出版学院)讲师;韦嘉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1 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