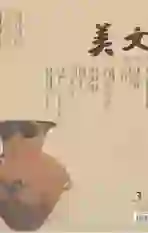猫不理
2024-03-08高悦坤
高悦坤
《猫不理》分为“成”“住”“坏”“空”四章,描述无知觉的求生本能和与之相伴的愚昧堕落。化用传统武术形意拳的意蕴,以招式动作引出情节和人物成长,武术自身的连续性正是人物行为的惯性。饥荒的背景下,主人公弘狸儿不仅感受到肉身的饥饿,也隐约对寻根本身产生怀疑,他被母亲托付给师父,但拜师求学并不只是为了活命,轻功的“轻”没有终点与指向,佛家的善也没有来由和去处,弘狸儿在无往无终的时间中保持着悬浮——他活在饥饿和清醒之间,将最强的力道用在最细微之处。在选择落地杀生的一刻,成长的动机与寻根的本能已经熄灭,但他并不走向堕落,成长的动机被视作一个幌子,弘狸儿学猫吃猫,传承下的唯一信物是荒年大地生生不息的饥饿。小说的亮点在于对天津文化和传统武术的运用,语言上同样追求北方口语的简白生动。
-成-
米汤清,五粒碎渣沉在乌木钵底。薄薄一层盖着米的水,在柴火上搅过,就成了师父说的乱乎粥。到观心寺的第二天,弘狸儿习惯了新鲜的一切。在这出家,好歹饿不死他了,舔干净这几粒杂米,指不定又能多活一会。
这些天,弘狸儿和师父吃了很多饭。离家的时候他们饥肠辘辘,一路从巫清辗转到锦南,渐渐远离了灾荒,肚子也慢慢填上了。过久了没有粮食和日照的日子,身上总没精气,两人涣散着一寸寸挪进了城。晌午过城门,下午才找到观心寺,金黄的太阳直勾勾对准他们,晒得背上似乎多了沉重的东西。师父习惯颔首行走,他步速快,僧袍不当风,总显得人前胸贴后背。师父盯着脚面弓身疾行,衣袖下夹着徒弟一条胳膊,弘狸儿那半边身子都觉得松快了。
咸鲜香气像凭空敲了声金锣,鼻子闻一下就能被勾住。是肉和酱的气味,弘狸儿仰着脖,使劲把香气全吸进鼻孔里。油亮亮的众生肉喷香扑鼻,弘狸儿错过鼻孔看见,师父也一节节把头昂了起来。
“和尚,这可贵。”
“来碗汤就行。”
店里卖罗汉肚(津菜,狗不理包子的酱制馅料。因肉皮层次分明,形似罗汉的肚子而得名。紧固不散,光泽透明,口感咸鲜,适口不腻,酱香醇厚),师父没要,过会端上来一碗浮着油星的末子汤。汤原本不卖,东家吩咐厨子用它做伙食,正好煮面,沾了肉腥的手擀面浸一浸汤水,敦敦实实挂上芡,菜码往里一拌就能养活一屋子伙计。
师父和弘狸儿绕着碗边一人一口,很快喝得油光满面。汤是烫的,师父咕咚一大口,弘狸儿吸溜一小口。小孩想,师父的嘴没准是一锅灶,赶路的时候,他坐在树墩上慢条斯理啃玉米,金黄的米粒越嚼越香,香得弘狸儿以为这就是师父要教的本事。师父嘴软,话说不响,吃起饭来,舌头像个喧腾的笼屉,饭菜到嘴里像又被熥了一遍,嘴巴一张一合,食物被慢慢翻搅,仍是热气腾腾的。师父吞饭反而像出锅,他总嫌吃得不够烫,弘狸儿担心,再烫点牙花子也要化了。
出家前,弘狸儿最后一眼望见家里乌糟糟的光景:太奶奶仰面横躺在弥勒榻上,身子刚被掰直,眼没闭全,嘴里挂着几颗苍耳。弘狸儿那时还叫着他的俗名钟生古,原本他排行最小,灾年之后,一场没由头的大火烧干了家里的粮仓,官客堂客们一哄而散,仆从逃也似的纷纷消失,后来家庙也蛀空了,只有家贼偶尔重游故地,大人们没力气抓贼,只抓一根梢棒,对着屋顶嚷白嗓子。
一年之间,钟生古的哥哥们一个接一个当起了长孙,轮到最后,小幺成了老大,裹太奶奶的织锦缎终于传到了钟生古手上——他把褥单铺展,压在老太太身下,提起两边覆上全尸。包太奶奶,好像包一块糖纸上的龙须酥。
喝完汤,師父抿嘴坐了一会。他把胳膊藏在袖子里,不着痕迹地摸到包袱,捻住一角掂掂重量,还对,两根硬邦邦的金条在里头。师父安了心,手依旧袖在那,端详起小徒弟弘理,这小子精瘦,跟腱长得惊人。头次见他,弘理在三进院正房的太师椅上坐着等死,入秋有一阵子了,天还是燥的,弘理光着身子罩在一件过大的长衫里,光腚牢牢坐在椅面上,小腿长长垂下去,远看活像个祭品。
他是明白死的。巫清的天燥了不是一两日,田间滴雨未下,颗粒无收,他的家人挨着饿、等着米,想着差不多的事,一个挨一个得死。与其逃荒死在街上,不如等县太爷救命,没有县太爷,还有大将军、大总统,这两个不管用,起义军和革命军不也说要挽救国民?连这个青那个白的教也会扯两嗓子治病救人的莲花落。再不济,中国兵不管用,外国人也成,租界的洋人既可恶又惹不起,可活得实在舒坦,要是他们再勤快点,占领了整个海河府,钟家人就有了在仇恨中安逸苟活的希望。
但谁也没来,世道和钟家十好几口一样,没打算进来,也不指望出去。三进院和海河府里里外外缄默着,默契得欲辨忘言。到了钟生古不得已被母亲送给和尚的当口,钟家算是彻底没了,钟鸣鼎食的钟,钟鼓馔玉的钟,钟灵毓秀的钟。
没了钟家,钟生古更不必叫这个名字,出家人先舍弃在家姓,法名由师父起,弘字辈,另一个字要取得天然巧妙,少了点起名赐号的机缘。师徒头回相见,两下里都还迷糊着,师父瞅见地上的香灰纸屑,想起幼时在家,年节下也是这么一地炉香屑、符纸灰,巫觋忙得团团转,嘴里唱得好听:“风调雨顺,天理昭昭。皇天后土,乾坤浩浩。”
叫他弘风、弘雨、弘昭、弘浩?没等师父开口,钟生古从呆坐的姿势里一跃而起,身形晃过眼皮,轻得像一根睫毛跌落。眼前的太师椅空了,找他,先察觉的却是眼珠转动的仪轨,视线在身后追捕,他却能反将人眼一军。钟生古前掌着地,落在几步外的莲纹砖上,没出什么动静。
这活脱脱是只狸猫。他侧身,半边先越出门槛,再用眼追,人早往西厢去了,他母亲住在那里。钟生古那截细长的小腿,像猫尾巴扫过师父的鞋袜,出家是一回事,有这样的天赋,不学轻功太可惜了。
叫弘理吧,小名就叫他弘狸儿。
-住-
观心寺的门推不开,弘狸儿爬上院墙,看到门槛上的野草长了有一人高。师父说,这是他师父当初收留他的道场。老师父圆寂的第八年,新住持擅作主张,包庇了一小撮逃兵,赶上那晚巡夜的警察和商户赌气,偏要临街挨户搜查一遍,这就抓了和尚的现行。观心寺上下全被警察厅押走充了苦力。
寺空了太久,天王嘴里结了蛛网,韦陀杵上缠着蛇皮,燕子把空巢遗落在结跏的佛足之间,狐狸脚沾了炉灰,在草席上留一片杂沓的印痕,到处是灰烬和野蓬,压灭了壁画上的光相,连菩萨低垂的眉目,也分不清哪段是眼珠,哪截是眼白。
翻墙进来的师徒,只留了一扇后角门出入,正门的闩被销死。锁门是当务之急,安顿下自己,靠的是闭气醒神。庙里缺少梯子,师父找来一根蜿蜒的虬枝,他把住枝干,让弘狸儿向上攀爬,拂尘掸扫过的飞灰细雪一样落在他的眉毛上。
大殿横梁上筑着鸟巢,弘狸儿伸手一掏,卵还在里头。师父让他把巢搬下来,他用腿脚稳着虬枝,一只手伸过来托住泥点子凝的窝。弘狸儿脱手,师父接歪了一点,巢穴和鸟胎碎在有裂纹的砖石上。“这都臭了。”师父用树叶拾掇干净鸟蛋,到黄昏,一对斑鸠先后飞进殿门,在梁上单调沉重地鸣叫了一会,天擦黑时又飞走了。
钟常氏的丈夫,两个月前演练香店鞭( 香店拳的器械门类之一,由乾隆年间武僧智远传授香店香场老板和工人的罗汉拳发展而来)时,被撩乱的错力牵住脑血,当下就中了风。钟家人习武学文有多板正,钟常氏都是看在眼里的。祠堂里一代代的碑匾,个个提起来不是英豪也是好汉。钟家祖上就拼个文武双全,儒生考举,背上要别一杆枪,武士提笔会作诗,挥剑能杀人。
死人尊师重教,屹立在祠堂散发森森冷气,外面的活人里,钟常氏最熟她的丈夫。钟兴善少时上了两套学,传统私塾和西式学堂都没落下,他懂洋文,也背程朱子,人家乍一问,都以为钟兴善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其实多问两句就知道,他一知半解的多,功夫到家的少。他爹钟斗复教子极严,两门功课外,族中习武的传统也不能舍弃。钟兴善学形意拳,这是父亲帮他做的选择。四岁时,钟斗复请来几个长辈,为儿子展示形意、八极、迷踪、谭腿、太极八卦,他让钟兴善自己选一种,他不知道,也不接受长子对真打真杀毫无兴趣。
钟兴善这辈子真正喜欢的,是梨园的武行。尤其长靠武生,不必杀将出去,登台亮相就胜过千军万马。他痴迷一夫当关的大将风度,输赢是前定的,几乎算弄虚作假,余下的戏才最稳健精悍。武生是把气运到极致的人,一招一式,都已在台上明白告知,髯口、翎子、靠旗,无不能拿来做文章,武生靴底带风,意念在脚下划出个圆场,钟兴善以为过瘾莫过如此,直到武行开口唱念,出音响遏行云,他一个激灵,惊喜得不知如何是好。走出戏场,钟兴善通身畅快,他要的就是这套气派。
父亲让他学形意拳,多半是因为形意稳扎稳打,出手规矩方正,能约束他的半吊子心性。教拳的师父极守本分,走四方步,挣八方财,他开口说话,人却在千里之外,话是话、意是意,好像四方的嘴是个山洞,真正的他正躲在深处念经。钟兴善曾偷偷盯过师父颈脉的起伏,发觉他心跳慢得出奇。他教拳,仿佛全世界都扎根在拳法上,从三体三尖讲到相生相克,条条框框,刻镂无形。不讲招式时,他又告诉钟兴善,祖师达摩练功全凭心意,所以书是书,开悟又是另一番本事——“要从纸上求佛法,笔尖蘸干洞庭湖”——话听得钟兴善心中生出怠慢,怠是心自怀胎,慢是公子脾气,他乏善可陈的肉身也跟着面目可憎起来。
为了开悟,师父让钟兴善每天站桩延气,以形调息。观呼吸时人虽未动,但气这种善变难明的东西,除非真练过,否则根本分不清虚实。阴阳二气穿过七窍,意气相合,形神赠影,关窍被疏通了,形意才能带出来。站桩并不讨厌,钟兴善知道男女之别始于气,更不用说十二形(即形意十二形拳,属形意拳的一大部分,是以拳拟十二种动物的生活形态和搏斗的特长而组成的形意传统套路。包括龙、虎、猴、马、鼍、鸡、鹞、燕、蛇、鸟台、鹰、熊)里的飞禽走兽,想打得好各个有套独门。他是乐于学十二形的,模仿动物就像上台唱戏,演得好有人捧场,真出手反而没意思。
气脉流通起来,万物都有了底。钟兴善的开悟,没点在精进武学上,全给了当票友这件大事。虎形带着怒气,白虎穿林而过,风声还留在衣袖里;鹤形收心敛气,居高临下的巧打,像松风中的高寿老人;蛇形连绵,步履沉在草中,游荡着向四周缠绕。钟兴善练拳不用拳,采了气就收官。巫清各个行当的票友都知道这号人,钟老板把拳法揉进武行里,身形一立就出角。
-坏-
大家族的女人往往最先觉察到时运的转变。前年起,钟常氏就惴惴的,觉越睡越少,夜里逃难似的,大大小小的包袱皮摊得满床都是。稍有值钱的物什,都被她换成了金银细软,房里的古董字画、瓷器古玩一天少似一天,钟兴善不常在屋里住,偶然回来看见枯山般的屋室和妻子,心下赶快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大难就要临头了,钟常氏不是通了灵才知道这些。虽然没念过私塾,但全巫清最好的先生都上过常府的门。钟常氏是以大家闺秀的标准培养至出嫁的,念书时,四部都略读过,杂书几乎没碰,除了一本殊胜到足以被赦免的《红楼梦》,钟常氏没有别的消遣。她的世界是映着大观园修建的,贾史王薛四家的倾颓,竟隐约得透过钟家显灵了。钟常氏常以为自己是孀居之人,偶尔撞见回家的钟兴善,不过是撞见亡魂留恋人间。
她原本住东厢,可前年开春以来,东厢门外总有些猫狗爱打架,小兽妖精似的拧作一团,叼着后颈交欢。猫狗扭在一处的情形少有,看着阴不阴阳不阳。不出三月,钟常氏门前交媾的刺猬、青蛙、瓢虫、黄仙、蝙蝠也多起来,几乎日日聚首。流言混着舌头渐渐欺压到她头上,海河人历来以为兽类盈门专管报喜报丧,这一看,钟常氏房里保不齐出了什么幺蛾子。
力排众议,钟常氏的陪房嬷嬷情愿不睡,夜夜守在院里赶秽物离开。立秋后第一场雨前,天闷得很,嬷嬷在槐树下等风把雨吹起来,暴雨乍落,她听到树梢有响声。一对正恩爱的鸮子被她亲手戳死,嬷嬷的三股叉杀生伶俐护生难,雨声中,闪电劈将过去,两只鸮的命立刻偿了一半。她原想杀一对怨侣警醒世人,自己却成了世人的警醒。
家里有胆子大正气足的奴才,看不过这样的邪祟,第二天便领着青莲教的道人,到少奶奶门前驱除邪魔。道人一聲令下,半个家的男仆红着脖子冲进去——什么都没有,听热闹的耳朵大失所望,屋里寂寥得像在下雪。钟常氏被直挺挺抬出来,没一点挣扎的意思。进屋找她时,钟常氏就在床上,她仰着面眨眼,不开口,不看人。为首的家仆略停一会,俯身对她说:“少奶奶,得罪您。”谈不上顺从还是反抗,钟常氏看起来无比正常,安详得好像她才是嬷嬷的死尸。
洒水、烧火、跳神,仪式折腾得毫无新意,到傍晚,神也要散去吃饭,钟常氏像用完的贡品,仍平躺着被抬回去。进屋前,她看着头顶槐树的华盖幽幽开了口:“搬到西厢去吧。”钟常氏知道,这段命该应上红楼里的淫生百祸、自杀自灭、奴大欺主。
钟斗复只当不知道家庙里的丑事,借坡下驴把秽气推给了儿媳。这几个月,他总风闻得常氏和旁人有了不清不白的勾当,院门前才会源源不断聚来妖精。较起真来,妖精还是自己的儿子。他知道那事许久,隐忍不发,懒得捅破。家庙里,钟兴善会过各路武行票友名角,庙僻静,又小,和风在里面也迅猛起来。钟兴善像小鬼找到了巢穴,堂而皇之在佛前苟且。
体面是靠真金白银砸出来的,家庙里的僧人优游自在,更衬得家仆心事重重,他们几乎不来还愿,入寺门的面孔也越来越稀少了。
钟家的家运被人命卡成几节,到钟斗复这代,已是白日依山的气数,蓬勃兴盛的旧景腾空了,换上的净是些枯槁的新人。可日薄西山的境况,毕竟不是他钟斗复一个人能挽救的,他不能把这样的预感宣之于口,也不会真的无为而治,钟斗复面对解释不通的事项,总是一样的态度:隐忍不发,懒得捅破,总是后退一步怨起世间法——生灭有漏,因果轮转,不如把鬓毛剃掉,可家庙又不能收留主人自己。
或许幼时被逼得太紧,钟斗复去世未满一年,钟兴善就彻底卸下了家族的兴亡。两个月前,他在前院演练香店鞭,为的却是台上的乌骓。香店鞭迅疾激烈,吞吐有节,与西楚霸王的武花脸最相宜,钟兴善想着“虞兮虞兮奈若何”,势打出去却被错力牵住了脑血,项羽也成了他最后一个角色。
家中无主,钟兴善唯一的孩子又只有六岁。
钟生古的抓周没有结果,周岁礼那天,他坐在大案上无动于衷,任凭钟常氏和奶妈怎么呼唤也不肯伸手。大人的耐心耗尽,他仍在圆心,乖乖垂头打瞌睡。钟常氏无法抱起他,之后逢人便问这是什么命数,莫衷一是间,来钟家化缘的行脚僧人告诉钟常氏:“这孩子自会了断我执法。”钟常氏听后大惊失色,儿子竟是个要遁入空门的。可真当粮仓烧尽,灾年乍起,送钟生古去寺里的,又是钟常氏自己。
-空-
灾荒蔓到锦南之后,弘狸儿发觉寺里的猫少了好多。
师父爱猫,但从不抱它们,他喜欢摸猫肚皮,可手一捧猫,神态总是残忍的,师父的手搜肠刮肚,从猫身上要的是自己。猫分两种,敦厚的惹人疼,皮毛油滑,浑身是劲,另一种尖脸立耳,骨相玲珑,瘦长得难以接近。师父常嘱咐弘狸儿,没到荒年,饭也不该吃太饱。瘪肚子才好练轻功,人饿薄了,腹部才好收紧,身量才够轻盈。再高的墙也拦不住这种人,猫落地好像栀子花凋谢,整朵跌落,胎骨连在一起,你就这样练。
观心寺的护生池干涸了多年,池底的砖石被晒得发白发亮,弘狸儿灵机一动,把猫养在了里面。师父每日早课之后,从角门离开,晚课前回来,那时,只要他兜着手站在护生池前,弘狸儿就明白,师父的僧袍里又有新小猫了。
全锦南的瘪肚子猫都在这了,满满当当一池子。师父嘱咐弘狸儿喂它们吃粥,之后看住哪几只先爬出来,就喂它们鼠干——他们刚到观心寺时,发现地窖里遍地死耗子,师父把耗子尾巴拴在麻绳上,一排耗子风吹日晒,终于晾成了能喂猫的肉段。晒肉那段日子,师父每天都在鼠辈面前做超度仪式,经忏经他一念,竟比大鼓还好听,弘狸儿求师父教他。
师父唱得快,嘴又软,稀里糊涂把超度做完,又匆匆忙忙准备离开。弘狸儿费一番功夫才听出几个半句,他缠着师父,除了轻功,经忏他也想学。
这话像提醒了师父,他让弘狸儿先学会提着自己悬梁——出门前,师父特意捆住弘狸儿的双脚,倒立着把他吊在了树下。弘狸儿大头朝下,看着狸猫到处乱爬疯跑,明白这是为了跟着猫师傅学习,他把注意力放在猫脚上,重心上下腾移,忽得脚一勾,学着猫下墙的姿势把自己慢慢撑了起来——全靠一张收紧的瘪肚皮。弘狸儿慢慢发力,终于用手攀住了绳索,世界又恢复了原貌。
许是名字起得好,过了一冬,弘狸儿和满院狸猫都活了下来。隔年开春,锦南县的谣言随着柳絮遍地滚,人们疯传今年是灾年,躲不过饥荒和打仗。弘狸儿看到,先是米价上涨、孕妇变多,再就是师父渐渐不能带猫回来,就连院里的猫,也越来越少了。如今,锦南有一多半人口在逃荒,剩下的是走不动的人,他们决心留在锦南等死。械斗、火灾、抢劫,似乎都避开了观心寺,这一来,寺院好像一面浮在锦南土地上的镜像。
猫是不会无故逃走的,它们认窝。何况弘狸儿练的就是这个——追着猫的步子,把猫落在后头。追上猫,手一鞠,就能把它们抓回庙里。为着这个本事,弘狸儿有了自己的传言,不知何时由什么人说起——锦南观心寺的弘理小师傅轻功了得,猫见了也会妒忌。传言散一散就成了奇闻,海河人爱起外号,弘狸儿的外号从此成了“猫不理”。
猫不理的猫当然偷不得。入夜,弘狸儿倒挂在柳树上,专盯着捉猫贼。天黑得深透,丑时才有一点人的动静,是师父在掌灯。师父脚下轻盈,意念方动,身形已在远处,他抓猫不上高地,平地行走就像飞。灯火幽冥,师父稳稳提住一只老猫的脖子,向暗处的水井走去。
水井边架着锅炖肉,地上的猫皮皱巴巴。师父说:“吃它吧,不吃也没别的。”
“师父不唱唱超度吗?”
“那全是戏词,我编的。”
“就当它是了。”
猫不理开口:
荣华好,无常到。( 《红楼梦十二曲 · 恨无常》,曹雪芹) 善惡生死,哪管人离恨?(昆曲《玉簪记·朝元歌》,高濂)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元杂剧《西厢记·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王实甫)
料今生,诉冤情,说惊魂,话愁肠。(参见京韵大鼓《剑阁闻铃》)但愿得,刻香檀做成神像。(昆曲《长生殿·哭像》,洪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