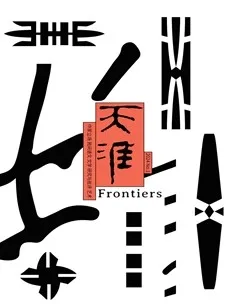小诗人的日常笔记
2024-02-22刘川
沉默的诗人
一大群诗人高谈阔论、滔滔不绝。突然一个诗人不说话,他沉默下来——他的语言之神溜号了、走掉了。
不,或许相反,是他的语言之神突然降临了,才把他从庸常的、虚假的語言交流中阻断,让他进入那真正的与神的对话——可以用语言,也可以不用。
笔记本的延续
?学生时代他偷偷写诗,在政治、历史或地理笔记本的背面,在这些与诗看似无关的学科作业本的背面。而今,他用单独的白纸本写诗,写完一读,发现诗的另一面,仍是政治、历史或地理,它们延续过来了,无法清除——但他微微一笑。
衣服上的台词
戏台上,同一个人,穿上薛仁贵的衣服就要说薛仁贵的台词;穿上杨子荣的衣服就要说杨子荣的台词。生活中也不例外,没人能够脱离衣服。衣服就是剧本,自带了一整套台词。
瓶子里的诗人
某诗人醉了,对着一只空酒瓶唱了好几首歌,然后盖上盖子从青海寄给我。我偶尔打开盖子听听——什么都没有。但是,并不能说什么都没有。一打开瓶子,我眼前就浮现出大醉的他对着瓶子唱歌的搞怪、有趣、可爱的场景。这难道不是一只装了诗人形象的瓶子吗?瓶子不再是空的。
空中的箭
罗宾汉死前朝远方射出最后一箭,说:埋我于箭落之处。
我亦射出一箭,告诉人:去,将我之墓地拿回来,我再射几次。
——诗人是不会死的,一落到地面、接触现实,便又活了,只有悬在空中,才是死的。所以这箭,让我死,也让我再生。
时间中只开一次的梅花
我家中一面镜子照了二十几年,前天不小心落地摔破了,才发现它的背面刻绘的是好看的梅花:也不知是镜子破碎使它开放了,还是它的开放使镜子破碎了。
左侧的乳房
古时亚马逊女武士为交战时更大幅度拉弓射箭而割去了左乳。尽管而今只从她们墓中出土一把剑和几个箭头,但她们右乳哺育过儿女,缺失的左乳参与了保护家园。写诗,你也要删去一些词语,为是使诗射得更远;用剩下的词语延续你作为诗人的生命。
身份的偷窃
他看中老乡的鸡,捉到手,如何带出村庄而不被发现呢?他把鸡放进了小提琴琴盒。就这样,这只刚刚为黎明啼鸣的公鸡又进入了琴盒形状的黑夜,而公鸡在黑暗中是不会叫的。村民们尊敬地看着这个艺术家背着琴盒离去——你看,用艺术及艺术家身份行窃,多么容易!
水的次序
今天上午,恭敬与数位长者座谈。
其实就是按资排辈,客套着分饮一大壶白开水。
回家又要被我家猫嘲笑了——白开水也分座次?
国土的延续
?俄语词汇的重读音节变化不定,而波兰语中重读往往是倒数第二个音节。
他从波兰移居俄罗斯多年。
他保留他的国土的方式是有意无意地在俄语词汇中,把重音放在倒数第二个音节。
复活的朋友
叔本华说:“每次分别都让我们提前尝到了死亡的滋味,而每次重逢则让我们提前尝到了复活的感觉。”一个朋友反复删我又反复申请加我,我想,他并非乐于“复活”,而是乐于处在“轮回”之中。他痴迷于在生死中的自我折磨。
虚拟的行走
在微信运动步数排行榜上,有人在办公室坐着通过摇手机攒步数登榜。虚拟地踏入现实,走入生活。此人很聪明,但他不知道,其实此乃诗人写诗最常用之法。
同龄的花
波齐亚说:“你手中之花今日才开,却与你同龄。”
是的,当你五岁见此花有五岁对花之感受,你五十岁见此花有五十岁对花之感受。
今日之花与你同龄,本质上是你从今日此花上看见今日看花之自己。
容易消失的文友
我无聊中用圆珠笔在掌心感情线上又画几条分叉之线。或许,会增加一些无比亲密之笔友、文友。?
不过,一洗手,他们又离我而去。我了解他们。
身上的先知
关节炎,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先知。一个气候变化先知。来自过去的经验总能作出预警。他的过去,使他知道未来。
词语形象的人
不知谁说过,“诗人是一个被翻译成词语的人”。
我不反对,只补充说:“诗人,正是一个被翻译成词语的人,但不是用词语把一个人翻译成诗人。他是词语形象的一个人。”
最小的力量
诗人在诗中用的力大小能启动核按钮便可。核爆炸的力量要在读者身上产生。阿巴斯说:“最有效的眼泪并不流到脸颊,而是当它在眼中闪动。”所以,诗人还要稍微向内用一些力,控制不让眼泪流出眼眶。
飞走的舌头
某人有一只鹦鹉,常学他说话。一日,鹦鹉飞走,他急忙登报:“本人走失鹦鹉一只。该鸟一切言论,本人概不负责。”声明也没用。鹦鹉,其人飞走之舌也。
文学作品亦然,虽然离开作者,却永远代替作者说话。
课本中的乌鸦
一只乌鸦口渴了,见山顶有半瓶水,便从河边衔石子投入瓶中喝水。问:为何不直接喝河水?答:课本中,最聪明的乌鸦的做法是投石子入瓶,已成世代乌鸦喝水之传统;喝河水,无传统,反祖制,不聪明。
衣服上的我
选择衣装,就是定义自己。打扮与装束,就是具体地描述和解释自己——
着拖鞋、摇蒲扇上街,就是五湖散人;
穿大裤衩、牵狗而行,就是乘桴浮于海,出走于世外。
空无的饵
许诺,诱饵之一种。
其饵乃虚拟、空无、或然之物,挂在钩上之根本不存在之物。
对人类晃一晃空钩就行,只有人类爱咬空空无饵之钩。
重组的石头
某一年,道观里的信徒们亲手拆了道观,用拆下来的全部石头建了一座寺院。这些石头除了各自位置有所变化,其他并无变化。这些信徒除了重建这座房舍,身体也并无变化,但他们一定与以前不同了。
丧失的箭
晨读《易·旅卦》第五爻,辞曰:“射雉,一矢亡。”
——一心想射到野鸡,却白白失去了一支箭。
邻家大哥天天买彩票却从未中奖,可谓日丧其矢也。
蚊子的去来
蚊子来咬我。我奋起一击,它飞走,翩若惊鸿。但我并不去追赶。我的肉体在此,它就会回来。
——如果它再也不回来呢?岂不是更好!
自身的遮蔽
诗人身上,一些器官常常遮蔽另一些器官。博纳富瓦说:“不蒙上眼睛,就看不清楚。”诗人对现实的“观看”就怕受到双眼看见的虚幻现象的干预,从而丧失理性。所以,在“事实”面前,需要闭上眼睛,用心灵再观看一会儿。
路上的石头
因纽特人去见仇家会送上一块石头。有时在路上见因纽特人带着一块石头,便可知道,他心里有个仇人。但路途漫漫,带着这沉重之物实在是负担。仇恨本身就是负担。当他突然扔了石头,你知道他饶过了仇人和自己。
云雾的形式
据说老虎下山吃了一个和尚又返回山顶。
而山顶只有一团云雾,看不见老虎。
即使看见老虎又能怎样,有虎皮遮挡,也看不见和尚是否在里边。
虎皮,帮助人们杜撰了又一团云雾。
无休止的循环
两个窃贼精于偷盗,只要房中无人,便能将财产偷回家去。巧的是,他们偷到了彼此家,他们的财产开始循环。穷人和国王也是这样,隔一段时间,从对方那里偷一下:权杖和锄头开始循环。
绳子的另一头
写作者永远处于未知之中。他在雾中捡起绳子一头,用力拉,不知拉出的另一头是一只狮子还是一个美女,绳子从未给予确切承诺。有时,他更迷恋手中这条绳子本身。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拉住了绳子,或许正是绳子神秘莫测的另一头把我拉到了今天。
迷失的虫
一只小虫在我书房迷了路:到处都是书,到处都是书,堆放得乱七八糟!在一只小虫眼里,这些书放的不同位置使它迷路。而它不知道,我也迷失在这些书中。我还以为我可以移动这些书的位置,其实,我被这些书彼此之间隐含的某些关系,铆钉在现在的位置。
苹果的贞操
苹果全身各处,都是它的贞操。不论全身任何一处,只要被人咬了一口,別人都不会再吃,只能由这个人继续吃下去。哦!这一口,也是这只苹果的命运。
伤疤里的虎
他曾在动物园当临时工,给动物投喂饲料,因操作失误,胳臂被虎咬伤。他每次喝酒吹牛逼吹不过人家,就一撸袖子,亮出伤疤,嘴里发出一声虎啸,说,老子都被虎咬过,还怕你们吗?就这样,虎在他身上又复活了一次。看他自豪骄傲的模样,仿佛他不是被咬伤者,而是那只猛虎。噢!人啊人,伤疤里供养着多少野兽!
不动的公交车
教室像公交车,坐两学期,到站,下车,到下一个年级另一个教室去上课;这里教室,另一批人上来。
办公室像公交车,坐若干年,有人升科长、处长,有人升局长、市长,到站,下车,退休或去其他办公室;另一些人进来。
双倍的砍伐
寂静的山林里有人砍树。他每砍一下,声音都撞击我身体颤动一下。
当山林传出一个回声,又撞击我身体颤动一下。
胡萝卜的干扰
在当当网查书,搜索俞敏,出现在一大堆俞敏洪当中;搜索刘川,出来好多重名的刘川;搜索葛亮,被好多诸葛亮夹带。真乃拔出萝卜带出胡萝卜,或者只有带出胡萝卜才能拔到萝卜。相似性的干扰,让萝卜还要从胡萝卜中再拔一遍。
手的分身术
对一只蚊子来说,手,是它的刑场、刑具、行刑者;
当然,手一合十,又成为它的超度者、悲悯者。
被定向推送的现实
对作家来说,他亲自面对的现实未必真实:马可·波罗写过一个小国,该国之人全生有尾巴,尾长一指,近似狗尾。当然,最大可能是,他越探访奇特,人们越给他编排奇特;若他喜欢鬼神,人们就给他讲鬼故事。作家惟有朝现实再深入一步。
故乡的迷失
我用我故乡的方言在导航系统里输入故乡的地址,导航无法识别更无法带我去往那里。
老鼠的显现
因为陈放于书橱太久,乐谱被一只看不见的老鼠啃咬,现在拿出来演奏,残缺处要胡乱发挥或跳过去。听上去,这支著名的曲子里像有一只老鼠,在啃咬乐谱。
画面的遵从
马克斯·恩斯特给自己的花园画了一幅画,画完发现少画了一棵树,他马上砍掉了这棵树。他遵从了他的画面。我无理由嘲笑他。为了喝咖啡我特意买了咖啡杯,因为别人都用这种大杯子,而不是用家里的茶杯——我遵从了别人的画面。
梯子上的人
小时候,我常躲开大人,爬到阁楼上玩。长大后,那里只放不用之杂物。有时,我仍扛来一架梯子,爬上去,并不上去玩,也不取用过去之杂物。我只是爬上去。每上去一阶,我就年轻几岁。
井中的和尚
某傻和尚回故乡遇到儿时的井,低头一看,井底也有一个和尚,叹道,原来我儿时就已经是和尚啦。读某大诗人传记,作者把这个诗人童年每件小事都写成他未来成为大诗人的征兆。在时间的井中,他和那个傻和尚有什么区别?
疾病的延续
人们疾病痊愈时,有的崇拜上了医生,有的仇恨上了疾病。他们并没有真正痊愈。
拨错的号码
陌生人都是从我亲友那里得到我电话号码。而昨天接到一个电话,他获得我号码的方式很特别,却并非不可能。他不认识我亲友,他只是给他亲友打电话拨错了一个数字。
哦!我与他亲友号码如此相近,请允许我把这也当成一种亲友关系。
镜子的介入
狗把镜子里的自己当敌人,愈加勇敢,吠而扑咬之。
人把镜子里的自己当高级的自己,每日三番五次妆扮之。
奇怪的是,狗与人,都利用了镜子的正面。在另一面,狗和人又回归了原来的自己。
头上的阶梯
尼采说:“假如我没有梯子,我就爬到自己的头上。”
我也从来没有自己的梯子,但我看见了空中伟大诗人向上行走的脚印,在他们肉身离开之后,在他们尘世命运终结之后,他们的事业仍在空中。
木桶的局限
每一只木桶里都住着一个哲学家。但木桶与木桶之间并不能交流。说是木桶也好,说是理论体系也罢,另一个哲学家只有进到这个哲学家的木桶里,二人才能对话。其实,每个诗人也都住在自己的木桶里。
黑暗中的人
我?认识一个盲人,他记忆力惊人,记着过去每次见面时我说的话。事实上,我并不需要这样一个行走在黑暗中却一直“抓住”我不放的人,他讲出我曾讲的话,仿佛他就是过去的那个我,在黑暗中。我希望过去的那个我自己睁开眼睛,离开我。
徒劳的反抗
昨天我逆时针方向跑了一小时。
尽管我知道我逆时针跑其实还是在顺时针跑。
尽管我知道我即使一动不动也是顺着时间的方向在极速奔跑。
空中的家园
蜂箱搬走后,晚归错过集体搬家的个别蜜蜂会在原来蜂箱所在处上空久久盘旋。这让我心碎。这也是诗人爱干的事!那空中的描绘,那空中盘绕出来的圈,不是圈,是失去家园者在虚无中画出来的家园。
双手的勾结
他左手画画,右手写诗,几十年了。他常摊开双手,看看两者的各自独立。其实右手写诗时常从左手汲取色彩与结构,左手画画时也常挪用右手里的意象与韵律。他摊开双手,其实双手根本无法分开。
恰好的书桌
诗人蓝蓝说:“在过去的岁月,我拥有一张恰好的书桌。”
是的。而我还要说,只要过去的岁月,便是我拥有的恰好的书桌。没有哪个遭遇、哪个经历、哪个年代,不是恰好实实在在支撑着我的写作。
诗人的方式
他讨厌鼹鼠却又需要一个伴,遂用一只不透明的盒子豢养它:盒子留两个孔,上边孔投食,下边孔清理粪便。他俨然饲养了一只长方形盒子。而我也不比他强多少。我买书买书复买书来为自己的一本书做写作准备,我用无数的书饲养一本看不見的书。
藏在诗的节奏中的生活节奏
他写不出诗,抽一支烟,接着写。他的诗中,总有两三支烟嵌入,你读不出来。自从我亲眼看见过他一首诗的创作过程,再读他的诗,我便能精准地找到他五元一包的黄山一品的嵌入位置。
第二次流亡
一天,流亡者被坠物击伤脑袋而失忆——他不再是流亡者了。他醒来,只是一个不知自己是谁的人。在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城市而已。?而那里的好人啊,千方百计治愈了他,让他记起从前他被迫离开的祖国,他啊,就这样又成了一个流亡者。
诗的力量
最轻的力量可以提起沉重大物。几克的力量可以提起一个人。
那天在公园,我看见一个肥笨的小男孩因为追赶一只白蝴蝶而跑上了高高的山坡。
丹顶鹤与马克·斯特兰德
诗人马克·斯特兰德说:“我用一条腿站立,另一条腿做梦。”
我不太信他真能用一条腿站立。
但我曾认真观察过,丹顶鹤入眠时,才是一条腿站立,另一条腿提起。它那条悬空的腿,一定正在做梦。
内心的电池
防止牛逃走,某人在牧场四周安装了电子栅栏。要用好多电池,费用非常高昂吧?并没有。只是最初一段时间,牛被电击几次,感到疼痛,便再也不去触碰电网,也再未用过电池。是的,牛在内心,至今还在源源不断给这些栅栏“通电”。——那些经验、教训,化作的电池,也使我们走不出隐形的栅栏。
现实改变了以后
“我以为看见一封信投在门廊,可那只是一片月光。”这是芬兰某诗人夜里的错觉。
然而电子邮件时代,再也不会来一封纸质信件了,那片错觉的月光,在大脑的潜意识里就是别的。
——我以为看见了一张电费或水费的催缴单。
玻璃瓶
你把一只大黄蜂放入玻璃瓶,盖上盖子。你听它歌唱,其实它在诅咒。它在挣扎、哭泣与诅咒,但因为隔了一只玻璃瓶,听上去它在歌唱。这玻璃瓶,这文学的修辞机制,在把苦难化为可耻的动听的歌唱。
山顶上的人
他每天早上爬上山顶都会遇见一个陌生人。他俩相视一笑并不交谈。如此数年。昨天在朋友饭局上,他突然发现,那陌生人也参加了。他马上借故离去,他想在山顶上保留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仿佛他是滚滚尘世之中,未开启的另一个自己。
散步到石头里的人
法国某广场上,为保罗·魏尔伦立着他散步的石头雕像。若干年前,他上街给妻子买药遇上诗人兰波,兰波未费多少口舌便说服他弃家一起散步,结果去各国云游并创作了大量杰作,成了伟大诗人。我每天散步必定回家,我不想散步到石头里。
半空中的人
小说家东君说:“梯子抽掉了,电工永远留在了半空。”
这种情形并不少见。我心眼儿实在,帮许多人当过梯子,当他们有些人爬到半空,就一脚踢开我,然后,继续向上爬。
周围的世界
诗人亚历山大·里斯托维奇说得好:“不是诗人使他周围之世界变得有诗意,而是他周围之世界使他成为诗人。”而我的悲哀是,我的周围没有真正的世界,全是诗人以及他们用词语书写出来的世界。我不要让这样的世界使我成为诗人。
狗身上的区域
去陌生人家里,主人并不显现他的“势力范围”。若被他家狗追着咬,它追你逃,它追得停下来的那个距离,便是这家主人的势力最大范围——狗知道它一旦超越这个范围,主人便不能罩着它了。是的,我经常从一条狗身上看见它主人的区域。
内在的眼镜
米沃什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我也是,离开故乡数十年,却一直用在故乡形成的眼光,看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地的关系,仿佛戴着一副内在的眼镜。
白天的圣贤书
小偷白天教儿子读圣贤书,并不觉得有何不妥。整个人间不论干什么的,都在白天读圣贤书。儿子长大,夜里也偷东西,白天也教他儿子读圣贤书。每代小偷都这样。他感叹:若没有这本书,大家都在白天做他们夜里做的那些事,该多么悲哀!
纸面上的翅膀
夜里,我听见鸟飞过。我仰头久久都看不见它。但我确信一只鸟从夜空飞过。我是诗人,若我不写下它扑喇喇拍击翅膀之声,便仿佛它从未飞过。而或许它才是真正的诗人,它并不为一张纸而存在。
墙上的小孔
一个判了无期的刑犯,每次通过围墙上的小孔看到外面自由的生活便痛苦不已。折磨他的不是狱中的刑具,而是这个小孔时时提示他永远失去的一种生活。他堵上了那个小孔,他以为他拯救了自己和狱中其他犯人。
间接的生活
顾城的诗:“这个岛真好,一树一树的花,留下果子。我吃果子,只是为了跟花,有点联系。”他吃果子是在观花。我吃的果子是苹果梨,一种嫁接水果,我想观看两棵不同的树如何长在一起。我们实在是忽视了太多间接的生活。
特殊的坐标
故乡,并不在异乡之内。
而异乡,却是故乡的一个坐标。
在异乡,永远知道故乡之方位、远近。
第三者
阿多尼斯说:“什么是拥抱?两者间的第三者。”叔本华好像也说:“人们爱的是对方身上的自己。”所以,拥抱还真是通过另一个人的身体接触另一个自己。这个只能通过他人呈现的自己,这个间接的自己,其实是一个和自己相似的第三者。
放大的小偷
夜里,赵家一条狗看见小偷,叫了起来。邻家狗听到狗叫也叫了起来。全村的狗听到狗叫也叫了起来。全镇的狗都叫了起来。但是,只有一条狗看见了小偷,其余的狗只是“放大”了小偷,使他充满了全镇。
左手的支持
诗人森子说:“?当你右手用力时,左手也暗暗使劲儿。”
当你右手写诗时,你左手做过的事情、获得的经验也在起作用。
当你写诗,甚至之前阻碍你写诗的那些事物,也在此刻助你写诗。
家人的显现
儿时不让上桌,小小的饭桌容不下八九口人,他就蹲在门口端着碗吃饭。而今,每次家人不在,独自在家吃饭,他都会离开一张大大的饭桌,去门口蹲着吃。他一找到童年的位置,就感觉有满满一桌子家人在陪他吃饭……
写作者的真诚与虚伪
风雪夜,我正奋笔疾书。有人用力敲打我门要进来。请原谅,我正在写作,不能打扰。
我流着泪,真诚写下的是,有一个冒着风雪、千里夜归的游子,正敲打紧闭的家门……
“鬼”的显现
顾随说:“一切议论批评不见得全是思想,因为不是他个人在说话,往往是他身上鬼在说话,鬼——传统精神,不是思想,是鬼在作崇。”——为避免顾随这个“鬼”(这里加了双引号,换个称呼是前贤)在我身上说话,我直接转述他的话。让“鬼”直接现身。
蜗牛戒指
那个坏小子,笑嘻嘻地把一只可爱的蜗牛放到她左手无名指上。“给你戴上结婚戒指。”
——据说这根手指上有一根血管直通心脏,能见证爱情。因此,她心里过电一般,颤抖了一下。
可是,他走了,忘了这事。而她,把蜗牛放进了首饰盒。
至今,这只蜗牛看似一个空壳,却还活着。
边界上的狗
有的边界上有狗,有的没有。其实,所有的边界本身就是一条狗。你不走近它,它无反应;你一接近,它便会有剧烈的反应。有人写探索之诗,引发众怒,其实他是踩到了他们身上诗的边界。
朋友的牵连
他给车子安装了北斗定位系统之后,不论开车去哪儿,都感觉有一颗卫星在茫茫太空里盯着他。
我是他朋友,每次蹭他车坐,都感觉,因为我是他朋友,这颗卫星也注意到了我。
墙的装饰
尼采说:“既不要在墙上画上帝也不要画魔鬼,谁这样做谁就会毁掉墙和邻居。”
不要美化或丑化你与别人的边界,可以挂上一幅画,但也要记得那只是对你自己生活的装饰。
山顶上的辨認
黄昏时分,先生看见一群人,便上了山,坐下后,那群人也上了山。他开口教导他们。而后,他下山;他们也下山。谁也认不出谁是先生,谁也认不出谁是弟子。是的,在山下,在黄昏,有些人,谁也无法辨认出来。只有在高高的山顶,才能辨认。
诗人身上的对话
帕斯说:“当真正的诗人与自己交谈,他就是对别人说话。”
这得有个前提:这个诗人身上有别人存在。他虽然只是一个人,但她是一个“个我”,又是一个“众我”,这样他越是真诚地与自己交谈,更多的别人越能听到。
星座里的星
构成星座的每颗星会因为人们看到了这个星座而使它从满天繁星中显现出来,但也会因为大多数人看的是这个星座而忽略它是单独的星。我说的是流派、社团、群落中每个具体诗人的处境。
纸条上的号码
某年,无人可联系的他,孤独至极之时,捡到一元硬币,便走进电话亭,顺手从地上拾起一张纸条,投了币,拨打了纸条上的号码。他让那张纸条和远方一个人发生了联系。而今,他在纸上写诗,想用这些字和所有人发生联系。
诗人的语言
他是诗人。他试图发出危急警告:洪水将至,再不撤离,必遭灭顶!但人们听不懂。因为他讲的是另一种语言,是用人们能听懂的字词组成的另一种语言。洪水过后,幸存者们推崇这种语言,以人人会说几句为荣,但他们不知道那是用来预告洪水的警报。
传说中的动物
据说美洲某地有一种动物,不管你转身多么快,它一直会躲在你身后,以至于没人真正见过它。当然,在我们这里,也有一种动物,不管你转身多快,它一定会站在你眼前。你说你看不见它。是的,但是它正时时刻刻、严严实实挡在你身前。我说的是,传统。
古怪的桌子
“多么古怪!”
半夜突然想到表舅常说的、不知他从哪里看到的一句话:“桌子用食物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又用桌面把人们隔开。”
那么我写作的桌子呢?写作时,它把我从人群中脱离出来,而它支撑我写出的东西,又使我和所有人发生联系。
飞翔的牙齿
戈麦斯说:“狗的叫声也咬人。”
这话放在狗身上不成立,放在人类世界才成立。互联网上匿名的攻击,就是从看不见的“狗”嘴里飞出来的“牙齿”,遇到谁咬谁。
读者的显现
打印机出错,文章打出来,纸上只有标点符号,未显现文字。我把它给一个读者看。若我给他看这篇完整的文章,他根本不知道他在这些标点处怎么停顿、换气、表现情绪。他从不知道读文章时,读者融入其中,只在标点处才露出头来。
身体的地理
背上,自己够不到之位置有痒。请女儿给抓挠。再上一点,再左一点,再回来一些。仿佛自己身上开导航。
?
警惕自己的人设
某部落,老?巫师喜欢扮演虎,变的次数多了、时间久了以后,在人们眼中,那只虎的形象就替代他,看不见他本人了。当有人真的被虎所伤,人们自然归咎于他。这回好了,即使非他所为,人们还是用猎杀虎的武器处决了人形的他。
红桃K的存在
一副扑克丢了一张红桃K,我们依然拿来玩,分牌到手谁手里少了一张便相当于他有一张红桃K,可与他手中其他牌组合。可见做人,有几个好友或兄弟之作用——别人会看见他们,即使他们不在你身边。
错过的回信
二十几年前,云南某座山上有个人,给我写了一封投稿信。信不小心遗落在书架中,直到今日翻书我才发现。对不起。想回信,但即使他还在高原、还在山上,他也下高原、下山了——今天的人们都已失去把一座山当书桌或把书桌当一座山来写字的心态了。对不起。
通往布达拉宫的路
因为朝圣者太多了,通往圣殿的路两旁便形成了市场。
所以不必担心找不到圣殿,两旁都支满了货摊的路便是。
——你唯一要警惕的是,沿途走下去你是成为一个朝圣者还是一个消费者。
复数的身体
米沃什说:“我与自己的身体保持距离。”
一个诗人过分忠于自己的经历,便会被自己的身体遮挡视线。适当跳出来一些,便会发现,作为诗人,他拥有更多的身体——他是一群人中的一个人。
身上的标准
法官斯特沃说:“我无法定义色情文学,但只要读到,就能认出。”他要亲自读读才行。对于诗,也不是规定用什么词、句式、意象或主题便是诗,而是要通过亲自去写、去读、去感受才知。诗的尺子,某种程度上说,只在人的身上带着。
被配合的伤害
卡内蒂说:“穆伊斯卡人相信,普通人无法不受伤害地承受王侯的注视。违法的人有时被判处接受王侯宰官的注视。”
因为被惩罚者也对此深信不疑,所以他们被那些大官注视之后,便因为过度的恐惧与焦虑,病倒了。
雾中的老虎
山顶有雾。他常上到山顶,猛地学一声虎啸。山下人皆传说山上有虎,莫敢上山。某日,他才行至山腰,便听到山顶有虎啸。他吓了一跳:真有虎?或另一人学了他的把戏?总之,利用这团雾,他欺骗别人,别人也能欺骗他。从此,他再也不敢上山了。
詞典的丢失
他想知道词典究竟为何物,便翻开词典查找“词典”这个词条。他找到了,原来如此。其实他还是错过了。这个查阅过程,这个功能显现,这个利用手段,才是真正的、活的词典,而不仅仅是那个词条。骑马找马,找到了马也可能失去了真正的马。
第二次的毛衫
她拆了前夫的毛衫,用这些毛线为现任丈夫又织了一件毛衫——她太珍惜这些上等织物了。而这个新的男人并不知晓:婚姻洗牌之后,一件毛衫也洗牌了,那些过去的线头、纠缠、死结、暗扣与矛盾,都成了新的。
关于不能做的事情
君特·格拉斯说:“我从事写作,因为我不能做其他事情。”
请允许我做两种理解:一,别的事情我不会做,才选择了会做的写作;二,对于受限制不让做的那些事情,我偏要用写作来做。
这是两种写作者。
桌边的狗
庄子去做客的人家有一条狗。它扑上来咬庄子,庄子知道它不会真咬,它随时听着主人的口令。果然,主人喊它,退下。不一会儿,庄子和主人,在一张桌边坐下。那条狗开始讨好庄子,因为他也成了桌子的一部分,这张桌子会分食物给它。
无关的信
邻居恳求朱哈给巴格达的朋友写一封信。“不,我可没时间去巴格达。”“为什么去巴格达呢?只是给他写一封信而已。”“我的字除了我没人认得,我写的信得我亲自去读啊!”
——今天许多诗人,其诗难解,但从没有哪个读者请其到现场解读,是因为这些诗(作为特殊形式的信),里面从没有与他们真正有关的内容。
自己身上的鬼
他痴迷打篮球,为提升弹跳力,便自逃生梯逐级向上蹲跳,每晚都有不明的啪嗒声自楼梯间响起。那栋楼开始传说闹鬼。他也听说了,不敢晚上再去跳。鬼便消失了。他从不知他是鬼又是怕鬼者又是止鬼者。他至今夜里不敢单独走楼梯。
脸上
某导演坚持给两百名临时演员各做了一条骑兵裤子。“这些裤子在镜头里根本看不见。”“不,可以从他们脸上的自豪中看见。”
写诗也一样,登过珠峰的人,你能从他的句子里看出来。
嘴里的镜头
拍照时人们常集体说“茄子”,用这个嘴型制造面部表情表达快乐的表象。因此,每当看到人们快乐的照片时,我总是想,他们可能并不快乐,可能正喊着茄子;或是更糟,他们嘴里含着“镜头”——因为受制于拍摄者,他们必须配合表演出快乐。
刘川,诗人,现居沈阳。主要著作有《拯救火车》《大街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