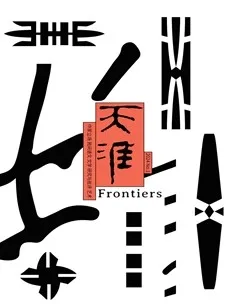寻找鹿溪
2024-02-22任白衣
一
白先生从未踏出鹿门书店一步,这间书店开张至今,也从未有顾客上门。书店前院的东北角,一架书柜,两张玻璃钢瘦腰椅,围着一个黑黝黝的火盆。火盆原是瓷白色的,书烧得多了,就成了黑色。这种黑色,是随时向人宣誓效忠的,是失去欲望的深夜狂潮退去之后,残留于日间的一抹堕落的灰烬。
白先生随手取出一本书,一页页地撕,残页再对折撕成两半,他陶醉于书页发出的悲鸣,更陶醉于烧书时那种介于生与死的灰烬味。老榕树里的鸟将鸣未鸣之际,他屏息聆听,黄昏的绿影千方百计地将鸟掩藏起来,鸣声依然流出了树心的欲望,犹如水晶雨点从翠绿云层中洒落。
白先生点燃了火盆里的书页,注意到身侧空空如也的座椅,就在火与鸟鸣的秋光里,他想起了鹿溪。
这座城市有些令人捉摸不定,人不如鸟,总喜欢用其他的东西替代他们的喉舌,鹿溪的舌头恐怕是被他的画咬掉了。白先生事后回想,如果鹿溪没有遇见国画,人生会是另一种光景,如果他没有遇见鹿溪,他还是原来的他。
在这样的城市,白先生的书店小得聊胜于无,他一时心血来潮,招聘了一名暑假工。无论是谁,都需要有人走进这间书店。鹿溪就读于深圳一所普普通通的高中,高高瘦瘦的,鲜嫩的胡须欲黑还灰,全身只有那件校服有一点可取之处。他来应聘时,白先生注意到他的衣服、头发凝结着清冷的白露,或许他来自一个秋风夕起的黄昏。后来,当白先生决定出门寻找他的时候,映入他眼帘的也是那片未响应的暮色。时间失去了它的进程,这令整座城市看起来都软趴趴的,摩天大楼、老村、古祠堂和他的书店,所有的建筑体内流淌的字符血液凝滞不动。
鹿溪在做自我介绍时说他喜欢国画,并向白先生展示他的新作:水墨舒散的云山,分不清性别与年龄的云寡欲无为,春色在树木的骨骼间晕开一团团心事重重的绿,苍老的山皱着眉头,细看之下又似摩天楼群,拥有三个影子的少年正在云烟飘渺处登天,脚下是无形的台阶,头顶是冷漠的月亮。鹿溪问,你认为他是要去摘月还是入月?白先生问,为什么画里的人会有三个影子?鹿溪的眼里浸透着一轮郁郁寡欢的月亮。这样的月色,就是答案。
白先生于是有了期待,国画里的书店是一种全新的解读,那是庄子遇见了孙悟空。他希望鹿溪将其画出来,让他拿到焚书角烧掉。这是鹿溪第一次遇到有焚书癖好的人,他注视着白先生,眼神发出淬炼艺术素材的笑意。
于是,焚书角多了一个沉默的旁观者。
白先生是在鹿溪缺勤的一个星期后,才意识到焚书角的座椅重新空了起来。仔细回想,鹿溪并没有给书店带来多少幻想的热度,他自身甚至比书店更加缺乏冒险精神,仿佛他的生命在另一个时间进程里。
白先生得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重新审视另一个被世人遗弃的解剖标本。鹿溪也是被这座城市剥夺了想象力的局外人。他那愤慨的血肉可以点燃太阳,早衰的心却成了一颗白矮星。白先生知道那种感觉,身在人海之中,找不到一个愿意跟你视线交触的人。人海就是死海。
暮光碎了一地,无人光临的书店静得有些让人活不下去,白先生决定出门寻找鹿溪。
这座城的街道一直在疯长,现代楼宇犹如一层层凝固的巨浪。白先生内心深处有一个秘密:他对这座城市怀有难以言说的恐惧感。他曾做过一个梦:深邃的海底沉眠着一头没有头颅的古兽。这并非他的恐惧之源,他躲在书店内,只为了避免被门外的海洋溺死。他亲眼目睹这片海洋溺死了无数光阴的讲书人。他不敢有丝毫的侥幸之心,他永远进化不出能在这样的海洋呼吸的鳃。
白先生以囚徒的姿势站在书店门槛上。鹿门书店的寂静同樣浩瀚无边,深似海,他在里面活得太久了,早已忘记了不敢出门的缘由,但身体还一直记得。他的脚尖始终保持在门槛外缘内侧,连一毫米都不敢超越。他的灵与肉,成了临时的敌人。
出不出门,这是一个问题,他知道只有迈出去,外面的人才能进得来,他也知道外面的人正等着一层层地剥开他的果皮,企图唤醒果核内的十三名虐待狂,他什么都知道。他眼里的雾影渗入了心脑,本能占了上风,身体乖乖地走回书店。老榕树下的座椅披挂片片新与旧的落叶,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除了落叶外,座椅已经找不到其他的饰品了。他坐下去,拿出手机翻看鹿溪的朋友圈。最近更新的信息是那幅山水画,鹿溪打上了画名——《三个影子的人》。
白先生给鹿溪发了一条信息。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手机悄无声息。他又发了一条语音。晚风翻起了层层的夜浪,他摁亮了书店里的灯。这一刻起,他的世界存在两种灯光:一种是书店的灯光,懒懒散散,透出一种秘密的温暖,宛若无头古兽的体温;另一种是除此以外的灯光,说谎的,虚假的,戏弄的,每一道光影都有一个癫狂的名字,每一道光影都纠缠着无数的趋光虫。
白先生打了一个冷颤。深海海底的无头古兽藏着一个痛苦难安的秘密。或许是它将自己藏在了这个秘密里面。白先生知道自己总有一日将会面对它。出于逃避这种命运的本能,白先生给鹿溪拨打了语音通话。第一通没人接。他非常有耐心地拨了第二通。一个急躁的烟嗓音在电话另一头叫了起来。白先生按住加快的心跳,抓起玻璃桌上的一片落叶,捏得手指关节发出紧张的声音。
你到底是谁?一个烟嗓音问。
白先生听到刀砍木砧板的声音,有种置身于一个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现场的恍惚感,凶手喊着下一个就是你。他慌慌张张地挂断了语音通话。秋夜漫漫,冷汗如露。白先生羞愧得无地自容。他的灵魂得了枯萎病,承受不起半点人间烟火的焦味。溺死时间的,不单是外面的人世之海,还有他自身的怪诞观。
这时,电话铃声追了过来。他本能地以为是快递或外卖,鹿溪的头像在手机屏里跳动。白先生的心跳转移到他的手指上,他恨铁不成钢地咬了咬手指,终于逼迫它以心平气和的姿态去按下接听键。
你是不是鹿溪的同学啊?
我……是他的朋友。
哦,原来是朋友,那你找我儿子有什么事?
就是……他之前不是在书店上班吗?这几天都没来了,想问问他是什么情况。
上班?我没听他说过,那老板有没有给他发过工资?
白先生愣了一下,仿佛听到来自另一个人世的风声。他组织了一下语言,还是不知道如何回答。
那就是有了,那间书店在哪里?
白先生报上了地址。对方说了声“我收档后过去拿”就挂了电话。
“烟嗓音”站在书店门口时,书店吐出的光与街灯将他的身影渲染成一个扭曲的生命体。这名中年男子的头发黑的软,白的硬,这令他的眼神显露出矛盾性——妥协的漠然与生存本能的癫狂。他全身散发出真实的气味,好像有成千上万的死鱼鬼魂游聚在其周围。他的嘴角挂着尴尬的笑。白先生拒绝将他与鹿溪的父亲联系起来。男子直接说明来意,白先生只准许他站在门口,他不能让这名来历不明的男子破了例规。两人互不退让。男子眨眨浮肿的眼睑,身上的灯光夜影,不论是浓的还是淡的,都悄无声息。他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带。
我是鹿溪的爸爸,来拿我儿子的工资。
鹿溪自己为什么不来?
那个没命仔来不了了,他走了。
男子说这话时,眼瞳的表面蒙上一层乳白色的麻木组织。他捧着一个布满多层次、多重迷宫的月亮,来到这里将其交给一个陌生人。一阵惊颤如黄河从九天上泄流而下,白先生听到别人的死讯,被剥夺的却是自己的生命,然后,一切又恢复了平常。
你说的走了,是死的意思?白先生说。
男子冷静了下来。有些如夜色般深沉的话语,只适合说给陌生人听。他说,五天前,鹿溪的班主任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鹿溪去参加班级暑假活动的时候,偷了同学的钱,我当时就问班主任他偷了多少,马上把钱补给了她,我做阿爸的,又没文化,除了给钱外,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他的妈妈是有讲了他几句,他还不服,说是没有偷,他妈妈跟我天天在菜市场杀鱼卖鱼,手脚不敢慢,心性是有些火爆的。结果,那个没命仔还要跟他妈妈打架,我没理他们,直接就出门去了菜市场。搞来搞去,生活,读书,学习班,样样还不都是要钱?听他妈妈讲,我前脚走,他后脚也跑了。到了第二日,班主任就来电话,说是鹿溪在学校的教学楼跳楼了。你说这不是读书读坏脑了?偷钱嘛,还了就算了,有什么了不起,我小时候也偷过,长大了还不是照样过日子?也没见我去杀人放火,你把书读好就好了,为什么要去跳楼?
灯光,夜色,幽暗的绿影,它们运用明暗的对比手法,联手将鹿溪父亲推回到古代山庙的一个时光点,让他成了一具褪色的泥塑。
你就没想过鹿溪是真的没偷?
这是老师说的,哪里还会有假?我们海陆丰人,老师的话就是圣旨。
我小时候经常把我爸骗得团团转,我爸到现在都把我当作是诚实的乖儿子。
鹿溪父亲的面色呈现痛苦难安的状态,曾经深信不疑的秘密,成了一个等待探索的深渊之国。他有些难以置信,一个微不足道的过错,竟然会发生这样的变异。他所有的精力都耗在拒绝承认儿子遭难的现实上,无法同时面对两个敌人。
要不你帮我查查看?我给你他班主任的电话,鹿溪的工资就当作调查费。
我去查?鹿溪出了这样的事,你做人父母的,还天天去菜市场开档做生意,我就是能查出点什么来,有意思吗?
我不去菜市场杀鱼,就会想去学校杀人。
这不是威胁,只是一种单纯的悲苦陈述。白先生的面色沉静了下来,无声地答应了,这位失败的父亲和他一样懦弱。他们彼此置换了敌人,构建了一个怪诞的互存关系。
二
阳光透着温暖的牛奶味,新到的一批书,安安静静地坐在书店的木门外,它們无法预知焚书角有一个火盆等候着它们,对它们而言,死亡还是一个遥远的概念。白先生站在木门内,将包裹拿了进来。书店这扇木门普普通通,像是他与这座城市保持联系的一页书。爬山虎沿着两边的篱笆开创一个新的王国,庭院如一泓轻盈的清水,春的气息,夏的蝉鸣,还有秋的露影,尽是白先生想要的,他知道只要自己不踏出门,便可一直做他的白先生。
白先生从新书的水墨香中嗅到了一首童谣的故事。一个无形的童话世界在他脑海里慢慢成形:带磁石的笔盒、玻璃弹珠、鹦鹉、闹海的哪吒、游戏里的英雄。如此热情、高贵的国度,却被书本出卖给了这座悖德的城。他不知道错的是谁,他一直在这间书店等待这样的国的还魂。
白先生叹了口气,亮起的手机屏幕显示鹿溪父亲发来的电话号码。他机械地迈出书店的门槛,不知道自己是要去寻找鹿溪,还是要去调查他的死因。一扇门,可以因他的选择,分别通往生与死的两极,他如何敢否定这座城、这间书店的怪诞?他的脑海里只有一张古老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鹿溪就读的学校所处之地是一座宋朝的古城。古城的旁边有一条颜色如琉璃绿般缓缓流淌的河,白首渔翁总会在拂晓的固定时刻,一根钓竿垂挂一线云烟里的晓月残星。他还记得那水声深处的故乡味。面前的街道华而不实,高低不平的建筑单调,靠装饰勉强扮演出繁盛的形状,一旦灯火不再亮起,荒废的灰尘会第一时间将它们腐蚀成一具水泥与钢筋的骨骸,朝每位过路人不停地吐它那颓废、灰暗的浓痰。
这是人的城,还是城的弃骨?
白先生想起不久前在门口发生的凶杀案,一只钢的鱿鱼捕食一群皮影戏里的水鬼,事后逃到了月亮,结局无人关心。那个月亮大得几乎占满了整片天空,表面铺着蓝的、绿的、白的玻璃碎片,仿佛它才是地球。
此时,白先生的脚尖距离门槛外缘约八厘米,这是他与鹿门之外的世界的距离,也是老榕树叶掉落地面的秒速。他的脚尖动了一下,挪了几下,这个距离并没有缩短一毫米,喉咙却几乎紧闭了,胸腔的风声回响在庭院里。风信子,紫婵,紫罗兰,那些含苞待放的,将花心付之夜色的,将花香交给泥土的,都不再想明天的事。缺乏美感的光刺破了夜的肌肤,海水从中拥挤了出来。它们的步态如凝胶,似沼泽,伪装出彬彬有礼的绅士派头。白先生双手紧捏大腿两侧的衣角,所有的光都变得刺目起来,玻璃弹珠在耳膜上跳一曲华尔兹,那韵律难以捉摸又不想妥协,最后都以露水的形式逃出他的肌肤,化作丝丝缕缕的风。
他为自己的轻率与鲁莽感到后悔,为什么可以这般轻易地接受鹿溪的死亡呢?这个想法犹如打开了一道闸门,无数的黑山羊从里面跑了出来,等待下一个觅食的机会。
白先生踮着脚尖走回了书店。他走得小心翼翼,生怕被无人光临的书店察觉。这里的树花草木,还有光影里的寂静,都在无时不刻地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整个书店都变得陌生,且有了敌意。他来到焚书角,拆开一个包裹,今天的书都是他从网站畅销榜里挑选的。活了几千年的文字,在这个时代哼着下流的小调,说着谐美的故事。思想一旦贫贱起来,活着就成了罪过,只有火焰才能让它们重新伟大。
白先生烧完一本书,才拿起手机,点开鹿溪班主任的电话号码,拨号键犹如深水炸弹的开关。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依旧保持观望的姿态,脑里却突然思考起一个问题:现在是什么季节?夜色里的花香是阳春的气息,身上的露水分明带着秋的清寒。
趁着他的大脑在解谜的时机,手指擅作主张,按了下去。
电话里的班主任表现得像一只癫痫病发作的蟑螂,说几句就笑几声,笑声沙哑、急促,仿佛整座城市都是她的敌人。或许她真的是蟑螂怪的化身,白先生毫不在乎,他自己就是一只神经衰弱的蜗牛。他们两人借由电话这种世故、冰冷的器物,各自现出了原形。
班主任向他抱怨贫穷的故乡给她带来的伤害,高中老师残留在她过往的色情污渍,学校的降薪,学生的可恶,还有同僚莫名其妙的恶毒。
鹿溪真的有偷同学的钱?白先生说。一场旱情正在他的发音器官上演,他的表情做作,像皮肉松弛的老媪僵硬地哭着。白先生知道他这种丑陋是愚蠢的,自找的。
这不是偷不偷的问题,我把鹿溪爸爸赔来的钱给那位丢钱的同学,他说他的钱已经找到了。我后来想清楚了,这名同学其实也没指名是鹿溪偷的。
那到底是谁指证鹿溪?
没人知道了,班上那么多学生,始作俑者已经没人知道了。你知道的,学生是群居生物,只要有人开了头,其他人就会纷纷附和,他们不会承担独自思考的风险的,他们很享受躲在始作俑者背后作恶的快感。
所以,鹿溪因为一场没有人证、物证的指控而跑去跳楼?
跳楼?班主任提高了声调,谁跟你说他是跳楼的?他是在教室里上吊的,不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绳子是他妈妈给他的,他跟他妈妈吵了一架,说是要去死,他妈妈就塞给了他一根绳子,让他找个没人的地方上吊。
白先生厌恶地挂掉了电话。在这出悲剧中,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白先生知道,包括他在内,所有的人都参与了。
鹿溪是跳楼还是上吊,这又是一个问题。
这座城市活得非常清醒,它有一个陋习,喜欢用新问题作为老问题的答案。无论是鹿溪的父亲,还是他的班主任,白先生都不敢专信一方。他们的社會身份正是他们苦难的源头。他们都是老狐狸,悄无声息地将苦难转移到鹿溪的身上,或许鹿溪最后的结局,正是他们潜意识里所期望的。
一个鹿溪,在一万个人的心里,有一万种死亡的方式。
白先生陷入了深沉的悲哀当中,为鹿溪,也为自己生而为人。这其实是一种虚伪的满足感,他心知肚明,自己连门都不敢出,比鹿溪的父亲和班主任更加卑劣。
门外传来人声。
来访者是位十三四岁的女生,身着初中校服,脚下穿黑白球鞋,抱着英语、语文与数学课本,眼瞳犹如盛满深黑果酒的夜光杯,清澈之余,藏满郁香的秘密,马尾辫温驯地垂挂在清秀的后背,影子则是一丛正在盛放的簕杜鹃。白先生看到街道的无数树影蠢蠢欲动,无名古兽的头发正朝她爬了过来。白先生在她单纯的五官上看到了一丝诧异,他横立于门槛内,丝毫没有侧身或退让的意思。无名古兽的头发追了上来,章鱼开始捕食簕杜鹃。这座人人都想闯进来的城市,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这样的无人察觉的凶杀案。白先生为了掩饰眼里的麻木,强迫面部的肌肉摆出一个世俗意义的笑姿。笑容仅维持不到三秒钟,他就觉得厌倦与疲累。
你找谁?
我爸说你在找我哥。
你来得正好,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爸说你哥跳楼,我查了一下,你哥的班主任又说他是上吊自杀的,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道的道德太过败坏了?
他们都是随口乱说的,我哥其实没有死,他只是逃了。
鹿溪妹妹的眼神坚定,她一字一字道出的话语也硬如钻石。白先生从她的话语中听不出熟悉的理性,他甚至怀疑这座城市只是某个哲人思考时,精神火花所闪现的幻影。幻影从诞生到消亡只是一瞬,城里的人寄生在这个瞬间,从海里的鱼进化到了用车轮代步的人。
那你说,你哥逃到哪去了?白先生说。
我哥之前就跟我说过很多次了,他说这座城市是虚构的,他想要带着他那幅《三个影子的人》的画,回到真实的世界。
白先生理解不了这座城市,却理解鹿溪的痛苦,承认这样的城市意味着同流合污。屈子月下问渡,最后选择了自沉汨罗。
你哥有说他是怎么逃出去的吗?
这我哥倒没说,我哥平时最爱跟我说话了,他说了很多,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过艺术是一种谬论,可是它使人自由,让人不必再为荒谬而死,就冲着这句话,我相信我哥一定还活着。
白先生无法在她的逻辑上找到破绽。他问,你找到那幅画了吗?鹿溪妹妹说,没有,一定是被我哥带走了,我也想跟哥哥一起走的,可是我哥选了他的画。我知道我爸他们跟你说我哥偷钱了,那不是真的,我哥的班主任是在公报私仇。她结婚的时候,全班就我哥没给她贺喜的钱,只是画了幅画当作贺礼,结果她当着我哥的面把那幅画撕碎了,嘴里还骂我哥不上进,都快高考了还有精力跑去画画。我哥也想给钱的,可是那要好几千块啊,我爸妈要杀多少条鱼才能赚够那笔钱?我哥跟我说班主任冤枉他偷钱时,我就知道,报复来了。之后,我哥就带着他的画逃了。
鹿溪的妹妹的花影被阴影章鱼啃食得七零八落,一直被笑容禁锢的凄凉光景露现了出来。她说她昨晚叫他哥给她拿客厅里的书,她喜欢在家里使唤她哥,她哥也乐此不彼。她只唤了一声,窗外很吵,屋里很静,没有人回应。她说她这才真正体味到失去亲人的感觉,很冷,很静,整座城市成了一座黑森森的原始森林。她又说,我哥人不在了,可是周围的人却一点感觉都没有,班级活动照常举行,我爸妈照样杀他们的鱼,连我自己也照样上补习班,一天假都不敢请,我敢说我哥一定还在这座城市里,你帮我把他找出来,我没钱,我可以每年都来你这里打暑假、寒假工,用工资来还你的调查费。
我就奇怪了,怎么你们个个都要我去找你哥?我跟你哥也不熟,你们父母呢?亲戚朋友呢?
我爸妈很古怪的,我哥不在了,他们只是随便编了一个借口,就继续去杀鱼了。他们一开始来这座城市,是想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学校上学,可是这些年下来,他们慢慢就变了,天天只想着去菜市场杀鱼。打个比方吧,要是我跟我哥在马路上发生了车祸,他们路过,知道是我们也不会停下来看一眼的,他们满脑子只有菜市场里的鱼,天天杀,没完没了,我也奇怪,那些鱼怎么杀也杀不完,鱼没杀完,他们就正常不了。我爸妈已经忘记了他们为什么来这座城市杀鱼了。
白先生有些羞惭,勉强地笑着,装出礼貌的样子。他慢慢地侧过身,慢得就像走向行刑台的死囚。他说,进来吧,我请你喝杯咖啡,你再跟我说说你哥的事。鹿溪妹妹怯生生地看向书店深处,天然的厌恶在她青花瓷般的面容上游走。她说,咖啡有什么好喝的,我哥上次让我喝了一口,整晚都睡不着觉。她说完表示要回去复习了。临走时,她说,你和我哥有点一样,眼里总是怕怕的,也不知道你们在怕些什么。白先生一时语塞。书店外面与里面的人,彼此看望的眼神都是一样的。鹿溪的妹妹的花影消失了,代之的是一个普通初中女生的身影。他看明白了,刚才目睹的怪兽食花的皮影戏,只是灯光与夜影的恶作剧。
当天晚上,白先生将鹿溪尚未结清的工资转给他父亲。他还未决定是否要接受鹿溪的妹妹的委托。鹿溪的父親、班主任和他妹妹所陈述的关于鹿溪的一切,本身就是一个人性悖论,一个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进行跳楼、上吊和逃离的行为。白先生认为他们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他们看到的只是鹿溪的一个影子。真实的鹿溪发生了什么,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次日。午后的书店,风信子,紫婵,紫罗兰,没有一片花色是多余的,阳光与老榕树划分出清晰的界限,一路朝西而去,寻找一个蜕变成暮光的节点。白先生又在焚书角的火盆里点起了火,这次的书名,他看都没看。火光里有一种哲学的语言,他的内心产生了将书灰塞入口中的冲动,人世不值得,只有灵魂才是合格的书页。他的时间层层叠叠,暧昧不明,人生就像一盅忘记放盐的靓汤,书店里的一切都不值得回味。他有些后悔,昨天不应该邀请鹿溪的妹妹进来的,书店里的清淡时光,往后怕是再无片刻的安宁了。
书店依旧无人光临,黄昏如约而至。
白先生在抖音上看到一则新闻:考古学家在深圳一所中学的挖掘现场挖出一座宋朝的古墓,木棺里面只有一具少年的白骨,白骨怀抱着一幅画卷。随着镜头的推移,那幅画徐徐而开,正是鹿溪之前那幅《三个影子的人》。他所有的生命活动都汇聚于他的眼瞳上,以至于他丝毫感觉不到自己在呼吸。他确信那具白骨就是鹿溪。鹿溪逃回了他的真实世界,又以非真实的形式回到了这座城。他只是抬抬手指,将屏幕中的画卷划走。所有死的鹿溪都不是他在寻找的,他的当下便是鹿溪最真实的死亡方式。
起风了。鹿门书店是他存在于人世的证据,此时,它在风声中逐渐缩小,小得连一片落叶都装不下。白先生茫然四顾,四周盘桓着顽固的死物,院子里的花草树木,还有店里的书卷味,一切都看不到变好的前景。鹿门之外,活着的鹿溪在等着他。
他走向门口,他要去寻找鹿溪。
任白衣,作家,现居广东深圳。已发表小说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