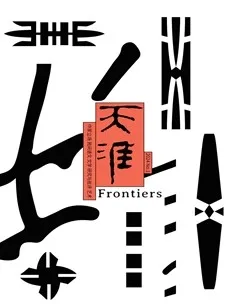记梦(2018—2019)
2024-02-22东西
资料提供者附言
2018年,我在构思并试图写作长篇小说《回响》。每天面对电脑,却写不出满意的情节和细节,于是删删改改,毫无进度更无惊喜,整天都泡在虚掷光阴的内疚里。为了对得起自己消耗掉的时间,便在写不下去时记录梦境,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还在写作,还能写作。但梦不是每天都有,而写却必须进行。非常神奇,自从我决定记梦后,梦就莫名其妙地多了起来,仿佛自己在讨好自己抑或梦在讨好手指,以至于我每天都是先记梦再写小说。梦是现实的投射,没有无缘无故的梦。梦也是一份心理学样本,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出潜意识,而又从潜意识里看到环境?任何时代的浩瀚之梦都由无数个人的梦汇集而成,就像点滴以成江海。这是一次没有设计的记录,真实是它的唯一原则。到了2021年9月8日,我的记梦行动中止,原因是《回响》的写作顺畅了,而梦也越来越少了。当我专心于正业时,副业就慢慢淡出。
2018年1月6日,周日
昨晚梦见自己回到家乡,在我就读和工作过的天峨中学打篮球(我的脚踝因打篮球受伤,半个多月没摸篮球了),与杨秀高(当年的体育老师)在中学面向公安局那一方的坡上打球。球场是新开挖的泥地,临坡一面没有防护,我担心篮球会随时飞下坡去。杨说我们会把球护住。我把正装脱在地上,换上运动服,在篮下投球。梦中隐约感到脚踝疼痛,匆匆收工。
这两天往返于深圳,去书城“深圳晚八点”讲课,在车站走了太多的路,惊动了脚踝。
2018年1月10日,周四
昨晚梦见自己提着几个行李箱去飞机场,到了路上,看见一列车,很长,像地铁的车厢,但是停在马路上。室内装修是S型座位。我上车找到一位置,放下手中行李,转身欲下车再去提放在路边的行李。车忽然动了起来,我跳下车,原先在路边等我的一对作家夫妇不见了,我放在他们身边的行李也不见了。那列车开走了,我顾此失彼,两头的行李均失。焦急,寻找,但都没有结果。最焦急的是丢失了电脑包,里面有重要文件。正在悲催之际,醒了。就想,梦境中的难题可以用醒来解决,但现實中的难题却不能在梦中解决。
中午,趁坐南航飞机回南宁,在机上睡了一觉。梦见一位著名评论家带着几个朋友到我的家乡谷里。准备吃饭,我进屋找酒。屋内的陈设却是南宁的次卧室和铂宫工作室的陈设。翻遍所有纸箱,竟然不见一瓶茅台。我收藏的所有茅台都消失了。我非常内疚,先前说好要用茅台招待他们,现在连一瓶都找不到。只好找了一瓶别的牌子的老酒,结果大家一喝,都摇头。这是第一次在飞机上做梦。
连续两梦都是丢失,可见这几天的焦虑。一是焦虑小说创作的进度缓慢,甚至没有时间创作(时间被会议和各种活动占用);二是焦虑过几天又要到北京跟陈建斌导演修改剧本。
2019年1月11日,周五
午睡,梦。作家朱山坡告诉我,某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到了广西,准备去北海。我一路打听,他到了我家乡天峨县。于是,我赶到天峨。他正跟一桌人喝酒。他说这几天太紧张劳累,今天要喝醉,放松一下。我加入餐桌,一一敬酒,才知道,他是被一位女老板请来的。他喝得高兴,竟然跳起了街舞。我跟他商量到学校做讲座事宜。他在纸条上写了三个字,这三个字我忘了。他说是一部电影的名字,我没看过,叫“肝什么”?这部电影讲的是建筑搬迁和平移的故事,他正讲着,我醒了。
这是一个与现实对应的梦。早上,学生论文预答辩,杨教授说了一个电影名,我没有看过,梦里出现了。午饭时,我去电联系北海文联主席,打听近期是不是要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过来?她说是的。不想这事提前出现在我梦里。
2019年1月12日,周日
昨晚有梦,记不住了,感觉是乱。正应和这几天的心情烦乱。上午去保养车子,午后回,补觉。梦见谁搬家,是个熟人,但忘了是谁。他说家里有50年前的柴火,要不要收藏?我一时冲动,脑海里闪过会不会有珍贵木柴?想去拿,但又想了想,50年的柴火,快变成灰了吧?于是没有出声。似乎还有杂乱的内容,但记不得了。记忆力越来越差是个原因,梦痕太浅也是原因之一。
2019年1月14日,周一
记昨晚的梦。梦见谷里村的三嫂遇到冤案,跟着我进城找人主持正义。她像“秋菊”那样跟着我。具体我不知道她有什么委屈,她边走边说村里的某某某欺负她,把她的一整箱物品拿走了,让我想办法帮她要回来。我忽然想起那个某某某,心有余悸,当年我似乎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随时受人欺凌。走着讲着,好像醒来。
后来,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贺先生的二十六楼,他让我品酒。我把六瓶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最好的是巴马瑶鹰拿来的50年(杂牌)老酒。梦跳切到河北作家李浩来广西,李约热组织夜宵。我们带着刚才品过的酒到富安居附近文联宿舍楼下的小饭店点菜。这期间接到贺先生的电话,他叫大家过去,说已经订好了航洋大厦通宵营业的某饭店。于是大家又往航洋大厦赶去。
2019年1月26日,周六
开会,宿邕州饭店。醒来记住一个梦。梦见在河池师专,我还年轻,到某副校长家求婚,买的是二手玫瑰,很胆怯。进门发现夫人和岳母在房里。她们穿越了,竟然生活在那个年代的那个副校长家里(这个副校长也穿帮了,他是我毕业以后才提拔的)。我生怕岳母反对,但因为她女儿同意,她也就默许了。
一个穿越的梦境。
2019年1月28日,周一
中午眯了一会儿,做梦。梦见自己从卧室出来,发现老人躺在铺在地板的被窝里。正要道歉,发现那人是L。L起床,上旋转楼梯,到一咖啡馆,找了一张长条桌坐上。我一直跟着,坐下后才发现旁边尽是孩童,Y坐在孩童中间,为他们讲故事。我滑到桌上休息。桌下几个孩子围观我。我离开,一痞子装扮的人追上来,要与我打架。我奇怪,问为什么?他指指我的脚。原来我的脚上缠满了纱布,我什么时候受的伤?他说从我的受伤情况来判断,我是好战之徒,故要找我打架。我赶紧溜走。
2019年1月31日,周四
开会,继续宿邕州饭店。凌晨做了一个梦。梦见几个人在我家聊天,其中有G先生,他像《安娜·卡列尼娜》(下卷)里维斯洛夫斯基挑逗吉娣那样挑逗L,眼睛直勾勾地毫不顾忌地看,让我像列文那样难受。这几天重读《安娜·卡列尼娜》,梦在模仿小说。之后,在一楼客厅(仿佛联排别墅的客厅),有一个篮球架,大家在投球(这是不是近几天和正华先生说回天峨过春节,约好打球的原因)。我发现球是瘪的,于是去找另外一个好的篮球,找不到,拿着瘪球出门,到右边汽修厂打气。打气过程中,发现球快裂开了(旧球)。于是另外找一个新球。充满气,拿回家里客厅发现又瘪了,原来那个黑色的球不是球,而是我平时背的双肩包。L在看电视,“马大姐”在远处做着家务什么的。我想那个新球到哪儿去了呢?想了许久才想起在广西民大的家里。
梦里我已经搬到东边的新房了。
2019年2月2日,周六
梦里,在某地开会,在山上。饿了,下山去吃饭。一群人。下山路上碰上WHF,她说下面有食堂。到了海滩边的食堂,有好多人在吃饭。海边有沙滩,有横生在沙滩上的椰子树,还有一些茅棚(无法确认,这些景象是否与上个月下旬去三亚度假有关?)转过几个茅棚,看见C罗在沙滩上颠球。有几个人围着。怎么会请到C罗?有人说是他来做公益,收入全部捐给穷人的孩子。
上山,记得有作家凡一平和鬼子。鬼子与人撞了一个满怀,把那人撞倒在路上。那人好像是WHF。
2019年2月6日,周三
4号回天峨过春节,宿天峨五吉大酒店。晚上做梦。梦见我们在广西新闻中心的楼上找509房间,碰见常哥,说某部门领导召集开会。大家都很忙乱,很紧张(这是否与常哥正在被安排写一出彩调剧有关?我当然也被牵入其中)。
梦里有梦?在梦之前,我在停车场停车。下雨了,我忘了关车门。于是,走出宾馆(不是新闻中心),往停车场走去。宾馆门前有立交桥。在立交桥下面遇克参同学。他拉我跟他打牌。我输了,打开背包,抽钱给他。一小偷凑过来,看见我包里的钱。我很紧张,抽了五十元给他。让他走。他走了。我們继续打牌。
因为回乡过春节,背包里确定放了几万元现金。另外,回乡过春节之前,一位剧院领导一直在跟我商量开某剧的策划研讨会。这个梦是否与这两件事有关?不知。
2019年2月10日,周日
春节,还在天峨。住五吉酒店,调了闹钟,今天要回南宁。闹钟还没到时,被梦搅醒了。梦见自己在一个课堂上,好像是学员,被老师点名对课本提意见。好多同学。我说这个课本没有创新,没有感情。正说着,一位本地的联通老总走进来,夸夸其谈,扰乱课堂。我看过去,课堂的一侧,坐满了他们公司的职员,一个个打扮得像空姐。原来,他们公司的职工也来听课,本来要请一位比我名气更大的作家来讲课,但那位作家没空,叫我顶上。梦里,我的身份瞬间从学员变成了老师。我对这位老总的表现极为不满,宣布下课。我们一起走出来,老总走在前面。我跟上,对他说你没有教养,试想如果是你在讲课,我在下面高谈阔论,你会怎么想?他做出一副谦虚的样子,其实骨子里并不谦虚,问我是吗?我说,是的,你没有教养。他再也没说话,朝长长的台阶走上去。我在后面跟着,加快步伐想超越他,想抢在他的前面走到台阶顶部的平台。因为,在那里停着我的车。我认为我的这辆车能证明我也不是没有财富。你老总虽然有钱,但我也不缺。但是,我还没走到台阶顶部就醒了。
晚上8点回到南宁,补记此梦。
2019年2月15日,周五
昨晚梦见父亲住院,好像是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现实中,我父亲从来没到过南宁,我工作不久,他就去世了)。我从外地赶回,看见H在医院里。是个大病房,有十几张床排着。我没看见父亲,只看见病床上零乱的被窝。也没看见母亲。只看见H。我说了一些感谢H的话。然后,想到一院(梦里在二院的东边,连在一起,像宾馆)还住着一个朋友,就想去看看。但我走出二院往东,怎么也找不到那幢梦里的一院楼房,似乎一院不在这里,是我记错了。我急赤白脸地转了几圈,从东边楼道走到西边二院,中途看见林老师和师母。他们住在一间小房里,我和L招呼他们。岳母也好像在场,她做了开胃的菜端上来。林老师说一直吃不下饭,只有喝几口茅台才想吃饭。我说马上回去给您拿茅台。大家摆菜,聊着,梦里已经忘记了父亲,好像来医院就是来看林老师的。
2019年3月3日,周日
昨夜的梦。梦见自己到了一个极具异域风情的地方,好像是墨西哥。我看见海边的椰树或者草棚,看见墨西哥汉学家L在一间房子的后面炒菜,她面前是一个大灶台,灶台上是一口大铁锅,炒的是杂碎,黑乎乎的一锅。我不敢吃。然后,跳到文学聚会现场,来了许多文学大咖。我找一个作家照相,以为他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好像他还活着),结果这个人竟然会说汉语。我知道搞错了,去找那个卷发的略黑的作家(我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长什么样)照相。这次找对了。我介绍我的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他一愣,说去年我们在法国见过面。于是,想起一次法国的聚会(梦里的想起,不是现实),一位作家向他介绍我,也讲了《没有语言的生活》给他听。他说这个小说很棒,构思太绝了,所以当时对我就有印象。
引发这个梦的原因可能是:一、经余华兄推荐,法国文献出版社正在跟我签订法文版《篡改的命》的合同;二、前几天跟陈建斌导演在北京讨论电影剧本《篡改的命》第四稿,他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构思简直就是奇绝。
2019年3月4日,周一
午梦。梦见一系列紧张的事情,却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和几个人在新都宾馆打牌(跟谁也是模糊的),一直打到深夜,J先走了。我打到深夜,出来见H与一红衣女子(相貌狰狞)在大门停车场等我,说是有要事商量。她俩吓我一跳,我心里一阵害怕。心想,难怪J先走了,是不是她已经看见她们故意先走的?那个红衣女子,仿佛中午下班时在电梯里看见的那一位?长相确实有点凶。至于紧张心理,一定与春节之后的系列压力有关。家庭的、单位的、身体的、经济的……
2019年3月7日,周四
午梦。梦见原也用纸包了捏曲的钉书钉、弯曲的针和一根小小的捏曲了的铁丝(像牙签什么的),落在地面,被苏格(我家养的猫)吃下。我们很紧张,却没有办法让苏格吐出来。苏格蔫头耷脑地躺在垫子上。我为苏格打麻药,动手术,目的是取出它胃里的针。肚皮剖开了,它的胃贴在脊梁骨,没有针,找不到,我很着急。想缝上,针又没取出来,而且也不知道怎么缝。L一时在我身边,一时又不在。我正在着急、担心的时候,恐怖的事发生了。一丁(我家的另一只猫)扑过来,竟然咬住苏格的内脏,扯下来跑开。我制止不住。苏格一命乌呼。痛醒,吓醒。
2019年3月11日,周一
昨晚,梦见和一群人在宾馆里,遇见领导Q。他休假,正在写小说(他怎么会写小说?)。胡红一说他有一个小孩要进西大附中读书(他的小孩子都工作了吧)。这个信息被同桌的什么人听到了。他们利用这个信息,打电话给领导说可以帮他的小孩子办进西大附中(现实是Q的级别比校领导还高)。他上当了,告诉了对方密码1024。我担心诈骗者会用这个密码攻破他的账户、信箱……内心一直緊张。
梦里出现一卡车茅台酒,似乎只要输入这个密码,那一卡车的酒就属于输密码的人了。脑海里出现清晰的画面,是流动的卡车上一壁的茅台酒箱。密码输入时,那一壁纸箱像电脑的屏幕。纸箱屏(类似电脑屏)有一条横杠,密码输进去了。后来,就断片了。
2019年3月12日,周二
记住昨夜的一个梦。梦见与陈建斌在山中一宾馆讨论剧本(现实中正在修改根据《篡改的命》改编的电影剧本),碰见一些熟人,都不明晰,是一些想见的人,也有不想见的人,一丝喜悦依稀记得。然后,我们往东,说是去上海。没有坐车,而是走路。建斌说一边走一边看拍摄外景。到了一临水的地面,草地上划着一排排格子,是划给人起别墅的。位置真好,水非常蓝。然后到一菜市,出现田耳和张柱林。田耳被陈导欣赏,说今后的剧本都找他策划和把关。然后,我们到一锯木厂,看见一截大木头放在木马上。陈导要我和他锯木头。我一边锯一边讲解,那是童年和少年在乡村看别人锯木的记忆。
2019年3月19日,周二
凌晨2点被噩梦惊醒。梦见L端着一盅黄灿灿的红茶进入卧室,说今晚要修改作品。我入睡,床竟然在路边,是露天的。我睡左边。床外的左边是一排冬青树,冬青树外是马路。景物是白天景物,几个人影从地铁口出来,经过冬青树外。一坨宽大的黑影停在冬青树前,我伸脚,竟然顶住了她的身体。她一动不动,向我压来。我只是感觉她要压下来,而其实这坨影子没动。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了我的双手和身体。我喊“杀人啦”“快来人啦”,瞬间惊坐起来,看着左前。卧室的灯还亮着。L还没睡,她说听到我喊。
接着,梦见自己与作家L,导演F以及演员F在卡拉OK包厢喝酒。我们都喝醉了。F把我引进洗漱间。我们亲热起来。正在欢悦之时,F忽然停止,说不急,等回宾馆休息了再继续。
接着又做了一个梦。好像是导演催剧本。我说快改好了。
都是令人紧张的梦。
2019年4月4日,周四
上午拜山回来,在饭店与黄家亲戚聚后回家,休息,做了一串梦。
之一:梦见在乡村有几圈牛,黑压压的一片。有人把牛从大牛圈里赶出来,关进四四方方的小牛圈里。牛关进去了,这个四四方方的牛圈就像一辆车似的动起来,沿着黄泥公路往城市的方向行驶。牛就是这样被运进城市的。但牛不规矩,又闹又踢。有人说,其实应该叫人赶着牛群进城。
之二:在一幢几十层高楼的底部,我有一套豪宅。作家H来访。我们没有坐电梯,爬了几十级红木做的楼梯,到达。我有一套高级音响。H要听摇滚乐。他找了许多过去的磁带来播放。
之三:在打篮球。像是露天球场。篮球飞了出去。阿团救球,场地变成清厢快线的路面。球飞下去。在水中漂浮前移。那球是我的。我盯住球。球越漂越远,漂进前面一座工地。桥面变成了大楼工地,我站着的位置变成了工地的楼层。球在地下层漂,漂到水面架着的木板下。
醒了。
2019年4月7日,周日
昨晚梦见与贺先生在韶山。发现我在多年前用150万元买了三百多亩地。这块地有山、有水、有石头、有树、有稻田、有人家,我沿边界周游一圈,保存完好,唯一有个地方被小卖部户主占去一尺宽,经当地领导协调,户主答应不再占。领导说这地盘必须马上动工,否则就要收回了。我着急,找贺先生商量,他说愿意用几千万把地买了,交给他的女儿经营农场。他女儿一直想自主经营一个农场。我的心里“啷格里个啷”,可惜醒了。
做这个梦的原因:一是跟贺先生和梅先生到韶山几次,均是陪他们去谈买地;二是梅先生在陈述买地理由时说要做实景演出,即稻田的艺术;三是本人有财富缩水的忧虑。
补记:前几天有零星的梦,没有记录。只记住其中一个,梦见余华来广西,大家相谈正欢,托我打电话给防城港某先生。我翻找电话记录,明明看见某先生的电话,却怎么也按不出来。着急,叫别人打,他们也按不出那个电话。拿别人手机打,也调不出。总之,此先生的电话是眼睁睁看着,却无法拨出去。曾经有过类似的梦,不知道是现实的什么投射?
2019年4月17日,周三
近日胸闷,很担心。午休时梦见自己到车站为母亲送行(母亲已去世多年,经常梦见她)。车站在南宁市圆湖路一带。因上午看了一个关于心梗的抢救短片,午休时似乎还惦记。这么想着,梦就开始了。我刚把母亲送进楼去(普通住房,小高层),就发觉她的身份证或什么重要证件忘带了。于是返身回去拿。母亲活着时与我同住在南宁市民主路,离梦中的车站很近。我刚要返身,就见常哥举着证件赶来。他说是来送证件的。我们走到楼下,正要对着二楼叫母亲。忽然,常哥晕倒了,因为心梗。我立即按上午看的短片知识展开营救。先是打他女儿的电话,现实中我手机里明明有,但梦中怎么也找不着他女儿的手机号。看看手机里的人的头像,估摸着拨一个。接电话的是我家从前的保姆,她说现在在常哥家打工。她说她马上告诉常哥的女儿。没想到,常哥这会儿醒了,他从地上爬起来,说没事,他要回去。我阻止他,他不听。然后我就醒了。
这是一个胸闷者因受现实短片的刺激而在中午做的梦。
2019年5月5日,周日
早上六点起床,记住一梦。梦见我还在河池工作,住在一个丁字路口的楼上,楼下是各色小卖部。我和原也还在睡觉。他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我们睡在一张床上。我看见H兄和S兄出现在楼下(睡在卧室里怎么会看见楼下)。他们说来看看我。我赶紧下楼迎接。路边摆了一张小桌,我们坐在桌边喝茶。H兄提出三人打打牌(他是不打牌的)。他说了一种湖南打法,我基本不会,但S兄很快就会了。我糊里糊涂地打着,想要去给他们买几条烟。我离开了,在河池的街道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烟摊。我在河池工作时的工会附近的街道一一出现。但就是没有烟摊。忽然想起,我的车上还有几条烟(回到现实,我的车上确定有几条别人让我转交而又一直转交不出去的烟)。我在二十年前的河池,寻找二十年后我在南宁的轿车。找着找着,一直没找到,梦就断了,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远道而来的朋友。
2019年5月29日,周三
与友人贺先生等,到一个有中国画风的地方,即有山有水有亭臺楼阁。贺要我说一句他楼盘的广告。本来,他想要我约几个作家过来,每人说几句,但他们都没有时间来。只好我来说。我说,投资有风险,买房要谨慎,我选某某楼盘。广告拍得很粗糙。贺说,没关系,先这么播吧。
画面跳转,我在一间房里。L在梳妆。我躺在床上,好像是熬夜打牌累了,需要补觉。另一位牌友,不知道是谁,躺在我身边一同补觉,两人躺在一起像同性恋。L梳妆完毕,站起来,画面立刻变黑。
在一个培训班,六张床位住了三个演员,我在其中。S兄来看我们,他也是来参加培训的。大家坐在床上聊天。忽然进来三位非学员,他们订了另外三张床。他们一边说话一边往地上吐痰。
三个梦断断续续,就像我现在的工作一样零乱。第一个梦,是因为我在贺先生处买了房子,有现实的投射。第二个梦,仿佛是我跟L刚结识不久的状态,那时我单身一人,常跟朋友们熬夜打拖拉机。第三个梦,没有来由。
2019年6月7日,周五
现实中遇到太多的鬼,梦里昨夜又遇见。一恶鬼在一米远处纠缠,于是我跟鬼对骂,叫它滚!它越来越凶,双方对骂升级。L在一旁安慰我,让我避让。但我还是对抗到底,直到骂醒。对那些生活中遇见的鬼,我总是站在鬼的立场和角度来劝说自己,原谅它们理解它们,不惹他们。但梦中,我终于跟鬼暴发了冲突。我想从今天开始,对生活中的鬼我也不应该妥协了,必须像鲁迅先生那样,勇敢地面对,哪怕独自战斗。
2019年6月13日,周四
午梦,在八腊乡。与L、原也回到乡里。好像是去参加胜业父亲的丧礼(他父亲早几年就去世了,是我的表姐夫,他不在八腊,而是在天峨县城),又像是为了回去看我的母亲(我母亲也在2007年去世了)。仿佛是办完了该办的事,我在一条小河边找到胜业,几个人年轻人陪着他。我说你们守夜辛苦了。但需要叫他去谷里跟我母亲办一份合同,像是汽车保险。我是为了照顾他的生意才跟他办的,甚至怀疑他收了我的保险金后会不会真的去保险公司帮我办理?但为了帮他,我必须这么选择(这个心情和近期我推荐一位朋友移民美国一样,我心里怕推荐会带出什么麻烦,但为了他我又不忍心拒绝,最终写了推荐信),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汽车保险要他去跟我母亲订合同。他说他马上去办。我说原也跟他同去,看看奶奶。他们出发了。
回到房间,L在看手机。我把刚才处理的事跟她说了。她翻身继续看手机。我的思维忽然跳到如何跟单位请假。我想说是回乡埋葬母亲,但母亲还活着,将来她生病了我又如何跟单位请假?于是就决定跟单位领导实话实说。醒来,无限伤感。母亲已经去世多年,我还吩咐原也和胜业去看她。母亲明明已离我而去,在梦里她还活着。而胜业,目前还关在监狱里。他是我的表侄。因昨天晚上聚餐时说到他,今天中午入梦来。
2019年6月15日,周六
午梦。俄国译者带了十几个人来旅游,大家坐在冰雪覆盖的地面围桌吃饭。凡先生和毛导演在桌。吃着喝着,凡先生跟一醉了的俄妇开房去了,那个俄妇明显在挑逗他。我跟毛喝了几杯,酒席处变成客厅。见那位翻译,好像是罗季奥罗斯基,他和他的夫人以及孩子坐在一起,我跟他聊了几句,就出门散步。
散步是正常的南方景色,一位衣冠不整者被两个戒严的人喝斥,说不体面,这几天有重要人物到来,所有人都必须穿戴整齐。我前面走过去L,她没有被拦,我被拦住了,因为我穿的变成了运动服,脖子上还搭了一条擦汗的毛巾。戒严的说我这种装束,有损城市形象。我辩解,甚至生气,硬闯过去。走着走着,L不见了。我来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有水库,有大树,有小岛,典型的山区。那里有一群值班的人。他们看着我,似乎很警惕。他们说明天这里有重大活动,不能出入。我说我只是来散散步。中间仿佛有我认识的人,于是我被允许走进山谷。前面走着一对母子,像是俄国罗先生的夫人和小孩。她们走进山谷后,被人跟踪。我怕他们出事,拼命追赶。但他们似乎是仙,快速登上山顶,不见了。我着急,心想万一他们不见了,我如何交待。好像他们也是我求情让他们进来散步的。我又返回了刚才那个有水库有人戒严的地方。遇见一位矮个子熟人,具体是谁不知。他允许我再次进入山谷。他跟着我进山。满山的树,很美。突然出现篮球场。他不见了。一群人在球场上打球。他拿着两个篮球上篮。因为他是隐形的,谁也看不见他,他可以在球场上躲开所有人的防守。而我看见他了。他是慢慢显现出来的,从球开始。
醒了。跳跃的梦。都是平时的生活场景,接待外宾,喝酒,散步,打球。但一直处在紧张中。这和我近期的内心紧张有关吗?
2019年6月18日,周二
在罗城参加会议,晚八点与凡先生赶回南宁。路上,H一直在用微信指责我,说我强求YY去参加什么活动。我反击,并责怪YY处理不当。我心情不好,心想今晚一定会做噩梦。果然,半夜梦见一条蛇咬我的右脸,后来是两个蛇头在咬右脸。我吓得往左边一翻身,仿佛跌落深渊。当我左边身子碰到床板时,惊醒了。
2019年6月24日,周一
昨晚梦,自己随一行人沿红水河谷往山区走。这一行人中有佩华,有领导张某。我们来到山中,是张的家乡。他的家乡正在搞旅游。他亲自出马做创意。我们看村里的第一个节目是灯光秀。一根大柱子,或一面墙壁,上面打灯光,演出一个穿越的故事。第二个节目,村民着少数民族服装,围坐唱山歌。张在里面,买力地唱。为村里的旅游业,他也是拼了。现实中,张是副部级干部。梦里他已经退休了。我竟然梦见他退休后的生活。或许,是周围越来越多的人退休的缘故。
2019年7月2日,周二
梦见几个熟悉的作家到八腊乡采风,印象最深的有佩华兄。去了一个老板,是谁不清,反正是附庸风雅的。他带了一位美人,脸色红润,年纪很轻。她趁老板闪开时勾引我。弄得我很紧张也很激动。但周围都是人,我保持了极度的克制,不至于丢脸。
然后,在八腊乡的正街中间,摆着地摊,可以喝咖啡(竟然如此洋气)。一位女作家说她想来想去还是要写作,是写作改变了她的命运,给了她最多的好处(现实中这位作家一直在写)。梦中,她像一位久不写作的人在自责。
2019年7月5日,周五
晨起,打球,右脚踝扭伤,已经是第四次了。这几天心情燥热,前天考核完毕,我在图书馆停车碰飞后视镜盖。今早又脚伤。想起昨晚一个梦,也许是不好的征兆。梦见孩子外婆家正在安葬外公(其实他外公已经去世多年了),仿佛是在一片草坡上。外公的尸体停在墓穴里。我们正在忙碌,忽然看见母亲拿着刀来帮忙砍草,她带着深深的内疚。母亲去世也多年了,我很高兴能在梦中看见她。
2019年7月5日,周六
昨晚梦见在编辑部,有点像我曾经供职的报社副刊部,但不是那栋二十层的高楼,而是三四层高的旧楼。办公室很宽,推车上摆满了报纸杂志。蒋作家要查资料,我把自己收藏多年的杂志(主要是发表我作品的)全部拿出来,让她翻查。仿佛一转眼,那些杂志全不见了。她说送到二楼当废纸打包了。我即奔二楼,二楼打包的人说已经让车拉走了。每天从这个地方要拉走几十包像单个书柜那么大的废纸包。我叫蒋赶快去追。但那么多一模一样的纸包,根本就找不回来了。我说太可惜了,里面有几位名家的长篇小说首发杂志,语带怨气。
梦跳了一下,回到编辑部,看见韩少功兄长和一位陌生人坐在里面。我准备泡广西茶让他喝。他说他自带了湖南茶。
2019年7月8日,周一
梦见桌前有一份合同,旁边站着NBA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和伊格达拉。我们在逼伊格达拉签约湖人。只记得这个画面,没有结束。这个梦和近日看NBA交易有关。因为是湖人球迷,我为他们补强着急。
2019年7月16日,周二
昨晚在梦里见到了久违的李冯。他是“三剑客”之一,后来辞职去了北京,据说现在住在北京郊区的别墅里,写作,拍电影。梦里,他住在一栋历史悠久的别墅里,我们坐在阳台上聊天。有几位作家,也有李冯的夫人(都是模糊的)。他办了一本画刊,约我给他一个访谈。我发愁,说现在的访谈大同小异,已经谈不出什么新内容了。但是,我想起广西大学有一位做桂学的专家曾经给我做了一个访谈(梦中梦,根本没有这回事),至今没有发表。我打听那个人,找了几个人,才找到他的电话。然后,叫他把电子版发过来。(为什么会梦到访谈?白天华东师大的肖庆国博士从网上查到了多年前一位记者对我的访谈,用微信发给我。)
作家們都到楼下去吃饭了。我还在楼上找邮箱地址,要把那份访谈发给某个人。明明是李冯约我,梦里变成要发给另一个人。我在台式电脑上捣鼓了许久,都没把电子信件发出去。突然手里出现一份打印的访谈稿,访谈者叫蒋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梦里曾出现三个字的名字。好像是发出去了,我下楼,在楼梯转弯处穿皮鞋,穿了很久都没穿上。我内疚,因为楼下等我吃饭的人已经等了很久,还有余华兄。我赶紧跑进一楼的包间。桌上每人一份越南米粉,就是在法国吃过的那种越南米粉,粉碗的旁边配了许多张牙舞爪的野菜。大家都说好吃。(为什么余华会出现在梦里?也许是白天我曾给他转发了一条微信推文的缘故。)
后面的就似乎断片了,或者梦就在这里结束了。有点想念李冯,记完这个梦,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2019年7月18日,周四
在墙门的前面有一块平地,两边立着几个讲坛。有疑问或需要帮助的人到这里求助。于是,那些有能力的人(竟然有NBA球星)都会走出来,为求助者解决问题。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能力指数,如果遇到指数高的,你的决议提案或者想要解决的问题就能解决(似乎是这样,有些模糊了)。最后是我出现在这里,我是来求助的?好像是,也不是,或是来解决问题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我的能力指数是57,不到60,非常沮丧。但有人说,这个指数已经是近期最高的了。
昨晚,一个莫名其妙的梦。
2019年7月23日,周二
梦见一个几百平方米的牛圈,所有人都出去,让工人起粪。这所有的人为什么聚集在这里?不知道。忽然这里就变成饭店。中间饭桌,周围是热气腾腾的各种小吃店。
一位县里的同学请我们吃饭。饭前,在一张长条桌边,他拿来一摞书,是他为我出版的作品集(为什么要他出版?)。旁边有谷里屯来的亲戚,好像是田兴强或秦树林。他们要把这书带回谷里。
忽然,同学脖子上挂着两块牌,是他父亲和母亲的灵牌,每块牌又变成小罐,里面装着他父母的骨灰。他说明天要回家乡安葬他父母。他说的葬是葬骨灰。墓地宽,可以合葬他父母两人的骨灰。
2019年7月24日,周三
昨晚梦到创作。梦见我创作一个男主人公,他一直在跟别人说他的夫人,后来发现夫人是他的虚构,他没有结婚,却骗了亲人朋友们一辈子。她夫人竟然是几个字母,在我的小说中。
2019年7月29日,周一
昨晚梦见满姐夫在一间零乱的办公室里,他有急事赶飞机,但要坐飞机需写一幅书法。他怎么也写不好,时间紧,他直接写了自己的名字。他拿着两盒美元,说是要强冻,仿佛是预苗(也许是他长期做防疫医生的联想)。有工作人员把那两盒塞进柜桶,柜桶竟然是冷藏器。坐飞机的条件是必须等这两盒全部冷冻。柜桶像书柜,外面遮一层纸,四处漏风,无法保住冷气。我们绝望地等着,似乎永远没有机会。
镜头转到草坡河滩。一群黄色的羊在河滩斗角,它们仿佛是监视我们的哨兵,不让我们离开。我幻想家乡有一群更威猛的羊,它们会来救我们。果然,沿着河滩走来一群威武的黑毛羊群,它们把看护我们的羊吓住了。我以为它们会跟这群羊斗角,不料它们左转弯,上坡,朝家乡的方向走去了。它们好像是要把这一群羊带回我的家乡。
羊群雄赳赳地走上草坡。
2019年8月5日,周一
半夜醒时,提醒要记住梦。但早上打完球,忘了。好像是几个梦叠加,只记得情绪,是愉快的情绪。仿佛是我和佩华兄等人开车去完成一个什么任务,车行在人流中,生怕碰伤人。而这个任务,是愉快的任务,并且有信心完成。
午睡,梦见歌手X到我家,邀请我为她写广播剧。家住一层,有一个拐弯的客厅,有点像我在河池时的房间,但楼层有区别,家具有区别,梦中这个更高档。母亲还活着,在厨房为我们泡茶。她主动拥抱我,还有亲昵动作。我让母亲先别泡茶,要找好的茶叶,我翻遍茶柜竟找不出一包好茶来。杯子摆上了,紫沙壶摆上了,却没有好茶叶,我非常着急。X似乎困了,到房间休息。我到处找茶叶,仿佛一种困境。忽然母亲拿出一小包好茶叶,像大红袍。我问,在何处找到的?她说,是H给的。H没有出现,茶叶她如何给?我困惑,开始泡茶。X起床了,来了一群她的熟人。家里很热闹。
2019年8月6日,周二
在一间会议室里,学校领导宣传有几位公示而不能提拔的干部。原因是他们有“瑕疵”。具体是他们到村里抓扶贫工作,收受了农民送给他们的土地,然后起了四合院。梦里出现一个坝子,中间一条长长的泥路,路旁有一个村庄。校长在晨跑。
然后,我尿急找厕所,有人指二楼。上去,有一个四方形卫生间。然后第二次尿胀,与柱林上去,发现下水道堵塞了,满满的一间水。有人在疏通。
再跳一梦,梦见自己收到一礼物(不具体),里面夹一封信。信抬头有来信者名字,叫WGG。她是一位女性,说想念我。此信正好被夫人看到。她问这人是谁?要我好好交待。她还说去年跟我去意大利旅游(现实是前年去意大利过春节),有一辆车差点把她撞倒,是我设计的,想谋害她。我拿信上楼,这个楼像是别墅的二楼。看着信,我不知道此人是谁?心想寄点礼物给我惹出一堆麻烦。正在忧虑,看见胡红一上楼,他的脚一瘸一拐,仿佛受伤了。而楼梯变成了毛坯房的楼梯,就是工地上还未建好的别墅楼梯。
醒来,凌晨三点。继续睡。
2019年8月12日,周一
昨晚梦见自己与家人坐在客厅里,西式的别墅客厅,有几个客人,气氛融洽。客厅有一张原木长条桌,岳父和客人坐在对面(岳父其实已去世),夫人和岳母坐在我这边。我出了一本作品集,很兴奋地拿出来递给岳父。他脸色突变,说这都是旧作品,不值得兴奋,应该写出新的作品来。众人尴尬(这正是我目前的焦虑,新长篇写作一直不顺畅)。
2019年8月13日,周二
昨晚梦:两个好朋友,在民國即崩之时,一个到了台湾,一个留在大陆。他们每隔一段时间交换一箱物品。台湾的拿来一箱食物,大陆的拿来一箱文件。大陆的拿到食物后,变卖,再买文件给台湾的。像小说构思。两人从青年一直交换到白发苍苍。
资料写作者:东西,作家,现居南宁。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