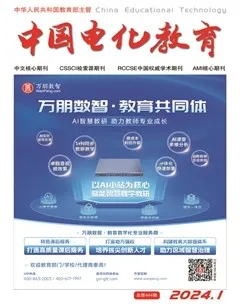学术部落及其领地:当代学习研究中三种文化的对立与融合
2024-02-18周子荷刘三女牙李卿郑旭东
周子荷 刘三女牙 李卿 郑旭东
摘要:该文使用学术部落及其领地这一学科文化的人类学隐喻作为概念框架,对当代学习研究的学术部落及其领地进行了分析,鉴别了其中存在的三种文化并对其内涵进行了阐释,提出学习科学的文化是认知的文化,学习技术的文化是认知造物的文化,学习工程的文化是造物的文化。以此为基础,对当代学习研究中三种文化的对立产生的历史后果及其超越进行了探讨,为此需构建科学—技术—工程的文化连续统,建立学习研究的“生态学隐喻”,改变学术部落中的学术实践,形成一种全新的、更具内在统一性的学习研究文化。
关键词:学术部落;文化;认知;认知造物;造物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本文系2023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具身视角下的智能教学场概念模型构建与应用策略研究”(项目编号:CCA230339)研究成果。
① 刘三女牙为本文通讯作者。
20世纪初心理学家转向教育[1],推动了学习研究从“猜想”到“科学”的历史跨越[2]。历经百年探索,当代学习研究已成为一个跨学科、多层次的专门领域,初步形成了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和学习工程三足鼎立、耦合发展的基本格局[3]。科学、技术和工程三种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激荡,既对学习研究的统一性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潜在地蕴含着开辟学习研究未来新天地的力量。
一、20世纪学习研究的部落及其领地
学习研究是一个公认的跨学科领域[4]。不同学科共同构成了一个多样化的学习研究生态系统,让对学习的探索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但如何理解和驾驭由跨学科带来的复杂性挑战,更好地促进学习研究这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演化发展,既有研究都是在学科交叉的意义上泛泛而谈。比彻(Tony Becher)和特罗勒尔(Paul R. Trowler)提出的“学术部落及其领地”概念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更有力的框架,有助于在文化这一层面上更加深刻地理解学习研究这一跨学科领域持续发展的内部动力机制。
(一)学术部落及其领地:学科文化的人类学隐喻
比彻和特罗勒尔在《学术部落及其领地》一书中将彼此隔离、共同性少、交流也不多的各个学科共同体比作“部落”,它们在同一块知识领地上生活与劳作,内部共享着相同的信念、文化和资源,但与其它的部落却很少往来。“学术部落”作为一个人类学隱喻,指向的是致力于某一学科知识领域的学者群体,他们共享着某种价值和文化、态度和行为方式。很早就有学者发现,“不同的学科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相互作用……许多学术范畴都有自身的学术部落”[5]。《学术部落及其领地》一书探讨的“学科地域”和“部落文化”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特定的学术群体组织及其学术生活的方式。这里的“文化”,代表了一系列被认同和接受的价值观、态度及行为的方式,并由于学术部落内部人群周而复始的知识活动得以整合、强化,成为一股影响学科实践潜移默化的强大力量。在不同的学科领地上栖居的学术部落必然会有许多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信仰及行为方式[6]。
学界围绕学科文化的知识、规范、行为及精神层面,对学科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克拉克(Burton R. Clark)将学科文化概括为一种“只能由其成员含糊地感受到而不易为外人所知觉”的“难以把握”之物[7]。学科文化还包括“偶像”:在物理学家的办公室中,墙上挂的画和书籍的封面都有爱因斯坦、普朗克……[8]。欧尼海伦娜(Oili-Helena Ylijoki)指出:“学科文化的核心可以概念化为道德秩序,它定义了流行于文化中的基本信仰、价值、规则与愿望,并构成了群落的根本特质”[9]。比彻认为,“使用文化的概念,意味着需要看到学科社群内或学科社群之间从知识的认识论结构到日常学术实践的社群因素整个范围展现出来的特征和模式”[10]。不同学者对学科文化的理解存在差异,体现了学科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张力。
(二)当代学习研究的学术部落及其领地
学习研究作为一项社会活动,各种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念会直接侵入到研究者的“实验室”之中。不仅如此,学习研究以人为首要对象,包括学生、教师、管理者、家长、政策制定者及他们所处的环境。这些对象都是主动的个体,涉及到认知、情感等隐性因素,行为极为多样化[11],而不是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被动材料,这赋予了学习研究综合性与复杂性的特点。为此,学习研究不断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力量,试图全方位理解和驾驭学习。当代学习研究渐成一个跨学科领域,包含了心理学、教育学、哲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在内的诸多学科。这些学科构成了学习研究的学术集群,且因学科之间具有的亲缘关系而共享着某种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但在宏观上却表现为三个边界明显的学术部落,即学习科学、学习技术与学习工程。三者发展的历史轨迹与追求的目标大相径庭,遵循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及价值观念。学习科学这一学术部落包含了认知科学、神经科学、教育学等,这片土地上的群体共享着有关学习研究的基本假设,以追求有关学习的真理为目标,强调逻辑、分析的思维模式,产出的是学习的科学理论。学习技术这一学术部落囊括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技术学科,部落内部分享着有关人类在教与学过程中运用的一切物质工具、方法技能和经验的知识,以探索学习实践中工具的应用为目标,体现了实用、目标导向的思维模式,产出的是学习的技术工具。学习工程这一学术部落则汇聚了系统工程、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部落成员共同探讨学习实践中综合各因素以达到系统整体最优的设计方法,以提升学习实践的效率为目标,反映了整体、系统的思维模式,多以团队为单元开展活动,整合科学理论与技术工具开展设计与造物,产生的结果有着更强的综合性。
(三)当代学习研究中的学科壁垒
学科高度分化和专业化是当代学术研究最基本的趋势,这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后果。前者催生了不同的学术部落,极大增强了学术研究的生态多样性,为知识创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后者则加剧了学术部落自身的封闭性,阻断了学术部落之间的对话与理解,扩大了不同学术部落之间的隔阂,并使其龃龉不断,其极端后果集中表现为学科“鄙视链”的出现。某些学科分支在自己的知识领域越挖越深,会“挤压学科整体文化,并……威胁到学科的统一”。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部落内部,成员相互分享着有关理论、方法论、技术和问题的信念,发展各自的文化;而在部落外部,不同部落则通过建立层层壁垒宣誓自己的主权,阻隔了部落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由此导致了文化的对立。具体到学习研究这一领域,可以发现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学习工程三个学术部落尽管共同栖息在学习研究这块领地上,但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壁垒。一个学科群体的职业语言和专业文献具有排他性的特点,在建构学科的文化身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有学者通过对学习科学与教育技术这两个领域之间论文互引的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与这两个领域相关的文献几乎没有重叠的部分”[12],二者之间的隔阂由此可见一斑。
学科交叉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杂交优势,可以为研究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过去一百年学习研究之所以不断取得进步,学科交叉发挥了巨大作用。时至今日,学习研究已经演变为一个包括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在内的一个跨学科领域,并形成了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足鼎立的基本态势。这是一种更高层面的学科交叉,也必然会给学习研究带来更大发展。然而,鉴于不同学科在进入学习研究这一领域时总是不可避免地秉持着各自原有的文化传统,尽管大家面对的是同一个研究对象,但并不必然拥有相同的学科愿景,原有的学科本位总是不免凌驾于学习研究这一新的学科本位之上。如果说,在具体的学科交叉时期,这些学科因为亲缘关系还或多或少地分享着一些共同假设,那么到了科学、技术与工程这一更高层次的学科交叉时期,相互之间的共识就变得更少了。
二、学习研究中的三种文化:内涵与释义
所谓“文化”,即“以文化之”。这里的“之”是指实践,“文”则是指以言语或器物等形式对实践的集中表达。学科文化则是对学科实践的集中表达。借助学术部落及其领地这一概念框架与话语体系,我们已经鉴别了当代学习研究中存在著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和学习工程三大学术部落,接下来就要对这三大学术部落在各自领地上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文化之内涵进行具体阐发。只有在真正理解这三种文化并把握其本质内涵的基础上才能找到促使其走向融合的道路。
(一)学习科学的文化是认知的文化
科学的文化是认知的文化。科学通过观察、归纳和演绎来认识世界,其中,物理学进化史生动展示了科学进程中的文化图景。从亚里士多德基于经验的猜想到伽利略根据实验的科学推理,再到牛顿对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深入挖掘,无一不展示了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以及他们之间共同的行为标准和模式、方法和设想[13]。无论是从个体心理发生的角度,还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看,科学始终都将对真理的“认知”置于核心位置,由此形成了不同于宗教沉思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追求。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涉及到复杂的认知策略,反过来加速了他们自身的认知发展:通过分析、比较、归纳和逻辑加工,个体的思维模式不断发展与深化,建立了一套更为健全的逻辑体系,它们共同为科学规律的挖掘提供了具有基础的洞察力[14]。
学习科学既然以把对学习的研究从“猜想”推进到“科学”为己任,自然深受科学所独有的这种认知的文化影响。学习科学的文化作为一种认知的文化,其特殊性体现在学习科学试图对“人是如何学习的”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而“人是如何学习的”这一问题是一个基本而重大的认识论问题,因此它指向的恰恰是科学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认知的文化何以可能这一更为深层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学习科学所展现出来的认知的文化不仅是科学总体上展现出来的认知的文化的一种亚型,更是其赖以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胚胎、母体与渊薮。正如康德从先验论出发以先天综合判断在哲学上回答了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科学的文化之所以是认知的文化,其深层原因也需要从学习科学日益展现出来的文化气质中寻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学家转向教育,学习研究由猜想走向科学,依次谱写了“动物是如何学习的”“机器是如何学习的”“人是如何学习的”的“三部曲”,分别建立了学习研究的“动物”“机器”“生命”隐喻[15]。进入21以来,学习科学的实践进一步为自身秉持的认知的文化塑造了交叉、多元、真实情境导向的特质。从知识构成来看,学习科学部落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广泛“邀请”了心理学、教育与认知神经科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加盟[16],体现了以学科交叉为特色的部落文化。从方法学的视角看,学习科学打破了科学与特定方法同义的神话[17],尤其是当一个问题没有被充分理解,缺乏可信的假设时,定性的研究方法如人种志[18]和其他工具如设计实验[19]对于描述复杂现象、生成理论模型和重构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形成了研究方法多元的部落文化。从研究关注的场景看,以“基于设计的研究”的提出为标志,学习研究不再仅仅只是在科学层面上关注实验环境中孤立的认知变量,而是更加专注于“在丰富的学习环境中对理论的实例化”[20],希望通过对真实情境下学习干预措施的形成性案例研究,促进学习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协同发展[21],由传统实验室向课堂真实情境这一学习研究范式的转变展现了部落文化之蜕变。这显然蕴含着对传统意义上以单纯的认知为目的的纯粹的科学文化的超越之萌芽。
(二)学习技术的文化是认知造物的文化
技术的文化是认知造物的文化。技术工具的发明与使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展现出了革命性的力量。诚如马克思所言,“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2]。芒福德根据技术要素的演进,将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划分为“始生代(风、水、木材)、古生代(煤、铁、蒸汽)、新生代(电、合金、轻金属)”三个阶段,技术要素的发展从早期以物质为基础转向以科学为支撑[23]。作为连接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工具中介,技术的首要表现形式为认知造物,即手段知识、诀窍、技能的物化,一种被设计用来维护、显示或服务于特定信息表征功能的人工设备(Artificial Instrument),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并发展人类的认知能力[24]。通过直接调节人类与对象的交互,或间接创建、操作虚拟对象世界或虚拟世界[25],认知造物构建了人类认知和改变世界的桥梁,促进了人类对于世界的解释与干预。
学习技术作为连接学习研究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践的关键桥梁,必然受到技术所独有的这种认知造物的文化影响,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对“科学知识何以支撑技术创新”这一问题做出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基于操作条件反射理论发明了一台教学机器,催生了一百年间教育领域技术原始创新的第一个范例[26]。广义上来看,斯金纳发明的教学机器是一种将有关人类行为的知识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的装置[27],它展现出来的是基于科学的认知造物的文化,而20世纪20年代教育心理学家普莱西设计的教学机器是借助于常识的经验造物,最终未能在教育领域得到推广与应用,究其原因,二者的根基全然不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没有科学基础作为基石,技术创新注定是走不远的。近年来,教育领域不乏基础科学促进技术原始创新的成功案例:一方面,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大部分基础研究是基于认知开展的[28];另一方面,通过直接调节学习者的交互过程,或间接操作虚拟对象、创建虚拟世界,人工智能能够实现对学生情绪的感知、识别与预测[29],有助于促进教育实践者对学习的解释与干预,搭建了学习者认知、改造世界的桥梁。从这一角度来说,技术的文化之所以是认知造物的文化,其深层原因也需要从学习技术日益展现出来的文化气质中寻找。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学习技术这一部落的领地日益扩张[30],学习技术的实践为其塑造的认知造物的文化赋予了跨时空、交互性、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特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不断向前推进,信息的传递更加快速高效,使学习研究领域内认知造物的文化快速演变,跨时空特征日益明显。日益增长的数字网络基础设施为学习环境创造了丰富的资源和工具[31],信息技术连接了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环境[32],并充分发挥其内在延展性[33],产生了“连锁反应”与“涟漪效应”,由此衍生出了更富交互性的部落文化:一方面,学习技术将单向传输的课堂转变为交互式课堂,使学生的思维更加清晰可见[34],改变了学习的形态;另一方面,学习技术创造的学习空间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人们可以分享经验和知识,重塑了学习的环境。同时,学习技术包括交互、自适应、反馈、非线性访问、关联表示等在内的强大“供给能力”为教师、学生等提供了“可操作的智能”,能够及时、适时地对学生进行预测、干预[35][36],促进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部落文化发展。
(三)学习工程的文化是造物的文化
工程的文化是造物的文化。工程是綜合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基于特定自然规律、社会目标需求开展的造物活动[37],使之满足认知需要的实践。对工程概念的认知还有一条路径,那就是通过看工程师干什么来界定工程是什么。阿瑟指出,“总体来说,他们的核心工作是对已有技术的计划、试制和继承,即设计和制造人造物”[38]。人造物是经由综合而成的,“设计出的”或“由……组成的”,是一种根据相应的物理法则与物质世界进行相互作用催生的存在上(Existentially)而非因果关系上依赖于人类的某种实体[39]。工程设计通过将外部世界的所有要求或限制转译成人造物的“物质和结构”,形成了一个“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交界面”,催生了内部环境为适应外部环境的产物[40],并在不断平衡二者之间张力与限制的同时,为人造物的更新与迭代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此造物过程中,不仅实现了知识的对象化[41],而且也促进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42]。
学习工程已然把推动学习的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为目标,必定受到工程所独有的这种造物的文化影响,其特殊性反映在学习工程试图对“如何在实践中促进人的发展”这一问题开展的探究。设计为造物提供了一套规划蓝图,框定的既是学习的环境,也是学习研究的环境。这意味着学习工程的造物建立在两个层面上:一是人类有目的的学习研究活动;二是为了创造人工物而开展的有目的的学习实践[43]。造物的目标直指对世界的改造,该过程不仅包含了一般意义上学习工程对物质世界的改造,而且通过改造客体世界,加速了对主体的社会性改造,即将原来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改造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前者为后者提供了造物的手段与条件,后者则对前者的进一步发展与超越。从这一视角来看,学习工程所呈现的不单单是工程这片土壤上展现出来的造物的文化的一种亚类,更是给养其进一步萌芽、生长、开花结出的硕果。工程的文化之所以是造物的文化,其深层原因也从学习工程的文化特质中日益展现出来[44]。
学习工程的实践塑造的造物的文化具有综合性、系统化、以实践为导向的特点。学习工程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学习实践的绩效。它涉及到不同类型的参与主体、不同维度的影响因素,是一项动态统筹的决策过程,探寻的是协调多种变量后的最优解,由此塑造了以综合性为特色的部落文化。学习工程的综合性反映了学习实践本身的复杂性,要驾驭这种复杂性,学习工程的知识领地不仅囊括了学习科学、学习技术、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而且还需以系统工程的整体性思维为基石,将构成系统的各组成部分进行统一筹划、设计、反馈与迭代,从而达到系统最优,这构成了学习工程之造物文化的系统化特色[45]。近年来,在学习工程这一部落中诞生了智能导学系统、学习分析系统等物化成果。智能导学系统围绕自动产生问题求解方案、表示学习者的知识获取过程、诊断学习者的学习活动、及时为学习者提供学习建议和反馈等功能展开广泛探索[46],学习分析系统在学习者知识、行为和经历建模、学习者建档、趋势分析等方面已得到成功运用[47]。这些都有效促进了教师优化教学和学生自我评估、诊断,充分体现了学习工程以实践为导向的部落文化。
三、学习研究中三种文化对立的历史后果及其超越
学习研究中三种文化的对立不仅制约了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和学习工程三个学术部落自身的发展,而且阻碍了相互之间的融合,严重影响了学习研究走向统一。在从本质上把握学习研究领域内科学、技术与工程这三种不同文化的内涵及其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唯有大力促进三种文化在对话和交流走向理解和融合,才能把学科交叉真正转变为一种推动学习研究走向统一的力量。
(一)学习研究中三种文化对立的历史后果
我们是生活在文化之水中的鱼,不可能摘掉自己的文化眼镜来观察世界。学习研究中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学习工程三个学术部落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研究方式与价值目标,分别代表了三个语言共同体,将独特的意义网络设施施加在自己领地的重要概念上,形成了各自的文化集团。三者以不同方式思考同一件事,不同视角类似于对一幅画的种种不可调和的理解,每种视角在每个语言共同体中都具有连贯性和相关性,但始终不会超越共同体的边界之外[48]。三个学术部落常常使用各种策略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保护自己的学术领地,有些以实物形态体现,另一些体现在成员的特殊性和制度的特殊性上。学科共同体中那些文化性更为明显的元素,如传统、习俗与实践,传播的知识、信仰、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以及交流的语言形式、符号形式,均构成了学术部落内部的界定标准。这无疑在学习研究中三种文化内部形成了一个功率强大的离心机,导致三者之间距离的疏远,并不断加深了三种文化的对立。比如,教学系统(Instructional Systems)是学习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学习科学无论是在目的还是在手段上都大有重叠。就研究手段而言,学习科学和教学系统设计都应用了教育技术,计算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二者的研究目的也十分类似,学习科学的目标是科学服务于教育,通过不断完善的科学理论得到更好的干预效果,教学系统关注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达到最佳学习效果。尽管如此,由于两个领域有着不同的价值观、边界与方法,这两个群体很难有机会真正接触对方,相互之间几乎没有对话[49]。
学习科学、学习技术与学习工程这三种文化之间缺乏开放式的交流已构成了当下教育与学习研究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进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并导致了严重的历史后果。20世纪初心理学家转向教育,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交叉融合极大提升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水平,却也使教育学变成了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面临着被教育心理学取代从而丧失自身合法性的危险之中[50]。和心理学当年的这种境况相比,现在有关学习的研究则等而下之。存在很多有关学习的研究,但却没有一个与之对应的专门知识领域,因为有关学习的专门知识绝大多数都可以被还原到其它学科领域。长此以往,作为学习研究不断向前推进最重要动力的学科交叉将慢慢丧失自身的历史合理性,逐渐蜕变为不断撕裂学习研究的一股负面力量。这会使学习研究的碎片化程度持续加深,进而使其在多学科交叉中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受到严重影响。学习研究将永远只能停留在松散部落的低发展水平上,难以实现由松散的原始部落群体向发展成熟、联系紧密的社群结构转变。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和学习工程也会陷入割裂和封闭的窘境,最终在窒息中走向消亡。由此带来的损失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工程化应用上的,也有智力和创造力上的。比如,没有学习科学的认知文化,学习技术在创造认知人造物的过程中必定缺乏明确指引,最终学习工程造物实践的效率也会降低。此外,三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封闭也会导致科研工作者看问题的角度受到限制,难以通过全方位的判断来做出抉择。为了实现学习研究的统一,不仅需要学科交叉提供新的思想资源,更需要通过打破这种文化对立,促进学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融合,把单维度的学科知识推演提升至多层级的学科知识建构。
(二)超越学习研究中三种文化对立的未来路向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斯诺(C. P. Snow)在《两种文化》中探讨的更多的还是人文这种传统文化在科学这种新兴文化面前所展现出来的傲慢,那么今天学习研究这一领域面临的则是科学、技术和工程这三种文化彼此之间的轻忽。三种文化的融合是学习科学、学习技术与学习工程三个学术部落走向统一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有必要在文化这一更为深层的意义上构造一个科学—技术—工程的连续统。从物质进化和学科分化的视角来看,自宇宙大爆炸对无生命物质开展研究的物理学,到围绕有生命物质进行研究的生命科学,再到聚焦人类展开研究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漫长历史向我们展现了自然界演进和学科发展发展、分化之间同构的逻辑,这意味着他们拥有共同的源头,知识的本身是统一的。学习科学、学习技术与学习工程三大学术部落之间全然不同的实践方式导致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学科“鄙视链”在文化冲突中逐渐凸显出来。“鄙视链”本质上是一种“圈子化”的教育逆动[51],有学者将其形象地描述为“用自己的虚荣和狂妄编制而成的‘皇帝的新装”[52]。三大学术部落的成员在各自领地内开展独立的学习研究,对其他部落的学科展现出极大的排异性,他们从分级而非分工的角度来对待不同学科,在不同学科之间构筑了层层围墙,使不同学科背景的人等级化,这种傲慢与偏见的态度过度彰显了学科文化的差异性,却忽视了对立背后蕴含的统一性。实际上,学习科学、学习技术与学习工程三大学术部落均源于相同的根结出的果实,他们共享着一些最基本的假设,有着相同的知识本源,这些學科本质上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为推进三种文化的融合,要加强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和学习工程三大学术部落之间的理解与对话,建立学习研究的“生态学隐喻”[53]。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学习研究犹如一个复杂的生态巨系统,学习科学、学习技术与学习工程构成了该生态系统中的三大群落,聚集了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系统工程等以学科为单位的物种。研究表明,物种丰富度赋予了生态系统强生命力,多样性高的群落在稳定性及功能性上显著高于多样性低的群落[54]。这意味着学习科学、学习技术与学习工程三种不同文化的对立不仅不是消解学习科学自身统一性的负面力量,反而是不断推动学习科学这一新生学科不断走向更高发展水平,开拓更加广阔之天地的重要动力。学习科学三大群落间物种的差异提升了学习研究生态系统多样性,三者在学科生态链上表现为紧密、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学习科学群落中的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物种为学习技术群落中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物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人工智能等物种的进化又为学习工程学术部落中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物种带来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反过来,计算机科学能够促进人工智能等物种的迭代与优化,而人工智能等物种的演化又有助于认知科学等物种基础理论的检验与完善。学科“鄙视链”反转为学科“依存链”!对于多学科交叉的学习科学来说,这就是异质文化激荡与融合在学科发展生态构建上展现出来的独特魅力!
有论者曾经指出:“学术部落和学术研究活动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忽视学术活动中的学术部落,与忽视学术部落中的学术实践一样都是片面的”。这意味着打破学术部落之间的文化对立,还需从改变学术部落中的学术实践入手。实践作为“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构成了认识发展的来源与基础,而认识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实践,并催生了相应的产物与成果——认知、认知人造物与人造物。就学习研究而言,这在学科意义上分别对应着学习科学、学习技术与学习工程。在学习研究的专业学术实践中,学习技术的认知造物是实践目标导向下实现由学习科学的认知向学习工程的造物转化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要最终现实地完成这种转化,对学习研究来说,不管是科学实践,还是技术实践,抑或工程实践,都需要摆脱文化沙文主义唯我独尊的态度,采取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立场,以打通学习研究中横亘在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之间的鸿沟,为统一学习科学认知的文化、学习技术认知造物的文化与学习工程造物的文化,形成一种全新的、更具内在统一性的学习研究文化提供脚手架。学习科学、学习技术与学习工程三大领域共同的先驱帕伯特(Seymour Papert)曾经指出:“当学习者通过制造、搭建物品并与他人分享来建构他们的理解时,学习是最有效的”[55]。学习的实践是如此,学习研究的实践何尝又不是如此?
四、结语
学术部落是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就像一个多声部的合唱,一个声部唤醒另一个声部,一个声部因另一个声部的存在而有意义,有时候是齐唱,更多的时候是不同声部的配合和碰撞,相反的声音更是能产生戏剧化的效果。文化并不是一种可共享的有形物质产品,而是一种在碰撞和交流中形成的顺手而优良的无形精神工具。我们应该把文化看成一种敲击世界的过程[56]。自然科学家约翰·巴罗(John David Barrow)写到,“不存在能够表达所有真理、所有和谐和所有简单性的公式,从来不存在能提供全部见解的万用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57]。现在到了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和学习工程这三种文化应该采取一种更谦卑之姿态的时候了,因为正如老虎、鲨鱼和鹰一样,每个团体在自己的领地内都是非常强大的,但在他人的领地却是无能为力的。
参考文献:
[1] Lagemann E C.An elusive science:The troubling history of education research [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23-40.
[2]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How people learn:Brain,mind,experience,and school:Expanded edition [M].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0.3.
[3] 周子荷,刘三女牙等.从学习科学到学习工程:历史跨越与未来走向[J].电化教育研究,2020,(11):5-12.
[4] Sawyer R K.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19-34.
[5] Ruscio K P.Many sectors, many professions [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20.331-368.
[6] [英]托尼·比彻.唐跃勤等译.学术部落及其领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 [美]伯顿·R·克拉克.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87-91.
[8] Clark B R.Academic Culture [R].New Heaven:Institution for Social Policy Studies,1980.
[9] Ylijoki O H.Disciplinary cultures and the moral order of studying–A case-study of four Finnish university departments [J].Higher education,2000,(3):339-362.
[10] Becher T,Huber L.Editorial [J].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1992,(3):193-199.
[11] [美]理查德·沙沃森,麗萨·汤.曹晓南,程宝燕等译.教育的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1.
[12] Hay K E,Deaton B E.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the learning sciences:A bibliographic analysis of two scholarly communities [C].Chicago: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2003.
[13] [英]C·P·斯诺.陈克艰等译.两种文化[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14] Carruthers P,Stich S,et al.The cognitive basis of science [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5] 郑旭东,王美倩.学习科学:百年回顾与前瞻[J].电化教育研究,2017,(7):13-19.
[16] Michael A E,Martin J P,et al.Reflections on the learning sciences [M]. 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126-154.
[17] Howe K,Eisenhart M.Standards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A prolegomenon [J].Educational researcher,1990,(4):2-9.
[18] Agar M H.The professional stranger:An informal introduction to ethnography [M]. San Diego:Academic press,1996.
[19] Brown A L.Design experiments: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in creating complex interventions in classroom settings [J].The 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1992,(2):141-178.
[20] Duffy T M.Theory and the design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Reflections on differences in disciplinary focus [J].Educational Technology,2004,(3):13-15.
[21] Rourke L,Friesen N.The learning sciences:The very idea [J].Educational Media International,2006,(4):271-284.
[22] [德]马克思,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3] [美]芒福德.陈允明,王克仁等译.技术与文明[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24] Norman D A.Design principles for cognitive artifacts [J].Research in Engineering Design,1992,(1):43-50.
[25] Norman D A,Draper W S.User centered system design:New perspectives in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M].Hillsdale: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6.67-85.
[26] 周子荷.教育领域技术原始创新的历史、逻辑与未来——兼论人工智能的教育意蕴[J].开放教育研究,2021,(2):34-41.
[27] Skinner B F.Reflections on a decade of teaching machines [J]. Sage,1963,(2):1-9.
[28] Fetzer J H.Asp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Dordrecht:Kluwer Academic,1988.195-208.
[29] 梁迎丽,刘陈.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现状分析、典型特征与发展趋势[J].中国电化教育,2018,(3):24-30.
[30] McCalla G.The fragmentation of culture,learning,teaching and technology:implications for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research agenda in 2010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2000,(2):177-196.
[31] Thomas D,Brown J S.A new culture of learning:Cultivating the imagination for a world of constant change [M].North Charleston: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1.
[32] Committee on How People Learn II.How people learn II:Learners,contexts,and cultures [M].New York: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18.164.
[33] Jung Y.A new culture of learning:Cultivating the imagination for a world of constant change [J].Studies in Art Education,2015,(3):281-283.
[34] Bransford J,Brophy S,et al.When computer technologies meet the learning sciences:Issues and opportunities [J].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0,(1):59-84.
[35] Teasley S D.Learning analytics:wher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learning sciences meet [J].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Sciences,2019,(1):59-73.
[36] Wise A F.Designing pedagogical interventions to support student use of learning analytics [A].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nalytics and knowledge [C].Indianapolis,IN:Education,2014. 203-211.
[37] Gabbay D M,Thagard P,et al.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M].Amsterdam:Elsevier,2009.
[38] [美]布萊恩·阿瑟.曹东溟,王健译.技术的本质[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99.
[39] Baker R L.The Metaphysics of everyday life:An essay in practical realism [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40] [美]司马贺.武夷山译.人工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6.
[41] Preston B.Artifact.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M]. London:Routledge,2020.209-221.
[42] Tuan Y F.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rtifact [J].Geographical review,1980,(70):462-472.
[43] Thomasson L A.Realism and human kinds [J].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2003,(3):580-609.
[44] 鲁洁.教育: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J].教育研究,1998,(9):13-18.
[45] Dede C.Next steps for” big data” in education:Utilizing data-intensive research [J].Educational Technology,2016,(2):37-42.
[46] 刘清堂,吴林静等.智能导师系统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J].中国电化教育,2016,(10):39-44.
[47] 闫志明,唐夏夏等.教育人工智能(EAI)的内涵、关键技术与应用趋势——美国《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报告解析[J].远程教育杂志,2017,(1):26-35.
[48] [美]杰罗姆·凯根.王加丰译.三种文化[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49] Kirby J A,Hoadley C M,et al.Instructional systems design and the learning sciences:A citation analysis [J].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05,(1):37-47.
[50] [美]埃伦·康德利夫·拉格曼.花海燕,梁小燕等译.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困扰不断的教育研究的历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9-68.
[51] 张亮,胡文根.高校学科“鄙视链”及其破解之道[J].现代大学教育,2019, (2):10-16.
[52] 罗文.“圈子化”培养违背教育本质[N].光明日报,2017-06-06(02).
[53] [美]伯纳德·科恩.张卜天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6.
[54] 徐炜,马志远等.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进展与展望[J].生物多样性,2016,(1):55-71.
[55] Martinez S L,Stager G.Invent to learn:Making,tinkering,and engineering in the classroom [M].Torrance:Constructing Modern Knowledge Press,2013.11-40.
[56] McDermott R,Varenne H.Culture as disability [J].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1995,(3):324-348.
[57] Barrow J D.Theories of Everything [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20.
作者简介:
周子荷:博士后,研究方向為学习科学、教育理论与国际比较。
刘三女牙: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大数据、智能教育、教育技术。
李卿: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信息科学、教育大数据。
郑旭东: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
Academic Tribes and Their Territories: The Antagonism and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Cultures in Contemporary Learning Research
Zhou Zihe1, Liu Sannyuya1,2, Li Qing2, Zheng Xudong3
1.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E-Learn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2.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Educational Big Data,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3.Facul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anthropological metaphor of academic tribes and their territories subject culture a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alyzes the academic tribes and their territories in contemporary learning research, and identifies the current existence of three kinds of culture as well as explains its connotat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at the culture of science is cognition, the culture of learning technology is cognitive creation, the culture of learning engineering is creatio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consequences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antithesis of three cultures in contemporary learning research, hold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hree different cultur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not only challenges the unity of learning research, but also contains the potential of opening up new horizon for future learning research. Therefore, theres a need to construct the cultural continuum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change the academic practice in the academic tribe, and form a new culture of learning research with more internal unity.
Keywords: academic tribes; culture; cognition; cognitive artifacts; creation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28日
責任编辑:李雅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