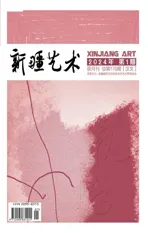诗化舞剧《只此青绿》的文化构想和精神旨归
2024-02-01□李煜李可
□ 李 煜 李 可

舞剧《只此青绿》剧照
诗化舞剧《只此青绿》兴起了当代舞蹈创作文化构想的新风尚,表面上看,其是再现北宋王希孟绢本设色画《千里江山图》的篆刻、织绢、磨石、制笔、制墨之工序,以抑扬顿挫跃音律于纸上,情摹魏晋舞风之妙玄,借舞蹈假面的肌理感其情由,仿佛是在叙述丽人之心事,摹拟山峦重叠之雄姿,歌颂山河之秀美,敬畏生命之磅礴伟力,富有神、逸、清之诗化格律,确有诗化舞剧之品格,舞韵中内蕴淡淡之忧思,亦符合清、雅、逸、玄的魏晋舞风与宋代的文化特质,符合舞剧创作与艺术学理论中的神、逸、清、雅、能、气、韵、妍、丽、巧、工之格律。但对《只此青绿》的大部分舞评,都将重点放在了青绿之色调、清雅之舞韵上,少了对舞剧之“史”的深探,也就缺失了对其“骨”的精准把握、对“神”的准确捕捉。

舞剧《只此青绿》剧照
舞剧《只此青绿》的实质应是以诗画叙事,以舞表情,以歌言志,抒画者胸中之哀思,忧大厦之将倾,思家国之情怀,为画者鸣不平。古代的文人雅士习魏晋之风,兴寄哀思、愤恨、担忧、无奈之情,将心象寄于诗、舞、画之中,汇集了理想与现实之矛盾。《只此青绿》的编导巧妙运用这种矛盾关系,画其骨抒其情,勾勒出了极具隐喻色彩的《千里江山图》,还原了王希孟的真实心境。《只此青绿》以丽人之姿绘文人尚情、忧思、忧国之雅骨,构建了独具风韵的青绿视相,歌雅正之声,留铁血忠魂,蕴含百折不挠之心理,以留磅礴生机于朗朗乾坤,诉说风骨长存,青绿精神不朽的别样心象。
诗化舞剧《只此青绿》若只根据舞形、舞情直接品评易得出以下结论:
从舞蹈形态进行分析,其并非宋代宫廷队舞与民俗民间队舞的形式,又非民俗舞蹈节庆化的场面,而是基于明清戏曲传统、芭蕾基训方式、当代审美意向所构建的中国古典舞的形态,符合古典舞蹈的传统审美范式。此舞剧呈现出抒情写意、缘神缘情的特质,颇具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轻、悲、哀为美的文化特质。此舞剧以女子群舞形象为主基调,来拟物抒情、写意造境,情摹各种山峦层叠起伏之画像,以青绿色调之服饰、女子秀丽典雅之姿容,恣意摹写沟壑纵横之山峦,给人以清新浪漫之感。特别是双袖下垂的服装造型,不仅像山之纹理,更临摹山间瀑布之状,兼之众女子忧叹之神情,给人以无限遐想空间,描容出万物复苏之新绿气息,山河连绵之锦绣画卷,有几分魏晋舞风之清逸与哀愁[1]。
然而这种品评并未见其质,仅以“诗化音舞”冠名,是对此舞剧不负责任的品评,严重忽视了对《千里江山图》作者人生际遇、情感、志向的考察,自然无法透过其人生观、情感观把握其历史观、价值观,从而一步步丧失了对其文化肌理到精神内质的思考。这种视而不见,是舞蹈评论对当代舞剧创作指导与构建现实意义的忽视。笔者认为,可从观形、探情、问志、问心、寻根、探骨、得神方面入手,开启《只此青绿》品评的新视野、新视角,从形情分析走向历史视域,以史观舞,以文释理,论从史出。
一、舞形之研判,舞情之暗喻
初观《只此青绿》,颇有宋代书画之气,却略显悲沉,是受程朱理学影响下的历史产物,更偏向现实心理之摹写。虽是宋代画作之场面,却不似宋代舞风之韵律,呈现的是古人摹写于书画之上的情态,暗含明代徐渭“摹情弥真”的创作思想。《只此青绿》以舞姿外秀女子之柔情,内藏尚情体国之悲,蕴含男子刚毅性格。这种阴阳互补、刚柔相济的辩证哲学,体现出一种恬淡的至高境界,是艺术之作的至高追求,也是文人雅士崇高的人生境界。舞剧以情为诉,借女儿身言男儿志,情之忧者,无非国事,国若不存,何以为家?以小见大体现士之大义,民之心愿,兼济天下之情。以诗表志,以舞寄情,充盈着深厚的生命意味,洋溢着文士的清流之气,暗喻着民族心理流向、民族气象。明线寄情抒怀,暗线悲情拓骨,女子之悲,皆出于国家不存之丧乱之境,而文士之忧皆为家国情怀而起。
北宋末年,大厦将倾,君主昏聩,奸臣当道,报国无门,编导以丽人之舞切入主题,实在恰如其分,此为体文人雅士忧患之心,呈现实心语的重要线索。舞剧明线抒情言志,暗线言史尚骨,丽人之舞衔接明暗两线,从明暗喻体中织构出理想之境的千里江山如诗如画与现实之景的山河破碎、国之不存的现实矛盾。此中丽人代表的是画者理想的情感归宿、精神寄托,是画者自己的傲骨,更是自我的独白与内心的情愫,是画象之外的士之耽兮。所见是山水,所忧为山河,心忧天地间,却百无一能,嗟乎哀哉!《只此青绿》中,丽人面现愁容,但亦怀希冀与傲骨,将释、柔、悲、殇、离之情愫不断交织变化,衍生出千里江山的无限希冀,对现实之境的无可奈何,以清婉、沉郁的舞风,诉说着神之玄妙、情之哀解,这是画师的无奈与心哀,亦是嵇康、阮籍等前贤寄情山水的缘由。

舞剧《只此青绿》剧照
《千里江山图》并非投君主所好而作,而是警示、陈情,图中千里江山是王希孟等众多文人梦之心象。《只此青绿》中的舞蹈之丽人也寓指文人,寄托了文人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而换来的却是理想的幻灭。《只此青绿》所承载的文士忧、愁、叹、悲之心境,暗蕴了忧患意识、家国情怀,以及民族风骨永存不朽、民族精魂屹立不倒的文化与精神。
二、以史观舞,问心寻根探骨
王希孟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读书人,儒家思想是其忧患意识与文士风骨形成的因由,文人修齐治平理想和北宋末年山河破碎的现实矛盾,北宋朝廷对文人思想、情感的现实压制,进一步揭示了以王希孟为代表的宋代儒生之境遇——忧心国事,报国无门,只得寄情山水,怅然于林泉。
儒家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曰成仁,源自《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曰取义,出自《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正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之所在,“仁”“义”不仅折射出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文士风骨,更关乎生死存亡之际的现实抉择,文人气节与情感道义的现实坚守[2]。
孔子对儒生的影响尤其深远,“正名分、兴礼乐”,以礼乐引导人心好恶、移风易俗,内蕴天下大同的现实理想,坚守人生道义,乐则韶舞,风乎舞雩是其理想之境,亦是天下大美,人心合和之境。此后,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儒学思想,提出乐民之乐的人生理想,将修齐治平与王天下、和天下的社会理想有机结合,表达了文人兼济天下、忠君报国之心,为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文士风骨的诞生构建了文化基石与现实养料。
如楚韵离骚之屈原、七步成诗之曹植、声无哀乐之嵇康、天生我才之李白、感时抚事之杜甫、屡遭贬谪之苏轼,哪一个不是才华惊世,际遇坎坷?虽人生际遇有所不同,但都是心怀家国的文士,他们都曾以陈情、上书、讽喻、刺美的方式规劝君主。曹植寄情赋诗,尽抒其情于《洛神赋》之中,言及了理想之雄健、洛神之美善、现实之凄清,彰显出超然绝俗的魏晋风度,留下了神、逸、清、妍的审美特质,而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更蕴含内藏外发的乐舞观,揭示哀情由心而生,关涉朝局与百姓凄苦,从内而外尽显乐之哀情,有志难伸,唯有寄情于物,托物言志,流连山水之间,从理想之辞赋音舞到怡然自得的心态,是一种情感的释然,此为缘神缘情之风尚,亦是魏晋风雅之玄妙。
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的辞赋之中多用比兴、借喻、象征手法隐晦地揭示统治集团的罪恶,面对生死,依然敢于痛斥司马家族之恶,体现了士人精神之不屈,文士风采之绝俗,魏晋风骨实乃文士之精魂所在。与此不同的是,魏晋是尚情的年代,而北宋是抑情尚理的时代,魏晋时期虽然混乱,但士人是空前自由的,诗词歌赋有着缘神缘情的玄妙特质。王希孟作《千里江山图》时,正值北宋徽宗时期,奸臣当道,言路闭塞,文人不敢直陈政事,不敢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唯有隐匿叙事,托物言志,隐喻表达成为一种世象,文人只能寄情于书画,将心中之情深藏于画作歌舞之中。王希孟以《千里江山图》恭祝北宋王朝兴盛不衰,实则暗藏对奸臣误国误君之切齿之恨。理想是一面镜子,照亮了现实的层层迷雾,隐喻表达了山河破碎、世风日下、文士风骨不再的无声哀嚎,表达了壮美江山不复,对民族风骨再次复归的希冀与愿景。
以上文人虽朝代不同,但都有一些共性:一是皆怀忧患意识、家国情怀和兼济天下的现实理想,且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二是仕途受阻,壮志难酬,人生坎坷,只能借物抒怀,将满腔家国情怀、忧患意识、文士风骨倾注于诗词画赋、歌舞音律之上,寻求心灵的慰藉、情感的平衡;三是心怀天下,胸有傲骨,敢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头可断血可流,不改其志,不屈于淫威,不坠青云之志。如此看来,儒家思想不仅在于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对世俗之中礼、义、廉、耻施教化之义,还对文人人生观、价值观的构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更深关民族气节。忧患意识、家国情怀、文士风骨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与脊梁。
三、探《只此青绿》之文化背景,勘编导之心核
《只此青绿》的历史背景和创造来源,亟需以宋、明、清的历史与文化为参照。因宋代程朱理学之沿袭,三纲五常等,哪个不是对女子的压迫?女子脚下是历史的尘埃与现实的镣铐。文化观念上的压迫,无时无刻不侵蚀着女性的心灵,封建礼教的摧残,逐渐压弯了女子的精神脊梁。在历史流变下,舞蹈形态、气度、风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汉唐魏晋舞风包容万象的大气变成了宋元以后的愁眉不展、内心积郁。宋、明、清戏曲形态传统的流转虽然是古典审美范式上延展,但也掺杂上了文化的陋习,沉积了社会审美的弊病。《只此青绿》的编导有意打破这种病态的审美,让女子从中破茧而出,走向独立,以丽人情怀为引,以女子形象为依,以青绿腰之形为点,历史视域为线,构织一种独特的历史与文化景观,与其说丽人之舞是其梦之心象,不如说文士之兴寄言志之产物,或者说是读书人饱受社会压迫欺辱的现实之象[3]。
由此可见,编导深谙审美之心理,暗喻之功能,形情之玄妙,文化之愿景,借饱受封建礼教压迫和心理摧残的宋代女子,以古典舞韵律构织心灵的回响,表面上是一种清婉哀叹的魏晋舞风,实则是对现实压迫的无声控诉。以历史为源,青绿腰应视为女性在历史中沉积的心理积郁,也是文人饱受社会压迫的现实形象,与《千里江山图》画作形成鲜明对比。女子是文士心象的产物,作为封建历史下饱受摧残的人群,编导以女子群舞的形式表情写意,以女子暗喻文人雅士,斥责着封建礼教观念的迂腐,寄寓着对家国情怀的无尽哀愁、无限忧思,慷慨悲歌与理想之境现实对比,是画者心象和历史景象的巧妙融合,伴随着悲、忧、释、怡四情,展开了《只此青绿》的千年画卷,揭示了文士关涉人生命运、精神坚守的文化构想。
古今文化传承、精神传承的现实构想与人类命运的思考,或是舞剧创作的一种新路径,以历史、文化、文人思想为现实参照物,以拟物造境从文化现象深入社会、人物的情感心理,丽人之舞是在描摹景物,更是在洞察、勘破王希孟内心情感与行为动机的心理之线、理想之果、悲痛之因。将王希孟一颗家国之心、一缕忧患之情、几分文士风骨与民族气节孕育于一场舞剧中,将忧、愁、离、恨、叹、愿之现实心理进行动态化摹写,以诗、画、舞、韵织构着古代文化的现实景观,《只此青绿》之主题,呈现着爱国之士无悔的选择,民族气节永垂不朽,生生不息之寓意。
四、古今思想文化在舞剧创作中的构建
如果说构建历史文化景观是为了满足当代人之审美需要与情感诉求,那么文化传承之义便是编导之现实心声,其最高理想正是颂其骨,但从形到情到心到骨,不能不涉及情感、历史、文化、心理的现实探索,不能不涉及古今思想文化的现实碰撞与现实构建问题,形成古韵与今韵的现实交织,呈现情感与历史的现实交响,以情为其核,青绿为形,舞为其韵,哀为其律,史为其境,文为其质,忧现其骨,而丽人之舞,兼具了神、逸、清、雅、能、骨、气、韵、妍、丽、巧等品格[4],这正是舞剧《只此青绿》的思想深度与情感表达的难点之所在,以女子拟物造境、作暗喻之笔展现实之画卷,可谓妙笔生花,既合古典韵律,又暗合暗喻、叙事、心理探索之现实功能。
丽人之舞的现实作用不在于丽人风姿的绰约,亦不在展卷、问篆、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之过程的揭示,而在于现实情感的抒发,侧重于物态化的拟象描容,以古代女子的娇羞、内敛、含蓄之表情,抒写故国之情怀,娴静恬淡之容下是忧患忧虑之思,呈现历史叙事与情感愿景共同构建历史文化景观的巧妙关联,这正是丽人之舞的拟物造境与画师情感心象描绘相通之处[5]。
此外,《只此青绿》的丽人之舞还有以情释志、以舞载道之功能,将忧愁之思,兴寄之情化于物象,言文士风骨于忧情,兴文道传承之话音,是文人墨客家国情怀的最深层的情感体现。当《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与编导周莉亚、韩真形成情感共鸣,思想形成有机碰撞之时,《只此青绿》的构想油然而生,主题逐渐成形,意蕴也愈发深邃。其不仅是绝美的诗化舞剧,更是关涉了文士风骨的遗存与再造,关涉青绿之意象的织构与心理叙事的进行,其以心物同构的最终目的,将当代审美文化与古代传统文化交织,对历史视域下民族心理、民族文化进行解构和再造,形成一种独特的现实思考与文化构想:
第一,舞剧创作要以形象为基础,以情感为内核,重视形情合一,情景交融,情态摹写,以情设舞要凸显人物性格,重视内心情感开掘与心理活动的呈现,以舞剧的民族性与情感性为要旨,构建民族心理,宣扬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民族舞剧、历史性舞剧创作应从中国古典审美出发进行品格构建,关注神、逸、清、雅、能、骨、气、韵、妍、丽、巧等品格与现实功用,与人物的形象、性格形成有机并联,形成古典舞派、古典文化的学理性研究,同时应关注抒情与叙事的辩证关系,尽可能地赋予历史文化气息与古代文化意蕴,构建舞剧形象应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形成现实联系,呈现诗、画、格、律与情、采、文、质的完美交融,让观众在欣赏中达到物我两忘的理想之境,实现舞剧形象的历史、心理探索与当代人情感、文化导向的有机共融。
第三,古代历史题材舞剧创作应该更具文化气息,应多关注历史之情境,做好环境的铺陈,多用拟人、象征、比兴、明喻、暗喻、对比的现实手法构造,多言人物行为动机及情感心理,让人物行为、内心情感与历史环境形成有机并联,织构人物性格命运,让人物形象更为丰满,意蕴更加深邃。
第四,构建历史文化景观之时,应怀民族文化传承之心。民族情感是民族舞剧创作的情感内涵,而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是民族舞剧的内在生命力之所在。要实现古代文化与当代审美文化、审美心理相契合,必须建构古今文化思想相碰撞、相交融的现实桥梁、情感纽带、历史关联,舞剧形象、文化风骨应是关键之点。
结语
古代题材舞剧创作不应只关注舞剧的诗性、形态、情感,更应该关注舞剧的内质,其文化风骨之所在,民族性是舞剧创生的内涵,民族精神应是此类舞剧创作的要旨。以忧患意识、家国情怀、文士风骨构建民族意蕴、民族精魂是舞剧《只此青绿》的最深的意蕴,其点睛之笔在于对道义的现实成全,对文人风骨的再度呼唤,希冀家国情怀、忧患意识的再度复归,唤醒民族精神内蕴的磅礴伟力。青绿精神与文人傲骨彼此缠绕、相互羁绊,永存于世,此为青绿的画外之音。以拟物造境手法表达文化象征之意味,阐释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之世情,编导让当代舞剧创作走入了现实表达与心理探索的历史性新纪元。

舞剧《只此青绿》剧照
编导还从文化心理特质出发,揭示了王希孟作画的隐逸之因,是对现实的逃离,对社会关系的摆脱,其特质是兼具儒道思想的产物,《只此青绿》的拟人造物之手法更隐心境与世情,与寄情于物有异曲同工之妙。“隐”是文人追寻自由之所需,人格之所求,这并非魏晋所独有的文化现象,宋代依旧如此,其中暗含了追求本体精神之自由与抑情尚理的社会文化的深层矛盾,而隐匿于物的现实表达,正是玄学文化的特殊表现,隐是心之规律,亦是心之求索,由心蕴情,心是隐之载体,隐是心之意向,逸是心之表现,皆藏于书画意境之中[6]。
民族风骨放眼于今日,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的审视?对灵魂的拷问与人性的探寻?《只此青绿》的丽人之舞、青绿之景、文士之情、山河之境的怀古之意,是山河破碎后的现实肌理。《千里江山图》与《只此青绿》都隐匿其情,皆披上华丽的绝美外衣。编导借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之故事作《只此青绿》,言王希孟之风骨,拟物山水之诗情,歌颂文士的气节,呼唤人性的复归,期待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历史和文士心理情感流变构建古今交织的文化历史景观,一吐文士之忧郁的心结,将文化构想与文士心理以共时性、历时性、模进式舞剧创作方式进行有机织构并蓄,以此开启民族、古代历史题材舞剧创作的新风尚、新格调、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