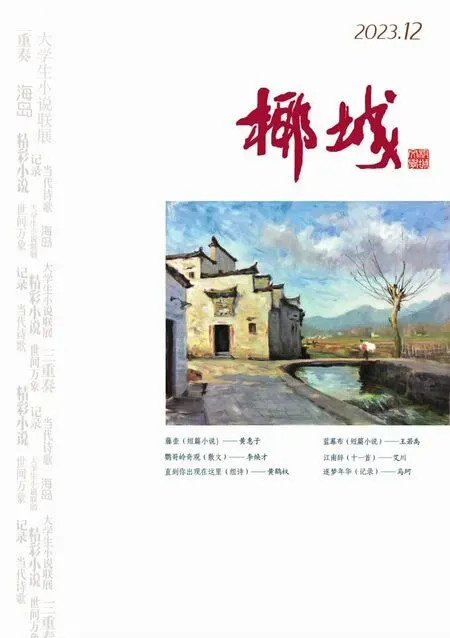鹦哥岭奇观(散文)
2024-01-30李焕才
◎李焕才
一
海外风光别一家,
四时杨柳四时花。
寒来暑往无人会,
只有桃符纪岁华。
小时候,听见有人吟诵这首诗,以为在唱山歌,长大后,知道是一首诗,再后来,又知道是明朝一个安徽桐城名叫方向的进士,到海南任琼州知府时写的一首七绝,一直传诵至今,成为海南风光的一张亮丽名片。
南海浩瀚无垠,烟波万里,碧浪连天,一座巨大的岛屿浮在漫漫碧水中,海浪拥抱她,海风抚摸她,阳光又给她倾注无限的热情……如此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她当然风姿绰约,亮丽迷人。
我就生长在这座得天独厚的岛屿上。
我没有踏出海南岛之前,并不知道我们这座海岛有啥特别,后来有机会到外边走了几遭,又在外头小住了一些时日,才突然发觉,生长在海南岛,原来是生活在斑斓的色彩中,天是青的、云是白的、海是蓝的、山是绿的,还有五颜六色的鲜花和灿烂的阳光……这只是目光所及的感觉,在感受上,又是另一番景象。海水、海风、海浪、雨水和阳光缤纷在我们的日子中,我们的生活活泼多彩,心里盛着快意,活得通透自得。
大风很恣意,呼啦啦从海上来,带来了大海的气息,也带来了温润的热气,海浪受风鼓动,欢欣鼓舞,天空上的骄阳也很兴奋,将无限的热情飘泼下来,岛上的万物当然很激动,在热闹中欣欣向荣。热闹和热情不受节制,变成了炎人的热气,但是别急,天空马上飘来一块黑云,凉风乍起,你还没回过神来雨水不由分说倾泻了下来,雨鞭噼里啪啦抽打在你的身上,顷刻间,你全身都淋个透了。这时你才发觉,氤氲在身边的暑气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有凉爽,在这一热一凉的变换中,感到无比的痛快。你再凝神四望,天地间被洗得干净透亮,空气也清新滋润,沁人心脾,不得不惊叹这天地的神奇。
海南岛四面环海,周边地势平缓,中部却群山簇拥,奇峰突出,连绵起伏,这分明是山和海在这座岛上天作之合呈现出来的默契状态,要连袂演绎出大自然的奇观。是的,海边的风总是使劲地吹,送来的热气在海边流连忘返,九百多年前到海南来的苏东坡已经有了真切感觉,写道:无限春风来海上……染得桃红似肉红。但是,从山上吹来的风都很温柔,带来的凉气恋恋不舍不肯离开。我的家在海南岛西北部的儋州,老家在儋州北面海边的一个渔村,新家在儋州的南面、靠近海南岛中部山区的那大镇。这一距离,让我领略到海的热烈和山的温馨。在老家,还傲游于滚滚热浪中,车往山区开,树木渐多,热气渐渐消退,到了那大镇,凉丝丝的,好不舒畅;到了夜晚,凉风骀荡,更是惬意无比。开始时,我总是把凉爽归功于那大镇周边的树木,树木挡住了热辣的阳光,才留住了凉爽。没错,树上的枝叶不停地摇曳,把炎热摇散,因而抱住了凉爽。可是,为什么山上吹来的风总是凉的,特别是,一两天就下一场雨,扬扬洒洒的雨水使暑气无法落脚。我不得不问,这山风从何处带来凉爽?这雨水何以来得这样频繁?我终于在地理书中找到了答案。越过了那大镇,便是海南岛的中部山区,群山连绵,树木铺天盖地,那莽莽苍苍的森林叫热带雨林。这热带雨林神奇地造就了一片片雨云,那雨云随风而至,慷慨地将雨水送到,就也送来了凉爽。我明白了,那大镇旁边有个大水库,是全国十大水库之一,几十年前周恩来总理曾亲笔题下“松涛水库”四个大字,正是蓄积丰沛的雨水而成。我更明白,海南岛之所以“寒来暑往无人会”,就是山和海共同演绎出的杰作,海上吹来了热带季风,山上的热带雨林又送来了凉爽的雨水,它们各自彰显,又默契合作,于是绝妙地成为大自然的空调机。
二
鹦哥岭横亘在海南岛中南部,处于海南热带雨林的中心枢纽,总面积50464 平方公里,跨越白沙、琼中、乐东、五指山、昌江五市县,是全国连片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热带雨林,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系列的说词还是没法让我窥到鹦哥岭的概貌。我站在高处远望,目光所及,只见山峦奇峰耸起,又逶迤蜿蜒,连绵千里,随着天上阳光强度的变化,那山色时而变成青绿,时而变成墨绿,甚至变成了黛色,有时,又通红一片,金光四射,好像阳光在山上燃烧,更让人诧异的是,那烟雾四时浮游在山上,飘忽不定,一忽抹去了山的一角,一忽山体变得朦胧诡秘,一忽又烟霭漫漫,全部山峦都隐蔽在雾海中,使人感觉,那里像是神秘莫测的仙界幻境。
鹦哥岭已被列为国家热带雨林公园。
我找一辆越野小车,请一位经常在野外开车的朋友当司机,揣着海南省作家协会开具的采访介绍信,兴冲冲上路。车子往南开,很快便驶进了浩瀚的绿色中,公路两旁的村庄、农场、溪流、湖泊流光溢彩,迎面涌过来,又迅速向后边滑去,涌过来的是美,滑过去的也是美。来到了一个卡口,向护林员出示我们的介绍信,算是正式进入了鹦哥岭热带雨林保护区。我贪婪地把车窗打开,让外边的清气扑进车来,感觉清爽、滋润、凉快,好不舒畅。汽车行驶在盘山公路上,路面变窄了,曲曲弯弯,又掩蔽在高大密麻的树木中,望不见来路,只能慢了下来。这个时候我也巴不得车开慢些,其实我们的车是开一会,停一会。我的目光一直抛在车窗外,路旁的景色连番冲击我的眼球,又牵扯我的好奇心。突然,一片鲜花疯狂地开在路边,得意地张扬它的艳丽,我们按捺不住,停车欣赏,又拿手机拍摄;突然,几棵大树纠缠在一起,互相依附中站成了独特的姿态,车又停下,感叹一番,又是拍摄;山那边的大片梯田扑入眼帘,层层叠叠,相接相连,水光和绿色互相映衬,美不胜收,我们又停车观赏。车子在一个拐角处停下,从山腰望去,山下的树林莽莽苍苍,无边无际,山风掠过,跌宕起伏,呼啦作响,犹如浩浩绿浪翻滚,我们的车子顿时像一只漂泊在茫茫大海中的小舢板。我极目远望,茫茫绿色中间铺着一片白色,那就是松涛水库。明白了,这个水库之所以名为“松涛”,就是因为它嵌在这大莽林中,松风浩荡,涛声飘扬。汽车穿行在大山中,越过了一个山头,就换一种景象,或奇峰高耸,或峡谷幽深,或悬崖矗立,或江流蜿蜒……让人目不暇接。
汽车不厌其烦百转千弯,跑过了很多座山,又是山,山外有山。其实,鹦哥岭是群山,不识大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依然兴致勃勃,却不跑了,不再舍近求远,此山望见那山高。
耸立在我们面前的这座山海拔1811米,是海南岛的第二高度,伟岸而又浑厚,山顶峥嵘奇崛,尖峰秀削,直冲霄汉,呈现出不凡的气度;山体磅礴壮阔,橫在我们的眼前挡住了半边天。旁边的护林员见我们的目光在山上留连,指着那云绕雾霭、烟气蒸腾的陡坡说:鹦哥岭周边人烟稀少,开发程度低,留有不少值得窥探的地方,上边,就是原始森林。我们望去,只见大树小树间杂生长,野草丛生,织成厚厚的绿色屏障,紧密地护住山体。
跟着护林员,我们攀过一块巨石,顺着一条崎岖小路爬上山去。说是“小路”,其实没路,踩在树木的缝隙,踩着厚厚的、湿漉漉的、软绵绵的枯叶,攀援藤蔓艰难地爬行。突然间,我们进入了一个荫蔽的世界。山风摇着树顶,阳光在高处闪烁,树下的光线却暗淡,也没风,有些热,可氧气足,还是感觉很舒畅;空气很湿润,一片树叶一片水,水从叶尖滑下,滴落在人的身上,透心的凉。深林里并不静寂,鸟叫声、蝉鸣声、各种动物的喊声,闹得人耳朵发麻;那蝴蝶在树上树下、在我们的身前身后纷飞,还有窜去窜来的松鼠,好像要把我们弄得眼花缭乱。我们还是静下神来,坐在一棵大树旁边的石头上仔细地看。这里的树木虽然密麻地挤在一起,可千姿百态各不相同,甚至找不到相同的树种。有趣的是,树木都像有意识似的,努力向上,争夺高处的阳光,有的很霸气,躯干粗壮高大结实,开枝散叶遮天蔽日;有的要急起直追,树干修长纤细、不蔓不枝,迫不及待往上窜;有的无奈地长得矮小,干脆不争,长出繁枝细叶,呈现出自己的特色;那些海芋很有意思,趴在地上,却张开比簸箕还大的叶片,以收集从树木缝隙漏下来的阳光……我们都叫不出这许多树木的名字。护林员说:原始森林的特点就是杂树丛生,鹦哥岭上尤其斑驳繁杂,植物种类繁多,是我国重量级物种天然基因库,共有植物2323 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就有5 种,如坡垒、伯乐树、海南苏铁、台湾苏铁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有28 种;另外有145 种和14 种分别被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及IUC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红色名录的不同受威胁等级;还有科学新种4个。
穿行在原始森林里要手足并用,抓住藤蔓以借力,又避免踩在苔藓上滑倒。然而,藤蔓又成为阻碍我们前行的藩篱。面前的藤蔓太多了,有的还缠绕在旁边的树上,一直攀爬到了树顶,更多的是密匝匝垂着,网一般纵横交错。特别是那树枝上生出的气根,有的比大腿还粗,有的像缆绳,有的只有手指大小,或垂下、或橫穿、或斜飘,有些索性搭在别的树上,变成了连理枝……两只变色树蜥在我们面前攀缘藤蔓爬到高处去,在上边跳跃攀爬嬉戏逗乐,我们抬头望,半空中竟然是一个缤纷世界。那些藤蔓或气根长着毛绒绒的苔藓,有的还长着异样的花草,周边树木的树干或树枝上长出各色各样的小树和花草,甚至有珍贵的兰草和灵芝草,有的树居然长着异种树的果实,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其树冠和树枝只有花和叶,腰间却结出一串串无花果。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些已经枯死腐朽了的树,树干上却长出另一种新树,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我们弄明白了,这都是那些昆虫、鸟儿,或者什么野兽制造出来的奇观。昆虫要捕捉阳光,可飞不了太高,只能在这个地方飞来飞去,也就不知不觉中在那儿传授花粉,树上的枝丫,或者有个鸟巢,就成了花草、小树生长的支点,动物叼个果在树上吃、鸟儿拉了一泡屎,也可能成为某种植物的种子,加上半空中阳光较充足,适宜植物生长,于是那儿小树横生、杂草繁盛、各色各样的花争妍斗艳,也就成为一个五彩纷呈的空中花园。
有一棵经常见人家拿来做盆景的五针松长得很高大,挺拔苍劲繁茂,独领风骚,下面的树根非常发达,高高隆起,像是四面砌着厚实的墙加固那粗壮的树干。护林员说:这叫板根。这儿土层薄,凸起的板根呈三角板状,起加固支撑作用,又增加水分和养分的吸收。不远处又有一棵很大的树,树根向旁边延伸,紧紧抱着一块大石头,样子很亲切。原来是树下的泥土被水冲跑了,它只好伸出许多树根抱住那石头,以稳固自己,变成了“树抱石”奇观。我们感叹,原始森林就是奇特,以其独有的方式呈现出异样的景象。我们又来到一棵更大的榕树下。它很霸道,独占一片天地,独木成林。它的气根从树枝垂下,落到了地面,又成了一棵树,于是周边数十、成百棵树都与它血脉相连,或者成为它的子孙。但是很诧异,这棵几人合抱不过的大树主干竟然是空心的。护林员半开玩笑说:这就是绞杀的证据。何谓“绞杀”?是这棵榕树后来才生长,可生长迅速,它依附旁边的一棵大树,气根攀缘在那树上,越长越粗,缠绕得越来越紧,不仅吸收那树的养分,而且将那树活活勒死了。榕树的气根把那棵被勒死了的树紧抱在里面,成了榕树的树干,那死树久而久之腐烂了,大榕树的树干也就变成了空心……虽然我们对大榕树的横蛮行为不屑,可不得不惊羡它强盛的生长力。
山上涓涓细流穿梭,不时传来淙淙的流水声,不一会,就看见一条小溪跌宕成瀑布,悬挂在我们面前。我们在一道大瀑布前驻足。一股洁白的激流从高处飞泻下来,撞在下边的石头上,飞珠溅玉,哗啦啦作响。那水很洁净,清晰见底,我掬一把洗脸,冰凉冰凉的,好不爽快。我望着那奔泻不息的水,在心里问,山顶没有河流、湖泊,这么多的水从哪来?这时,突然下雨了,山风摇着树木,雨水随之泼了下来,整座山犹如一架巨大的钢琴,风声、雨声、流水声、松涛声共响,像在弹奏一曲气势恢弘的交响乐。雨刚停,阳光马上赶了回来,山上水汽蒸腾,烟雾缭绕,有的雾霭弥漫在山顶,有的飘移在山坡,有的氤氲在山脚,有的游荡在我们的身前身后,突然,那烟雾疯了似的,奔涌翻腾,整座山黑朦朦的,我们都淹没在雾海中。烟雾来得突然,去也迅速,很快便散开了。我们转身要离开那瀑布,我突然想到李白的《庐山瀑布》,念道:疑是银河落九天。旁边的护林员说:这瀑布的水是雨水,也是山泉水。他又说,热带雨林犹如一座巨大的水塔,雨水积蓄在山上,就变成了泉水,也就形成湖泊或溪流,又汇集成江河。鹦哥岭片区,湖泊星罗棋布,江流纵横交错。海南岛的第一大河流南渡江和第二大河流昌化江的发源地,就在鹦哥岭;北坡形成南渡江水系,南坡形成昌化江水系。海南面积最大、蓄水最多、灌溉范围最广的松涛水库和发电量最大、水坝高度长度堪称亚洲第一的大广坝水库,都属于鹦哥岭水系……下山的路上,我还在想鹦哥岭的水。原来这座山不声不响的在滋润大半个海南岛,默默地给我们造福。难怪早期环保运动领袖、国际知名自然生态作家约翰·缪尔说:“森林是河流的源泉,也是生命的源泉。”是的,森林不仅养育了人类,也孕育了人类的文明。
三
鹦哥岭周边大多居住着黎、苗族同胞。海南的原住民就是黎族人。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领兵登上了海南岛,将海南岛纳入大中华的版图,此后汉族人陆续上岛,到现在,汉族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黎族,大都居住在沿海地区,好不热闹,可黎族同胞还是无动于衷,依然坚守在深山老林里,让人很想知道个所以然。后来,我似乎想明白了,应该是黎族同胞的大山情结所然。他们读透了大山的奥秘,大山无限的恩惠,使他们能够在大山里营造出美好的生活。的确,深山里的黎族同胞有自己的快乐日子。我曾经被黎族同胞的山歌声感动,虽然听不懂他们的方言,可那音符跳跃着快乐的节拍,歌声出口婉转悠扬,像春莺鸣于幽谷,像泉水奔泻在山涧,入耳生情;再看歌者的表情,沉浸在歌声的旋律中,如醉如痴,那是幸福的情感在他们心间奔涌。那精美绝伦的黎锦更让人叹为观止,可以从中看出黎族同胞对大山衷情和执着的生活理念,看出他们的聪明勤奋和心灵手巧,看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热爱和对幸福的向往。黎锦的用料是当地的麻、藤、葛和棉,通过纺、染、织、绣等四大技艺进行艺术创作,又从当地的蓝靛叶、板栗树皮、黄姜茎等天然植物提取颜色作为染料。那高难度的双面绣,准确而又精细,正反两面的图案色彩相同,针法一致,轮廓层次分明,真是巧夺天工;其图案原型来于自然,以大力神纹、龙纹、蛙纹为主,体现出生命的力量和对自然的崇拜。据说,一件黎族服饰需一位绣娘每天8 小时绣3 个月以上,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鹦哥岭片区有黎族人口一万多,大多居住在山的皱褶里,好不容易才望见一个黎寨。为了保护水资源,为了对热带雨林实施整体保护,处于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区域内的村庄都整体迁移,更难以见到一个黎寨。下午,在护林员的指引下,我们的车停在山脚下的一个小山岗边,步行了百把米,走过一块缓坡,来到一个黎寨,只有几户人家,分散在树林里。走进一间平顶房,有一对夫妻,都五十出头了,穿汉族服装,男的稍黝黑,女的长得水润。屋里的陈设很简单,除了桌、椅、床、柜,还有一台电视机,却没有风扇。男主人热情地请我们坐下,见我们的目光在屋里巡睃,笑着说:山里四时凉爽,我们从不吹风扇。我问:孩子们不在家吗?他说:孩子在山外头工作,让我们也出去住,我们跑了回来。我问为什么,他说,舍不得离开这大山呀!我们是大山养大的,这山这水这草这木都很熟悉,哪能说离开就离开。我说,你们对大山真有感情。他说,祖祖辈辈得山神护佑,哪会没感情。我问,山里的日子怎样?他说,靠山吃山哩,吃的不用愁,有野菜、有野果,还有山薯、山芋、山兰米,不过,我们还是吃自己种的,山里土地肥沃,不缺水,扔下个石头都要发芽。我望见那缓坡上有番薯地、玉米地、花生地、蔬菜地,还有瓜棚豆架,缓坡旁边又有一大片种水稻的梯田。我问,你们没打猎吗?他说,打呀,扛杆猎枪上山,就有野味吃,可现在不再打猎了。我问,为啥?他说,我们守住大山,动物也守住大山,与动物伤了和气,山神发怒了,要有灾难的。我不相信有山神,但是知道,一旦鹦哥岭的生态遭到了破坏,将从根本上影响海南岛整体气候,使海南岛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我说,应该保护大山。他说,是呀,十几年前来了一批大学生,应该是山神请来的,他们说山上一草一木、飞的、爬的、钻地的都有用。后来我们不再打猎了,树也不乱砍,现在又有几百个护林员守着大山。此事我曾听说,2007 年有27 名大学生走进鹦哥岭,致力于热带雨林研究和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带来快食面、饼干、八宝粥、火腿肠,可主人说我们是贵客,一定要吃他家的饭!他杀一只大公鸡,到房前屋后摘来蔬菜瓜果,又煎一碟河里捞来的鱼,把山兰米酒拿了出来。
太阳下来了,落在山上,一片通红,像是漫山枫叶,又像遍野鲜花。我们在那平顶房前喝酒,又吃着飘过来的彩霞,兴致勃勃,全身泛着霞光。桌上的菜都很可口,那鸡肉甜美、脆香、有韧劲,尤其那豆角、萝卜、白菜鲜嫩爽口。男主人看见我们吃得香,得意地说:这菜不施化肥,不打农药,都是纯天然的。女主人补充说:这里的菜有山野清气滋养,味道就是好。女主人很健谈,三杯下肚便打开话闸给我们讲山里的故事。她说,他们家以前住船形屋,后来住茅草房,现在又住水泥平顶房。她说,以前都穿黎族服装,上几辈的女人还纹脸,现在的穿着打扮和山外的汉族同胞都一样了。我说,你穿上黎锦一定很漂亮。她说,可漂亮了,逢年过节或者有大活动,就拿出来穿。
天黑了,我们在那平顶房前面的空地上搭帐篷睡。女主人很细心,过来关照说:你们放心睡,山上的野兽不来骚扰的,有野猪过来偷吃地里的番薯,见有人,就跑开;我家养两只鹅,平时在屋前屋后吃草,蛇都不敢靠近,触碰到了鹅屎,蛇皮就烂了;我在旁边烧一把香草,蚊虫也都躲远远的。
半边月亮斜挂在天边,星空灿烂,山野朦朦胧胧,偶尔掠过一道淡淡的光,很神秘。夜晚并不清静,虫鸣蛙叫闹得欢,偶尔还听到野兽在吼叫。山风来得很随意,不知不觉就到了,摇着周边的树木,摇着我们的帐篷,把天上的月亮和星星都抹黑,雨水跟着赶了过来。山雨不是那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状况,属于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势态,哗哗啦啦,噼噼啪啪,把我们堵在帐篷里。但是,风雨急急地来,也急急地停。一个夜晚风雨来过许多次,我们只能待在帐篷里,卧听“潇湘夜雨声”。
四
我们是被鸟吵醒的。鸟起得比我们早。从帐篷里探出头,天才蒙蒙亮,鸟儿们欢快地跳跃在枝头,把天幕撞破了,漏出一道道曙光。早上的烟雾很着急,翻腾奔涌,可是挡不住阳光的脚步,很快,彩霞从空中落下,飘在山上,漫山姹紫嫣红。像是哐啷一声,山顶冲出一颗大太阳,红彤彤的,山上好像燃烧着熊熊的火焰。随着太阳冉冉升起,颜色渐渐变淡,变成了白色,天地间无比开阔光亮。
今天我们要在山上看动物。这座山很特别,以动物命名,我们当然要探个究竟。海南人把鹦鹉叫鹦哥,说是山上有成千上万只绯胸鹦鹉,人们才叫鹦哥岭。又说,《海南纪行》 一书有记载,1882 年美国传教士香便文来海南旅行考察,路过琼中的什运乡地区,看到漫山遍野飞舞着绯胸鹦鹉,景象十分壮观。我们当然也想目睹这一奇观,何况鹦鹉会说话会唱歌,看见、听见成千上万只鹦鹉说着唱着,那将是怎样一个奇异的景象。却有人说,之所以叫鹦哥岭,是因为险峻的峰顶耸起一块巨大石壁,傲对四野,远望酷似鹦哥的嘴,因而得名。不管怎样,鹦哥岭已经激起我们浓烈的好奇心,山上的植物千姿百态使人眼界大开,我们还要进入动物的世界,窥探它们的行踪,目睹它们的活动状况和生活风貌。
进山之前,我已翻阅相关资料,又读过了著名作家杨海蒂的热带雨林名作《这方热土》,得知鹦哥岭不仅具有植物种类的多样性,其优越的生态环境尤其适宜动物繁殖生长。动物不用忍受寒冷,不愁食物匮乏,不必迁徙当候鸟,因而物种丰富繁多,且数量很大,仅脊椎动物就有512 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9 种,如云豹、海南孔雀雉、圆鼻巨蜥、大灵猫、小灵猫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65 种;昆虫有1607 种,单单蝴蝶就有407 种,金斑喙凤蝶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可以说,这里是植物的天堂,动物的乐园。
大早,那位护林员便来和我们汇合。早上动物要在山上觅食,我们须趁早进山。我们顺着鹦哥岭金矿瀑布下游的山涧一路寻觅。昨天那位黎族同胞已经告诉我们,动物多活动在近水的地方,他曾经在山谷的一条河流边见到一条两米多长的大蟒蛇。护林员也如是说,他经常巡山,的确河谷两旁多有动物活动。护林员对山上的动物了如指掌,我和他说鸟类,他如数家珍般一口气便说出几十种鸟儿的名字,如:黑枕王鹟、印支绿鹊、银胸丝冠鸟、红头咬鹃、褐胸噪鹛、栗颊噪鹛、黑喉噪鹛、灰喉山椒、白喉冠鹎、灰头鸦雀、山鸡、纹胸鹪鹛、红尾歌鸲、斑尾鹃鸠、塔尾树鹊、纯蓝仙鹟、绿鹊、冕雀、山皇鸠、大盘尾、小盘尾、黄冠啄木鸟等,另外又点到海南特有的鸟类,海南画眉、海南柳莺、海南孔雀雉,以及极为罕见的、全球性易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山鹧鸪、海南虎斑鳽……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海南森林鸟类总数的百分之九十,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这里花很多,红黄粉白紫、形态各异,点缀在绿色丛中,表现出别样的美。穿行在树林间,眼睛很辛劳,五颜六色的蝴蝶、千姿百态的蜻蜓、奇形怪状的蜘蛛、古怪离奇的蛙类、丑陋不堪的鼠类,让人目不暇接……虽是让人诧异不已,可仍满足不了我们的猎奇欲望,往更隐蔽深幽处寻觅。为避免惊扰动物,我们走得很慢,小心翼翼,又东张西望,但还是惊动了一些动物,松鼠迅速往树的高处爬去,有的野兔在我们的跟前溜走,一只大鸟在我们前面扑棱棱飞起,身旁常听到窸窣的声响,分明是有动物在悄悄地躲开。这里并不清静,各种鸟的声音不断地传来,叫得很欢,又很悠然,也许是它们在交谈,也许是在赛歌,或许是它们发出招引异性的求偶信息,但是,它们都躲在枝叶繁茂的树上,很难看到鸟的身影。可幸的是,我们终于看到了几只鹦鹉,绿绿的,比树叶还绿,分散站在枝头,吱吱叫,可惜不是成千上万成群结队。我们看见几只叫不出名字的小鸟在树上一边啁啾一边啄吃山果,又看见一只赤色的鹧鸪躲在树头旁边的草丛里傻乎乎伸出个头,眼睛滴溜溜瞧着我们。我蹑手蹑脚靠近去,一脚踩在身边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上,脚底一滑,一趔趄,险些跌倒,情急中抓住了旁边的一棵小树。这一抓不得了,树上一窝蜜蜂嗡嗡飞起,朝我蜂拥而至,有的叮我的脸,有的蜇我的脖子,有的咬我的手臂,我吓坏了,一边啊啊的喊,两手来回驱赶,又急忙跑开,幸好蜜蜂们没有朝我追过来。我身上被蜇了许多处,麻辣麻辣的。护林员说:小蜜蜂叮没事,过一会就好了,黄蜂,或者排蜂,就厉害了。我要看身上的叮痕,却看不清,原来着急地拍打蜜蜂时,把鼻梁上的眼镜也拍掉了。好在是老花镜,没眼镜也能看路行走。护林员过来把蜜蜂赶跑,取下了蜜巢,我回头去找,发现眼镜就丢在距离蜜巢不远的树根边。戴回眼镜,躲在草丛里的那赤色鹧鸪不见了,树上那些小鸟却依然快活地在啄吃山果。
第一次让蜜蜂蜇伤,虽然没事,多少也有些吓人。不过,这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护林员不再领我们穿密林,沿着一条山间小路行走。平时山上没人,这小路其实是护林员巡山时踩出的一条羊肠小道。我们边走边拨开横在前面的树枝,我的手伸了过去,吓一跳,啊一声缩了回来,又急忙退了几步。前面那树枝上缠着一条脚拇指那么粗的青竹蛇,绿绿的与树叶的颜色相近,蛇头伸着,眯着小眼睛看来。这通体翠绿的青竹蛇很毒的,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护林员却不在乎,说:别怕,它不主动攻击人的。这位护林员就是黎族人,对蛇很熟悉,又很友好,他是“美孚黎”,也叫“蚺蛇美孚”,认为蛇有神力,视蛇为图腾,他们的祖先纹身或纹脸,就刺上蚺蛇状的花纹。护林员抓手中的竹竿敲打旁边的树枝,来个打草惊蛇,那蛇慢慢地爬开了。我们继续寻觅,更小心了,不仅要注意动物的动静,还要看旁边的树枝有没有蛇。前面一棵猴头杜鹃很繁茂,树上那粉红色的杜鹃花有碗口那么大,热烈地拥抱枝头,一片灿然。我们站在树下,看一只圆鼻巨蜥,说是它凶猛好斗,可爬在一棵枯树上却慢吞吞的。我那司机蓦地啊一声,拉住我。我回头看,见一条眼镜蛇王缠在树枝上,吐着红红的长信,正虎视眈眈瞧着我们。眼镜蛇剧毒,一招毙命。我本来就怕蛇,吓得身上的肌肉在弹动。护林员说:没事,它身缠树枝,无法攻击人。护林员见我仍怯怯的,又说:其实,动物更害怕咱们人呢。
是不是我们在侵犯动物的领地?
我们从另一条小路往回走。突然,一只孔雀雉从旁边走了出来,好漂亮,羽毛一层盖一层,银灰色,还有好看的斑纹,静静地站在我们跟前。孔雀雉不惊不忧,像是特意出来让我们一睹它的尊容,它转了几转,接着得意地开屏,突然,搧动翅膀飞走了。来到一棵高大的坡垒树下,一头好大的猕猴蹲在树头边,突然掉头,噼里啪啦三两下便蹿上树去。它又回头来瞧我们,见我们都望着它,头晃两下,做出高兴的样子,接着在树枝间跳去蹿来,又一只手抓住树枝,吊坠身子,悠来晃去,像是要给我们展示它那矫健的身材和攀爬技巧,又像在逗着我们玩。也许是它进化得比较接近我们人类,给我们一种亲切感,我们友好地朝它摆摆手,它居然嗷嗷叫几声,可惜,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动物都藏在深山的隐蔽处,不易找见它们。我们回到了车上。车子穿行在山间公路上,我的思绪却仍牵挂在动物身上。我想,这森林里的动物应该活得很自在吧,应该的,世界是大家共有的,它们应该有个安逸生活的地方,我们和它们应该和睦相处,和谐地活在这个地球村上。
五
鹦哥岭是个神奇的地方,我们在寻找更多的神奇。
白沙黎族自治县境内有个巨大的陨石坑,直径3.7 公里,从远处望去,可见一个完整的盆形凹坑,是70 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坠落爆炸而形成,科学家估算,那坠落的陨石直径约380 米。这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陨石坑,比著名的美国亚利桑那陨石坑、苏联爱沙尼亚陨石坑还久远。神奇的是,在陨石坑内,手表被磁化停止了走动,摄像机也不能正常使用,离开了,就神奇地恢复正常。科学家测算,陨石撞击地球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360 颗投放在日本广岛上的原子弹,造成岩石碎裂熔化、岩浆溅射,此处矿物质相当丰富,一块数平方厘米的样品居然检出48 种矿物。我猜想,这或许与手表被磁化的现象有关,也可能有更神秘的原因。我非常惊讶,这里的植被居然覆盖得很好,胶林莽莽苍苍,茶树遍野青翠,特别值得炫耀的是,此地产出的白沙绿茶质优、色美、口感好,饮誉海内外。殊不知,陨石坑四周的连绵绿色恰好和鹦哥岭的漫山苍翠连成了一片,融为一体。源头在鹦哥岭的南渡江就从陨石坑的旁边流过,得益于鹦哥岭热带雨林气候的温泽和丰盈水系的滋润,才生机勃勃,遍野泛绿,出奇地玉成了上天和大自然的完美联姻,共同演绎出奇观。
鹦哥岭半山腰耸起一座丰碑,那高大厚实的基座上站立着一位英姿飒爽、气宇轩昂的战士,犹如一棵直插苍穹的青松,基座刻着“琼崖抗日先锋” 六个金色大字。这里就是白沙起义发源地,又是琼崖纵队司令部旧址所在地。我从缭绕在深山密林中的缕缕烟雾读到了一部让人热血沸腾的红色历史。1942 年,国民党当局对当地百姓进行残暴统治,激起了黎、苗族人民极大愤慨,1943 年6 月,国民党当局集体屠杀苗族同胞1900 多人,黎族首领王国兴等人领导4000 多名黎、苗族群众于8 月12 日揭竿起义,至26 日,参加起义的黎、苗族群众达2 万多人次,后来,退回鹦哥岭,坚持抗暴、抗日斗争……1945 年,琼崖纵队司令冯白驹和王国兴在鹦哥岭会师,在便文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1947 年1 月,琼崖党政军机关迁移到便文村,这里成为琼崖纵队司令部,当年5 月9 日至26 日在这里召开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10 月20 日至11 月30 日又召开琼崖纵队首次代表大会,确定琼崖革命斗争从游击战自卫转向运动战反攻,拉开解放海南岛的序幕……不难看出,发生的这一切,都依托一个强大的背景,那就是深山密林。就是说,深山密林能抵御枪林弹雨,保护需要保护的人,又给他们以野果野菜填腹,让他们去做应该做的事。
我在鹦哥岭的半山腰上踯躅,吹着清爽的山风,望着这座不言不语的大山,越看越觉得它气度不凡。它以博大的爱让海南岛风调雨顺,为人们谋福祉,又散发山野清气,孕育出这许多有浩然正气的人,悉心庇护他们坚持23 年红旗不倒,终而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