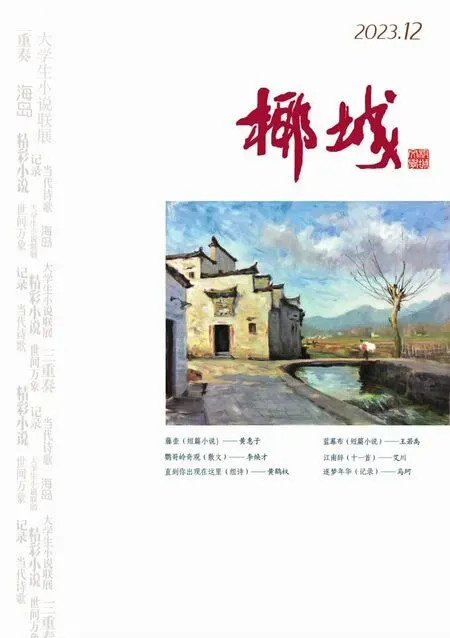铁匣子
2024-01-30徐玉向
◎徐玉向
直到多年后,我的眼前常常浮现一个场景:年迈的祖母独自坐在床上,隔了一小会又探起身子,抠出深藏着的铁匣子,就着昏暗的灯光,将里面的票子一张一张反复点数清楚,长舒一口气后,再顺着靠墙的床框塞到最底下一层。她安置好一切,关了灯继续坐着发一会呆,最后卷上被子沉睡在夜色中。
2007 年初秋,我在深圳接到弟弟的短信。他说,早上祖母突发脑溢血,已从医院送回了家。参与抢救的医生说,估计晚上就会咽气。
接到短信时,我正在福永镇上,只差几步路就到火车票售票点了。几天前才从重庆回到深圳。接了宁波一个项目的邀约电话,用最快的速度做好出发的准备。这下,行李都不用准备了,只差一张车票了。
售票点的营业员查到当天下午五点有一趟车去蚌埠。犹嫌太晚。去隔壁的万里航空查了一下当天的机票。营业员扫了一眼显示屏,说只有明天飞合肥的了。赶紧扭头买了火车票,跑回住处,提了行李就往深圳西站赶。
火车上,我电话问弟弟家里情况。弟弟说母亲已在家里着手处理祖母的后事,要我不必过度担心。“94 岁的祖母好像睡着了一般,这种病来得快,现在也没有办法,好在没有痛苦。”我问他脑溢血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引起的。他说没有。最近祖母的身体一直不错,饭量也好,昨晚上还在屋后的伯母家说话呢。今天上午12 点左右,弟妹去给她送眼药,发现门没打开。她赶紧叫人破了门进去。祖母仰身倒在床上,上衣已穿好,两只手紧紧抓着裤子,一只脚刚蹬进裤子里,另一只还在被窝里。她的那根桃木拐杖就在床头靠着。
参与抢救的医生推断,可能因为祖母性子太急,且年纪太大,血管脆弱。一大早起床时,她神志尚没完全清醒,弯腰提裤子,一用力,脑部缺氧诱发的溢血。
祖母在世时曾说,要撑到我讨了老婆才会走。我们堂兄弟几人,除了小我十岁的妹妹,连弟弟都结婚了,两个堂哥的孩子早就上小学了。她说这话时正是弟弟大婚后不久。那时她已有些耳背,精神却非常不错。记忆里的长发已剪成短发。对于当年她那头青丝,祖母还是非常自豪的,年过90 仍没有一根白发。可能是因为烧水洗梳不便,才剪了短发。对于她这一辈女性来说,剪了短头发披散着头发,实是无奈之举吧。
祖母从出生一路撑到现在。且不说她少年时代经历多少自然灾害和疾病、战争,也不提她自小就被送到舅舅家寄养,壮年在抢收庄稼还失去了一只眼睛,五十多年只能靠一只眼过活。与她同时代的老人,无论身体还是生活水平比她好得多的人均先她离开了。包括我的祖父,一个号称三棍子都打不死的壮硕汉子。在祖父离世的十五年后,她又送走了我的父亲。那是她最引以为荣的小儿子。
当祖母说要撑到我讨了老婆才会走时,我笑着说快了。有一次她追在我后面,不停地问谈得怎么样了。我被问急了,只好转身就跑。她狠狠顿着拐杖,说我一天到晚像个无事的和尚,到处跑到处溜,连个女人都说不上。说着说着,她自己却笑了起来。
父亲去世后,我常往寺庙跑,听了一个亲戚的怂恿,还差点剃了头。当时想得挺简单,剃了头就去佛学院待三年,回来当个小庙的主持,既有钱补贴家用,又有前程,最主要的是没有找老婆的麻烦。百年之后,一炬付身,一了百了。
母亲听后把我骂个狗血喷头,坚决不同意签字。自此,从广东回来探亲的有限几天里,我基本不沾家,把百里之内的大庙小庙都跑遍了,还拜了师傅。师傅说皈依不影响讨老婆。
我也曾带过几个姑娘来家作客,家里人和亲戚朋友也发动起来,也介绍过几个他们认为条件还算不错的女孩子。遗憾的是,没有一个成为她的孙媳妇。
这一次,我希望祖母能撑过去。至少撑到我讨了老婆,至少能再多看我一眼吧。
在我6 岁那年,刚过70 岁的祖父病故。那次也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离开。可能是因为时间太久,或是我太小,祖父及那场葬礼只给我留下一个囫囵的影子。
印象中的祖父,是位身材结实的大汉,常常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其实藏在帽子里的是一个光亮亮的脑袋。家里人说他会打拳。一次,他在伯父屋后的院子里在晒稻草。我说想跟你学拳。他说管。条件是要我自己先躺在稻草上,把两手背在后面,不用手能自己站起来。可惜我试了几次都不成功。他背着手站在院子边上一直看,最后一摆手,我知道彻底没戏了。
祖父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七,我的祖母理所当然成了同辈中的“七嫂子”。当时,同辈中仅有一个比她年长的四祖母还在世。祖父在世时,她一直在做低调的女人。据说祖父是个暴脾气,遇事不顺心一蹦八丈高。对祖父有限的记忆里确实有过这样一个场景,祖父一句话,让她憋在小厢房里半天没露面。
祖父出殡当天晚上,我看见祖母的面前跪着父亲和伯父,以及两个姑妈。前一天还在觅死觅活地哭闹,第二天她要人找来个木棍当拐杖。不久拿起祖父的烟袋,按了一锅烟丝,划着洋火,竟自吧嗒吧嗒地吸了起来。在村里老头子吸个旱烟是个派头,老嬷嬷吸烟也不是没有。她给我们的说法是这个家还要一个撑门头的,老头子死了还有老嬷嬷。自此,家族内有什么事,都是她代表我们两支人家去参与,家中事务也由她居中协调。
有一年春节,电视台来拍花鼓戏和民俗,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穿戴一新,坐在镜头最前面。事后,祖母一脸笑容地回到院子,说电视台里的人说的,徐郢的两位老太太像个菩萨。她说的两位老太太,一个是大祖母一个是自己。大祖父一直是家族的掌舵人,是祖父的胞兄,大祖母的年龄却比祖母小上近十岁。
父亲病逝不到一年,正在上班的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姨姐夫在电话那头气愤地说我妈被家后面的人打了。我一听,有点反应不过来,家后就是伯父家呀,那是父亲的亲哥哥亲嫂子,一家人一直关系很好,况且,还有祖母在,他们怎么会打我母亲。我在千里之外的南方打工,弟弟在省城读书,妹妹还在读小学,家里仅有母亲一人。是什么事到了让他们对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动手的地步。
姨姐夫语气坚定地要我回来办一件事。我知道那是什么事。我也相信只要我开了口,很快就会有一帮人冲过去。可是,我犹豫了,我也猜到会是谁挑的事。我回去收拾一下是痛快了,等我一走,一定会有更严重的报复。我说不回去,姨姐夫口气就不对了。我气愤地挂了电话。再往家里打电话,已没人接了。
姨姐夫打这个电话时,是发生在母亲被家后面几个人全力打骂几天后的事了。据母亲后来回忆,她被打之后,那段时间在家中几乎无路可走。市区的大姨姐后来回忆说,一天她下班回来,发现母亲一脸伤痕坐在她家门口,什么话也没有。她赶紧带着母亲去医院。后来我在老宅的一个旧提包里发现了那份门诊记录,上面清楚地记录:头部被打伤4 天,4 天前被手抓伤面部,同时用拳击伤头部,当时面部流血,目前感到头晕,胸闷,颜面伤口疼痛。面部有伤口9-10 处,下唇有3 处,创面有脓性,头面部裂伤并发感染。
母亲也是个要强的人,父亲去世后她独自支撑着家。她曾几次写信和电话催我回家。倘若我在家附近找份工作,春秋两季也可以帮家里收拾庄稼干些农活,家里有个成年男子有很多事也好处理。当时我刚出去两年,心正野着,一直拖着没回。祖母与母亲的脾气素来不对付,同住一个院子,朝夕相对,难免生些事端。家后面的因父亲不在,诸事大不同以往,连去茅厕和进出院子的路都堵上了。我记得五六岁时,因为茅厕前的小路大伯母与母亲争吵。父亲去上班,其他人没人去劝架,身材瘦小的母亲就吃了亏。
这一次,母亲便央求祖母出来说话。祖母因父亲去世,心思便寄在大伯父一家身上。婆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现,为了祖母的事小姑妈也与母亲争执过。有一次,祖母竟拿着一个碗,拄着拐杖在大马路上,叫喊着去要饭。幸被同宗长辈劝回。理由是母亲一个女的带三个孩子不容易,你这么大年纪出去要饭,丢家门的人,现在哪家缺你一口吃的。
祖母搬出了院子,住进了伯父家。不久就发生了母亲被打的事情。事后听邻居们说,动手的是伯母和大堂兄。去茅厕的路被堵上了,母亲在院子东南角临时搭了一个茅厕。进出院子的路不让走,好在我家前面的堂伯父准备把一面墙推了,让出一条路。这期间,弟弟把每月的生活费省下一部分,都悄悄给了祖母。在她们的夹缝中,无助的弟弟曾一个人跑到父亲的坟上哭泣。等我知道这些事,已差不多是五年之后了。
那年春节,我回家时看到了母亲脸上的伤疤。她没有主动提起。倒是祖母跑过来诉说着母亲的种种不是。母亲就搬了个凳子到院子里给我补背包。我回单位后,母亲就去工地上帮工,到处找活。常常,家中仅剩十多岁的妹妹照看着家。
2005 年秋天,随着弟弟参加工作家中有了转机。母亲带着弟弟和妹妹,搬进了市区边缘的城中村出租房。她一边在附近做手工赚钱贴补家用,一边照顾弟弟和妹妹的生活。在邻居的劝说下,母亲同意祖母搬回到院子里,住进了我们的堂屋。
回家的火车上,我一会与家里人联系,一会想着关于祖母一点一滴的往事。我说卡里还有钱,要是不够家里再添些,祖母的事情应该是我们家要承办的,不要因为父亲去世就不办,办完这件大事,母亲就有了一个不错的交待。弟弟回信息,二堂兄说我大伯父出钱。让人意外的是,家人在收拾祖母的遗物时,在床上翻到一个盛着钞票的小铁匣子。统计完里面的钞票,小姑妈说,剩下的费用几家平均摊。我仍坚持由我们来办。大姑妈身体一直不好,得到消息后正从百里之外的城市往回赶。
祖母怎么会在床下的小铁匣子里留了两千块钱?我总认为是别人放的。弟弟说她自己攒的。她很早就跟我老姑提过了,也只告诉过她一个人。那她怎么攒的呢?我读中学,她在碾盘桥的自留地还能种菜卖。近年身体不行了,基本也没了经济来源。“主要是家里人给她零花钱”。弟弟说,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攒的,这几年给她钱的人多,但用钱的地方极少,又花得细,全都攒起来了。她吃的也不错,两三天就买条鱼吃,院子里还有自己种的菜。
我一时无语。祖母攒钱的事应该很早就开始了,至少,父亲去世不久就开始了。“一百块的票子里,还有一张老版。”
祖母的遗体被抬到堂屋,家里人在收拾她床上的遗物。大家都奇怪,小姑妈为何不停地翻祖母的衣服。她一件一件地提起来抖了抖,再沿着袖口往上捏。她翻过衣服后,开始掀被褥,一层一层揭,没有放过一个角落。终于,在床与褥子相交的最靠墙的一侧,她摸出一个铁匣子。当着众人的面前,她数了数里面的钞票。
20 张一百块面额的钞票,原本紧紧地叠在一起缩在一处,如同一位十恶不赦被长期囚禁在阴暗死牢里的犯人,猛地一下子重见了天日。也许,看到它们的人,会同时松了一口气,恰如监狱门口迎接出牢人一般。他们的心情一定是轻松的,甚至是意外的、喜悦的。然而,我听到这消息时的心情却如受害者的家人,我宁愿这个恶魔永远被关在那个阴暗的角落,永不得见天日!或许,这个小小铁匣子里的2000 块钱,就是祖母在父亲去世后一直撑下来的底气,是一位乡下老人留给自己的最后颜面。
祖父去世之后,碾盘桥的那块地就成了祖母的心头肉。即便是冬天,从新桥到碾盘桥的路都被雪盖住了,她仍用一支长棍子为她绑着裹腿的小脚探路。寒风用力扯着她的围裙,却拦不住她前行的步伐。严寒装满她背上的粪箕,却掩不下她蹒跚的脚印。她想去,就一定要去,也一定会去,即使一刻也不能等!
在那些寒冷的冬天,即使到了碾盘桥,她能看到什么?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总觉得,光秃秃的碾盘桥在冬天实在没什么可看的。父亲每次都把炉火烧得旺旺的,让她不要去了。可是,她每次都固执地单独跑出去。她给我们的理由,是家里闷得慌,出去透透气。
父亲去世之后,祖母就很少去碾盘桥了。偶尔去一下也是转转就回来。父亲病重之时,她把抽了多年的烟也戒了。也许,从那个时候,她开始考虑在小铁匣存钱的计划吧。
那个小铁匣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即使撑着脑袋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事后也一直没有机会瞻仰这个传说中的神奇物件,以至多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个谜。我始终觉得这个物件应该不会太大,外表一定不会光鲜。也许是锈迹斑斑,也许黯然无色。我甚至会想,到底用了多长时间,祖母才会往这个小盒子里填一张钞票呢?或是很久之前就存够了,还是直到去世前一个晚上,刚刚凑齐能给自己买一付棺材的钱呢?
我是最后一个赶到家的。大姑妈早我半天就到了,他们说要等我回来才能出殡。祖母孤零零地躺在堂屋的中间,一盆焚尽的纸灰上腾起一缕细细的青烟。
揭开盖在脸上的火纸,耳边再也听不到祖母追问我讨老婆的事了。摸一下她的手,怀念着曾经无数次由我搀着去串门,无数次递来吃食的温度。她的床头毫无征兆地刮起一阵小小的旋风,卷着纸灰在屋子里转了几个圈,终又飞了出去。巷子里突然喧闹起来,拖拉机将一口小巧的棺材运进了院子。主事的翠清祖父指挥大家把棺材抬了下来。
当晚,院子里灯火通明,我用一层纸细细地糊在棺材的底部,为祖母整理一下新房子。这也是我最后能做的事了。父亲活着的时候,她有事都会找父亲。父亲不在了,有些事我得学着去做。
一条狗,探头探脑地朝屋里望。我赶紧把它赶走。父亲一直说祖母胆小,我在家的时候就听她说过怕火葬。她是老时代的人,总觉得入土为安。可是她没有祖父的福气。
在殡仪馆的火化炉前,我一直守着祖母。二堂哥留下陪着我,其他人都在外面等着。
在送进去之前,工作人员问还要不要看一眼,我说要。他们拉开链子,祖母的眼睛一直闭着。
很多人怕这块地方,我却早已无所畏惧了。土葬、火葬、水葬包括天葬,只要有人料理,都是一种回归自然的表现,无非是早一天迟一天的事情。我站在那个地方,其它几个火化炉也都在工作。奇怪的是这里除了活着人的哭泣,连火苗的声响都不曾听见,可是,工作人员却示意那些大声哭泣的人小点声。
去世人的遗体,在那个小小的铁匣子里慢慢消失。而他们的灵魂呢,也许会永远地飘荡在某个阴暗的角落,也许会进入轮回。虽然,乡下人对于人去世后的去处有着种种说法,但毕竟也只是传说,且每一种说法都不尽相同。我不知道,素来胆小的祖母,在独自前行的陌生路上是否还能撑得住。
我知道,送祖母最后一程,让她彻底与这个世间再无牵挂的铁匣子,不就是她早些年就已亲手物色好的小家伙吗?只不过,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冰冷,一个滚烫。滚烫的会一直重复着热度,但没人会记住它的模样。冰冷的却会成为家族的传说,我们也有义务把这个传说一代一代传下去。当然,还包括我的祖母。
在刘桥的丁字路口,老姑妈在烧祖母衣服。她特意把祖母那根桃木拐杖也丢进了火堆。有了这根拐杖,路上应该会好走些吧。
我总觉得,祖母是不想走的。我后来听说,抬棺的人刚过山岗,绳子就断了。一个抬棺人的脚被砸出了血。也许,你对那片生前无数次走过的埋着无数先人的坟地,仍然恐惧。我知道,你不想走。
幡子在半空中晃晃荡荡。引着送葬的队伍,从我家院子的门外一直延到二里外的刘桥。一面面花圈被扛着,每走几步,亲属得跪拜一下,唢呐声鞭炮声用盖过锣鼓,掩住了我们的哭声,直冲向云霄。
所有人都加入到出殡的队伍里。祖母的娘家人和舅舅家的人,祖父那一辈的亲戚,父亲姐妹几个的亲戚朋友和同事,我们小一辈的亲戚朋友,同宗五服之内的族人,连妹妹也有同学过来。除了我一个光杆司令,没有女人和孩子,没有同学,没有同事。
围观的人都在议论,说这是近年送殡人数最多的一次。没想到,祖母去世了,还要为自己为儿孙撑一份体面。老一辈的人都羡慕祖母,去世前没有受一点罪,一下子睡了过去便安然走了。这是什么修为?祖母安然走了,而他们还不知道自己会以什么方式离开呢。
当天,全部事情处理完,天已黑了。母亲说要回去了,明天雇主还要起早送货。我说送送你吧,母亲说不要送。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默默的没有话语,送到大井沿,她执意要我回,说村口就可以打到“拐的”。
望着母亲渐渐消失在夜幕中的孤单背影,我的泪水终于落下。我不知道我的泪水,是为了刚去世的祖母,还是执意离开村子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