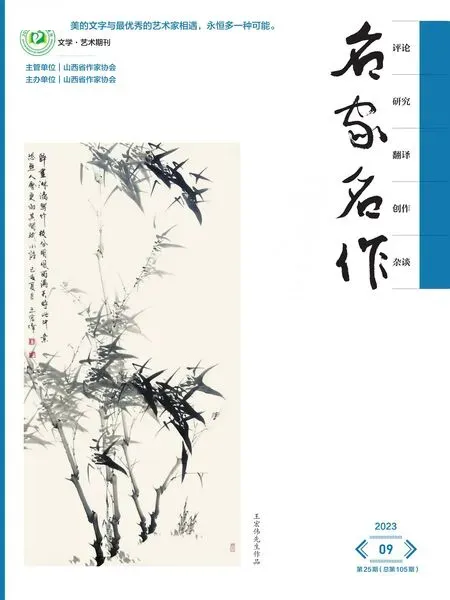性别文化视域下《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2024-01-28褚晶
褚 晶
一 、传统性别文化
《白鹿原》以族长白嘉轩为叙事核心,用白鹿两家的矛盾纠葛组织情节,反映了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儒家伦理道德,展现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中地区的历史变迁,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民族近代史。这部小说主要写了五十多年来以男性为主导的重要历史事件,如易地、交农 、农协斗争等。作家笔下生动的男性形象很多,如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鹿兆鹏、黑娃等,占据作品的篇幅长、比例大。但历史的变迁绝不只有男性,女性在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传统的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男女共同组成家庭单位,女性角色必不可少,所以陈忠实在作品中也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但是她们中的多数依托于男性,是凭借男性的需求与审美塑造出来的,被沦为面容模糊的“群体背景形象”,少部分着笔较多的女性形象也被塑造得脸谱化,或是符合男性期待的具有母性、妻性的完美女性,或是离经叛道的“妖女”。关于女性形象的概念,学者李兰认为,“女性形象指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种种外在和内在的表现形式,它既包含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人生经历,也包括人物外在表现出来的外貌特征等,是文艺作品所描写的女性形象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独有的思想、品质、行为、习惯等。艺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受到创作者自身女性意识的影响,同时也取决于艺术作品内容本身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整部作品对女性的态度从开头就奠定了基调,开头第一句就写到“白嘉轩一生最引以为豪的是娶了七房女人”。陈忠实曾亲口阐释过写这一男性话语的目的,这句话是给秉德老汉临终前的话和白赵氏“女人不过是糊窗户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的话做铺垫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三朝古都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的男权主义思想。男女人物截然不同的叙事书写背后是作家本人意志的体现,也是其在生存地域传统性别文化影响下的无意识选择。
陕西关中地区南倚秦岭山脉,四面有天然的地理屏障,自古以来易守难攻,是帝王建都的风水宝地,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受地形封闭和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生产模式的长期影响,这里的社会逐步形成正统守旧的风气,百姓维护正统,忠君爱民,保守封闭,以儒家文化为本。白鹿原作为关中农村地区,更是深受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成为关中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一个缩影。中华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深层心理结构,其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讲究伦理,通过规约、教化、习俗等方式限制女性自由,由此形成了农耕社会里的传统性别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男性是一家之主,男女有别,女性被要求三从四德,两性地位不平等。陈忠实自小生活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他无意识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在这种儒家文化浸润下的父慈子孝、男耕女织的社会,而这种影响被他投射到了作品之中。他所生存的传统封闭的地域环境不仅与他作品的内容和意象选择息息相关,还影响到他作品的内在精神和性别书写。他的作品将关中地域的性别文化符号化,形成了一种地域性的集体无意识,对我们认知传统性别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陈忠实谈个人写作动机时说到,他被县志上密密麻麻书写着的节妇烈女的名字所震撼,那些苦守贞洁的寡妇用放弃一生的自由换得县志里几厘米长的纸条记载,甚至没有名字,只是普通的某某氏,他决心写些有正常人活着的需求的女性。由此可见作家生存地域中的女性处境。作家的出发点是为这些被性别文化荼毒的女性控诉,但他也摆脱不了传统性别文化在其身上的烙印。这种地域文化语境造成的作家思想的局限性是难以消除的。
二、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很多,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逆来顺受,处在被男性压制地位的贤妻良母形象;一种是积极反抗男权,追求女性自主的叛逆者形象。传统女性如白赵氏、白吴氏、朱白氏、鹿惠氏……她们一生相夫教子,连个自己的名字都不曾有。着墨稍多的白嘉轩老婆仙草是贤妻良母的代表。她非常符合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角色设定,一生都在为丈夫为儿女而活,操持家务、传宗接代。仙草是男性喜爱和赞赏的女性,她充满妻性和母性,小说字里行间毫不掩饰对仙草这一形象的欣赏。她本不是个俗气的女子,愿意嫁给死了六房老婆的白嘉轩,打破了白家人丁不旺的传统;她温柔贤惠,从娘家带来了罂粟振兴了夫家的家业,甚至死亡也是因为拒绝了白嘉轩躲瘟疫的安排。仙草以丈夫为天,有勇气、有魄力,她一直希望替丈夫受灾,临终前还对丈夫说:“我说了我先走好!我走了就替下你了,这样子好。”但是一直到死,她也没能见到孝文和白灵,丈夫顾虑自己的颜面导致她含恨而逝。仙草是完全被男人站在男性视角上定义的女性形象,缺少自主性,沦为男人的附庸。
而另一女性田小娥由于背离传统封建文化对女性的设定,一直被斥责为“婊子”“烂货”,始终被儒家文化的捍卫者白嘉轩打击,拒绝她进祠堂,连最后暴发瘟疫的责任也要推卸给她,说她是妖孽,修塔去镇压她,连下葬时的蝴蝶也被认为是妖蛾,要捕杀干净。田小娥是《白鹿原》中一个由传统女性向新型女性过渡的女性,她被奴化、被伤害,但是她没有像那些任人宰割的传统妇女一样,而是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呐喊。
《白鹿原》让这些没有文化、命运坎坷的女性拿起人性欲望作武器,去摧毁残酷的宗法社会,挑战传统性别文化的秩序和伦理。
田小娥如此,鹿兆鹏媳妇鹿冷氏也是如此。鹿冷氏长期守活寡,丈夫鹿兆鹏不愿承认他们的婚姻,不愿回家,但父亲和公公只顾他们自己的颜面,让她长期活在压抑和寂寞之中,最终她在被公公轻薄之后得了疯病,被自己的父亲毒死。她的死是封建礼教下的男权对女性的轻视与迫害,她完全沦为男权社会的祭品。
白嘉轩的独女白灵是具有彻底反叛精神的时代新女性。白灵被视作白鹿的化身,是作者心中理想女性的化身,就连在白鹿原上可叫神人的朱先生在看见白灵的眼睛时也做了这样的评价:这双眼睛习文可以治国安邦,习武则可能统领千军万马。
自小到大白灵都比哥哥们更聪明活泼,特别受父亲的宠爱,但当她擅自悔婚丢掉父亲的颜面后,白嘉轩就坚决与她断绝了关系。由此可见,女性一旦触及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都会被毫不留情地抛弃。白灵是美好的化身,是积极争取独立自由的时代新女性,但这样的一个新女性最终却殒命于以男性为主要群体的政治集团的内斗中。这一悲剧结局似乎暗示了在一个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里,新女性是无法走通解放之路的。虽然白灵的生命光彩绽放得很绚烂,但“儒家文化对于女性的轻视是《白鹿原》始终不肯放弃的一个观念”。在这一观念的驱使下,像白灵这样与传统礼教相背离的女性就注定无法得到完满的结局了。
三、女性反叛意识的进步性
女性在传统性别文化中处于弱势地位,男性支配了物质生产、社会生活,是性别话语的中心,女性只能接受被凝视、被支配的命运。近年来,随着女性意识的崛起,广大女性渴望自由自主,逐渐形成了一种现代平等的性别文化。而《白鹿原》虽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但依然存在女性表达反叛意识的话语空间。这些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拒绝接受被传统观念定义,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萌芽与觉醒,具有进步性。
作家陈忠实的思想是传统儒家思想,但田小娥的形象却是赤裸裸的反面形象,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反抗。关于她,作家有大量的性描写,借用性来表现她对传统礼教的反抗。她三次通过性这种原始欲望来反抗命运的不公。一开始她被父母出售给年龄够得上给她做爷爷的郭举人作为性奴隶而供养着,她让郭举人吃下尿泡过的枣进行无声抗争,后又通过“勾引”黑娃,和黑娃私奔完成第一次性反抗;通过与白孝文发生关系,带着白孝文堕落以报白嘉轩之仇,完成第二次性反抗;她意识到被鹿子霖性利用后,通过对他的脸撒尿并嘲笑“鹿乡约,你记着我也记着,我尿到你脸上咧,我给乡约尿下一脸”,完成第三次性反抗。田小娥具有反抗且不妥协的精神和性自由的意识,她的所作所为是对传统儒家禁欲的重击。性是人最原始的欲望,弗洛伊德说“性欲是指人们一切追求快乐的欲望,性本能冲动是人一切心理活动的内在动力,当这种能量(弗洛伊德称之为力必多)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机体的紧张,机体就要寻求途径释放能量” ,田小娥所做的一切无非是顺应了自己的本能欲望。她勇于追求自己的性解放、性享乐,她的性不再只是为了三从四德、传宗接代。
田小娥在被鹿三杀死后还魂到鹿三身上,借由鹿三的口控诉:“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子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小娥没有犯过大错,她内心向往过平常妇女的日子,她的“放荡”是为了活下去。陈忠实给了小娥内心独白的机会,表达了对她的同情与悲叹,这也体现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反思。
白灵是作家塑造的新时代反抗者,她坚定不移地与传统性别文化作斗争,代表了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反抗封建礼教、建立现代性别伦理、尊重女性生命的成就。白灵的出生似乎就预示着她的命运,她出生时远方正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她拒绝缠足,以死相逼进入学堂,她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洗礼,走上了叛逆的道路。白灵是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战士,在当时的环境中她坚持革命,甚至因为革命理念不同而放弃与鹿兆海的感情。她勇敢背离父辈的传统道路,做事果断绝情,直接让人捎给婆家一封信悔婚:你们难道非要娶我革你们的命?她外出求学,加入共产党,打破藩篱与鹿兆鹏结合,直至最后被活埋时依然大声痛骂破坏革命的毕政委。虽然在应该如何对待背离传统的女性上作家的态度是具有矛盾性的,但白灵的形象寄寓了作家对美与理想的追求,她接受新教育,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积极反抗斗争,找寻自我价值。
四、结语
综上所述,《白鹿原》中的两性关系是全面多样的,有白灵与鹿兆海纯洁的爱恋,有白灵与鹿兆鹏以假变真的情爱,有田小娥和黑娃冲破礼教誓死在一起厮守的绝爱,也有非常传统的白嘉轩与仙草相敬如宾的恩爱……这类两性关系有和谐、有冲突,但无一不反映出传统性别文化视域下女性卑微的命运。女性被男性支配,在家中无法赢得匹配的地位,得不到他人的尊重,丧失了基本人权。无论是把女性当作生儿育女的工具、对贤妻良母的女性给予充分肯定,还是将反抗叛逆女性视作“妖女”,对其彻底否定,无一不是在扭曲和异化女性,这背后体现的是传统性别文化积淀下的男权集体无意识。作品的写作年代是1993 年,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文化领域陷入尴尬处境,陈忠实对传统儒家文化包括传统性别文化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提醒读者重视封建思想给女性加上的沉重镣铐,但由于自身思想的局限性,他无法提出出路与方法。但幸运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了女性价值,努力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勇于与传统性别文化作斗争,勇于摆脱自身被歧视、被差别对待的困境,积极追求男女平等。女性价值也越来越被社会重视,社会各界也正在积极完善各种制度保障女性权益。我们试图形成一种新型现代性别文化,找到真正有效摆脱女性生存困境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