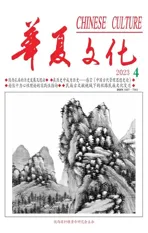简论《尚书》“五福”的生命智慧
2024-01-25张方圆
□张方圆
“五福”是中华文化中古老且在历史上一直发挥重要影响的传统幸福观、生命观。“洪范九筹”在《尚书·洪范》的记载中虽被箕子描述为上帝传授给禹用以治国安邦的九条大法,但作为最后一筹重要组成部分的“五福”观念映射出神权政治蓝图下人权统治手段与民众生活价值旨归的统一。《洪范》云:“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其归纳了人生的五种幸福,分别为长寿、富贵、健康安宁、喜好美德以及老而善终。“五福”不仅表达了个体幸福观的五个方面,还饱含着识读人生、应对危机的五重生命意蕴,即五福六极的辩证思维、德寿福长的生命智慧、立体积极的健康观念、善生乐死的生死观照以及生命永续的时空设定,这为面临着内外多重危机风险的现代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与生命智慧。
一、五福六极的辩证思维
在《洪范》第九畴中,“五福”与“六极”分涉“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与“凶短折、疾、忧、贫、恶、弱”,虽然在数量上并未完全对称,但从天地阴阳的角度而言,“五福六极”二者的内容、性质等属性呈对称状,其以系统客观、辩证统一的生命存在观为世人展现了古人对生命历程与生活构成的双重逻辑构造。
首先,“五福六极”体现了生命历程顺应自然规律的系统性逻辑。《尚书正义》曰:“‘五福’、‘六极’,天实得为之,而历言此者,以人生于世,有此福极,为善致福,为恶致极,劝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极”在这里被描述为劝人行善、追求幸福的一种手段,也表达了生命存在的多样性与自然客观性。生命并非单纯“福”或“极”的单一状态,而是拥有不同的内容。古人归纳、总结了人的生命境遇,并将其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这种呈现并未有意回避或者刻意厚此薄彼,而是以生命历程的视角对生命价值进行客观的排序和布局,体现出过程价值论取向。
其次,“五福六极”体现了生活构成要素之间的辩证性逻辑。“五福”作为幸福观的五个方面,客观上体现出明显的理想性与积极性,同时各要素之间也具有转化与制约意义。从君王政治统治角度而言,“五福六极”是治国安民的手段,即“飨用五福,威用六极”;而在庶民生活理想的认知与追求上,其揭示了宇宙事物的普遍规律和现世生活的生存之道,即福祸永在、趋利避害。同时,《洪范》还建立了“五事”与“五福”的创生关系,并提供实践论意义上的操作范式。“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晢,聪作谋,睿作圣。”即为“貌、言、视、听、思”五个方面修养操习的具体规定。同时,文献还将“五事”与庶征进行了关联,阐释了“敬用五事”对休咎结果的影响。尽管其反映出比较强烈的神性色彩,但“五事”作为天人感应的中介,已表现出参赞化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与实践性。上至君王、下至百姓,“五福六极”的言说和运用是被锚定在政治方略与世俗生活中的,这种对待生命危机的坦荡与豁达,特别是致力践行的态度,已成为了中华民族应对生命危机的集体无意识。当危机出现之时,中国人对福祸依存转化的理解就构成了面对困顿的接纳和缓冲,同时也增进了度过危难的信念与希望。
二、德寿福长的生命智慧
长寿在“五福”之中位列第一,成为中国人对幸福的首要定义。《尚书正义》云:“寿,年得长也。”,长寿何以成为“五福”之首?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寿”基于古人短寿的现实考量和自然期盼,其二,“寿”表达了古人对道德与智慧的崇敬与追求。
首先,古人的预期寿命较短,“寿”是对生命存在的必然追求之一。有学者考察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山东邹县野店大汶口时期墓葬、上海青浦裕泽遗址、晚商殷墟中小墓等出土人骨年龄,并综合《大英百科全书》记载的历代西方人口平均寿命,推论出周代人口的平均寿命当在30-34岁(焦培民:《先秦人口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46页)。《尚书》成书时代约在西周末年至春秋中叶,因此《洪范》篇所示“五福”之寿所提出的历史时期的人口平均年龄,大致与30-34岁相符。据国家发改委《“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报告,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93岁,与现代人相比古人显然是短寿的。又据《道德经·五十章》所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综合以上,我们大抵可以推断,在古代受外部环境动荡、个人养护失当等局限,能够寿终正寝、安享正寿的人其实是少数。因此,“五福”中第一福“寿”的提出是建立在残酷的现实基础之上的。古人对长寿的追求自然成为了幸福观的重要部分,这是古人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也是生命存在称其为“存在”的生生不息之力量的反映。如若没有生命本体的存有,则没有承载幸福的前提条件。长寿成为“五福”的第一要素,体现了生命存在的客观历史性。
其次,长寿者往往是经验与智慧的象征与传承者。寿者代表着拥有成熟的生命态度和至高的道德素养。《论语·雍也》记载:“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结合历代名家注解,有学者归纳出“仁者寿”的三重含义:“其一,仁者之性好仁乐仁,终生不移,如山一般安固不摇,其能济人之困,助人之生,犹如大山可生长万物一般;其二,仁者以仁为毕生追求,本无贪欲,故而心神安静;其三,因其情欲寡少,心神安静,故而长寿。”(焦国成:《仁者寿发微》,《中州学刊》2022年第6期,第78页)此番总结,道出了寿与德的因果联系:仁德是寿者的人生追求与修养路径,寿是为仁者并不主动追求却必然达成的效用与结果。古人短寿的历史情境若通过现代危机观来分析,其间饱含着华夏由个体自我而涉及家国民族的重重生命危机,此番沉重、忧虑的况味难以言表,但古人如山般安稳、静然而又生生不息的生命态度,以及德寿福长的实践性生死智慧,涌动着永不磨灭的精神力量。这对现代人的危机应对与处置仍然是充满生命力的宝贵思想启示。
三、立体积极的健康观念
《尚书正义》中孔颖达对康宁的解释为“无疾病也”,然也有孙星衍注疏引郑玄曰:“康宁,人平安也。”。可见,“康宁”之意在古人的理解似乎并不单一。回溯《尚书》全文,“康宁”亦出现在《多士》与《多方》中:“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多士》);“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多方》)。周公代表成王发布诰令意在告诫殷人及叛国臣民,将殷人迁往洛邑以及对不服从命令者予以惩处,并非周国不按德教的原则给予和平安宁的生活,而是他们不尊崇天命自取祸害所致。此两处“康宁”,都不指“无疾病”,而是生活安宁、无动乱之意。综合书中多处“康宁”的含义,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五福”中的“康宁”,不仅是指身体无疾病,更有心理意义上的平静和社会意义上的安定,是融通了身体(physical)、心理(mental)、社会(social)三个层面的健康观与幸福观。
首先,这个立体积极的健康观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定义不谋而合。1948年,世卫组织提出了“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的观点。而“五福”生命观则证明了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已具有“身心社”统一的全人健康观的雏形。其第一个层面指向个体身体层面的“无疾病”,第二个层面指向个体心理层面的安平宁静,第三个层面指向社会组织层面的安定和平,三个层面的和谐统一才是完备的健康状态。同时,个体健康福祉的达成是社会治理成效的体现,人民福利愿望与理想生活的实现根植于个体的奋斗,也依赖统治者对人民的爱护、德治的施行。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康宁”健康观是富有先见的,其为现代健康观的建立与福祉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
再者,“康宁”并不仅仅指向健康,它呈现的是以身心康宁为基础,以幸福生活为旨归的社会福祉。同样,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观也在日益严峻的全球共同危机中迭代发展,由“身心社”的健康观升级到了指向健康与幸福的融合。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日内瓦福祉宪章》,提倡“一种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精神幸福感和社会福祉融为一体的积极的健康观”,同时更强调通过“全球、社会、社区和个人健康及福祉的整合性投入,改变社会结构,以帮助人们去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健康”。“五福”着眼于生命的长度也不忽视生命的质量与高度,在诠释的沿革中演绎中国幸福观与生命观的历史性与现代性的统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四、善生乐死的生死观照
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疏“考终命”为“成终长短之命,不横夭也”,并认为“是言命之短长虽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长之命以自终,不横夭者亦为福也。”此种“考终命”之善的达成,承认生命的有限性,也强调生命的主体性,并将寿终正寝的原因归结为“安分遂性”,其包含了从“自命与自终”向“使命与善终”的转化、创造过程,它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命的性质与主体性。《尚书正义》引《左传》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古人生命观的存在论基础是天命观,人禀受天地的周正时中而存在,如若对天命之性遵循或破坏,则可引发福与祸等不同结果。这之中有两层意思:第一,命数的初始是上天既定的,受天地之中而生,有长短之分。第二,人最终命数差异的原因在于人是否遵循天命,是否遵照礼义、威仪的准则去生活。有能之人得以圆满自然的死亡,从而获得福分;而不遵照天命的人就可能自取祸害。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是天地创设基础之上的一种自定义,宇宙天地的作用成为一种基础,而人对生命之善的追求是被动的天命框架内的主动性体现。
其二,生命价值与死亡品质。“短凶折”是为“祸终”,但历史上还有一类死亡是持义秉礼、舍身取义之死,它们虽然也有可能是未冠、未婚或是丧弟失子之类的“短凶折”,但却被列为善终。这种矛盾如何解释?或许我们需要越过死亡的表象,去追寻儒家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在儒家传统中,除却自然生命的长短,精神生命的长度、高度、厚度同样不可或缺,甚至说是优先被讨论的议题。“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孔子对生死福祸的因果性给予了道德方向的规定:不正直的人在世间的生存,只是出于侥幸而避免了灾祸。在儒家看来,生命价值与死亡品质是优于生命长度的,它们才是“善终”的核心参照因素。
因此,“考终命”所体现的福善,并非单纯只是尽享天年的独善其身之终,更指向了人伦使命的进德修业之生。“善终”实质上是通过“善生”建构的,没有“善生”便没有“善终”。生命最后的安宁之福或生命终点对人生整体的价值评价,是建立在“过好怎样的人生”的基础上的。在“自终”与“善终”之间,中国古人通过“自命”与“使命”的自觉转化,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文信仰和实践抱负,构筑起了一条通达的桥梁。
五、生命永续的时空设定
“五福”表面上以长寿为始、以善终为末,实质上是以生观死、以终为始,通过长寿康宁、进德修业的在世修养,成就正终、善终的意义人生,继而达成生命不朽的永续经营之道。儒家文化承认肉体生命的有限性,同时也保有精神生命、人文生命在时空中传递和延展的可能性。此番“生死有无”之间,衬托出儒家精神于时空序列中的生成性与超越性。
第一, “彝伦攸序”的礼乐生活构筑了生命价值与生命品格的空间生成。中国人的生命价值是在关系空间中被定义的。从微观来看,个体生命在亲亲尊尊的空间伦理、道德规范中,创造出生命的意义空间。《礼记·礼运》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这十个方面的“人义”即为对不同生活空间内的人伦关系做出的道德规定。而从宏观来看,家庭、族群、村社、民族、国家等自小而大的礼制空间所生成的集体品格或组织精神,将会生成化解群体危机、安顿生命困顿的重要财富。“生生”不仅是宇宙的规律,也是伦理之善。中国人坚韧、顽强、乐观的民族品质,使得他们在“无康宁”的动荡社会、民族危机之中也从未放弃过求生和复兴。“哀乐相生”“祸福相依”在意识层面化解危机的焦虑感,“五福”的追求在实践层面让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成为一种不断行进的标的和不断锤炼的生活样态。
第二,“三不朽”的实践路径构建了生命价值与生命品格的时间超越性。古人重史,更重视青史留名。《尚书·君陈》记述了成王在周公去世之后任命君陈代为治理东郊殷民的策命之辞,其在阐明德政主要内容时指出:“尔克敬典在德,时乃罔不变,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尔之休,终有辞于永世。”这段文字主张对法制秉持敬畏恭谨的态度,将政教提高到大道的水平,由此将获得相对好的结果——不但成王能多福,君陈的美名也能为后世之人所称颂。可见,进德修业、流芳百世的“不朽”思想在此已有所体现。而为世人所耳熟能详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则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分别指向以道德品质树立典范、惠泽百姓;以丰功伟业应对危机、成就功绩;以著书立说传承智慧,后世流芳。“三不朽”反映的是以理想人格与生命智慧的不朽对自然生命可朽的抗争与对经验世界的超越。其途径有二:一是将个体生命汇入家族生命之中,通过生命遗传的物质形式与史志仪礼的精神形式得以传承广大;二是投入到更加宏大的历史叙事中,通过践道、殉道的方式名垂青史,在身后的世界中传递出精神生命的荣光。
“五福”观念闪耀着深远的文化印记与思想底蕴,是中国人生死智慧在上古时期的典型代表。面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时空中所蕴藏着的各种危机与挑战,中国人发展出了一种应对危机的独特文化范式,即通过五福六极的辩证思维、德寿福长的生命智慧、立体积极的健康观念、善生乐死的生死观照以及生命永续的时空设定,在德福修养中转化生命困顿,在积极创造中实践生命价值,在善终传承中实现生命超越。以上的生命智慧或可成为一种资源与借鉴,在现代人面对外部世界的不断变化与内部心灵的失序风险时,得以自觉回向中华传统文化,发掘出其当代价值,积极探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路径,以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之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