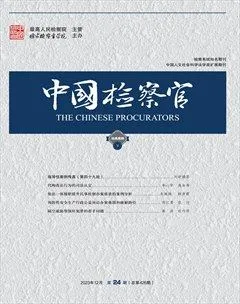网络犯罪辅助行为的性质
2024-01-18姜子明徐世博
姜子明 徐世博
一、基本案情
2022年3月至4月,行为人操某在上线“铁猴”(身份不明,未到案)的安排下,纠集多人以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册的微信账号,向不特定对象添加微信好友进行聊天并取得信任。操某等人让微信好友下载安装二手车众筹平台软件并注册会员后,再将其拉入相关微信群中,在微信群内发送虚假众筹资料、充值情况与获利截图等信息,引诱被害人在平台内进行注册投资。随着参与众筹人员增多,投入资金累计达到一定数额后,操某便会根据上线的指示关闭平台服务器,投资者将无法登录平台提现。截至案发,各被害人实际被骗资金1000余万元,操某陆续转出资金800余万元交给上线。
二、分歧意见
网络犯罪辅助行为,是指行为人在明知他人从事网络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仍然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为其违法犯罪活动提供相应辅助的行为,主要表现包括但不限于网络非法推广引流[1]、网络虚假宣传、网络资金结算等方式。该行为利用各类新兴网络技术为网络黑灰产业“供粮输血”,造成网络黑灰产业的蔓延,社会危险性較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为有效遏制网络犯罪,对网络犯罪采取“打小打早”的策略,增设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犯罪辅助行为进行规制;2019年10月,最高法、最高检出台《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以设置较低入罪门槛,规制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和其他帮助行为等方式对网络犯罪的严惩立场。[2]但是由于网络犯罪辅助行为存在主观明知模糊、行为手段多样等特征,司法实践中对于相关行为的认定莫衷一是。在本案中,对操某行为的具体认定存在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操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从主观方面来看,操某对于上线“铁猴”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是明知的,但对于上线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则并不清楚。同时,结合操某实施的组建微信群、发布虚假众筹信息等行为来看,其在明知他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仍通过网络信息技术进行辅助。从客观方面来看,操某所实施的组建微信群、发布虚假众筹信息等行为,符合刑法第287条之一第1款“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与“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等规定,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操某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综合在案证据只能证明操某在明知上线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犯罪的情况下,为犯罪活动提供推广引流、电脑操作技术和支付结算帮助行为,其与上线事先无诈骗通谋或共同故意,诈骗活动结束后也没有将上线骗取的财产据为己有,因此操某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操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操某明知他人利用网络进行诈骗,并帮助他人实施具体的诈骗犯罪行为,使得以上线“铁猴”为首的诈骗团伙得以通过虚假网站诈骗被害人钱财,该行为系共同诈骗行为,应当以诈骗罪共犯处理。
三、评析意见
由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网络犯罪共犯之间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交叉性,司法实务中经常难以区分,本案突出表现为对行为人操某实施的网络诈骗辅助行为以及其主观明知程度的认定不一。在上述意见中,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不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为有效应对网络信息犯罪愈演愈烈之势,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将原本仅规制网络犯罪实行行为的刑法触角延伸至设立网站、通讯群组、发布信息等网络犯罪的预备行为。[3]从实务研究来看,仍可以以犯罪形态的差异就操某是否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进行分析。犯罪预备是犯罪实施之前的准备行为,突出表现为犯罪预备的时间早于犯罪实行行为,且预备行为还未直接与侵害对象发生直接关联,还未出现具有犯罪危害与后果的直接风险。
第一种意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论证了操某在明知他人实施违法犯罪的情况下,通过实施组建通讯组、发布虚假信息等行为为上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了充分准备。但是从本案情况来看,一方面操某的违法犯罪行为在上线违法犯罪实施过程中仍然存续。在本案犯罪实施过程中,操某仍参与引诱投资、资金结算等活动,其行为不符合犯罪预备的时间要求。另一方面,操某除实施一般性的网络技术辅助行为外,还实施了帮助上线进行支付结算、关闭网络服务器等行为。显然,其行为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犯罪预备行为。因此,操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二)不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刑法第287条之二第1款规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从主观上来看,本罪的明知为概括内容的明知,即行为人对他人实施的犯罪实行行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认知,但并不要求行为人能够明确知道他人实施犯罪的具体内容、性质。从客观行为来看,法条列举了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行为,而最终落脚点为帮助,也就是说构成本罪应当为为相应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明显达不到帮助程度或超过帮助范畴的行为则不构成本罪。
第二种意见将行为人操某所实施的相关帮助行为与上线所实施的诈骗犯罪进行了完全割裂,并且进一步认为操某与上线的主观犯罪故意也相互独立。实际上,操某所实施的相关违法犯罪行为与上线的诈骗犯罪关联相对较高,因此将两者之间完全区分有待商榷。从主观方面来看,操某根据上线“铁猴”的安排,纠集他人实施了发布虚假众筹信息、引诱被害人投资以及对诈骗款项进行结算等与诈骗犯罪关联紧密的行为,操某对于上线实施诈骗犯罪已经具有较高的认知程度,超出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于主观方面的认知标准。从客观方面来看,操某所实施相关行为的犯罪作用、危害后果已经明显超出了帮助行为。从犯罪作用来看,如果没有操某的系列违法犯罪行为,则本案的诈骗犯罪难以顺利实施,其作用较为关键;从危害后果来看,操某通过实施行为不仅直接骗取了不特定对象的大额资金,同时还通过关闭服务器等方式阻断了被害人提现的可能性,其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大。
(三)构成诈骗罪共犯
第三种意见则从操某所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其自身的主观认知进行了综合分析。从客观上来看,操某的行为已经与上线的诈骗犯罪深度关联,其违法犯罪行为是上线诈骗犯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主观上来看,操某参与了诈骗犯罪中的准备、诈骗以及赃款结算等环节,其对于自己参与诈骗犯罪的行为是明知的。
1.单项意思联络之下网络犯罪共犯认定的可行性分析
在传统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中,二人以上均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构成共同犯罪的前提条件。共同犯罪行为人之间需要就实施共同犯罪行为存在意思联络,达成合意。[4]然而,网络共同犯罪行为较之于传统共同犯罪模式产生了一定变化。就本案而言,首先,行为人之间属于单线关系,上线仅与行为人操某之间存在联系,再由操某分派任务给其他人员,各行为人之间的犯罪意思联络趋于弱化。其次,由于网络空间具备虚拟性、不特定性、异地性,本案中未能获得上线的有效信息,诈骗行为实行者难以到案,致使意思联络难以得到有效证明。最后,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相较于传统的帮助行为,独立性和危害性可能更强,其对于完成犯罪起着越来越大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危害性凸显。[5]
由此可见,传统共同犯罪理论难以对网络空间共同犯罪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将单向意思联络纳入网络犯罪共同犯罪故意中则可以大大降低司法取证难度,从而达到打击网络空间犯罪的效果。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高一部电信网络诈骗法律适用意见》)第4条第(三)款第5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体现出在信息网络犯罪中对于单项意思联络中明知型共犯的规范倾向。
2.主客观综合认定本案行为人操某为诈骗罪共犯
具体到网络诈骗辅助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是辅助诈骗行为人与网络诈骗实行人之间呈现“一对多”的结构方式,即辅助诈骗行为人为多個诈骗犯罪实行人提供网络技术帮助行为。此种模式下辅助诈骗行为人的帮助行为呈现独立化特征,其对诈骗主体所实施的违法犯罪内容并不关心,因此不能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对具体诈骗犯罪为“明知”状态。即使辅助诈骗行为人按照常理能够判断出固定话术信息为虚假借贷、融资等信息,也难以达到刑事犯罪意义上的“明知”故意,不宜认定为诈骗罪共犯。二是辅助诈骗行为人与诈骗犯罪行为人之间为“一对一”的结构方式,即辅助诈骗行为人只向某一特定诈骗主体提供网络技术帮助。此种情况下,即便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具备共同犯罪意思联络,仍可以根据辅助诈骗行为人对诈骗犯罪的明知程度以及对诈骗活动起到的作用大小等因素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诈骗共犯。如果辅助诈骗行为人主观上对诈骗犯罪达到基本认识,且其实施的行为已经与诈骗犯罪行为高度关联,且能够直接对具体犯罪客体造成侵害,则可以认定行为人构成诈骗共犯;反之,如果辅助诈骗行为人对诈骗犯罪认知不足或在诈骗犯罪中的地位较低、发挥作用过小,则难以认定其构成诈骗共犯。
回归本案,行为人操某仅与上线“铁猴”进行单线联系,且仅为“铁猴”提供辅助服务,属于“一对一”的链条关系。从主观方面来看,操某与上线“铁猴”联系紧密,“铁猴”安排操某实施了组建微信群,发布虚假的众筹信息,诱导他人注册投资、赃款处置等系列违法犯罪行为,虽然操某没有与“铁猴”直接接触,对于“铁猴”的具体诈骗情况难以完全认识,但是基于操某与“铁猴”的沟通交流以及操某所实施的系列行为,可以推定出操某对于“铁猴”实施诈骗犯罪具有基本认识。从客观方面来看,操某参与了本案的整个诈骗犯罪过程,尤其是其实施的诱导投资、处置赃款、关闭服务器等行为直接作用于被害人且危害较大,其实施的系列行为对于诈骗犯罪的顺利实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行为已经与诈骗主体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综上,行为人操某为诈骗罪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