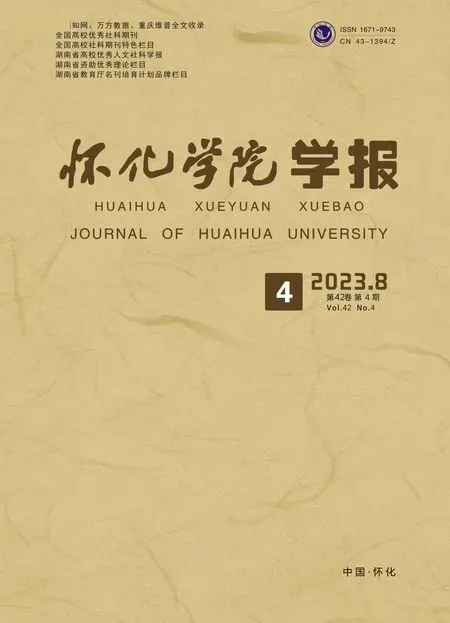血缘与地缘:梭戛长角苗的社会与秩序
2024-01-17杨元丽王顺松
杨元丽, 王顺松
(1.贵州省博物馆,贵州 贵阳 550081; 2.多彩贵州文化投资集团,贵州 贵阳 550081)
一般而言,人类学、民族学对西南山地民族社会结构的研究通常聚焦于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家屋社会与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组织,并围绕此间展开对其社会内部运行逻辑的探讨,尤其关注仪式的展演与实践对地域社会的整合作用。贵州省六枝特区梭戛长角苗是一个典型的村寨聚落姻亲网络构成的社会,血缘与地缘是其社会整合的主要机制,信仰仪式更在其社会运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梭戛陇戛长角苗族
在贵州省六枝特区西北部与织金县交界处居住着一支被称为“长角苗”的苗族支系。“长角苗”①亦称“箐苗”,“长角苗”是汉语称谓的他称。
传说清代初年这支苗族奔逃至此,躲入茫茫深山,他们称茂密的森林为“荣”(音译),“荣”即是“山林”、“箐”的意思;因此自称“蒙荣”②,即“箐苗”,意为躲在深山箐林中的苗族。《百苗图抄本汇编》一书中记录了这一说法:“‘箐苗’一名源于该苗族群体的自称‘蒙荣’,含义是指森林中的苗族。他们通用苗语西部方言贵阳次方言的西北土语,其分布区集中分布在今贵州省普定、织金和六枝三地的毗连地带。”[1]可见,百苗图中的“箐苗”条记录的便是这一居住在织金、六枝等地属苗语西部方言贵阳次方言区的苗族支系。从《黔苗图说》中可见其妇女所着下裙与如今的箐苗百褶裙有些许相似之处。然而,“箐苗”指称的却不只是如今的长角苗,还包含了周边相邻地区的歪梳苗、圆角苗、短角苗。
如今这支只有5000 余人的长角苗支系,以头戴的木质长角为识别物,主要集中分布在相邻的12 个村寨之中。所居之地跨越两县三乡,即六枝特区梭戛苗族彝族回族乡安柱寨、高兴村陇戛寨、补空寨、小坝田寨、高兴寨;新华乡新寨村大湾新寨、双屯村新发寨;织金县阿弓镇长地村后寨、官寨村苗寨、小新寨、化董村化董寨、依中底寨。这些村寨之间以婚姻为纽带,维系着血缘与地缘的情感联系。其中高兴村陇戛寨便是笔者的调查地点。自1998 年梭戛生态博物馆落地陇戛寨,这里俨然成了梭戛长角苗的文化中心。在许多语境中,“梭戛”并非如行政区划中的“乡”一级别的,而是特指梭戛生态博物馆所在地或是以陇戛寨为中心的更小的地域范围,以及与陇戛寨长角苗一样的同族群的人。
陇戛寨为高兴村下辖村民组,截止2020 年,全寨共有144 户603 人。陇戛寨坐落在山坳中,民居高低错落有致,面谷靠山。据寨上的老人说,先民们来到陇戛定居已有300 多年,最初只有几户人家,现已传至十余代,居民由杨、熊、王三个姓氏组成。
长角苗称家族为“献”(音译),“献”有“献饭、供奉”之意。根据各个家族祭祀祖先的代数来相区别,有三代共同祭祀的祖先的为“三献”,有五代共同祭祀的祖先的为“五献”。结合长角苗打嘎的丧葬仪式中指路歌的唱词所描述的长角苗先民迁徙的路线与田野调查资料,最早在陇戛寨居住的是李姓家族,但因李家人丁凋零,现在已经没人了。而后其余几个先后迁入陇戛寨的家族情况如下:
第二个家族—五献熊(熊振全家):织金—三家庙—安柱—陇戛,原为歪梳苗。
第三个家族—三献杨(杨朝忠家):织金—三家庙—陇戛,原为弯角苗。
第四个家族—五献杨(杨少益家):织金—陇戛,原为歪梳苗。
第五个家族—五献杨(杨宏祥家):织金—陇戛,原为歪梳苗。
第六个家族—三献杨(杨得学家):纳雍—发离—桂花树—陇戛,原为弯角苗。
第七个家族—三献杨(杨国学家):三家庙—陇戛,原为圆角苗。
第八个家族—二献王:水城—纳雍—吹垄场地—安柱—陇戛,原本就是长角苗。
这七个家族最晚于20 世纪30 年代都己迁入陇戛寨,基本的迁徙走向都是从北向南从织金县与纳雍县迁入。[2]
二、血缘的纽带
(一)耗子粑节
在长角苗的社会生活中,节庆民俗是最为惯常的集体活动,耗子粑节便是其中一项。耗子粑节苗语称为“咳哉”(音译),它是长角苗以家族为单位祭祀祖先的仪式活动,通常在火塘旁进行。
传说,旧时有一年耗子特别多,庄稼受灾严重。“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耗子鬼作孽,为控制它自由出入人体,继续为害,人们用粑粑堵上病人的七窍,令鬼与人同死。鼠才得以控制。后来人们每年冬天都做粑粑,以防鼠疫鬼,渐成俗。”[3]从那以后人们在农历十一月任一个龙日每个家族都要组织打耗子,并用糯米打一大块形状似耗子的糍粑供奉祖先,故而称为耗子粑节。
长角苗过耗子粑节以家族为单位,不同的家族在具体的祭祀时间、仪式细节等方面有所差异,但都由各自家族的家师来主持仪式。家师是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角色,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家师。苗语称家师为“松丹”(音译),是家族中执掌丧葬仪式的人,一个家族一般有两三名家师。长角苗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每个家族都需要有专门的人来记住家族里每一代人的名字,能准确辨别各自复杂的亲属关系及亲属互相的称谓。这对长角苗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家师一般是由家族男子中记性好的,最好是有些文化水平的人来承担。
在商定好的耗子粑节这一天,十二寨的同一家族每年轮流在各个寨子里选一户家中有年长老人的家庭,全部族人都集中到这家去。如果当年家族中有老人过世,则耗子粑节就必须要到这家去过,每家带去一块粑粑,人们称之为“被窝粑”,意为十一月冬日天凉,要给祖先“盖被窝”了。
(二)仪式与秩序
据陇戛寨村民口述的耗子粑节仪式如下:众人在墙角放两个条凳,上面铺上一张凉席。家师拿着竹卦一边敲打一边逐个喊祖先的名字,每念到一人,就说一次“洗”,且舀水往地上倒一下,意为给祖先洗脸,直到所有的祖先都洗到。接下来家师拿一个酒碗,为每个祖先献酒,同时家里的男人们把打好的粑粑成对地摆在一张席子上,再摆上若干个装着甜酒的碗,一般三献家族摆三排,五献家族摆五排。家师继续指着一对粑粑念读每一个过世先人的名字,三献就念到三代内过世先人的老名③,五献就到念五代。念完之后先把所有的小碗粑粑都撤走,只留三个大碗献饭,并再一次念诵每一个祖先的老名。上述步骤完成后,家师还要挨个念读在世亲人的名字,这也是耗子粑节的结束仪式。人们供奉完祖先后,将所有粑粑与甜酒一起煮成一大锅给全家族人同共享用。
仪式是秩序的体现。耗子粑节是长角苗人祭祀祖先的仪式,从空间范畴上来看,其活动地点在火塘旁。列维·斯特劳斯在1970—1980 年代基于北美、东南亚、非洲的亲属制度研究提出“家屋社会”(House-based Society)[4]的概念,指出家屋是一种社会结群(a social grouping)方式。在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家的核心是婚姻的缔结与孕育子女的过程,随着子女的成长,他们也将构建新的核心家庭,家屋的构建代表了原有家庭的分裂与新核心家庭的产生。家屋不仅是一座房子,更是一个以此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社会的缩影。从村寨的形成来看,陇戛寨由七个不同血缘家族组成,家族形成时间短,以最基础的核心家庭为单位。
如果说长角苗社会的核心是家庭,那么作为家文化物质载体的家屋的核心便是炉灶。因此火塘是家屋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多重的文化属性,火塘在长角苗的空间、日常与象征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可以说“生火”即是“生活”。
炯咋④啊,我就要走了。
我生病的时候你不管我,我呻吟的时候你不说话。
如今我就要走了,不要再难过。
——《开路歌》[5]
不仅如此,长角苗社会中,火塘确立了家庭话事人的地位,在家庭形成后,火塘便约定俗成作为家庭话事人的男女主人的卧房。火塘不仅是日常生活空间,更是是许多仪式性祭祀活动的空间,是长角苗传统的神圣空间。这里世俗空间的神圣化过程体现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互融,通过仪式将物质空间转化为精神文化空间,表达出家屋社会中的各种规范,为个体指明了行动逻辑与方向,实现社会空间的升华。耗子粑节通过共同的祭祀行为将生活在不同村寨的同一家族的人们联结在一起,祭祀实际上划定了人群的范围,从“核心家庭—房族—家族”由小到大的聚合过程,实现了以血缘家族为单位的社会关系整合。血缘即是结合的核心要素,也是家族维系的唯一凭证。仪式唤起了个体对群体的深层认同,加强了集体的联系,同时发挥着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曾提出过“神圣事物”的概念。耗子粑其形似带来了灾祸的耗子,但通过吃掉塑造成“耗子”的糍粑即表示消灭了灾祸。因此,耗子粑既是污秽的化身,又是洁净的良药。这样一个社会集体生活的矛盾产物作为一种“符号”,其本质即社会力量的体现,它规定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仪式的对象即是家屋社会中的祖先,又是神话了的鬼神。通过为祖先“洗脸”等仪式行为,代表了除秽与新生,人、鬼神、祖先三者在仪式中达成平衡与和谐。
在家族中,家师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记住每一代逝去先人的名字,通过念诵先人的名字让人们真切体会到彼此的亲缘关系,引发共同情感的表达,达到纪念的目的。同时,集体仪式的展演对群体认同具有强化功能。念诵名字的过程也是个体身份自我认同、个体对祖先、对神鬼信仰的认同过程。家族的延续与传承观念随着家师念诵的每一代祖先的名字得以不断根植与强化。
三、地域性社会的整合
如果耗子粑节是以家族“献”为单位的祭祖仪式,那么祭箐仪式便是以村寨为范围的地缘组织的集体活动。在连绵的深山箐林中,世代繁衍的长角苗,依然保存和延续着自己独特而自然的风俗,他们敬畏自然、遵从自然。在陇戛先民的迁徙过程中,他们认为是层层箐林保护其躲避外敌的侵扰,林中有山神、树神世代庇佑他们的子孙,神树便是神的使者。因此,人们便选定寨旁林中参天的古树作为神树,于每年农历三月第一个龙日举行盛大的祭箐仪式,通过扫寨、封山、祭箐、看龙坛等一系列礼仪,以祈求神的保佑。
(一)祭箐仪式
首先,扫寨。“祭箐”也叫“祭树”或“祭山”。祭箐仪式前要先扫寨,由鬼师主持。鬼师苗语称为“弥拉”(音译),是长角苗社会婚丧嫁娶、祭祀等重大活动中代表人们与神、鬼等超自然力量的连结的桥梁,在长角苗社会中起重要作用。后勤等相关事宜则由村民轮流组织承担,每年七户村民为一组。
一大早,寨子里家家户户都要先将房屋清扫干净,同时女主人会包好一包煤灰挂在门外的树枝上,等待弥拉挨家挨户将其收走,煤灰与“霉”“晦”谐音,寓意将不好的事情都扫除带走。
弥拉来时,一只手拿着响竹⑤,另一只手提着一桶酒,身后跟着三个人,一人端着簸箕,一人牵着一只公鸡,最后一人则负责扛着挂满煤灰包的竹子。
扫寨要每个村民家中都扫到。每来到一户村民家中,弥拉一手打着响竹,一手抱着公鸡,一边念诵着吉祥语,并在走出房子前洒下几粒黄豆,助手则收走了村民家放在门口的灰包,等挨家挨户扫完后,弥拉一行人从寨子的西边径直出寨,直到遇见第一个三岔路口才停下。弥拉指挥助手将挂满煤灰包的竹竿丢掉,并杀鸡祭祀。弥拉示意村民们用稻草搓成绳子,系在东、南、北三面寨口两侧的树上。等到弥拉扫寨完成从西寨口出去之后,也立即用草绳将西面的寨口也封住,此举意为封寨,将一切厄运挡在寨门之外。至此,扫寨完成,弥拉便带着助手往神山上赶去,而杀掉的鸡在扫寨完成后便归弥拉处置了,作为其扫寨的酬劳。
其次,祭树。上午扫完寨,下午便可祭箐了。祭箐实际上就是去寨子外的神山祭神树。在长角苗人的观念中,神山上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动的,神树更是不能砍。
祭祀开始,寨里德高望重的寨老带着男人们到神箐里的神树下,先用四个树杈搭出一个架子放上祭品,接下来由寨老领头敬酒、杀鸡。陇戛寨有三个神箐⑥,每一个神箐都要祭到,每个神箐需要杀两只鸡来祭,将鸡腿肉剔除后看鸡腿骨上的鸡卦卜吉凶,然后将其挂在神树上给神树敬酒即可。三处神树重复着相同的仪式。
再次,看龙坛。祭完神树还要看龙坛。龙坛是陇戛初建寨时埋在寨子高处的土陶坛。由一个属相是龙的村民将坛口的石板打开,以便于观察坛内水位的深浅。如若坛内水清满盈,则预示着这一年将风调雨顺,反之则有灾害之忧。杨××是陇戛寨的“祭宗”⑦,待仪式结束,由他说吉言后即可封坛。
祭祀仪式结束,众人在山上分食酒肉,安排下一年仪式的操办者。七个留下的鸡头被分给下一年轮值的七户人家,一户一个。
以上三个仪式步骤分别对应了三个层次的内涵:扫寨关注的核心是个体家庭的安宁,祭树则是守寨,看龙坛则是对建寨历史的回望。
(二)社会组织的建构与秩序
民俗事项是民族社会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它表现为各种仪式与民间信仰的交织,并往往围绕着对超自然信仰的崇拜而形成的观念与行为。
长角苗先民们将自然环境的力量神化,认为无形的山神主宰着村寨的吉凶,于是通过在特定时间与空间中的集体活动形成一种可供个体遵循的规范与秩序,通过相同的集体记忆的个体便能与集体发生强烈的互动与连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无论是耗子粑节还是祭箐仪式在自然科学发展的今天早已失去了原始宗教与巫术的功能,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群体整合的目的,更多的是对共同祖先、共同历史的认同心理与强化。祭箐仪式与耗子粑节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结群纽带。耗子粑节代表了以血缘家族为单位的集合体;祭箐仪式则通过具有地缘性的共同崇拜与信仰,以家屋整合为村落。最终长角苗社会民间的社会结构表现为:核心家庭—“献”—寨—十二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扩大构成血缘家族,家族之间通过血源关系、婚姻关系紧密结合,构成村寨组织,村寨之间则是以婚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地缘组织。正如埃文斯普理查德主张的,基于血缘的继嗣群原则与基于地缘的共居原则并非对立的,而是一种共存关系。[6]
在长角苗社区中,十二个村寨都是相对独立的村寨,即是通常所说的自然村。村寨民族成分单一,因此相对封闭与独立。一般认为,各村寨中,自然领袖寨老、寨主(如村组长)和鬼师有着天然崇高的地位,实际共同治理了村寨,寨主从事行政管理,寨老从事道德管理,鬼师则从事精神控制。然而在探访时发现,情况并非全然如此。
以陇戛寨为例,村民杨××是人们公认寨老,但他自己并不承认,他说长角苗社区也并没有“寨老”这个称呼。解放后,陇戛寨的第一任村长是杨××的父亲,第二任村长便是杨××。由此分析,或许是由于杨××作为村民组长,又实际担负起了所谓寨老的职责,管理着村寨的各种日常事务,德高望重,故而人们在回应学者们的采访时就附会的认为杨××是寨老。总的来说,寨主和寨老的推选制度或许真的存在过,但随着老一辈人的记忆已经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而现今“寨老”的称呼更多是众多关注梭戛的学者对寨中自然领袖的“概括”。
就官方层面来说,陇戛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行政上隶属保甲制下的甲长所管辖的村寨;而在实际事务中,陇戛村民作为金姓彝族地主的雇农,则直接受到彝族地主在寨中指派的委托人,也就是被人们称为“老寨”⑧的本寨村民的约束,这实际上是彝族土司制度在当地的残存。如今长角苗村寨的民间事务,诸如婚丧、祭祀等活动中,的确存在村民自发形成的各项活动的主持者与领导者。“寨老”实际指的是村寨中辈份高、年长且有威望的老人,是自然形成的精神领袖,寨老不是特指某一个,而是一类人。而“寨主”在现今常常与现代政治体制下的村民组长相重合,是实际为村寨办各种事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的精明能干的人。
寨老主持祭箐仪式表现出了新的文化内涵,即血缘亲属关系到地缘关系的扩大。神箐即是村寨的守寨神,成为公共祭祀的对象,划分了同一个祭祀圈。祭箐仪式作为一个族群性、地域性的文化展演,固定而严肃的仪式规则持续建构了长角苗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不断强化民间话语权威,不断重申了长角苗建立在血缘亲属关系和地缘基础之上的非制度化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和结构。通过寨老、鬼师、家师等特殊角色在各种民俗仪式中共同发生作用,使得一个由血缘、姻亲、地缘等多种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得以建构与正常运行。
四、国家在场与社会重构
21 世纪以前,陇戛长角苗一直隐于大山深处,默默无闻。直到1998 年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将生活在这里人们带入现代文明变革的滚滚浪潮之中。
(一)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立
1985 年,安来顺将“ecomuseum”翻译为“生态博物馆”。1994 年9 月,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刊主编苏东海与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理事、挪威《博物馆学》杂志主编约翰·杰斯特龙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学会委员会年会上,就生态博物馆和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后,专家们从中国本土实际出发,创造了自己的模式和做法,将这颗国际生态博物馆理念的种子最先种在了中国梭戛这片土地上。
1995 年在贵州省政府的支持下,贵州省文化厅的推动下,被誉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的苏东海带领的专家团队,同挪威的博物馆学家组成了在贵州开发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课题组。课题组经过科学考察和论证后,制订了《在贵州梭戛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报告》,随后国家文物局和贵州省政府批准实施这一项目。1996 年,该项目被纳入《中挪1995—1997 年文化交流项目》中。
1997 年10 月23 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及皇后宋雅出席了该项目的签字仪式,签署了《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中挪两国开始在贵州省合作建设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在国家文物局与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以及挪威合作开发署的无偿援助下,中挪两国专家共同努力使得梭戛生态博物馆筹建完成。1998 年10 月31 日,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正式宣告开馆,约翰·杰斯特龙作为挪威的代表出席了开馆仪式。
(二)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跳花节
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对梭戛来说无疑是一场历史性变革。随着博物馆的建立,打通了这里与外面世界联通的路。
1998 年梭戛生态博物馆建成后,为了扩大影响,长角苗传统跳花坡习俗演变成了有展演性质的跳花节,地点固定在了高兴村,时间也固定在正月初十这一天,成为当地一个盛大的节日。
伴随着国家的影响力日益深入到民间社会,仪式中的“国家符号”也就越来越多,哪怕是根植于“草根社会”的仪式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嵌入国家权利和国家的表述符号,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民间仪式的“国家在场”。[7]
跳花节中的国家在场首先体现在对跳花节的命名、选址与时间的规定上。首先,长角苗的“跳坡”(坐坡)先后经历了“跳花坡”与“跳花节”的更名。其次,跳花坡的选址也是国家力量作用的结果。据了解,有一年跳花地址选择时,原本看中的场地没有得到土地主人的同意,但是政府为了节日的效果而出钱征地,从那之后,跳花便有了固定的宽阔场地。然后,当地政府为了迎合旅游资源开发以带动经济的号召,将长角苗独特的文化资源以及梭戛生态博物馆的特殊性作为一面鲜明的文化品牌旗帜向外宣传。就活动内容来说,除了保留长角苗传统规则体系中的祭花树、抢花线等内容外,还增加了有预演的节目会演,参与跳花的群体不再是单纯自发的青年男女,还是能因此获得酬劳的工作人员与演员。最后,作为官方代表的政府官员为跳花节站台发言,以及受邀参加跳花节的各路媒体,也是国家力量浸透乡村社会文化网络的体现。
文化是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一种特有的乡村符号。在梭夏这样贫困的民族村寨中建立生态博物馆,国家力量的介入改变了长角苗社会原有的面貌,“跳花坡”至“跳花节”的转变使得跳花场不再纯粹是未婚青年男女交往的场域,更是一种融合了地方传统文化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节日文化。
长角苗社会的运行也从传统话语权威主体的作用,加入了现代行政话语权威主体的力量。寨老、寨主、鬼师等自发形成的非制度性传统话语权威即使在现代行政体系完善的今天,也深刻影响并规范了长角苗社会成员的行为与社会的运行,在与国家力量的碰撞与融合中,在自我的调适与外力的协同作用下,长角苗社会不断地被重构,共同维系了现代长角苗社会的运行与秩序。
随着社会变迁与国家在场,跳花的展演形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伴随着这些变化,跳花的性质、目的、意义、功能不断重构着长角苗社会。
首先,由官方参与组织并规定了跳花节举办的时间,以及跳花广场上随处可见反映国家意志的标语,无一不是国家作为符号在场的表现。既通过跳花节传达国家意志,又强调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宣传及生态博物馆品牌的打造,使跳花节逐渐成为传统资源与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的节日文化。其次,传统跳花以民俗信仰集会为主题,由长角苗村寨自发组织开展,并以“花树”为中心,跳花时有传统信仰意味的“砍树、栽花树”祭祀仪式,也有世俗的男女共跳芦笙舞、三眼箫吹奏、对歌等即兴歌舞表演。而社会变迁中、国家在场下,如今的跳花节则以官方意志为主导,由政府主办,并以官方出资修建的固定的文化广场为中心,整个活动虽然保留了传统的“砍树、栽花树”等祭祀仪式,但形式上已经由传统的全民狂欢变成了舞台展演性质的活动。可以看出,以给未婚男女提供相识机会的集会目的已从主位退居次位,更多是以集聚人群、打造长角苗文化旅游品牌、助推文化旅游为目的。再次,无论是传统跳花还是国家在场下的跳花节,长角苗传统芦笙舞、三眼箫吹奏等都作为展演的主要内容被搬上舞台,但同时还增加现代主流音乐舞蹈结合长角苗服饰等节目,其功能因此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自娱自乐倾向于向外界宣扬的展演,反映了国家意志符号逐渐融入了传统民间习俗庆典的过程。
在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背景下,“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性符号”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以其强有力的资本与权力资源塑造了长角苗社会新的群体价值观念,推动了长角苗传统文化的转型,为其传统文化活动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总之,耗子粑节与祭箐仪式都是梭戛长角苗文化信仰的重要表现形式,都表达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祈求祖先庇佑的美好愿望。同时,在共同的仪式与信仰活动中,社会组织与人际关系网络得以构建,族群认同得以加强。如耗子粑节具有强烈的族群专属性,无形中强调了族群的边界与血缘家族的独一性。另外,祭箐仪式虽在许多周边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但长角苗的祭箐仪式反映了当地社会中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的高度融合。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8]
随着现代化浪潮席卷而来,在生态博物馆建立与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外界的力量尤其是国家的力量提供了一个契机,加速了长角苗社会的变化发展。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使“长角苗”“梭戛”成为一种“符号”,通过对当地文化和资源的整合,梭戛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
总的来说,现代长角苗社会是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与官方社会组织两组形态的叠合;是一个在现代政治行政体系下的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相结合的社会结群单位。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中,梭戛长角苗社会不断发生转型,形成并内化为新的地方性规则,形塑着现代长角苗的社会与秩序。
注释:
①“长角苗”为苗族的一个支系,以其服饰中戴长木角头饰而有别于其他民族及支系。此称谓为民间惯用的汉语他称的称谓。“长角苗”这一称呼因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立被外界广泛关注与熟知,故因“长角苗”这一称谓现实的知名度,本文中特使用“长角苗”一词泛指的生活在六枝、织金交界的这支苗族。
②音译,也译作“蒙戎”。
③在长角苗社会,当女子生育之后,意味着核心家庭构建完成,夫妻双方都将在孩子满月给孩子取小名的同时各自取一个“老名”,表示自己过渡到人生的另一阶段。取老名与取小名显然最大程度达到了这个目的,通过孕育孩子给予女子身份的归属,同时强调了夫妇社会角色的转变。可以说,取老名是长角苗男女的第二次成人礼,标志着少男少女时代的终结。
④上世纪末,陇戛寨里多数人家只有一间房。低矮昏暗房里,进门一眼就能先看到用黄土堆砌的炉灶,当地居民称之为“炯咋”(音译)。
⑤响竹,即将竹子一头剖成四片,人拿着不剖的一头摇动,竹片打在一起便可发出啪啪的声响。
⑥陇戛寨有三个神箐,据学者吴秋林在《梭嘎:苗人文化研究》中的田野调查认为,陇戛寨的三个神箐或是因为过去祭箐是以氏族为单位的,每个姓氏家族单独有一个神箐。其一,陇戛寨中主要有熊、杨、王三姓,三个神箐或可对应三姓家族;其二,在调查中得知,在祭箐时,只有杨家才有说祭祀词及摔木片的行为。
⑦祭宗,这里指的是主持和主导整场祭祀的寨老。是笔者在田野调查时受访者以汉语解释其在长角苗社会中的含义。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长期遭受匪患,为得到武装保护,长角苗家庭每年要向周边的豪强大户上交玉米,与之结成互保关系。民国时期,陇戛寨长期依附于梭戛彝族金姓地主,老寨便是彝族地主在陇戛寨中指派的委托人,负责管理本寨的雇农及收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