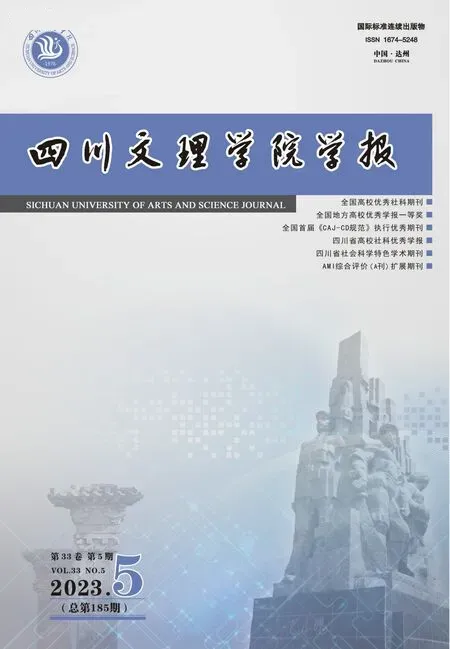何以有执着书写巴山的热情
——田雁宁中篇小说论
2024-01-16陈桃
陈 桃
(四川文理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从时下的文学史来看,“田雁宁”或许不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名字,即便说起田雁宁,大家更多的是提出关于他商业创作的相关话题.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巴山作家群”的巨大存在,田雁宁的少壮有为以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颇有声望使得田雁宁及其中篇小说获得揄扬不断的同时,还具体地阐释了“巴山”的符号意义——巴山、巴水、巴人多维关联之间的哲学境界与诗学想象.田雁宁的中篇小说主要集中在《田雁宁文集》第一卷《绿水伊人》之中.在这部四十余万字的作品中,田雁宁用诙谐、戏剧、庄重、寓言的语言氛围,熔铸了以乡土情结为底色的“巴山”系列中篇.
1 庄重灵动的乡土叙事
田雁宁的中篇小说故事容量丰富,不仅有乡村原始生命力的感性记录,更渗透出巴人与天地的本质奥妙.这既源于多声部叙事的交响,也归功于田雁宁对巴山文学“矿藏”采掘得透彻且广博.在《田雁宁文集》第二卷《巴山》自序中,田雁宁将巴山喻为“一部竖立天地之间怎么也翻不完阅不尽的大书奇书”,认为读懂巴山,“才真正明白什么是中国”.正如作家东西曾说:“乡村与我有一条相连的脐带,这条脐带让我知道乡村与亲人们的真实状况.只有知道乡村,才敢说知道中国.”[1]
《唢呐,在金风里吹响》讲述因定下“小儿亲”的牛新坤与竹叶儿从彼此的厌恨、磨难到最后互相理解、自由恋爱的曲折动人故事.竹福根因为贪念牛洪禄一壶大曲酒,便同意让自己的女儿与牛洪禄的儿子牛新坤“捆绑”在一起,定下“小儿亲”.牛新坤与竹叶儿逐步长大,彼此的厌恨也越来越深,且各自有了喜欢的对象.竹叶儿的生病催生牛、竹两家关系的恶化.牛家执意退亲,并索赔所送财物.竹家认为牛家不守信用,且为竹叶儿治病,无力归还牛家钱财.戏剧性的是牛新坤与竹叶儿也正是因为经济往来推进了彼此的互动、了解到再次结亲.《唢呐,在金风里吹响》再现了物质困乏之外“小儿亲”的形成路径.牛新坤与竹叶儿从退亲到再次结亲试探了“小儿亲”这一习俗的内在边界.牛新坤与竹叶儿在一系列事件中的绝望、挣扎与折返中建构了完成时态的未来叙事——现代文明进程中还深藏在巴山的传统陋习的必然“离场”以及乡村理想伦理的期盼,也宣示了巴人在苦难面前所能承受的种种考验.《唢呐,在金风里吹响》除开用荒诞叙事派生出庄严与恢弘的乡土主题之外,用经济纽带来表现巴山年轻人的坚韧、忠诚与深情也是该作品的又一动人之处.
《巴人村纪事》延续了田雁宁短篇小说《小镇人物素描》的叙事结构,但《巴人村纪事》更显内容与艺术的水乳交融,这得益于田雁宁写作空间的拓展与写作技艺的进一步圆熟.《巴人村纪事》对乡土人事的思想提纯与动态写真使文本呈现出史诗的品质.《巴人村纪事》由九个彼此独立、逻辑自洽的故事组成.《大刀》中的“大刀”在文本中具有传奇性与多义性.“大刀”不仅是巴人村不可多得的“革命文物”,还是夕老爹难以排除的情结.“大刀”杀敌无数,可也在历史的混乱中酿成了错误.“历史现场”的惊心动魄不是把“大刀”放进展览馆就能说得明白的,夕老爹索性把众多人前来索取、珍藏的“大刀”改造成了一把锄头.和平年代的“大刀”从冰冷的武器变成掘土垒坟的锄头,以断夕老爹对班长的相思和对冤死亡灵的悼念.《悬棺》与《大刀》存有共同的庄重叙事模式,但意图各有所指.与《大刀》再现巴人村的红色革命记忆不同,《悬棺》的叙事维度指向了巴人精神遗产的超时空魅力与民族大义.福全的儿子志康战死云南前线,福全决定以巴人村祖先的方式将志康的棺材架在山岩.山岩上岿然不动的“悬棺”作为一个符号,让巴人村的人民获得精神的洗礼与内心的净化.《牛车》将“一男二女”的传统叙事进行颠覆,展现巴人村的人情世故与刚烈率直.《反刍》与《水土》则以诙谐的方式,表现巴人村的男人女人的爱情故事.
田雁宁执着且擅长讲巴山乡土的故事.故事里的巴山纪实与想象,宏大图景的勾勒以及细部修辞的妙用,灵动立体地再现了巴人社会的生活图景与社会伦理,辽阔了读者对巴山的认知.这些巴山故事的连缀成就了田雁宁有目共睹的“文学巴山”.
2 平民书写的人文抚慰
田雁宁仿佛是一位执着的精神守望者,他不间断地用平民视角、语言与意象去刻画伫立在巴山乡镇社会犄角旮旯的愚昧者、妥协者与反抗者并与对其忠心不二.或许是文人的责任、巴山的包容与过于负载的历史苦痛、人生艰辛共同规训了田雁宁温和、宽厚与从容的性格特征,而这些性格特征又投射在其中篇小说的书写之中,使得田雁宁的中篇温婉惬意.这当然不是说田雁宁的中篇缺乏感伤的气质,乡村社会与生俱来的藏污纳垢在田雁宁的中篇没有被遮蔽,呈现为骇人的真相、乡村的悲歌与柔肠百结的故事.
《遥远》里的老实人满珍的不幸以为母亲借钱治病为中心而延展开来.因借钱而被骗卖到异地河南.数年后,当满珍意外得知母亲的离世,她离开亲生骨肉,踉踉跄跄地回到故乡.满珍的回归,得到的不是理解与同情,而是嘲弄与利用.胡疤子被视为满珍被拐卖的“中间人”而遭受牢狱之苦与心灵折磨,但在出狱之后办理采石场带动乡邻致富以驱内心之疚.满珍的青梅竹马与爱恋对象杨润林则从政为官,并娶其好友碧儿为妻.杨润林以手中的权力与胡疤子的愧疚为依凭,对其不断打压,幻想获取更多钱权.杨润林的欺瞒、自私与狭隘如一柄利剑让胡疤子的隐忍并没有保全其身,而是节节败退,并且最终刺向了满珍的胸口.对于满珍来说,故乡遥远、亲人疏远、人心隔离.小说最后没有“闪现”美满的局面,而是让外乡逃难者聂蛮胡子寻找负气出走的胡疤子以及满珍的落寞作为结局.聂蛮胡子作为满珍“事件”的旁观者,他的正直、粗犷与良善印证了他所追寻的对象——胡疤子品性的向善性,也从侧面提示了杨润林不良企图的失败以及这颗乡村权力结构中的“毒瘤”和乡村秩序的不确定因素终将被清除的事实.与此同时,小说中满珍对聂大胡子的突然“表白”也使得文本出现无法缝合的分裂感.
如果说《遥远》是田雁宁作为写作主体用“文学虚构”作用于“社会解剖”,那么《女人•男人•舢板船》则以“非虚构”的方式进行“灵魂拷问”.春阳镇是个热闹非凡的小镇,这里物产丰富、交通便利、风气开化.罗顺成是掌舵舢板船的行家,但他靠岸春阳镇既不为寻找生财之道,也不贪图佳肴美酒,而是迷恋能干贤惠、文静娟丽的秀嫂.秀嫂有一个女儿,也曾有过一个丈夫.秀嫂的凄楚与罗顺成的同情汇流之后,便产生出绵绵爱意.可好景不长,罗顺成执意要秀嫂在船上过日子的强烈“攻势”遭到秀嫂“顺记豆花饭”小店的坚决“抵抗”,两人感情虽深,却不得不分道扬镳.而这个时候,给罗顺成造成过深深伤痕的安安又出现了.罗顺成与安安曾意外相逢并私定终身,然而一天早上安安的悄然离开与数年的杳无音信让罗顺成备尝爱情的心酸与苦恼.罗幺叔跟罗顺成有同样的遭遇,也解释了作品中为什么罗幺叔每次路过春阳镇都不上岸的原因.安安的离开,是想助推罗顺成造船梦的实现;秀嫂的不肯上船,是因为城镇人的不习惯与顾及女儿幼小.好在,故事的结局是罗顺成与罗幺叔互相解开彼此的心结、体悟出为人的方圆智慧,敞开心扉拥抱属于各自的幸福.事实上,罗顺成的感情突围与折返提示了众多行船人的共同心理症候——“时代理想”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紧张与失衡而带来的精神苦痛.田雁宁始终关注着乡村世界的某些精神性缺失,他的文本介入、深情款款表露出参与重建乡村精神世界的坚定态度和战略眼光.如此般高尚的写作良知与文人情怀实现了对那些暴露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的文本的超越,也使得田雁宁中篇小说的话语体系与结构图式无限地延展着中篇文本自身持久的美学张力与哲学境界.
3 和善忠厚的巴山赤子
所谓的“和善忠厚”在这里有两层意思:首先,是指田雁宁所表露出的敦厚和善的文人气质;其次,是指他的中篇所持续的写作立场.田雁宁性格温和、儒雅博文且勤奋上进、笔耕不辍.田雁宁籍贯虽是重庆铜梁,但出生在达州开江.巴山的自然资源、人文历史赋予了田雁宁独特的性灵与纯朴,加之在巴山的知青体验、求学生活与就职生涯,巴山对于田雁宁来说是就不仅仅是单向度的生命“血地”,还是其哲学沉思与美学凝练后的“纸上故乡”.
《绿水伊人》是作家田雁宁潜入巴人文化心理结构底部而讲述的温情故事.主人公黄秋阳出身于碧溪镇的书香世家,黄秋阳的中文、数理化拔尖,却执意要考取美术院校,黄秋阳在学习西洋画还是中国画左右摇摆的同时,也注定了他参加高考的失败.黄秋阳和杀猪匠何青林与妓女月妹子的女儿何水苗两情相悦后,他便坚定了专研中国画的想法,并在与何水苗的热恋中,不断提升了绘画的水平和获得越来越多的外界肯定.恋爱的甜蜜使两个年轻人憧憬着美好未来,他们以为放弃远大的前程理想或者舍弃成为山区民歌手的机会,两颗心就可以靠得更近,但横亘在他们爱情面前的是门第的差距、“黄”“川”间素有恩怨的派系之别.对黄秋阳的学业、婚姻忧虑最多的是义无反顾从北京到碧溪镇从事乡村教育的妈妈——卢京华.卢京华对儿子黄秋阳的考虑、担忧符合情理,但她想到自己无悔的选择似乎对黄秋阳与何水苗的情感又多了一丝理解.最后小说以何、黄两家共闹元宵进入小说的高潮和达到爱情的圆满.在《绿水伊人》中,显性获得的是一个美满的爱情故事,而隐藏其中的更是巴山人民的淳朴、通达与友善,也是田雁宁作为写作主体对“生于兹长于兹”的巴山的乌托邦般重构与深情告白.
现代的巴山早已不是唐人刘禹锡诗句中所描述的那样:巴山“凄凉地”,只能“弃置身”.在田雁宁眼中,巴山大有可为.留在巴山,即使身体不能,那就安放灵魂或者留下牵挂成为田雁宁的中篇所具备的特殊魅力与乡土情怀.《月亮溪》中的月亮溪远离城市、山川巍峨、草木丰茂.月亮溪的山民剽悍但忠厚、女子淳朴且秀美,正如山歌所唱:“山虽穷来水不穷,人虽穷来心不穷.”《月亮溪》围绕年轻人在巴山的去留展开叙事.姐姐秀月和一个知青热心热肠地恋爱三年后因知青的归城遭到抛弃,直到令人担忧的二十五岁的到来,秀月依然没有定亲.来自繁华省城且是林业学院的大学生方辉的出现擦亮了秀月锈迹斑斑的人生.方辉热爱大山,属于森林,为此还与心爱的姑娘分了手.方辉对月亮溪的喜爱让秀月重新估衡了对家乡的评价也重拾起爱情的信心并步入婚姻殿堂.秀月的妹妹新月向往省城,坚信月亮溪的妹子可以在大城市立足,但新月喜欢的岩生却执意要在月亮溪闯出一片天地.月亮溪虽小,但却是岩生的理想世界.犹如田雁宁所执着的乡土叙事,何尝不是以“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写中国.在《月亮溪》中,虽说土地不再是农人的“命根子”,而是多元生活要素之一,但“从作品中可以看出田雁宁是倾向于农民立足土地来治穷致富的”,[2]这是田雁宁故土情结的真情流露,也是对城市与乡村并非平衡的双向流动的隐忧.
结 语
田雁宁“作为忠诚于大巴山的当代作家”,[3]巴山对于田雁宁来说有着文学创作的起点与标志性意义.巴山是田雁宁中篇,乃至短篇最为执着、留恋与反复耕耘的文学场域.可谓没有“文学巴山”,田雁宁后期广为人知的商业创作或许会逊色不少,自然也就无法建立起他的“小说帝国”.正如贾平凹从“商州”出发,然后叙写“秦岭”;莫言从“高密东北乡”抵达了遥远的异国他乡,田雁宁的巴山“出发”与“返回”,既是其中篇小说的制胜之道,更是令人瞩目与难能可贵的创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