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缘政治视角下的产业发展与文明演进
2024-01-14续芹
续芹
产缘政治视角下的产业发展与文明演进续 芹张笑宇《产业与文明:复杂社会的兴衰》从产业的角度来回顾了文明史,内容肯定主要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的事儿了。之前人类社会除了农业,并没有什么其他产业,那时候并没有形成“正增长秩序”。人类对能量的利用效率很低,苦苦挣扎在“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全球化几十年之后,目前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社会,牵一发动全身。有时候,你牵动引线,并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现代社会为了适应分工合作的安排,教育体系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专业划分。这导致了我们每个人都仅仅熟悉自己周边事物、仅仅了解自己专业领域,人们据此作出决策,但他们可能无法深刻知晓自己决策可能给自身(或社会)带来的确切影响。那我们是否要因此畏首畏尾,无法决策呢?我认为,也不是。我们需要掌握决策方法,并了解复杂社会的特点,尽可能多的掌握事实和信息,运用批判性思维来决策。至于最终的蝴蝶效应和结果,那是社会自然演进的过程,我们无法左右。
这本书中,张笑宇讨论了产业的形成、产业对社会的影响、产业对国家间博弈的影响三个主要问题,并分别用“漏斗-喇叭”模型、“三流循环理论”和产缘政治来解释他的观点。
产业的形成产业的形成需要技术,技术是产业形成的前提。但是否新的技术一定会形成产业呢?答案是否定的。产业的形成需要有土壤。某项技术必须经过“商业化”“产业化”,使得发明人有利可图,证明这项技术能够找到运用场景,证实这项技术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求,才能够形成产业。张笑宇用“漏斗-喇叭”模型来解释复杂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逻辑。
在另一本《技术与文明》书中,张笑宇就提到很多技术在古代早已被发明出来,但没有形成产业。因为这些技术没有被用来满足大众的需求,而是作为奇淫巧计供宗教、皇权使用。大众如何才能有需求?需要大众“有钱”和“自由”。机缘巧合之下,在英格兰形成了一群比较富裕的市民,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需要照明、取暖,于是对周边煤炭采集形成旺盛的需求。蒸汽机最初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满足煤矿矿井抽水的需求。可以说,蒸汽机能够被发明出来,是因为煤老板愿意给钱。
而且产业和技术之间复杂的演进关系,可能是一开始人们想都想不到的。煤炭相比木柴能量单位更高,运输成本更低,伦敦的市民纷纷改用煤炭。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需求,他们需要换锅。于是又带动铸铁技术的发展,而铁艺的提高又助推了蒸汽机零件的改造和升级。
又例如,铁路如何被发明出来?一开始也是为了矿井里面运煤而设计使用的。
由于蒸汽机启动能耗较大、成本较高,这样就形成了人歇机器不歇、三班倒的情况。于是夜间照明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需求。围绕照明,形成了一系列的发明创造。为了让照明效果更好,人们不断寻找可以燃烧的物质。最终,石油的开发和利用、发电机的发明,使得人类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
汽车这个产业在一开始其实同时存在蒸汽机汽车、内燃机汽车和电动汽车三股力量。只不过福特用流水线方式生产,降低成本,才使得内燃机汽车胜出,其他两种车型竞争失败。近些年随着电池技术的发展,电动汽车才又回到人们视野。
再比如,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发展其实离不开游戏产業的繁荣。没有那么多爱打游戏的人,也不会有今天的ChatGPT。
因此,作者感慨道:“纽卡门蒸汽机只能用于矿井中的抽水工作,亚伯拉罕·达比公司只是一家铸造铁锅的公司,屈尼奥的蒸汽机汽车完全失败,特莱维西克的火车跑得还没有人快,拜耳和巴斯夫早年只是污染河流的染料作坊而已,没人想到它们会成为今天的巨头……许多创新型技术,早期需要度过漫长的尴尬期。”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人类对能量流运用的一次实质性提升,之前人们只能利用自己和动物的体能,和一些少量的自然能(风能、水能)。但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人们可以将煤炭的热能转化为机械能利用,人类对能量的利用能力显著提升。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入了石油这种新的能源,又发明了电能的利用方式,也标志着人类对能量利用效率的显著提升。
但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化革命)对能量效能的利用上却没有显著变化,因此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这一次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效果与前两次相比其实是很弱的。
创新这件事是否能够由政府完成呢?试错阶段最好还是交给千千万万的企业来完成,因为我们并不确知哪个方向是可行的。早期新技术盈利的应用场景很难判断,是完全靠市场试错试出来的。早期印刷机盈利靠印刷赎罪券,早期蒸汽机盈利靠给矿井抽水,早期铁路盈利靠运煤,早期化工盈利靠开染坊制染剂。政府可以做的是创造宽松的经营环境,让市场发现那些可以盈利的新技术。
古典民主为什么出现在雅典,因为雅典的部队以海军为主,需要依靠水手的力量,平民个体的力量在政治中就显得很重要。斯巴达为什么是贵族统治,因为斯巴达部队以陆军为主,当时主要是重装步兵,只有有钱人才有财力置办重装,因此他们有话语权。古罗马的共和制本质上是一个依靠骑士阶层的军国组织,要置办骑士装备也得有钱,因此是贵族统治。这个实力变化带来的政治变化,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物学院包刚升《抵达》一书中也清晰地描述过。在欧洲大陆,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国王的汲取能力提升,欧洲大陆上其实兴起了君主独裁的风潮。不过,那时候民主、平等等观念通过启蒙运动已经深入人心,世界已经回不去了。
民主并不天然就是一个好东西,相反,由于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这让古代的政治学家们对古典民主十分反感。民主可能的问题有:可能选出不称职、不优秀的人;没有力量与之制衡;如果大众认知水平较低,民主就会陷入争吵和短视;民主不符合信仰原则,容易释放激进和狂暴力量。这些都是很早人们就认识到的民主的问题。但为什么近一百年民主大行其道,为什么人们不再担心那些“民主”的坏处了?答案可能就在于工业化以及物质财富的积累。
1835年托克维尔在对美国的民主实践观察和研究之后,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中认为美国当时被“拉平”的社会现实造就了美国民主。张笑宇提出要理解这些巨大的社会变化,通过“三流循环”来观察是一个好的角度。能量流、产品流和资本流,作者用这“三流”来解释复杂工业社会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博弈,认为这个模型是简洁适用的。
产业革命往往起始于资本流、爆发于能量流,大规模变现为产品流。
张笑宇对两次工业革命的“三流循环”做了图示,书中结合产业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分析。
张笑宇的视角是宽广的,他能够将古今中外的一些历史时刻贯穿起来,形成自己对历史的一种解读和思考。例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为什么能够推行下去,离不开世界范围内的“白银大发现和循环”。张居正并不知道自己的改革有赖于美洲的探索;而腓力二世也不知道自己国库的稳定有赖于东亚政局的稳定。
资本流说到底是基于“信任”。国家与资本之间的互动可以追溯至14世纪的佛罗伦萨,前段时间看过的雅各布·索尔《账簿与权力》正是对这段故事的精彩回顾。几次大的力量更迭,西班牙、荷兰、英国都与国家利用“资本”“金融”的力量息息相关。很多学者认为七年战争中,英国之所以战胜法国就是因为英国政府发行“公债”,善于运用信贷市场。
能量流则体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对煤炭的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石油、电力的利用。城市是能量的集中营。煤炭行业由于有井下这个“隔离空间”,又由于煤炭运输相对是一个重人力的活儿,这就给了工人力量崛起很大的实力。
产品流体现在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产品上。工人阶级要发出声音,他们就需要控制产品流。例如,煤炭工人就需要展示他们控制煤炭流的能力,他们的确有这个能力。于是,工人通过罢工等方式为自己争取到一些权益。铁路工人也具有这种隔离空间(可以形成组织)和控制产品流的便利,因此铁路工人为自己争取权益也很常见,并取得很大成效。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整个人类的社会观念、组织形态、政治制度和家庭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塑造了现代社会。由于城市化、大量人口聚集,使得工人阶层和后来出现的中产阶级有了一定话语权,这给人类政治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工业体系、工业规律强化了人们的量化思维和因果思维,给人们带来了秩序感和组织感的同时,也带来了规则和服从。
但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这次人们主要是利用石油资源,但石油开采能够给工人提供的隔离空间并不多,而且石油运输的管道化使得工人控制产品流很难。因此,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工人很难组织起有效的罢工。并且这时候劳资双方经过之前的斗争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妥协和对话机制,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系统内部”(马尔库塞《马克思主义、革命与乌托邦》)。
张笑宇认为新时代的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在控制能量流和产品流上可能都有点弱,因此,他们的话语权不高,甚至他们构建这种能力的意图在全球化时代被极大削弱了。想象一下,一个公司的客服部门其实是聘用的海外员工,这些员工并不会为了公司在本部受到的不公待遇去斗争。但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这样的,信息流对于当今社会的人们来说也非常重要。不体会到痛苦,可能就不会觉得幸福。人就是这样的。事情只有到一定程度,才会触发反应。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复杂社会的崩溃也仅仅需要几十年时间,要维持一个复杂社会,需要在充足的资本流基础上,推动技术进步向着提高物质生产能力的方向前进。
权力是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有三种力量最容易转化为权力:暴力、财富和观念。很多时候权力的获取是依靠暴力(拳头大)积累了财富,创建了相适应的观念而得以贯彻和保留。古代的权力是这样的,现代社会其实也并没有脱离这个范畴。
张笑宇提出了“产缘政治”的概念,认为现代主权国家主要通过对一系列关键技术、产业链和产业人口的合法主导权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凯恩斯主义看到了“自由放任”的弊端,提出政府需要干预和介入。因为等待市场自然“出清”的过程,必然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在经济危机期间严重的阶级矛盾把希特勒这样的人推上台的事例。当然,哈耶克对此的反思是要警惕“理性的自负”,还是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这矛盾吗?这并不矛盾。政府虽然无法知道应该发展什么,但政府应该知道哪些是绝对不能做的(辜朝明《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
张笑宇在书中讲述了铁路产业如何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普鲁士靠领先的铁路建设和铁路军事动员,战胜法国。之后,欧洲各国都在疯狂扩充铁路资源。德国工人的增加使得原来的地主没有了仆人,种地的人少了,地主们提出要提高关税,保护德国的农产品。这样就使得德国与原本交好的俄国有了嫌隙(俄国对其出口粮食)。最终一战爆发的时候,一开始俄国觉得自己产粮大国,打仗时粮食不会有问题,但事实是很快城市就缺粮了。俄国的自耕农很快就退掉了自己私营的农场,回到公立农场混日子,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铁路动员能力使得一战时几乎是所有能够被动员的人力都上了战场,机枪扫射又让这些人一批批倒下。到一战后期,几乎所有的军队都哗变了。
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的赔款,是德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这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张笑宇认为,美国的发展本身绝不是“自由放任”的结果,而是政府强有力引导的结果。美国建国者之一汉密尔顿的著作中其实就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产业化思维。他断言,人的天性是善于模仿的,如果没有人迈出尝试的第一步,整个共同体就会害怕尝试未知事物,美国因此会停留在农业经济。因此,他主张与英国搞好关系,引进技术,發展工业。美国也确实执行了这个政策,并快速发展起来。
书中用石油产业来进一步描述“产缘政治”。从美国石油资源的发现和开采,到洛克菲勒石油公司被分拆。20世纪初,美国的石油产业在全球处于垄断地位。二战之后,美国是如何利用“产业”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影响力的呢?可能的路径,一是通过“技术种族隔离”,即只将技术交予它认同的人选。二是通过“信仰隔离”,利用他国内部的信仰问题,找到代理人。学术上有了一个“资源诅咒”的说法,越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工业化水平反而会停滞不前,产业难以转型,政治十分腐败,经常出现寡头和独裁者。在石油时代,输油管把工人与能量流隔离开来,他们很难发声。用张笑宇的话说就是,在“技术”“民族”“地理”三重隔离之下,谁又会去关心他们呢?
二战结束后,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本身就是“产缘政治”的典型代表。美国专门成立了经济合作局用来推行计划。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获得了整个“马歇尔计划”资金的5%(约6.85亿美元,分六年给完),用来资助海外的秘密行动,宣传美国模式的优越性。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提倡“绿色革命”,推广农作物、化肥和灌溉技术,有效遏制这些地区的共产主义革命。
从产缘政治的角度看,苏联不是美国的对手。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天然带来的技术商业化漏斗不健全;虽然它能源丰富,但在技术上受制于人;美国将一些木马技术故意泄露给苏联间谍;造成西伯利亚油气管道大爆炸,给苏联经济带来重创。加上阿富汗战争,产缘政治、地缘政治双管齐下,肢解了苏联。
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力量”符合人们天然的价值取向——努力应当有收获,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通行的普世价值观在产业化上得到了很好体现,这也是它飞快壮大发展起来的人性基础(我只要努力干活儿,我就有好生活)。
近四十年来,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享受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红利,成为了世界制造中心。
全世界的假发有一半是河南许昌生产的,全世界的小提琴有三分之一是江苏泰兴黄桥镇生产的,全世界的酒店用品有40%是扬州杭集镇生产的,全世界25%的泳衣是辽宁葫芦岛兴城生产的。还有中山的灯具、福安的电机、周宁的钢贸、四平的换热器……
在未来,机器化生产能够替代人类绝大多数现存劳动时,人们如何在寻求价值感、认同感上获得满足,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更加专业化的社群、更加精细化的服务、更加多样化的需求可能会被创造出来,人们的价值认同、幸福满足是在与其他同类的密切互动中产生的。我们要立足今日,拥抱未来。
未来,张笑宇寄希望于核聚变能够为人类带来新的能源革命,而小行星采矿也可能给人类带来新的能量资源。
而回到最初,如何才能够促进技术进步、通过“三流循环”,并最终产生“产缘政治影响力”呢?需要保持有活力的、繁荣的市场。繁荣市场从哪里来呢?来自人们的信心和需求,来自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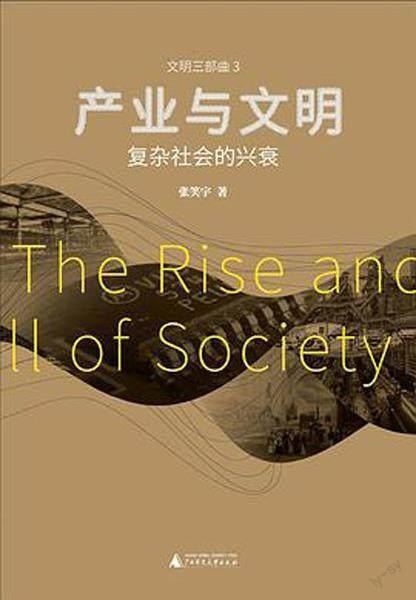
张笑宇/著
张笑宇讨论了产业的形成、产业对社会的影响、产业對国家间博弈的影响三个主要问题,并分别用“漏斗- 喇叭”模型、“三流循环理论”和产缘政治来解释他的观点。
如何才能够促进技术进步、通过“三流循环”,并最终产生“产缘政治影响力”呢?需要保持有活力的、繁荣的市场。
繁荣市场从哪里来呢?来自人们的信心和需求,来自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