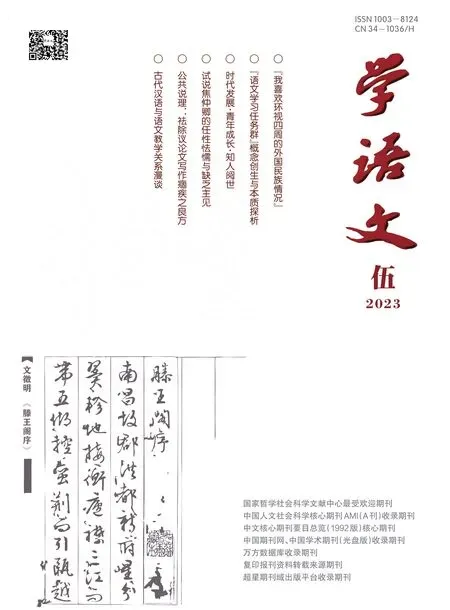“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
——《歌德谈话录》阅读之五
2024-01-09陈文忠
□ 陈文忠
1827 年1 月31 日的谈话,特别显示出歌德的世界眼光。当晚的话题,广泛涉及德国文学与欧洲文学,欧亚文明与中华文明,并提出了“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世界文学的时代来临了”等重要命题。在歌德看来,当时的德国人过着一种基本上是“孤陋寡闻”的生活,而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各民族之间的文明互鉴和文化互鉴。因此,歌德对爱克曼说:“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1]108歌德“环视四周”的宏阔文化视野,以德国为中心,不断向整个欧洲、整个世界扩展。
一、“孤陋寡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歌德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除了自身特具的自强不息的“浮士德精神”,还有两大现实动因:德国人的“孤陋寡闻”和德国文学的“可怜落后”。
首先是德国人“孤陋寡闻”的生活状态。十七世纪“太阳王”时代的法国巴黎,是欧洲最辉煌的文化中心;当时邦国林立、文化落后的德国,则被视为北方荒原上的“野蛮人”。法德两国文化的反差,直至歌德时代仍没有根本改观。斯达尔夫人在《德意志论》一书中,对比了德法两国人不同的生活习性:“在法国,阅读一部作品大抵是为了议论它;在德国,大家几乎是孤独地生活着,因而要求作品本身给读者作伴……孤寂的人由于缺乏外部运动,便需要内心的激情来代表这种运动。”[2]2-3德国人孤独隐居、互相隔绝的生活,必然造成全民性的“孤陋寡闻”。
1827年5月3日,歌德赞叹法国青年评论家安培尔的高明见解,再次感到德国人的“孤陋寡闻”。1826年,歌德戏剧集的法文译本在巴黎出版。安培尔随即在巴黎《地球》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高明的书评”。歌德对这篇书评非常赞赏,并对这位未曾谋面而堪称知音的评论家产生了浓厚兴趣,试图弄清他的个性。他和爱克曼一致认为:“安培尔先生一定是个中年人,才能对生活与诗的互相影响懂得那样清楚。”正巧,安培尔来到魏玛拜访歌德。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活泼快乐的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
爱克曼认为,这可能是感性审美不同于理性判断。歌德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源是文化积淀和文化视野:“我们全都过着一种基本上是孤陋寡闻的生活!我们很少接触真正的民族文化,一些有才能、有头脑的人物都分散在德国各地,东一批,西一批,彼此相距好几百里,所以个人间的交往以及思想上的交流都很少有。”然而,像安培尔这样的法国青年则不同,他们生活在作为“世界首都”的巴黎:“一个大国的优秀人物都聚会在那里,每天互相来往,互相斗争,互相竞赛,互相学习和促进。那里全世界各国最好的作品,无论是关于自然还是关于艺术的,每天都摆出来供人阅览。还试想一想在这样一个世界首都里,每走过一座桥或一个广场,就令人回想起过去的伟大事件。”通过一番对比,歌德说:“这样想一想,你就会懂得,一个像安培尔这样有头脑的人生长在这样丰富的环境中,何以在二十四岁就能有这样的成就。”
其次,德国人的“孤陋寡闻”,导致了德国文化和文学的“可怜落后”。当天,在与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比较后,歌德感叹地说:“我们这些德国人和他们比起来,显出怎样一副可怜相!”德国文学的可怜,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质量上。
首先是有影响的作品数量少。德国文学史可以从12世纪前后写起,到18世纪末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虽历时一千年,真正有影响的作品则屈指可数。1825年5月1日,歌德谈论希腊悲剧衰亡原因时曾说:“如果当时的情况就像我们可怜的德国现在这样,莱辛写过两三种,我写过三四种,席勒写过五六种过得去的剧本,那么,当时希腊也很可能出现第四个、第五个乃至第六个悲剧家。”希腊悲剧的衰亡是一个复杂问题,此处不论。歌德关于“可怜的德国文学”的描述,虽不全面,确是实情。
其次是作品内容的文化成熟度低。歌德以“席勒写过五六种过得去的剧本”为例评价道:“席勒写出了《强盗》《阴谋与爱情》和《费厄斯柯》那几部剧本时,年纪固然还很轻,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三部剧本只能显出作者的非凡才能,还不大能显出作者文化教养的高度成熟。”具有非凡才能的席勒作品尚且如此,其余则可见一斑了。
那么,德国文学好作品数量少、质量低的原因何在?歌德指出:“这不能归咎于席勒个人,而是要归咎于德国文化情况以及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在孤陋生活中开辟道路的巨大困难。”德国人的“孤陋寡闻”和德国文学的“可怜落后”,是互为因果的。
二、环视欧洲各国民族情况
歌德的每一篇谈话,都离不开环视欧洲各国的民族情况,离不开欧洲各国之间的文学比较和文化比较。一部“歌德谈话录”,不妨是一部“欧洲文学谈话录”,也是一部“欧洲文化谈话录”。
从环视的范围看,歌德以德国中部的魏玛为基点,目光遍及整个欧洲。从南欧的希腊、意大利、塞尔维亚,到中欧的瑞士、奥地利;从西欧的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到东欧的斯洛伐克、匈牙利、俄罗斯以及北欧的瑞士、芬兰等等。歌德对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风土人情、文学艺术都有深入观察和丰富学识,并成为诗歌创作的题材。如著名的“悲歌”《罗马悲歌》,警句诗《威尼斯,1790》以及《宴歌集》中的《西西里民歌》《瑞士民歌》《芬兰人之歌》《吉卜赛人之歌》等等。
塞尔维亚的历史文化和民间文学,歌德做过专门研究,发表了《塞尔维亚的歌》这篇名文。对法国和英国这两个近邻的文学风格,则有精细观察和精辟见解。1824年4月14日,在比较德、法、英三国的文学风格时,歌德指出:“哲学思辨对德国人是有害的,这使他们的风格流于晦涩,不易了解,艰深惹人厌倦”;相反,“英国人照例写得很好,他们是天生的演说家和讲究实用的人,眼睛总是朝着现实的”;同样,“法国人在风格上显出法国人的一般性格。他们生性好社交,所以一向把听众牢记在心里。他们力求明白清楚,以便说服读者;力求饶有风趣,以便取悦读者。”德、英、法三国文学和文化的比较,成为“谈话录”的重要论题,不断提及,不断深化。
从1786年9月3日至1788年6月18日歌德的意大利之行,更是其一生中“环视四周”的重大事件。歌德谈及此行目的时写道:“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按我的方式去享受。我要努力学习伟大的文物,在我届满四十岁之前,学习和发展自己”;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又表示:“我将变成一个新人回来。”[3]5-6歌德做到了!在意大利期间,歌德不仅完成了多部重要作品的创作,而且改变了自己的艺术观,由狂飙突进运动的主将,变为古希腊罗马古典艺术的崇拜者;不仅学习了绘画艺术,而且还钻研自然科学,包括气象学、地质学、矿物学和生物学等等。经过这一次“环视四周”的旅程,歌德变成一个知识更为丰富,学养更为深厚,视野更为开阔的“新人”!
从环视的重点看,法国、英国和古希腊是最重要的对象。歌德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崇拜是无以伦比的,这表现在“首先要学习古希腊人,永远学习古希腊人”的态度上,并由此开创了德国文学史上以歌德为代表的“古典文学”时代。[4]5歌德有句名言:“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所谓“古典的”,就是指古希腊的文学作品。1827 年1 月31 日,歌德明确表示:“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后一句道出了以古希腊人为“模范”的原因。
歌德对英法两国的关注各有侧重。法国是德国的紧邻,歌德对法国文学,可谓如数家珍。从古典主义时期的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和布瓦洛,到启蒙运动的勒萨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达朗贝尔、博马舍;从浪漫主义的夏多布里昂、斯达尔夫人、雨果,到现实主义的贝朗瑞、司汤达、梅里美、巴尔扎克以及批评家圣伯夫等等;17世纪到19世纪法国重要作家都进入歌德视野,并做了精辟论述,稍作条贯,可构成一部歌德眼中的“法国文学史”。
歌德谈论的英国作家少于法国。伟大的诗坛巨人莎士比亚和被歌德写进《浮士德》的“文坛泰斗”拜伦,是歌德反复谈论的对象。此外,还谈到弥尔顿、斯泰恩、哥尔德斯密斯、菲尔丁、理查森、彭斯、穆尔、司各特、卡莱尔等等。但是,歌德对英国文学的评价却远高于法国文学。首先,他把英国文学称为“最卓越的文学”,并指示爱克曼“应该在像英国文学那样卓越的文学中抓住一个牢固的据点”。其次,他认为英国文学是德国文学的重要来源:“我们德国文学大部分就是从英国文学来的!我们从哪里得到了我们的小说和悲剧,还不是从哥尔德斯密斯、菲尔丁和莎士比亚那些英国作家得来的?”(1824年12月3日)为此,歌德“对英国人民极感兴趣”,曾对英国的H先生表示:“五十年来我一直在忙着学习英国语文和文学。”其实,歌德对英法两国文学的不同评价,是同他的文学观以及“植根本土”和“符合性格”的原则密切相关的。
三、“设拉子夜莺”·印度文学·中国文学
1815 年,歌德在《西东合集》“序诗”性的《赫吉拉》开篇写道:“北方、西方和南方分崩离析/宝座破碎,王国战栗/逃走吧,逃向纯净的东方/去呼吸宗法社会的清新空气。”[5]588对于欧洲人来说,“东方”是一个广袤而神秘的区域,包括阿拉伯和波斯,印度和中国等等。中亚的波斯文明、南亚的印度文明和东亚的中华文明,正是歌德关注的三个重心。
先看歌德与波斯诗人哈菲兹的精神交往。1828年3月11日,歌德回忆了自己创作《西东胡床集》的情境。他说:“十年或十二年以前,在解放战争后那些快乐的日子里,我全副精神都贯注在《西东胡床集》那些诗上,有足够的创造力每天写出两三首来,不管在露天、在马车上还是在小旅店里都是一样。”《西东胡床集》又译为《西东合集》,可解释为“西方诗人写的东方诗集”,这是歌德一生中最辉煌的诗集。《西东合集》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歌。这部诗集堪称欧洲文明与波斯文明互相融合的艺术结晶。
哈菲兹(1320—1389)是14 世纪波斯抒情诗人,一生共留下五百多首诗。诗人幼年丧父,全家移居伊朗西南部法尔斯省的省会设拉子,故被誉为“设拉子夜莺”。他的波斯文《哈菲兹诗集》于1791 年第一次正式出版,旋即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传遍世界。黑格尔在《美学》中引用过哈菲兹的警句诗:“世界的行程是一把血染的刀,滴下的每点血都是皇冠”等等。
歌德是1814 年6 月读到哈菲兹诗集的德文译本的。他立即被哈菲兹的诗所吸引,从中发现了自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歌德盛赞哈菲兹:“你是一艘张满风帆劈波斩浪的大船,而我则不过是在海涛中上下颠簸的小舟。”哈菲兹的诗境为歌德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歌德的诗兴和灵感重新被激发。1815 年和1816 年,歌德写下了大量诗作,最后辑成一个集子,于1829 年出版,这就是著名的《西东合集》。
《西东合集》共十二篇,即《歌手篇》《哈菲兹篇》《爱情篇》《观察篇》《怨恨篇》《格言篇》《帖木儿篇》《苏来卡篇》《酒保篇》《警喻篇》《巴斯人篇》《乐园篇》。每一篇自成一体,都有它的中心和主题;十二篇又是一完美的整体,一个“令人惊讶的整体”。歌德在诗中出现,时而是读者,时而是诗人,时而是东方商人,时而是基督徒,时而是穆斯林,时而是古希腊的崇拜者。哈菲兹也在诗中出现,时而是个歌唱者,时而又成为被歌唱者。同时,歌德化身为哈菲兹,哈菲兹化身为歌德。西方与东方,德国与波斯,歌德与哈菲兹,来回变动,实为一体,体现了歌德东西方文化是“孪生兄弟”的观念。《西东合集》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义,德国诗人海涅有精彩的论述。[6]58-59《西东合集》既是西方诗人向东方发出的问候,也是纯净的东方向西方吹去的清新空气。
再看歌德对印度文明的关注。1824年2月24日午后,爱克曼去看歌德,他发现歌德为他所写的《印度的贱民》的评论文章做了一个附录。经过歌德的处理,这个题目给人以更完整的印象。歌德对爱克曼说:“你趁着写那篇评论的机会研究了一番印度的情况,你做得很对,因为我们对于自己学习过的东西,归根到底,只有能在实践中运用得上的那一部分才记得住。”这件事充分透露出歌德对印度社会和印度文化的丰富知识。
其实,歌德对印度文学同样极感兴趣,高度重视。他阅读过不少翻译作品,形成了独到的印度文学观。1818 年前后,他在《印度文学以及中国文学》一文的开篇写道:“如果我们不同时也想到印度文学,那我们就真是不可思议。印度文学所以令人赞叹,是因为它一方面不同于最深奥的哲学,另一方面又不同于最奇特的宗教;通过与这二者的斗争,它获得最卓越的本色;它也从这二者之中吸收营养,但以使自己能具有内在的深度和外在的尊严为限。”[7]255换言之,印度文学是“最深奥的哲学”与“最奇特的宗教”互相斗争、对立统一的结果。这是一个深刻的见解,揭示了印度文学独特的文化本质。黑格尔在《美学》中也有相似的论述。[8]84但黑格尔用哲学语言表达的观点,远不如歌德的明朗清晰而富于启示。
在这篇文章中,歌德对《沙恭达罗》《牧童歌》和《云使》等印度经典作品做了要言不烦的分析,显示出歌德超凡的审美感悟力和艺术分析力。他对《沙恭达罗》的论述最为精彩。歌德说:“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沙恭达罗》,几十年来我们为它倾倒。女性的纯洁、无辜地顺从、男子的健忘、母亲的隔离、父母由于儿子而和解以及最自然的状态,这一切在这部作品中都通过诗化而得到升华,升腾成就像云彩在天地之间飘浮那样的奇观,由诸种神和神之子演出了一场极为平常的自然大观。”[7]255情节的叙述极为简洁,风格的描述则富于诗意。
歌德对印度文学的关注,虽然没有碰撞出《西东合集》那样的杰作,但在无意中激发了他的灵感,滋润着他的诗笔。歌德《叙事歌集》中的《神与舞女》、《抒情篇》中的《贱民》等,就来源于印度文化和印度社会生活。《神与舞女》最为动人。歌德在诗中描写了一个妙龄舞女与天神摩诃天的爱情悲剧。舞女虽与天神“只做了一夜夫妻”,却愿意承担忠贞的妻子的义务,随亡夫殉葬,以冀一同升天。诗的结尾写道:“爱人投入他怀抱里面/跟他一同飘飘上升/忏悔的罪人使天神欣慰/不朽的圣神伸出了火臂/把沦落的人带上了天庭。”黑格尔在《美学》中把《神与舞女》称为“宣教故事”[8]114-115。实际上这首“基督教故事采取了印度打扮”的爱情诗,蕴藏着歌德本人对他妻子克里斯蒂阿涅的忠贞之爱的感激之情。因此,与其说是“基督教故事采取了印度打扮”,不如说是“歌德故事采取了印度打扮”。
再看歌德对中国文学和中华文化的认识与评价。1827年1月31日的谈话就是从中国传奇与中华文化谈起的。爱克曼听说“中国传奇”,便以为“一定显得很奇怪”。歌德解释道:“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歌德的这段话,令人想起之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中关于中国“道德文明”的描述。[9]5歌德是否读过《中国近事》无从查考,但他认为,在中国“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的看法,与莱布尼兹是一致的。
16至18世纪,欧洲大地刮起了一股中国风。其间,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情况的游记和报道,并翻译印行了不少中国的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歌德读过的游记和报道有《马可·波罗游记》《中国详志》等;读过的哲学著作有《孔子哲学》《中国六经》;读过的文学作品涉及戏剧、小说和诗歌三大文体。其中,戏剧有《赵氏孤儿》和《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等;小说有《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以及译自《今古奇观》中的短篇;诗歌有《诗经》和《百美新咏》中诗作,等等。[10]67-69
歌德还翻译过几首唐诗,其中一首是唐明皇梅妃的诗。梅妃是唐明皇宠幸的妃子。诗才敏捷,容貌美丽。杨太真进宫后,明皇就把梅妃居于别宫,置之不理。有一天,外国进贡宝珠,明皇忽然想起梅妃,命人把宝珠赠她,她却把宝珠退还,作一首诗寄明皇。诗曰:“柳叶蛾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诗意哀婉,深藏怨情。陈铨评歌德这首译诗:“歌德把凡是不亲切的字眼,淘汰罄尽,完全用德文里最纯熟的词句。他不描写任何的装饰,只形容梅妃精神上的状态。”[11]96这样一来,这首诗就由中国的变成德国的了。歌德通过翻译读中国诗,要比一般读者理解得更深入。
儒家经典和文学作品的阅读,对歌德产生双重影响。一是不断获得并深化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认识。歌德不仅认为“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并进而指出,中国人“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历史将证明,歌德的洞察是深刻的,论断是正确的。二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歌德的文学创作,其中被认定的有两种,即悲剧《哀兰伯诺》和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哀兰伯诺》的剧情明显受到《赵氏孤儿》的影响。主人公哀兰伯诺婴儿时,父亲被妄图篡权的李库斯暗害,自己后来却被杀父仇人错当作亲生子抚养成人。从哀兰伯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立下的誓言看,剧情若继续下去,他极有可能会像赵氏孤儿一样报杀父之仇。但《哀兰伯诺》只写成了两幕,歌德晚年为之感到遗憾。
《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由十四首抒情诗组成。组诗作于1827 年5 月,是歌德阅读《花笺记》《玉娇梨》以及《百美新咏图传》后写成的。从组诗题目和诗的内容看,歌德把阅读中国作品的感受,与自己当时的见闻思绪揉合在一起,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创作出了中国因素和德国因素融为一炉的抒情杰作。组诗第八首“中德”因素的糅合最为明显。诗曰:“暮色徐徐下沉,景物俱已远遁。长庚最早升起,光辉柔美晶莹。万象摇曳无定,夜雾冉冉上升。一池静谧湖水,映出深沉黑影。/此时在那东方,该有朗朗月光。秀发也似柳丝,嬉戏在清溪上。柳荫随风摆动,月影轻盈跳荡。透过人的眼帘,凉意沁入心田。”诗的上半阕写的是眼前实景,下半阙“此时在那东方”以下,便是歌德想象中的中国月夜景象。组诗的中国因素,鲜明地体现在艺术风格上,格调恬淡、明朗、清新,没有飞腾动荡的诗兴,抒情含蓄、委婉、蕴藉,没有强烈的情欲。
在环视东方的诸外国民族中,歌德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关注,远超波斯和印度,因而被尊为“魏玛的孔夫子”[10]48。
四、“植根本土”与“符合性格”
就是在1827 年1 月31 日这个晚上,歌德在畅论中国传奇和中国道德后,重申了“诗是人类的公共财产”,进而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歌德说:“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如果说歌德的“世界眼光”表现为“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那么“世界文学”的概念正是其环视欧洲和亚洲、西方和东方后的思想结晶。
“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首先,它充分证明歌德是当时最具世界眼光的西方哲人之一。歌德的概念比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这个概念早了20 年。二者的区别在于,歌德从普遍人性出发,马恩则是从经济和世界市场观点出发;然而,人和物,一体两面,不可分割。其次,它指出了人类文学发展的光明前景和终极目标。歌德坚信:世界文学的形成有助于在各民族之间“实现真正的普遍容忍”,因此“只有属于全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10]164。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文学的概念寄托了歌德关于人类未来发展的理想,表现了歌德胸怀天下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成为老年歌德的精神归宿。
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具有双重目的:既为了促进各个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也有助于各个民族自身的进步发展。[7]380如何在促进各民族之间互相了解的同时,又有助于各民族自身的进步发展?歌德提出了两条原则,即“植根本土”与“符合性格”。
首先,文化互鉴和文学互鉴必须“植根本土”。1824年2月4日,谈到当时一些德国人企图人为地把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场景搬到德国来,歌德为此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植根于本土、出自本国一般需要、而不是猴子式摹仿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对于某一国人民处在某一时代是有益的营养,对于另一国人民也许就是一种毒药。”这是处理民族之间的文化互鉴和文学互鉴的至理名言。
二百年来的世界史证明,无论政治制度、文化观念、文艺创作,凡是“猴子式摹仿外国”的做法,无不成为祸害本国的“毒药”;只有“植根本土、出自本国需要”的借鉴,才有助于促进本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文学的发展。首先,从发展规律看,脱离本土,脱离国情,简单照搬,机械模仿,必然会造成“水土不服”的现象;既不可能植根本土,还会打乱出于民族传统和本国需要的发展进程。其次,经典的民族作家的标志,就在于他能深刻把握民族思想和民族感情。歌德指出,所谓经典的民族作家,就是“他不放过他同胞的思想中的伟大之处,不放过他们感情中的深沉,不放过他们行为中的坚定不移和始终如一,他自己充满民族精神,并且由于内在的禀赋感到有能力既对过去也对现在产生共鸣”[7]12。再次,从文化影响看,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别林斯基曾以歌德为例说过一段名言:“歌德的创作无论如何繁复和包罗万象,他的每篇作品都洋溢着德国的、再加上歌德的精神……越是有天才的诗人,他的作品越是普遍,而越是普遍的作品就越是民族性的、独创的。”[12]77最后,还在于鉴赏趣味的民族性。周恩来说:“艺术还是要立足于国内,在我们民族的基础上发展。不然,人民通不过。”[13]177这是一句大白话,而真理就是大白话。艺术要立足国内,富于民族的审美趣味,人民才能通过。
其次,学习他人,接受影响,必须符合自己的性格。1825 年5 月12 日,歌德明确指出:“关键在于我们向他学习的作家须符合我们自己的性格。例如卡尔德隆尽管伟大,尽管我也很佩服他,对我却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相反,“我每年都要读几部莫里哀的作品,正如我经常要翻阅版刻的意大利画师的作品一样”。
如果说“植根本土”是就自身需要而言,那么“符合性格”则是就学习对象说的。歌德强调学习的对象必须“符合我们自己的性格”,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对象的社会性质与自己相符合。这就是普列汉诺夫说的:“一个国家底文学对于另一个国家底文学影响是和这两个国家底社会关系底类似成正比例的。当这种类似等于零的时候,影响就完全不存在。”[14]286二是对象的思想观念与自己相符合。歌德一生强调自然、强调现实,强调客观。他说:“自然从来不开玩笑,她总是严肃的、认真的,她总是正确的;而缺点和错误总是属于人的。”(1829年2月13日)歌德对英国作家比法国作家更感兴趣,就是因为英国作家“讲究实用,眼睛总是朝着现实”;这符合歌德的性格,也符合歌德强调客观自然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三是对象的个性情趣与自己相符合。歌德对卡尔德隆与莫里哀的不同态度就是如此。老年歌德“逃亡东方”,同样是“纯洁的东方”符合老年歌德的心境。宗白华认为:“歌德老年时且由西方文明逃亡东方,借中国印度波斯的幻美热情以重振他的少年心。”[15]5这不无道理。
此外,歌德还强调,对于“符合自己性格”的对象,既要学习其长处,又要摆脱其束缚,对于莎士比亚这样伟大的典范,同样如此。1825 年12 月25 日,歌德无比感慨地说:“他太丰富了,太雄壮了。一个创作家每年只应读一种莎士比亚的剧本,否则他的创作才能就会被莎士比亚压垮。我通过写《葛兹·封·伯利欣根》和《哀格蒙特》来摆脱莎士比亚,我做得对;拜伦不过分崇敬莎士比亚而走他自己的道路,他也做得很对。”既要学习莎士比亚,又要摆脱莎士比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走自己的路,这是何等的气魄!
早在1808年歌德就强调:“外来的财富必须变成我们自己的财产。要用纯粹是自己的东西,来吸取已经被掌握的东西。”[7]264歌德最终成为“最伟大的德国诗人”,成为“最大的欧洲天才典范”,除了天才与勤奋,同“外来的财富必须变成我们自己的财产”的创造性转化的观念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