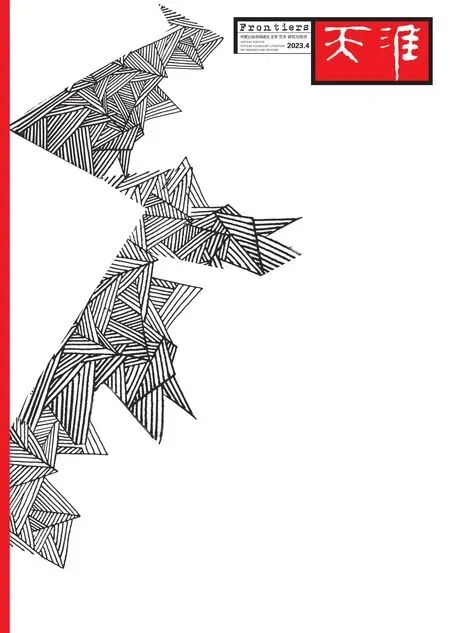风人
2024-01-08浦歌
浦歌
我的奶奶,在她死后才开始了真正的生活。她还活跃在我们周围时,她的一双裹足小脚就像要消失了的两个顿点一样,在真实与虚无的边界进行着交锋和磨砺。她若有若无地存在于我们家庭,有时候,刚开始漫长的夜间闲聊,她就躺在家里唯一一把旧太师椅上,半张着嘴靠在椅背上睡着了。而我们也早就忽略了她的存在,她就像我们家庭可有可无的填充物,我们很难不忽略她。她织布的时候,我们只听见梭子在丝线中沙沙的穿梭声,听见嘎嘎的夹板声,而她一声不吭,就像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动作中消失了一样。她无声无息地移动着小脚,将物什放回到原来的位置,让锅里的饭煮沸。有些晚上,家里没有亮灯,一片漆黑,等爷爷摸索到炕头时,奶奶仍与黑夜混在一起,就像她并不存在一样。直到死去的那一刻,奶奶才第一次真正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感觉到,一阵风从她嘴里绵绵不绝地出来了,此后这风在我们家族里盘旋,拂动我们困顿迷惑的意识。
奶奶的葬礼上,风使得头顶的帐篷啪啪作响,我们全都知道那是奶奶。风将老柳的胡子吹得偏向一边,将翠花的筷子吹掉地上,将我爷爷脸上的两行老泪吹落到衣衫上,那也是奶奶。画在黑色棺材上面的弯弯曲曲的金色瓜蔓,也被隐秘的风吹得四处伸展,它们扭曲着身子努力攀附在棺材边缘,伸出它们惊慌的头部。
也许受风的诱导,大伯的头发不再下垂,开始乱蓬蓬地向上生长,叔叔走路越来越一翘一翘的。只有爷爷精神萎靡,被糖尿病摆布,每天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他走路不稳的时候,常常伸开手掌,在空中扶一下,就像那里有一个扶手一样。神婆大妈在檀香缭绕的烟雾中,也隐隐看到奶奶无拘无束的踪影。父亲长出翅膀那天,我们终于可以确认,这也是风的诱惑。
由于病痛折磨,父亲已经很少到田地里。他只是有些羞愧地用衣服挡住了那双刚刚显露的翅膀,它们就像一对对称的白色花苞一样。等它们展开时,刚开始还湿漉漉的,干了之后,我们发现了上面羽状的毛。那时候,父亲还非常有耐心,他对着借来的一面镜子,让我拿着我家脏兮兮的双喜圆镜,他要看到它们。父亲瞪着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好久。那时,难以觉察的风正轻轻拂动上面的羽毛。那也许是奶奶也在好奇地摩挲它们。
我也处处都能感觉到奶奶,她仍然无法离开我们。有时候,她从远处袭来,将我们晾晒的有破洞的旧衣裤灌满,它们在空中鼓鼓地摆动腿脚,就像奶奶上炕时正在脱掉鞋子一样,这让我似乎重新看到她那肥胖沉重的身子。晚上下地回来,在屋后的巷子里,她常常触摸我的后脖颈,我回过身来,会发现身后高处的一枝槐树枝在轻轻晃悠,那是她溜走的影踪。她甚至在我母亲的柴火里出入,挑逗那里的火苗,发出噗噗的声音。不过,夏季到来的时候,我感觉她会离我们越来越远。那年天气最为酷热,太阳像炉火炙烤红薯那样,熏蒸着我们的小村庄,田地上空的空气像僵住了似的,长时间一动不动,只要你敢动一动,它就会像砂纸一样摩擦我们的脸面和脖子。太阳将我们脚下的黄土地面炙出一块块发灰发黑的焦土,散发出使我们神智不清的土腥焦味。
正是那一年,父亲种了十几亩棉花地,它们一块块散布在土岭高高低低的梯田上。酷热让病痛中的父亲焦躁不安,他站在棉花地里,棉花叶面被晒得微微翻卷,然而它们依然在暗中乱长贼芽和贼枝,那会使得棉花真正的枝桠长不出棉铃。父亲预感到他即将病倒,不停地催促我们掐贼枝。他喝骂我和弟弟,因为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抬起身子,伸展一下腿和腰。弟弟还常常掐掉了好芽,留下贼芽。在我们眼前,是一株株相仿的棉花株苗,都有一根棕绿色的主杆挺立在土里,都有相似的一蓬蓬叶子和枝桠长在上面。我们低下身子看过去,棉花地长得看不到尽头,在一片发蔫的绿色之外,横亘着裸露而焦黄、像是流动着火气的高岭尖顶。这很容易使我变得恍惚,失去时间概念,汗珠一直在脖子上慢慢滚动,然后滴到土里,如此周而复始。我偶尔抬起头,感觉自己就像被打晕了似的,昏昏沉沉的。
或许由于疲劳,我经常会在一瞬间陷进黑沉沉的睡梦中。很快,一个隐匿的世界像热闹的蜂窝一样,嗡嗡嘤嘤向我迎面袭来,向我展示更多的空间和肌理。有时,那是一个毛茸茸的世界,等我行走的时候,轻盈的毛摩擦着我疲惫的身体。有时,那像是一个静态的世界,眼前只有一个鸡蛋花苞,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我看到鸡蛋花正在缓缓开放。有时,我梦见自己从梯田台阶上往下跳,腾空落在松软的土地上面。我能感觉到奶奶的存在:等轻盈的毛在拂动、鸡蛋花在梦里轻轻摇动,凉爽的风在空中掠过我的肋骨,使衣襟不停摆动时,我知道那是奶奶在陪伴我。我甚至嗅到奶奶身上干煮饼一样的味道,看到她的黑色衣服,她头上的发髻,她小心翼翼走路的姿态,她的八字小脚。好像我的意识正在雕塑奶奶的形象,她越来越鲜明:她的圆脸,她眯缝着笑着的小眼睛,她的小心眼,她过分胆小的性格,甚至她无限投射的内心。有一次,我半夜从炕上起来,开始梦游。我走到院子里,出了院门,进了屋后的巷子,走到爷爷家,睡到奶奶的被窝里。等我醒来的时候,爷爷那像浓痰一样浑浊的眼睛,正怜悯地看着我。爷爷家里散发着鳏居者的特有气息,锅碗像是陈列品一样,氛围显得寡淡冷清。失去了身体肥胖的奶奶的陪伴,爷爷显得过分瘦弱、单薄和孤单,无依无靠。他常常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裤裆里散发着尿骚味,喉咙里发出孩子一样轻微的哼哼声。那时候,奶奶可能从我身边的任何地方浮现出来,地面的尘土痕迹上,雪连纸上,被烟尘熏黑的墙壁上,香椿树干的老皮上,甚至在空无一物的空气中,都有她呼之欲出的无形身影,那或许就是风制造的隐秘幻影。
神婆大妈正在寻觅奶奶的行踪,她说,奶奶滞留不去给家族带来了不祥。大伯在给大队烧窑的时候,砸伤了腿,现在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叔叔家的西红柿菜地被病虫害侵袭,一个个青色西红柿像临终病人似的,在皱缩的叶子下长出了霉点。我的父亲病情加重,还长出了难以示人的翅膀。因为糖尿病,我爷爷的脚趾发黑腐烂,走路疼痛。大妈也常常感到心慌意乱,呼吸困难。这都是奶奶造成的。
大妈家的神龛上方,挂着巨大的玉皇大帝像,他过分白皙的下巴上是一绺棕色的胡须,一轮太阳像焦黄大饼一样在他的脑后浮现。他端坐着,脚底下是一团团白色祥云。大妈点燃香烛后,青色烟雾缭绕在玉皇大帝身上,在上面留下灰尘和污垢,团团白云上满是絮状的陈年粉尘。干瘦的大妈开始对着神龛祈求,她用泼辣的言语指使另一个世界,那里熙熙攘攘挤着各路神仙。随着大妈念起咒语,那个无形世界刮起一阵旋风,玉皇大帝以一种宽容敦厚的态度观看着大妈作法。那时,初升的缕缕阳光,在院子里的枣树上留下金箔般的光斑,光斑像媚眼一样闪着光,传播着隐秘的信息。接近中午的时候,大地再次沉浸在酷热之中,大妈家像炼丹熔炉一样,令人难以呼吸,神仙世界也蒸腾出汗水特有的酸臭味,为暑热增添了古怪的味道。这对奶奶无疑是当头一棒,遏制了奶奶恣意的冲动。
那些天,我们每天都在棉花地里,被太阳的毒液浸蚀,世界在我们周围无法补救地剥落了釉彩。我和弟弟似乎看到一个虚假的父亲,他像是在田地里干活,又像并不存在一样,他有一副病恹恹的、令人产生幻觉的神态。他的虚弱已经到了让人费解的程度。在酷热和汗水里,家族的生活像是在原地打转,无法前行。大伯冒着暑热,瘸着腿,还要为砖窑的炉火加炭,烟火熏蒸着大伯的瘦脸,他枯瘦的身体在火焰的热光里飘忽不定,像是正在被锤炼成一件薄薄的小小的器皿。谁也没有留意孤单的爷爷,更多的时候,他像虾一样弓着背,躺在炕上,他刻意留在迟钝乏味的物质世界里,通过停滞和无知无觉,钝化心中过分敏锐、刺痛的感觉。他通过近于固体的意识接近了奶奶,以至于他有一种神志枯竭之感。那是一个像砖石、木头一样稳固的世界,意识会在那里被牢固地、平静地凝固。爷爷风起云涌的过往,也蕴含在其中:他在战场上落荒而逃的形象,像木雕一样僵立在无数形象之中,那两颗即将穿过他的小腿、脚部的子弹,像是被麻醉了一样,停驻在他的皮肤表面。爷爷无知无觉地攀附在这庞大的世界里,在曾经经受过的无数次考验里,寻求到不会过时的安慰。
奶奶去世的时候,爷爷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之后,他的眼睛变得通红浑浊。他看着四周的样子,就像在默默流泪。等爷爷不得不走出屋子的时候,他用发馊的脏手帕擦擦额头上的汗。随身携带手帕是爷爷当国民党军官时,养成的唯一一个“奢侈”的习惯。尽管走路不稳,他也会努力挺直腰板,在颤颤巍巍中,展示出某种摆脱农民身份的优雅。那是一个像废纸一样干巴巴的日子,丝毫没有奶奶的影踪。他讶异地看着天气的变化,太阳光毒辣地射向小小的院子,形成一片炽热耀眼的虚光,几乎要变成流体的光线,将黑暗威逼到了室内。爷爷出现在屋外,眯起眼睛,被刺眼滚烫的洪流包裹。爷爷茫然地看向门外,巷子空荡荡的,门口边奶奶常坐的大青石被暴晒得发烫,露出镜子一样闪光的釉面。整个村庄几乎没有阴影,像烤焦的起面饼一样在太阳下面摊开。爷爷伸出手,发现空中没有一丝风。
家族像蒺藜一样长满了芒刺,攀附在混乱的枝叶上,被恶毒的太阳晒得越来越坚硬干巴。我们像是被大妈引到了邪路,沿着一条更加盲目的道路前进。一天中午,在棉花地,我居然在烈火般的太阳下面,恍恍惚惚进入了梦游状态,沿着梯田外面细细的陡峭小路要往回走。弟弟说,我在路边崖畔的草丛里被父亲一把抓了回来。那一刻,我深陷梦境的身体,像刚刚从冰窟里捞出来一样充满寒意。一股热浪袭来,热风吹暖了我的身体,直到浑身酥痒,像是要伸展出许多枝叶,我才终于完全清醒,感觉重新回到了人间。
爷爷为我请来一名老中医,他将皱巴巴的手放在我的手腕上,勘探我身体内部的阴与阳,以及气血的运行。在他的紧紧靠在一起的三根手指下,我感到血管一突一突地震动,就像奶奶作为胎儿在那里萌动,片刻之后,我第一次真实感觉到了奶奶的存在,她像刚出生的鸟儿一样,虽然看不见但轻轻跃动着,栖息在我的呼吸里。一种陌生的沉痛感遍布我的身体,让我倦怠和无力。被大妈追着的狼狈逃窜的奶奶,或许正在我的身体里建立她隐秘的堡垒,准备东山再起。老中医说,我是阴血不足,肝阳偏亢,神明失灵。我应该滋养阴血,安神定志,柔肝熄风。他慢悠悠在纸上写出了一个单子:生地、白芍、当归、生石决明、珍珠母、朱砂。那些天,父亲正在抽空研究《山西中草药》,这是他的救命法宝,也是他坚实的人生堡垒。他试图在玄妙的药理中,找到力量与大妈无限的魔力对峙,并且自以为得计。送走老中医,他在昏黄的电灯下,翻开厚厚的书,一个一个地找到这些中药的彩页,看它们的性状,推演它们的药性与药理。父亲赤着上身坐在炕上,背上的新生羽毛被看不见的风轻轻拂动,这激发起罕见的平静、优雅、充满知识性的时刻。
奶奶开辟出另一个人生,她像复像一样,附着在别人的身上,我从每一个人那里,都能看到奶奶惯常的动作,比如母亲抓头发的样子,父亲走路前倾的样子。她还出没在别人的嗓音里,使得别人的声音里不得不藏着她无法磨灭的音调。甚至在弟弟幼稚的童音中,她也调皮地出现在尾音里,让我浑身一个激灵,以为她就在身边。从我家院子的土崖上面看过去,河滩边的绿色田地里总有几个弯腰干活的身影,她们完全就是奶奶的翻版,具有一样的动作习惯,使得我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亲近感。隐秘的风掠过河滩上的一块块田地,翻起一片片泛白的明晃晃的叶子背面,那是奶奶正在袒露她的内心世界,清新而又令人焦灼。它又吹拂了路面上的尘土,使它们孤苦无依地久久地荡在空中,最后迷乱而轻率地散入庄稼地里。风最后来到我家院子当中的两棵香椿树上,像翻找东西一样伸进枝叶中,叶片发出一阵阵哗啦哗啦的声音。接着,倏然一下,风游进了我的鼻孔,接通了我的身体,使我差点噫气,一个感情丰富、形象丰满的奶奶一下子充盈了整个世界,隐秘的幸福感让我迷醉。我像是进入了奶奶所统治的庞大帝国,在那里体会她不可测度的意志。
那时,大妈像是已经完全深入神魔之界。她家的窗台下乱扔的烂鞋子、几块破砖,都不像是随随便便的物件。在泥里打过滚的脏黑猪,一只眼睛糊着干泥,如同受到某个神灵的役使,正在她家院子里哼哼着走动。墙角下栽种着一排歪歪扭扭的大葱,葱管深绿得发雾,鼓胀胀的,一副伸头探脑的样子,带上了说不来的仙气。她扛着锄头去田地,跟路上不同的人插科打诨,说话轻松放肆。然而,她与父亲过于严酷的风格完全不同,她解构了父亲严肃的生活,几句话就像解开绳索一样,将父亲板结、繁琐的生活玩闹似的解除掉。她慢条斯理地从巷道走过来,从她出现在路的那头开始,被太阳烤得明晃晃的路面像是完全顺从了似的,静悄悄地等着她走过。那正是我们家在崖上吃饭的时间,桌子摆在门口骡圈边的阴凉地里,一脸沉闷的父亲远远就听到了大妈跟邻居的打趣声,他在严酷而绝不苟同的世界里努力维持自己的尊严,然而一种轻佻的氛围立刻如约而至,大妈迈着散漫的步子,离我们的院门越来越近,这进一步动摇了巷子里的肃穆感,也一下子解除了我的警戒,我感觉自己凝重的生活四分五裂,瞬间轻飘飘地浮游起来,在变得轻松欢闹的洪流当中,只有父亲的脸上依然是令人可笑的倔强。父亲眉头紧锁,已经嗅到了浓重的侵犯气息,他像即将愤怒的公牛一样,头在饭桌上方一晃一晃的,长年穿在身上的褴褛的蓝色中山装,像盔甲一样,将他长翅膀的身体裹在里面。
老先生,大妈说,都后晌了才吃午饭哩?
大妈的大眼睛笑意四溢,语气中的调侃像飞扬的沫子一样滋出,完全粉碎了我们家生活的沉重本质。这无疑刺痛了父亲,他却找不到任何可以使用的武器,因为那一刻,大妈充满了让人无法解释的引力,我一下子迷失在大妈的神奇魅力当中。她说话时咯儿咯儿的笑,像两手拉伸绷紧的一弹一弹的皮筋,最终因为突然放松瞬间瘫软一样,这让身边的一切都丧失了理性,进入了无法思考、放任自流的漩涡。大妈的身影在半月牙形、长了酸枣丛的土崖边缓缓走远,像禽类隐没在草丛,慢慢地消失在路的尽头。那一刻,我们都觉得,整个巷子和那条重新变空的小径,依然存留着大妈制造的纷乱笑意,像大公鸡蓬松的羽毛一样,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原状,重归稳重、紧凑的秩序。
大妈像是施了魔法一样,向我展现出无穷无尽的魅力,使我终于明白,我的苦日子都是父亲带来的,生活原本可以轻松、诙谐,可以添加嘲弄的快感,不必深陷严厉的泥潭。然而,这一念头也许正是一切即将结束的开始。第二天,我的后背被太阳晒伤,晚上我只好侧躺着睡觉,我有时能隐隐闻见一阵生肉的腥味,那味道就来自我刚刚开始褪皮的后背。我进入梦乡之后,后背却始终像醒着一样,隐隐作痛。即使有风轻轻在上面吹拂,也只会引起灼烧感,就像被风吹出了火苗一般。在梦中,大妈就是那个治愈我的创伤的人,她慢慢拿起一块沾了凉水的湿布,贴在我的后背。我仔细分辨她喜欢戏谑嘲弄的眼神,从里面寻找她流露的情感,希望她将我当成她自己的儿女。我心中充满了逃离父亲的愿望,只有在大妈所创造的轻快的氛围里,我才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自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只是梦游到了大妈家,我正躺在大妈家的炕上。大妈站在客厅的神龛前,正在上演逮奶奶的好戏。那时,瘦小的大妈已经被法力控制,像注满了气体一样膨胀了起来,她手持一块红布,口中念念有词,那些词语像活物一样,在客厅里掀起一阵阵风波。有时,风在我的鼻孔中急速进出,使我的喉咙时时像打结了似的噎住。奶奶像一首令人痛心的童谣一样被驱赶出我的身体。一阵阵风在大妈家四处出没,把她家油腻脏污的风帘刮得唰唰作响,还将大伯挂在墙头上的发霉的草帽掀起来,在空中旋动着,最后落在了门外的地上。最终,一阵风从窗户那里仓促涌出,不得不走上了狼狈的逃亡之路。
大妈乘胜追击,扬言要在我家重新布置神龛,以便让奶奶无处可逃。两年前,她刚刚将神龛粘上我家黑乎乎的墙壁,就被信奉无神论的父亲取了下来。从那之后,大妈的神力和父亲的人力之间,就有了一场持久的暗中搏斗。父亲的武器就是剑拔弩张,是无上的严厉,怒张的双眼。大妈所运用的是她天然的诙谐和轻佻,以及神符和咒语。第二天一早,大妈就带着她的神仙兵团,直捣我家。父亲当然不能容忍别人摆布他的生活,不过,大妈没有让父亲得逞。大妈还在屋后的巷子里时,我们就听见了她那锥子一样的脚步声,母亲害怕会有一番无法预料的家族内斗,便掩饰着紧张说:
来了!
父亲依然躺在炕上,虽然照旧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然而他扬起脸,就像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一样,露出正义凛然、以静制动的表情。可惜的是,大妈一踏进我们的家门,父亲的意志就像被一种可笑的事物麻痹了,他不停地摸弄头发,头发瞬间变得乱糟糟的。他眯着眼睛,看上去像没有睡醒似的,脸上露出懵懵懂懂的神情。大妈从容不迫地在我家安置神龛的时候,父亲居然没有出来阻止。那时,我们才惊奇地看见,父亲后背那一双巨大的翅膀不知何时已经塞满了屋子,他似乎只是翅膀中间一个小小的躯体,正非常害羞地将头埋在被子里。在大妈点燃香烛、朝着神龛念念有词的时候,父亲被迫忍耐了大妈愚蠢的喃喃声,那声音像是一串无头无尾的咒语。
这是父亲和大妈无数次较量中让他感到最耻辱的一次,父亲的翅膀转弯抵着屋顶和墙壁,难以挪动。大妈走了之后,父亲一下子虚弱下来,甚至无法撑起翅膀,巨大的翅膀像抹布一样软软地翻卷着,拖在炕上。终于,父亲爬了起来,用脚在地上摸索着寻找鞋子,两大卷软塌塌的翅膀从炕上拖下来,挨挨挤挤着聚在门槛上,不少羽毛落在地上。父亲好不容易走到院子里,似乎在期待着什么。我们也跟在后面,也期待着发生什么奇迹。然而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风拂动羽毛。是啊,我们相信,父亲的巨翅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奶奶似乎为父亲提供了一条非人间的道路,只是奶奶已经狼狈逃窜,无法兴风作浪。父亲把身后拖拖拉拉的翅膀抖了抖,翅膀就像拖在地上的旧门帘一样,只撩起一点尘土来。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狼狈、卑微而又荒唐的生活。之后,病重的父亲顺势选择了从生活中逃离,在母亲的陪伴下,父亲神情恍惚地住进了几十里之外的县立医院。
奶奶的风或许真的可以鼓起父亲的那双翅膀,然而父亲命定无法到达这一冥冥中盲目开启的目的。父亲住院之后,我和弟弟跟爷爷一起生活,第二天,爷爷只好带我们去梯田上的棉花田地继续干活。爷爷用嘲讽的语气说:
咱们替你爹去受罪!
那是奶奶最后一次出现在我们周围,她催生了我们心中最后的一个萌芽,只是这萌芽像贼芽一样无法结出果实。形销骨立的爷爷蹲在棉花地里,看着望不到头的田地,露出一副茫然若失的表情。田地里,我们还能到处看到父亲以前那种虚弱的幻影,他依然隐隐让我和弟弟感到畏惧。临近中午的时候,疯癫的太阳暴晒出土壤里硫磺的气味,一动不动的空气,就像马上要点燃一样,看不见的火苗正舔舐我们的脖子和脸。在战场上,无数次经历溃败和逃亡的爷爷,早已经掌握了失败的技术,他痛苦地哼哼起来,用听天由命的态度望着棉花地,不知道在向谁抱怨:
累死了啊!
他的腰已经弯了下去,不时地用手掌撑着地往前走,他将手放在枝桠下面,每次机械地掐掉一个贼芽和贼枝,他就要顺势叹一口气。
爷爷也许看透了,所以他不像父亲那样使用蛮力,而是自嘲和微微的讥讽。他粗糙干枯的手指,伸向棉花株苗的枝叶连接处,就像在触摸世界一个隐秘的机关。他不是要掐掉什么,而是在施魔法麻痹它们的意识。他以哭爹喊娘的方式,慢慢将世界凝固在他的意识里。
一点风都没有啊!热死了啊!爷爷叫喊。
奶奶就是那时出现的。她四处逃逸,并谨小慎微地隐藏在某个地方,现在她冒着巨大的风险,裹挟着热浪远远地扑向我们,在我们心里摧放出最后的一个个花蕾。我们呼吸到了热浪里熟悉的奶奶的气息,她摇动满地的棉花株苗,我们甚至在每一片叶面上看到奶奶微笑的形象。接着,我们感觉到周围小小的风在流动,它们就像一条条啪嗒啪嗒的大鱼,在我们周围的空气里窜动。也许我们早该明白,奶奶已经再也不会有大的行动。就在此后不久,我们听见一阵阵像是蚂蚱跳动的声音,就像有东西在卷曲的棉花叶面上啪的一声弹走了,那也是奶奶。之后,爷爷抖开他发馊的手帕,捏在手中,我们看到最后一缕风栖息在上面,使得手帕轻轻摇动。接着,我们周围的空气一下子松懈下来,陷入了沉寂死灭的炎热当中。
那或许就是奶奶最后的遗言,爷爷站在那里,似乎一下子洞悉了人间的秘密,那阵飘忽的风,像是化解了他心里绷紧的最后一根弦。
那时,我和弟弟早已放弃了努力,我们已经停歇下来,只是看上去在努力。颓丧的爷爷承认了失败,再次哼哼唧唧叫唤起来,他抬起头,说:
干不完了,咱们回吧!
我们同时感觉到,空气中有一种东西消失了。那天晚上,窗外刮起了一阵阵大风,接着是一场暴雨。我和弟弟跟爷爷躺在炕上,听着风簌簌地经过我们的院子,那是一阵阵虚无空洞、没有任何本质的风。我知道,它将吹拂我们以后所有的命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