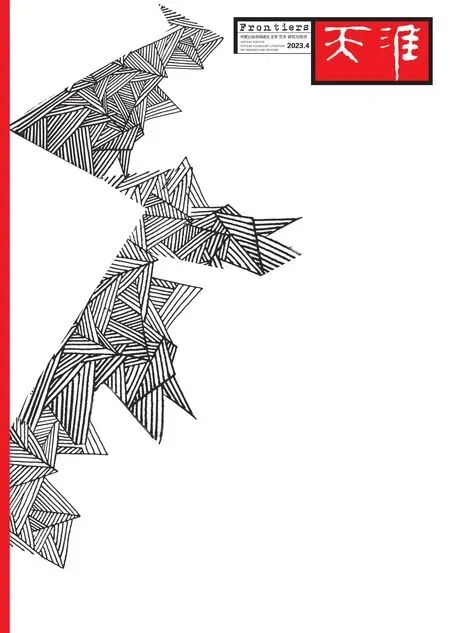打捞
2024-01-08徐威
徐威
一
贺来兮消失两年零八个月后,派出所的人在三舅家的院墙上刷了一行大字:缅北诈骗窝点人员之家。我赶到的时候,红色油漆尚未干透,刺鼻的气味以此为中心,向四面八方飘去,在村庄中左冲右撞,激起阵阵涟漪。
我推开门,看到三舅他们在院子里抽烟。我喊了几声,给他们发烟,接着和他们一样,低着头抽起来。烟雾愈加缭绕,仿佛大家可以就此隐匿身形,仿佛羞耻就会随即远去。一根烟抽完,大家依旧无言。四表哥又派了一轮,这一次大舅没有接。他干咳了一阵,抬起手在半空中左右挥舞了几下,然后问我:“相安,老老实实说,他到底有没有和你联系过?”
话没落地,大家的眼睛就齐刷刷地望了过来。三舅妈端着茶壶要去添水,此刻也止住了脚步。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了无数次,可我仍然不知道,究竟怎样的回答才算妥帖。我只能实话实说:“没有。”我一边摇头,一边发誓:“我发誓,真的没有,不骗你们。”
三舅妈用手抹了抹眼睛就走了。两年多了,我的每一次摇头,都像风扇扇片一样,反复在他们身上割出一道又一道口子。我清楚他们为什么总会追着我来问。我有八个表哥,贺来兮是最小的一个,与我同岁,只大我三天。从初中到高中,我们都是同班。高三那年,我们从普通班考进重点班,住同一个宿舍。那时,他们都说,家里终于要出大学生了,一出就出俩,一出就都是进名牌大学。那时,贺来兮说他想去西安,问我要不要也考西安交通大学。那时,我们眼中都有着闪亮的光芒。
在之后的好些年里,我和贺来兮一直想不通,命运为何突然就转向了。我们六点起来背《滕王阁序》和“疯狂英语作文一百篇”,各科高考模拟题做到凌晨,日复一日。我们兴致勃勃地商量着哪个专业好,究竟要把诗与远方放在北京、上海、西安、广州还是深圳。我们想过各种可能,始终没有往坏处想。而事实是我们的远方与北上广深毫无关联,甚至连省会都到不了。近在咫尺的远方毫无吸引力,公办二本师范院校的两张录取通知书从一百多公里外的市里寄来,让那个炎炎夏日看起来充满了秋天的萧瑟和寒冬的凛冽。
家里同意我们复读一年,但老天爷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那几年,复读生越来越多,引发了众多应届高考生家庭的愤怒。据说有人到市政府门口举了横幅,县教育局和各高中的校长被狠批一顿后,紧急出台文件,本年度严禁招收高考复读生。复读班就地解散,我们在补课半个月后第二次背着行囊走出一中校门,再也没有回去的可能。那天晚上,月明星稀,蛙鸣阵阵,我和贺来兮在村后的田埂上喝了四瓶啤酒,抱头痛哭。贺来兮说:“相安,有些人的人生巅峰就是高考,之后就一直走下坡路了,也没什么值得羡慕的。多么悲哀,对吧?”他站起身来,举起酒瓶,邀月共饮。贺来兮把酒瓶往遥远的夜空中用力一扔,说:“人生才刚刚开始,又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对不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晚贺来兮说了一堆奇奇怪怪的话,他负责说,我负责点头。
四表哥说让我再去找同学朋友打听打听,我嘴里说好,实际不抱希望。他接着又问:“来兮有没有女朋友?或者前女友?喜欢的人?”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们不知道的是,贺来兮这些年没有任何谈情说爱的念头。他在高考前跟我描绘过一次他和贺秋颖在西安古城墙下并肩漫步的美好幻想,之后再也没和我提过爱情。“成功才是紧要的,搞钱才是王道。你腰缠万贯的时候,还怕没有漂亮女人?”有一次,他看到一部电视剧,只瞄了一眼就说:“这剧名,挺好。”我一看,剧名是《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我知道他的梦是真的碎了。我可以接受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也可以接受以后去做一个中小学语文老师,尽管我并不喜欢文学,也从没想过走上讲台。贺来兮和我不一样,他比我更有想法,也更执着。因此,当他西装革履天天往外跑,甚至告诉我哪几家KTV有特殊服务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意外。他一门心思创业,从跑宿舍推销插排、路由器,到淘宝卖女装和化妆品,失败一次又一次,乐此不疲,斗志愈发昂扬,我没有觉得意外。我唯一意外的是——他怎么跑到电信诈骗那儿去了?对他来说,这有点太低级了。
三舅一直没说话,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四个舅舅中,他脸皮最薄,最看重别人对他的看法,所以总是和气待人,从不与人红脸。贺来兮失联的事情,以前顶多算是存在各种各样的谣传,只要我们不认,别人也不敢明着说。现在,院墙外的那一行红色大字,就像是一把最锋利也最晃眼的刀子,彻彻底底地把三舅钉在羞耻柱上,在往后的岁月里都不得动弹。
气氛愈加地沉闷,我想要说一些安慰的话语,却始终想不到能够说什么。最后,我只好说:“三舅,至少他还活着。”三舅先是一愣,接着眼泪毫无征兆地扑簌簌地往下掉。
二
从三舅家出来,大舅问我派出所有没有熟人。在他看来,一个镇中学的政教处主任,大小也是个官,有事总该能用上力。我说我会去找人打听,有新情况再跟他汇报。他问要不要去他家再喝点,我摇了摇头,说想去看下外婆。
外婆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到老却不住任何一家。大舅三舅还在村里,四舅远在郑州。二舅尚未娶妻就因塌方事故不幸离世之后,她独自一人固执地守在村子深处的老屋里,沉浸在越来越浓郁的静谧之中。老屋门前的巷子,数百年来都是村庄的核心地带,青砖石径,人声鼎沸,而今四处都是断壁残垣,清寂无声。
外婆坐在门口晒着太阳打盹,我喊了几声她才悠悠醒来。她从竹椅上起身,问我怎么来了,又问我母亲是不是也来了。不等我回答,她就奔厨房而去。我知道她又要给我煮鸡蛋,从小到大,每一次我们过来,都是这样。我说:“不用煮啦,刚在三舅家吃过饭了。”她说:“要的要的,一会儿就好。”我说:“那就煮一个。”她一边说着好,一边飞快地往锅里下了六个。
我吃了俩,撑得不行。外婆从橱柜里拿出一个塑料袋,把剩下的鸡蛋装了起来,让我带回去吃。她又从枕头边取出她的手机,说手机坏了,听不到响,最近都接不到电话。我把手机重新设置为响铃模式,把音量调到了最大,接着无意中看到她的通话记录里有数十个外省市的陌生来电,包括好几个海外虚拟号码。更重要的是,每个号码都有或长或短的通话时间。
我说:“这些陌生的号码,尤其是一长串的,要么是广告推销,要么是电信诈骗,都是假的,以后你不要接了,更不要相信,会上当受骗的。”外婆说:“我晓得了。”说完,她又加了一句:“反正也听不懂。”我打算把那些常见的诈骗手段,什么你家人出车祸住院、涉嫌传销、银行卡冻结、公安局让去一趟等等,和她说一遍,她却摆了摆手,说:“我晓得呢,派出所和村里都来讲过课。还说要在手机上装什么东西,装了以后骗子的电话就打不进来了。对了,装一个可以领一桶油。”我问:“那你领了没有?”外婆说:“他们不让我领,说我这手机装不了。”我和她打趣,说:“要不给你换个智能机?下次再去把那些油啊米啊通通领回来。”外婆当即摇头,语气坚决:“我又没有银行卡,骗不到我。”
坐了大约半个小时,又按照外婆的指示把屋里那些红薯、腌菜缸从这个角落挪到了那个角落后,我准备回去。走到门口,外婆突然拉住我。她问:“来兮找回来没有啊?这么一个大活人,说丢就丢啦?”她又说:“这个打靶鬼,点良心,他要是像你这么乖就好了……”她一边说,一边抹眼泪。我把外婆扶回屋里,拉着她的手,没有说话。外婆抽泣了好一阵,最后对着饭桌上的智能机器人发脾气:“鬼东西,你说来兮哪去了?”
机器人没有回应,外婆只好艰难地用普通话念出两个字:“兮宝!”
智能机器人的屏幕这会儿亮了起来,它说:“我在呢!”
外婆又喝道:“来兮呢?”
它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听懂,请再说一遍。”
外婆转过头对我说:“相安,你把它带走,我看着就怄气。”
我笑了笑,随后听到机器人说:“是的,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啊!”
我知道外婆只是说说而已。桌上的这个智能机器人,外婆要求大舅他们每半个月都要过来给它换电池,不管电池还有电没电。这是贺来兮众多失败产品中的一员。当初,他有感于农村和城市的独居老人越来越多,孤独得没人搭理没人聊天,萌生了智能陪伴这一念头,后来就有了这一款“夕阳宝老年智能陪伴与安全监护机器人”。按照他的设想,这是一款能够自主代替子女陪聊、远程视频通话、智能监控、完成生命体征状态监测并自动报警的全能系统。想法有了,但他不懂技术。起初,他想在网上找人编写一套人工智能程序,接着发现那些报价他根本承受不起。后来,他找了个在校学生,编写了一套相当简单的程序,又自己设计了个卡通造型,就算是1.0版本了。我说:“这会不会太不智能了?”贺来兮说:“智能也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嘛,就当是先试试。”我又觉得这个名字取得不太好,太庸俗了。贺来兮说:“你不懂,土才好,越土越好。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取个洋气的,或者英文的,怎么打开市场?不过,‘夕’字确实寓意不大好,老人肯定都觉得晦气,那就换成我名字中的‘兮’字吧。兮宝兮宝,有我挺好。”
外婆手中这一个智能机器人发出的是贺来兮自己的声音。贺来兮把自己的声线与音色录了进去,以后即便他天南海北地飞,兮宝仍然可以代替他陪伴外婆。出发点挺好,外婆也很感动,只是贺来兮千想万想,没有想到外婆不会说普通话,而这个智能机器人也没有高级到能听懂我们的方言。因此,外婆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掌握了“兮宝”这两个字的普通话发音——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接到指令,启动对话程序。我笑贺来兮:“要不你再装一个我们的方言系统?再去网上买个方言包?”贺来兮脸色发白:“十里不同音,你知道这是多大的工程吗?你知道这得花多少钱吗?”
这次创业就此宣告失败,只留下一个兮宝,没日没夜地与外婆“神仙对话”。
三
我打开微信和手机通讯录,上上下下划拉了许久,确认我并没有镇上派出所民警的联系方式。两个多月前,我跟着邓校长参加过一个饭局,其中有一位是派出所的副所长。我给他敬了两杯酒,但没好意思加他的微信。我不大热衷这样的交际,加微信这样的技能确实是不够熟练。我原本想给邓校长发个信息,请他把周所的微信名片推送给我,迟疑了好一阵儿,还是选择了放弃。我想,周副所长大概率已经不记得我了。
夜里我翻来覆去,折腾了许久才睡着。睡着就开始做梦,接着再次醒来,如此反复。在梦里,贺来兮从一个铁皮房中奔跑而出,跨过铁栏,撕心裂肺地喊着我的名字,让我救他,带他回家。下一个梦中,他的右手手掌已经消失不见,鲜血将纱布染红,还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掉。再后来,贺来兮整个人都飘了起来,他直盯盯地看着我,浑身颤抖,嘴唇哆哆嗦嗦地一张一合。他焦急而又愤怒地说着什么,可我一句也听不到。
这一次惊醒,彻底打消了我再睡的念头。我打开电脑,确实搜到一些类似的新闻报道。或许,贺来兮只是被骗过去的?他只是被逼无奈?被人控制住了?我越往这方面想,越觉得可能。贺来兮想成功,想成人上人,他各种折腾,也各种看不惯,但是,他不坏。然而我没有办法确认,更没有办法以几个梦来请求警方对他进行解救。我打开微博和博客,消息框里除了一些广告推送,没有任何异常。我把所有用过的邮箱都登录了一遍,甚至把那些垃圾邮件也一一翻看了,没有一丁点儿贺来兮发来的求救信息。我登录QQ,点开贺来兮的QQ空间,里头已经四年没有更新日志和说说了。
天色泛白的时候,我再一次告诉自己,贺来兮确实与我们失联了,不能再抱有幻想。太阳初升,红霞漫天,我却感觉到一阵悲凉,为贺来兮的杳无音信,更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我去了一趟派出所,没有见到周副所长。值班的人问我有什么事,我问周副所长在不在,他摇了摇头。我说,想问问缅北诈骗窝点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们怎么确定贺来兮就在那儿?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摆了摆手,说:“不要瞎打听,你们要做的,就是赶紧联系上他,劝他回来。”末了,他又说:“执迷不悟,拒不回国,到时候户口都给你注销了,还得连累你们家里一堆人!”
坦白讲,他的态度令我感到气闷,但我无法理直气壮地把他怼回去。我在派出所对面的早餐店里要了一碗云吞,开始想我究竟可以找谁。云吞吃完,我终于想起大学时候隔壁班的李天义。我听他宿舍的人说起过,他好像就在公安系统,只不过是在邻省。我跟人要了他的微信,一直到下午,他才通过验证。下课后我给他拨了个微信语音电话,很快被拒绝了。他回了一句:“在忙,晚点联系。”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李天义才发信息过来,说是刚下班。我连忙表示歉意。信息写了很长,但其实干瘪无力,毕竟我和他之前并不太熟。我问他是否方便语音通话,他直接拨了过来。一阵略微尴尬的寒暄之后,我把贺来兮的事情和他简单说了一下。
我说:“我已经和他彻底断了联系,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警方是怎么知道他在缅甸搞电信诈骗的?有没有可能是搞错了?”
李天义斟酌了一下,说:“警方对这些人员的掌握,一般就那几种途径。一个是原本就在派出所视线内的人,比如服刑出狱人员、重点监管对象之类的。他们要是突然消失,或者他短期内暴富,或者是我们听到别人说他出了国等等,就有可能会去查查。查什么?查他的身份证、电话、银行卡、微信、微博、QQ、抖音……”
我说:“他的号码早就打不通了,微信也一直联系不上,QQ也从没见他登录过。”
李天义说:“所以,我想更大的可能是有人把他供了出来。举个例子,假设广东警方破获了一起跨国电信诈骗案,被抓人员在讯问中提供了一串名单,其中就有你的表哥。那么,这个信息就会通报给户籍所在地的警方。你们镇派出所也就知道了你表哥在缅北,知道他在进行诈骗活动。”
我说:“所以我们派出所现在也不知道贺来兮是什么情况,对吗?是生是死,也不知道?”李天义沉默了一阵,说:“理论上是这样的。”
我想到昨晚的梦,心里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我说:“义哥,你能不能帮帮忙,在你们系统里头查下他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李天义说:“不可能的。”
最后,我说起昨天他们在三舅家的院墙上刷的那一行字。李天义长叹了一口气,略为感慨地说了一句:“基层派出所也不容易,也是没办法。”我说:“这是违法的吧?是不是侵犯了隐私权和名誉权?至少不合规矩吧?都说祸不及家人,可他们这么做造成的伤害多大啊!”想到三舅那颓败的神态和突如其来的泪水,我头脑一热,接着说:“我们可不可以去申请撤销?或者去上访?”李天义不大赞同我的想法,他略带疲惫地说:“相安啊,咱有多大力,就干多大事。”
四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只能这样安慰三舅他们。平静的水面,越是折腾,水花就越多。那些激荡的涟漪总有消失的时候,在它们消失之前,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岸边静静看着。至少水面终究会回归平和。底下的暗流我们无法控制,但可以假装它们不存在。
三舅越来越不爱出门,出了门也是快步疾走,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多的时候,他把院门紧闭,待在院子里抽烟,或者在屋里看电视。看什么其实无所谓,主要是有点声响。同样爱上看电视的还有外婆,我几次过来,都看到她认认真真地坐在三舅家的电视机前,右手食指在左手手掌上轻重不一地点着,不时摇头晃脑,嘴巴里还嘟嘟囔囔。
我以为她最近终于想通,愿意在三舅家待着了。三舅却摇了摇头,说:“她就是过来看电视。”这一段时间,她每天早上吃了早饭就过来,过来就要开电视,电视剧、广告、动画片、新闻啥都不挑,带字幕就行。吃了中午饭再看一阵,她就回老屋。我还挺纳闷,外婆什么时候能听得懂普通话了。三舅说:“连蒙带猜呗,她以前读过两年高小,认得一些字的。”我说:“要不在老屋也给她弄台电视?”三舅说:“整个村子就剩她在那儿住,闭路线都挪走了,弄台电视过去也放不了。”我说:“行吧,这样也挺好,至少每天能看到她,也安心。”
放寒假那天下午,我在街对面看到外婆从镇上的一家手机店走了出来。我喊了她几声,她没听见。手机店是我们班里一个同学的家长开的,我问他我外婆怎么过来了。他说:“贺主任,这是你外婆啊?老太太身子骨挺硬朗,自己跑过来说要充话费。”我面露疑色,老板接着说:“是挺少见的,现在的老头老太太都是让家里人充。再说,现在网上交话费这么方便,又不像当年。”我说:“她充了多少?”老板说:“五百。”他说完,赶紧拿出手机,把充值记录给我看。他说:“贺主任,我可没骗她,真给她充了五百。不过吧,收了十块钱手续费。哎呀,这事儿闹的,之前也是不知道她是你外婆,实在是不好意思,我马上转回给你。”
我说:“不用不用,不过她充那么多话费干什么?”老板左顾右盼,把我拉进店里,说:“贺主任,咱也不是外人,我说几句,你不要生气。”我点了点头。他继续说:“老太太这话费有点猛。”我说:“你是指……”他凑到我耳朵边,小声说:“这两个月,老太太来了七八趟,在我这儿都充了快两千块钱了。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上网用了流量,可我一看,她那个是老人机,没法上网的。”老板说完看着我,犹豫了一下,又说:“你最好打听打听,她这话费都用去哪了,可别被骗了。”
我让老板把这两个月的充值记录找了出来,截了图发到我微信上。等我从店里出来,外婆已经消失不见。
五
我到老屋的时候,外婆还没有回来。门关着,但并未锁。从屋里到厨房,我都打量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直到我在外婆的枕头底下摸出一本作业本。本子没什么特别之处,怪异的是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电话号码。最左边看起来像是日期,中间是电话号码,右边打满了勾和叉。
我粗略一翻,这本子都已经快写完了。上面的电话,大多都是153、162、167、170、173、177、185、191 开头,有几个一看就是虚拟号码或者海外号码。我随便抽了几个号码,用手机在百度上一查,归属地是上海、北京、宁夏、广州、深圳、厦门、昆明等,唯独没有我们本地的。
我不知道她哪来这么多外地号码,更不知道这些勾勾叉叉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把本子原原本本地放回枕头底下。我想把这几张照片发在家族群里,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可又怕平添波折。纠结了一阵,我想我还是应该为外婆保持沉默,至少在这个谜题尚未解开之前。
到了大舅家,他正在院子里杀鸡杀鸭。我问大舅:“今天什么日子,整这么丰盛?”大舅乐呵呵地说:“上午不是放寒假了嘛,等下你哥他们就从县城回来。接下来不得闲咯,六个孩子丢给我们。”闲聊了一会儿,我旁敲侧击地问:“外婆说最近她的手机不大好用,是不是刚好没话费了?”大舅叼着一根烟,一边给鸭子拔毛,一边说:“怎么会?每个月我都给她那个号码充三十块钱。再说了,基本都是你们打给她,她又不怎么会往外打电话。”过了一会儿,大舅说今晚就在家吃吧,我说我去三舅那儿一趟。他说:“那你把他们也喊过来,一起热闹下。”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三舅正在电视机面前的取暖器旁取暖,还没开始做饭。见我进来,他挪了挪位置,把“小太阳”朝我这边。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过年了,天气越来越阴冷,我把手贴近取暖器,好一阵儿才感觉到手上的寒凉在逐渐褪去。三舅问:“放寒假了?”我点了点头,说:“外婆最近是不是经常打电话啊?几次给她打电话,都是在通话中。”三舅说:“不晓得啊,她最近都很少过来。”我说:“她最近不看电视啦?”三舅说:“天冷,懒得出来了吧。”
我们取着暖,接着就无话可说了。坦白讲,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时候,我越来越畏惧到三舅这儿来。我知道他不会问我,但一进屋,我脑子里就全是贺来兮。有两回,我自己憋不住,主动说起他,三舅只听着,一声不吭,仿佛我没说一样。手开始暖和起来,我左看看右看看,没话找话地问三舅妈哪去了。三舅说:“回娘家扫年了。”我说:“你怎么没一块儿去啊?”话一出口,我就开始后悔。果然,三舅又陷入沉默之中,眼睛盯着电视,仿佛那些浮夸的保健品广告真的趣味十足。这时,大舅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还在三舅这儿,喊我跟三舅一块过去吃饭。
三舅不想去。我说:“你这儿一个人,也没做饭,走吧。”三舅没应声。我说:“今晚咱喝几杯。”三舅还是没说话。我说:“刚刚我从大舅那儿过来,我看到他买了一副大肠。你就当过去给我炒一盘酸辣大肠吧。大舅那手艺,你知道的,不行。”连拉带拽,我终于把三舅哄出了门。
大舅家人多,满满当当坐了两桌。这久违的热闹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温暖。三舅坐了一会儿,起身就说要去炒大肠,大舅把他拉住了。大舅说:“放心,放心,你阿嫂炒的味道也不会差。”我们几个就围着火盆抽烟,把厨房交给了舅妈和表嫂她们。我纠结着要不要把外婆的事情说一说,大表哥却把话题引向了贺来兮。他先是长叹一口气,接着说:“今年来兮要是也能回来过年,那就圆满了。”大舅啪的一巴掌就打在他肩膀上,眼睛瞪着他,示意他别说这个。大表哥被大舅的反应吓了一跳,接着又有些尴尬。刚才那一巴掌,拍得很结实,屋子里一大家子老老少少都听到了。所以,我看到他硬着头皮又说了一句:“我又没说什么,这也不说,那也不说,真当没来兮这个人了?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嘛!”大舅起身就要揍他,被三舅拦了下来。
折腾了好一阵,大家才又坐了下来。四表哥给大家发了一圈烟,接着大舅对大表哥说:“你待会自罚三杯,好好跟你三叔赔罪。”大表哥点了点头,三舅却摇了摇手,说:“他说的也没错,说什么赔罪。”大舅舒了口气,把烟点上,问:“来兮还是没来个电话?”三舅不说话,大舅又对着我说:“相安,你呢?联系上他没有?派出所那边有没有新情况?”我说:“有消息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了。我跟我同学打听过,他说我们派出所基本上也不知道啥情况,只知道来兮在缅甸。”我把李天义的推测给他们说了一遍,他们也觉得有道理。大表哥说:“那我们还是只能等着?等他回来?他会不会是因为知道回来要坐牢,不敢回来啊?”四表哥赶在大舅再次发火之前把话接了过去,说:“相安,你的手机一刻也离不得身,二十四小时开机,不要静音,也别震动,最好是响铃模式。来兮要是找人,肯定是找你。”
我说:“我一直等着呢。”
大表哥抽了一根烟,说:“三叔,老是这样等也不是办法。现在来兮就像是一条鱼掉进了大海里,不管他是自己游进去的,还是被人丢进去的。海那么大,鱼那么小,光靠他自己游回来,难。当然,找也难,真真切切是大海捞针啊。不好找,但我们也得找啊。”
我明白大表哥的意思。对汪洋大海来说,来兮这条鱼算不上什么,连个小浪花也翻不起来,就算翻起来了,下一刻也就消失了。可是,他对我们来说不一样。他这条鱼,不管有没有翻身,不管处境如何,此刻都是我们面前的庞然大物。他现在随便吭个声,都是一声巨响。可惜的是,我们听不到他吭声。他只留给我们一团迷雾,如同深渊,如同无底洞,要把大家伙儿都卷进去。我们迫切地想把他找到,迫切地想把他捞回来,为了他,也为了这个家。然而,两年多时间过去了,我们用尽了各种办法,依旧一无所获,依旧一筹莫展。
大舅妈端菜上桌的时候说:“要不要去找仙婆问一问?”她把酸辣大肠往桌上一放,两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又凑了过来说:“鬼狐坑那个桂琴嫂,最近又比较准了。上个月,福坤婶家的孙子在镇上走丢了,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派出所的民警查监控也没看到他哪去了,都不知道他是自己跑了还是被人抓了、拐了。实在没办法了,福坤婶去问桂琴嫂。人家跳了一段,醒来就说要往寨头山的东头去寻。哎,还真找到了。这孩子在山里硬生生饿了三天,可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他三叔,待会儿你把来兮的八字给我,我明天就去问问。”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接大舅妈的话,只有大舅冷哼了一下:“迷信!”
三舅把烟头往火盆里一扔,用手搓了搓脸,说:“过完年,我出去找他。”大舅又在大表哥手臂上拍了一巴掌,说:“他懂个屁,你听他的?你去找?去哪找?去缅甸?”
大舅越说越气,用手指着大表哥说:“要去也是他去!”
大表哥说:“我去就我去!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
说完,大表哥对着我又说了一句:“相安,我们一起去。”
六
这顿饭吃得并不那么舒畅,尽管到了饭桌上我们就再没提贺来兮。我猜想,在贺来兮回来之前,家里这样的聚餐可能都会如此小心翼翼。他的消失确实把整个家族都卷入到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尤其是三舅和三舅妈,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脊柱仿佛枯朽了一般,一天比一天松垮,一天比一天更经不住地心引力的拉扯。
同样焦心的还有我的外婆。晚上吃饭前我准备去喊她过来,大表哥说他去喊过了,外婆不想过来。吃完饭,我走出大舅家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外婆对大表哥说,天气冷,加上夜都黑了,她已经吃过晚饭,明天再过来看这些孙儿。这很反常,平日里她最念着这些孙儿和曾孙,现在他们回来了,怎么会不想见?
我走到半道儿,又折了回去。
整条巷子只有外婆住的那间房子还亮着灯。我悄悄地走近,隔着门听到外婆在打电话。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此刻已经是夜里九点十八分。我弯下腰,从门锁边上的门缝往里看。外婆正坐在床头,桌上摆着那本写满了电话号码的作业本。
她带着老花眼镜,一边看着本子,一边拿出手机在按。
拨通之后,她两只手捧着手机,哆哆嗦嗦地把手机压在耳朵上,接着我听到她说:“喂,贺来兮在不在?我找贺来兮……”
电话断了。
她放下手机,拿起一支笔,在那本作业本上划拉了两笔,又按了一个号码:“喂,贺来兮在不在?我找贺来兮,我是他奶奶……”
我不知道她在给谁打。
我吃惊地发现她今晚说的是普通话。
电话再次被挂断。
我看到外婆又划拉了两笔,再按号码,再打: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喂,贺来兮在不在?对对对,他叫贺来兮,贺!来!兮!……”
我蹲在门口,泪流满面,但不敢发出一丁点儿声响。
外婆拨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划拉了一个又一个勾勾叉叉,直到再也没有可以划拉的对象。
这时候,床头的机器人发出贺来兮的声音:“我在呢!”
七
几天之后,我接到外婆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用普通话找贺来兮。我们这才知道,外婆已经开始随机拨号了。大家再一次聚集在三舅家,商量应当如何是好。大舅和表哥他们带着外婆去县城医院做了检查,各种报告单都没有显示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医生说,老太太身体还行,就是精神上一下子有点转不过弯来。医生还说,解铃还须系铃人。
道理都懂,可这个系铃的混蛋我们找不到。寻找贺来兮成为一个难题,大表哥脑洞大开地提出一个想法——找不到就制造一个新的贺来兮。他和外婆说:“贺来兮昨天晚上打电话回来啦,公司这次终于做成啦,越做越大,业务都做到埃塞俄比亚去了,今年过年没法回来啦!”外婆眼睛一亮,问:“埃塞俄比亚?哪个鬼地方哦,不是说缅甸吗?”大表哥说:“那都是别人瞎说的,他在非洲呢!非洲,全是黑人的地方,坐飞机都要一整天。”外婆又问:“不是诈骗?”大表哥说:“没有,他在非洲卖衣服呢。国内十几块钱的衣服,运到那边能卖好几百。”外婆说:“好好好,那就好。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我和他说几句。”大表哥说:“这有时差呢,时差你懂不懂?我们白天,他们晚上。我们晚上,他们白天。埃塞俄比亚现在都凌晨三四点了,来兮早就睡觉啦。”外婆说:“你在骗人。”大表哥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外婆说:“你给他打个视频电话,我要亲眼看到兮宝。”大表哥只好说:“那我过两天让他打视频电话过来。”
“相安,你会搞电脑,能不能P一个来兮出来?会动,会说话,能和奶奶视频那种。”大表哥问我,我其实也不懂,只好摇摇头。大舅对大表哥的行为表示质疑,他说:“能骗一天,还能骗一年?还有,你这骗得有点假,要是我我都不相信。”三舅却站在大表哥这一边,他说:“能撑一天是一天。你们先哄着她,我出去找。”大舅说:“这都快过年了,天大地大,你上哪儿找去?”三舅吐了一口烟,说:“去云南,去边境。”
大家都表示反对。这样毫无准备、毫无计划地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几千里之外,去找一个失踪了近三年的人,堪比大海捞针。再者,三舅活了五十年,去到最远的地方就是市里,普通话听得懂,但并不怎么会说。还有,他不会网上购票,不会用打车软件和导航软件,更不会用电子支付。争执了一阵,大表哥说:“我去吧。”
我刚刚一直都没有说话,主要原因是我认为这种找法没有多大的意义。或者说,我们也许可以先试试其他的方法。仅仅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实在是有些渺茫。所以,在他们都停下来了之后,我说:“我们的思路其实要变一变,这才是目前最应该要做的。”
我说:“贺来兮现在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一无所知。以前村里有谣言,说他做生意失败了,说他跑路了,说他欠了几百万了,说他在外面和人打架把人打坏了,还有说他和一个富婆私奔了,反正啥奇奇怪怪的都有。现在,按照派出所的说法,他又是在缅甸搞诈骗。这些信息,我们目前都不能真正确定。但是,不管贺来兮是不是在缅北,是不是在搞电信诈骗,他的失踪对我们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种羞耻。尤其是外面那行字刷上去之后——他越是不回来,他的罪名就越确定。”
我看了一眼三舅,停了一下,接着说:“所以,我们都认为越少谈论贺来兮越好,都认为知道他失联的人越少越好。这样也没错,他这个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可是,我们现在不能再这样自我欺骗了。捂是捂不住的,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我们都管不着,也管不了。我认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贺来兮失踪快三年了,我们甚至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这话说得有点重,我看到三舅的身子微微颤抖,但我已经别无选择。我继续说:“仅仅靠我们家里这几个人的力量,说去外面找,实在是太难了。我们现在就应该广而告之,应该大张旗鼓地去找他,坦坦荡荡地把他的失踪告诉任何一个可能和他有联系的人,尽可能地发动更多的人提供信息。我们可以去找派出所,去找报社、电视台,我们要在QQ、微信、网络论坛,铺天盖地地发布寻人启事。我们甚至可以给提供确切消息的人报酬,两千、三千或者五千。能问的人都去问,能打的电话都去打,能发信息的地方都发。总而言之,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转发,让更多的人帮助我们一起寻找贺来兮。”
时间只会是一种麻药,永远不可能是解药。我说完之后长舒一口气,终于感觉到一阵轻松。好几分钟都没有人接话,我点了一根烟,说:“三舅,大舅,各位哥哥,你们都不说话,我就当默认了,待会我就写寻人启事。”
八
寻人启事不到十分钟就写好了,挑贺来兮的照片却花了近一个小时。他的单人照并不多,我选了他失联之前最新、最清晰的一张。我面前更多的是他和大家的合照。这些合照,每一张都能够迅速地把我拉回到过往的某一个瞬间,久久不能回到现实。比如我们一起在高三(9)班班牌下面意气风发地笑着,那时我们都感觉自己会有美好的未来;比如大一那年寒假,我们一帮人在屋后旷阔的田野里烤番薯,除了我们俩之外,其他人都在外省读书,学校都比我们好,为此贺来兮说这次聚会并没有什么意思;比如我们戴着学士帽神情庄重地站在大学门口,原想留下一张正式一些的照片,结果照片中我们背后是杂乱的各式人等;比如我第一次穿着西装去应聘,贺来兮因为我不会打领带而训斥了我大半天;比如我们光着膀子在一间狭小的民房里忙着打包各种女装包裹,那时候他的网店在投入了近一万块钱的宣传费之后终于有了一丝起色;比如我们用手揽着对方的肩站在山巅,那会儿他刚买下一辆九成新的二手凯美瑞,提到车就说要带我去兜风……
坦白说,我本不精彩的人生中,那些稍能回味的事情大多都与贺来兮有关。我就像是他的一个影子,对他而言,并不能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顶多算是陪伴。只是,后来他越跑越快,越跑越远,而这个影子时常跟不上。直到现在,影子彻底失去了他的踪迹。
我还发现一张他和贺秋颖的合照。确切地说,也不能称之为合照。照片是从讲台往下拍的,那时候他们还是同桌,位置刚好在照片的最中央。那一刻,他们笑得羞涩而又腼腆。我心里默默地算了一下,发现这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
我把寻人启事编排好,截图成一张图片,发到了家族群、同事群、同学群、同乡群甚至是各届家长群里,接着群发给了我所有的微信好友和QQ 好友,然后又在朋友圈发,在微博上发,在我们本地的论坛发。我已经顾不上这样群发会不会引来别人的反感,也顾不上这样群发会不会对贺来兮的形象造成破坏。
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事情。只要能够有他的任何一丁点儿消息,那就值了。
寻人启事留的是我的号码,我在里头说提供线索或帮助的有重酬。但我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打电话过来,更没想到打来电话的是十多年没联系的贺秋颖。
她说:“相安吗?我是贺秋颖,贺来兮到底是怎么回事?”
坦白讲,在那一瞬间,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不知道是因为贺来兮,还是因为贺秋颖。我简单地把事情解释了一下,然而她并没有再细问。
她接着说:“你这样发,其实力量还是有限,能看到这张寻人启事的人仍然是很有限的。”
我知道她说得对,然而,此刻我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语文老师,不是奥特曼,也不是钢铁侠。
我叹了口气,说:“还能怎样呢?茫茫人海,我只能尽可能地广撒网,然后等待一个奇迹的发生。”
贺秋颖说:“事在人为,人定胜天,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我问:“什么意思?”
贺秋颖说:“你找我啊,我们公司专门做这个的。不出三天,我们就能把这个寻人启事整成热搜,我们就能让几千万上亿人知道这个事情。我们甚至还可以让很多的明星和各种大V 转发这个寻人启事,当然,这个价位就比较高了……对了,我突然想到,热搜的关键词和话题,可以叫‘寻找贺来兮’,或者叫‘来兮,归去!’……”
贺秋颖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我说我要回去和他家人商量一下,回头再给她回复。电话挂断之后,我在想,倘若贺来兮看到现在的贺秋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表情?他是否还会想着和她一起漫步在西安的古城墙下?
之后的几天,我的电话接连响起。起初多是问贺来兮究竟怎么回事的,后来多是问所谓重酬究竟是多少钱的。我一次又一次接听,一次又一次地失落,直到开始麻木,直到开始畏惧。
我每天都到三舅家一趟。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自己并非孤身一人。我都如此,三舅他们承受的该是何等痛楚?每次想到这儿,我对三舅和外婆的心疼就多了一分,对贺来兮的愤怒也多了一分。
腊月二十四那天,三舅问:“有情况吗?”
我说:“没有。”
三舅又问:“是不是奖金还不够多?”
我说:“这不是奖金的问题。”
三舅像往常一样,点了一根烟,盯着电视,装作若无其事。
我说:“不过,有一个好消息。”
三舅迅速地转过头来:“什么消息?”
我用手指指了指外面,说:“墙上那行字,过几天派出所会派人来抹掉。”
三舅又惊喜又疑惑:“真的假的?为什么?”
我说:“这种行为,其实是违规的。”
喝了一壶茶,抽了两根烟,三舅说:“我去杀鸡。你别在这待着了,去老屋坐坐,喊你外婆一起过来吃饭。”
我点了点头,从村里的小卖店买了一斤小面包、两包葡萄干和两袋山楂片,往外婆那儿走去。这些都是她爱吃的小零食。我远远地就听到一群孩子追逐打闹的声响,大舅家的六个孩子,此刻都在。老屋终于有了久违的热闹。
他们模仿着外婆平日里的做派,一声又一声地用普通话喊着:“兮宝!兮宝!兮宝!”
机器人都快响应不过来了,它一遍又一遍地回答:“我在呢!我在呢!我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