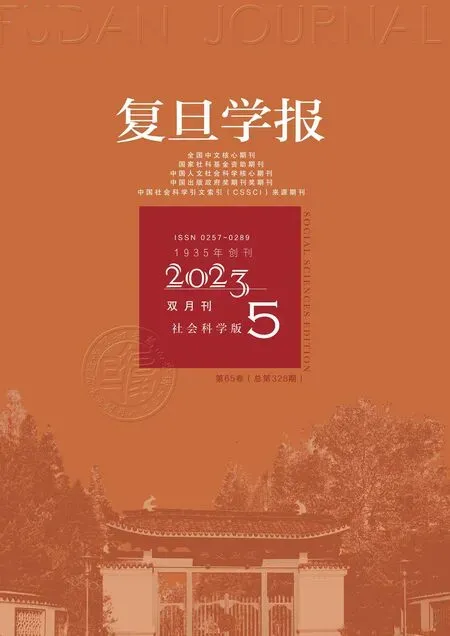古典诗歌用典论
2024-01-08程羽黑
程羽黑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艺术研究院,上海 200240)
用典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特征。胡适说:“自中古到近代,中国诗文简直是典故的天下。”(1)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9页。这一概括固然失之简单,忽视了钟嵘、皎然、严羽等不主张用典的论者(2)钟嵘《诗品》:“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强调诗与文不同,不贵用事。皎然《诗式》谓“诗有五格”,“不用事第一”。严羽《沧浪诗话》:“夫诗有别才,非关学也。”批评“近代诸公”之诗“多务使事”。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0页;李壮鹰:《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6页。,但确实抓住了主要事实。尤其是唐代以后,杜甫的诗成为典范,而“一字一句皆有来历”(3)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22页。正是杜诗为人所称道的特征,带动了诗坛主流对用典的追求。宋代大诗家苏轼、黄庭坚、陆游皆以善用典故著名(4)关于苏、黄、陆三人善用典的评价甚多,兹不繁引,各举一例。赵令畤《侯鲭录》:“东坡作诗妙于使事。”方回《瀛奎律髓》:“山谷最善用事。”赵翼《瓯北诗话》:“放翁以律诗见长……使事必切,属对必工。”“古体诗才气豪健,议论开辟,引用书卷皆驱使出之,而非徒以数典为能事。”孔凡礼点校:《侯鲭录 墨客挥犀 续墨客挥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8页;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66页;曹光甫校注:《赵翼全集》(伍),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68页。。我们甚至可以说,反对用典的诗论家,只是反对过多用典、使用僻典,而并不反对适度用典、使用熟典。
以往讨论用典的著作不少,多聚焦于典故的使用方法和技巧上(5)罗积勇将历代关于用典的研究著作分为“如何恰到好处地引用典故”和“关于用典方式的研究”两大类,前者是技巧,后者是方法。近年来关于个体诗人和时代用典风格的研究也基本在此范围之内。罗积勇:《用典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23页。,可说是一种“共时性”的研究。作为文学手法,古典诗歌的用典有其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狭到广、从粗到精的发展过程。通过“历时性”的整体考察,可以较全面地了解诗歌用典的来龙去脉,洞悉其机制,观察其趋势,发掘其意义,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弘扬这一中国古典文学的宝贵遗产。
一、 诗歌用典的渊源与情境原则的确立
中国诗歌用典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诗经》中存在大量与金文相同或类似的短语,如“旻天疾威”(6)见《大雅·召旻》。金文用例如《毛公鼎铭》:“愍天疾畏。”《毛诗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58页;《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41页。、“出纳王命”(7)见《大雅·烝民》。金文用例如《师望鼎铭》:“虔夙夜出内王命。”《毛诗注疏》,第1786页;《殷周金文集成》,第1481页。、“日就月将”(8)见《周颂·敬之》。金文用例如《史惠鼎铭》:“日就月将。”《毛诗注疏》,第1784页;钟柏生等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第531页。、“夙夜匪懈”(9)见《大雅·烝民》。金文用例如《中山王厝方壶铭》:“夙夜篚懈。”《毛诗注疏》,第1787页;《殷周金文集成》,第5142页。,等等,以往学者多以为金文引自《诗经》,近年的研究则揭示了两者可能都来自当时的成语(10)陈致:《“不吴不敖”与“不侃不忒”:〈诗经〉与金文中成语零释》,《诗书礼乐中的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41页。,可以说是一种“语典”。不仅如此,《诗经》中还有篇目不同而语句近似者(11)王靖献以米尔曼·帕里和阿伯特·B·洛尔德的口述套语创作(oral-formulaic composition)理论解释这一现象,认为这些“套语”(formulae)是《诗经》作为口头文学的特征。见王靖献著,谢濂译:《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154页。,如《王风》《郑风》《唐风》皆有《扬之水》,前两首都以“扬之水,不流束楚”“扬之水,不流束薪”(12)《毛诗注疏》,第354、438页。起兴,显然应有承袭关系或共同来源。清华简《耆夜》记载武王伐耆后,归于文太室行饮至之礼,与群臣作歌五首,其中周公所作《蟋蟀》与传世本《毛诗》差别甚大(13)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50页。,而皆以“蟋蟀在堂”起兴,上博简《孔子诗论》则记录孔子说《蟋蟀》的主旨是“知难”(14)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9页。,又与清华简本、传世本不同,参照《扬之水》之例,三诗不无同题异作的可能。柯马丁认为,这些诗篇的相同语句来自共同的“素材库”(15)柯马丁著,顾一心、姚竹铭译:《早期中国诗歌与文本研究诸问题》,《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应当视为“引用”。(16)Martin Kern, “Quotation and the Confucian Canon,” Asiatische Studien / Études Asiatiques LIX.1 (2005): 293-295.可注意的是,无论“扬之水”还是“蟋蟀在堂”,意象鲜明,含义可辨,都已突破了单纯“语典”的范畴,而初步具备了“事典”的性质。(17)“语典”与“事典”之别可参罗积勇:《用典研究》,第51页。
《诗经》对用典的影响也体现在春秋时代的赋诗活动上。在朝聘、会盟、燕飨等公共场合,赋诗者引用《诗》句表达己意,所谓“赋诗断章,予取所求焉”。(18)《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77页。钱锺书敏锐地指出“赋诗断章”与后世用典的关系:“皆假借古之‘章句’以道今之‘情物’,同作者之运化;初非征援古语以证明今论,如学者之考信。”(19)钱锺书:《管锥编》(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29页。换言之,赋诗的原则不是符合原旨,而是切合情境,留下了相当大的发挥空间。当然,弹性仍有限度,《左传·襄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杜预注:“歌古诗,当使各从义类。”孔颖达疏:“歌古诗,各从其恩好之义类。高厚所歌之诗,独不取恩好之义类,故云:‘齐有二心’。”(20)《春秋左传正义》,第939页。依晋侯、荀偃之见,温宴上的赋诗者必须在表现“恩好”的诗篇中选取章句,否则便是“不类”,违背了诸侯和洽的主题。刘知几《史通·言语》谓其时大夫、行人“语微婉而多切”(21)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49页。,“切”正是春秋赋诗的理想境界,而后世用典同样以“切”为贵。
战国晚期出现的《楚辞》是中国诗歌的另一源头。姜亮夫以为,屈原《离骚》、《远游》、《悲回风》皆有“仆夫悲余马怀兮”之句,仆、马并举,当是用《周南·卷耳》“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之典。(22)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姜亮夫全集》第7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5~146页。考虑到《离骚》前文“陟升皇之赫戏兮”(23)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增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92页。与《卷耳》“陟彼砠矣”(24)《毛诗注疏》,第52页。同用“陟”字,亦能对应,此句确有暗用《诗》典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用典在先秦诗歌中虽已具备雏形,但多为直接引用——借用前引钱锺书“运化”一词,此时的“用典”可谓有“运”而无“化”,屈原此句则运而能化,显示出卓越的文学技巧。不过,《楚辞》中虽有不少见于《诗经》的用词,却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稳定的用典手法。《楚辞》的一大特色是数量庞大的古代人名,其中大部分出现在作者所征引的古事中,偶尔也有与主角互动者,如《思美人》:“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25)② 《楚辞章句疏证》(增注本),第1740~1741、1730页。造父是周穆王时人,按常理不可能为屈原驾车,此处似乎是用典指代善驭者,但屈原笔下人神杂处,《思美人》前文“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26)② 《楚辞章句疏证》(增注本),第1740~1741、1730页。中的“丰隆”便是雷神,而屈原作品中又常有驱遣神灵的情节(27)如《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吾令帝阍开关兮”、“吾令丰隆乘云兮”;与《思美人》同为《九章》之一的《惜诵》中也有“令五帝以折中兮”、“吾使厉神占之兮”。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增注本),第370、402、422、1412、1454页。,依照惯例,这里的造父也应理解为超越世俗时间的神格形象(28)典籍中确有造父神格化的传说,如《论衡·命义》:“天有王梁、造父。”《晋书·天文志》:“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造父”为星官名。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8页;《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0页。,而不宜视为代称。类似的情况屡见不一见(29)如《离骚》:“吾令蹇修以为理。”《惜诵》:“命咎繇使听直。”蹇修、咎繇为古人名,皆与神并列,可见其必为神格形象。王逸注:“使古贤蹇修而为媒理也。伏羲时敦朴,故使其臣也。”“言己愿复令山川之神备列而处,使御知己志,又使圣人咎繇听我之言忠直与否也。夫神明照人心,圣人达人情,故屈原动以神圣自证明也。”已明其非代称。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增注本),第426、1417页。,虽有零星例外(30)如《怀沙》:“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 此处的“离娄”当是明目者的代称。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增注本),第1677~1678页。,但总的来说,《楚辞》仍处在简单引用的阶段。
从现存的文献看,先秦诗歌的“用典”绝大多数只是径引成语与史事,尚不能如后世作者用自己的语言组织典故,使其成为作品的有机部分。但我们不难看出,用典的传统在中国诗歌的源头已开始萌芽。尤可注意者,《诗经》的用典手法固然原始,春秋时代的赋诗却奠定了以切合情境为主导的用典原则。可玩味的是,这一原则主要来自引用者而非创作者。《汉书·艺文志》:“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31)《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55~1756、3951页。明确将“聘问歌咏”的赋诗者视为后世文人的前身。近有研究认为,《诗经》在春秋时代完成了从仪式文本到辞令文本的转变,其背景是诸侯霸主带动的礼乐复兴。(32)马银琴:《春秋时代赋引风气下〈诗〉的传播与特点》,《中国诗歌研究》第20辑,2003年,第166~167页。作为辞令的赋诗可以说是一种“二次创作”,同时也拓展了《诗》的解释层次。(33)董治安曾举例说明春秋赋诗中对诗的解释多有为汉以后人所沿袭、采用者。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第33~34页。我们将会看到,赋诗中体现的这一开放的特点贯穿了整个诗歌用典的传统。
二、 用典对“套语”的超越
汉乐府诗是中国诗歌主流从四言诗过渡到五言诗的重要一环,其中出现了较为成熟的用典手法,如瑟调曲《善哉行》:“惭无灵辄,以报赵宣。”(34)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6页。反用《左传》灵辄向赵盾报恩之典(35)灵辄报恩事也见于《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公羊传》、《史记》,唯有《左传》言其姓氏,《史记》则误作“示眯明”。相关考证可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61页;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55页。,颇见巧思,已非《诗经》、《楚辞》中常见的简单引用可比。汉乐府诗中还有源自《诗经》的“语典”,如《汉书·外戚传》所载《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36)《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55~1756、3951页。用《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37)《毛诗注疏》,第1847页。之典。值得一提的是,《诗经》原文仅有批判“女祸”的负面意义——所谓“妇言是用,国必灭亡”(38)见孔颖达疏。《毛诗注疏》,第1847页。,《李延年歌》则从“倾城”一词衍生出“倾国”,通过夸张的手法表现佳人的美貌,无论主题和用词,都与原文有别,作者根据情境灵活用典,展现出醇熟的文学技巧。但我们也应注意,汉乐府诗中的典故多仅用字面,而不涉及原文的深层含义。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受汉乐府影响的早期五言诗中。(39)汉代的乐府诗和五言诗的区别存在争议,文献记载中常有混淆。赵敏俐认为两者皆为可歌之诗,本质上并无不同。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9~30页。字面引用可说是一种“套语”,读者不必明了典故,也能完全把握意义。宇文所安举《古诗十九首》第十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终日不成章,泣涕泪如雨”之例,诗用《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之典,同样是写织女织不成布,《诗经》原文意在指出织女徒有其名,此诗则借用字面,表现织女对牵牛的思念。宇文氏以此说明汉乐府和早期五言诗中的用典多非对《诗经》的“学究化”应用,而来自经典通俗化后形成的“习惯性引用语”,作者对典籍并无深入理解,所以经常是偏离原文的标准解读。(40)宇文所安著,胡秋蕾、王宇根、田晓菲译:《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84页。宇文氏所举之例未必恰当,因为当时已有牵牛织女的传说,作者应只是在诗中转述(41)牵牛织女传说可以上溯到秦代,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已将牵牛、织女拟人化。至东汉时,该传说已大体成熟且广泛流行,如应劭《风俗通义》:“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河南南阳白滩东汉画像石、山东肥城孝堂山石祠画像中皆有牵牛织女情节的图像。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06页;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00页;王修中等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6卷,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91页;罗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文物》1961年第4、5期合刊。,而非根据《诗经》用词自创故事,与对典籍的理解无甚关系;但此时的诗歌主流尚未脱离字面引用确是事实。
用典超越“套语”,有待于成熟的文人诗出现。传世的汉代诗歌中,有明确作者的文人诗普遍比乐府诗用典更多,且与原文的“标准解读”更加切合,如秦嘉《赠妇诗》之三:“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清晨当引迈,束带待鸡鸣。”(4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87页。四句之中,连用《召南·小星》:“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周颂·载见》“龙旂阳阳,和铃央央”、《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43)⑦⑧⑨ 《毛诗注疏》,第126、407、1967,1967,409,407,335页。之典。该诗是秦嘉赴京上计后的寄妻之作(44)见《玉台新咏》所载诗序。原文作“上掾”,逯钦立考证为“上计”。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3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87页。,细察上举用典,无论与主题还是原文,皆能吻合无间:《小星》之典符合《韩诗》“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45)《韩诗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页。的解说,切合秦嘉职卑事劳、为人任使的郡吏身份;《载见》的主题是“诸侯始见君王”(46)⑦⑧⑨ 《毛诗注疏》,第126、407、1967,1967,409,407,335页。,与秦嘉代表郡守入京若合符节;《女曰鸡鸣》不但有“士大夫以君命出使”(47)⑦⑧⑨ 《毛诗注疏》,第126、407、1967,1967,409,407,335页。之义与上计照应,且“女曰鸡鸣,士曰昧旦”正是发生在夫妻之间的对话——所谓“夫妻同寝,相戒夙兴”(48)⑦⑧⑨ 《毛诗注疏》,第126、407、1967,1967,409,407,335页。——紧紧扣合了“赠妇”之题。该段用典妙在化实为虚,以“出使”主题网罗典故,虽未尽脱“套语”之习,也难称成熟,但作者能在严格把握典籍“标准解读”的基础上切合情境,体现出明确的典故意识。该诗下文还有“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49)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87页。显然是《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桃),报之以琼琚(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50)⑦⑧⑨ 《毛诗注疏》,第126、407、1967,1967,409,407,335页。的五言改写,足见作者对典故原文的重视。
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邺下文学推动了中古诗歌的第一次高潮,五言诗得到长足发展,但此时的诗歌受乐府俗乐影响甚巨。钱志熙以为,当时的乐府诗多用旧题,其选题与庀材,或多或少地受到古辞的影响,形成一个自身内部衍生的题材系统。(51)钱志熙:《论魏晋南北朝乐府体五言的文体演变——五言体之间文体上的分合关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这导致了建安诗歌的叙事与抒情经常受制于既定的程序,“套语”等简单引用仍是这一时期的用典主流。真正带来变革的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阮籍。在其《咏怀诗》中,典故与原文语境关系密切,产生了互文见义的效果,如《咏怀》之四:“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清露被臯兰,凝霜沾野草。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52)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9页。“天马”句典出《郊祀歌》:“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53)《汉书》,第1060、171页。“西北”一词则出自《汉书·张骞传》:“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54)《汉书》,第1060、171页。注家多不解“天马”句与全诗的关系(55)相关讨论可参程羽黑:《阮籍〈咏怀诗〉“天马出西北”解》,《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2辑。,实则《郊祀歌》下文有“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56)《汉书》,第1060页。诸句,写乘坐天马游历仙境,此句即成仙之意。阮诗下文言世事无常,盛者必衰,末句又与首句照应,意谓若非王子晋这样的仙人,天壤之间谁能久驻容颜?“天马”之典的内涵必须联系原文才能把握。《咏怀》的用典超越了“套语”,典故不再是提供例证或增添辞藻的工具,而成为表达诗意的主体部分。以典表意使诗歌文本“归趣难求”(57)⑦⑨ 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第151、152、34页。,读者“信其但然而又不徒然,疑其必然而彼固不然”(58)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77页。,得以开放性地解读诗意。
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的作者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语言组织典故,在形式上摆脱了原封不动引用的“套语”。建安时代的诗人已能使用“变体”改造前人的诗句,如曹植《送应氏二首》之二:“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改写自《古诗十九首》:“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59)关于魏晋诗歌“变体”可参宇文所安的讨论,此处所举用例即来自其书。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第80页。大体上保留了原句之意。阮籍之诗虽能以典表意,但在文字上仍以径用原文为主,如《咏怀》之十一:“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60)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251页。连用《招魂》:“湛湛长江兮上有枫”、“皋兰被径路兮斯路渐”、“青骊结驷兮齐千乘”、“目极千里兮伤春心”(61)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增注本),第2336、2344~2346页。诸句,阮诗于前两句照抄,于后两句也只是略作改写,并无多少文学意义上的修饰。钟嵘《诗品》评价阮籍“无雕虫之巧”,《御览》本“雕虫”作“雕斲”(62)⑦⑧⑨ 《毛诗注疏》,第126、407、1967,1967,409,407,335页。,无论“雕虫”还是“雕斲”,都反映了阮诗基本未对原典进行雕琢。这一情形随着诗歌语言的发展而逐渐改变。郭璞是东晋初年最重要的诗人(63)《文心雕龙·才略》:“景纯艳逸,足冠中兴。”《诗品》:“始变中兴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可见这是当时公认的评价。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701页;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第318~319页。,有“变创”(64)⑦⑧⑨ 《毛诗注疏》,第126、407、1967,1967,409,407,335页。之目,其诗用典已有显著的炼化,如《游仙诗》之一:“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65)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65页。前两句用《史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尝为漆园吏,楚威王闻庄周贤,使厚币迎,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子亟去,无污我。’”与《列女传》:“莱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阳。或言之楚,楚王遂驾至老莱之门。楚王曰:‘守国之孤,愿变先生。’老莱曰:‘诺。’妻曰:‘妾之居乱世,为人所制,能免于患乎?妾不能为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莱乃随而隐”(66)见《文选》李善注。五臣注文字略有差异,见下。刘跃进:《文选旧注辑存》,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4105页。之典。原文并无“傲”“逸”二字,“傲吏”、“逸妻”是作者根据故事的精神提炼出的新词,所以五臣注在引用原典后特意标注“故云傲吏”、“是曰逸妻”。(67)刘跃进:《文选旧注辑存》,第4105、4105页。后两句用《易》“九二,见龙在田。龙德而正中者也”、“羝羊触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之典,虽非严格对仗,但作者以同出《易》的“龙”“羝”相对,颇见文心。后世的诗法要求对偶的出句有典,对句也应有典,否则便是“缺偶”(68)旧题王昌龄《诗格》谓诗有“犯病八格”,“缺偶病二。诗中上句引事,下句空言也。”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诗上引事,下须引事以对之。若上缺偶对者,是名缺偶。”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0页;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200页。,这一意识已滥觞于此时。晋宋之交是中古诗歌的转折期(69)沈德潜《说诗晬语》:“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32页。,其时诗坛的代表人物谢灵运和颜延之精心熔铸典故,用词极为紧凑,如谢灵运《折杨柳行》:“否桑未易系,泰茅难重拔。桑茅迭生运,语默寄前哲。”(70)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6、228页。用典如《易》之《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泰》:“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系辞上》:“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谢灵运将前两典浓缩为“否桑”“泰茅”二词,又在“桑茅迭生运”一句中暗用“否极泰来”的易理,以“桑”“茅”代替“否”“泰”,推陈出新,将否泰相通的“套语”转化为师心独造的奇句。此诗用语过于迂曲,令人有“狮子搏兔”之感,在谢诗中并非上乘,但最能看出谢灵运对典故的雕琢。
用典对“套语”的超越体现在诗人加强典故与原文的联系和利用自己的语言组织典故两方面,前者扩展了诗意的纵深,后者则凸显了作品的独创性,使用典成为中国诗歌中极为重要的文学手法。明人许学夷认为“汉魏人诗,但引事而不用事”,“至颜、谢诸子,则语既雕刻,而用事实繁”(71)许学夷:《诗源辩体》,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4页。,以“引事”和“用事”形容两个时期用典的差别,极为精到。许氏此论仅指“事典”,我们可以单独抽出“引”与“用”二字,概括汉魏以来用典的发展:“引”是对文句的采撷,“用”则是对原文的深入汲取和对作品的有机融入。有趣的是,当“用”成为主流后,“引”反而给人以清新质朴之感,成为复古诗风的一大特色,如李白《前有樽酒行》:“美人欲醉朱颜酡。”几乎照搬《招魂》:“美人既醉,朱颜酡些。”(72)詹瑛:《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425~426页。大有飘洒恣意之妙,但细察此句,李白改“既”为“欲”,变“完成时”为“将来时”,一字之易,便觉精彩胜过原文,可见他似“引”而实“用”,不露痕迹,更显高明。随着用典技术的发展,外露的刻画渐为人所不取,“水中著盐”(73)蔡絛《西清诗话》:“作诗用事,要如释氏语:水中著盐,饮水乃知盐味。”《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493页。般的运化成为诗艺精妙的象征,但拒绝“套语”是中国诗歌一以贯之的理念。
三、 典故的衍生、扩展与转移
典故与原文紧密结合,使用典的标准日趋严格。蔡絛《西清诗话》:
熙宁初,张掞以二府初成,作诗贺荆公,公和曰:“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以示陆农师,农师曰:“萧规曹随,高帝论功,萧何第一,皆摭故实;而‘请从隗始 ’,初无‘ 恩’字。”公笑曰:“子善问也,韩退之《斗鸡联句》:‘感恩惭隗始’,若无据,岂当对‘ 功’字也?”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为倒置眉目、反易巾裳,盖谨之如此。(74)⑩ 《宋诗话全编》,第2487、2834、2950~2951页。
陆佃(农师)指出“恩从隗始诧燕台”用《战国策》“请从隗始”之典,但“恩”字不见于原文,王安石引韩愈、孟郊《斗鸡联句》释其来历。(75)此句应是韩、孟联句中的孟郊语。本作“受恩惭始隗”。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94页。这一故事反映了至迟在宋代,用典须字字有据已成为对佳作的隐性要求,同时说明所用对象不限于原始典故,还包括该典的用例。换言之,用例本身也成为该典的一部分。我们可将此现象称为典故的“衍生”。
试举一例。“团扇”是古典诗歌中的常见之典,源于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76)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17页。江淹拟之作《班婕妤咏扇》:“纨扇如团月,出自机中素。画作秦王女,乘鸾向烟雾。”(77)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9页。添入“秦王女乘鸾”的新要素。刘禹锡《团扇歌》:“团扇复团扇,奉君清暑殿。秋风入庭树,从此不相见。上有乘鸾女,苍苍网虫遍。明年入怀袖,别是机中练。”(78)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37页。在江淹诗的基础上,又加入“网虫”等意象。苏轼《和张耒高丽松扇》:“犹胜汉宫悲婕妤,网虫不见乘鸾子。”(79)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27页。所用班婕妤之典实已囊括江淹(“乘鸾”)和刘禹锡(“网虫”)的用例。“衍生”增强了典故的开放性,给予作者更大的选择空间,同时也鼓励了创新,避免了典故的“套语化”。
随着诗歌的发展,典故的范围也在扩张。周紫芝《竹坡诗话》:“东坡云:‘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80)⑩ 《宋诗话全编》,第2487、2834、2950~2951页。“熔化”便是将“不典”者化为典的过程。苏轼和黄庭坚皆以“熔化”著名,朱弁《风月堂诗话》:“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81)⑩ 《宋诗话全编》,第2487、2834、2950~2951页。许尹《山谷内集注序》:“其用事深密,杂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说,《隽永》、《鸿宝》之书,牢笼渔猎,取诸左右。”(82)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5页。可见两人都极大地扩展了典源。值得注意的是,苏、黄皆有“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之论——苏轼《题柳子厚诗》:“诗须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83)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09页。黄庭坚《再次韵杨明叔小序》:“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84)⑤ 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第303、339页。所指虽不尽同,但已足见两人在通过运化“故语”和“俗语”推陈出新上达成了共识(85)钱锺书《谈艺录》:“《后山集》卷二十三《诗话》云:‘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圣俞。答诗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耳。”,圣俞答书似已失传,赖后山援引,方知山谷所本。”则此言当为梅尧臣语。钱锺书:《谈艺录》(上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2页。。元好问批评当时诗人用典不问出处:“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86)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58页。“曲学”“小说”当即前举苏、黄所用“街谈小说”“鄙俚之言”“虞初、稗官之说”,可见其影响之大。
“以故为新”也意味着赋予旧典以新义。黄庭坚本人便擅此道,如《题石恪画尝醋翁》:“石媪忍酸喙三尺。”(87)⑤ 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第303、339页。用《庄子·徐无鬼》“丘愿有喙三尺”之典,原文以鸟之喙长比喻人之善辩(88)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50页。,黄庭坚则用来形容老妇尝醋时忍酸嘬嘴之态,极为生动。(89)任渊注引洪觉范《僧宝传》宝峰洪英禅师偈:“阿家尝醋三尺喙,新妇洗面摸着鼻。”(《僧宝传》传世本作“三赤喙”,当是字误。)似谓黄庭坚用偈语。但《僧宝传》成书于宣和六年,黄庭坚已去世,宝峰洪英与黄庭坚同时,难以判断先后。如黄庭坚确用其句,正可见其“以俗为雅”,且拈出“忍酸”,较原偈更加明豁。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第339页;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佛光大藏经·禅藏·史传部·禅林僧宝传(外三种)》,高雄:佛光山宗务委员会,1995年,第449页。这样的典义“转移”(90)罗积勇《用典研究》第四章第二节“转义式”分析了语义上的转移,专指通过比喻、借代、双关等途径生发的引申义,与本文所论文学内涵的转移无关。罗积勇:《用典研究》,第84~92页。在近代以来的古典诗歌中尤具现实意义。试举一例。苏轼《白水山佛迹岩》:“何人守蓬莱,夜半失左股。”传说浮山是蓬莱山的一部分,从海上漂浮而来,与罗山相合,形成罗浮山,苏轼用《易·明夷》“夷于左股”之典(91)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079页。,将蓬莱丧失浮山比作被人割去左股。苏轼此句虽造语隽拔,却无甚深意,作为典故使用范围有限。晚清以来国势颓靡,诗人转而用苏诗之典指代割地之耻,如丘逢甲《秋兴次张六士韵》:“两帝中央谋混沌,三山左股割蓬莱。”(92)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郑孝胥《十一月廿八日书事(俄人据旅顺)》:“蓬莱左股已遭钳,渤澥东门枉戒严。”《题吴干城观察边城筹笔图(吴已殁)》:“南藩隳缅越,左股折蛮瓯。”(93)郑孝胥:《海藏楼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4、80页。陈三立《雨中柬季词》:“犹阅斗蛟虬,益令饲豺虎。匈奴断右臂,蓬莱失左股。”(94)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李宣龚《芝罘杂诗(壬子)》:“蓬莱失左股,已破铁门限……何日张吾军,国耻长在眼。”(95)黄曙辉点校:《李宣龚诗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页。潘伯鹰《次韵华辅邀游北陵》:“大塚仍留皇太极,蓬莱左股待谁收。”(96)潘伯鹰:《玄隐庐诗》,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30页。其中邱逢甲一联出句用《庄子·应帝王》南、北海之帝共凿中央之帝浑沌(97)郭庆藩:《庄子集释》,第309页。之典,形容列强觊觎中国,对句以苏典表现《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两句都用旧典写新事,铢两悉称,极为贴切;潘伯鹰之句写“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隐去“割”字,可见该典的新义已深入人心。“转移”使典故得以随时代发展而产生新的内涵,体现了用典的“情境原则”。成功的“转移”甚至比原义更加妥帖,如上举之例,变神话描写为“国家叙事”,仙山“蓬莱”在新语境下成为“神州”的象征,“割股”则形象地表达了国土沦丧之痛,较苏诗更为深刻。
典故并不是封闭的“资料库”,而是能够通过衍生、扩展、转移等途径与时俱进的有机系统。无论哪种途径,都需要“熔化”的步骤,使其与诗歌固有的语言匹配,避免突兀与扞格。反过来看,典故本身也在影响诗歌的风格。王士祯《带经堂诗话》:
自何李、李王以来,不肯用唐以后事,似不必拘泥。然六朝以前事,用之即多古雅,唐宋以下便不尽尔,此理亦不可解。总之,唐宋以后事,须择其尤雅者用之;如刘后村七律专用本朝事,直是恶道。(98)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844页。
认为不必墨守明代前后七子(何李、李王)不用唐以后事的复古主张,但也承认六朝以前的典故可使诗歌呈现古雅的风貌,对唐宋以下之典则须分辨雅俗。王氏以诗人的直觉把握到其中的微妙之处,此“理”究竟是否“可解”,应如何解,将专文另析。
四、 余 论
综上所述,中国诗歌中的用典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就奠定了以情境为主导的原则。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用典超越了径引成语与史事的阶段,也从“套语”中挣脱出来。诗人由“引”而“用”,致力于以自己的语言“运化”典故,使其成为作品的有机部分,用典水平也成为衡量诗歌的重要指标。
新文化运动中,“用典”被当作传统文学的特点而成为批判对象。胡适在掀起文学革命的《改良文学刍议》一文中,提出了八条主张,第六条便是“不用典”。(99)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第319页。《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认为“用典”是“文言”的病灶所在:
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这都是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迭”、“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请问这样作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既不能表情,哪里还有文学呢?(100)此处所论兼包诗文。胡适留美期间曾在寄任鸿隽等人的诗中写道:“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可见诗文不分是其一贯态度。《胡适文集2》,第46页;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15—191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
这样的批判在某些方面确实切中了用典之弊,但有两点不能成立。第一,文学水平本有高下之分。传统诗歌中确有大量滥用典故的庸作,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一态势,但所谓“旧文学”的评价体系同样否定俗劣的用典。与胡适同时代的旧诗大家陈衍便对此深致不满:
自前清革命,而旧日之官僚伏处不出者,顿添许多诗料。“黍离麦秀”、“荆棘铜驼”、“义熙甲子”之类,摇笔即来,满纸皆是。其实此时局羌无故实,用典难于恰切。前清钟虡不移,庙貌如故,故宗庙宫室未为禾黍也。都城未有战事,铜驼未尝在荆棘中也。义熙之号虽改,而未有称王称帝之刘寄奴也。旧帝后未为瀛国公、谢道清也。出处去就,听人自便,无文文山、谢叠山之事也。(101)陈衍:《石遗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
陈氏批评部分遗老诗作滥用亡国之典,于当时的情境全不切合。所以,将用典不当之例作为批评用典的根据难以成立,即如上述,古典诗歌同样拒绝“套语”。第二,典故不是“死文言”,而是随时发展的。语言文字的作用固然在于“表情达意”,但是否使用日常语言不应是判断文学价值的标准,诗歌作为一种超越日常功用的文体更是如此,何况古典诗歌流派众多,并非都与日常语言隔阂。事实上,杜甫便以擅用俗语著名,张戒《岁寒堂诗话》:“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102)《宋诗话全编》,第3236页。宋诗尤其受到俗语、方言等日常语言的影响(103)周裕锴认为:“在宋诗人看来,当这些禅语、俗语侵入典雅精美的诗歌词语系统之时,立即以其非诗化的形态带来一种新鲜的刺激力,这一点恰巧可以医治传统诗歌陈言充斥之‘俗’。”周裕锴:《以俗为雅:禅籍俗语言对宋诗的渗透与启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而如前所述,“街谈市语”也可成“典”,“但要人熔炼耳”。
古典诗歌的典故在当代有着重要意义。相较于文章的“功能性”用典,诗歌的“文学性”用典更具激发情感的力量。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典故含蓄而隽永,其背后是深厚的历史沉淀,较直白的语言更能深入人心。在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当下,运用典故阐释时代精神,给典故注入新的含义,是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