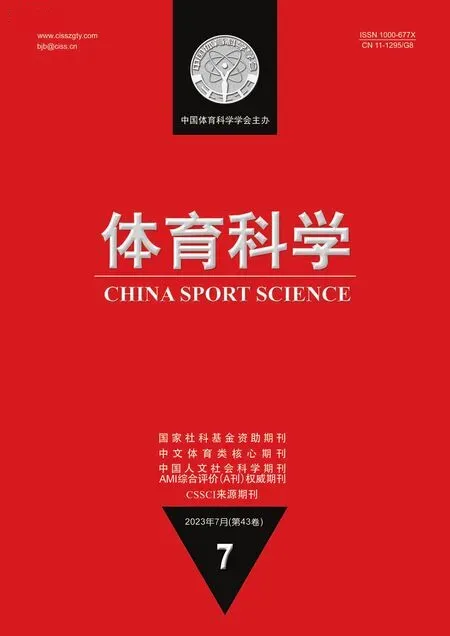轨迹与转折:中国优秀运动员成长历程研究
2024-01-04王富百慧陈小平
王富百慧,陈小平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61)
人们习惯性地用年龄去框定优秀运动员成长历程,将其描绘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分段特征,称之为“竞技运动年龄”或“运动寿命”(刘敬行,2016),并从生物学意义判断它们关联着人体机能变化以及最终表现出来的竞技能力(彭杰,2004)。尽管上述定义呈现了学者们对于年龄的多维理解,但无论是日历年龄、生物年龄、运动年龄的划分(彭杰,2004),还是从生命周期视角将7 岁、12 岁、18 岁、23 岁、30 岁左右作为进入基础训练、专项提高、最佳竞技、竞技保持、退役(刘敬行,2016)的门槛年龄,本质上都是在呈现运动员的成长轨迹。
对于优秀运动员而言,开始专业训练、首次参加重大比赛、首次获得金牌、首次突破世界纪录都是其成长轨迹中十分重要的转折事件,每出现一次转折都意味着职业生涯的转变。在多数人观念里,尽可能早地参加世界级比赛和尽可能快地获得金牌是决定优秀运动员培养走向的关键事件。这就意味着不能笼统地关注门槛年龄,而是要聚焦于成长轨迹中出现的每一次重大转折,关心何时发生转折,估算发生转折的可能性有多大,了解驱动每一次转折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竞技科学不是思辨,是需要通过实践检验和实证分析的科学范畴,如何通过实证研究去验证并解释每一次重要转折,是体育科学领域内的一个全新话题,也是竞技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看似差之千里的学科交叉融合的亮点。
优秀运动员的培养应走出传统的天赋与训练因素主导所带来的局限,将目光拓展到成长背景和社会情境之中,从过程视角去解读每一代优秀运动员成长的事件结构,总结影响每一次转折的关键要素。如果只将目光局限于训练科学,或认为门槛年龄比转折事件更具意义,那就忽略了培养路径与运动员个体成长轨迹协调发展的需要。只有充分论证上述问题,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描绘优秀运动员的成长轨迹,从中探寻不同时代运动员的成长规律,分析竞技能力转折的驱动因素,从一个新的视角思考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问题,这对于优化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培养效率更具指导意义。
1 理论综述
作为一种分析范式,生命历程理论对“时间观”有其独到的解释,并派生出了一套极具解释力的概念体系,它以轨迹、转折、持续去描绘在环境-个体的交互作用下个人发展的方向和路线,常用于规划多个生命轨迹之间的协调发展,明确诸如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什么年龄该成为怎样的角色等社会普遍认可的年龄规范。轨迹是一生中长期稳定的状态或角色,转折代表了轨迹方向的变化,持续则是轨迹中历次转变之间的时间跨度(包蕾萍 等,2006),为阐释优秀运动员成长历程提供了概念基础。如果将运动员职业生涯的全过程视为“轨迹”,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能力发展期、竞技提高期、竞技持续期、成绩反复期等,直至退役。其中,进入国家队、首次参加世界级重大比赛、取得最好成绩或夺得金牌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代表了“转折”,每次转折之间的过渡时间即为持续。不言而喻,转折是连结环境、机遇与个体主动性的节点,而持续则是以系统观呈现优秀运动员成长时序和发展动力的重要体现。
生命历程研究不仅能够在一个共同概念和经验性研究的框架内清晰呈现优秀运动员成长轨迹中的每一次转折及影响因素,还可以对成长历程的社会意涵做出解释。在已有研究中,运动寿命限定的门槛年龄表达了时间性特质,曾被简单直观地评判为一个运动员的发展潜力,认为中国优秀运动员竞技生涯的巅峰期往往只有短暂的几年,尽管近些年来有研究认为普遍存在的过早职业化和过早专项化训练正在无形中成为继年龄之外限制发展潜力的重要因素(米靖,2016),但在职业生涯中能否按照被期待的年龄规则发生转折一直是一代代优秀运动员不得不面对的“年龄困境”。
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来看,除却时间性之外每个运动员的成长轨迹还兼具时序性和个体化意涵。时序性强调每个阶段之间彼此关联且有序,例如,在能力发展期开始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训练干预,其时长显示了运动员对训练的敏感性,是影响竞技成绩提高速度的重要因素。虽然门槛年龄是参照生物年龄规则构建的序列选择过程,但也承载着每一个优秀运动员成长轨迹的重要转折,是标注其成长历程的“第二种时间”。在讨论个体化意涵时,与将优秀运动员成长成才归因于训练理念、训练方法、技术进步和环境改善等在内客观因素(陈小平,2018;黎涌明等,2020),以及意志品质、心理韧性、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运动智力、成功信念、人际关系等主观因素(韩学民 等,2009;张忠秋,2015)不同,生命历程研究更为关注时空变化造就不同代际之间成长轨迹的差异,强调每一个体必定是嵌套在培养环境之中的,不同时代、地域和启蒙条件下成长的运动员,其成长轨迹注定全然不同,这也就意味着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培养体系可能塑造了多元成长路径,个体禀赋和能动性可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近年来,有研究尝试从社会学范畴探讨奥运冠军的成长规律和时序特征,其开创意义在于试图针对优秀运动员成长成才提出带有普适性和规律性的实证结论(陈辉等,2022;胡海旭 等,2021;姜桂萍 等,2012,2013;刘叶郁等,2022;罗孝军,2013;孙国涛,2015;吴殿廷 等,2007;杨国庆 等,2021;杨世勇 等,2021;赵一平 等,2009),但止步于尝试通过共时性分析去解释奥运冠军成长成才的群像特质,未能从更宏大的理论视角去诠释优秀运动员成长历程中的轨迹与转折,进而总结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经验以及赋予其上的体育发展纵深。
事实上,以往研究中强调单个项目的技术能力和不同项目之间的技术能力差别,关注专项成绩增长并以年龄作为优秀运动员成长规律的判断依据,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但除此之外,应尝试从更为宏大的视野去思考,如何打破年龄制度对优秀运动员成长历程的限制,转而更加关注成长中的“事件”,将优秀运动员作为一个群体,从整体性视角考察每一代优秀运动员的成长轨迹和职业生涯的转折,通过与世界优秀运动员成长轨迹进行对比,思考在国际运动训练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的今天,中国优秀运动员培养亟需寻找的新思路。因此,研究将在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以成长轨迹中的重要转折为标志事件,描绘中国优秀运动员①研究中的中国优秀运动员是指参加过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三大国际赛事的中国籍运动员。竞技时间的分布特点并勾勒其成长轨迹,尝试从社会学视角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阐释我国优秀运动员的成长历程。
2 研究设计
2.1 分析方法
在以往优秀运动员成长时序特征的研究中,主要通过“平均值±标准差”的方式计算平均年龄,反映研究样本总体的年龄集中趋势或平均水平,简洁明确地体现了我国优秀运动员在不同成长阶段的年龄分布特征,呈现出一种“群体画像”。与之不同的是,本研究更为关注优秀运动员成长轨迹中的转折事件,以过程视角来分析优秀运动员的成长轨迹。研究将重点剖析3 个问题:优秀运动员更可能在哪个年龄发生转折、发生转折的可能性有多大、什么原因驱动转折的发生。本文将聚焦“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和“取得最好成绩”这两个关键转折事件②目前学术界较为关注开始专业训练的年龄,即“始训年龄”,本研究未将其纳入的原因在于:1)在数据的整理过程中发现,问卷中对参加哪种级别的训练视为专业训练的起点没有标准定义,导致数据中存在较多的错答和漏答;2)相较于始训年龄,研究更为关注能力发展期和竞技提高期两个持续期的时长和每个持续期起止转折事件的风险率。。“首次参加重大比赛”是指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世锦赛和世界杯,“取得最好成绩”定义为截至调查时点在上述赛事中取得的个人最好成绩。将“从出生到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和“从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到获得最好成绩”两个持续期分别定义为能力发展期和竞技提高期(图1)。

图1 理论框架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研究将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上述3 个问题。首先,利用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测算我国优秀运动员能力发展期和竞技提高期的持续时长,估算在某一年龄发生上述两个转折事件的风险率①风险率,是事件史分析方法的核心概念。在离散时间模型中,解释为每一个体将在某一特定时点发生事件的瞬时可能性,表示观测个体在某一状态持续时间t 后,在往后的单位时间区间内发生事件的概率。为便于理解,后文中除必要标记外,模型解释时“风险率”均以“可能性”代替。,描绘优秀运动员成长历程中的结构性差异。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是一种非参数估计的事件史分析方法,是生命历程研究中最为经典的研究工具。其计算原理为计算出每个时点关注事件未发生的风险率,然后将逐个风险率相乘得到存活至该时点的风险率,最终估计得到Kaplan-Meier 生存曲线。生存时间和风险率是该方法的两个重要概念,与平均值±标准差的计算意义不同,生存时间不单是通常意义下生物体的存活时间,而是泛指研究者所关心的某个现象的持续时间,在本研究中即为能力发展期和竞技提高期的持续时间。通过中位生存时间解释约有50%的优秀运动员在某个年龄完成了首次参加重大比赛或取得最好成绩,通过风险率测算优秀运动员在某一特定年龄发生转折的瞬时可能性大小,以Kaplan-Meier 函数图呈现优秀运动员的成长过程并比较分析结构性差异,用Logrank 法检验统计学差异。
其次,本研究重点解释发生转折的驱动因素,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中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分别解析驱动优秀运动员更早完成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和更快取得最好成绩的关键因素。由于参加比赛的时间取决于赛季安排和比赛计划,运动员参赛、获奖概率差异较大,风险事件并非在每一天都均匀发生,因此本研究适用于离散时间假设。利用离散时间logit 模型进行函数估计,通过最大似然值法使模型参数值是样本发生概率最大的值。计算公式如下:
P(t)为个体在时间t 上经历某事件的概率,值域在[0,1]之间。x1为独立于时间的变量,x2(t)为随时间变化的变量,ln 为自然对数。根据研究需要,等式右边既包括独立于时间的变量,也同时包括时变变量或以常数项a(t)随时间改变,每个值代表不同的时期。常数项通过一组虚拟变量估计。
2.2 数据来源
研究优秀运动员的成长轨迹并讨论其成长历程的重要转折事件需要纵向数据,但目前关于运动员成长历程的数据收集及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训练过程中持续追踪收集运动员成长历程的数据仍有一定困难。因此,为全面收集我国优秀运动员从后备人才到进入国家队的成长经历和培养环境资料,课题组于2021 年针对蹦床、举重、皮划艇、赛艇、射击、射箭、体操、田径、跳水、花样游泳、自行车等11 个运动项目的318 名国家队优秀运动员开展成长经历追溯性问卷调查,除个人基本信息和家庭状况外,全面回溯了其早期训练经历及培养环境、运动等级晋级历程、参赛情况、职业生涯重大事件及不同时期的训练方案等。
与追踪调查相比,追溯性调查可能会由于个别调查对象记忆模糊、主观回避造成一定程度的信息缺损、偏误,或者调查对象在调查时点尚未进入关注事件,导致数据的“删失”。本研究将通过事件史分析法有效规避以上问题,该方法的优势恰好在于可以有效处理固定观察期内尚未发生终点事件或无法明确其具体发生时间的样本数据,并在计算过程中处理删失问题,能够更为准确地呈现优秀运动员的成长轨迹并分析影响转折的因素。
2.3 变量测量
能力发展期是一个与时间相关的变量,表示从出生到首次参加重大比赛所经历的时长。在分析能力发展期的时长时,结局变量为首次参加重大比赛(0=未参加,1=参加),起点为出生年份,终点为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年份,参加比赛即为“风险事件”,未参加比赛为“生存”状态,能力发展期即为第1 个“生存时期”。竞技提高期表示从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到取得个人最好成绩所经历的时长,结局变量为取得最好成绩(0=未取得,1=取得),起点为运动员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年份,终点为截至调查时点获得最好成绩的年份,将个人获得最好成绩视为“风险事件”,未取得最好成绩为“生存”状态,竞技提高期即为第2 个“生存时期”。
在分析驱动转折的关键因素时,因变量为是否发生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即运动员在某年龄是否有过参赛经历,分为未参加和参加两种状态;是否取得最好成绩即运动员是否在某年龄参加上述赛事时取得个人最好成绩,分为未取得和取得两种状态。自变量包括主观胜任、成长经历和训练环境3 个维度。其中,主观胜任包括发展期望、对成功关键的认识和自信心3 个变量。成长经历包括伤病、早期专项化、比赛次数和专项训练时间4 个变量。以往研究表明,运动员成长环境中教练方式和科技保障是促进其快速成长的两个重要因素(黎涌明 等,2020),因此,在问卷中设计与教练交流沟通的频率和有无训练监控两个问题来测量训练环境的作用。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项目类型及持续期对数4 个变量(表1)。由于本次调查覆盖项目类型较多,将重点聚焦体能类项目和技巧类项目,体能类项目包括田径、自行车、赛艇、皮划艇,技巧类项目包括蹦床、体操、花样游泳、跳水。持续期对数分别为能力成长期时长和竞技提高期时长的对数。

表1 变量定义与赋值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Assignment
3 研究结果
3.1 我国优秀运动员成长历程中的两次转折特征
3.1.1 能力发展期的Kaplan-Meier风险分析
如图2 显示,横轴为能力发展期持续时间,纵轴为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风险率,即参赛风险函数值。我国优秀运动员能力发展期平均为14.74 年,中位生存时间为15 岁,表明半数优秀运动员在15 岁时完成首次参加重大比赛(表2)。Kaplan-Meier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我国优秀运动员在10 岁前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为4.11%,在15岁前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为64.38%,在20 岁前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为97.26%。我国优秀运动员能力发展期时长约为15~20 年。

表2 不同人群首次参加重大比赛风险根据K-M方法的时间分布情况Table 2 Time Distribution of Risk for Different Populations Participating in Major Competi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Based on K-M Method

图2 我国优秀运动员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风险K-M函数图Figure 2. K-M Function Diagram of the Risk of Chinese Elite Athletes Participating in Major Competi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在能力发展期,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年龄存在性别差异。女优秀运动员的能力发展期平均为13.97 年,中位生存时间为14 岁。男优秀运动员的能力发展期平均为15.45 年,中位生存时间为15 岁(表2)。如图3 显示,女优秀运动员10 岁前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为5.71%,15岁前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为74.29%,20 岁前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为100%。男优秀运动员10 岁前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为2.63%,15 岁前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为55.26%,20 岁前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为94.74%。通过Logrank 检验进一步验证了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性别差异,男优秀运动员在各个年龄阶段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均低于女优秀运动员。上述结果证明,男优秀运动员不仅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年龄大于女优秀运动员,并且在各年龄阶段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也小于女优秀运动员。

图3 不同性别优秀运动员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风险K-M函数图Figure 3. K-M Function Diagram of the Risk of Different Genders Elite Athletes Participating in Major Competi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在能力发展期,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年龄存在代际差异。“80 后”“90 后”“00 后”优秀运动员的能力发展期平均为14.5年、14.22年和13.58年,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在14岁、13 岁和12 岁(表2)。在15 岁前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分别为50.00%、51.11%和88.46%(图4)。通过Logrank检验发现,越年轻世代的优秀运动员首次参加重大比赛时间越早,在青少年时期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大于以往世代。2000 年以后出生的优秀运动员中,15 岁之前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最大。

图4 不同代际的优秀运动员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风险K-M函数图Figure 4. K-M Function Diagram of the Risk of Elite Athletes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s Participating in Major Competi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为呈现不同类别项目的优秀运动员成长轨迹的差异,研究进一步针对技巧类项目和体能类项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技巧类项目和体能类项目中的优秀运动员能力发展期平均为13.67 年和15.21 年,中位生存时间为分别为14 岁和16 岁(表2)。技巧类项目的能力发展期短于体能类项目,其中,技巧类项目的优秀运动员在10 岁前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为6.38%,15 岁前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为68.09%,20 岁前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可能性为100%。体能类项目的优秀运动员15 岁前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为57.69%,20 岁前完成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可能性为92.31%(图5)。相较于技巧类项目而言,体能类项目的优秀运动员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年龄更大,且各年龄段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更小。
3.1.2 竞技提高期的Kaplan-Meier风险分析
自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开始,我国优秀运动员在1 年内获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可能性为24.1%,在2、3、4 年内获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可能性分别为34.5%、55.2%和72.4%,在5 年内获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可能性为89.7%。优秀运动员从体坛新秀到在国际大赛中斩获个人最好成绩的平均时间为3.45 年,有50%的优秀运动员在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后的3 年内获得个人最好成绩,整体而言获得个人职业生涯最好成绩的黄金时期在其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后的5 年之内。其中,以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后第1 年的培养效率最高,15 岁前完成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优秀运动员在1 年内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可能性大幅增加(图6)。

图6 优秀运动员取得最好成绩风险的K-M函数图Figure 6. K-M Function Diagram of the Risk of Excellent Athletes Achieving the Best Performance
通过Logrank 检验发现,在竞技提高期中,运动员取得个人最好成绩在性别方面无显著统计学差异,但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竞技提高期的第1 年是女优秀运动员取得最好成绩的黄金期,可能性为30.8%;2)在竞技提高期的前2 年内,女优秀运动员取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大于男优秀运动员;3)男优秀运动员在竞技提高期的第3~4 年将进入取得最好成绩的黄金期,3 年内取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为62.5%,4 年内取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为93.8%;4)总体上,男优秀运动员的竞技提高期平均为7 年,女性则平均为11 年。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男优秀运动员具有后程优势且竞技能力提高速度快于女优秀运动员(图7)。

图7 不同性别优秀运动员取得最好成绩风险的K-M函数图Figure 7. K-M Function Diagram of the Risk of Different Gender Excellent Athletes Achieving the Best Performance
我国优秀运动员竞技提高期呈现代际差异,表现为越年轻世代的优秀运动员从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到取得最好成绩的周期越短,“90 后”在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后的1 年内取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为17.4%,“00 后”在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后的1 年内取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提升至60%。代际之间的竞技提高期逐渐缩短,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培养效率正在逐步提升(图8)。

图8 不同代际优秀运动员取得最好成绩风险的K-M函数图Figure 8. K-M Function Diagram of the Risk of Excellent Athletes Achieving the Best Performance across Different Generations
通过对比发现,体能类项目优秀运动员的平均竞技提高期比技巧类项目长。其中,技巧类项目的优秀运动员成绩黄金期更短,集中出现在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后的第3年,3 年内取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为60.0%,4 年内取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为90.0%,5 年内取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为100%。体能类项目的优秀运动员竞技提高期持续时间更长,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后的第5~7 年是其成绩黄金期,1 年内取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为31.6%,2 年内取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为42.1%,5 年内取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为65%,10 年内取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为95%(图9)。

图9 不同项目类型的优秀运动员取得最好成绩风险的K-M函数图Figure 9. K-M Function Diagram of the Risk of Excellent Athletes Achieving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Events
3.2 我国优秀运动员成长历程中两次转折的驱动要素分析
3.2.1 影响能力发展期内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风险因素
如表3 所示,与模型1 相比,模型2 的解释力得到提升,其结果表明胜任因素、训练环境、成长经历均对于缩短优秀运动员的能力发展期、尽快实现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加速早期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3 能力发展期影响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风险因素Table 3 Risk Factors Affecting First-Time Participation in Major Competitions during the Ability Development Period
在早期培养过程中,胜任因素对于运动员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运动员主观上有明确发展期望对缩短能力发展期有着显著正向作用。相比于没有目标,自我发展期望越高的运动员早参赛的可能性越大。参加训练之初即有明确奥运金牌目标的运动员,其参赛的可能性平均增加70.4%。在成功关键因素认识的引导方面,认为先天禀赋和后天意志更为重要的运动员,其参赛的可能性比仅依赖训练环境的运动员分别增加80.2%和23.3%。建立自信对于缩短能力发展期具有正向作用,始终保持自信的运动员参赛可能性更大。
能力发展期内的成长经历也对优秀运动员成长历程有重要影响。研究结果显示,6~8 岁时开始专项训练其早参赛的可能性将平均减少45%;9~12 岁时开始专项训练,其早参赛的可能性平均减少18.8%。与此同时,每周专项训练时间每增加1 小时,早参赛的可能性平均减少23.2%。能力发展期开始专项化训练并不利于提升培养速度,可能会对运动员在成长历程中以合适的年龄及时进入竞技提高期起到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
这一时期的训练环境也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在能力发展期内学会与教练沟通交流将有助于提高运动员的成长速度。每次训练都与教练进行讨论的运动员早参赛的可能性平均增加51.6%。此外,早期阶段在有训练监控的环境中训练对于缩短培养周期具有正向作用,有训练监控的运动员早参赛的可能性平均增加77.2%。
3.2.2 影响竞技提高期内获得最好成绩的风险因素
与能力发展期不同,竞技提高期内运动员的主观自我认同作用不再发挥主要作用,训练成为影响成绩的关键要素(表4)。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在夺取奥运金牌上有明确目标的运动员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可能性平均增加28.8%,但竞技提高期内的训练时间、伤病情况和参赛数量均对能否尽早获得个人最好成绩有显著影响。其中,每周专项训练时间每增加1 小时,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可能性平均增加51.2%;每增加1 次世界级大赛参赛,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可能性平均增加15.9%,但一旦出现伤病,取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将平均减少25.5%。除训练经历外,训练环境也对竞技能力提升有重要影响。与能力发展期相同,竞技提高期与教练保持必要的、精简的、适当频率的沟通对运动员取得个人最好成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每次训练或成绩不理想时都与教练保持沟通的运动员获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可能性增加80%以上,即便每周仅保持有限次数的沟通,获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也将有所提升。竞技提高期的训练监控对提高运动员个人成绩的作用同样显著。与没有训练监控相比,在训练时有训练监控的运动员获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可能性增加60.2%。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员在进入竞技提高期后能够正确认识提高成绩的因素也十分重要。研究结果显示,与认为个人身体条件对提升成绩更为重要的运动员相比,认同教练水平、训练负荷、有无伤病等训练条件更为重要的运动员,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可能性平均增加18.5%,认同训练设备、场地、科研、康复等保障性条件更为重要的运动员,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可能性平均增加70.2%。此外,进入竞技提高期后,年龄成为影响成绩的重要因素,对从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到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周期长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每增加1 岁,获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平均减少44.2%。

表4 竞技提高期影响获得最好成绩的风险因素Table 4 Risk Factors Affecting Achieving the Best Performance during the Competitive Improvement Period
4 分析与讨论
身处某一社会结构中的个体,生命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有被设计的角色规范并承载着相应的年龄制度,这种蕴含着丰富社会意义的时间被格伦·埃尔德(2002)定义为“生命历程”,它对“时间”意涵的阐释成为社会学探讨轨迹与转变时最主要的研究范式(郑作彧 等,2018),为本研究建立起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以时间性、时序性和个体化共同建构的成长秩序,标注了每一名优秀运动员成长的轨迹与转变。以往研究更多聚焦于时间性,对时序性和个体化讨论尤显不足,这也成为本篇探索性研究的出发点,除却对我国一代代优秀运动员群体画像的描述之外,探讨对于未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更为关键的2个问题:如何通过轨迹中的转折去找寻优秀运动员成长过程中的普遍规律,如何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去解释这一规律。
研究发现,我国优秀运动员职业生涯的能力发展期平均为14.74年,竞技提高期平均为3.45年。其中,技巧类项目的优秀运动员能力发展期平均为13.67 年,竞技提高期约为3年。体能类项目的优秀运动员能力发展期平均为15.21年,竞技提高期约为5~7 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体能类项目优秀运动员达到竞技黄金期的年龄约为20~22 岁,这一规律与国际相关研究结论较为一致。例如,根据哈特曼的长期跟踪研究,德国男子公开级赛艇运动员达到世界冠军的平均年龄为23.5 岁,世界网球排名前10 名的男、女选手从开始打职业比赛到进入前10 名的平均时间分别为4.4 年和3.3 年。如果把他(她)们开始参加职业比赛作为运动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么基本在3~4 年的时间里达到职业生涯的竞技高峰(top 10),此后进入高水平保持阶段。
与此同时,我国优秀运动员的成长轨迹呈现强结构性、持续稳定性和相互关联性的规律特点。具体表现为:
1)无论哪个世代,成长时序的结构性日益增强。即越年轻世代的运动员,能力发展期和竞技提高期越短,意味着他们越早经历重要的转折事件。“00 后”运动员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平均年龄为13.58 岁,相较于“90 后”和“80 后”分别提前了0.64 岁和0.92 岁。“90 后”在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后的1 年内取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为17.4%,“00 后”在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后的1 年内取得最好成绩的可能性提升至60%。这可能与科学选材与训练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关,尤其是2000 年后世界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明显提升,新理论、新方法不断改变,甚至颠覆传统的训练,以此提高了年轻一代优秀运动员的训练质量和效益。
2)无论哪个发展阶段,成长的性别差异均呈现持续稳定的特点,即女运动员的先发优势明显,男运动员的后程能力较强。能力发展期内女优秀运动员的成长速度快于男优秀运动员,且在各年龄阶段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可能性也高于男优秀运动员。但在竞技提高期,女运动员斩获成绩的优势年龄处于低龄段,男运动员的成长速度更快,竞技后备能力在这个时期得以发挥,在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后的第3~4 年普遍进入取得最好个人成绩的黄金期。整体看来,男优秀运动员在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后更快取得个人最好成绩。
3)无论成长速度如何,职业轨迹中每个转折之间都相互关联。尽管每个运动员以相似的顺序和不同的速度经历转折,但成长路径的整体结构是嵌套且彼此影响的。例如,15 岁前完成首次参加重大比赛的优秀运动员在1 年内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可能性大幅增加,且获得个人职业生涯最好成绩的黄金时期更可能出现在其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后的5 年之内。
在讨论影响职业生涯中两次重要转折的关键要素时发现,运动员在不同成长阶段培养的重点应有所不同。能力发展期内驱力培养和训练经历对能否尽早实现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参加训练之初即有明确奥运金牌目标的运动员,其参赛的可能性平均增加70.4%,始终保持自信的运动员参赛可能性更大。但在进入竞技提高期后,专项训练和参赛经历成为尽早取得最好成绩的关键因素,如专项训练时间每周增加1 小时,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可能性平均增加51.2%;每增加1 次国家级和世界级大赛参赛,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可能性平均增加15.9%。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培养一名优秀运动员,除了施加合理的训练手段之外还应“因势利导”和“顺势而为”。
所谓“因势利导”就是在基础能力培养阶段,应着重关注对人的培养。不应通过人为塑造的“年龄层级”试图以一个恰当的时间安排去设计运动员成长的轨迹和转变,而是培养其学会设计目标、正确认识成功的关键因素并建立对未来职业发展前景的自信。在迈入职业化训练早期,培养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与进行科学训练几乎具有同等价值,对于运动员终身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优秀”与“一般”的差别之所在。“顺势而为”则体现在训练方法和手段要顺应成长过程中每个阶段的生长发育特点。在本应培养基础能力的时候不必过早开展专项训练,本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专项训练在竞技提高期可以发挥正向促进作用,但在能力发展期则发挥一定程度的负向作用,即每周增加1小时,早参赛的可能性平均减少23.2%。
值得注意的是,客观上,科技保障和“教训关系”对于转折的驱动作用贯穿于运动员职业轨迹的各个时期。训练监控、教练互动以及保障条件对于缩短能力发展期和竞技提高期均发挥了正向作用。主观上,运动员对科技保障和“教训关系”的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成才的速度。例如,认同训练设备、场地、科研、康复等保障性条件更为重要的运动员,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可能性平均增加70.2%,提示仅在能力发展期和竞技提高期提供科技保障和建立良性“教训关系”是不够的,还应着重加强运动员对于二者重要性的认识和认同,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
5 启示与思考
由本研究的结论引申3 点思考:1)中国优秀运动员的成长轨迹与世界同类项目、相同级别运动员呈现相似的规律,主要表现为在相近的年龄区间内完成首次参加重大比赛并尽快取得个人最好成绩。如世界排名前8 的高水平短跑运动员能力发展期平均为20.75 年,竞技提高期平均为5.75 年。但从国际短跑运动员的成长规律来看,以速度和爆发力为主要竞技能力的短跑项目竞技水平高峰应该出现在20~25 岁,与之相比,我国短跑名将苏炳添的成长可谓是“大器晚成”,分析发现,苏炳添的能力发展期为20 年,基本符合世界短跑优秀运动员前半程的成长规律,但竞技提高期却长达12 年,且在该时期的后半段才出现成绩显著提升,26 岁时突破10 秒达到世界优秀水平,29岁以9.91 秒平亚洲纪录,32 岁在东京奥运会上以9.83 秒创造了新的亚洲记录(图10)。尽管短跑在我国是非优势项目且苏炳添自身也具有独特性,上述差异不足以代表我国短跑优秀运动员成长轨迹的整体规律,但苏炳添在竞技能力自然发展的最佳时期出现“错位”现象却值得深入思考,这是否源于我国短跑在高水平训练阶段出现问题,仍需从更为深入的研究中获得可靠证据,避免更多优秀运动员的成长轨迹经历“大器晚成”。

图10 东京奥运会进入男子100米决赛的高水平运动员成长时序期Figure 10. Growth Timeline of High-Level Athletes Entering the Men’s 100 m Final at the Tokyo Olympics
2)我国优秀运动员成长过程中蕴含着相似的“年龄制度”,对其成长与成才过程进行了刻画。每名运动员都在各个相似的年龄区间,积极争取身份角色的转变,成长轨迹成为一个可以用时间测量的过程和一种同质化、标准化并可预见的时序过程,使得职业生涯可以被理性的规划、划分和排序。而在此过程中,教练员以分类者和调控者的身份出现,对每个阶段角色身份的转变进行标准化,为每一名运动员的成长规划相似的轨迹,汇聚成为国家选材与培养模式的一部分,最终成为被普遍认可和接纳的“年龄制度”。不言而喻,从培养角度而言,以“年龄制度”作为评价运动员与培养阶段匹配度的重要标准,既表达了对培养路径和方向的规定,同时也呈现了一种期待。这种成长模式孵化于中国举国体制的培养环境之中,便于以可评估、有效率方式来组织和管理运动员,使其成长轨迹的每个阶段都可以清晰地加以区分,通过理性的时间规划来调控运动员成长轨迹中的角色转变,提升了成才的可预测性。但对于每名运动员而言,在其成长历程中的每一次转折都不能背离这一时间节奏,一旦背离将意味着脱离培养期待,可能背负着来自客观评价的不利影响。本研究并不否认这一时间节奏的合理性,但对隐含在节奏之中的筛选和淘汰机制是否适应运动员的成长规律存疑,因为本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年龄在进入竞技提高期后才成为影响转折的重要因素。这是否意味着在能力发展期可以不必过度关注年龄,而是要强调基础能力的培养,进入竞技提升期后再重视年龄门槛的作用,根据生理发育进程设计具有年龄门槛特征的培养和训练方案。
3)对于优秀运动员的培养目标应从“冠军”转向“人”。在训练科学的传统思维内,学者们对于天赋、机能、训练等生物驱动的重视远胜于社会性视角的分析。每名运动员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培养制度却用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筛选标准来框定每个人的发展路径,使得同一时代背景和相似培养环境下的一代运动员具有整齐划一的成长历程。在个人成才轨迹中忽视了尊重个性,对一代人成长规律的发掘又缺少共性,这是目前我国优秀运动员选材与培养过程中呈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应从优秀运动员个体成长轨迹和成绩期待两个层面看待培养问题。尽管从生物学角度上看,在人体机能最佳的阶段给予运动员恰当的训练以促进其成才是关键期的意义所在,但一直以来缺少一个视角去探讨如果错过了转折关键期,那么错过的是一种期待还是成才的能力和动力?对于这个问题显然无法仅从生物驱动角度去解答,应从个体和社会进行综合考量。对于一名优秀运动员而言,尽管运动生涯的持续期与生理年龄相关,对每个阶段竞技能力评价不可避免的受制于年龄制度,但通过不断反思回溯自己的训练历程,以科学训练、有效规划和主体决策能动地创建更长的竞技持续期,这本质上是在生理年龄的范畴下、在年龄制度的框架内,个体对“年龄困境”的突围和面对成绩期待时所展现的主体选择和表现能力。而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对人体机能的无尽探索正在拓展代际间竞技时长的跨度,提高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科技含量,提高运动员的成材率,也为优秀运动员成长轨迹走出有限时间困囿提供了客观条件。虽然上述研究过程更为复杂和系统,但这个视角无论对于运动员个体的发展决策还是中国竞技体育培养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尽管本研究针对优秀运动员成长历程展开了深入讨论,但仍有3 个问题尚未触及。其一,越来越多的大龄优秀运动员开始挑战年龄制度的边界,但这一越界并未成为主流,绝大多数运动员依然沿着年龄制度结构成长,使得最佳竞技状态持续期更长且稳定,但这本质上不是制度结构是否适用的问题,而是在科技助力下,从原有制度结构转向一种新制度结构的问题,暂且称之为年龄的“再制度化”。由此引申思考:他们如何突破现有培养环境和制度结构的限制,形成新的成长历程实践,这一实践如何调适和改良制度化结构,这或许是未来培养体系应改革的方向。其二,每一代运动员都历经共同的制度化结构,他们的成长历程会呈现一定程度的重合和同质,但每个时代的制度化结构都对应着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期待,不同代际之间的成长历程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意味着同代中的分化和代际间的差异将可能成为研究优秀运动员培养模式的重要突破口,着眼于分化之中的关键要素和差异之间的进步要素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其三,胜任因素是与制度化结构并驾齐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对于优秀运动员来说可能扮演着内驱力和人生规划的双重作用。虽然成长轨迹中的转折并非偶然而是呈现一种制度性,但通过经验研究探析胜任因素对制度化的“越轨”路径及其未来可能衍生的新结构去向,廓清构成每一代优秀运动员成长历程的所有决策序列背后的规则结构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数据可获性不足和研究视角局限是导致以往相关研究捉襟见肘的两个关键因素。研究优秀运动员成长的轨迹与转折需要追踪数据,但目前我国对于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竞技体育发展规律尚处于起步阶段,收集每一名优秀运动员从开始训练到职业退役的“成长史”数据仍具有一定困难。传统的运动员选材与培养研究更加重视实验研究和训练实践,相比较而言,缺乏有关选材与培养的常规性、专业性调查,更没有长期追踪调查数据库,很多数据仍处于一种零散的、局部的、个体性的状态,运动员成长数据收集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相关体育部门如何发挥组织优势,共同开展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建立优秀运动员成长数据库,也是未来体育领域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只有足量的数据作为支撑,才有可能将理论和思辨操作化和实践化,从历史、社会、个体三维视角去观察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历程,了解每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成长轨迹,分析其成才的动力要素,熟知一代又一代优秀运动员的培养路径和发展轨迹,剖析中国竞技体育在选材和培养中的问题,并提出更具科学性、普适性、规律性的理论,为体育发展赋予历史和时代的纵深感。
尽管举国体制形塑了优秀运动员成长历程的制度性结构,但这一制度性结构是与时俱进的,我们应以更为深邃的思考和多维的视角去观察、探讨与解释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改变培养模式的目的就是要呈现一个超越传统制度化结构的、新的成长过程曲线,意味着未来对于运动员的培养,应首先着眼于对成长历程意义的理解,并将每一次驱动转折的关键要素教育内化为成长过程,而不仅仅是以服从和筛选为基调的金牌取向,这也将成为除年龄制度之外的一个对优秀运动员成长成才十分重要的意义结构。培养模式的创新与改革应基于这样一个底层逻辑,即“成长历程应成为制度作用和主体实践共构下的一个整体,它是既可以被客观规划,也需要实践者的主观期待”。因此,从后备人才选拔的那一刻开始,就不应将运动员困囿于筛选机制之下,过于强调成长历程中所谓的年龄门槛,而应探索建立一个多元、科学且相对稳定的制度结构,并科学设计驱动每一次转折的关键要素,激发每一名运动员对于自身的发展期待,通过制度与行动共同构筑的成长历程将更具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