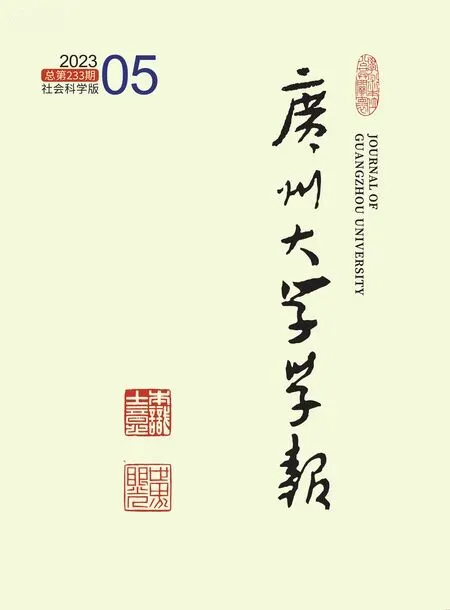以色列建国叙事与集体记忆
——重读伊兹哈尔的《黑泽废墟》①
2024-01-03钟志清
钟志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以色列建国与希伯来语复兴、大屠杀一样,在民族构建进程中占据着制高点之位。回顾历史,尽管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从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论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即后来的犹太民族国家,但直至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宣布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即联合国181号决议)才有可能将他们的理想化作现实。决议限定了英国结束其在巴勒斯坦地区委任统治的期限,更重要的是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阿拉伯和犹太两个国家。这一决定在犹太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多年颠沛流离且历经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将这一决定视为神迹以及全球正义体现的标志,但阿拉伯人却将其视为公然的错误和强制行为,号召通过武装行动来加以抵抗,从此,针对犹太人的袭击甚至屠杀此起彼伏。[1]1948年5月15日,就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宣读《独立宣言》并宣布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埃及、外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五国阿拉伯军团联合起来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在以色列方面看来,这场战争是捍卫主权的战争,官方称之为“独立战争”;但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眼中,这场战争就是一场“大灾难”(Nakbah)。这场战争十分惨烈而艰苦,从交战结果上看,阿以双方均伤亡惨重。以色列阵亡人数约六千人,约占当时国家人口的百分之一;阿拉伯方面阵亡人数约为以色列的二点五倍。战争一直持续到1949年3月,最终以色列险胜。
早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之际,现代希伯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一直在建构着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历史与记忆。当然,亲历战争的一些作家中不乏歌颂以色列士兵的英雄主义之人。但意味深长的是,也有一些作家并没有大肆歌颂以色列“以少胜多”战胜阿拉伯军团的战争神话,目睹正在阿拉伯废墟上崛起的新建国家,尤其面对大批流离失所的阿拉伯难民时,他们不免遭受良知的拷问。[2]在这批作家中,萨迈赫·伊兹哈尔(S. Yizhar)极富代表性,他在1949年5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黑泽废墟》[3]描写了以色列士兵对阿拉伯村民的驱逐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自省,并把时下巴勒斯坦难民的苦境与历史上犹太人的受难经历建构关联,在以色列的集体记忆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就在近期美国布兰戴斯大学舒斯塔曼以色列研究中心(Schusterman Center for Israel Studies)举办的以色列研究暑期班上,奥尔珈(Olga Gershenson)等学者在谈及以色列集体记忆这一话题时,均援引《黑泽废墟》,认为无论小说原作还是影片均占据了经典地位。
一、个体记忆的塑形:“我”与“他者”
《黑泽废墟》是一篇现实主义小说。它以作家本人的战争体验为原型,带有强烈的个体记忆色彩。②叙述人“我”是一个年轻的以色列军事情报官员,可被视为战争期间一类以色列士兵的代表。这类士兵虽然参与了战争,但能够对战争中的敌对方,即我们所说的“他者”,或者说处于弱势地位的阿拉伯人表现出同情与关怀。这种现象,尚未引起国内读者的广泛关注。
形成伊兹哈尔关怀“他者”理念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其家庭背景有关。伊兹哈尔原名伊兹哈尔·斯米兰斯基(Yizhar Smilansky),是苏联新移民的后裔,出生在以色列中部雷霍沃特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伯祖摩西·斯米兰斯基 (Moshe Smilansky)秉承社会主义理想抵达巴勒斯坦,主张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和平共处,是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最早表现阿拉伯问题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父亲杰夫·斯米兰斯基(Zeev Smilansky)既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又从事写作,还在农业聚居区务农。杰夫既像当时的一些犹太农场主那样在果园里雇用阿拉伯工人,又坚信做“希伯来劳动者”是犹太人回归土地的一个重要因素。[4]与其伯祖和父亲相对,其舅约瑟夫·维茨(Joseph Weitz)则主张从阿拉伯人手里赎回土地。几位长辈尽管对待阿拉伯人的态度不尽相同,但都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做法感到震惊。[5]在这样家庭长大的伊兹哈尔自幼把阿拉伯人视为巴勒斯坦风光天然的组成部分,他称在看风景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风景中的阿拉伯人。[5]也就是说,他不仅意识到以“我”为代表的犹太共同体的存在,也意识到作为“他者”的阿拉伯人的存在,尤其承认阿拉伯人与土地、与风景的自然和谐关系。“我”与他者的这种关系,就像列维纳斯所言:“他者”不再存在于主体之外。“自我”与“他者”并非相互游离,而是相互交织,[6]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以奥兹为代表的以色列左翼人士所倡导的,以及与我们国家所支持的“两国论”主张一致。这些理念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构思。在《黑泽废墟》这篇作品中,他既写出了战争的惨烈以及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也展现出以色列士兵作为“闯入者”破坏了阿拉伯人与巴勒斯坦自然环境水乳交融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负疚与道德危机,甚至批判了以色列士兵在参与军事行动时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带来的灾难。
小说的中心事件写的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士兵征服、毁坏阿拉伯村庄,并驱逐其村民的军事行动。大致情节是,以色列士兵奉命来到一个要被清空的阿拉伯村庄时,村里大多数年轻人都已经转移到了周围山上,留下的主要是老人、体弱者、妇女和儿童。士兵们按照战前命令炸毁房屋,将村庄夷为平地。在书写策略上,小说并没有直接切入以色列士兵攻占阿拉伯村庄这一中心事件,而是首先铺排了叙述人“我”及其士兵群体在执行“焚烧-轰炸-关押-装载-运送”任务前夕的精神状态,从“兴高采烈”地像前去郊游到经历紧张焦虑、单调乏味的漫长等待之后变得极度无聊,想要回家,想要发泄,其泄愤的对象不仅有毛驴、骆驼等牲畜,还有手无寸铁的阿拉伯村民。
小说描写了“我”所代表的以色列士兵和阿拉伯“他者”的几次交锋。这些交锋不仅是推动情节演绎的手段,而且也是展示以色列士兵心灵冲突的途径。以色列士兵与阿拉伯人的交锋既包括与阿拉伯个体的相遇,又包括同阿拉伯群体的相遇。但两种情境中均表现出弱者在强权面前的无助与无奈。更进一步说,“我”与“他者”之间的交锋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体现出一种复杂与多元的形态。小说既体现出战时期间以色列士兵的心灵冲突,也揭示出阿以关系的复杂性。小说中的“他者”——阿拉伯村民一律没有名字,而是用老人、哭泣的女子、怀抱婴儿的女子、盲人、瘸子等一些象征性的符号代替,这些人用眼泪、恳求、谦卑、屈从、哀嚎来回应打破他们宁静生活的以色列士兵,但基本上没有任何反击。 这样的书写策略透露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要展示以色列士兵的英雄主义,而是把关注视点投向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他者”。
第一个与以色列士兵相遇的阿拉伯人是个白胡子老人,他对以色列士兵毕恭毕敬,十分顺从,希望以色列士兵允许他在离家时带上驮着他全部家当的骆驼。而以色列士兵在对待阿拉伯人的态度上却不尽相同。叙述人和一些士兵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对老人表示同情,建议直接放走老人;但以军官摩西和阿里耶为代表的另一些士兵却认为,如果双方角色发生置换,那么阿拉伯人肯定会置犹太人于死地,不想轻易放过阿拉伯老人,让阿拉伯老人在活命与骆驼之间做出选择。这里,以色列军官既是攻占阿拉伯村庄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又是以色列集体阵营中的代表,强者的化身。他的态度喻示着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对阿拉伯人的强硬态度。文本中温和派与强硬派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以色列国家内部在巴以问题上所持有的异见。这样的争论基本上在以色列政治话语中延续了七十余年。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出,在阿以问题上,许多人依然坚信只有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
如果说这位白胡子的老阿拉伯人尽管恭顺但敢于向以色列人提出要求的话, 那么多数阿拉伯人则表现出一种沉默,其中包括脸庞枯槁、身上散发着臭气、因害怕而默不作声、躺在地上的老妪;闻风丧胆的阿拉伯男子;聚集在无花果树下一言不发、只是偶尔发出叹息的男子,以及默默哭泣的女子;水坑旁静静坐在那里的盲人、主动选择蹚水走过水坑的瘸子;等等。
与第一个老人相比,这些阿拉伯人表现出恐惧、怯懦、悲恸,甚至讨好以色列士兵。比如,一个阿拉伯男子在以色列士兵面前十分恐慌,身体几乎无法动弹,只好朝以色列士兵露出充满歉意的、无意义的微笑。另有一个老人则用一套祝福仪式来欢迎以色列士兵,甚至向自己的同胞讲述以色列士兵的优点,等等。凡此种种,均表现出弱者在强权面前的无能为力。这些个体与集体形象隐喻着失去土地、失去财产、淡出中心与历史舞台乃是1948年战争期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共同遭遇。
“他者”的无助与呐喊唤醒了叙述人“我”的伦理认知与责任。具体到 《黑泽废墟》这篇小说,作家首先展示了以色列士兵的心灵冲突,尤其是部分士兵在弱势群体面前表现出来的同情。其次将这种冲突置于战争的背景之下,既透视出战争的残酷性,又表现出具有道德意识的个体人,在国家利益与道德规范面前陷入举步维艰的两难境地。参加驱逐行动的个别以色列士兵把驱逐阿拉伯村民之举视为“肮脏的工作”,并质问指挥官“为什么要驱逐他们?”,指挥官将这样做的原因归结于行动命令。战争期间,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似乎成为一条准则。但是它与犹太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爱邻如己”的宗教理念,与某些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试图同阿拉伯人在一块土地上和平相处的理念,与作为普通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发生抵触,部分以色列士兵认为“我们没有权利把他们从这里赶走”。
列维纳斯曾经指出:暴力主要不在于损害和毁灭人;它更在于中断他们的连续性,使人们扮演着那种他们在其中不能够认出自己的角色;使他们背叛;不仅背叛诺言,而且背叛他们自己的实质;使他们完成那些把行为的一切可能性都摧毁的行为。[7]对于以色列士兵来说,他们的作为不仅与犹太传统发生断裂,而且印证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某些主张,即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初理念中便有驱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计划。[8]说到底,叙述人“我”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实际上体现了他已经陷于为秉承犹太复国主义道德理念所应承担的义务以及“作为人”在1948年战争中应采取何种行动之间的冲突。或更进一步说,在道义与以色列国家生存权之间具有不可祛除的联系。在这方面,小说并没有给予清晰的审视,或者说,身为以色列犹太人,伊兹哈尔从内心深处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何在以色列建国的过程中,能否以道义手段对待另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利的问题始终无解的缘由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叙述人及其战友即使陷入了情感与道德悖论,但不能说是无辜的。
二、历史、记忆与道义思考
依照创伤记忆学者拉卡普拉的理论,我们可以把创伤叙事中的人物划分为不同类型。如果我们把“他者”——阿拉伯人视为受创伤的主体,那么驱逐他们的以色列士兵则成为“做坏事的人”,或者“做错事的人”(wrongdoer),[9]确切地说是错误指令的执行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平庸之恶”的化身。在此语境下书写的创伤叙事也成为救赎的一种途径。 正如小说开篇所述:
这一切发生在很久以前,但从那时起就一直困扰着我。我试图用流逝岁月的喧嚣来淹没它,降低其价值,用匆匆的时光来钝化其边缘,我甚至还设法冷静地耸耸肩膀,设法看出整件事毕竟没有那么糟糕……但无论如何我不能保持沉默,我应该开始讲述故事。[3]33
如前文所示,小说发表于1949年,此时第一次中东战争刚刚结束。作者将这个故事归于遥远过去发生的事,而故事本身一直困扰着自己,既表明他从内心深处不愿触及这一事件,又是表明这一事件本身对其影响之深远。作者并非客观而无动于衷地记述事件本身,而是把叙述人“我”当作错误指令执行者的代表,这暗含着对以色列国家军事命令的批判意识。
由于曾经在1948年战争中做过情报官的伊兹哈尔本人一再声称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是他亲眼所见,所以一些学者认为这篇作品便带有了报告文学色彩,[10]67叙述人本人也成为灾难的见证人,兼具作家与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作家的责任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提醒人们勿忘人性与道义等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历史学家则是记忆医生,必须在道德压力之下行动,来修复一个民族或人类的记忆。记忆和现代史学本质上与过去有着根本不同的关系。后者并不是试图恢复记忆,而是建构一种全新的记忆。
历史学家要做的不只是填补记忆的空白,而是不断地挑战那些保存完好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小说是用见证人的手法描写1948年的战争对阿拉伯村民命运的影响,以及对参与战争行动的以色列士兵的心灵震撼,因而具备了历史小说的特征。[11]93-94更为重要的是,它所涉及的中心事件在战争期间具有典型性,黑泽废墟不过是战时被毁弃的数十个阿拉伯小村庄的冰山一角,村子里阿拉伯弱者的遭际隐喻着当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共同命运。而围绕着究竟是否把巴勒斯坦阿拉伯村民从他们居住多年的村庄赶走,将其运送到其他地方,使之永远不能回归这样一个放逐行动的争论与反省中,这些矛盾达到了高潮。
难民问题是任何战争无法避免的问题。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之际 ,有几十个阿拉伯村庄的村民遭到以色列士兵的驱逐,背井离乡,近七十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沦为难民。约16万留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成为新建犹太国家内的少数民族,而被毁坏的阿拉伯村庄有的成为以色列的耕地,有的成为犹太人定居点。[12]失去土地和家园无疑导致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也埋下了日后巴以冲突的祸根。
在文本中,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女子典型地体现出遭驱逐的巴勒斯坦阿拉伯百姓的悲伤、愤怒和潜在的仇恨。按照作家描述,女子在悲伤中表现出坚定、自制与冷峻,好像只有她“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而她手里领着的孩子也在绷紧嘴唇哭泣:“你们对我们都干了些什么?” 母子二人的步态中似乎含有某种呐喊,某种指责。女子就像一头母狮,即使她的世界现在已经变成废墟,可她不愿意在以色列士兵面前崩溃。而孩子的心中仿佛蕴涵着某种东西,某种待他长大之后可以化作他体内毒蛇的东西。[3]74-75这对母子的愤怒不仅令主人公深感愧疚,而且预示着巴以两个民族冤冤相报的未来。
更加触目惊心的是,作为个体士兵,叙述主人公不仅要经历良知与道义的拷问与困扰,而且从眼前遭受驱逐的阿拉伯受难者的命运,联想到犹太民族近两千年来颠沛流离的流亡命运。尽管他本人没有经历过大流散,但是驱逐阿拉伯村民的一幕幕场景,尤其是把阿拉伯人装上卡车押走这一细节使之在有生之年第一次理解了流亡的含义,进而凸显了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的共同受难体验:
有什么东西犹如闪电一样击中了我。突然间,一切似乎都具有了不同的含义,更确切地说这含义便是流亡,这便是流亡,流亡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把他们送去流亡。[3]74-75
小说中濒临结尾这一著名段落把眼下以色列人驱逐一个弱势群体的行动与犹太人的过去建构起类比关系,触及了学界经常探讨的犹太人角色模式转换问题,即在欧洲遭受欺凌的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把不幸转嫁给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换句话说,在欧洲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在欧美等国家的支持下试图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家园,却损害了另一个无辜民族的利益。小说结尾清晰地将这种关联展现到读者面前,即军官所言,只有把这些阿拉伯难民驱逐,才可以安置从各地返回的犹太难民。如果说1948年的战争将以色列犹太人的身份从受难者转化为拥有独立国家主权的人,那么,与之相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从自己土地上的主人转化为难民,即新的受难者。这样的结局无疑挑战着伊兹哈尔和1948年一代作家的良知:
永远不会被收割的农田,永远不会被灌溉的种植园,将要荒芜的小路。一种毁灭感,无价值感。到处布满了蓟草和有刺的灌木,一片荒凉的昏黄,一片喧闹的荒野。从那些田野中已有指责的目光朝你张望,那无声的责备目光就像表示责备的动物,紧盯着你,追随着你,令你无法躲避。[3]68
文本中呈现的巴以冲突问题,牵扯出中东历史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时尚处年幼但经历过耶路撒冷围困、素有“以色列的良知”之称的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在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ATaleofLoveandDarkness)中反思道:
欧洲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和镇压等手段伤害、羞辱、欺压和迫害犹太人,最终听任甚至帮助德国人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连根拔除。在阿拉伯人看来,犹太人不是一群近乎歇斯底里的幸存者,而是欧洲的又一新产物,拥有欧式殖民主义、尖端技术和剥削制度,此次披着犹太复国主义外衣,巧妙地回到中东——再次进行剥削、驱逐和压迫。而在犹太人眼中,阿拉伯人也不是休戚与共的受害者、共患难的弟兄,而是制造大屠杀的哥萨克,嗜血成性的反犹主义者,伪装起来的纳粹。[13]348-349
这段描述在相当程度上道出百年来巴以冲突的本质,尤其揭示出欧洲国家为追逐自身利益,在巴勒斯坦历史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无论在现代以色列还是现代巴勒斯坦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受难者的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欧洲无法生存的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被居住在那里的阿拉伯人视为新的殖民者,而犹太人则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视为新的杀戮者。本来在《圣经》中有兄弟之缘的两个民族开始血拼。第一次中东战争非但没有把以色列这个新建的犹太国家消灭,反而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失去了分治协议中划归在其名下的土地,而这部分土地被以色列、埃及和约旦三国瓜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百姓从此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据2023年7月笔者在拉马拉阿拉法特纪念馆看到的图片介绍,1949年2月24日,以色列和埃及签署休战协议,加沙由埃及管辖。1949年4月3日,以色列与约旦签署休战协议。翌年4月24日杰里科会议后,西岸正式成为约旦王国的一部分。在这方面,美籍巴勒斯坦裔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的话十分发人深省,他说:“今天,每当巴勒斯坦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总是在讨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主题:阿拉伯朋友和以色列敌人是如何对待我们的。有时候很难说是谁在哪里对我们更糟糕。”[14]
三、从小说到影视:集体记忆的重构
一部作品有时会唤起一个民族的良知。[15]《黑泽废墟》不仅是希伯来文学作品中少见的反映以色列“独立战争”历史的小说,而且成为以色列历史,至少是以色列集体记忆中一篇重要的文献,在以色列民族记忆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将历史书写、对过去的记忆以及历史含义这三个被犹太历史学家耶鲁沙米尔(Yosef Hayim Yerushalmi)视为《圣经》中相互关联的三个要素整合起来,[11]xvii且随着以色列社会与政治的变迁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按照历史学家阿尼塔·沙培拉(Anita Shapira)的划分,把小说所引起的公众回应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 年到1951年小说发表初期引起的争议阶段,当时的许多读者亲历战争时期的军事行动,其关注焦点主要置于战争期间的良知与道义问题上。当《黑泽废墟》与伊兹哈尔的另一个短篇小说《俘虏》在1949年9月结集出版后,很快便成为畅销之作。到1951年4月为止,便已经出售4354册,这对有限的希伯来语读者群来说显然数量可观。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大量的书评和评论文章,多数批评家赞赏伊兹哈尔作品的文学品质,比如,作家描述事件的能力、独特的风格、士兵们在会话中使用希伯来口语进行交流、自然风光的描绘乃至描写阿拉伯人的方式等;但对作品的内容与理解上却表现出多元倾向。[16]其富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第一,多数批评家称赞作家的坦诚,有勇气公开士兵们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赞扬其道德立场。[17]认为这篇作品向年轻一代表明,在激烈的战争期间,人道主义意识不能麻木,反映出有良知作家的内在痛苦,等等。[16]第二,一些批评家相信,伊兹哈尔披露了以色列“独立战争”后人们不仅目睹了新建国家逐渐走向繁荣,而且同时又趋于野蛮、把基本的道德价值踩在脚下的过程。他敏锐地意识到:“昨天受折磨的受难者变成眼下捡起皮鞭折磨人的人,昨天遭驱逐的人而今在驱逐别人。那些多少世纪遭受非正义对待的人自己变成了迫害者。”[16]第三,但也有一些批评之音。批评家们认为事件本身不具有代表性,伊兹哈尔过于片面,他把阿拉伯人描写为无辜的任人摆布的羔羊,没有提到阿拉伯人经常制造恐怖活动、屠杀犹太人的行径。1964年,这部作品成为以色列中学生的选读读物,但学校并没有让学生分析作品的道德冲突,而是分析作家创作的形式与审美。[15]
第二阶段是1978年围绕《黑泽废墟》电视脚本能否上演展开激烈争论的阶段。事情的导火线在于:1978 年,一向对歧视、社会不平等、战争伦理与以色列的贫穷问题等主题感兴趣的导演拉姆·莱维(Lam Levy)将丹妮埃拉·卡米(Daniella Carmi)根据《黑泽废墟》改编的脚本拍成电影,且邀请了四个阿拉伯村庄的村民担任演员,其中就包括带小孩的阿拉伯女子。与小说相比,影片显得比较柔和,甚至加进了小说中并不存在的年轻女话务员达利亚与青年军官调情、相恋等细节,给乏味的军旅生涯带来了几分浪漫色彩。影片以充满乡愁的柔和的口哨音拉开序幕,随之画面立即转向嘈杂的军事基地,年轻而充满激情的士兵们接受命令前去征服阿拉伯村庄。对此,阿拉伯村民不但没有任何抵抗,而且平静地接受了一切。
形成小说记忆与影视记忆差异的原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现实环境发生了变化。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③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④之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范围内逐步确立了其合法性,舒缓了其民众的心理压力。其次,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使得以色列人意识到流亡中的犹太人在欧洲的无助,对犹太人的流亡体验报以同情和理解,乃至与当地阿拉伯人的生存境遇发生共情。再次,就在电影拍摄期间,以色列正在与埃及进行和平谈判,和平进程的开启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重新审视历史冲突。
但是当时以贝京为首的右翼政府将这部作品视为反以色列的宣传素材。以色列教育文化部在影片上演前夕下令禁演,奥兹等20多位作家对此提出抗议。这一事件不仅涉及媒体自由问题,也涉及以色列公共生活是否有道德勇气进行真正的自我评估问题。[10]68人们甚至把请愿书送到了高级法院。一个名叫马克·塞戈尔(Mark Segel)的新闻记者指出,影片制作人的目的并非是要艺术地再现战争,而是要表明犹太人是侵略者,阿拉伯人是烈士,进而具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含义。[10]68一位以色列国会议员甚至主张,这部影片应该与阿拉伯人屠杀以色列人的纪录片一起上演。最后,以色列教育文化部取消了禁令,影片在以色列得以公演,引起轩然大波。作家、导演和编剧均受到了攻击。如果说围绕影片能否上演的争论集中于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否拥有媒体自由等问题,那么脚本内容的重构则表现出以色列一批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比如,在小说中,叙述人的反战理念并没有得到所有战友的认同,甚至遭到一些战友的质疑。与之相对,在影片中,以色列士兵似乎表现得更为人道。即使在射杀逃跑的阿拉伯人时,也故意未能瞄准,表现出不愿伤害阿拉伯人的主观愿望(而小说中的阿拉伯人显然被打伤)。影片中的军官曾给阿拉伯人送水,一个士兵甚至给了阿拉伯人食物(相形之下,小说中的以色列士兵则显得比较冷酷,甚至听任瘸子蹚过水坑)。从某种意义上,影片是把小说中以色列内在的心灵冲突以画面形式呈现出来。同时揭示出清理村庄的真实目的并非是把阿拉伯村庄清除,而是要把阿拉伯村庄转化为犹太人定居点。
由此引发了影片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影片中反映的事件是否在“独立战争” 时期具有普遍性等诸多问题的讨论。其中还涉及为什么影片只表现了以色列军人驱逐阿拉伯难民,而没有表现阿拉伯人对犹太人所施行的种种暴行;为什么要重揭旧日创伤;等等问题。一些人甚至也对作品本身提出质疑,认为它曲解了以色列“独立战争”的形象。尤其是把以色列人用卡车运送阿拉伯人的行动比作犹太人在历史上被迫经历的死亡之旅,更令一些人无法接受,认为会给以色列的敌人以口实。从这个意义上,本来是根据反映个体以色列士兵的心灵传记改编的影片却变成带有集体记忆色彩的重构历史的文献。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更多的则是历史事件本身,而不是以色列士兵针对历史事件的反思、回应与心灵震撼。进而在一些评论家看来,这部影片缺乏艺术优长。[18]
右翼人士认为,犹太人渴望并应该回到先祖生存的土地上,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的做法,这是历次中东战争的根本原因。但是1948年战争对以色列人来说,确实是一场生死之战。而影片脱离了 1948 年的历史语境,人们的视点则从对以色列究竟可以继续存在还是会遭到毁灭的问题转向巴勒斯坦人的生存问题,这种以偏概全的方式势必造成对作品本身的某种曲解。[19]但是,左翼人士则认为影片本身反映了战争悲剧,引发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黑泽废墟》的上演可以说重新塑造了以色列人对1948年战争的记忆。这部影片虽然讲述的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它上演后,观众会认为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以来,犹太人的行动基本上就是赶走阿拉伯人,杀害无辜,驱逐老人、妇女和孩子。但是,正像犹太历史学家沙佩拉指出,并非《黑泽废墟》小说或作品本身破坏了以色列人的声誉,而是把一个民族从其土地上赶走这个行动本身是不光彩的,定居到人家的居住地的行动是耻辱的。[16]伊兹哈尔的小说反映出“独立战争”时期的历史真实,批评这篇小说与阻止其影片的上演无异于试图掩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实现自己返回锡安的梦想过程中的劣迹。就像作家奥兹所剖析的那样,“我们的做法就像把一具死尸藏在地下室里”,“我们正在掩饰将要化脓的伤口”。[20]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以色列人正是在复国与负疚的困扰中不得释怀。
四、结 语
从《黑泽废墟》最初面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十余年。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黑泽废墟》在参加过以色列“独立战争”的人们中间引发的是一场道义的争论,那么时至如今,以色列经历了“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两次黎巴嫩战争、两次巴勒斯坦人起义,政治现实又发生了变化,新历史主义思潮兴起,曾经伴随着1948年战争结束而淡出人们观察视野的诸多问题此时又浮出地表,以色列人更为关注的则是由道义延伸开来的国家政治形象问题,以及对巴勒斯坦的政策问题。战争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历史学家、文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对战争的解析实际上一直在继续。在这方面,以伊兹哈尔为代表的一批希伯来语作家带着道德勇气,采用多种艺术手法诠释了七十余年来以色列历史、记忆与以色列人的心灵冲突。
举例说来,伊兹哈尔的同代作家本雅明·塔木兹(Benjamin Tammuz)在带有自传色彩的短篇小说《游泳比赛》(″The Swimming Race″)中[21],展现了以色列建国之前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和平共处的生活状态,书写了以色列叙述人与幼时曾在一起进行游泳比赛的阿拉伯玩伴在攻克一个阿拉伯院落时相遇,叙述人的战友不慎走火把阿拉伯人打死的残酷现实,叙述人在失落与自责中慨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输者。第二代以色列本土、希伯来语作家奥兹在意识形态上属于伊兹哈尔的左翼阵营,在文学传承上也深受其影响。在其最富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对犹太与阿拉伯阵营对联合国181号文件的不同回应做了惊心动魄的描写。在奥兹笔下:犹太人一方爆发出吼声,那叫喊令人胆寒,划破黑暗、房屋与树木,穿透大地,那叫喊可以撼动山石,让你血液凝固,仿佛已在这里死去的死者和正在死去之人瞬间拥有了叫喊的窗口。随即,代替惊恐尖叫的是欢乐的怒吼,沙哑的哭喊声响成一团,“犹太民族活下去了”。与之相对,阿拉伯人一方正沉浸在一片沉寂中,沉寂也许酷似表决结果宣布之前犹太居住区的可怕沉寂。[13]362-363莫言称这—场面是奥兹为世界文学做出的贡献,它必将成为经典,它已经成为经典。[22]奥兹用犹太民族狂欢与阿拉伯民族沉默的巨大反差,预见到巴以双方兵刃相见、血雨腥风的未来。另一位左翼作家约书亚(A. B. Yehoshua)在中篇小说《面对森林》(″Facing the Forest″)中,描写了以色列森林在阿拉伯的废墟上拔地而起,而身为守林员的阿拉伯人的舌头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被割断,进而凸显了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失声的现实。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这位阿拉伯哑巴在一位年轻以色列人的煽动下烧毁了象征国家的森林。
总体上看,这些作品既蕴含着深邃的历史记忆,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回响,表现出具有良知的以色列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奥兹在访问中国时直陈其“两国论”的主张,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国家,与以色列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则代表着左翼知识分子对巴以两个民族和平前景的期待。
【注释】
① 副标题使用“重读”一词,是因为笔者曾经在《变革中的20世纪希伯来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中讨论过这个文本,当时采用音译法,把书名译作《赫伯特黑扎》。小说原名KhirbetKhizeh,指的是一个虚构的阿拉伯村庄。Khirbet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废墟,Khizeh是阿拉伯村庄名。此次采取音译与意译结合的方式将书名译作《黑泽废墟》,能与文中描述的肮脏、阴暗的环境形成某种关照。文中许多想法是在此次翻译的过程中萌生的。
② 本文在使用集体记忆这一术语时,受到哈布瓦赫记忆理论的启发。参见阿斯特里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第175-186页。
③ 六日战争,指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五战争”。1967年6月5日,以色列为削弱阿拉伯联盟的力量,解除边境危机,相继空袭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而后又发起地面攻击,阿拉伯国家奋起反击。战争共持续6天,以色列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老城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数十万阿拉伯平民逃离家园而沦为难民。
④ 赎罪日战争,指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10月6日,埃及、叙利亚等国家在犹太人斋戒日那天向以色列发动战争,试图收复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丧失的领土,赢得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埃及、叙利亚赢得了战争初期的胜利,但以色列最终在美国的支持下反败为胜。这场战争给阿以双方均带来惨重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