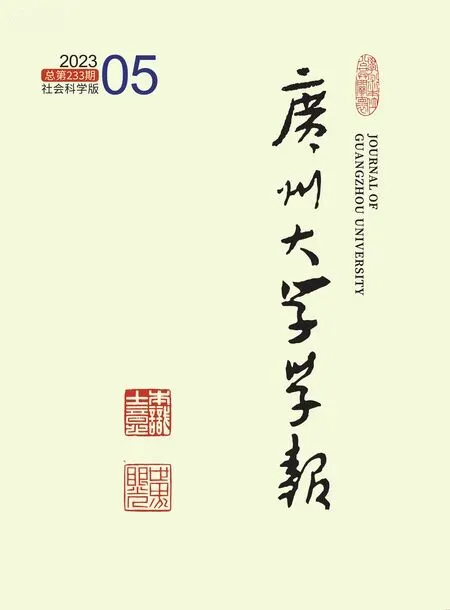加勒比科幻文学中的杂糅性与群岛意识
2024-01-03王梓钰
苏 娉,王梓钰
(华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科幻小说的诞生与西方殖民历史和殖民话语的产生、发展息息相关。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暴风雨》(TheTempest,1611)、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Travels,1726)所描写的殖民扩张与征服对随后出现的科幻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化论、人类学与殖民意识形态和历史相互交织,共同促进了十九世纪中后期科幻小说的萌芽”[1]2。在此基础上,19世纪末最为狂热的帝国主义扩张使这一时期成为科幻文学发展的关键期。[1]2-3,[2-3]殖民活动中对未知他者的探索欲望和时空维度上向外扩张的野心,加之纸媒的广泛宣传,直接推动了20世纪初“科幻”(science fiction)这一术语的产生,以及20世纪中期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出现。伊斯塔万·希瑟利-罗奈(Istvan Csicsery-Ronay Jr.)曾提及科幻形成的三个重要条件,即科技发展对帝国主义扩张欲望的激发,西方霸权对服务于自身殖民扩张的文学、文化工具的需要,以及对完美科技帝国的想象。[4]因此,早期的科幻小说不仅反映了欧洲帝国主义带来的政治和文化转变,还残留着对殖民主义的持续映射。科幻小说在西方国家的流行与帝国主义扩张历程齐头并进。英法两国在殖民扩张的高峰期率先见证了科幻小说的繁荣,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国家紧随其后,随着他们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帝国主义竞争中,这些国家也分别迎来了科幻小说的大爆发。[1]3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地球未开发区域的日益稀缺,科幻小说越来越倾向于以遥远星球或未来地下世界为背景,但大多数科幻作品仍然局限于殖民话语的意识形态和认识论框架中。[1]10后殖民理论家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曾提及科幻有一种帝国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根源于人类征服、统治外星他者和外星空间,并建立银河帝国的欲望”[5]。因此,西方科幻作品在想象未来的同时,往往渗透着殖民主义话语和意识形态。
一、科幻、殖民主义与去殖民进程
随着科幻文学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欧美科幻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影响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虽然大部分殖民地在二战后纷纷获得独立,但科幻文学仍然以西方科幻为主流,并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占据科技中心的西方国家才配拥有对未来的想象。由于西方国家科技发达,不仅西方读者,甚至一些落后地区的读者也都抱有这种偏见和刻板印象,认为落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创造不出什么像样的科幻文学。科幻是对未来的想象,尤其是对高科技未来的想象,而那些落后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却相对缺乏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其命运与未来似乎就是跟随西方国家的脚步,不断学习、模仿、追赶,却永远不可能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更不可能取得令人瞩目的科技突破。因此,以科学和技术为中心的科幻通常被视为一种西式文类,“像可口可乐、大汽车、计算机一样是西方文化的标志”[6],“科幻属于发达国家”于是逐渐成为一种刻板印象[4, 7],并内化为“西方精心构建的认知特权”的重要一环[8]。科幻是重构已知世界、开辟介入世界新可能、为全人类寻找另一重未来的有效工具,但科幻界来自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作家的声音却十分微弱,并且常被主流科幻界所忽视。科幻与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西方霸权主义的重要工具,然而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也可以反过来运用科幻想象自己国家和地区民众的未来,打破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的桎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的落后边缘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科幻文学,它们常常被称为后殖民科幻文学、全球南方科幻文学或第三世界科幻文学。这些作品对后殖民和全球化的特殊语境做出回应,已然构成科幻文学的一个自主流派,却尚未获得学界的足够关注,许多学者很难将落后的第三世界与源自欧美的科幻传统联系在一起。第一本后殖民科幻小说集是2004年加勒比牙买加作家娜洛·霍普金森(Nalo Hopkinson)和后殖民学者乌平德·姆汉(Uppinder Mehan)主编的《梦寐以求:后殖民科幻与幻想》(SoLongBeenDreaming:PostcolonialScienceFiction&Fantasy)。对后殖民科幻作品的学术研究则始于21世纪初,2010年后才初具规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2010年出版的《科幻、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后殖民文学与电影研究文集》(ScienceFiction,ImperialismandtheThirdWorld:EssaysonPostcolonialLiteratureandFilm)、2011年出版的《后殖民主义与科幻》(PostcolonialismandScienceFiction)以及《后民族幻想:后殖民主义、世界政治与科幻研究文集》(ThePostnationalFantasy:EssaysonPostcolonialism,CosmopoliticsandScienceFiction)、2012年出版的《全球化、乌托邦和后殖民科幻:新希望图景》(Globalization,UtopiaandPostcolonialScienceFiction:NewMapsofHope)。这些研究以后殖民视角批判性地审视与殖民遗产和历史相关的科幻作品,其中包括来自加勒比地区的一些科幻小说,但并未对加勒比科幻小说的独特之处给予特别关注。加勒比科幻文学通常被笼统地归类为第三世界科幻文学、后殖民科幻文学、非裔或拉丁美洲科幻文学,本身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加勒比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表科幻小说,但直到2005年以后,加勒比科幻作品的数量才有了较大增长。加勒比地区比较有名的科幻作家包括牙买加作家娜洛·霍普金森、埃尔纳·布罗德伯(Erna Brodber)、斯蒂芬妮·萨拉特(Stephanie Saulter),格林纳达作家托拜厄斯·巴克尔(Tobias S. Buckell),巴巴多斯作家卡伦·劳尔德(Karen Lord)、罗伯特·爱迪生·桑迪福德(Robert Edison Sandiford),古巴作家佑斯(Yoss,原名:José Miguel Sánchez Gómez)、奥古斯丁·德罗哈斯(Agustín de Rojas)等。尽管大多数读者和批评家仍然没有注意到加勒比科幻文学,但加勒比地区不断涌现的科幻作品证明加勒比科幻文学是无法抹杀的存在。加勒比科幻作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运用科幻小说的一般惯例,将西方科学话语与加勒比地区独特的文化生产以及本土或殖民化知识体系相融合。加勒比科幻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创新性地将加勒比文化元素,如神话、民间故事、传说、寓言、民间音乐、仪式、宗教信仰以及当地方言克里奥尔语等,融入传统西方科幻小说的叙事中,呈现出一种多维度的杂糅性。除了凸显加勒比文化背景外,加勒比科幻文学还呈现出一种根源于本土地貌与地理环境的群岛意识。这一群岛意识是一种以群岛的多样性、流动性和动态性为前提的关系思维模式,[9-10]打破了二元论、二分法和静态模式,强调对他者和异文化的尊重,挑战西方认识论和思想霸权,认可群岛中岛屿(以及社会中主体)的集体性和相互联系,群岛视角下的岛屿成为地理空间移动和文化迁移交流的节点。杂糅性和群岛意识几乎贯穿了加勒比地区所有的科幻作品,这些作品呈现出一种植根于殖民历史的抵抗精神,成为去殖民运动的重要文本实践。
二、加勒比科幻文学的多维杂糅性
位于中美洲的加勒比地区有着特殊的殖民历史,曾沦为欧美国家,主要是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的殖民地。直到今天,加勒比地区仍有部分海岛为欧美殖民地。殖民时期,白人殖民者在加勒比地区开辟了许多种植庄园。由于当地印第安人几近灭绝,为填补劳动力空缺,白人殖民者从非洲贩卖了大批黑奴到加勒比地区,19世纪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被废除后,又从印度和中国贩运了大批契约劳工以替代黑奴。因此,加勒比地区是世界上种族、文化、语言最为复杂和多样化的区域之一。多民族混杂,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形成了一种极富张力与动力的杂糅文化,在其文学作品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特殊的殖民历史以及杂糅文化的影响下,加勒比科幻文学在关注殖民主义的同时形成了多维度的杂糅性。
加勒比科幻文学杂糅性的第一重维度是将西方传统科幻元素与加勒比历史元素以及民间文化元素,如民间奇幻故事、神话、传说等融合在一起。加勒比民间文化元素又同时混合了来自非洲、印度、中国、欧洲等多个地区的民间文化传统,打破了各种体裁的界限,尤其是奇幻和科幻的界限。霍普金森曾对加勒比科幻进行界定,并多次以“加勒比寓言小说”(Caribbean Fabulist Fiction)代指加勒比科幻小说,认为“西方主流视角下的科幻基于对世界的怀疑与理性思考,致力于对不可知的现象予以科学、合理的解释”;而加勒比及其他非西方文化则持有另一种观念,“他们允许非理性、不可知、神秘的力量与日常生活并行同在”。[11]例如,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所阐释的黑人宇宙观是一种“超现实与世俗生活的紧密糅合”[12]。世界观的不同导致加勒比地区的科幻创作呈现出与西方科幻相异的特质,形成了一种集超自然元素、魔幻色彩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之大成的叙述风格。霍普金森在编纂加勒比科幻小说集《棉花树根的低语:加勒比寓言小说》(WhispersfromtheCottonTreeRoot:CaribbeanFabulistFiction,2000)时选取了众多“奇幻”而非“科幻”文本,体现了加勒比科幻中西方“科学”传统与东方“幻想”传统相结合的特质,着重突出加勒比历史文化的根源意识。佑斯同样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科幻进行区分,认为“来自第一世界的读者易于接触高精尖科技,因此更习惯科幻作品对科学技术的夸张叙述与极致想象。而来自第三世界的读者仅对高端科技保有剪影式的印象,因此在科幻文学的高科技迷雾中更倾向于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的幻想色彩”[13]。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科幻与奇幻、想象与现实的界限在加勒比科幻文学中一再模糊。托拜厄斯·巴克尔的“异邦系列”(Xenowealth Series)小说以外太空为背景,书写了对现实的另一重想象,构建了一个与加勒比现实世界相平行的跨种族宇宙共同体——具有加勒比风情的“新阿内加达”(New Anegada)。在“新阿内加达”上生活着非裔、以亚洲人为原型的“洪蝈”(Hongguo),以及土著人“阿兹台卡”(Azteca)等。白人退场,有色人种占据巴克尔小说的主要角色,展现了后殖民语境下的多元种族、文化关系,引发读者深思:如果没有白人殖民的介入,世界将会发生何种改变?在一个仅由有色人种构成的世界,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级制度是否还会存在?霍普金森则在小说《圈圈里的棕色女孩》(BrownGirlintheRing,1998)中,将加勒比传统与加拿大文化背景相结合,囊括了与巫毒教有关的各种仪式、符号,并将非洲神话中的诸神与自然现象及基督教传统相联系。民间元素的引入在西方纯粹的科学幻想中渗入现实意识,使科幻成为有关现实的某种寓言。后殖民创作多以过去为导向,旨在反映殖民历史对殖民者以及被殖民者的现实影响,却鲜有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加勒比科幻成为连接多元文化的桥梁,在意识形态领域为第三世界人民开辟出一片未来天地。
加勒比科幻文学杂糅性的第二重维度是其叙事语言混合了前殖民宗主国语言(如英语、西班牙语、法语、荷兰语)和加勒比当地各种克里奥尔方言,这几乎在所有加勒比科幻作家的创作中均有所体现。埃尔纳·布罗德伯在小说《简与路易莎很快就会回家》(JaneandLouisaWillSoonComeHome,1980)中将标准英语与牙买加克里奥尔英语并置,并将克里奥尔方言的句法与音调一同融入人物对话中,多语种混杂体现了蕴含于语言背后的多元文化取向。巴克尔和霍普金森在移民北美后依然注重加勒比方言的运用。在巴克尔的作品中,口语、方言、语言的特性将主人公与特定的文化地域联系起来,成为个人身份的重要构成。例如,《水晶雨》(CrystalRain,2006)中,约翰经由虫洞来到新世界却失去了所有过往记忆,语言成为他与旧世界的唯一联系。独特的口音不断提示着他“外来者”的身份,也使他在新世界逐渐找回自我意识,语言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纽带。经由这一纽带,读者与主人公得以在现实与虚构、过去与未来之间穿梭,使其创作呈现出科幻感与现实感并行交织的效果。霍普金森的《圈圈里的棕色女孩》《午夜盗贼》(MidnightRobber,2000)混合了克里奥尔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在运用克里奥尔语时还在牙买加、特立尼达、圭亚那方言之间切换。这一类似“编码转换”(code-sliding)的语言策略一定程度上是对加勒比人语言模式的模仿,他们“在一个句子中会包含多种不同的语言模式,从标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向克里奥尔模式靠近”[14]。语言的混杂不仅是对殖民历史与霸权的抵抗,还渗透出加勒比科幻作家深厚的群岛共同体思想。多元语言与复杂的殖民历史并未将加勒比地区隔离成一个个孤立区域,反而成为全加勒比共享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财富,进而内化为加勒比身份的独特象征。
该杂糅性的第三重维度是将加勒比的多元口述叙事元素糅入传统科幻叙事中。加勒比地区复杂的殖民历史生发出动态深厚的口述传统,其广泛借鉴了来自非洲、印度、中国、欧洲以及美洲印第安的民间元素,成为加勒比文化身份的重要构成。霍普金森是将加勒比口述传统引入科幻创作的先驱之一,《午夜盗贼》以“呼喊-回应”的口述传统搭建小说结构。整个故事由一位叙述者娓娓道来,最后结语也颇具加勒比特色:“告诉乔治,故事讲完了。我们得让天堂守门人知道,我们对阿南西的邪恶之举并不认同。”[15]这是加勒比口述传统中的经典结束语。阿南西(Anansi)是非洲和加勒比神话中的蜘蛛人,作为故事知识之神,是所有说故事者的保护神。他同时也是恶作剧精灵,以骗术出名,所以加勒比民间说故事者常常用此结束语来表明自己并不认同阿南西的恶作剧行为。这一结束语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作为听众的读者与叙述者之间建立亲密联系,读者被叙述者一同纳入“我们”的范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均归顺于这一加勒比文化传统。同样,在巴克尔构筑的未来世界,口述传统不仅没有被磨灭,反而成为国族历史传承的重要手段。口述的故事是动态、人格化的,赋予科幻背景以人性内核。西方世界在思想文化领域一直秉持着书面优于口述,科学胜于民俗的层级观念。加勒比科幻文学将口述传统引入科幻创作是对欧洲主导的知识体系的颠覆,其独具特色的杂糅思想相对调和了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和二分法,从知识生产领域呈现出当代加勒比作家的自主性与抵抗精神。
三、加勒比科幻文学的群岛意识
加勒比科幻文学第二大特点是其特有的群岛意识,主要体现在加勒比科幻文学作品所建构的具有群岛特性、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时空体以及这些文本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颠覆上。首先,加勒比科幻文学中的流散主题凸显了离中有合、失落与联系并存的群岛特性。巴克尔在《水晶雨》中尤其强调了 “岛民”身份及其流动变迁。两位主人公在地球上是岛民,移居新星球后仍然在海岛生活,承载着双重岛民身份,由此暗示了地球的殖民历史对外太空后殖民未来的形塑作用。尽管过去的历史和记忆可以被抛弃,一切看似都被推翻重来,但后殖民流散身份内核在本质上并未改变,岛民身份使被割断的一切联系又得以重建。在卡伦·劳尔德小说《最好的可能世界》(TheBestofAllPossibleWorlds,2013)中,萨迪拉星(Sadira)被毁,该星球难民前往与家乡具有相似特质的天鹅贝塔星(Cygnus Beta)生活。劳尔德将天鹅贝塔星描绘成一个典型的难民、种族、文化大熔炉,是加勒比地区的缩影。萨迪拉星人穿越众多地域,深入多元文化,以期重建失落的萨迪拉文明。他们重返前殖民地,向兄弟星球寻求庇护,重建精神连结的做法使人联想到非裔流散群体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上述作品的叙述视角从西方科幻传统中技术发达的主体转向科技欠发达、文明进程被中断甚至被毁灭的主体。他们运用殖民者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表达自身的经历与现实。加勒比科幻文学中的流散主题是整个加勒比地区,乃至整个非裔流散群体经历的映射,文化根源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暗线。海岛与大陆,地球与外太空,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命运相互交织,互为关联。
其次,许多加勒比科幻作家的创作受到殖民历史与现实的驱动,透露出对核武器以及科技发展的忧患意识,传递出一种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的群岛共同体意识。多米尼加作家雷伊·埃马纽埃尔·安杜哈尔(Rey Emmanuel Andújar)的短篇《胜负难料》(“Gameon”,2014)中,“古巴导弹危机并没有终止”[16],作为导弹发射基地的加勒比地区相比美国的竞争对手苏联付出了更为直接、惨痛的代价。导弹发射后,美国在本国领土边界外建立起保护罩并抵御了大部分不良影响,但“对加勒比地区而言,这一保护罩却像一面反光镜,使加勒比岛屿承受着双倍的辐射”[16]。作者以此讽刺美国对加勒比地区的科技殖民,并进一步警示核战争所造成的生态灾难以及人性摧残。古巴作家雅斯敏·西尔维娅·波塔莱斯(Yasmín Silvia Portales)在短篇《弗拉基米尔·杰尼索维奇·希门尼斯的奇怪决定》(“Las extraas decisiones de Vladimir Denísovich Jiménez”,2016)中质疑了苏联的军备竞赛对古巴主权的侵占。该小说将核危机穿插于一系列有关亲密关系的叙述中,探究核灾难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正如加勒比科幻小说研究学者塞缪尔·金斯伯格(Samuel Ginsburg)所说,“核辐射能够悄无声息地渗透并重塑生物以及社会结构的基础壁垒”[17]。古巴作家埃里克·莫塔(Erick J. Mota)的小说《额外工作》(TrabajoExtra,2014)中,负责运输核武器的船员相互猜忌,然而却鲜有人质疑货物本身的危险性,只有凯警告道:“这是一种剥削……他们在利用我们做一项极度危险和违法的工作。该工作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会让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18]佩雷斯揭示了核武器的持有者与受害者之间巨大的地位落差,以及放射物处理背后蕴含的不平等霸权逻辑。加勒比地区历史上的古巴导弹危机牵动着所有加勒比作家的神经,核战争与科技灾难题材在加勒比科幻作家的笔下不仅是简单的“幻想”或“虚构”,更是某种程度上的“现实”。后殖民与科幻研究学者杰西卡·兰格(Jessica Langer)在《后殖民与科幻》中指出,“科幻的一个重要力量是能够提供一种暂时的‘双重意识’,帮助我们在历史与潜在的未来之间建立连结”[19]。加勒比科幻作品的时空观、科技观与发展观从来都不是割裂的,其想象、创造的未来总是具有某种程度的熟悉感。加勒比群岛的殖民历史与地理环境孕育了加勒比科幻作家的群岛意识与责任感,使他们在潜在危机面前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群岛共同体意识。
此外,加勒比科幻还致力于书写个体与他者的相遇,通过科幻想象探索深藏在人类社会文化中的矛盾、对立、不平等问题,以群岛多样性、流动性、动态性的关系思维模式挑战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与思想霸权。《午夜盗贼》的主人公唐唐由于父亲和自己所犯的罪行被迫多次迁居。被流放到新哈弗韦树星球(New Half-Way Tree)的唐唐时刻被人性的黑暗面折磨,身心遭受巨大创伤的唐唐最终逃往野森林,并在野森林与土著人和动物一起构建了一个稳固、友爱、相互尊重的跨物种共同体。这一叙述模式颠覆了西方传统中以物种、种族、肤色、阶级等为区分的社会等级体系,对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话语进行陌生化处理。来自文明乌托邦的女孩最终在象征荒蛮落后的动物世界中找到归属。霍普金森将加勒比动物寓言元素引入科幻叙事,同时超越了传统的动物寓言,体现了第三世界作家对“何以为人”的再定义、再思考。牙买加作家卡罗尔·麦克唐纳(Carole McDonnell)的短篇《通用语》(“Lingua Franca”,2004)通过书写一个新生族群与强大地球族群的相遇,揭示了地球人(Earther)对埃奎达人(Aqueduct)语言、领土、知识领域的多方入侵。小说聚焦于语言殖民,以此影射英国殖民者将英语强加于土著人的霸权行径,反思不同文化相遇碰撞的得与失。斯蒂芬妮·萨拉特的小说《宝石标志》(Gemsigns,2013)书写经基因改造的新生族群“宝石人”(gems)与地球的原生族群“标准人”(norms)之间争取基本公民权利的系列斗争,展示了他者如何被主流社会所接纳,以及对现有社会制度和认知结构的思考。圭亚那作家卡琳·洛瓦切(Karin Lowachee)的短篇《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Ones”,2004)中,自由斗士小队在战斗中突然得知他们一直仇视的对象“洛波人”(Lopo)是他们的父母。小说通过他者视角的突转,探讨了自我与他者身份、仇恨、驱逐以及土地安置等问题。“他者”是后殖民科幻与西方主流科幻文学的共同话题。西方科幻传统倾向于忽视存在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将“他者”预设为“外星人”,以此减轻帝国扩张与征服所带来的负罪感,这实际上延续了西方主导的文化偏见。相比于对他者的征服,加勒比科幻文学更加注重与他者交流、融合,在与他者的相遇中审视自身。加勒比科幻作品中,本土身份与他者身份是多样的、流动的,“他者”的未来不再是简单地被同化、消灭或边缘化,而是具有创造自己未来,并与本土文化并行发展、相互融合的可能。
四、结 语
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幻作品致力于将民族文化与殖民历史、国家现实以及科幻传统相融合,形成了与欧美科幻相异的独特风格,但一直以来却因不符合西方认知传统而被边缘化。与欧美科幻传统相比,后殖民科幻文学并非梦想乌托邦的再现,也缺乏帝国扩张的雄心与压迫感,而是普遍弥漫着一种失落感、疏离感与危机情绪。加勒比科幻文学在具备上述特征的同时,还呈现出植根于其独特的民间文化、殖民历史以及地理环境的杂糅性与群岛意识,却鲜少被视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加勒比科幻文学的杂糅性展现了蕴含其中的丰富多元的文化、语言以及叙事传统。群岛意识则植根于现实,将身份、历史、国族关系的离合与流变作为加勒比地区人口流动、国家成长以及文化迁徙交流的隐喻。加勒比科幻文学书写游走于欧美科幻传统与加勒比政治文化现实的中间地带,展现了与西方不同的世界观,其对未来的想象更具现实性与寓言性。如果说西方科幻传统旨在以科技理性对我们身处的现实进行“祛魅”,那么加勒比科幻文学则以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对现实与自然界进行“复魅”,并挑战西方科幻传统中的层级观念与二元对立思想。加勒比科幻文学不仅面向加勒比读者,其内含的杂糅性与群岛意识超越了地理、技术与国族边界,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均能从中获得共鸣。
在科幻领域之外,加勒比科幻文学还具有更为广阔的价值。它将科技视角纳入当代后殖民研究的范畴,成为全球去殖民运动的重要文本实践。佑斯在《出租星球》(APlanetforRent,2001)中表明,殖民活动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剥夺了被殖民者对未来的期许,持续性的殖民压迫使他们“不需要考虑五十年,或十年以后的事,甚至都不需要考虑明天”。[20]而科幻创作则赋予了包括加勒比地区在内的边缘群体以想象、开创未来的可能。因此,对加勒比科幻文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保存、延续加勒比民族文化遗产,重塑国族精神,还在于对抗那些试图压制、抹除加勒比未来的霸权话语,对加勒比文学研究、科幻文学研究以及后殖民文学文化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