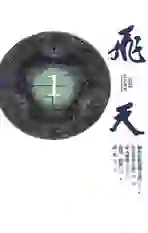散文写作的权威性在哪里
2024-01-03贾想
贾想
五年前,我和赵琳相识于眉山的诗歌夏令营。本以为他来自西北,天地苍茫,万物生长,应是个壮汉。不想见了人,憨态可掬,性格温柔,不纯然是泥做的,倒有几分是水做的。原来他来自“陇上江南”——陇南。俊秀山川,果然养人性情。他待人体贴,做事周到,面对我们这一众散兵游勇,勇担班长重任。临别,他忽然要在诗集上留几句诗,作为给我的寄语。诗的内容我已忘记,但干净、真诚,充满绵密的回声。这就是他的行事风格,无声无息的相处当中,已经对你产生了深厚的革命友情。就像他在诗歌里珍重语言的相遇一样,在现实中,他珍重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那是一种毫不掺假的珍重。
后来,赵琳成为“甘肃诗歌八骏”之一,马踏飞燕,往天高地阔处去了。这一天,他约我写一个评论,想起眉山往事,我欣然应允。结果他说:散文的。好吧,在我们一别两欢、各奔前程的几年,赵琳同志已经破圈发展,成为丰子恺散文奖的青年得主。犯难的是我,从不知道散文还需要评论。因为在我看来,文学评论就是现代散文的一种,给散文写评论,等于大葱炒蒜,吃馒头配面。好在他说,自由发挥。这就等于说他不挑食。
那么,我也勇担一次重任,就从他的多栖写作说起吧。
一、草的世界不能被压缩:从现代诗到现代散文
多栖写作,其实并不稀奇。诗歌也好,散文也好,都是独立的审美主体借助语言的随物赋形。尤其是在中国,现代诗与现代散文是一个娘胎里诞生的,使用的都是“白话文”这一套语言。白话散文文无定形,应用极广。白话诗一直想要从白话散文无处不在的言说之中挣脱出来、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具有美学合法性和形式自足性的文体。但由于对于“字”传统的放弃,进而对于严格的对仗、音韵学等古诗形制的放弃,自过去的眼睛看,现代白话诗其实不像“诗”了。就像拔了毛的孔雀,现代白话诗成为特征不明、身份可疑的一种文体。
而赵琳之所以会从现代诗走向现代散文,在我看来与这两种文体纠缠不清的发生史十分相关,需要放在“诗的散文化”这一问题背景下理解。早在夏令营时期,我就感到赵琳的诗歌与我所熟悉的现代诗不大一样。他的诗多多少少总给我“满溢之感”,他会在诗歌的短小形制里,铺展开一个辽阔而静谧的世界,有草原、星空、花草、牛羊,也有村庄、父辈、饮食、男女。现代诗歌的形制不能满足他,不能穷尽他的表达欲望。所以在我看来,他其实是一匹被关在诗歌马厩里的散文之马。早就有解放诗的桎梏,走向散文的冲动。
我甚至认为,他那慢条斯理的语言,他要表达的那个“稳定的世界”,与现代诗这个容器其实并不那么相合。在我的偏见里,现代诗所表达的世界,是一个与古典世界发生了断裂的世界,是一个被现代工业革命所侵占和改造了的世界,一个再次变得问题重重的世界。其时间是“寓永恒于一瞬”的时间,其空间是失去了稳定性的、破碎的空间。因此,现代诗的语言应该是压缩、加速、提纯后的语言,因为要在微小的时空完成语言的起飞,需要非常快的加速度。这就决定了,现代诗不是诞生于一双满足的眼睛对世界的长久凝视,而是诞生于一双失去了耐心的眼睛对世界的匆匆一瞥。
但赵琳是一个对人、对事充满了耐心的人。当他看世界的时候,他是从一株草的眼睛里看。在草的眼睛里,世界不是高速摄影之下的轮廓、印象、感觉。相反,这是一个高度稳固的视角,可以清楚、分明地看到一个个具体的形象,感受其形其色其味:“那些花苞还没开,需要春风去吹开,随后是蜜蜂和蝴蝶,再晚一场春雨,满地的梨花堆在屋外,打开窗户,淡淡的香味,和新茶差不多。”草的视角,还是一个隐入尘烟的视角,赵琳以自己的“不见”,换来了众生的“见”:“阳镇的孩子们在雨中洗澡,女人在雨中坐在门槛纳鞋底,男人们在阁楼修缮农具……”
这就是他心心念念的世界,这个世界具体而微,众生平等。这个世界“积攒着充足的氧气和雨水”。赵琳要看顾的是那么多,诗歌的小体量,怎么可能盛得下呢?一个被现代社会的力度和速度所压缩的世界,是可以装进现代诗的,但是,草的世界不能被压缩——这就是他的表意总是从现代诗这个形式容器里面满溢出来的原因,这就是他逃离诗歌马厩、奔向散文草原的原因。
二、长时段事物的召唤:散文的结构
如果要借助一个非文学的领域来帮助我们理解散文写作,特别是散文的结构问题,我大概会选择历史学。
就写作的对象来看,散文写作与历史写作高度相似。年鉴学派认为,历史写作的对象有三种。一是长时段的事物,描述人和自然所构成的环境史,以千年为单位。二是中时段的事物,描述人类群体生活、经济活动与社会变迁,以几百年为单位。三是短时段的事物,描述事件和人物的历史,以几十年到百年为单位。在年鉴学派看来,完整的历史写作需要将三个时段的景观都呈现出来,三个时段的事物的组合,就构成了历史写作的结构。
现代以来的小说和诗歌,处理不了这么庞大的材料。他们死死盯着短时段的事物,尤其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一生,现代诗甚至要把这一生以微分的方式,切割为无数奇迹的瞬间。但散文不一样,散文写作和历史写作一样,对于材料的呈现具有很大的野心。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事物,全部是散文写作的对象。诸子百家的散文,侧重对长时段问题的思考与解答;叙事详尽的历史散文,侧重中時段的朝野变迁;游记小品与人物传记,侧重短时段的个体行踪。散文的对象无所不包。散文的了不起是在这里,散文的麻烦也在这里——材料过多,对象过杂,反而难以结构了。
回过头看赵琳的这篇散文,他为了让自己的文章形成一种结构,颇费了心思。他从长时段所关注的环境史(日月星辰、四季变换)起笔,以中时段所关注的人类群体生活史(阳镇的风土人情)为描述主体,以短时段所关心的人物与事件的历史(洛阳、谢齐的婚恋)为穿针引线的线索,最终收笔,重新回到长时段事物的怀抱:“阳镇的很多事物没有变化,小路上的花草还是原来的种类,雨水也是无比熟悉的味道,大地只有一种声音……”
这个结尾与《活着》的结尾如出一辙:“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大地”,这一最典型的、最稳固的长时段事物,这个不朽的母亲,永远在语言的尽头、文章的尽头,“召唤”着从中国大地生长出来的作家。大地就是中国人的归宿、中国人的彼岸、中国人的安魂曲。在短时段事物(有限性、有死性)中开始,在长时段事物(无限性、不朽性)中结束,这就是包括散文在内的中国文章的结构秘密。
三、无依之地:散文写作的权威性问题
谈到什么是小说,什么是诗,我们虽然各执一词,但总能得出一个结论,说出我们心目中小说的长相,诗的长相。但很奇怪,谈到散文,我们经常无从谈起,谈起了也经常不敢妄下结论。人事变迁是散文,花鸟鱼虫是散文,历史轶事是散文,玄学哲思也是散文。由于涵盖了长、中、短三个时段的材料,散文经常信马由缰,边界很不清晰,似乎生活在一个“无依之地”:一切居无定所的文字,都可以归入散文。
现代分工形成了现代社会纷繁的“技艺”。与其他文学门类相比,散文看上去最没有专业壁垒,也就最不像一门技艺。从传播力和影响力上看,这的确是一部小说占据C位的文学时代。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观园里,散文家也许一直都没有自己的“怡红院”或者“潇湘馆”。当我们谈论当代文学,编写文学史,我们经常忽视散文这种不好把握的文体。这大概就是我所感受到的散文的处境。
身处“无依之地”,这是散文的大自由,也是散文的大苦恼。这个苦恼的核心是:散文写作的权威性在哪里?
首先,历史写作以其严谨的考据术、证伪术与证据法,民俗学、人类学以其深度的田野调查,新闻报道以其准確、客观的事实呈现,确立了在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内容领域的“事实性权威”。其次,小说、戏剧、诗歌等文体,通过想象力以及强修辞性的话语,分瓜了短时段内容的想象主权,一同确立了在短时段领域的“想象性权威”。最后,现代互联网的资讯民主运动,如信息时代的普罗米修斯盗火,将获取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信息以及借助信息下判断的能力,从专家的手中夺回了大众的手中。各个社交平台上漫天纷飞的观点类文章,让散文所能提供的价值性信息大幅贬值,散文仅剩的“价值性权威”也被严重削弱了。
一个文体,如果不能在某一个领域提供一定的权威性,那就像一个国家失去了军事上的威慑力,很快就会被别的写作话语所侵占,丧失它的主权。当这个文体的主权丧失掉,它会继续存在,但会成为一种被强势话语所殖民的文体,一个殖民地。而今天,历史写作、非虚构、报告文学、新闻写作,各种相对强势的话语组成的联军,正在包围散文。
——当然,永远会有人站在另一边,认为这只是自然科学的分类学思维在作怪。我们完全可以无视这些“威胁”,敞开一切文体的边界,不去做伤筋动骨的区分。我们完全可以拆除散文与其他文体之间的高墙,让散文与其他文体流动起来,回到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写作传统。就像赵琳在《阳镇,阳镇》当中做出的尝试——将民俗写作、小说叙事与诗歌的感受力注入散文,让散文继续保持开放、杂糅和无边无际。
这就是今天的散文:焦虑,同时充满乐观主义。
责任编辑 郭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