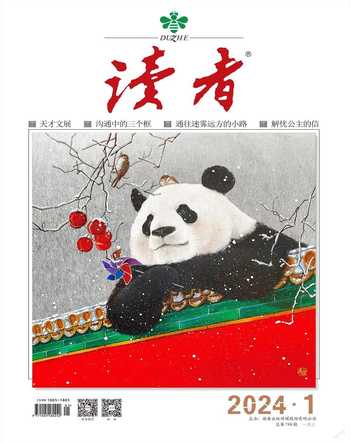月光不是光
2024-01-03陈仓
陈仓

每次回乡,我都会陪我爹睡觉。我不知道除了陪他睡觉,还能为他做点儿什么。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共同的话题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只是老眼瞪着老眼,彼此心事重重地望着对方。陪我爹睡觉,就算最深入的交流了。
回峦庄镇的第一天晚上,陪我爹睡觉时,我爹给我讲了好多话,都是一些家长里短。他说,我叔叔去世后,院子真正地空了,他在空院子里栽了一棵核桃树,不想邻居家反对,硬把树苗给拔掉,他们还吵架了;他说母亲坟前的那块地,我一个表哥想拿去做菜园子,他舍不得,就和我表哥闹翻了。
我爹说什么,我都劝他看开一点儿,这么大年纪了,还计较那些干什么呢?我还举了我叔叔的例子:“他生前与你争来争去,如今他一去世呀,不全是你的了?你哪天去世了,这些也自然就是别人的了。”
第二天晚上,我爹的话少了,他睡得十分踏实,我无论是起床看书,还是外出赏月,弄出再大的动静,都没有干扰到他。他打呼噜时,我是踏实的;如果听不到呼噜声,我就十分担心,担心他没有呼吸,没有生命体征了。我回来之前,峦庄镇是下过很长一段时间秋雨的,这几天正好放晴了,蓝天显得十分空远。此时又恰好是农历八月中旬,正所谓“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我清晰地听见了哗哗的流水声。我抱着我爹的一双脚,看着窗外徐徐升起的明月,心情十分复杂。我爹的脚彻夜冰冷,而月亮也一直是冰冷的,它们在我面前是多么相似啊。天上的月亮宛如我爹的脚,我爹的脚又宛如秋后的月亮。半夜,月亮升到山头时,照得整个小镇如白天一样亮,恍惚中像午夜的城市,街灯仍然没有熄灭一般透明。我悄悄披衣起身,站在三层楼的楼顶,看着寂静的大山,看着缓缓流动的小河,看着洒在庄稼地上的月光。我感觉时光果真停止了,或者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生命存在,只有自然,只有宿命。
我拿出手机与照相机,希望拍下那厚厚的月光,或者月光下的树影,但是,月光就是月光,它与阳光或灯光是彻底不同的。阳光与灯光是可以反射的,这样照相机的成像原理才会生效。但是,月光是拍不出来的,无论我用什么技巧,都是拍不出来的。我突然领悟过来,月光其实不是光,仍然是黑暗,或者说掺进了太多的黑暗,像面粉里掺进了太多的水一样,是烙不出大饼的。月光从窗口照进来,洒在我爹的身上,丝毫没有打扰到我爹,反而已经融入我爹的身体,让我感觉我爹与月光格外相似,甚至他就是一摊凝结的月光。我爹年轻时,充满了活力与生命力,整个人闪耀着火热的光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生命之光里渗入了太多的苦难和黑暗,慢慢就转化成了死亡之光。死亡之光就是月光,同样没有反光,是无法复活与再生的,只能悄然流逝。
山里的秋天,早晚温差十分大,有太阳的时候温度是二十四摄氏度,半夜就降到十多摄氏度了。我爹的肩膀裸露在被子外边,他却浑然不知。在一个人睡觉的日子里,他的冷是没有第二双眼睛发现的。一个人的冷暖,除了自己感知,再不会被第二个人发现,就是说一个人的身边,如果只有自己的眼睛,以及只有审视自己内心的眼睛,那么,这双眼睛一旦闭上,整个世界就为之关闭了。这才是真正的孤独。我替我爹掖了掖被子,尽量让自己的身体靠近他的身体,把他的脚尽量揽进自己的怀里。奇怪,整整一夜,我没有暖热我爹的脚。当然,那轮月亮也是冷的,照样没有一丝反光。
陪我爹睡觉的那几天,我还发现我爹的穿着十分特别,贴身穿的是一件藏蓝色的短袖T恤,上面套着一件方格子的长袖衬衣,再外边是一件黑呢子大衣。夏衣,秋衣,冬衣,我爹的这种混搭穿法,别人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但是,我一眼就看明白了。老婆说:“爹穿的衣服怎么那么眼熟?”我说:“这都是被我淘汰的旧衣服呀。”在上海,每次老婆想扔掉一些旧衣服时,都遭到我的极力反对,我要留着带回家给我爹。但是,老婆说:“爹哪能看得上?应该给他买新的。”有次我爹到上海,我就搜寻出几件旧衣服给了他,那件T恤与那件衬衣,是我穿剩下的名牌服装,那件黑呢子大衣是我岳父的遗物。这三件衣服在我爹的眼里,应该是最好最美的。所以,为了迎接我们,他不顾春夏秋冬,统统裹在身上。
也难怪,他平时穿得再好,对于一个孤独的人,有谁会去欣赏呢?
(檬 男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月光不是光》一书,黄思思图)